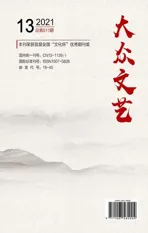平乐镇故事与颜歌风格
2019-01-28喻赛琼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210097
喻赛琼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210097)
80后作家颜歌的《我们家》《平乐镇伤心故事集》等作品均以平乐镇为发展空间,其原型是颜歌家乡四川郫县。作品自问世以来,批评学者多关注于其中的方言写作。阿来在推荐语中说,“方言是一个壳子,一个承载思想的壳子,它提供了一种表达可能,也造成了一种表达的限制,但是颜歌突破了这种限制”。语言固然是故事表现形式的重要构成,但一方文化建立在一方水土之上,平乐镇故事发生在这种四川小镇中,正如徐勇所言,“空间既是故事的主人公置身其间发展演绎其故事的背景,也可以是作者想象与思考世界的方式和角度”。平乐镇不仅承载着独特的地域文化,塑造着性格各异的故事人物,更体现着作者的选择与思维方式。在这里,颜歌坦言:“我对我们的生活生来悲观。我所看见的世界就像十年前从成都回郫县的那条马路,肮脏,无序,混乱,尘土飞扬而令人窒息……我相信这样城乡结合部是我的伊甸园,而我充满喜悦地从这里翻找诗篇。”选择以平乐镇为空间,展现小镇(城乡结合部)的混杂性与敞开性,在缓慢的变化之中思考它的变与不变,川味语言与川味人物以及川味风情一起,熔铸在颜歌的小说中,成为独特的颜歌风格。
一、川味语言与四川风味
在作品中加入方言特色,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早已有之。李劼人《死水微澜》中的四川方言,周立波《山乡巨变》中的湘方言,到贾平凹《秦腔》中的陕西方言以及金宇澄《繁花》中的上海方言。它们增添了文学作品的地方色彩,塑造着带有地域特征的人物形象。
颜歌在《我们家》《平乐镇伤心故事集》中较为熟练地运用了家乡四川郫县的方言。方言的使用不仅止于“婆娘”“瓜皮”“龟儿子”“白脸鸡儿”等方言词汇的呈现,或者是肥肠粉、花椒、海椒、豆瓣酱等带有地方风味的物品的展现,更为重要的是人物形象的刻画。颜歌在访谈中一再否认其创作并非方言写作:“一直以来我都在强调我要做的不是方言写作,而是在中文写作里加入地方化的‘活肉’,让我们用来进行文学书写的中国语言文字更丰富、更有趣。中文和‘方言’不应该是一个二元对立的静止关系,而是一个互相融合、互相丰富的进行中的变化。”诚然,方言不应该与普通话截然对立,作为语言的表现形式的一种,它都是在描述内容、传达思想情感等方面与普通话一样,甚至对于无阅读障碍的读者来说,更多了一分贴切与亲切。
《我们家》中的薛胜强从搅豆瓣到跑销售到做厂长,虽然没有太多文化,却是一个实在的四川汉子。作品将薛胜强肚子里“怪话”与实际表达的话语放在临近位置,较好地刻画了他性情耿直却为人忠厚的特点。以爸爸薛胜强与大伯段知明的交往为例,爸爸在大伯回乡给奶奶准备八十大寿时,看到段知明心里就怪话不断:“段知明你这个白脸鸡儿!说些话比婆娘还阴阳怪气!”“段知明你这鸡儿敢跟老子喝酒,老子不弄翻你我不姓薛!”开口说的却是:“哥这个想法真的不一般,我就想不出来,的确脱俗!”《白马》中的姨妈也是如此。美人迟暮之后凶狠异常,教训自己的女儿是“张晴,你饿死鬼啊!偷啥子嘴嘛!”教训欺负“我”的陈子年是:“所有的人都看见我姨妈立刻像豹子一样腾了起来,当着人家爸的面一把揪起陈子年的耳朵,骂他:‘你这个娃娃不学好!这么小嘴就这么歹毒!啥子叫做没有妈!……我就是她的妈!’”姨妈、姨父以及爸爸之间的纠葛暂且不论,但姨妈对“我”的关心和照顾却是跃然纸上。
像爸爸薛胜强与姨妈这样的带着川味耿直甚至泼辣的人物不胜枚举,他们鲜活地生活在四川小镇,从小离不开火辣的花椒海椒面,自然带有这一地域自己的特色。这样,川味语言与川味人物以及川味风情一起,熔铸在颜歌的小说中,成为颜歌风格的外在形式。
二、走出与回到小镇(“城乡结合部”)
平乐镇这一“城乡结合部”有它的混杂性与敞开性,有它的变与不变。它是作品故事发生的场地,是作品人物活动的范围,更是作者颜歌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从幻想奇幻故事到回归故乡,颜歌经历着走出与回到小镇的历程,并在这一历程中思考着家乡小镇的变与不变。
在作品中建构自己独特熟悉的地域,颜歌承续着这一技法。《我们家》(浙江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的封底上写着这样的宣传语:“鲁迅有鲁镇,沈从文有湘西,福克纳有约克纳帕塔法镇,马尔克斯有马孔多,莫言有高密东北向,颜歌有永安平乐镇。”商业时代需要足够有噱头的宣传,将颜歌与鲁迅、沈从文等人的地域创作并列其公允如何暂且不论,但我们能够看出,颜歌的平乐镇写作已经渐成系列且博得大家关注。《关河》是少时写作的古代奇幻故事,《良辰》中开始出现了故乡的痕迹,《异兽志》中故乡的痕迹逐渐加重,到《五月女王》中,故乡这一熟悉的社会空间已经演化成颜歌的取材空间,成为颜歌“第一步彻头彻尾关于‘平乐镇’的长篇”。到《我们家》与《平乐镇伤心故事集》中,平乐镇正式成为显著的空间标志,甚至出现的文章的标题中。
平乐镇的原型郫县以豆瓣酱而闻名。郫筒镇四条街,一个十字路口,梧桐树还有肥肠粉。西门成长的豆瓣厂青年薛胜强,南门操扁褂的青年子弟,北门办商的外地人,东门的官家子弟,颜歌将镇上的各种各样的人物裹挟进她的作品。这一表现空间的城乡结合部,既有其不变的“乡”的特征,也有其变化的“城”的特点。从其稳固的一面来看,小镇还保留着乡村式的熟络与温情,以及由此而来的家长里短、流言蜚语:十分关心唐宝珍婚事的蒋幺姑、宋二嫂(《江西巷里的唐宝珍》),真心照顾别人家幼女的余婆婆、孙爷爷(《白马》),给奶奶过生日主要考虑排场与邻居看法的段逸兴一家人(《我们家》),等等,这些无一不显示这小镇中存留的古老乡村形态。而开放局面的打开与经济的发展,也有小镇带来不一样的事物:着急下海的周伟、孙正军,关心股票的小秦、朱姐(《奥数班1995》),讲着流利普通话的播音员姑姑和教授大伯(《我们家》),这些特征又显示着现代化的都市气息。在颜歌看似客观的表达中,我们不难观察出其的主观倾向:下海发财的周伟、孙正军面临破产与被捕,热衷于股市的市民在股票暴跌中手足无措(《奥数班1995》);说着普通话的姑姑和大伯与我们家始终有着距离,而吃着肥肠粉、骂着怪话的爸爸确实真正的主心骨(《我们家》);风情万种的唐宝珍在经历人民教师、拆迁办主任等相亲对象后,嫁给了小镇青年、杂货铺老板钟贵峰(《江西巷里的唐宝珍》)。
从少时天马行空的走出小镇,到青年时期的回归小镇,颜歌说:“在二十多岁的时候一直写平乐镇,我想是因为自己总是非常地怀念过去,怀念我和父母一起生活的世界。因此,不管我人在哪里,我总是写过去的小镇,现在想起来是一种心理治疗。归根结底,我只能从自己的趣味和经验出发来写作。写平乐镇是我的一个心结,纠纠缠缠写了快十年。”回到故乡、回到童年固然是许多作家的写作习惯,但选择郫县这样的小镇(“城乡结合部”)则另有深意。
三、小结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传统中,作家们要么在寓所之内以饱含乡愁的笔调书写着回不去的乡土故园,要么直接表现上海、北京等大都会的金迷纸醉,夹杂其中的小镇虽有表现但终不成主流。而放眼当代文坛,在我们熟悉的70后、80后作家中,双雪涛、班宇反复书写的没落东北,徐则臣反复表现的故乡花街与进不去的北京城,这些在当代文坛中较为活跃的年轻面孔将视野从单纯的大都会或乡村转移到没落的城市或小镇,不啻为一种重要转变。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城镇化率显著提高。固然有许多的年轻人闷头往北上广深等大城市奋斗,但也有越来越多的从小镇成长起来的小镇青年重新回归故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