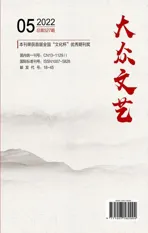深山中的“凝视”
——电影《暴裂无声》权力景观与阶级镜像的展现
2019-01-28辽宁师范大学影视艺术学院116000
(辽宁师范大学影视艺术学院 116000)
忻钰坤在《心迷宫》中通过多层叙述视角的叙事,展现了当下人们精神层面和生活层面的割裂,以及人们窘迫的生活下对自我身份认同的缺失。而在《暴裂无声》更延续了缺失这一主题,将一个失语的小人物混搅在所谓的中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透过小人物所谓的挣扎与反抗,去揭示话语意识、权力景观与阶级镜像。
法国思想家福柯将话语放在非常重要的位上,在福柯分理论中话语与权力是密切相关的。权力给予话语以荣誉和威力,话语是权利的象征。话语是权力化的话语,而话语实践本身是实施权力的工具和过程。人们在对话语顺从的同时也会通过各种手段对话语进行反抗与颠覆,这也是对权力的抗争。在影片《暴裂无声》中,正是展现了这种顺从与反抗,并以此召唤出现实的真相。
一、话语场中权力的顺从与抗衡
福柯在《话语秩序》中表述“不存在和知识构成无关的权力关系,同时也不存在与假设权力关系存在并与其构成无关的知识”,换言之“话语即权利”或“权力即话语”。权力作为话语的运作机能,在话语场中存在着流动性和不稳定性的特征,随之就产生了权力的顺从与流动。
忻钰坤的两部电影,都致力于探寻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对话语的顺从与抗衡。“说话”意味着展现自己的内心,更意味着表达自己的诉求。而电影通过对“哑巴”张宝民、律师徐文杰以及煤矿老板昌万年的说与不说,将不同阶层在话语场中对话语与权力的顺从与抗衡进行了深刻的揭示。
影片的叙述线索是张宝民找儿子,也是寻找自身话语权利的过程。生活在偏远地区的张宝民,因为不愿签署土地征用协议书而与其他想拿到补助的村民起了冲突,打斗过程中不慎将丁海的左眼戳瞎,无奈之下签署了协议书并远赴奉县挖煤赚取医疗费用赔偿丁海。在这场同一阶层的话语权博弈中,“哑巴”张宝民并没有说话的权力,他想与权力的反抗,却也无疾而终。
话语是一种具有社会性的行为,张宝民、徐文杰与昌万年所发出的话语正是代表了三个不同阶级,每一种话语都服务于一种意识,都是一种权利的运作。
张宝民处于社会最低阶层,也是社会话语场的最外围。在社会中,他更多的是一个权力的失语者。但是没有话语权并不代表着对当下权力的永远顺从,影片中的他,自始至终都在用最微弱的言语—肢体语言进行反抗,他不停的与他人打架,来表示自己的不满。正是因为他话语的缺失,所以他只能通过不断地通过暴力行为表现自己对权力场的反抗。虽然在社会的话语场中他是一个没有话语权的“哑巴”,但回到家中他却占据着话语场的中心位置:妻子对他的话说一不二,岳母也只敢在他不在家的时候偷偷地对小琴抱怨他是个“愣头”,至于儿子他更是权威的象征,否则也不会出现儿子为保护羊而被错杀的惨状。
昌万年,是电影中的绝对权力者,他占据的权力话语场的最中心的位置,处在话语场外围的底层阶级以及依附于他的中产阶级都只能成为他权力下的顺从者。所以影片中展现的昌万年看似朴素,但其说出的每个字每句话,都有着不容置疑的资本和权力。张宝民的原始冲撞抑或是徐文杰的中产阶级的反抗,对昌万年的权力都构不成较大的威胁,最多的只不过引发其内心的一丝波澜。
徐文杰作为一个典型中产阶级的代表,他的职业使得他的话语更多的是象征着国家的权力和法律的尊严。他原本在工作中有着相对稳定的话语权,这个话语权不仅仅是国家法律赋予他的权力,更有凭借自身的努力而在事务所中占据的中心位置。但当他选择站在国家法律对立面时,原本国家赋予它的权力便与他背道而驰,与此同时自己努力争取来的权力也因为其错误的选择而丧失。面对昌万年时,他亦是一个权力的“失语者”,他在昌万年巨额资金的利诱下,对昌万年所代表的资产阶级进行攀附。因为选择了依附,其只有在资产阶级“话语”下顺从的本分,却没有当面反抗资产阶级的资本。此刻,他仅仅是站在权力话语边缘的人,其一举一动都受到资产阶级的驱使,纵使拼尽全力做出反抗,也不过在资产阶级的权力场中揭起一丝丝的涟漪。
巴赫金曾说过,语言是人类基本生存方式,一个人的言行举止一定会带有着某种观点或者是价值表达。而忻钰坤通过不同阶级的人的话语与权力,将人与人之间,人与阶层之间、阶层与阶层之间的种种复杂关系关联起来,形成一个话语场,抑或是一个权力场,不同阶级在“场”中所能够发言的机会,则代表了他们在这个话语场中的权力。
二、“缺失”与“反抗”构成的权力景观
忻钰坤将叙事视域聚焦到“人的言语及其身体语言”上,透过人物不同的语言将故事架构起来,从而揭示偏远地区的社会现状,更展示了一幅不同阶级的权力景观。影片中出现的不同群体的话语受到主体声音的制约,但最终聚集到“权利场”中,并不断进行着博弈。如果说《心迷宫》中讲述的是父亲如何用权力及话语帮助儿子掩盖罪行,体现出官场景观的冰山一角,那么《暴裂无声》则是将“阶级”“权力”“失语”等关键问题鲜明的展现在权力场之中。影片中的“哑巴”张宝民,更是处于权力金字塔的最低端,他在被权力所奴役的过程中,也起着搅动和反转权力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导演旨在通过处于权力金字塔底层的“失语”人群的生存视角去结构当下社会体制、以及资本驱使下的权力怪相。
《暴裂无声》讲述了三个人或者是三个阶层的图景:偏远山区的张宝民、中产阶级律师徐文杰以及资产阶级煤矿公司董事长昌万年各自为各自的权力奔波。他们分属不同阶层,本应没有直接的瓜葛,但他们之间却因为孩子汇聚到一个共同的权力场,呈现了不同阶层的人物的完整镜像与反叛。
首先,影片的开始便交代出悬念,张宝民的儿子磊子丢了。张宝民在找儿子的过程中,回忆起与村民的一系列冲突展现出的不仅仅是张宝民的“失语”,更是村民们抑或说整个阶层的选择性“失语”。面对自己要失去的赖以为生的土地,表面上除了张宝民其他人是主动签署土地征收协议但其实都是一种无奈之举,一种对生活,对上层阶级的妥协。他们唯一的反抗途径就是影响十分微弱的肢体语言,他们在权力的“失语”与身体的反抗中构建出底层人物生活的无奈。
随着剧情的推进,徐文杰的女儿被昌万年的手下绑架。徐文杰作为一名律师,他的话语不仅仅是自己权利的体现,更是国家权利的代表。但是这种权利却在自我的利益的选择以及昌万年这个资本主义的胁迫中丧失了原本的主动性,成为上层利益的帮凶与附庸。徐文杰利用法律的漏洞帮助昌万年逃避法律责任,这也是造成整个悲剧故事的源头。他包庇昌万年的违法行为,是导致张磊死亡的诱因。选择昌万年的徐文杰,他通过自己的话语,帮昌万年逃脱了刑事责任,但也在资本的驱使下丧失了话语权,更使法律的权威得到了亵渎。徐文杰在体会过失去女儿的痛苦后,依旧对张宝民儿子的隐藏之地保持失语状态,展现出的人性的自私、冷漠与卑劣,通过徐文杰话语的“得到”与“缺失”,展现出中产阶级在社会盲目追求经济发展的状况下的畸形状态。但徐文杰对昌万年也有反抗,他的反抗更多的是利用自身的话语,他将昌万年的犯罪证据进行了整理与备份。他在权力场的边缘,使用自身的权利对昌万年为代表的资产阶级进行了反抗。在话语的“缺失”与“反抗”中,我们可以看到中产阶级的权利景观在利益驱使中的畸形与委曲求全。
昌万年作为影片中权力金字塔的顶级人物,他的话语在影片中是不容置疑的,他去小学捐赠校区时王校长对他的百依百顺,大金对他的唯唯诺诺,甚至是李总被迫将公司送给昌万年等等,影片中的所有的影像符码,昌万年都是一个发号施令的权力者,但是在面对张宝民找儿子过程中的挑衅,昌万年始终保持一种“失语”和忍耐的状态,但这种沉默却不是权力的丧失,而是更好维护自身权利的一种方式。
影片的结局,徐文杰与昌万年受到了法律的制裁,但是张宝民却依旧找不到自己儿子的尸体,他依旧是被压迫在最底层的“失语”阶级,却又只能被迫接受。这也是当下为经济发展而被牺牲了的那一部分底层人民的真实写照。
三、阶级镜像与权力依附在影像符码中的呈现
在《暴裂无声》中,导演在对人物进行塑造的同时,也对阶级镜像进行了呈现。其没有在情节中进行直截了当的交代,而是通过具有意味性的影响符码对电影的叙事进行了升华。
张宝民、徐文杰以及昌万年都是具有隐喻性的符码,三个人分属三个不同的社会阶级,其举止行为也代表了三个阶级的不同现状与心理。昌万年,是出于金字塔上层的成功商人,他仿佛是食物链的顶级支配者,所以吞噬和猎杀对于他来说理所当然。而底层人物张宝民和他的妻子以及儿子,却没有捍卫自己权利的能力,甚至连基本说话的权力都被剥夺。他们像绵羊一样,没有丝毫的攻击力却不断的被别人剥削、伤害。村里的人如张宝民一样,都是被剥削、迫害的对象,当矿产被无限的开发,昌万年这种所谓的顶尖人士会成为此次事件中的最大获利者,而村民只能默默接受其所带来的水源污染、土地塌陷、种植土地消失以及亲人患病等等现实,他们既没有办法逃离,也不能维护自身的权利,甚至是一直被蒙蔽在真相之外。作为一个积极反抗的异类,他凭借着原始的蛮荒力量横冲直撞,却也是没有目的的横冲直撞,其只能成为切肉机中的短暂卡住切肉机继续运行的一根小骨头,对资产阶级的所作所为产生不了丝毫影响。但是当昌万年的手下追打张宝民时,曾被张宝民刺瞎左眼的丁海却帮张宝民躲过了追打,这展现着底层人之间的惺惺相惜。但与此同时,同为底层人的村长,却想尽办法取悦昌万年,希望能借助昌万年的权力,使自己脱离底层阶级。村长、张宝民以及丁海仅仅是社会底层阶级的一个缩影,在相互帮助之间却又充满着矛盾,对权力渴望的同时又出于本能的对权力进行反抗。
徐文杰,作为一个中产阶级的代表,其工作性质本应该使其成为人类良知的捍卫者,但他却在自我利益以及上层阶级的压迫下,成为上层阶级的附庸品和帮凶。当张宝民帮助徐文杰找到女儿时,徐文杰凝视着山洞,仿佛在凝视着自己的内心与良知,但是他却选择了逃避,在拯救自己女儿的恩人与绑架自己女儿的仇人之间,选择了权力的一方。徐文杰不仅仅是一个个案,他代表的是中产阶级一种典型,他选择攀附权力与自身保护,在张宝民、徐文杰与昌万年在后山打斗的过程中,在他们俩在监狱受审的过程中,徐文杰将中产阶级在经济浪潮中的心理扭曲以及对权力的攀附展现的淋漓尽致。
张宝民、徐文杰与昌万年,导演通过这三个人展现出三种阶级的现实图景,表现了他对现实问题的审视,更将当下的阶级镜像以及权力攀附问题的血淋淋的呈现。伊芙特·皮洛曾说:“我们应当在符号中发现可见形象之外的超出直接感觉的意义,这是只能通过间接方式去理解的意义。”忻钰坤通过一系列的符码,展现了当下身处不同阶级的人们的生活图景以及那种在经济浪潮下被积压的已经畸形的为攀附权力而不顾一切的现实状况。
影片的结尾,虽然昌万年和徐文杰都受到了法律的制裁,但是张磊的尸体却依旧无处可寻。那座类似金字塔的山被炸了,但是又形成了一个新的金字塔,又形成了一个新的权力场。对于张宝民这种依旧处于底层阶级的人民来说,生活的麻木以及荒诞依旧在有条不紊的上演,并不断掩饰着遗失在现实中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