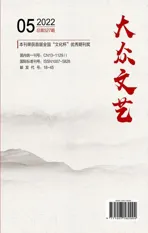乐亦有道
——探析神经喜剧的发展
2019-01-28辽宁大学110000
(辽宁大学 110000)
随着《夏洛特烦恼》、《西虹市首富》等开心麻花系列电影在国内市场的走红,喜剧电影开始越来越多的受到关注,然而其内容形式在学术界总不免被打上娱乐化的标签。如何在日趋类型化的喜剧电影中挖掘、传递大众社会文化意识,是当代电影研究者值得探讨的命题。神经喜剧片作为古典好莱坞时期盛行一时的喜剧类型电影,在机智对白、两性对抗的喜剧模式下表现了一定的大众文化形态、阐述了性别意识,并在上个世纪由弗兰克·卡普拉、霍华德·霍克斯及乔治·库克等极富创造力的导演探索成熟。研究神经喜剧片的叙事策略以及发展历程对当代我国喜剧的发展显然具有重要意义。
类型电影研究专家托马斯·沙茨认为“一种电影类型同时是一个静态又是一个动态系统。一方面,这是一个关联到叙事和电影成分熟悉的程式,其目的在于不断地重新考察一些基本的文化冲突……另一方面,文化态度的变化,新的有影响力的类型电影、工业的经济情况等,持续地改进着任何一种电影类型。”1,神经喜剧片显然也具备一个静态系统、一个动态系统,将这两个系统做理论上的分开论述将有利于我们从历史的角度纵向以及电影本体的角度横向认识神经剧片。此外,神经喜剧片的消亡——或者更准确地称为衰退,对于整个电影史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只有将其弄清楚了,才能更好地认识神经喜剧片的发展动力、了解喜剧应当如何发展。
一、神经喜剧片的静态系统
“神经喜剧”一词最早来源于电影杂志《综艺》对于卡洛·郎白在《我的高德弗里》(《My Man Godfrey》)中表演的评论,其后,在1939年出版的《美国电影的崛起》中被正式命名为一种电影类型。2但这种命名并非没有争议,1959年乔治·萨杜尔在《世界电影史》当中就将其称呼为轻松喜剧,此外,对于神经喜剧与浪漫喜剧的界限学界也存在诸多论争。也许用电影人物自己的语言能够更好地给这个类型的电影贴标签。卡普拉导演的《迪兹先生进城》(《Mr.Deeds Goes to Town》)当中,角色法尔克姐妹对主人公的评价“他有些疯疯癫癫的”“永远也摸不准他到底想干什么”,霍克斯的《女友礼拜五》(《His Girl Friday》)当中女主的未婚夫也对女主有过类似的评价“她和其他所有人都不一样,你永远也不知道她下一刻想做什么”,由此可见电影创作者在创作伊始就有意地将神经喜剧片的主角塑造成“让人摸不准的”“神经兮兮的”人物形象,这也就使得这种人物形象成为神经喜剧片的标志特点之一。
除了形象标志以外,托马斯·沙茨还指出类型电影有着特定的类型图像。不同的类型电影的图像志代表着不同的意义。尽管托马斯·沙茨认为神经喜剧片所代表的是不确定的空间,没有一定之规的场景图像,但奢侈装修的建筑与乡村朴素的住所对比出来的场景印象已经成为一种非具体的影像标志进入了观众的头脑。当观众在《一夜风流》(《It Happened One Night》)中看到破败的乡村景观以及阔绰的邮轮豪宅,在《休假日》(《Holiday》)当中看到温馨的小公寓以及装有电梯的奢侈房间,在《史密斯先生到华盛顿》(《Mr.Smith Goes to Washington》)中看到史密斯拥挤的小房间以及纽约高大的建筑、白宫豪华的装饰,心中自然会将其对号入座至神经喜剧片的类型图像,这种心理机制不亚于看到荒原和牛仔打扮时对西部片的联想。
罗伯特·麦基在他的《故事》中指出喜剧次类型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喜剧攻击的焦点和嘲讽的程度上。3“喜剧攻击的焦点”在神经喜剧当中表现为乡村—城市的阶级文化冲突,这种冲突常寓于性别冲突中表现,最后又经常通过两性情感的和解来化解。神经喜剧片的开山之作《一夜风流》首创了这种模式,来自乡村阶级的男记者看不起城市阶层的富家小姐,在一段传奇式旅程之后,两人之间的差异因情感上的契合而消失,这直接影响到之后的《罗马假日》(《Roman Holiday》)等作品,但这种偷换概念解决冲突的方式常被电影研究者诟病。对于大众来说过于意识形态的东西难以理解消化,而两性关系则是可以普遍接受的,基于神经喜剧片通俗的电影定位,不难理解其叙事模式选择的缘由。
在神经喜剧的静态系统中内在的文化冲突是最根本的,它成为神经喜剧片演变过程中不断被重新回答的问题。
二、神经喜剧片的动态系统
与其说一个类型片的动态系统是影响着类型片的发展的,不如说所有的类型片都是处于被整个动态系统影响的范畴,因为社会文化态度、工业发展情况、重要类型电影的影响等等都是整个社会文化系统当中的,而类型电影所表现的文化冲突只是隶属于社会文化系统的一部分。当然,对不同的文化冲突,处于各个位置当中的社会文化形态起着不同的作用。
工业发展情况对于神经喜剧片起着间接、客观、根本性的作用。神经喜剧片是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由弗兰克·卡普拉导演的《一夜风流》开启的,其成功的原因部分在于其对该时期的阶级对立现状的嘲讽。卡普拉以市民阶层的立场维护了现有的文化状况,给了当时物质上不充裕的广大市民群众心理安慰。虽然其衰退的具体标志不详,但得到广泛认可的是,自二战爆发,神经喜剧片在电影市场上的霸主地位就明显让步。加上美国经济的恢复,减小了神经喜剧给观众带来的心理需求。
尽管神经喜剧片盛行时期仅仅在19世纪30、40年代,但在这短短的二十年时间当中,人们对于城市—乡村的文化冲突的态度变化也比较明显,这种变化表现在各个时期的电影对该文化冲突的解决方式当中。早期的《一夜风流》和《迪兹先生进城》是以乡村男性对城市女性的征服来表现文化融合、解决文化冲突。到了三十年代末期的《休假日》则表现出对不可调和的文化冲突的转移,在该片中来自乡村的男主角并没有将原来的城市女性征服、驯化,而是赢得了另一位身处城市文化但向往乡村文化的女性的爱情,这部电影承认了城市—乡村文化冲突的不可调和,并试图通过巧妙的情感情节设置转移对这一文化冲突的解决。到了四十年代的《女友礼拜五》则完全否认了这种冲突解决的可能性,被城市生活包围的女性主人公找了一位乡下的未婚夫,试图通过和他结婚回到“自然”的乡村状态,但最后在前夫的设计下又回归了城市忙碌的生活状态,这完全背离了卡普拉在《一夜风流》中开创的平民主义风格,电影虽然探讨的是人物对自身属性的认识,但其中对城市忙碌生活的重新赋魅使得电影回归了在《一夜风流》之前的城市阶层观点。与之相反的是,作为神经喜剧片的创始人卡普拉,他一直坚持着他自己朴素的平民主义,这到四十年代中后期的《生活多美好》也都没有改变。
卡普拉电影表现的文化意识是他可作为电影作者讨论的要素,同时其叙事策略流变的过程对研究神经喜剧片叙事策略的发展也有可参考之处。在《一夜风流》当中,男女两性的冲突即文化冲突对立的双方,两方的和解直接被表现为阶级冲突的和解。而《迪兹先生进城》、《史密斯先生到华盛顿》、《约翰·多伊》(《Meet John Doe》)这三部曲当中,男女两性的冲突已经不是主要冲突了,女性最后都会被男性的文化特征吸引征服,从而帮助男性在阶级冲突中赢得胜利。到了《生活多美好》(《It’s a Wonderful Life》),乡村—城市的对立并没有得到明确的解决,而是在一个情绪激昂的高潮中结束了叙事,女性成为了全剧的情感副线,由“天使”引导男性主人公找到了自我合理——坚定了自身行为正当且合理的信念。这三个阶段当中,都出现了慈祥高大的“父亲形象”,在《一夜风流》中表现为女性的贵族父亲,《迪兹先生进城》和《史密斯先生到华盛顿》中是公正、体察民情的法官和议会主席,《生活多美好》中则是上帝,这些形象是电影主要人物行动是否成功的重要因素。假如没有公正的法官或者议会主席,那判断主人公是否“正义"的主要人物就会缺席,而主人公行动是否能成功也得加上问号。甚至在《生活多美好》当中,没有了上帝,主人公就会直接失去生命。这些设置是现实中最不可捉摸的不确定存在,因此这些都成为了对卡普拉电影过于理想主义评价的要点,这也是悲观主义者对卡普拉信念怀疑、乐观主义者对卡普拉信念追逐的原因。
卡普拉这种巧妙转变冲突双方以适应自己文化态度变化的叙事策略是发展类型化电影必备的技能。库克的《休假日》在卡普拉的《一夜风流》和《迪兹先生进城》之后诞生,其中避开冲突双方而引进第三方回避冲突的手法未尝不能说是卡普拉给的灵感。
三、神经喜剧片衰退的原因
沙茨认为类型的持续成功主要依赖于主题诉求以及对待文化冲突态度上的灵活性。4琳达·威廉姆斯则认为“类型的成功,常常是根据观众对于银幕上看到的东西的动情模仿程度来测量的”5。在探析神经喜剧片的衰退历程时,我们不难发现这三个因素对其造成的重要影响。
主题诉求的减小是神经喜剧片衰退的主要原因。经济的恢复,使得神经喜剧片在经济大萧条时期对观众的安慰性优势荡然无存。神经喜剧片文化冲突解决方式的多样性也使得阶级和解的趋向愈来愈不光明:库克、霍克斯等电影创作者对乡村—城市文化的融合并不乐观,这种消极的认识使得观众兴味索然。另外,外部环境(二战)对观众的注意力也有相当的转移。观众对国际热点问题的关注使得神经喜剧片当中两性冲突的问题流于轻浮,明星服役的大规模转移,也降低了神经喜剧片中明星的影响力,这些内外因素共同造成了神经喜剧片主题诉求的下滑。
神经喜剧片对待文化冲突态度的灵活性在其后续的发展中面临了一个显而易见的瓶颈以及流变。卡普拉的《生活多美好》几乎跳脱了神经喜剧的范畴;“霍克斯的《妙药春情》(《Monkey Business》)以及《我是个男性战时新娘》(《I Was a Male War Bride》)没有发展神经喜剧的主题,而是预见了电视里刚刚萌芽的情景喜剧。”这种流变引发的是其他喜剧的发展而不是神经喜剧的主题延伸,使得神经喜剧片发展后续乏力,但这种流变对于整个电影史来说,不能完全被称为一种遗憾。尽管20世纪下半叶,有部分在神经喜剧片鼎盛时期产生过巨大影响力的导演试图复兴神经喜剧,但明显有心无力。卡普拉和霍克斯两位导演只是重拍其早年的作品,而新兴导演的成功作品也极少,明显呈现出对待文化主题态度的创新与后劲不足。
至于动情模仿程度,神经喜剧片不同于其他情节片,它依靠机智快速的对白、承袭莫里哀以来的“闹剧”的动作元素博取观众眼球,这些元素让神经喜剧片具有难以“模仿”的特征,同时主人公乖僻的性格也很难同大众取得共情。在情节剧当中,女性总是担任打动人的事物,神经喜剧片中叛逆而又充满理想主义光辉的爱莉(克劳戴·考尓白饰),处于腐朽奢侈阶层但仍具童心的琳达(凯瑟琳·赫本饰),内心藏着对美好事物的向往而又机智聪慧的Clarissa Saunders(乔恩·亚瑟饰)都或成就或增持了一个个女性明星。但到了20世纪下半叶,打动观众的女性塑造也因为不易突破的“疯疯癫癫”的性格而逐渐陈腐,这在很大一个程度上减小了观众的动情可能性。喜剧本来的特质、女性角色魅力的流失都让神经喜剧片的动情模仿程度始终保持在很低的水平,其持续的成功也就失去了一大助力。
四、小结
开心麻花系列影片所走的类型化道路和神经喜剧片一样主要以两性和解作为冲突解决方式为主,但在叙事节奏上、解决方式的灵活性上、以及传达的社会文化意义上的深入把握与真切传达还远远比不上神经喜剧这一好莱坞古典喜剧,除了在形式上学习其,从其衰退的原因中吸取教训,更重要的是把握住神经喜剧在电影传达中表现出来的社会文化意识,将其运用在自己的喜剧发展当中。正如乔治·萨杜尔所说“笑本身就是对专制暴君进行斗争的一个合法手段”6,这才是喜剧电影的意义所在。国内喜剧电影应该摆脱娱乐化标签,让乐亦有道,让通俗大众的国产喜剧电影也成为一门艺术。
注释:
1.托马斯·沙茨,好莱坞类型电影[M].冯欣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24.
2.沈文烨.笑声中的颠覆:美国神经喜剧研究[D].中国艺术研究院,2017(5).
3.罗伯特·麦基,故事[M].周铁东,译.天基: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89.
4.托马斯·沙茨 ,好莱坞类型电影[M].冯欣,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37.
5.琳达·威廉姆斯.电影身体:性别、类型与滥用[G].范倍译//杨远婴主编.电影理论读本.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339.
6.乔治·萨杜尔,世界电影史(上)[M].徐昭胡承伟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5:3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