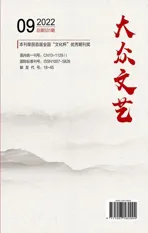“边缘人”身份对谢灵运诗歌创作的影响
2019-01-28江南大学人文学院214000
(江南大学人文学院 214000)
“边缘人”这一概念最早由德国心理学家库尔特·勒温提出,它泛指对两个社会群体参与都不完全,介于群体之间,找不到认可感和归属感的人,他们多出现于时代变革之际,无法割裂从前的身份和习惯,也无法适应新的环境和要求,因而在心理行为上表现出紧张、失落和特立、反叛的属性。
谢灵运就是一个典型的“边缘人”代表,他生于东晋末期,是著名的谢家后裔,出生时正迎来家族“诸谢皆富贵,轰隐交路”的鼎盛时代,但随着先祖的逝去,灵运尚未充分享受谢氏大家的福泽荫蔽,便被迫卷入了群雄混战、风云际幻的时代浪潮,之后辗转多主,却再没回到旧时的风光与荣耀。从命运的“宠儿”到天地的“客儿”,“边缘人”身份带来的焦虑、紧张与彷徨,最直接地作用在谢灵运的文学创作之中,并对其作品产生了一系列复杂、显著的影响。
一、摇荡无寄,故而山水——对诗歌题材的影响
谢灵运15岁便继承祖父爵位袭封康乐公,21岁任琅琊王大司马参军,极高的出身和起点造就了他自视甚高、不甘平凡的心性,但在诸雄混战的时代面前,缺少政治眼光的灵运始终没有得到平步青云的机会,27岁离开跟随五年身败权落的刘毅后,谢灵运版至刘裕的太尉参军,随后几番辗转,均未得重用,直至刘裕改朝降爵之际,灵运以一封明为感恩、实为泄愤的《谢封康乐侯表》,彻底断送了他在新朝廷的仕途,坐实了“边缘人”的身份。422年,谢灵运出为永嘉太守,自此开始了边远地区的外放生涯。
谢灵运的山水诗主要创作于永嘉、始宁和临川三个外放之地。之所以出现这样题材的创作转向,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被“边缘化”的现实际遇,使他有机会得以纵览自然山水,有感而发,即《文心雕龙》所说的“感物吟志,莫非自然”。在前往永嘉的路上,谢灵运创作了《过始宁墅》、《富春渚》、《七里濑》等诗,表达自己“资此永幽期”“将穷山海迹”的目标;永嘉任职期间,又先后写作了《登永嘉绿嶂山》《游岭门山》《横阳诸山》等16首山水诗作,山水题材占这一时期总创作量的三分之二;临川时期,也有《登庐山绝顶望诸桥》《题落峭石》等山水作品,所有景观均来自他外放期间的所见。长久挣扎于政治边缘的痛苦,使得谢灵运在外放之后彻底显示出放弃融入新权团体的超脱姿态,转而将视线和心灵放诸于山水之上,可以说正是“边缘人”的离群,才使得大量的自然风物有机会涌入灵运的审美视野,成为他文思的源泉与创作的材料。
创作题材转向山水的另一原因,在于山水大川不仅作用于谢灵运的感官,还进一步作用于他的心灵,成为他“边缘人”身份极好的精神慰藉。公元423年,灵运在写于永嘉的《述祖德》中言:“高揖七州外,拂衣五湖里……遗情舍尘雾,贞观秋壑美”借歌颂先祖的卓越功绩与淡泊志趣,表达自己身为谢家人的骄傲和效仿他们归隐的决心。作为“边缘人”,灵运最深的焦虑来自于对归属感的缺乏,尤其在经历外放之后,新的生活环境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他平庸无为的事实。既无法融入新的权力团体,又无法返回谢门的往昔尊耀,山水,在此时便成为一条最可行的心灵逃逸路径。写谢家祖宅的《过始宁墅》,有“岩峭岭稠叠,洲萦渚连绵……挥手告乡曲,三载期归旋”,借对故乡河川的歌咏,给徘徊无依的心灵重归旧地的许诺,借此完成对“边缘身份”的短暂逃离,制造出一种坐拥名士身份的自我想象。
事实上,通过山水题材的创作,谢灵运确实得到了“每有一诗至都邑,贵贱莫不竞写……远近钦慕,名动京师”的认可,找到了他所期望的那份自尊感。正如白居易《读谢灵运诗》中所说“谢公才廓落,与世不相遇。泄为山水诗,逸韵谐奇趣”,原本用来否认“边缘感”的山水创作,最终在文学的世界中成就了谢灵运名垂千古的不朽之心。
二、山水涤情,仕隐两难——对情感取向的影响
谢灵运在创作题材上转向山水,说到底并不是基于个人审美思考所作出的主动选择,而是为了对抗“边缘人”身份带来的脱离团体的孤独感与焦虑感被迫作出的妥协,所谓的放诸山水,实际上也只不过是他面对灰暗现实的倦怠与让步,他的心中始终将传统儒家士大夫建功济世的理想放在第一顺位,诗歌中显示出的对待山水与朝堂的模糊态度,多半也是他求而不得的自我解嘲。
谢诗情感的矛盾性从表层来看是庙堂与山水之间选择的矛盾,从深层来看是标榜清高和渴望理解之间的矛盾。公元426年,权臣徐羡之、傅亮被宋文帝刘义隆斩杀,新皇为笼络贵族、装点门庭,征灵运为秘书监。灵运初诏不就,后在好友写信敦请的情况下入京出仕,虽因不满修书文职很快就讽旨自解了,但在此次二仕为官之前,谢灵运已经在众多的山水诗中显示出自己决意归隐、不问世事的志向,如今做出这样言行不一的举动,其“进退出入”的矛盾心理,可见一斑。
乡人孔淳之曾评价谢灵运“希心高远”“志在轩冕”,高门出身的背景决定了他“身在江海,心存魏阙”的潜在心理,但褊急敏感的性格和自视甚高的期许,又注定了他在复杂诡谲的政治权谋中难以成功。展志不得,又不甘落寞,这份仕与隐的矛盾,究底还是来自于“边缘人”身份对寄托之所从属不清的混乱结果。纵观灵运的一生,几番辗转进退,却始终不得重用,这种渴望认同而不得的失落,最后直接发展成他诗中自我标榜的矛盾,《东山望海》中有“非徒不弥忘,览物情弥遒。萱苏始无慰,寂寞终可求”的剖白,《斋中读书》中有“昔余游京华,未尝废丘壑。矧乃归山川,心迹双寂寞”的不甘,试问一位一心隐匿的山水诗人,怎会在书写淡泊和自然之外,不断地发出知音难觅的孤寂之声?谢灵运诗歌中频频出现这些的矛盾取向,正是他“边缘人”身份的情感外现。
三、显隐之间,繁复曲折——对艺术形式的影响
钟嵘《诗品》评灵运诗说:“才高词盛,富艳难踪……颇以繁芜为累”,才盛繁冗,正是“边缘”身份在谢诗形式上的影响所在。
豪族出身的精英身份和山水隐匿的被迫选择,使得谢灵运在创作时既想显露自我的才华,又想标榜超脱的志趣,造成了诗歌在辞采、意象和典故的选取上,虽精巧深奥却用力显著,不厌其烦的洗炼和铺陈字句,常使读者颇感负累。以《石门新营所住,四面高山、回溪、石獭、茂林、修竹》为例,“嫋嫋秋风过,萋萋春草繁。美人游不还,佳期何由敦”短短两联就化用了《九歌·湘夫人》“嫋嫋兮秋风”、《楚辞·招隐士》“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楚辞·少司命》“望美人兮未来”和《九歌·湘夫人》“与佳期兮夕张”四个句典,如此连篇累记,颇有炫才之嫌。
叶嘉莹在《汉魏六朝诗讲录》中评价谢灵运的山水诗,说到它“也谈哲理,也写感情,但山水是山水,哲理归哲理,感情是感情。”解释其原因,是因为“他的心中充满了矛盾和挣扎,远远没有达到陶渊明那种融会贯通的境界。”贵族出身的谢灵运,不管仕途现实多么的不如意,对真正的江湖生活在潜意识里始终是排斥的,《斋中读书》说“执戟亦以疲,耕稼岂云乐”,“边缘人”身份虽然赋予了谢诗“大必笼天海,细不遗草树”的细致与巧思,却始终无法帮助他找到真正的依托与归宿,这种寻觅的焦虑反映在作品上,自然雕琢、曲折之感多,自然、圆融之感少。
毫无疑问,“边缘人”身份给谢灵运的人生和心灵带来了深切的痛苦与焦虑,为了摆脱这种煎熬,他在精神世界和文学创作中做出了各种努力:题材上大范围转向山水的诗歌,在开辟新题材的同时为后世仕途失意的士大夫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心灵假栖息之所;情感上取舍两难的矛盾,唤起了后人对人生归属的思索与共鸣;艺术形式上有意识地斧凿和显才,侧面推进了诗歌形式的成熟与发展,可以说,也正是“边缘人”的身份赋予了谢诗独特的风貌与深刻的内涵,成就了谢灵运在文学上的传奇与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