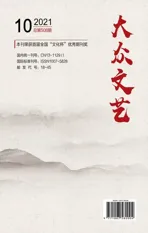朱利安对中国绘画内涵“民主协同性”法则的解蔽
2019-01-28成都大学610106
(成都大学 610106)
视觉优先于听、嗅、味、触等感官系统,在西方传统绘画中体现尤为明显。因过度推崇视觉,同时又受制于欧洲大陆理性传统规约,由此使得西方绘画朝几何图像、抽象化、固定化知觉客体方向发展。“视觉中心”(线性透视)和“逻各斯中心”合谋使得画面景象显得静止单一。“阿尔伯蒂的透视法意味着从单一中心出发,在视觉金字塔尖构建整个视觉,随后产生对灭点以及地平线的几何学规定,那么,这种要求显然与郭熙所讲的多重视角(高远、深远、平远之‘三远论’)统统相抵牾”1。
“视觉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极端后果在于将整体风景区隔成单一画面(“观者”的主体性边界):一边是摆在眼前被打量的知觉测量客体,另一边是主体眼光的“真假”巡查。“视觉如是地走在‘本质性’路上,就是识别‘这是什么’或识别‘物质性’;但是它失去了蕴含的氛围”2。
一、多感官之间的民主协同,而非“视觉中心主义”逻辑判断
中国画没有陷入西式“视觉中心主义”的逻辑统摄。除了眼睛,中国画会考虑其他感官缺席者的在场性问题,以此摆脱视觉单一性的贫乏及固有的专注性可能带来的封闭性弊病,“摆脱它消失于其中固执的无谓重复,从而通过它提供通向事物深度的入口。”3在目光游动过程中,神思遐想会展开丰富的精神活动。于是,画家所思、所想的内在景象会自由率性分配到笔下山水峰峦、花草树木、烟云雾气等元素上。眼睛“所见某景”被转换到“从什么到什么”之景象神思妙想上来。不固恋、不执着于某一点。而是在多元景物之间来来往往。
中国画并没有滞步于视觉思维,也没有立足于柏拉图“理式”,并非要将绘画描绘为对理念光芒的媒介分享——因占据而将自身抬升到理念美(普洛丁)的统摄位置,或对理式美、善进行绘制再现——或从“经验上凭借眼睛的审查、根据判断力的选择而发现确定的形式”4;或从诸多不确定的具体实物中抽离出共同的本质属性,以便构造一个可确定的知觉客体。宋元山水画竭力避免“以形写形,以色貌色”(宗炳《山水画序》)的生硬做法。谢赫“六法”中也没有像西人那般热衷于有色物质(油画、水彩等颜料)厚度、密实性的探究。
与之有别,西洋风景画发展依托的是“主观-客观”视野二分逻辑。它受古希腊理性目光的特权位置和“知、情、意”(康德)三分法则制约,它“趋向于将实在优先构想为一个认知对象,精神从视看感觉提升到本质的建构,而视看则受到理性的矫正、构造和超越……但中国人并不把世界观建立在认知活动上,而是建立在且入且出的(外-内)的呼-吸上……并不依据存在范畴及形式与质料的关联去构想本源性的实在,而是将之构想为‘气息-能量’”5。
然而,中国古人不倾向于描刻,不会一笔一画地描摹眼中之物,或在外观广延上依附于眼睛,或通过笔端将它复制在画布上,保持与外在世界的分离,或将它锁闭在一个隐秘空间里成为某种西式实存。
二、多感官在“山水-云雾-烟气-峰岚-山骨-林霄”中交互映射
不像西方传统画追求单一的视觉对象客体,中国画内涵的多相感知系统让“山水-云雾-烟气-峰岚-山骨-林霄”可以相互隐没,从而解除西式“视觉中心”的专制霸权,将山川景物由“对象性”视察引向“圆桌对话”式民主共融场域。
所以,郭熙说,山形可“欲耸拔,欲轩豁,欲箕踞,欲盘礴,欲浑厚,欲雄豪,欲精神,欲严重,欲顾盼,欲朝揖……欲上有盖,欲下有乘,欲前有据,欲后有倚,欲上瞰而若临观,欲下游而若指麾。”(《宋人画论》)石涛指出,我们可以从“位”“神”“化”“仁”“东”“静”“礼”“和”“静”“智”“文”(石涛,《苦瓜和尚画语录》资任章第十八)等多层面对自然景物进行领悟。因为,“横看成林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苏轼《题西林壁》)之故。
中国画始终保持着对眼、耳、鼻、心、神、意等多项触知神经元的开放性。因为中国画推崇“以一管之笔,拟太虚之体,”以“竖划三寸”彰显“千仞之高”,在“横墨数尺”之间“体万里之回。”(宗炳《画山水序》)在纸张的有限空间里,讲究用最少的简名笔触勾勒山峰的气象。在山之眉额颊辅,水之婉转多姿间勾勒宇宙的苍茫气息。它要描绘的是那种对宇宙广袤性的化约和对宇宙虚空的缩象,此等抱负,绝非眼睛一种感官所能胜任的工作。它需要各感官神经元之间的民主协同,方能接近“画意道根”。
王维说“凡画山水,意在笔先”(《山水论》),宗炳指出要“应目会心”,方能“神超理得”(《画山水序》);郭熙强调“须养的胸中宽快,意思悦适”,才有郭若虚的“灵心妙悟,感而遂通”(《图画见闻志》);再有,顾恺之的“迁想妙得”(《魏晋胜流画赞》),刘勰的“思接千载”、“视通万里”(《文心雕龙•神思》),郑燮的“胸有成竹”(《郑板桥集》),原济的“物随物蔽,尘随尘交,则心不劳”(《石涛画语录》),邵梅臣的“神气行于理法中,乃有生趣”(《画耕偶录》)等都是对诸感知元的民主开放性、交互协同性过程肌理、脉络气息的变相描述。
其实,郭熙、石涛、董源等画论大师的“民主协同”多元立场很早已为我们打开了一个难以进入的非本体、非形而上、非神学之门,从而“一锤定音地中止了在与非在的相互孤立甚至排斥……重新找到了一种连续的、过程的、不间断的结构,它们将在场与缺席不加区别地混在一起,显得模糊而弥散。”6这或许是中国山水贡献于世界最为重要的法则价值。
三、多感官联动开启中国山水画的整体气韵
古人偏爱山水,并非单纯为了“看”,而是要让心、神、意等诸感官逗留、嬉戏于山川云雾之间。神思遐想、心性感悟于山水峰峦、花草树木。于是,“山所特有的丰盛性适合所有可能……它种种形式的无限变化在云间若隐如现,盛景迭出,如同从不可见之中涌现出来……山之大,把所有视角包含于自身;‘大’意味着向任何可能性视角开放,意味着不排他……它的方式是弥漫的,从而不被理解,它既不施加限制也不遭遇抵制;它的威力在于无所求取,也无所强制,但就像风一样,他形成了涵容性影响力、不可指定性”7。
整体立场的无限性,足以让观者能像画中人物一样任意“来-去”、“进-退”、“出-没”、“显-隐”。“一方面,将目光一直引向具体的物质化,造就可见者的现实性;另一方面,将目光带向不甚分明的远处,让可见者在那里渐隐消失。画中风景既呈现又退隐”8。
随着立足点移动,胸中景象不断丰盛起来:“正面溪山林木,盼折委曲,铺设其景而来,不厌其详,所以足人目之近寻也,旁边平远,峤岭重叠钩连缥缈而去,不厌其远,所以,极人目之旷望也。”(郭熙《林泉高致•山水训》)如果用阿尔伯蒂线性切割法来处理古人心中风景,则会将变幻不居的气韵弄得支离破碎,不仅会阻断“气息-能量”在散点视角之间的自由呼吸,而且会切断画面向“禅道”精神气韵维度提升的通路。
可见,中国画家对山水的整体领悟,完全不同于西方解剖学、物理学意义上的理解认知,更不像西人那样将风景视为被丈量的工具(“人是万物的尺度”)。“中国山水画绝不像西洋画那种被当作受其单一视域限制的具体片段,它每一次都让各元素的视角整体发挥作用,这些元素既彼此对立又相互呼应;画笔所要把握的正是动态的总体性。中国画家都要画出诸事物的完整进程和各极无尽多样的全部游戏”9。
总之,中国山水画并非单纯为了“看”,而是要让心、神、意、味等诸感官相互协作,以便让“我”逗留、嬉戏于山川云雾之间。在山水峰峦、花草树木中心驰神往。眼睛“所见某景”被转移到神思妙悟上。不固恋、不执着某一点,而是在多元景物之间来来往往。在曲折通幽中,浮想联翩、流连忘返。
注释:
1.3.4.5.7.8.9.[法]朱利安.大象无形:或论绘画之非客体[M].张颖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317、29、395、258、115、320、258页。
2.6.[法]朱利安.山水之间:生活与理性的未思[M].卓立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1、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