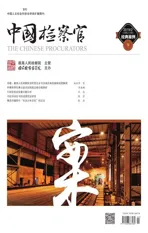强制猥亵罪的构成要件与入罪标准研究
2019-01-27/文
● /文
由于我国采用的是立法定性兼定量的模式,因此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规定的大量行政违法行为与《刑法》中规定的犯罪行为是存在重叠的,这些重合的行为通过情节、数额、结果等要素区分为行政违法行为与犯罪行为,分别处以治安处罚和刑罚,强制猥亵行为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4条规定了对猥亵行为的行政处罚,同时,《刑法》第237条规定了强制猥亵罪及其适用的刑罚。[1]但二者之间缺乏统一的区分标准,以下面两个案件为例:
[案例一]2006年3月4日,马某与刘某(女)共同乘坐出租车。途中,马某在出租车的后排座位上强行对刘某实施亲吻、抚摸等动作。后刘某打电话报警。警方调查认为马某的行为违反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对刘某处以行政拘留10日的处罚。[2]
[案例二]2013年4月10日,王某在酒后跑到三楼卫生间接水,见卫生间内有一条女士内裤,便对着内裤进行手淫,恰巧碰到受害人李某到卫生间洗漱,王某就一把抱住李某,准备实施猥亵行为,李某尖叫,王某怕被人发现仓皇逃跑,后王某被检察院以强制猥亵罪提起公诉。
在第一个案例中,马某对刘某实施了亲吻、抚摸等行为,公安机关查证后对其作出行政拘留10日的处罚。而在第二个案例中,王某仅是抱了李某一下,就被以强制猥亵罪提起公诉。
通过两个案件的对比可以发现,强制猥亵行为罪与非罪的认定标准在司法实践中比较含糊,难以做到罪刑责相适应。这一方面是因为现行法律缺乏明确的依据,公安机关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容易发生权力的滥用。另一方面是因为全国没有统一的罪与非罪的区分标准,各地司法机关在实践中可能采取不同的标准,这就容易导致“同案不同判”或者判决结果违反罪刑责相适应原则。在司法实务中,正确区分《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一般猥亵行为与《刑法》上的强制猥亵罪,关键在于明确强制猥亵罪构成要件的含义及罪与非罪的区分标准。
一、强制猥亵罪的构成要件
我国《刑法》第237条规定了强制猥亵罪,但对“猥亵”“强制”的含义并未作具体表述,这导致对该罪构成要件的理解一直存在很大争议。
(一)猥亵的含义
针对“猥亵”这一规范要素的内涵,中外学者的表述存在区别,我国刑法学界亦尚未形成共识,争议的焦点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
1.本罪是否为倾向犯
即猥亵行为是否要出于满足性欲或者追求性刺激的目的实施。部分学者对此持否定态度,其理由主要有:首先,刑法条文中并未写明本罪的成立需要行为人出于满足性欲或者性刺激目的这一主观构成要素。其次无论行为人是否有此目的,都不会改变行为造成的对被害人性的自主权的侵害结果。再次,行为人的行为倾向十分抽象,隐藏于其内心世界之中,很难对其进行客观判断,这不符合法律明确性和可操作性的要求。[3]
否定说的观点看似有道理,却忽略了我国刑事立法的实际情况。我国《刑法》除了在第237条设立了强制猥亵罪、强制侮辱妇女罪,同时还在第246条设立了侮辱罪。由此,猥亵行为、侮辱行为及上述三个罪名之间的区分成了我国刑法学界的难题。而只有将强制猥亵罪界定为倾向犯,才能协调好这三个罪名之间的关系。可以认为,强制侮辱妇女罪与侮辱罪侵犯的法益并不相同,前罪侵犯的法益是妇女自身的性自我决定权,后罪损害的却是他人的名誉权。[4]前者与后者是特殊法与一般法的关系,因为侵犯妇女性的自主决定权自然也会侵害妇女的名誉权,此时按法条竞合处理即可。而强制猥亵与强制侮辱的区分就涉及到猥亵行为与侮辱行为的界限。事实上,单从客观行为上判断,很难区分猥亵行为和侮辱行为。因为猥亵行为与侮辱行为侵犯的法益都是妇女的性羞耻心或自主决定权,“猥亵行为包括了伤害妇女的性的羞耻心、违反善良的性道义观念的一切行为,而侮辱行为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超出这一范围”。[5]犯罪行为的判断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猥亵行为与侮辱行为在客观行为上存在难以区分的模糊地带,此时我们就需要考虑行为人的主观状态,只有这样才能厘清两者之间的界限。将强制猥亵罪认定为倾向犯,猥亵行为要求行为人主观上有满足性欲的目的,而侮辱行为则不要求行为人有这种内心倾向,如此便能理顺二者之间的关系。例如,行为人出于打击报复的目的,逼迫被害人脱光衣物并为其拍摄裸照,随后将拍摄的照片公开张贴在街道上。由于行为人拍摄裸照并不是追求非法的性方面的目的,而是出于打击报复的心理动机,宜将行为人的行为认定为侮辱行为而非猥亵行为。综上,根据我国现行立法体系,将本罪认定为倾向犯更为适宜。
2.本罪保护的法益
有学者认为,“该罪保护的法益是被害人的性自主权、性羞耻心和社会风化。”[6]对此,笔者持不同的观点。首先,本罪规定于我国《刑法》第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民主权利犯罪部分,立法者的初衷便是侧重于保护与公民人身权利相关的法益,因此将本罪的法益理解为社会风化似有不妥。另外,我国传统文化中长期要求妇女遵守“三从四德”,视“贞洁”高于一切,如果此时将本罪保护的法益理解为社会风化和社会秩序,会使被害人在受到侵害之后因顾及到他人的看法以及社会名声的束缚,畏惧通过法律维护自身权益。其次,性羞耻心是基于各人的主观感受而言,因人而异。如对于从事性工作者而言,由于长期从事该行业,其性的羞耻心可能弱于其他人。[7]另外,如果将本罪的法益理解为性的羞耻心,那么法益侵害结果的严重程度取决于对被害人性的羞耻心的侵害程度。但是由于每个人的主观感受和承受能力的不同,可能同样的危害行为,有些被害人认为虽然侵害了性的羞耻心但是可以忍受,有些被害人会觉得难以忍受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这就使得对于法益侵害结果的判断十分困难,有悖于法律的明确性和可操作性的要求。
笔者认为,将本罪保护的法益理解为被害人的性自主权最为合适。首先,刑法将强制猥亵罪规定在第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的犯罪之中,表明法律对本罪的价值取向——即对公民个体人身权利的保护。猥亵行为之所以规定为犯罪,不仅仅是因为其有伤社会风化,更重要的是其侵犯了公民性方面的自主权。刑法的价值取向是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性自主权作为一项重要的人身权利已经是各国刑法学界的共识。其次,将本罪的法益理解为公民性的自主权,可以淡化社会风化、传统道德观念对妇女的束缚,使社会民众清晰地认识到强制猥亵罪的本质是对被害者人身权利的侵犯,应当谴责的是犯罪行为人而非受到侵害的被害人,使社会公众卸下对被害人的“有色眼镜”,鼓励被害人放下思想包袱,如实陈述犯罪事实,这样更有利于打击此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
(二)“强制”之认定
对于强制行为的规定,大致存在两种立法模式。一种以德国、日本和韩国为例,认为强制行为是指暴力或者胁迫手段;德国、奥地利刑法更加严格,要求将胁迫行为限定为“以生命、身体的现实危险相恐吓”。在上述国家,利用他人神智不清或无法判断、无法反抗的状态下实施的犯罪,一般不认定为手段行为具有强制性,而是另依其他规定对其加以定罪处罚。[8]另一种是将强迫行为描述为暴力、胁迫或其他手段,“其他手段”便涵盖了更多可能出现的情况,扩大了强制行为的范畴。[9]
我国刑法规定,构成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要求行为人的手段行为必须具有强制性,行为人的手段行为包括暴力、胁迫或其他方法。那么利用被害人熟睡、醉酒或病重情况下形成的不知、不能、不敢反抗的状态,可否认定具有强制性,属于“其他方法”呢?笔者对此持肯定的观点。首先,利用他人熟睡、醉酒或病重状态实施猥亵行为时,表面上并没有采取具有强制性的手段行为,并未对被害人的身体、精神产生压制反抗的效果。但是强制猥亵、侮辱罪的本质就是违反被害人的意志,侵害被害人性的自主权。也就是说,当行为人利用被害人上述不知、不能反抗状态对其实施猥亵行为时,其猥亵行为本身就带有强制性,因为被害人此时明显处于反抗困难的境地。其次,在某些国家的刑法中,会专门另行设立“乘机猥亵罪”“准猥亵罪”等罪名[10],使上述情况排除在本罪适用范围之外。但我国刑法并未作出特别规定,如若对该种情况不加以处罚,不仅与人民群众朴素的法正义观相悖,也不利于对法益的周全保护。最后,虽然我国并没有司法解释对强制猥亵、侮辱罪中的“其他方法”加以阐明,但是在1984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发布的《关于当前办理强奸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第2条明确规定,“强奸罪中的‘其他手段’包括利用妇女患重病、熟睡之机对其进行奸淫的情况。”[11]强奸罪和强制猥亵、侮辱罪都是侵害妇女性的自主权的犯罪,可以比照强奸罪中关于“其他手段”的司法解释来理解强制猥亵、侮辱罪。综上,利用他人醉酒、病重、熟睡等状态实施猥亵行为应当认为具有强制性,属于“其他方法”,构成本罪。
二、强制猥亵罪的入罪标准
如前所述,我国刑法采取的是立法定性兼定量模式,《治安管理处罚法》与《刑法》中对猥亵行为的规定十分简单,从法条表述上难以进行科学合理的区分。如何区分强制猥亵行为的罪与非罪,科学的衔接行政处罚与刑罚之间的关系,既遵守罪刑责相适应原则,又不违反刑法的谦抑性,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把握。
(一)坚持宽严相济原则,对《刑法》中的猥亵行为适度限制解释
既然区分对猥亵行为施以治安处罚或刑罚的关键在于行为的“量”,由于案件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完全精准的量化分析又难以实现,加之现行法律缺乏对此问题的规定,就需要通过宽严相济的原则来处理实践中的模糊问题。
“猥亵”作为刑法中典型的规范构成要素,对其内涵的理解往往跟随一国法律及社会伦理、风俗的变迁发生变化。当前刑法中强制猥亵罪的前身来自于1979年《刑法》中流氓罪的规定。[12]1984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流氓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强调要严格区别流氓罪与一般流氓违法行为,并指出“情节是否恶劣”是区分二者的关键。[13]1997年《刑法》修改时,将流氓罪进行拆分,分离出来的罪名就包括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和猥亵儿童罪。[14]
现行刑法中对强制猥亵罪的规定并不像1979年《刑法》中,明确要求“情节恶劣”等限定条件,因此根据刑法的谦抑性以及罪刑责相适应原则的要求,在解释现行刑法中“猥亵”一词时,宜适当缩小其范围,如考虑猥亵手段、针对的身体部位、行为持续时间的长短、对被害人身体伤害的程度及对社会风尚的冒犯程度等,综合判断其是否达到需要动用刑罚处罚的程度。[15]对于那些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行为,作为行政违法行为处罚即可。(1)行为针对的身体部位。一般而言,行为针对的身体部位所代表的性色彩越明显,行为的违法程度便越高。如行为人隔着被害人衣物碰触其背部或手部,一般作普通违法行为处理;但若行为人将手伸入被害人衣物内抚摸其胸部、臀部,便可成立犯罪。[16](2)行为持续时间的长短。一般而言,行为持续时间越长对法益的侵害程度就越高。如一男子行走在路上,突然强行搂住走在他前面女生的腰,而后立即松手,由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宜将其作为犯罪处理。但若该男子将该女子搂入怀中,控制该女子后长时间实施抚摸行为,便构成强制猥亵罪。(3)行为产生的后果。如行为人对妇女实施猥亵行为后,造成妇女精神失常或者自杀的,此时行为人的行为造成了法益严重侵害的后果,构成强制猥亵罪。
(二)结合案件事实,分析是否存在“暴力、胁迫或其他手段”
对比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4条及《刑法》第237条的文字表述可以发现,是否存在“暴力、胁迫或其他手段”是区分猥亵行为与强制猥亵罪的关键。首先,要将强制猥亵妇女行为与非强制性猥亵妇女行为区分开来,强制猥亵妇女罪只惩罚以强制方法猥亵妇女的行为,对于非强制性的猥亵妇女行为不能视作犯罪。但是,并非任何强制猥亵妇女的行为都构成强制猥亵妇女罪。刑法虽然未规定“情节严重”之要件,但不能将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强制猥亵妇女行为视作犯罪。
上文已经针对强制猥亵、侮辱罪手段行为的强制性加以讨论,此处不再赘述。例如,在公共场所公然露阴,因为其不具有强制性,并不构成强制猥亵罪。再比如,某女甲醉酒未拉窗帘赤身裸体躺在家中床上,窗户对面的男邻居边看该女边手淫,虽然其行为是猥亵行为,且利用了被害人醉酒的状态,但是因行为人只是在一旁观看,未与被害人发生身体上的接触,行为人的行为不具有强制性,不构成强制猥亵罪。
(三)全面分析案件,综合判断行为社会危害性的大小
上文提及我国的刑事司法体系采取的是立法定性兼定量模式,刑法与行政法相互衔接,共同发挥社会治理的作用。而为保证刑法的谦抑性,只有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较大,达到需要动用刑法对其加以处罚的程度,才会将其认定为犯罪。笔者认为,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如果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可以认为猥亵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较大,达到了需要动用刑法加以处罚的程度,可以以强制猥亵罪定罪处罚:(1)多次猥亵他人或一次猥亵多人的;(2)猥亵他人致使被害人轻微伤以上的;(3)猥亵他人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例如严重损害被害人的心理健康,造成被害人自杀等)。
三、结语
由于我国刑法采取立法定性兼定量的模式,因此常常出现同一类危害社会的行为根据犯罪情节是否严重区分为行政违法行为与刑事犯罪行为,达到通过《治安管理法》与《刑法》协同作用,共同维护社会秩序和保护法益的目的,即“出行入刑”与“出刑入行”之间的相互转化。但在实践中,对于同一类危害行为,“行”与“刑”并非泾渭分明,而是存在着交叉重叠的模糊地带,在刑法分则并未明确规定罪量要求的情况下,需要在实务中找到一个合理、统一的标准。[17]猥亵犯罪就是如此。
区分行为人的猥亵行为究竟属于犯罪还是一般违法行为的关键在于科学衔接《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刑法》。为了防止司法机关滥用权力,避免错判导致对行为人权利的侵犯,维护司法公正和人民群众对法律的信任,我们必须遵守罪刑责相适应原则,对“猥亵”一词的内涵进行合理限制解释,同时以是否存在“暴力、胁迫或其他手段”及行为造成的社会危害性大小为标准,准确界定强制猥亵罪与一般猥亵行政违法行为的界限,做到治安处罚与刑罚的科学衔接。
注释:
[1]《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4条规定:“猥亵他人的,或者在公共场所故意裸露身体,情节恶劣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猥亵智力残疾人、精神病人、不满14周岁的人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
[2]伊乐林:《强制猥亵妇女治安处罚与刑事处罚的界限》,https://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13/06/id/1014392.shtml,访问日期:2018年12月22日。
[3][日]参见西田典之:《日本刑法各论》(第三版),刘明祥、王昭武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4页。
[4]参见陈家林:《<刑法修正案(九)>修正后的强制猥亵、侮辱罪解析》,载《苏州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
[5]张明楷、黎宏、周光权:《刑法新问题探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57页。
[6]王政勋:《强制猥亵、侮辱罪构成要件的法教义学分析——基于原型范畴理论的研究》,载《法律科学》2018年第4期。
[7]参见汪雪城:《新强制猥亵罪的法理解读和规范评价——简评<刑法修正案(九)>第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载《法律研究》2016年第2期。
[8]参见张明楷:《外国刑法纲要》,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8页。
[9]参见王作富主编:《刑法分则实务研究》(上),中国方正出版社2010年版,第1039页。
[10]《日本刑法典》第178条规定趁机猥亵罪,“趁他人心神丧失或者不能抗拒,或者是他人心神丧失或者不能抗拒而实行猥亵行为”。
[11]参见1984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当前办理强奸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第2条规定:“其他手段是指犯罪分子用暴力、胁迫以外的手段,使被害妇女无法抗拒。例如,利用妇女患重病、熟睡之机,进行奸淫;以醉酒、药物麻醉,以及利用或者假冒治病等等方法对妇女进行奸淫。”
[12]1979年《刑法》第160条规定:“聚众斗殴,寻衅滋事,侮辱妇女或者进行其他流氓活动,破坏公共秩序,情节恶劣的,处7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流氓集团的首要分子,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
[13]该解答还指出:“侮辱妇女情节恶劣构成流氓罪的,例如:1.追逐、截堵妇女造成恶劣影响,或者结伙、持械追逐、截堵妇女的;2.在公共场所多次偷剪妇女的辫发、衣服,向妇女身上泼洒腐蚀物,涂抹污物,或者在侮辱妇女时造成轻伤的;3.在公共场所故意向妇女显露生殖器或者用生殖器顶擦妇女身体,屡教不改的;4.用淫秽行为或暴力、胁迫的手段,侮辱、猥亵妇女多人,或人数虽少,后果严重的,以及在公共场所公开猥亵妇女引起公愤的。”
[14]参见赵俊甫:《猥亵犯罪审判实践中若干争议问题探究——兼论<刑法修正案(九)>对猥亵犯罪的修改》,载《法律适用》2016年第7期。
[15]同[14]。
[16]参见王政勋:《论猥亵行为违法性程度的判定》,载《法治现代化研究》2018年第4期。
[17]同[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