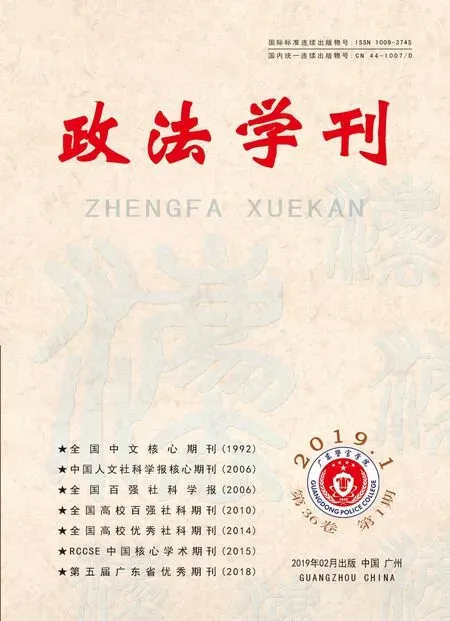《监察法》与《刑事诉讼法》衔接专题研讨
2019-01-26刘计划
刘计划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定不移地推进反腐败工作。在深入推进反腐败工作时,党中央积极推进国家监察体制改革。2016年12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2017年11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在全国各地推开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在试点基础上,2018年3月第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下文简称为《监察法》),正式将监察制度纳入到我国政治制度中。为了适应《监察法》的实施,2018年10月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对刑事诉讼法作出部分修改补充。《监察法》的制定和《刑事诉讼法》的修改,解决了两法重大冲突的问题,但也使得两法衔接问题凸显出来。依据《监察法》规定,监察机关有权对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案件进行调查并对违纪案件监督检查,职务犯罪案件的处理则涉及到《监察法》与《刑事诉讼法》的衔接问题。监察机关在调查职务犯罪案件时应当依据《监察法》的规定,而检察机关和法院在办理职务犯罪案件时却适用《刑事诉讼法》。《监察法》中调查程序与《刑事诉讼法》中侦查程序的规定并不完全一致,而且受条文总量限制以及规制领域不同,《监察法》难以照搬《刑事诉讼法》的相关条文,这也使得监察调查程序自身的正当性面临诸多质疑。为了确保监察调查与刑事诉讼的有效衔接并确保监察调查程序的正当性,《监察法》与《刑事诉讼法》的衔接成为学界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
本期研讨围绕“《监察法》与《刑事诉讼法》衔接”进行,集中发表由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杜磊博士撰写的《监察自治理论及其适用界限研究》、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孔祥承博士撰写的《留置措施规范化论要》、由南开大学法学院高通博士撰写的《论监察机关收集和运用证据的要求和标准——基于〈监察法〉第三十三条第二款的分析》等三篇文章,旨在对《监察法》与《刑事诉讼法》衔接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几个问题进行专题研讨。
三篇文章对两法衔接的关注点有所不同。杜磊文关注的是《刑事诉讼法》能否适用于监察领域的问题,其从监察程序排斥《刑事诉讼法》适用的实践出发,提炼出监察自治理论,并认为虽然监察自治理论的产生存在特定的制度和实践背景,但监察自治理论也不是要塑造一个优越于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的独立主体,其适用应当存在一定的界限,监察自治理论并不适用于处理监察和检察、审判的关系。孔祥承文关注的是留置问题,其从学界对留置性质的诸多争论出发,认为留置应当定位为一种特殊的逮捕,属于一项由《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干预措施,为实现留置的法治化,应当以宪法的视角引入基本权利干预理论,并推动留置条件的体系化与阶层化,最终将留置分为普通留置与重罪留置,并将留置条件区分为基础性的证据要件、否定性要件的罪责要件以及核心要件的社会危险性要件。高通文关注的是监察证据与刑事证据的衔接问题,其从《监察法》第三十三条第二款出发,分析该条款承担的功能,并认为该条款将《刑事诉讼法》中的证据规范引入到监察程序中来,但该条款的适用也存在一定限度,一个是该条款无法将刑事证明规范引入监察程序中来,二个是该条款仅适用于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案件的调查。
这三篇文章涉及到《监察法》与《刑事诉讼法》衔接中几个争议焦点议题,具体来说:
第一,《监察法》与《刑事诉讼法》的关系问题。从《监察法》规定来看,《刑事诉讼法》并不是监察机关办理案件的法律依据。但因职务犯罪案件在监察机关调查完毕后,仍然要移送审查起诉和审判,故其与《刑事诉讼法》存在密切关联性。对于此种关系,杜磊文认为《监察法》和《刑事诉讼法》在涉及到腐败犯罪处理上属于特别法和一般法的关系,当《监察法》没有规定的时候,应该适用《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孔祥承文在论证留置制度中亦提出《监察法》与《刑事诉讼法》间特别法与一般法的关系,并参照《刑事诉讼法》中逮捕的条件来设计留置制度。但特别法与一般法的定位仍然面临一个问题,即这种定位是否意味着在政纪监督检查以及职务违法调查中也需要遵循《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呢?这实际上就涉及到如何理解《监察法》第三十三条第二款的问题,该条款规定“监察机关收集、固定、审查、运用证据时,应当与刑事审判关于证据的要求和标准相一致”。高通文谈到这一问题,并提出《监察法》第三十三条第二款虽然在监察程序中引入《刑事诉讼法》,但其适用是存在一定界限的。
第二,如何防范出现“调查中心主义”的问题。为实现建构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中国特色国家监察体制的监察体制改革目标,《监察法》赋予监察机关充分的职权,并建立较弱的外部监督制约机制。这也出现了杜磊文中提到的国家监察活动形成了一个几乎完全自我封闭活动场域的现象。虽然《监察法》规定了强力的内部监督制约机制来确保监察机关办案的准确性,但这也大大强化了监察机关作为一个整体的力量,使得监察机关在面对检察院和法院时呈现出强大的优势地位。监察机关优势的政治地位也使学界对检察院和法院在办案中能否实现对监察机关的制约产生诸多疑问,进而开始担忧“调查中心主义”的出现。这也是该三篇文章的共同担忧。为了防范“调查中心主义”的出现,杜磊文中提出监察机关的自治应当存在一定界限,监察调查活动要受到检察院和法院的监督制约;孔祥承文中提出应当运用宪法、监察法以及刑事诉讼法的一体化思维,以基本权利干预作为留置的理念,保障被调查人的基本权利;高通文中则提出应当利用《监察法》第三十三条第二款,来实现法院、检察院与监察机关之间的权力制约关系以及监察程序自身法治化的目的。
第三,是否有必要建构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二元调查机构的问题。我国采用违法与犯罪二元论,行政违法调查与犯罪侦查是完全区分开来的。但《监察法》对于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不再作二元区分,监察机关统一行使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调查权。那么,此处的统一行使是否意味着职务犯罪调查和职务违法调查由监察机关同一个内设机构来实施。如果由同一内设机构来调查,这就意味着违法与犯罪二元论在监察案件中彻底消失;但如果是由不同内设机构分别调查,这意味着监察案件中仍然存在着违法与犯罪的区分。学界对此问题是存在较大争论的,有学者认同“程序一元论”,也有学者认同“程序二元论”,还有学者提出“程序二元、证据一元”的模式,高通文中也提到这一问题。但无论是采用何种模式,都要回应一个问题,即如何平衡发现违法犯罪事实与人权保障间的关系问题。依据《监察法》的规定,监察机关在调查职务违法案件时,可以采用先前属于侦查的措施,这些措施比先前的违法调查措施强制性更强、对当事人权利限制更多。这极大扩充了监察机关的权限,但这种权限扩张的正当性以及边界又在哪里呢,是否造成打击违法犯罪与人权保障关系的失衡?孔祥承文中提到的基本权利干预理念以及比例原则似乎能为我们提供一些借鉴。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给既有的制度带来诸多冲击,甚至对我们传统的公平正义理念也带来一定冲击。本期所组稿件中实际上也反映出这种矛盾心态,一方面我们对监察体制改革寄以良好的希望,另一方面我们希望用既有的制度和理念来改造或限制监察权,防范一个不受制约权力利维坦。当然,对于新生事物的矛盾心态非常常见,而且这种心态对监察制度研究和发展也是大有裨益的。我们也希望通过本组稿件,能够进一步深化对监察制度的研究,进而促进该制度的不断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