苔菲的编年史
2019-01-25曾昭华
曾昭华

苔菲(1872-1952)
二十年前,翻譯家蓝英年先生曾向中国读者介绍一位叫苔菲的俄罗斯作家,蓝先生说:
苔菲这个名字对中国读者十分陌生。其实何止对中国读者,对俄国读者同样陌生。七十年来的尘埃已经把这位步入国际文坛的女作家深深掩埋起来。她那些脍炙人口的幽默小说不再成为人民的精神财富。苔菲被她的祖国忘却了。
不过,就在同一篇文章里,蓝先生又补充了一个细节:
一九四六年夏天西蒙诺夫和爱伦堡访问巴黎,斯大林给他们一项任务:动员布宁或苔菲回国。布宁是第一位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俄国作家,在苏联和西方世界很有影响,而斯大林把苔菲同布宁相提并论,说明他如何看重她。(蓝英年《青山遮不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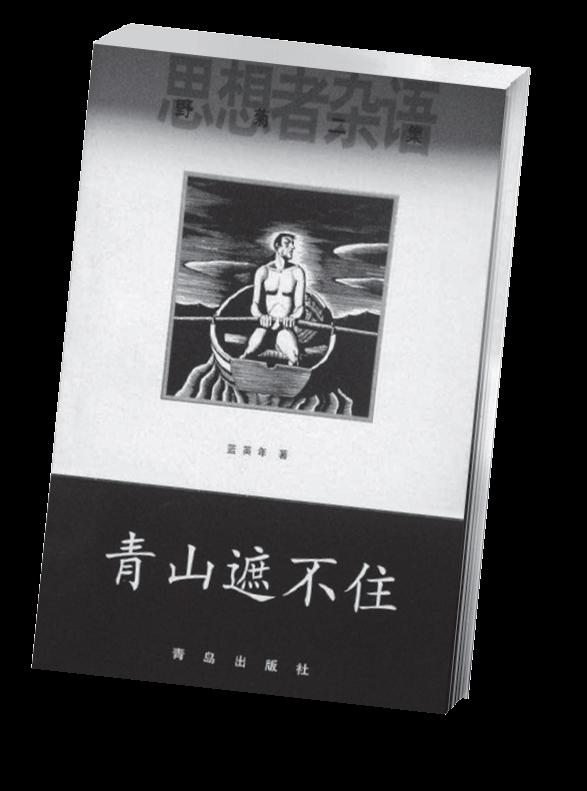
《青山遮不住》蓝英年著青岛出版社1998年版

苔菲《我的编年史》谷兴亚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还应提到的是,在这之前,俄国罗曼诺夫王朝最后一位君主,尼古拉二世在一九一三年庆祝罗曼诺夫王朝三百周年庆典时,宫廷准备出版纪念册,大臣询问尼古拉二世收入哪位作家的作品时,沙皇说:“苔菲,只收她一个人!别人谁也不收!”可见苔菲的名声和影响力。
最近由河北大学教授、翻译家谷兴亚先生翻译的苔菲力作《我的编年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用既风趣又朴实的语言,像讲故事般向世人袒露她不为世人所知的一生。
在《我的编年史》开篇的序言中,作家、评论家斯·尼科年科以略带调侃的风趣语言说:“苔菲是‘无与伦比的……苔菲不以表象论是非,她力图进入人的灵魂深处,剖析每一个人,理解每一个人。而且她完成这一切时总是面带微笑,诙谐,甚至还似乎带着几分歉意,做到惊人的自然而有分寸……”这些话恰如其分地再现了苔菲的人格特点和作品的不同凡响。她的开篇回忆录也同样富有高度的艺术性和幽默感。在回忆录里读者看到的不仅是苔菲的生平,更多的是她的“故事”。《我的编年史》虽然以纵向时间表述了她的一生作为,但读者看到的却是有趣味、有情节、有思考、有温度的“人生大戏”!
苔菲是作者的笔名。她的真名是娜杰日达·亚历山德罗夫娜·洛赫维茨卡娅。她父亲出身贵族,曾是教授、律师、编辑、出版人和出色的演讲家。母亲是法国人,谙熟欧洲文学,掌握多国语言,而诗歌是她的最爱。苔菲在这样一个家庭里出生、成长,培育了她深厚的文化素养。苔菲和哥哥姐姐在父母的言传身教及家学氛围熏陶下,从骨子里滋生出对文学和诗歌的爱好。苔菲的姐姐玛丽娅·洛赫维茨卡娅终于成为世纪之交的著名女诗人,生前曾三次获得普希金文学奖。苔菲继姐姐之后,一九○一年在《北方》杂志上发表诗作《七颗宝石》。这首诗歌虽然没有得到普遍认可,但这是一个开端。苔菲天生富于幽默感,观察力极强,想象力极丰富。她笔名的来历就足以说明这一点。她在散文《笔名》中写到,她曾写过一个剧本,她在剧院里和戏剧界还没有任何关系,剧院会接受她的剧本吗?这时她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俗话说得好,“傻瓜走运”,不妨取个傻瓜名字作笔名,于是她就用了“苔菲”(Тэффи,大意为“傻人有福”)这个古怪的名字去碰运气。结果不出所料,她成功了!这个夺人眼球的“苔菲”,引起了剧院老板的强烈好奇心。正是苔菲的幽默语言和剧情,让老板一锤定音:“上演!”
对于读者,特别是喜爱苏俄文学的中国读者来说,大多关注的是苔菲生平的精彩所在,以及她是如何受到读者的喜爱,又是如何在读者视线中消失的。这一切,都可以在《我的编年史》里找到答案。
对于一个恋国恋家的文学家来说,离开故乡且前途未卜,是一件多么令人沮丧的事情。苔菲的故事便从这里开始了。在社会变革的战乱年代,她的生花妙笔被搁置。更重要的是到了食不果腹的地步,再加上周围的人的怂恿鼓动,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跟着一个化名叫古西金的经纪人,随着流亡的人群踏上去国的旅途。
笔者在阅读《我的编年史》开头部分时,便心有存疑:为什么作品的开篇是“回忆录”,第二部分才是“编年史”?当读完了全部作品,方才明了苔菲的良苦用心。因为在她的一生中,令她终生难忘的是“去国怀乡”之情!而在她由俄罗斯到乌克兰,直到法国的逃亡是她一生的不灭记忆!这第一篇的“回忆录”就是陈述她在逃亡旅途中的艰难险阻;于是“回忆录”便成了“编年史”里的重中之重。
“拥有一个有趣的灵魂,是对抗死亡最好的良药。”苔菲的这句话竟成了她背井离乡,甚至一生坎坷的谶语。
在经纪人古西金的带领下,苔菲与友人、作家阿维尔琴科结伴而行,在辗转旅程中满眼的嘈杂、混乱、阻挠、交涉,他们遭遇偷盗,又不断转车—“这就是‘逃亡。到基辅去,无奈,不想离开,但还得走。”这种矛盾的闪念时刻在苔菲心中翻滚。所幸的是苔菲一行,有名人大腕,有演员名角,一路上有惊无险!
他们终于到达乌克兰的第一个村庄,然而还有很远的路。为了生活得像个人样,这是他们离开莫斯科的主要原因。然而苔菲的所思所想突然会把见到的一切化作一股“灵光”, 一眼便能看出别人的可笑之处。然后化作一缕文思,化作一串串妙语连珠散发给大家,又化作一股温度融化着同伴内心的冰冷。在走向基辅的途中,大兵的欺辱,小城关卡的“检疫”,德国哨所的“例检”,都在头脑机敏的古西金和苔菲的名声的震慑下化解了。当他们跨进基辅的边界那一刻,他们并没有欢呼雀跃。
“回忆录”是一段不堪回首的苦难逃亡,这段回忆虽然只是她人生中的一个步履,一个“音符”,但在苔菲心中却似乎是她的全部,是她刻在骨子里永远的锥心之痛。所以在这段回忆以后才进入她的“编年史”。
苔菲的编年史,绝非是读者印象里的年代顺序记录史,而是把她记忆中的那些活生生的人和事,展示在读者面前。她说:“我在一生中曾遇到过许多有趣的人,我只想像讲述活生生的人那样讲述他们。”于是她的“编年史”就这样下笔了。
第一个人就是库普林。库普林不仅是她的文友,更重要的是他们两人的思维频率产生的“共振”,因为库普林的个性给予她深刻印象。库普林虽然酗酒成癖、粗口狂骂、大吵大闹……然而他还有另一面。苔菲说:“……他在我们文学大家庭却异常谦逊,平易近人。许多小作家去找他,他都热情诚恳地接待。”然而,“他不是一个‘老实人,不是意志薄弱的好好先生,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
笔者曾读过库普林的几部中长篇小说如《阿列霞》《石榴石手镯》《亚玛街》等,从这些不朽的著作中可看出作者丰富的情感和理智的思考。在这样一爿精致细腻的精神世界里,怎么能容得下周遭的污垢、混沌、欺骗与杀戮……于是在环境的压抑与恫吓中他的神经总处在紧张和矛盾中。也许正是如此的内心张弛使他的文思高亢和低沉相互交织起伏。
对于梅列日科夫斯基和季·尼·吉皮乌斯夫妇,苔菲不惜笔墨,大胆铺开。因为圈子里的人对他们都“不十分亲切”。而苔菲却认为这“既残酷也不公道。决不能忘记,做一个人非常不容易”。对于一些人对这对夫妇既刻薄又恶毒的评价,苔菲不敢苟同。在文学成就上,梅列日科夫斯基曾与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布宁并驾齐驱,是苏俄文学史中重要人物。当然苔菲也在《我的编年史》中坦诚地说:“要讲述梅列日科夫斯基夫妇很难。”因为在苔菲心目中,梅列日科夫斯基夫妇是一对怪人,虽然在苔菲的笔下没有过激的语言和恶毒的描述,但坦述了她对二位的不理解和不欣赏。
至于吉皮乌斯,苔菲既喜欢她又客观地评价她。吉皮乌斯既聪明又尖刻,直到她丈夫去世后,甚至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刻,苔菲才感悟到这位从里到外标新立异,思维、举止怪异的女诗人的内心世界是孤独的。苔菲与吉皮乌斯的特殊友谊是在特殊环境、特殊爱好与共同困境里形成的。苔菲对他们夫妇的客观评议和不同寻常的交往,足以证明苔菲为人大度、宽容、善良,有着高端的智商和情商。
塞纳河畔的“蓝色星期二”是文人聚会的标志。在这个群体里无一不是俄罗斯文学白银时代的文坛巨匠!诗人巴尔蒙特、伊戈尔·谢维里亚宁、作家阿列克谢·托尔斯泰、阿尔卡季·阿维尔琴科、列昂尼德·安德列耶夫、诗人阿赫玛托娃、诗圣古米廖夫、勃洛克、诗人瓦西里·卡缅斯基等等都活跃在苔菲的笔下。他们各具特色的个性与文品、人品让读者一目了然。
在文化出版界,苔菲的名气越来越大,关注她的人越来越多。于是她与从事地下工作的布尔什维克有了交集。二十世纪初,她曾通过《交易所新闻》报帮助高尔基接收革命文件。一九○五年她在《新生活报》文学部任职并为该报撰稿,曾多次接触列宁,还与列宁在一起工作过。在与列宁一起工作期间,苔菲对列宁的印象是不错的,她在《我的编年史》里说:“列宁举止异常朴实,从不装腔作势。列宁与马拉们(泛指列宁的得力助手)说话时的语调是友好的,和善的,耐心地给他们讲解他们一时不能理解的东西。他们也衷心感谢列宁的教诲。”她认为列宁很机敏,很能观察到一个人的长处并给予恰当的工作。
苔菲还接触了一位“神秘人物”,他就是在尼古拉二世时期自由出入宫廷的拉斯普京。苔菲与拉斯普京只见过两次面,但给她的印象是,“他的面貌却像尖利的刀剑镌刻,坚硬、鲜明、清晰地留在了我的记忆中”。在苔菲的一生中见过无数真正的当之无愧的名人,而“这个人是唯一的不可复制的,完全像个杜撰出来的人。他在传奇中生活,在传奇中死去……是一个半文盲农夫,沙皇的谋士,好色鬼和祈祷者,嘴上不离上帝的变化多端的妖怪”。
苔菲与拉斯普京见面很偶然。两位圈子里的人鼓动她去见一个“神秘的人”,就是拉斯普京。当然见这样一个人也是蛮有意思的,由于好奇与“有意思”,苔菲很想親眼见见这位“重量级人物”。

苔菲1929年在法国南部
在一位朋友M家聚会,当然都是有身份的人。朋友故意把苔菲安排在拉斯普京旁边就座,为的是让她能直观了解拉斯普京的言谈话语。拉斯普京很注意苔菲(从照片看,苔菲美丽、沉稳、灵秀、高贵的气质令人瞩目),挑逗、暗示、轻微触摸苔菲的肩膀并劝酒,苔菲不为所动。拉斯普京从未被拒绝过,苔菲的漠然置之,使他痛苦得浑身战栗,但他压抑着。拉斯普京极力劝说苔菲到他家去,给她祈祷,为她解除“爱情上的”痛苦,遭到苔菲拒绝。这对拉斯普京来说简直不可思议。苔菲是机敏的、庄重的,一眼看破拉斯普京的肮脏灵魂。
第二次为了看看他的“跳大神”般的舞蹈苔菲又去了。他的挑逗、轻微触摸的“催眠术”还是没有得逞。拉斯普京似乎震怒了,猛地跳起来跟着鼓点狂跳,不顾一切忘我地跳跃,这就是他最拿手的“幻术”了。在苔菲看来,他只不过是一个半文盲的农家神汉而已!苔菲有眼光、有主见、有预感,她绝不相信他所谓的祈祷和上帝,他只不过是“着了魔”的、掌握了“催眠术”的能言善辩的巫术师而已。苔菲看透了他,厌恶他,远离他。苔菲的朋友却从苔菲那里得到了第一手“资料”,最后拉斯普京死无葬身之地。
的确,《我的编年史》印证了二十年前蓝英年先生的论断:苔菲可以说是果戈理的嫡系传人,只不过他们的思维方式不同,语言表达各异而已。在写作方法上他们各走极端。果戈理把想到的一切先写在纸上,搁一段时间后再抄写修改。他的创作过程是在纸上完成的。而苔菲是“我坐下来写作之前,故事从第一句到最后一句都已想好”。她认为这是游戏,这是欢乐。苔菲的创作过程是在脑子里完成的。《我的编年史》不仅能使读者看到苔菲一生的步履,也能从每个人、每件事里窥视苔菲的神来妙笔。
在法国巴黎塞纳河畔侨居的大批苏俄文人学者,无不是俄罗斯文学白银时代的璀璨明星。在这个群体里苔菲无疑展示着她的聪明才智并得到众人的爱戴。关于苔菲有许多著名作家的回忆文章,所有这些文章都对苔菲赞赏有加。回忆录作者们直白地赞赏她的“俏皮、俊美、机智、善良和聪明”。
目空一切的布宁,写信给苔菲时说:“……您记住,您不仅对我们珍贵,对许多人同样珍贵,您真是非凡的人……上帝让我认识您对我真是莫大的幸福。”
古典文学最后一位大师库普林赞叹道:“儿童爱读她的书,少年爱读她的书,自食其力的成年人爱读她的书,白发苍苍的老年人也爱读她的书。”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驰骋诗坛的格·伊万诺夫预言道:“这是俄国文学中的罕见现象,无法解释的奇迹,一百年后人们将为此惊讶不已……”
以历史小说著称的流亡作家阿尔达诺夫说:“在赞赏苔菲天才这点上,政治观点不同和文学趣味各异的人都是一致的。我记不起还有哪位作家、评论家在读者心目中获得如此一致的好评。”(以上四人评论均摘自蓝英年《青山遮不住》)正如文章开头所谈到的俄罗斯历史上的两位统治者:尼古拉二世和斯大林,他们无论是政治观念还是所处时代都迥然不同,但对苔菲的重视与喜爱是不容置疑的。
在半个世纪的创作生涯中,她成果颇丰,在离开祖国之前她就在报刊发表了数百篇随笔、评论、小说、诗歌特写和回忆录,并出版了小说集《幽默故事集》(两部)、《于是变成了这样》《旋转木马》《僵死的野兽》《生活》等,还有诗集《七重火焰》及几个剧本等。侨居国外时她始终与当地报刊合作,又出版了十九部著作,用“著作等身”来形容苔菲恰如其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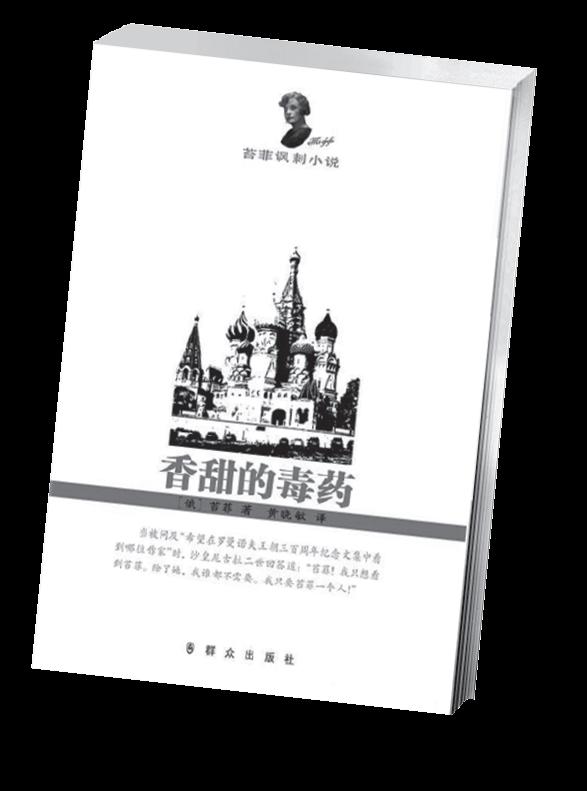
苔菲《香甜的毒藥》黄晓敏译群众出版社2013年版
苔菲—娜杰日达·亚历山德罗夫娜·洛赫维茨卡娅,伟大的、幽默的女作家,在她的“回忆录”和“编年史”中没有纯属她个人私生活的东西。她把个人的痛苦、哀伤、不幸和煎熬留在自己内心,而把幽默、诙谐、欢笑、温暖遍撒给他的挚友、亲人和合作者。当我们读完苔菲《我的编年史》后,读者会不约而同地发出一个声音:她在任何情况下都“思维敏捷、判断缜密、诙谐幽默、与人为善”。
苔菲晚年是在病痛中度过的,虽然她念念不忘的是祖国故乡的热土,然而她却客死在塞纳河畔的法国巴黎。不过,她留给故乡乃至世界热爱文学的人们的精神财富必将永世流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