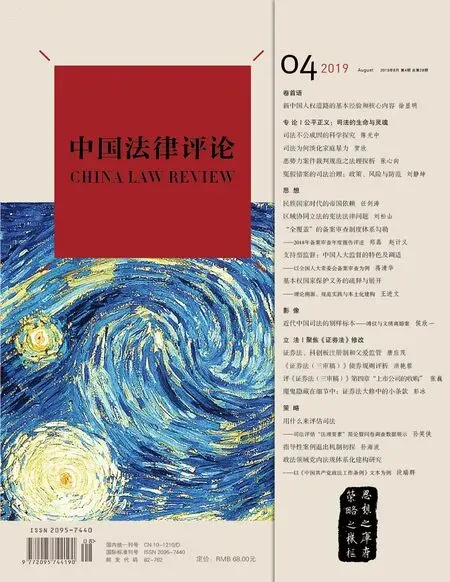指导性案例退出机制初探*
2019-01-25孙海波
孙海波
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人员
中国政法大学比较法学研究院副教授
随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的出台,具有中国特色的案例指导制度于2010年年末得以正式确立,这标志着中国司法界和理论界对于判例制度的摸索和研究又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在中国这样一个以成文法为主导形式的大陆法系国家,实行判例制度也从理论构想变成了客观现实,以至于有学者将这种实践称之为“中国式的普通法”。1See Mark Jia, "Chinese Common Law? Guiding Cases and Judicial Reform", Harvard Law Review, Vol.129, No.8 (2016),pp.2213-2234.在过去几年里,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发布了21批共计112件指导性案例,案例数量越来越多、覆盖面越来越广,案例制度的发展重心已慢慢转变到实践适用的问题上来。在实践中,当事人往往将指导性案例当作证据来提交,要求法官参照或拒绝参照从而来维护己方的权利诉求;而法院有时也会以明示的或默示的方式主动援引指导案例,这么做有利于保持法律的统一适用和化解疑难案件的裁判僵局。尽管如此,我国指导性案例的司法适用局面也只是初步打开,使用的断裂性(很大一部分还尚未被适用过)、启动的混乱性(被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而提出)、参照的规范性(只提要求而不附加论证理由)、隐性适用盛行等不良现象普遍存在,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制约案例指导制度的健康发展。
为了克服实践中存在的适用难点,最高人民法院2015年发布了《〈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就指导性案例的遴选标准、发布主体与程序、参照适用标准以及退出机制等内容作出了明确、细致的规定。就像法律必然面临立、改、废的命运一样,在推进案例制度建设的过程中也会清理和废止一些旧有过时的案例,同时选编和补充一些新的具有代表性的案例,通过推陈出新,形成一个不断流动和变化的案例集群。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为了让案例制度获得新鲜的活力,相关主体在何种情形下、基于何种程序可以废止指导性案例?是否允许法官在审判实践中规避既存的指导性案例?法官规避指导性案例的可能理由有哪些?法官不当规避指导性案例应承担何种责任?以上问题综合在一起构成了指导性案例的退出机制,本文尝试初步描绘这一制度的主要结构形式和内容。
一、对几点常见误解的澄清
在正式讨论指导性案例的退出机制之前,有必要先澄清实践中普遍存在的几种误解。当论及指导性案例时,应该认识到它已经不再是一种简单司法判决的载体,而是由最高司法机关通过严格法定程序加以选编和发布的,具有一定的规范性拘束力的“判例”。2对指导性案例的效力学界素来存在争议,主要有事实拘束力、规范拘束力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准规范拘束力三种观点。参见张骐:《再论指导性案例效力的性质与保证》,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3年第1期;以及雷磊:《指导性案例法源地位再反思》,载《中国法学》2015年第1期。面对“各级人民法院审判类似案例时应当参照指导性案例”这一强行性规范,人们难免会产生这样一种感觉,认为法官不能背离指导性案例,因此不存在“指导性案例的退出机制”。在一次法院系统的会议上,一位法院干部就曾对笔者所使用的这一概念提出了根本性的质疑,认为这一提法不符合案例指导制度的精神,指导性案例是拿来用的而非让法官选择规避适用。对此,笔者将对这些误解加以说明和澄清,借此为指导性案例的退出机制正名。
第一,应认识到退出机制是整个案例制度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退出机制的存在,可以让案例制度获得开放性和包容性,同时也让法官在适用指导性案例时具有自主性和判断权,避免在个案中机械性地照搬照抄裁判摘要所造成的实质不正义。显然,提倡退出机制并不是要否定或破坏案例指导制度,它是案例制度发展所不可避免要涉及的内容。《实施细则》中已经初步为这一制度的存在提供了正式的规范性依据,我们需要探索的是如何让退出机制与选编机制、参照适用机制等内容之间,形成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
第二,“应当参照”并不意味着“毫无理由地必须参照”。
“应当参照”对实践主体提出了比“可以参照”更强的规范性要求,这意味着法官在裁判过程中对“参照义务”是不能随意放弃的。然而,不能随意放弃并不意味着绝对不能放弃,正如法律在某些情况下由于自身的一些原因具有可废止性(defeasibility),指导性案例也不总是能够在所有案件中都要求法官适用自己。指导性案例生产机制的行政性和程式化,3参见郑智航:《中国指导性案例生成的行政化逻辑》,载《当代法学》2015年第4期。会使某些案例先天就带有缺陷,或者伴随着政策改变或社会的发展而丧失存在基础,因而必然面临着废止或在个案中被规避适用的命运。
第三,退出机制并不赋予法官自由背离乃至恣意漠视指导性案例的权力。
有人可能会担心,退出机制会不会为法官提供了一个轻视指导性案例的机会或借口,只要他想规避就可以任意地作出规避决定。不得不承认,这种担心是很必要的,如果法官可以自由地背离指导案例,那么案例制度势必会被彻底架空。退出机制的内涵是丰富的,它会在程序步骤、实质理由以及责任负担三个方面尽可能最大限度地限制法官的恣意行为,从而确保相关主体只有在极个别特定的情形下,严格遵照特定的程序才能废止指导性案例的效力或背离不该参照的指导性案例。除此之外,任何缺乏充分理由或错误地漠视指导性案例的行为将要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
第四,指导性案例的退出并不意味着案例指导制度的消灭。
指导性案例与案例指导制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两者是点与面的关系。指导性案例是案例指导制度的重要构成性要素,但是案例制度本身是个内容更丰富的概念,是一个包含指导性案例选编、发布、参照适用和退出于一体的动态体系。仅仅有指导性案例还尚不足以确立这一制度。同样的道理,在实践中清理或规避一定数量的指导性案例,也不足以从根本上撼动这一制度。因此,要正确认识和处理指导性案例与案例指导制度之间的关系,案例指导制度的正常运转离不开退出机制,而退出机制非但不会摧毁案例指导制度,而且还会为这一制度的发展不断注入新鲜血液。
通过以上讨论,我们看到如果将案例指导制度看作一个综合系统,那么退出机制应该是其中必不可少的重要一环。任何一个判例(案例)都有自己的生命,有的因为蕴含着一般性的法律原则、原理或精神而历久弥新,而另外一些则随着时代变迁而走到自己生命的尽头。为了不断给判例体系注入新鲜的活力,有必要弄清楚退出机制到底是怎样的一套制度。在我国,狭义的退出机制主要是指专门主体对指导性案例的清理或废止,有时也被人们归入指导性案例的选编范畴,而广义的退出机制还包括法官对指导性案例的规避适用,对此我们将分别予以介绍和讨论。
二、指导性案例的清理或废止
判例汇编(law report)是判例法得以运行的一个重要条件,通常只有被选中并刊载在判例汇编中的判例才具有正式性的拘束力。当然,由于判决本身的多样性,加上判例编制主体既有官方的又有民间的,这就使事实上并非所有的判决都能得到汇编,而法官也时常可能会引用未经汇编的或来自判例汇编之外的其他丛书的判例。4参见[美]格伦顿、戈登、奥萨魁:《比较法律传统》,米健、贺卫方、高鸿钧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58页。判例法的精妙就在于它是灵活与稳定的统一,遵循先例是一个兼具变与不变的过程。判例汇编会定期或不定期地将一些过时的或有重大内容缺陷的判例加以清理或废止。当然除了这种有意的清理活动之外,某个判例由于与新的判例在内容上存在冲突而遭到长期漠视,或者其所蕴含的先例规则与新的成文规则相冲突,这种情形下判例也会失去其效力。
清理或废止,在本质上是对判例效力的直接否定。在一些地方,比如我国台湾地区,还存在一些变更判例内容的做法,这可以看作一种对相关判例之效力的间接否定。依照台湾地区“法院组织法”第57条第1项之规定,“‘最高法院’之裁判,其所持法律见解,认为编为判例之必要者,应分别经由院长、庭长、法官组成之民事庭会议、刑事庭会议或民、刑事庭总会议决议后,报请‘司法院’备查”,该法第2项又进一步规定,“‘最高法院’审理案件,关于‘法律’上之见解,认有变更判例之必要时,适用前项规定”。法院所作之判例也应像法律一样具有一定的安定性,它能够给人们以一定的信赖,因此不得随意变更,需要遵循一定的程序或符合相应的条件,方可为之。这里,比较有争议的一个问题是,变更之判例应从何时发生效力,台湾地区对此大致有三种不同观点:其一,效力应追溯至判例所变更之判决公布当日以前要件事实已终结之案件;其二,只适用于该变更之判例公布后要件事实尚未终结之案件;其三,判例变更时除发生嗣后效力,同时也对要件事实已告终结之原因案件发生效力。5参见孙铭宗:《台湾地区判例制度之评析与检讨》,载《江海学刊》2014年第6期;林合民:《论“司法院”解释及判例变更之时的效力》,载《台湾宪政时代》1987年第4期。以笔者之见,依照信赖保护原则,判例就像法律一样,一般只对变更以后的法律事项产生约束力。故而所变更之判例原则上对其之前的案件并不具有约束力,如果新判例的适用更有助于保护争讼当事人利益的,也可以有限地承认变更之判例的溯及力。
变更判例与废止判例,从语义的角度来看也是不同的,变更意味着一定是改变了过去旧有的东西,同时又要以新的东西取而代之。换言之,变更判例是一种推陈出新,意味着要以新的观点取代法院以前对于某个法律问题的旧有观点,而废止判例只是推翻或取消了法院之前对于某个法律问题所持有的见解或立场。6参见王泽鉴、杨日然、黄茂荣等:《判例之拘束力与判例之变更》,载《台大法学论丛》1980年第1期。从这个意义上讲,变更判例是先破后立,废止判例是只破不立。
现在我们转向判例的清理或废止,由于这种活动触及对判例效力的直接或根本否定,通常是由特定主体进行的,具体来说是由有权创制判例的主体来完成的。这也是清理和废止判例与规避判例之间存在的一个根本性区别,后者在活动主体上并不加严格限定,只要是法律适用者,在实践中通常都有权规避指导性案例。
(一)活动主体
在我国,对于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只有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有权作出判例编撰活动。在检察案例指导制度中,有一项制度叫“宣告失效”,这与清理或废止在实质上是基本一样的。对于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只有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有权作出清理或宣告失效的决定。其法律依据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第19条之规定,“宣告指导性案例失效,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决定。”鉴于此,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内部分别成立了专门机关,集中统筹和执行指导性案例的清理和废止工作。
通过上面的讨论来看,在我国指导性案例的清理或废止主体具有专门性或特定性。除此之外,它还具有单一性,分别只有一个单一的特定主体有权从事此类工作,作为个体的法官无权对指导性案例作出此类具有“准立法性质的”否定性评价。这一点上,普通法系的司法实践是完全不同的。在普通法系国家中,除了集中的判例编撰工作之外,还有一项重要的“推翻判例”(overruling)制度。“对先例的推翻实质上是法院在相互冲突的诸多价值中进行选择和判断的过程,法律一方面必须保持一定的稳定性,另一方面又必须适应时代进行自我变革,以在社会中发挥应有作用,推翻先例可以说就是在稳定与变革性之间所作出的价值选择。”7何家弘:《外国司法判例制度》,中国法制出版社2014年版,第95—96页。从推翻判例的主体来看,一般上级法院可以推翻下级法院的判例,本级法院可以推翻自己先前的判例,原则上下级法院无权推翻上级法院的判例。通过对比发现,普通法系国家在推翻先例方面,主体也仍然是相对特定的,只不过其范围会更加广泛一些,形式也会更为灵活一些。
(二)清理或废止判例的条件
判例的作出与公布,本身代表着官方对于特定法律议题所持有的见解,按照平等对待的原则,人们有理由相信自己的类似争议在未来会被以类似的方式而解决。如果允许相关主体任意地变更或废止判例,就会对现行的法秩序的统一性带来干扰,整体上降低法律体系的有效预期。因此,对于判例的清理或废止要设定一定的条件限制,只有判例在出现以下情形的时候才能启动清理或废止的程序。大体上讲,主要包括两种情形:要么判例完成任务,已经过时,而与新的情况或局势格格不入;要么判例本身在内容上存在缺陷,或与法律之间存在冲突。
《实施细则》第12条规定了两种情形下指导性案例失去指导作用:第一种情形,指导性案例与新的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司法解释相冲突。在我国,指导性案例具有一种接近法源或准法源的地位,但它仍然与作为正式法源的成文法存在本质性差异。如果指导性案例与新的成文法内容出现冲突,其效力自然无法压倒成文法的规定。第二种情形,是为新的指导性案例所取代。指导性案例之间出现观点冲突的情形难以避免,如果针对同一个法律问题,新的指导性案例改变了在先的指导性案例的观点,那么旧有的指导性案例将会失去效力。在以上两种情形下,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展开清理和废止工作。
《规定》第19条明确列举了宣告失效的几种情形,分别是:(1)案例援引的法律或者司法解释废止;(2)与新颁布的法律或者司法解释冲突;(3)被新发布的指导性案例取代;(4)其他应当宣告失效的情形。具体来说,第一种情形是指导性案例做出的成文法依据丧失了,因此其继续存在的正当理由也就不复存在了;第二种情形是与新的成文法相冲突,其所蕴含的裁判观点已被新的权威性观点所取代;第三种情形实质上是旧有的指导性案例所蕴含的裁判观点被新案例中表达的观点所取代,同样也就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此外还有一个兜底性条款,比如指导性案例疏漏了非常重要的事实,结果导致法律的适用出现严重的错误,在指导性案例出现或存在这种实质性缺陷的情况下,也可以成为宣告该案例失效的一个重要理由。
从普通法系的实践经验来看,推翻先例的理由也涉及很多方面。布莱恩·A.加纳(Bryan A.Garner)详细地提出了六种可能性理由,包括:第一,先例判决与明确的法律原则出现冲突;第二,先例裁决是单个的,做出来之后一直未被适用或参照过;第三,法院对于某个重要问题的判决现在遭到了严重的质疑(seriously doubted);第四,先例裁决作出时的客观情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第五,被推翻的先例尚未建立起重要的信赖利益;第六,尽管推翻先例可能会影响到一些个体的或私人的权利,但是它首先出现了错误,它产生了普遍的不正义。8See Bryan A. Garner eds., Law of Judicial Precedent, Thomson West, 2016, pp.396-401.英国学者尼尔·达克斯伯里(Neil Duxbury)也介绍了推翻先例的两点重要理由:首先,最明显的一种是下级法院在创制先例时犯了错误,这是针对上级对下级法院发布的判例而言的。但是,如果是涉及推翻自己的判例,或者推翻同级法院的判例时,则会是一个更加棘手的问题,此时不仅要确认出现错误,而且要有十足的把握认为这是个“足够清楚的错误”(clearly wrong)。其次,有的时候法院在推翻先例时,可能还需要有更强的理由。比如说,很确信推翻错误的先例将会给法律带来一种整体的改进,哪怕有时候只是一丁点的改进。又比如说,所期待实现的改进是单靠立法干预所无法实现的。9See Neil Duxbury, The Nature and Authority of Preceden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118-119.由于推翻先例在普通法中已经进入法官造法的范畴,所以实践中往往会对这种行为施加非常严格的限制。
(三)清理或废止判例的程序
清理或废止判例不是任意进行的,除需要满足以上诸种条件之外,还意味着这种活动应遵循一定的程序或步骤。就目前关于指导性案例的规范性文件来看,无论是针对法院还是检察院的指导性案例的清理或废止,都尚无明确、直接的规定。
此前学者们曾争议过,对于指导性案例的废止,是否应该经过一个特别确认的程序,还是将这个问题留待后案的法官根据具体情形自行定夺?对此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指导性案例的废止应由发布机构根据下级法院、当事人的申请,或者依职权予以废止,在废止的程序上应当同确定指导性案例的过程一样规范,并加以公布;第二种观点认为,指导性案例的废止应采自然死亡规则,无须经过专门的废止程序,旧的指导性案例与新的指导性案例相冲突的自然失去效力。”10参见胡云腾、于同志:《案例指导制度若干重大疑难争议问题研究》,载《法学研究》2008年第6期。笔者赞同第一种观点,理由在于:第一,中国的法官、司法制度与普通法系存在很大差异,法官无权自行宣布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导性案例无效;第二,指导性案例的清理或废止属于广义的指导性案例的编纂范畴,既然对于指导性案例的选编已经设定了一些严格、明确的程序,那么对指导性案例的废止自然也要采取同等严格的程序;第三,如果采取自然废止论,难题在于谁来判断前后指导性案例是矛盾的或冲突的,何种矛盾或冲突能够足以导致其中一个彻底失去效力,如果将这些问题完全交给后案中法官自行判断和决定,难免会造成认识和判断不统一的混乱局面。
鉴于此,笔者倾向于主张应为指导性案例的废止设立一套程序规则。以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导性案例为例,可以在借鉴指导性案例选编程序的基础上提出一些基本的构想。根据《实施细则》第4—8条的规定,清理或废止指导性案例的程序应大体上包含以下内容:第一,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统一行使清理或废止指导性案例的权力;第二,各级法院、案例指导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陪审员、专家学者、律师、当事人,以及其他关心人民法院审判、执行工作的社会各界人士,认为指导性案例符合废止条件的,均可以向案例指导办公室提出废止建议;第三,应该提出书面的废止理由;第四,被提出废止请求的指导性案例由案例指导办公室按照程序报送审核。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的印发各高级人民法院,并在《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人民法院报》和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公布。
对于指导性案例的推翻活动,在普通法系国家并无明确的程序限制,而是采取由法官个人自主决定的模式。这种模式对法官个人的职业素养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尤其是要求对遵循先例的原则有足够深的认识和运用。此外,这种推翻还会受到整个法律职业共同体的监督。即便如此,在推翻先例的问题上,实践中还是形成了一些共识性的限制规则,这里我们只介绍一个比较具有代表性也很重要的规则,即推翻先例前的评估和权衡程序。法院需要评估推翻旧有先例、创制新的先例,是否能够阻止造成更大的危险,这种评估将是一个略显复杂的活动过程。11See Douglas E. Edlin, Common Law The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49.同时这也是一个权衡利弊的过程,权衡维持旧先例与坚持适用新先例哪一种做法利大于弊,只有确证坚持适用新的先例能够在整体上带来更小危害时,推翻先例才具有了一种初始的正当性理由。用加纳的话来说,即便是推翻了先例,其所带来的伤害也必须要小于继续维持先例所可能带来的伤害。12See Bryan A. Garner eds., Law of Judicial Precedent. Thomson West, 2016, p.388.进行利益的评估和权衡,构成了法官在推翻先例前通常要履行的一个程序。由于两大法系的司法制度、法官思维等的不同,中国案例制度中应设立一套严格的清理和废止程序。
三、对指导性案例的规避适用
广义的判例退出机制,除了判例清理和判例废止这一专门化的行动之外,还包括审判实践中法官对于判例的规避适用。它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法律适用活动,有智慧的法官会设法规避一个不恰当、不相关或有问题的判例,同时尽可能找到一个与眼前争议案件真正相关、相似的案件,这也一直被认为是普通法之精妙或灵活性之所在。在构建我国特色案例指导制度的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块内容就是引导法官合理地规避对指导性案例的适用,从而确保在个案中真正地实现裁判正义。在大陆法系国家,下级法院一般不能推翻上级法院的判例,但是实践中却可以基于一些理由偏离上级法院的判例,比如说,为了更加严格地遵守法典或成文法文本,或者是为了在特定个案中实现正义或贯彻某项政策而不得已偏离某个先例中的解释。据调查显示,芬兰、西班牙、瑞士的下级法院很少偏离上级法院的判决,但是一旦做了,他们往往倾向于以一种明示的方式进行。13See Neil MacCormick and Robert S. Summers eds, Interpreting Precedents: A Comparative Study, Dartmouth Publishing Company Limited, 1997, p.523.我们这里的讨论主要关注,法官在对指导性案例的规避适用过程中,是否需要借鉴德国建立一种特殊的判例偏离的报告制度?规避适用的实质条件(理由)有哪些?规避适用判例是否需要遵循某些程序性的规则(形式性要件)?
(一)不宜建立背离判例的“报告制度”
前文提及在推翻先例的问题上,普通法系采取了法官自主的模式,在规避适用判例的问题上将决定权交给作为裁判者的法官个人。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德国建立了一种独具特色的判例偏离的报告制度。在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判例可以看作行使宪法解释或违宪审查权的结果,因而具有正式的法律约束力,并能够成为正式的法律渊源,各级法院在审理类似案件时应像遵守法律一样遵守这些判例。除此之外的其他法院的判例,并不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而只具有事实上的拘束力。尽管如此,由于各种原因,“联邦最高法院的判例几乎总是得到下级法院的遵循。类似地,州法院的判例也几乎总是得到本州下级法院的遵循,并且也经常得到其他州的下级法院的遵循。而本州的其他法院或其他州的州法院至少也会参考这些判例。地区法院的判例几乎总是得到本地区的基层法院的遵循”。14张骐等:《中国司法先例与案例指导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97页。由于判例所蕴含的重要价值,法律职业共同体对判例在实践中的功能和作用达成了共识,因此实践中法官对于判例的偏离或规避适用就不应当是随意的。
这里应先予以澄清的是,联邦宪法法院的判决由于对所有法院都具有正式拘束力,因此即使其他法院认为联邦宪法法院的判决有误仍无权随意偏离之。对于其他法院的判例,比如联邦法院的判例,如欲偏离则应履行报告义务。这一制度被规定在《德国法院组织法》以及其他程序法中。具体而言,包括这样三种偏离情况:第一,在联邦一级法院体系中,如果五个联邦最高法院的某个法院想要偏离另一个最高法院的判决,则需将分歧提交至最高法院联合大审判庭;第二,在联邦最高法院内部,如果联邦最高法院的某个审判庭想偏离另一个审判庭的判例,则需要将分歧提交至大审判庭;第三,如果一个州高等法院想要偏离另一个州高等法院或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则需要将案件提交至联邦最高法院。15参见高尚:《论德国法中偏离判例的报告制度》,载《法律适用》2017年第2期。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并不是在所有的情况下都可以产生偏离判例的报告义务,有两项条件特别值得重视或考虑:其一,发生偏离所涉及的问题必须是法律问题,对于事实问题所产生的分歧或争议一般不会产生偏离报告义务;其二,仅就法律问题而言,一个判决中所涉及的法律问题有时候是复数的,但并不是就其中每一个问题都可以产生偏离的报告义务,通常能够产生偏离报告义务的仅仅是其中对判决而言具有根本重要性或决定性的难题。16参见陈兴良主编:《中国案例指导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723—724页。为对特定判例的偏离设定一项强制性的报告义务,目的是确保法院能够尊重那些在审判实践中所累积形成的“持续一致的见解”,促进法律的统一适用和实现类似案件类似审判。
除此之外,在相关主体漠视这一报告义务而任意背离判例时,法律也设立了一套救济和监督机制。比如说,“如果联邦最高法院审判委员会或者州高等法院在发生判决偏离的场合,违背了《德国法院组织法》的规定的报告义务,则可以针对该判决提起宪政抗告,原因在于此种条件下基本法所规定的当事人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遭到了侵犯”。17同上注,第726页。设立这样一整套的程序,目的在于限制专断的司法自由裁量权,维护法律体系的一致性和可预测性。如果容许法官任意背离已经存在的判例,或者说对于偏离判例作出一种不妥当的解释或安排,那么法官将不会以“类规则推理的方式”(rule-like fashion)来解释或适用判例,因此会牺牲掉作为合法性价值的实质法治,会丧失客观性、确定性以及平等性等。同时允许任意偏离,会使整个法律体系变得效率低下,法官需要每一次都重新考虑、解释、权衡案件的争论点,即便是类似的案件也可能被以一种不类似的方式处理,这违背了遵循先例的基本要义,付出的成本会比较高,可能会产生更多的诉讼、需要更多的律师、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和物力。18See Neil MacCormick and Robert S. Summers eds., Interpreting Precedents: A Comparative Study, Dartmouth Publishing Company Limited, 1997, pp.526, 520.德国独具特色的判例偏离报告制度带给我们的最大启发,就是要为偏离判例设立一套程序性规则。
至于这样一套程序规则是什么,是不是一定要建构一套类似于德国的报告制度,则是另外一个问题。依据笔者的观察,德国的判例偏离报告制度与德国复杂的法院体系、三审审级制以及违宪审查制度等联系在一起,它的产生有着特定的司法传统和法律背景。在我国,不宜采纳一种类似于德国的判例偏离的报告制度。理由如下:
第一,我国指导性案例并非正式法源,不具有严格法律意义上的拘束力。其事实性拘束力源自于两个层面:一个是形式层面的,它是由最高人民法院经过特定程序加以遴选、讨论和公布的,具有一定的外在权威形式;另一个是实质层面的,指导性案例本身判决观点正确或提出了正确的实质性理由,而说服后案法官在审理类似案件时对自己加以参照。19参见张骐:《再论指导性案例效力的性质与保证》,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3年第1期。对于指导性案例的背离,虽说不像对法律的背离那样要求严格地加以限制,但这种背离行为也不应是随意的。这体现为,法官在决定规避适用指导性案例时,应对自己的决定行为提供充分的理由加以论证。这种说理的义务或责任,所要服务的目的或起到的作用其实和德国偏离判例的报告制度是一致的,只不过后者有专门的法定程序加以保障和实施。
第二,德国设立专门的偏离报告制度,目的是为了确保三审法院内部的司法统一。根据《德国法院组织法》的规定,审判庭提交至“联合审判庭”或“大民事审判庭”的案件主要包括“基于观点分歧的提交”与“基于原则性意义的提交”两大类:前者主要针对具体的法律问题,并且产生强制性的提交义务;后者针对的主要是具有原则性意义的法律问题,并且审判庭可以自行斟酌是否将其进行提交,通常如果认为提交可以促进法律的发展或统一司法便会选择提交。20参见卢佩:《司法如何统一——以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判例为实证分析对象》,载《当代法学》2014年第6期。这一套制度设立的目的,首先并不主要是为规范判例偏离行为本身,而是为了解决最高法院内部的意见分歧。21参见曹志勋:《论指导性案例的“参照”效力及其裁判技术》,载《比较法研究》2016年第6期。在我国,为了解决法院内部不同意见的做法有很多,典型的比如审委会集体讨论、审判长联席会议制度、个案请示与批复制度等。22参见孙海波:《疑难案件裁判的中国特点:经验与实证》,载《东方法学》2017年第4期。故而,在这些制度之外并无专门再设立一种偏离判例报告制度的必要。
第三,这一制度的冗余性还在于,如果偏离判例的行为都要上报最高人民法院,这一方面随着指导性案例数量的激增,会加大审理法官和最高法院的负担;另一方面也会进一步加剧司法的行政化色彩。23参见曹志勋:《论指导性案例的“参照”效力及其裁判技术》,载《比较法研究》2016年第6期。对于法院如何将争议问题或案件层层上报给最高人民法院,实践中已经形成了独特的做法,专门增设判例偏离报告制度也势必会与三大诉讼法在某些规定方面出现不一致之处,增加协调成本。除此之外,在司法责任制改革的背景下,2018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的实施意见》,其中第9条规定:“各级人民法院应当在完善类案参考、裁判指引等工作机制基础上,建立类案及关联案件强制检索机制,确保类案裁判标准统一、法律适用统一。存在法律适用争议或者‘类案不同判’可能的案件,承办法官应当制作关联案件和类案检索报告,并在合议庭评议或者专业法官会议讨论时说明。”这一规定将类案的检索与参照当作一种司法义务,也可以有力地对法官任意偏离判例的行为构成一种客观的限制。
综上,德国偏离判例的报告制度对思考指导性案例退出机制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但是考虑到这一制度产生的制度和法律背景,以及其所承载的独特目的和功能,在我国不宜直接建立一种类似的制度。
(二)规避适用指导性案例的实质理由
有学者认为司法裁判公正的品质,源自于法官如下的三个承诺:对正义目的的承诺、对司法职业主义的承诺以及对理性裁判方法的承诺。就最后一点而言,一种科学的裁判方法要求法官必须对其裁判结论提供理由加以证立。24See John W. McCormac, "Reason Comes Before Decision", Ohio State Law Journal, Vol. 55, No.1 (1994), pp.161-166.正如古老法谚所表达的,“无理由即无判决”,法官不仅应为其裁判提供理由,而且从逻辑上理由还应走在结论之前。如果法官在偏离决定作出之前,未提供理由或提供的理由不够充分,那么这种对判例的规避行为就是一种不正当的规避。这里我们仍以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导性案例为例,谈谈规避适用的主要理由可能有哪些,其中部分可能与清理或废止指导性案例的情形存在交叉。
1.指导性案例已经过时
最高人民法院在遴选和编纂案例的过程中,不仅要考虑案例本身的典型性与代表性,同时还要考虑判决的法律效果、社会效果以及政治效果等。案例指导制度在维护社会稳定和促进社会和谐方面能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这尤其体现在指导性案例所具有的政策性功能方面,“指导性案例既反映了最高人民法院对于样板案件裁决的认可,也反映了最高人民法院对样板案件的选择与‘修饰’,尤其是基于司法政策考量的选择与‘修饰’。一个原生效判决之所以能够作为样板被选择成为指导性案例,并且在成为指导性案例过程中之所以被如此非彼地加工,其中体现了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政策的倾向性”。25王绍喜:《指导性案例的政策引导功能》,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8年第5期。典型的如:指导性案例第4号“王志才故意杀人案”就旨在明确判处死缓并限制减刑的具体条件,从而贯彻少杀慎杀、宽严相济的死刑政策;指导性案例第89号“‘北雁云依’诉济南市公安局历下区分局燕山派出所公安行政登记案”,该案判决理由之一是公民任意创设姓名会增加社会管理成本、降低社会管理效率,可以说具有十分鲜明的政策性色彩。
普通法法系的学者在论及遵循先例原则时也提到,“遵循先例原则有一个很强的预设,即不应推翻先前的裁决,但是它并不禁止这样的实践。如果一个法院打算改变法律,它可以基于政策性的理由这么做”。26Kenneth J. Vandevelde, Thinking Like A Lawyer: An Introduction to Legal Reasoning, Second Edition, Westview Press,2011, p.131.伴随着政策的改变,在过去特定时期特定政策背景下选编的指导性案例将会失去继续存在的客观依据,而变成一种过时的东西。比如说,假定在未来国家放开对公民选择姓名权的限制,像“王者荣耀”“北雁云依”这种名字也很难说就真的在实质性意义上危害到公序良俗价值,那么伴随着国家政策的变化,指导性案例第89号便会过时而退出历史舞台。对于过时的指导性案例,在尚未被相关机关清理之前,法官可以通过规避适用来偏离它。
2.内容存在实质性缺陷
在普通法系的司法实践中,下级法院的法官不具有推翻上级法院判例的权力,因而在实践中遇到内容上有缺陷的判例时,可以选择区分(distinguishing)或规避适用。同样的道理,当指导性案例在实质内容上存在缺陷时,法官没有义务去重复或复制过去的不正义。大体说来,这些缺陷可能包括:
(1)指导性案例在事实认定方面,遗漏掉或错误地归纳了案件中的一个或多个关键性事实(material fact),也就意味着法官对于案件的基本认定存在严重失误,这进一步导致法律适用出现错误。对于这种由事实认定错误导致后续法律适用出现错误的情形,显然属于内容方面的实质性缺陷。
(2)在法律适用以及裁判理由论证方面出现问题。单纯的适用法律错误可能实践中并不是非常常见,但是在判决证成方面可能经常会出现问题,而判决的证成与对法律的理解和适用往往又是联系在一起的。仍以指导性案例第89号为例,为了证明“北雁云依”这个姓名不合法,法官机械地套用了相关立法解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99条第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22条的解释》)的规定,认为“北雁云依”这个姓名的选取不符合司法解释所允许的两种情况,即选取其他直系长辈血亲的姓氏,或因由法定扶养人以外的人扶养而选取扶养人姓氏。而仅凭个人喜好愿望并创设姓氏不符合立法解释第2款第3项(有不违反公序良俗的其他正当理由。少数民族公民的姓氏可以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的情形,因此不应获得支持。仔细推敲这一论证显得非常粗糙,法院似乎并未集中力量讨论这种行为到底有没有违背公序良俗,而只是简单下了一个结论,并未提供实质性的充分理由。27这一点笔者受到了南京大学法学院陈坤教授的启发,在此特别予以感谢。因此,单从这一点来看,这个判例在实质论证上便存在缺陷。
(3)指导性案例的内容或蕴含的裁判规则与法律相冲突。其中,可能会具体涉及这样几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指导性案例与基本的法律原则出现冲突;其二,指导性案例与新发布的法律、行政法规或司法解释相互冲突。这两种情况属于两种不同性质的法律渊源之间的冲突,指导性案例是一种非正式的、辅助性的法律渊源,而法律原则、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司法解释均是正式性法律渊源,指导性案例的参照要求自然会被后一种更强的权威性理由所凌驾。或者借用一些学者的话说,原有指导性案例的裁判规则已经被制定法所直接吸收、推翻或替代了。28参见于同志:《论指导性案例的参照适用》,载《人民司法》2013年第7期。在以上这样几种情形下,由于指导性案例在内容上所出现的实质性缺陷,因而给法官规避适用它们创造了理由。
3.指导性案例之间相互冲突
针对同一个法律问题,在不同时期可能会形成数个不同的指导性案例,而这些案例之间在法律观点上可能会出现不一致。法官需要根据具体情况作出判断,然后在它们之间择一选择适用。指导性案例出现冲突,一般的选择规则是在后的指导性案例效力优先于在前的指导性案例,这是因为后来者往往代表最新的裁判观点和立场,但也并非绝对如此。如果后来的指导性案例存在先天缺陷,比如存在前面所讲的各种缺陷,那么法官仍然可以选择在先的指导性案例进行参照裁判。因此,当数个指导性案例发生冲突时,法官究竟应选择何者来参照,还是需要结合具体情况进行判断。
4.实质不相似或不相干
最后一点理由,也构成了实践中法官规避适用指导性案例的常见理由,即眼前待决案件与指导性案例在实质上并不相似或不相关。29参见何家弘:《外国司法判例制度》,中国法制出版社2014年版,第94页。待决案件与指导性案例具有实质相似性,才是参照指导性案例进行裁判的合理前提。在实践中,可能会面临这样两种情况:第一种,当事人主动提出了一个可能相关或相似的案件,法院经过审查、判断,认为两案之间在实质上并不相似,可以采取规避适用的决定;第二种,法院主动提出一个可能相似或相关的指导性案例,当事人一方提出充分的理由加以反驳,认为该指导性案例与待决案件之间并不实质相似,法院经过审查同意的,作出规避适用指导性案例的决定。普通法系中的“区分先例”的运作,也恰恰是以此为基础和根据的。
(三)不当规避适用指导性案例的形式
自案例指导制度确立以来,中国法官在实践中已经开始尝试参照或援用指导案例。据相关统计显示,截至2018年12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共发布的20批106例指导性案例中,已有78例在实践中被参照,还有28例尚未被援引过,与2017年同期(60例)相比,被应用的指导性案例数量增加了18例。30参见《重磅!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司法应用报告(2018)》,载“北大法宝”微信公号,2019年4月1日。笔者曾将当下中国法官参照适用指导性案例的实践格局归纳为六个方面的特征:使用的加速性、提出方式多样化、断裂性、不规范性、间接性以及当事人主导型。31参见孙海波:《论指导性案例使用的特点与难点》,载高鸿钧主编:《中国比较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19—328页。其中指导性案例使用的不规范性问题特别值得注意,这种不规范性又包括:对指导性案例的性质认识存在误区、只关注指导性案例的形式而疏忽其实质内容、任意启动对指导性案例的使用、漠视或参照指导性案例的随意性等。32参见孙海波:《论指导性案例的使用与滥用——一种经验主义视角的考察》,载舒国滢主编:《法学方法论论丛》(第3卷),中国法制出版社2015年版,第233—240页。这里我们也来简要讨论一下,在规避使用指导性案例的实践中存在哪些不规范的现象或形式。
1.对指导性案例效力性质的认识存在错误
指导性案例毕竟不同于一般的判决,它是经过特定的程序从判决中遴选出来的、具有较强代表性、能够发挥一定指导性作用的案例。同时,不得不承认,指导性案例在效力性质上又不同于普通法系中的先例。因而,它更像是一种介于普通判决与作为正式法源之先例之间的一种过渡性存在,以至于某些学者称其为“准法源”,“是中国法院在司法裁判中基于附属的制度性权威并具有弱规范拘束力的裁判依据,因此既不同于判例在普通法系中的法源地位,也不同于判例在民法法系中被作为非法源来对待的境遇,而是走的中间道路”。33雷磊:《指导性案例法源地位再反思》,载《中国法学》2015年第1期。由于指导性案例形成所具有的制度性权威和实质性权威,使法官在背离或规避指导性的时候不能是任意的。然而实践中,我们注意到一些法官仍然以我国不是判例法国家,成文法是唯一正式性法律渊源为由,拒绝在裁判实践中参照或援用当事人一方所提供的指导性案例,这样一种做法明显就是误解了指导性案例的效力性质。另外,笔者在基层法院调研中还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如果上级法院的指导性案例与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导性案例相冲突时,基层法院更倾向于参照上级人民法院的典型案例,这主要是由于上诉审的存在,上级法院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决定自己的案件在上诉审中是否会被改判。
2.形式上规避而实质上隐性适用
指导性案例的适用,本质上属于案例推理或判例推理,这依赖于一套复杂的归纳性思维,由于中国法官很少系统地接受过这方面的训练,加上中国判决书格式的特定结构没有为判例推理和说理创造出比较好的条件,使实践中法官即便认为某个指导性案例具有可参考性仍选择形式上规避,但暗中参照该指导性案例的裁判结果或裁判精神的方式。笔者将这种做法称为“隐性适用”,其背后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这种隐性适用,在形式上规避本该加以参照的指导性案例,至少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它仅仅将指导性案例当作达到某些目的的工具或手段,只注重案例的形式而不关心其内在的实质,因此本质上是一种工具化的案例适用观;其次,它人为地遮蔽和扭曲了案例适用的过程和事实,指导性案例与待决案件事实之间的比对、相似性判断、运用案例进行推理和说理等活动均被掩饰,使这种活动无法接受法律共同体的约束;最后,隐性适用还是一种司法虚饰的表现,违背了法官诚信裁判(judging in good faith)的基本要求。34参见孙海波:《指导性案例的隐性适用及其矫正》,载《环球法律评论》2018年第2期。与隐性适用这种做法相对的是,如果实践中存在本该参照的指导性案例,尤其是当事人一方提出某个指导性案例要求法院加以参照时,法官负有强制性的回应义务,这一点在《实施细则》中有所规定,如果拒绝参照或援引该指导性案例,法官必须履行说理和论证的义务。
以上,便是规避适用指导案例实践中的两种较为常见的不规范做法。德国学者阿列克西(Robert Alexy)曾提出过判例适用的两条规则:(1)当一项判例可以引证来支持或反对某一裁决时,则必须引证之;(2)谁想偏离某个判例,则承受论证负担。35参见[德]阿列克西:《法律论证理论:作为法律证立理论的理性论辩理论》,舒国滢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341页。归结为一句话,无论法官是选择参照还是拒绝援用判例,都必须对自己的决定提供理由加以论证。尤其是在规避适用指导性案例时,必须以明示的方式回应:究竟指导性案例出现了以上所讨论的哪一种情形,不宜在判决中加以参照或援用。
四、初步的结论
卡多佐(Cardozo)曾提醒人们必须牢记:“法律的确定性并非追求的唯一价值,实现它可能会付出过高的代价。法律永远静止不动与永远不断变动一样危险,妥协是法律成长原则中很重要的一条。”36Benjamin N. Cardozo, The Growth of the Law,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24, p.17.指导性案例的退出机制,便是协调法律体系稳定性与灵活性的重要桥梁。离开了退出机制,案例指导制度将失去鲜活的生命力。同时,如果允许过时的或有缺陷的指导性案例继续存在并发挥效力,势必会在个案裁判中导致种种不正义。即便在判例作为正式法律渊源的普通法系国家,也不得强迫法官去遵循一个有问题或有实质性缺陷的判例,法官也没有义务去复制过去的某种不正义。至此,对于指导性案例的退出机制问题,我们大致可以形成这样几点初步的结论:
第一,要正确对待指导案例的退出机制,它是案例指导综合体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这一制度的存在并不是要从根本上取消或摧毁案例指导制度,而是要通过不断将过时的或有缺陷的指导性案例加以清理或废止,或者赋予法官在案例参照实践中灵活规避不相关或不相似案例的权力,为案例制度的健康发展和顺利运行不断注入新生的力量,也让案例指导制度真正成为一个动态的、不断向前循环和发展的制度。
第二,在我国不宜专门建立一种类似于德国的判例偏离报告的制度。在德国这一制度的重要价值在于统一最高法院内部的司法意见,而非规范偏离判例的行为本身。同时,该制度的产生是与德国复杂的法院体系、三审终审的复杂审级制度联系在一起的。在我国,已有类似制度能够发挥判例偏离报告制度的功能。除此之外,如果允许实践中法官在决定是否偏离或规避适用指导性案例时都向最高人民法院提交报告,这不仅会严重加剧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负担、浪费司法资源,而且还会不可避免地造成与三大诉讼法之间在对接协调上的困难与冲突。
第三,法律适用者应负论证之义务,无论是专门主体对指导性案例进行清理或废止,还是在裁判实践中个体法官决定偏离或规避适用指导性案例,都必须对自己的决定提供充分的理由加以论证,其通常既包括形式层面(程序性)的,也包括实质层面的各种理由。否则在不加论证或说理的情况下,任意清理或规避适用指导性案例的做法,都将是恣意、专断的,需要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
第四,无论是对指导性案例的清理或废止,还是在个案裁判中对指导性案例的规避适用,目的都是为了激活案例指导制度的生命力。到目前为止,由于指导性案例的数量仍相对有限,清理或废止的活动还尚未真正实践过。但是伴随着人们“判例意识”的增强,相关主体在实践中应用指导性案例的实践活动会越来越成熟。如何正当地规避不相干或不合适的指导性案例,成为一个非常具有现实性的议题。这既有赖于整个法律职业共同体的监督,也有赖于法官自身职业素养的提高,此外还依赖于一定的责任监督机制的确立,不当废止或规避指导性案例的行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