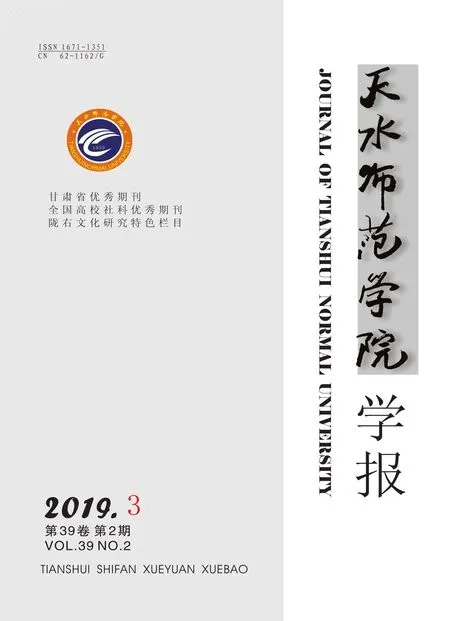庐山净土思想与六朝诗创作观探析
——以咏物诗为例
2019-01-21钟志强
钟志强
(南昌师范学院 文学院,江西 南昌330032)
庐山净土思想对六朝诗歌创作观念有独特影响,是研究佛教与诗学关系的重要部分,而学界相关研究尚不充分。普遍信仰净土思想的六朝文士,其审美情趣和创作实践一定程度上受到净土思想的影响。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拟从净土像化思想、简易的修行法门、生死轮回观三方面阐述庐山净土思想对六朝咏物诗意象、文风等方面创作观念的影响。
一、净土像化与“重象”创作观
佛教因拜佛像的缘故,被称为“像教”。而本文所说“像化”即指佛教(像教)之教化。这与佛经中诸神佛、菩萨为了普度众生,以方便智慧之法,通过变化成不同的形象,假名说众生以因果,导人向善有关。《大方等大集经》即载:“是菩萨作种种神通变化,以是神通为化众生。……化众生故作是示现,示现是已,随其所应而为说法。”[1]净土诸经为坚定信仰者勤奉佛法,较其他宗派更为注重对阿弥陀佛佛像及其所居之西方极乐净土的描述和铺陈。如《佛说无量寿经》曰:
佛言:“成佛已来凡历十劫。其佛国土自然七宝——金、银、琉璃、珊瑚、琥珀、车璩、玛瑙——合成为地,恢廓旷荡不可限极。悉相杂厕,转相入间,光赫焜耀,微妙奇丽,清净庄严超踰十方一切世界众宝中精,其宝犹如第六天宝。……又其国土,七宝诸树周满世界——金树、银树、琉璃树、颇梨树、珊瑚树、玛瑙树、车璩树——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共合成。”[2]270
慧远的著作中含“象”(像)之意的词汇有:象、像、相、形、仪、容、迹、名、实、物、体、影、器、境、法身、法相、圣体、色身、变化身、涅槃等。相较于当世别的高僧,慧远本人对佛之象(法身)很是执着。如:
远问曰:“佛于法身中为菩萨说经,法身菩萨乃能见之,如此则有四大五根。若然者,与色身复何差别,而云法身耶?经云法身无去无来,无有起灭,泥洹同像,云何可见?”[3]70
远问曰:“众经说佛形,皆云身相具足,光明彻照,端正无比,披服德式,即是沙门法像。真法身者,可类此乎?……将何所引,而有斯形?”[3]80-81
因此,慧远主张心中观想佛之相好与功德的观想念佛。较其他宗派,慧远代表的庐山净土思想对佛的法身更加执着。这种思想若反映在文学上,则可视为其更加注重“具象”的作用。因为欲求佛理需借可感之物(如佛之相好)为方便的接引,所以诗歌创作则需通过具象发挥作用。其《念佛三昧诗集序》曰:
夫称三昧者何?思专想寂之谓也。……故令入斯定者,昧然忘知,即所缘以成鉴。鉴明则内照交映而万像生焉,非耳目之所暨而闻见行焉。于是,睹乎渊凝虚镜之体,则悟灵相湛一,清明自然;察夫玄音之叩心听,则尘累每消,滞情融朗。[3]30
我们可通过慧远早期一首以佛像为吟咏对象之作——《襄阳丈六金像赞》为例来阐述其这种“由象至意”的创作观念。其文曰:
堂堂天师,明明远度。陵迈群萃,超然先悟。慧在恬虚,妙不以数。
感时而兴,应世成务。金颜映发,奇相晖布。肃肃灵仪,峨峨神步。
茫茫造物,玄运冥驰。伟哉释迦,与化推移!静也渊默,动也天随。
绵绵远御,亹亹长縻。反宗无像,光潜影离。仰慕千载,是拟是仪。[3]40
按诗歌主体内容看,诗人并未描摹出佛之具体相貌。如其文所言“反宗无像,光潜影离”。虽言“无像”,但重点仍是借“像”宣扬佛理和功德——仰慕千载,是拟是仪。我以为,慧远虽受玄学影响,但与玄学提倡的“得意忘言”不同。就诗歌意象而言,物象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有重要的中介作用。它并非后世那种遗形取神的重“神似”的创作思想。中国传统思想中的“象”思维,与慧远论“神”的实有思想,既对慧远创作中“象境”思想的产生有重要影响,也无形中影响了六朝诗人的创作观。
钱志熙《魏晋诗歌艺术原论》曾说:“一般说,东晋前中期山水观照中玄鉴和朗鉴的特点,与晋宋之际的范山模水、钻情草木差异较大,体现了不同时期的不同的山水观照风格,造成不同的山水美。”[4]我们认为,生活于晋末的庐山慧远与当世文人多有交集,庐山净土的像化思想或与晋宋以来“文贵形似”的诗歌创作风潮不无关系。如此期以谢灵运诗作为代表的山水诗多被人诟病篇末“玄言的尾巴”、程式化而缺乏真情等。这种影响自然波及了咏物诗的创作。如晋代许询《竹扇诗》和习凿齿《灯》:
良工眇芳林,妙思触物骋。篾疑秋蝉翼,团取望舒景。[5]894
煌煌闲夜灯,修修树间亮。灯随风炜烨,风与灯升降。[5]922
上述二诗的创作主旨当然不是仅仅描摹中心“物”象,而是借“竹扇”和“灯”来阐发玄理。但我们发现这种咏物诗较魏晋以前的同类作品更加注重描摹物象,出现向“赋物诗”[6]创作风潮过渡的倾向。罗宗强先生认为:“始于晋宋之际而迄于山水诗形成,因人化自然成为人的‘无机体’,自然‘物’便获得了独立的审美价值。反映在文学创作上就是山水、咏物等题材大量进入诗文,并‘追求一种写实倾向’。”[7]这段时期以曹毗《霖雨诗》、王韶之《咏雪离合诗》、袁淑《咏寒雪诗》等为代表直接描摹物象为主体的咏物之作大量出现,这类诗作难以再寻觅玄理的踪迹,自然之景与“物”甚至已成为艺术表现领域的独立审美对象。
我们认为,以慧远为代表的庐山净土思想较其他宗派更执着于佛之法身、相好,其对玄学等中土思想的吸收和本质上的区别,僧人和当世诗人的交往形成的传播力,(如慧远与谢灵运)对“物象”成为诗歌表现领域的独立审美对象的出现存在一定的影响。
二、简明法门与省净诗风
佛教净土虽有弥勒净土与弥陀净土之别,但二者之净土世界都是皎洁清净的所在。《菩萨本行经》称:“由如来过去心净离著,不害众生,故所行之处,脚足不污,虫蚁不损。……菩萨在干土山中经行,土不著足。”六朝信仰净土思想的文人很自然会将净土世界的佛、菩萨作为效仿之榜样。对于经玄风洗礼过的六朝士人而言,“求精求真、以少总多”而非繁缛绮语才是含文学创作在内的处世之道。达成此道只需做到两点:其一是净心,其二以最简便方式修行。如《佛说无量寿经》曰:
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无量寿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寿终时,无量寿佛,与诸大众,现其人前,即随彼佛,往生其国。[2]272
若有众生,闻其(阿弥陀佛)光明威神功德,日夜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国。[2]270
比起弥勒净土等需成就唯识心定等高难度的门槛而言,弥陀净土的法门则简便易行:第一,听闻阿弥陀佛名号而常修梵行;第二,听闻阿弥陀佛的神威功德,不断称说;第三,发菩提心,专念阿弥陀佛,并修功德。需说明的是,以上三点提及的“修功德”并不是一定要布施大量财物而是只要下定决心,则人人可行的标准。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执持名号,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一心不乱,其人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与诸圣众,现在其前。其人临命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2]347
也就是说,只要连续七天称念阿弥陀佛,即可见到阿弥陀佛,死后即往生西方净土极乐世界。如此简易而不繁琐的修行方式辅之以净心发愿就能最终成佛,自然容易吸引大量信众。而六朝士人广泛信仰的净土思想的“简易求真”无疑在文坛也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这个反响就是诗人创作诗歌形成了追求简易明快、省净的诗风。这从当世的文学批评中亦可看出端倪。如:
沈隐侯曰:“文章当从三易:易见事,一也;易识字,二也;易读诵,三也。”邢子才常曰:“沈侯文章,用事不使人觉,若胸臆语也。”深以此服之。祖孝徵亦尝谓吾曰:“沈诗云:‘崖倾护石髓。’此岂似用事邪?”[8]
南朝文坛否定繁缛的文风,称之为“绮语”。“绮语”于南朝文论术语中可指繁缛的文风。可见于《文心雕龙》,如《明诗》曰:“晋世群才,稍入轻绮,张潘左陆,比肩诗衙。采褥于正始,力柔于建安。”又《情采》有言:“韩非云:‘艳乎辩说’,谓绮丽也。绮丽以艳说,藻饰以辩雕,文辞之变,于斯极也。”又《诠赋》云:“景纯绮巧,缛理有余。”其本源于佛教用语,是净土理论常出现的概念,被视为四大口业之一。如《法苑珠林·弥勒部》中引《敬福论》称:“身三过:杀、盗、淫。口四过:妄言、绮语、两舌、恋口。意三过:谓贪、镇、邪。”因六朝文士普遍持净土信仰,所以文士将佛教所谓的“杂秽之言”引入文学批评领域,袭用其“繁褥庞杂”之意。由之可推知,“绮语”当为文学创作过程中的“骄拇枝指”——是应删去的无益部分。“绮语”越少的作品越被视为佳作。于是谢灵运的诗作被萧纲《与湘东王书》批评为:“时有不拘,是其糟粕。”不拘就是缺乏剪裁的意思。钟嵘也说谢灵运的诗“颇以繁富为累”。又如《文心雕龙·练字》就说:“自晋来用字,率从简易;时并习易,人谁取难?今一字诡异,则群句震惊;三人弗识,则将成字妖矣。”这些都可视为六朝文坛明确对简明省净文风的支持。可以说这种追求诗歌创作观渗透到了尤其是齐梁以降的咏物之作在遣词造句、用典等各个诗歌创作的环节。现例之如下:
白水满春塘,旅雁每回翔。唼流牵弱藻,敛翮带余霜。群浮动轻浪,单泛逐孤光。悬飞竞不下,乱其未成行。刷羽同摇漾,一举还故乡。[5]1646
细雨阶前入,洒砌复沾帷。渍花枝觉重,湿鸟羽飞迟。傥令斜日照,并欲似游丝。[5]1965
上述咏物诗的作者力除晦涩文字和累赘辞藻,目的是以浅易助成表达上的流畅。又如首提“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的谢脁,其《咏竹》就用字平浅晓畅,几与口语无二。我们认为,在诗歌创作主体仍为士族文人的六朝时代,诗人追求简易省净文风并不是向底层民众推广自己的作品。而可能只是一种受到净土佛教思想影响下的文学审美趣味和诗歌创作观念的改变。
三、诗人生死观与意象的时空性
净土思想对六朝文士精神世界另一个重大影响是在生死观。先秦儒家的思想不直接谈及生死问题,有所涉及也是采用回避的态度。如《论语·先进篇》曰:“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子曰:‘未知生,焉知死?’”朱熹对此解释道:“死者人之所必有,不可不知,皆切问也。然非诚敬足以事人,则必不能神;非原始而知所以生,则必不能反终而知所以死。盖幽明始终,初无二理,但学之有序,不可跟等,故夫子告之如此。”[9]而庐山弥陀净土对生死、未来所持的开放、乐观态度给予六朝文士前所未有的震撼,具有独特魅力。属于大乘佛教的弥陀净土思想为满足信众现实的心理需求,营造了一个美轮美奂的西方极乐世界。相对于战乱频仍的现实苦楚世界,西方极乐世界是那样的令人向往。加之往生西方极乐净土是简便可行的。因此,这一超验世界的编织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六朝文士对死亡的好奇心理,并在潜移默化中转变了他们的生死观。他们不再如此抵触与惧怕死亡,死亡在他们眼中也不再是终结与黑暗,反而象征一种幸福和新生。
六朝诗人在净土生死观影响下,对世界万物与人生产生了新的看法。他们将净土思想与人生紧密联系,他们不再迷恋于世间万物的表象而是努力通过万物去探寻人生或宇宙中更深层的本质。受佛教净土思想滋养,诗歌创作的思想内涵更为丰富,更具哲学意味。现摘数首咏物之作为例:
蒲生广湖边,托身洪波侧。春露惠我泽,秋霜缛我色。根叶从风浪,常恐不永植。摄生各有命,岂云智与力。安得游云上,与尔同羽翼。[5]1417
天霜河白夜星稀,一雁声嘶何处归。早知半路应相失,不如从来本独飞。[5]1978
梅含今春树,还临先日池。人怀前岁忆,花发故年枝。[5]2057
就个体而言宇宙的永恒与自身生命的短暂构成了突出的矛盾。在有限的生命中应竭力把握时空中的偶然实现灿烂的人生。汉魏时期对生命无常的哀叹,以“悲”为主题的情绪,在南朝诗人的笔下,悄然发生了变化。“蒲”虽“常恐不永植”,但顺应命运也可游云端之上,获得另一种生命的体验。大雁独飞却不代表失意而是代表了另一种生命价值。树木花草面对时间的流逝,不再是直线式的一去不返。在佛教三生观影响下,万物的时间序列也由直线变成了循环的模式。因此,悟道佛家妙理,个体生命中短暂、有限的体验就转变为永恒与无限。这种不畏惧死亡的人生态度增添了士人实现生命密度和质量的可能。他们对生命崭新的认识,他们在生命挫折后的乐观生命意识也在其咏物之作中不经意地流露。以慧远为代表的净土思想为六朝咏物诗披上了一层朦胧而更具哲理性的面纱,此乃其创作特质之一。
综上所述,庐山净土思想以对佛之相好的强烈执着,引起了六朝文士对独立之物审美价值的重视。其简易的修行法门不仅赢得了大量信众,还在无形中使诗人将这种务求省净的思想运用到诗歌创作中。而大乘佛教对生死等根本问题的解答不但缓解了文士的焦虑而且重塑了他们的思维,并提升了其咏物之作的哲理高度。俄国宗教美学家E·P·雅科伏列夫在谈到艺术与宗教的关系时指出:“艺术和宗教相互作用的这个历史过程导致的结果是,世界宗教几乎把所有的艺术——无论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艺术——都纳人自己的结构中。但是,这个过程也产生出致命的后果:由于各种艺术对宗教意识的多方面的影响,宗教意识的樊篱已被拆除,宗教开始丧失自己独特的幻想内容。与此同时,形成了一个与传统宗教思维相距甚远的、新的美学和艺术的环境。”[10]可以说以慧远为代表的净土思想在融入中华文化过程的同时,形成了一个新的美学和艺术环境,也使得一代诗人的创作思想悄然改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