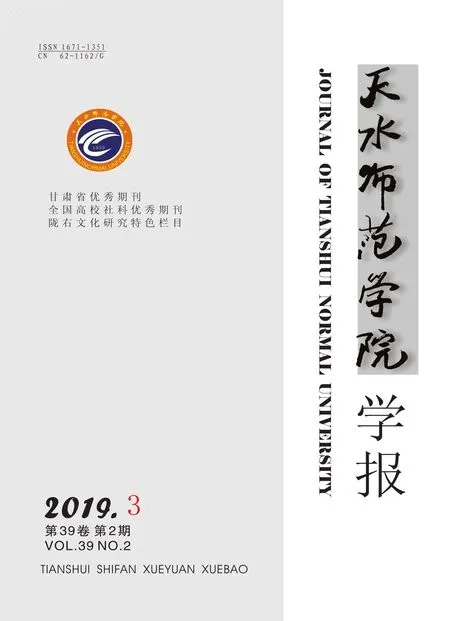论巩建丰的思想、著述及其价值
2019-01-21赵逵夫
赵逵夫
(西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730070)
《朱圉山人集》是清代初叶甘肃著名的理学家和杰出的诗人巩建丰的著作总集。从诗歌创作来说,甘肃有成就者,此前有生于明清之际的巩昌的王予望、兰州的郝壁、狄道的张晋,下来就要数巩建丰;而从作学问尤其在理学上的功夫、体会与著述来说,伏羌(今甘谷)巩建丰为清代甘肃第一人。
巩建丰(1673~1748),字文在,号渭川,别号介亭,康熙五十二年进士,其门生通渭李南晖《巩介亭先生传略》云:“累官翰林院学士侍讲,直起居馆。挟一匣肩舆中,朝暮自随,其所记录,虽子弟及门秘不以示也。乡会试屡同考官,甲辰主四川乡试,又出为云南学使,所取每多知名士。迁侍读学士。致仕归。”[1]其一生,一是侍候皇帝读书,讲其疑难,备问疑与讨论;二是负责一省办学教育行政、考试等事以及参与乡试阅卷。古代承担这两类职责者大体上是两种态度:一种是看风使舵、逢迎皇帝、长官,趁机交接权贵、从中得利,一种是守正洁身,恭谨从事,也不违法背礼以就人。巩建丰属于后一类。他生于西北,性鲠直,在职期间,又进一步研读理学论著,四十一岁进入仕途即侍君讲读,常以儒学宗师自视,不会因眼前利益而改变初衷。所以,尽管他受到雍正皇帝的重视,有机会与当时的权贵与名流接触,但他既没有因此而谋肥缺,也没有交接学界高明,走向深研文史、潜心考究的路子,最终是潜心理学研究。
巩建丰的走向理学研究,也同他一生大部分的生活环境有关。据其门生黄元铎所撰《介亭巩公墓志铭》言,巩建丰于雍正壬子夏四月“请假归里后以官徵,不復出”。是年六十岁。则其在京、外任首尾二十年。归家十六年后卒,享年七十六岁。则在家乡的时间五十六年。甘陇之地在唐五代之后渐为偏僻之地,社会风气、学术上较京畿一带、中原与东南迟滞守旧,由于清初文字狱的严厉,学者们转向古籍整理诠解与音韵、文字、训诂之学;东南一带及晋冀之地商业活跃,小说、戏剧、曲词创作空前繁荣。甘陇一带文人作词、曲、小说者极少,作学问者或从事于文化典籍的考究校释,或承宋代以来传统,由经学而转入理学。巩建丰之成就于理学,即是如此。
北宋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张载(1020~1078)为凤翔郿县人,清初之时今定西、天水一带属陕西省,故巩建丰从地方传统上将张载作为前辈贤达宗师。张载为嘉佑进士,官至同知太常礼院,曾在关中讲学,其学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吕大忠、吕大钧、吕大临、李复、张舜民等高张其帜,形成关学,影响甚巨。关学主张“学贵有用”,重视研究井田、宗法、封建、军事,崇尚三代之治,躬行礼教,而排斥佛老,以“气”为万物本源,认为万物的运动是由于其对立的“两端”或“两体”相互感应,主张“穷神知化”,“穷理尽性”,[2]基本上接受了关学的基本精神与理论。巩建丰自受学以来慕明代著名理学家薛瑄(1389~1464)之为人,同张载理学在实质上一脉相承。故其门人李因培在其《朱圉山人集序》中说:“自横渠先生倡道学于关西,后如先生之比,罕有其伦。”巩建丰作为当时大儒,除自幼勤于读书,从各种历史事件、各家学说中归纳出基本“理”,同时也同他能着力于联系实际,并体现于自身修养有关。李因培《序》中曾引其师巩公所说:
体忠达信,守礼奉法,修体之本也;父慈子孝,兄友弟恭,齐家之本也;兴利除害,礼士爱民,作官之本也。得其本而推广之,则节目可次第行矣。[1]328
这实际就是巩建丰一生所遵循。此《序》中还引了巩公的一段话:
尝爱诸葛武侯“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二语,讽诵不休。及自入庠、登朝以迄归田,五十馀年中,目睹声色货利、纷华靡丽之物,只常守“淡泊宁静”四字,幸不为其所染,而庶几免大咎者以此。[1]353
这些在今日之从政者,甚有借鉴意义。以此观之,理学未必空谈无用之学,而真正是关乎人生、关乎现实、关乎社会安定的学问,在任何时候都会有打着各种招牌、披着各种外衣自我标榜,干伤天害理、借“理”杀人的人,在封建社会末期当民主思想兴起之时更有不少人借君臣父子之义打压青年人,抵制民主运动。那是借着理学的工具保护各种反动的封建制度。在今天封建制度已被彻底砸烂的新时代,人们的识别能力已大大增强,我们应当挖掘传统理学中有利于提高国民素养、社会发展的因素,联系当下的现实加以阐释,予以继承张扬。
《朱圉山人集》第一卷为《就正编》,为作者74岁时集平时所记心得,由李南晖编次而成,应为巩公的最后一部著作,前有《自序》。其下为《研经》,共二十一条,前十四条为论《易》理者,皆联系社会人生言之,与谈象数者不同,句句切于义理。如其第十条云:
为学莫大于好古积学。《易·大畜》之《象》曰:“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夫德散见于言行。古人已成之迹,其最可法也。故必多识以畜之,则德进于日新,而不自知其光大。彼以致虚寂为德者,适见其陋而已矣。[1]345
现在很多人说到加强个人修养、改变工作作风,只是口上说说,在下面干了很多违背党纪国法之事。有的领导怕犯错误,推卸责任,没有担当,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这些难道能算是有高尚的道德修养吗?如果能多读书,知道历史上很多很多巨贪都没有好下场,在古代被满门抄斩,或主要成员被杀、其他流放于边远之地者甚多,知道这些,自然就会知道什么事可做,什么事不可做,有所畏惧,有所警戒。这样,国家事业也少受损失。就犯罪者来说,有不少也是国家花很多钱多年培养出来的,一旦受到法律制裁,从人才方面也是一个损失。无论从事行政工作、事业管理,还是负责企业,都应在思想上、个人品德修养上严格要求自己,绝对不能踩法律的红线。干具体工作也有一个方法问题;人与人的交往,单位与单位之间协调沟通,也有一个正常的互助互利原则。所以,巩建丰论《易》联系现实而谈理,正是将传统文化中的光辉之点挖掘出来,使人人皆知,体现在人的行为中去,以利社会正常发展。这在今天仍然是有意义的。
《研经》的后七条分别论《诗》、《书》、《礼》、《春秋》,也能从切近现实的方面言之。当然,其中也有些从学术方面论述个人看法,如言《礼记》中《檀引》本是解“经”之“传”,因汉儒于秦火之后采辑补缀,将其与其《大学》、《中庸》等本为经者并列编为一书,“殊失孔子定《礼》之意”。还有对其中一些记叙不可靠的评点,也都可以看出巩建丰读书除从理学的角度加以发挥引申外,也从文献的角度对其中一些学术性问题进行深入思考,提出自己的看法。
第二章为《考史》,虽皆就历史上之大事宏观论之,而往往真知灼见,令人眼前一亮。如云:“赵宋开国,家法严,伦理明,所以后来无女主之祸,而有曹、高、向、孟之贤,异于汉唐远矣。”历来论古史者,都着眼于汉唐开疆拓土及同西域等周边之交流,成一时强盛帝国一点,称作“汉唐盛世”,而巩公则着眼于朝政制度。则汉唐两代都是开国之君谢世后出现女主专权,在女后取得君主大权和后面的重新归于正宗过程中,都要经历一番折腾,对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安定都造成很大影响。而北宋之时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文化教育得到空前发展,在中国古代史上是空前绝后的。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以北宋之时最为突出。由此也可以看出巩公史识之不凡。其下《讲学》、《立教》、《论古》、《感时》、《崇正》、《辨邪》、《居官》、《涖民》、《燕居便抄》等章所论,皆有精辟之见,不一一列举。
《朱圉山人集》的第二卷为《奏疏》,第三卷为《书柬》,第四卷为《序》,第五卷包括《论》、《考》、《说》等体文字,第六卷为《传》、《墓表》、《墓志铭》等。其前五卷,也多有发人深省之处。如第五卷之《风俗论》云:
风之行也自上,而俗之靡也不尽关于上。其始也,一二人倡之,既而千百人和之,如水溃堤,狂澜肆溢,而莫可防遏。虽有勇者,卒莫可施其力,无他,势使之然也。[1]411
下面举了伏羌县朝山的风俗,“不过愚夫愚妇,祈福邀神,并不害于俗。其后国家休养生息,民间渐富,有的人聚会矢盟,假敬神之美号,造淫佚之恶习”。最后弄到“奸棍诱赌,荡破家中之产”。所以,俗有人使之坏,必要有人倡之使其归于正。读书、受教育多者应该主动承担责任,使地方保持良好的风气。这当中的道理,值得人们关注。卷五《程淡远传》写了乾州程淡远的事迹如当战乱之后“分田田人,人有未遽受者,先生曰:‘苟可以利若俯仰,我奚爱此数块土也。’”还写到其支持一些家境困难的学生能继续攻读等事迹,之后说:“太史公曰:‘谚曰:里有君子,而风俗化。’淡远先生,其化俗者耶?”说地方上有学问之人应以救贫济因、助学倡善、转变风俗为己任,不能让一些吃喝嫖赌、招摇撞骗之徒把地方的风气弄坏。其他各卷也多有联系现实论事给人以启发,激励、引导之作。故巩公虽理学名家,并不空谈礼义廉耻,而是充满人情味和带有强烈的现实感。这些论述中也同样表现不凡的史识。《程淡远传》开头说:“家传与史传异,其人可史,每每取信家传、行状、志铭,皆其具也。读昌黎诸家传,窃怪志状太夥,或过其实。唐宋以还,史家资焉。大抵文益显,其真益衰;始以翼史,卒以乱之。可胜叹哉!”他对韩愈的墓志铭之类的失真和一些史书的失真表示极大的不满。这是很多文人甚至治史者所不具备的眼光。
第七卷至第十二卷为诗,以体分类而列,其中词只有二首,这也同西北尤其秦陇之地自宋以后商业欠发达,人口稠密的都市少,舞榭歌楼极稀少有关。甘陇诗人能作词曲者极少。巩建丰存诗三百多首,同其文一样,极有情,而情依于理,理见于事,既表现出甘陇一代儒宗深厚的情怀,高尚的品质,也可以看出他确实是关心国计民生,关心教育,关心对社会风气扶持引导之用心。如五言古诗《乞妇答》写因遭灾,很多人吃草根树皮。一个穷苦妇人乞讨中听说有京官来,想上陈百姓之疾苦,结果呢?“无奈虎狼役,鞭扑扼其吭。四路如张网,何处喊冤鸣?”《老农叹》、《观稼》等诗反映了大体相近的社会现实。再如七律《不寐》,其前四句云:
市粮腾贵价难均,眼见饥民颠沛身。一岁叠荒糠作面,十家九空灶生尘。[1]
诗人并不因为这些内容有损于当时“盛世”而装聋作哑、熟视无睹。诗人不寐非因个人家庭之事,而是社会民众之事。他作为一位杰出的理学家,不是事事循规蹈矩,以封建统治阶级法规为准,不敢越雷池一步,而能凭心反映社会的矛盾,揭示出社会的阴暗面。
巩建丰诗中也有些访古抒情之作,很可以看出诗人的胸怀情趣。上文已谈到他对诸葛亮的崇拜。卷九有七律《澜沧江谒武侯祠》,卷十又有七言绝句《过沔县吊诸葛武侯墓》,都可以由之看出诗人的情怀。诗集中关于天水一带名胜之诗也比较多。如七律《初秋登秦州城楼观修罗玉桥》:
爽气高迎百尺楼,旷观景物望中收。西通雪岭清沙塞,东走黄河顺曲流。万户烟攒云欲合,千村树立翠还浮。新桥此日安隆栋,老友欢声颂都侯。[3]141
诗作视野开阔,很有气势,其他如五律《玉泉观抒怀》、《登台望南山诗》等也都很有诗意。其《二月中旬往秦州道上遇雨之作》:
春半老身怯雨寒,使君揖我就征鞍。四周草树生机畅,一带园田播种安。民瘼已知通郁气,士风直欲障狂澜。主人无限绸缪意,喜共阳和布教宽。[3]170
这是应州官之请赴秦州书院任教途中作,写途中所见风景甚美,但由“民瘼”一句可看出他对民间困苦的关心,只是言作官者以能了解民情,上达而下抚救之。“士风”一句即表现出其《风俗》一文中所表现士人当障恶风而畅良俗的思想。诗中既有写景,也表现出其思想情怀。其七律《秦州书院勉诸生力学》中“桃李浸浇须畅幹,矿沙锻炼待成金”等语,也表现出他在培养人才上注重德教的方面。
《朱圉山人集》中各体诗歌都不追求奇崛警句,语平实而引人深思,多可玩味。巩建丰是清代甘肃杰出的诗人之一。
霍志军教授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对地方作家作品特别关注。十多年前同聂大受教授一起编写了《陇右文学概论》一书,虽成书出版于甘肃省社科院《甘肃文学概论》之后,篇幅也较前一书小,但内容上有前一书未及者,突出的一点便是增列了巩建丰。此次搜集《朱圉山人集》的各种印本、抄本,几次到甘谷的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查访,并到民间了解,尽量求其完整,补其模糊不清之字,以求成最完整的本子,以便流传于后,不使有憾。除校勘之外,还对其中一些人、地、事件和较生僻词语作了注,以便更多的人阅读、了解。
中国可谓诗之国,从古至今,历代著名诗人不少,名篇不计其数,作为一个文明古国,历代从事学术著述的也不少。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教育,各地都应弘扬优秀的文化遗产,使这些有成就的诗人、作家、学者的心声、呼喊、告诫为广大群众所闻知。因为这些诗人学者的著作所反映人、事、山川、景致跟当地人民最为贴近,其内容更易被理解。所以,在着力改变甘肃面貌的当中,也应把前代贤达的著作整理出来,剔除其封建性糟粕而弘扬其民主性精华,作为今天改善民风民俗,提高国民素质的一种教材。《朱圉山人集》中在今日读来仍具教育意义、启发意义的东西不少。该书的出版是甘肃古代文化整理研究的一个大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