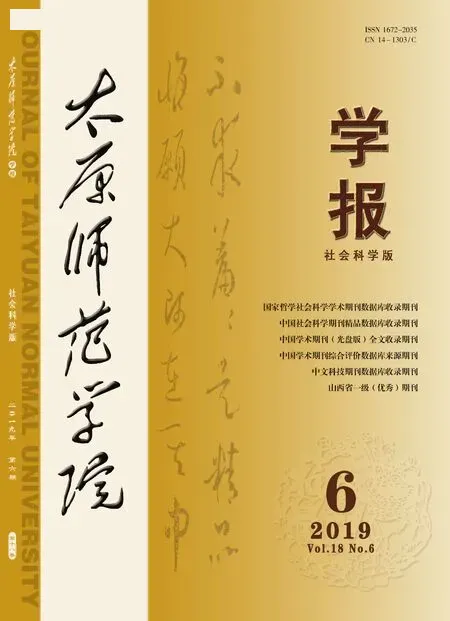张之洞通经致用教育观述论
2019-01-20孟旭
孟 旭
(太原师范学院 发展规划处, 山西 晋中 030619)
张之洞大致是在山西巡抚任上(1881—1884年)开始逐渐转化成洋务派的。在这以前,他曾任浙江乡试副考官、湖北学政、四川乡试副考官、四川学政等职,负责地方的科举与教育事宜。在考官和学政任上,张之洞兴办书院,大力讲求经学,整顿学风,提拔奖励有真才实学的人。如他在四川建立尊经书院,延聘名儒为师讲授,并依照阮元杭州“训诂精舍”、广州“学海堂”规制,手订教条,还撰写《輶轩语》和《书目答问》作为指导士人读书做学问和修养品德身心的读本,在当时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书目答问》至今仍为治中国旧学者所重视。在湖北学政任上,张之洞创建了经心书院,别学舍为“经义”“治事”两斋,努力培养实学人才;在山西巡抚任上,张之洞创建了令德书院,要求学生读书以汉学为本,做人以宋学为本,严禁吸食鸦片,不准学生沾染一丝专课时文的晚清书院恶习。
在张之洞的这些早期教育实践活动中,他始终坚持的是通经致用的教育观,目的在于培养能效力清王朝的所谓“通经致用之士,经世致用之才”。
一、通经致用的知识论
《书目答问》《輶轩语》和《尊经书院记》,是张之洞在光绪元年(1875)前后,任四川学政时,为指导尊经书院学生读书学问、修养品德以及在科举考试时应注意的事项所写的著作和文章。
《书目答问》是一部指导士人治学门径的重要书目,《輶轩语》则是指导士人如何读书、如何做人的一本小册子,这两部书集中地反映了张之洞通经致用的知识论。
在《书目答问》序中,张之洞明确地表示了他的写作目的:“诸生为学者来问应读何书,书以何本为善,偏举既嫌挂漏,志趣学业亦各不同,因录此以告初学。”[1]623因为张之洞认为,“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1]623,所以需要“分别条流,慎择约举,视其性之所近,各就各部求之”[1]623。也就是说,这本《书目答问》是想为初学者解决两个问题,即哪些是比较重要的书和哪些是比较好的版本。
《书目答问》作为一部指导士人治学门径的举要书目,如何从浩如烟海的图书中慎择约取,选出其中基本的具有代表性的或带有总结性的著作,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但要选择哪些是重要的书,除了作者张之洞本人的学识外,还必定涉及和反映其治学的基本观点,即知识论观点。张之洞的《輶轩语》系统地阐述了他的知识论观点,而他的《书目答问》则是其知识论观点的具体化。
张之洞在《輶轩语·语学第二》中提出了著名的“读书期于明理,明理归于致用”的主张。他说:“书犹谷也,秋获舂揄,炊之成饭,佐以庶馐,食之而饱,肌肤充悦,筋骸强固,此谷之效也。若终岁勤动,仆仆田间,劳劳爨下,并不一尝其味,莳谷何为?近人往往以读书明理判为两事,通经致用视为迂谈,浅者为科举,博洽者著述取名耳,于己无与也,于世无与也。亦犹之获而弗食,食而弗肥也。”[2]610“使者谆谆劝诸生读书,意在使全省士林美质,悉造成材,上者效用国家,其次亦不失为端人雅士,非欲驱引人才尽作书蠹也。”[2]611所以,张之洞要求士人“读书宜读有用书”,那么,什么样的书才算是有用的书呢?按张之洞的观点,有用就应该是“可用以考古,可用以经世,可用以治身心”[2]608。能起到这三种作用的书,就算是“有用”的书;能起到这三种作用的知识,就算是“有用”的知识了。可见张之洞通经致用知识论的核心,即是认为士人掌握知识应该具有选择性,而选择的标准是看它是否“有用”,是否具有“考古”“经世”和“治身心”的作用。
出于“考古”和“治身心”的目的,张之洞主张“读书宜多读古书”。他说:“除史传外,唐以前书宜多读,为少空言耳。大约秦以上书,一字千金,由汉至隋,往往见宝,与其过也,无亦存之。唐至北宋,去半留半;南宋迄明,择善而从。”[2]604由此观点出发,张之洞在《书目答问》里收录了大量传统的先秦两汉古籍。尤其主张读书“宜讲汉学”,也就是提倡阅读汉代学者注经讲经的书籍。他认为汉代学者对经书的研究校注,“义有师承,语有根据,去古最近”[2]599。他指出当时阮元主持校刻的《十三经注疏》虽然不是汉代学者所作,但“《注疏》所言即汉学也”[2]599。他指出了汉学的两个特点,一是音读训话,二是考据训诂。他指出:“音训明,方知此字为何语,考据确,方知此物为何物,此事为何事,此人为何人,然后知圣贤此言是何意。”[2]599所以,只有努力学习和研究汉学,字求其训,句索其旨,才能真正达到通经的目的。
张之洞要求士人“读经宜读全本”,以了解经书的全貌,反对读删节本。他还要求“解经宜先识字”“读经宜正音读”,以求达到明训诂、知源流、考古义的目的。他认为,“宜专治一经”,十三经卷帙浩繁,不能尽通,专治一经,即已不易,士人应该专治其一,再及其他。但仍须参考诸经,博综群籍,方能通此一经。否则,此一经亦不能通。他告诫士人“治经宜有次第”,“非谓此经精通,方读彼经,谓浅显者未明,则深奥者不必妄加穿凿,横生臆见”;“治经贵通大义”,“每一经中皆有大义数十百条,宜研究详明,会通贯穿,方为有益;若仅随文训解,一无心得,仍不得为通也。考据自是要义,但关系义理者,必应博考详辨,弗明弗措。若细碎事体,猝不能定,姑仍旧说,不必徒耗日力”。[2]602可见张之洞对“通经”的指导是极为具体详细的。
除了经书而外,张之洞还在“史部”“子部”“集部”和“丛书目”项下收录了大批的古籍,对于学习历史方面的知识,张之洞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读史“宜读正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二十四史为“正史”“信史”。所以,他要求“凡引据古人事实,先以正史为凭再及别史、杂史”。张之洞还建议士人注意阅读《资治通鉴》和《文献通考》,他认为,读《资治通鉴》能“知历朝大势”;读《文献通考》能了解历代经济、典章制度,“尤便于用”。他认为,“读史者贵能详考事迹、古人作用言论”;可以“推求盛衰之倚伏,政治之沿革,时势之轻重,风气之变迁,为其可以益人神志,遇事见诸设施耳。”[2]604也就是说他希望士人通过对中国历史的学习和研究,通过“考古”,了解历朝的经济典章制度和政治的得失,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为将来步人仕途、经国济世做准备。
在张之洞看来,读子部书的目的在于“通经”。他说:“子有益于经者三:一证佐事实;一证补诸经伪文、佚文;一兼通古训、古音韵。”[2]603这里的子部书,主要指的是周秦诸子之书。对于阅读集部书,张之洞也提出了具体的指导和要求。
张之洞认为,阅读经、史、子、集四部之书,不仅具有通经致用和考古方面的作用,还能起到“治身心”的作用。他说:“儒者自有十三经教人为善,何说不详?果能身体力行,伦纪无亏,事事忠厚正直,自然行道有福,何用更求他途捷径哉。”[2]604在他看来,士人们完全可以在通经的过程中,吸取和接受儒家正统的纲常伦纪,形成士大夫所应该具备的道德修养,从而达到“治身心”的目的。他认为宋学更宜于“治身心”。他说,“好读书者宗汉学,讲治身心者宗宋学”。他特别推崇宋代朱熹的《近思录》一书,认为“《近思录》一书,言约而达,理徐而切,有益身心,高下咸宜”。[2]604很显然,张之洞在治学问题上尊崇汉学,是提倡汉学重训诂考据的严谨态度;在制行方面推崇宋学,则是赞赏宋明理学持志主敬的修养功夫。
张之洞一方面大力主张“读书宜多读古书”,认为古人的知识理论水平远较后人为高;另一方面,他又大力宣扬“今胜于古”的思想。如他在《书目答问》一开始的“经部”下说:“经学、小学书以国朝人为极。于前代著作撷长弃短,皆已包括其中,故于宋、元、明人从略。”[1]628以《诗经》为例,《书目答问》共举有关著作五十余种,大部分是清人的著作。又如“小学”部分,《书目答问》收书一百一十余种,其中大部分是清人的著作,达八十余种。张之洞在“史部·地理”类下又说:“今人地理之学,详博可据。前代地理书特以考经文史事及沿革耳。若为经世之用,断须读今人书,愈后出者愈要。”[1]658在这一类著作中,除了收录《三辅黄图》《水经注》《元和郡县志》等张之洞所谓的用以“考经文史事之沿革”的古籍外,还收录了大量清人著作及《新译海塘辑要》《职方外记》《坤舆图说》等翻译著作。在“子部·天文算学”下张之洞又说:“推步须凭实测,地理须凭目验,此两家之书,皆今胜于古。”[1]674这类书籍在《书目答问》中,以其是“极有益于经济之学”,收录达六七十种之多,其数量在“子部”中,仅次于“儒家”著作。其中除了清人著作占相当比例外,还收录了《代数术》《曲线说》《数学启蒙》等翻译著作。
从这里可以看出,张之洞所主张的“多读古书”,与他的“考古”和“治身心”有更密切的联系,通经致用则是其主要的目的。而他所强调的“今胜于古”,则出于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许多后人的研究成果业已超过前人,如经学、小学等类的清人著作;二是后出的书有的远较前出者为精确,如地理、天文、算法之类,因此他又要求在某些内容方面多读今人的著作,这同样与张之洞通经致用的主张相联系。这种对古今知识关系的看法就张之洞本人的观点来看,两者之间并没有截然的界线,不论是提倡“多读古书”也好,还是强调“今胜于古”也好,其目的均可以归结到一点——“有用”,即“考古”之用、“经世”之用、“治身心”之用。因此我们可以把张之洞的知识论概括为通经致用的知识论。不论在对士人所学知识的选择上,还是在对学生学习知识的目的上,张之洞均是以通经致用作为衡量标准的。
要想达到考古、经世和治身心的目的,只要通过大量的读书实践和自我修养就可以了;但要想达到经世致用的目的,如果不通过科举考试成为一名政府的官吏,即使知识再多、本领再大,即使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通经致用之士,经世致用之才”,也不可能施展抱负。所以,张之洞当时虽然已经认识到了时文制艺的腐朽无用,认识到了科举制度对人才的摧残和埋没,但他还是不得不努力教导士人们致力于科举考试,以求进入仕途,得到施展经世致用抱负的机会。在《輶轩语·语文第三》中,张之洞专门对科举考试的内容,如时文、律诗、赋、经解、策论、古今体诗等科目应具备的知识和应注意的事项,进行了详细的指导性阐述。对于考试试卷中应避免的文字、考场纪律、考试卷的格式要求,都进行了详细具体的指导。
二、品德修养论
在早期的教育实践活动中,张之洞教导士人读书做学问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治身心”,也就是进行道德品质方面的修养。注重对士人进行品德方面的培养训练,是张之洞通经致用教育观的一个重要内容。
在大的伦理道德规范上,张之洞一贯严格要求士人恪守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等封建道德以维护专制社会等级秩序。他还把清代的《卧碑八条》以及《圣谕广训十六条》作为士人的行为准则,要求士人“恭敬遵守”。在具体的品德修养方面,张之洞极为推崇宋代理学的修养功夫,赞扬“宋学贵躬行,不贵虚谈”[3]760,要求士人注重自身的品德修养。他还根据当时四川省的士风,对尊经书院的士子提出了品德修养方面的具体要求。
(一)“德行谨厚”
张之洞说“德行不必说到精深微妙处,重心术慈良,不险刻;言行诚实,不巧诈;举止安静,不轻浮;不为家庭事兴讼;不致以邪僻事令人告讦,不谋人良田美产;住书院者,不结党妄为;无论大场小场(科举考试)守规矩,不生事;贫者教授尽心,富者乐善好施,广兴义学,捐钱多买书籍,置于本处书院,即为有德。”[2]594在张之洞看来,人们应该“心术慈良”“言行诚实”“举止安静”,不险刻,不巧诈,不轻浮,不兴讼,不谋财,不邪僻,不结党,不妄为,科举考试守规矩,不生事,热心于教育事业,即是安分守已、“德行谨厚”的人。
(二)“砥砺气节”
张之洞说:“世人立身涉世,居官立朝,皆须具有气节。当言则言,当行则行。持正不阿,方可无愧为士。……气节非可猝辨,必须养之于平日,惟寒微时即与正士益友以名节廉耻互相激发,则积久而益坚定矣。”[2]594张之洞认为人们应该言行一致,“持正不阿”。为此,必须在平日或寒微的时候,便与好友以名节廉耻互相激发。所谓的“名节”与“廉耻”,便是“忠孝节义”等伦理道德和实行这种“忠孝节义”的廉耻之心。
(三)“人品高峻”
张之洞说:“不涉讼,不出入衙门,不结交吏胥,不参与本州县局事,……求功名不夤缘,试场不作弊,武生勿与帽顶(蜀人谓匪类为帽顶)来往,即为有品。”[2]594张之洞认为,人品的高峻,就是不管世事,埋头经文;不结交吏胥,科举考试不作弊以及不与坏人来往等等。
(四)“习尚俭朴”
张之洞说:“惟有力行节俭一策。尝谓一乡风俗,视乎士类,果能相率崇俭,乡里必有观感。浮华渐除,生计自然渐裕,城市读书人大戒专讲酬酢世故,即异日显达仕宦,亦望以此自持,则廉政无欲,必有政绩可观。”[2]595张之洞希望士人戒除酬酢人情世故的恶习,以崇节俭、除浮华。他认为,如果士人们认真崇俭,即使以后做官为宦,也会廉正自持,做出政绩来。更值得一提的是,张之洞还把士风和社会风气联系起来,认为改变士风是改变社会风气的关键。这也是张之洞重视士人品德修养的一个重要因素。
(五)“立志远大”
张之洞希望士人不仅在学术上,而且在品德修养上都要有远大的志向。他要求士人要常与古代的圣贤比较,不断充实自己,这样,品行和学业自然就会不断有所增长和提高。另外,张之洞还严禁士人吸食鸦片。他说:“世间害人之物,无烈于此……伤身耗财,废事损志,种种流弊,不能尽言”[2]598。张之洞认为,只有从以上几方面修养品行着手,扭转士风,才能达到扭转“近日风俗人心日益浅薄”的局面。
三、读书方法论
张之洞不仅为士人指出了一条以通经致用为准则的学习和获取知识的门径,使士人得以依据他的《书目答问》,从浩如烟海的书籍中慎择约取,获得能够“考古”“经世”和“治身心”的知识学问;而且,他在《輶轩语》和《尊经书院记》中还对士人在读书学习过程中具体应注意的问题和应掌握的方法,进行了经验性的阐述,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条:
(一)读书宜择
张之洞指出,读书宜有“择术”。“经史、小学、舆地、推步算术、经济、诗、古文、词,皆学也,无所不通者,代不数人高材。或兼二三,专门精求其一,性有所近,志有所存,择而为之,期于必成。非博不通,非专不精。”[3]758张之洞认识到,人的学习能力是有限的,兼通各学科的通才不过是有数的几个人,即使是兼通几门的人才也是少数。所以一般士人就应该在博的基础上去精求一门,选择的根据是在通经史等所谓的根柢之学的范围内,以及士人自己的志趣爱好。
(二)读书宜定课
什么是“定课”?张之洞说:“人立日记一册,记每日看书之数,某书本几卷起,第几卷止。记其所疑,记其所得,无疑无得不可强书。不贵多,贵真;过目不贵猛,贵有恒;不贵涉猎,贵深思;不贵议论,贵校勘、考订;不贵强记,贵能解;不贵创新解,贵通旧说;不贵更端,贵终卷。”[3]759可见张之洞“定课”的读书方法主要有四层意思:一是制订出每日的读书计划,每日要“记其所疑,记其所得”。这颇与子夏所说的“日知其所无,月无忘其所能”有相通之处。二是存疑深思,即对每天所记的疑问不轻易放过。“不贵涉猎,贵深思”。三是循序有恒,他告诫士人读书“过目不贵猛,贵有恒;……不贵更端,贵终卷”。四是“贵通旧说,不贵创新解”,只要求士人能准确理解古人文章的含义,反对“妄加评论”。
(三)读书宜用心
有人问,如果“依课计功而无所得”,是什么原因?张之洞回答是“不用心之咎也”。他说:“平日嬉娱,临课而搜腹,日日课试,无益也。翻书抄撮,姑以塞责,检之不能得,读之不能句,摘之不能得其起止,抄考据之书不能辨其孰为引正语,孰为自下语也。抄记事之书,不了然此事之原委也。如此则抄之而仍忘,引之而不解,虽日日抄书,无益也。作为文章,以抄袭为逸,以储材为劳;读近人浅俗之作则喜,古集费神思则厌。甘仰屋而课虚,不肯学古而乞灵,虽日日为词章,无益也。”[3]759在这里,张之洞批评有的士人平日嬉娱,读书不用功;有的士人读书不认真,不求甚解,敷衍塞责,虽然天天都在读书,却事倍功半,一无所知;有的士人贪图安逸,不愿深思细考,因而不阅读古人有深奥含义的书,只读一些近人的“浅俗之作”,认为如此不用心读书,自然难以领会到书中精深的道理。因此他告诫士人要“用心”读书,要求士人阅读深奥的古书“必求其通”,“不能通者,考之群书,勿病其繁;问之同学,不以为耻。文章纵苦涩,勿因人纵蹈摹古之讥;勿染时俗之习,如此而不效,未之有也”[3]759。可见张之洞的“用心”,不仅包含有用心思考的含义,而且还包含着用心研究考证,为解决疑难,不耻于向他人学习和请教的意思。如果真能做到这些,读书便会有心得。
(四)读书宜博
张之洞说:“先博后约……无论何种学问,先须多见多闻,再言心得,若株守坊本讲章一部,兔园册子数帙,而云致知、穷理、好学能文,世无其理。”但张之洞又指出“天下书老死读不可遍”,所以,博览群书也要有一定的规范。这个规范是,“古书不可不解,有用之书不可不见,专门之书不可不详考贯通”[2]606。“非博不通,非专不精”。[3]758循着这些规范和要求,士人就不会去盲目而漫无边际地读书了。
实际上张之洞的“读书宜博”,也是围绕着“考古”“经世”“治身心”的宗旨来限制博览范围的。
(五)读书宜有门径
张之洞认为,读书“泛滥无归,终身无得;得门而入,事半功倍。或经、或史、或词章、或经济、或天算地舆。经治何经,史治何史,经济是何条,因类以求,各有专注。至于经注,孰为师授之;古学,孰为无本之;俗学、史传,孰为有法,孰为失体,孰为详密,孰为疏舛;词章,孰为正宗,孰为旁门,尤宜抉择分析,方不致误用聪明”[2]606。张之洞首先指出了寻找读书门径的重要性,接着他又为士人推荐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他说:“读《提要》一过,即略知学问门径矣。”[2]606此外,张之洞还本着“以约驭繁”和“通经致用”的原则,撰写了《书目答问》,它较《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更为概括简洁,适合当时士人的需要。
(六)读书不必畏难
张之洞认为,今人读书远较古人读书要容易得多。今人读书只要取古人现成的东西,即所谓“诸公作室,我辈居之;诸公制器,我辈用之”[2]610。所以,与古人相比,今人读书畏难的思想是不可取的。张之洞批评了那些推说“记性不好”“无书无暇”而懒于读书的人。对于所谓“记性不好”的借口,张之洞说:“每见今人不好读书,辄以此借口,此欺人也。日记一页,月记一卷,十年之内可记百余卷矣。非不能,实不为耳。朱竹坨有言,世岂有一览不忘、一字不遗者,但须择出切要处记之耳。竹坨为本朝第一博雅人,其说如此,以告读者”[2]610。对于推说无书无暇的人,张之洞说:“能购,购之;不能,借之。随得随看,久久自富。若必待插架三万,然后议读,终身无此日矣。即使《四库》骈罗,岂能一日读尽。何如姑尽所有,然后再谋其他。更有一蔽,劝人读书,多谓无暇,不思嬉游、昼寝,为暇多矣。一页数行,偶然触目,他日遇事,或即拾收其用。自非幼学真读书者,断无终日正襟危坐,限定读书时刻之事也”[2]610。张之洞所提倡的这种克服一切困难,挤出点滴时间读书学习的精神,至今仍是可取的。
四、结语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张之洞早年通经致用的教育观,完全是中国传统儒家的教育思想。
第一,在教育的作用上,张之洞继承和发展了儒家“化民成俗”的教育作用论,企图通过“教士”改善士风,进而达到改善民风、淳化社会风气的作用。在张之洞看来,“一乡风俗,视乎士类”,只要加强对士人的教育,改善士风,民风和社会风气自然也会因之而好转起来。这种观点过于强调了“教士”对“教民”的作用,而忽视了晚清民风士风日渐低下的社会历史根源,但张之洞重视教育对于社会风气的影响是有其合理性的。
第二,在教育的内容问题上,张之洞继承和发展了明末清初思想家、教育家王夫之、颜元等人的思想,主张学习能够经世致用的学问,批评了八股制艺的空疏无用。在他所创办的尊经、经心、令德等书院,张之洞讲求“根柢”“致用”之实学,培养和提拔了一批实学人才,给晚清没落腐败的旧教育带来了一丝生气。
第三,张之洞在早期所要培养的理想型人才——通经致用之士、经世致用之才,实际上就是这样一种人才:在知识上博古通今;品德上孝悌忠信,安分守已,温良恭俭让;政治思想上忠君爱国;学术态度上崇敬古今圣贤学者,对古人的著作不“妄加批评”,尤其时时记着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这种人才,出则可以为“名臣”,处则不失为“名儒”。做“名臣”时,可以经国济世,加强和维护专制制度;为“名儒”时,又可以维持名教纲常,改善士风民风。
第四,张之洞虽然是一名教育实践家,他早年曾创办了尊经、经心、令德等书院,并亲自给书院学生讲过课,但他毕竟只是一名侧重于从宏观上规划和指导教育实际的教育家,并没有长期系统地从事具体的教学实践活动,所以与中国古代的许多教育家相比,他的教学理论就显得十分单薄,谈不上有系统的教学思想。至于他在《輶轩语》《尊经书院记》中所罗列的读书方法,则多是对自己长期读书经验的总结和概括,并没有上升到很高的理论水平,这是张之洞教育思想中的薄弱环节。
总之,早期的张之洞还是属于封建巩固派营垒中的人物,他对于旧教育的整顿以及他的通经致用教育观,对于空疏腐败的晚清旧教育来说,是有进步性和积极意义的。但与当时的早期洋务派奕、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所提倡的洋务教育理论和实践相比较,却要落后许多,并有着本质的差别。他所欣赏的“通经致用之士,经世致用之才”,还远不能与洋务教育所培养的通晓近代西方工业、军事技术的人才相提并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