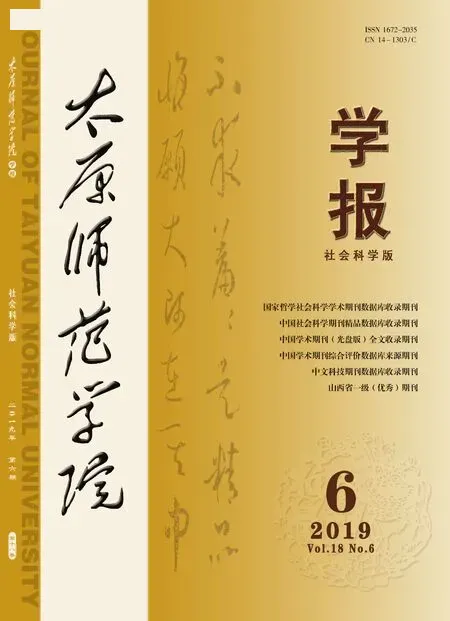郭绍虞语言文字观及其新诗建构理念
2019-01-20任小青
任小青
(复旦大学 中文系, 上海 200433)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讲究句法、声律的诗学传统,且这些句法、声律在诗法、诗格中一直占居着重要的位置,是旧体诗特别是格律诗维护自身体性的关键要素。尽管从“诗界革命”以来,旧体诗人一直在探寻使旧体诗焕发生机、适应新时代的有效表现形式,但他们的举措尚且在引俗语、外来事物入诗,追求浅显通畅,不曾有打破旧风格的主张。然自胡适提出“诗体大解放”,新诗便陷入语体和文体的选择困境。语言和文字之争成了新旧文学家议论的焦点。郭绍虞洞察到新诗创作之所以不能取得满意的成绩,根本症结在于新诗人不能正确地看待诗歌和语言文字的关系。对于郭绍虞这一颇具识力的论断,学界已有注目,但研究主要集中于探讨他在修辞和语文教学方面的成果(1)高万云《郭绍虞在修辞学研究方法上的重要贡献》(《当代修辞学》2013年第1期),注意到了郭氏修辞学与批评史研究之间的关系,对其打通学科界限为修辞学研究方法给予的启示意义予以揭橥。赵志伟《兼顾读写,欲求两全——郭绍虞国文教育思想述评》(《语文建设》2017年第2期)《郭绍虞论文白之争和文字改革》(《语文建设》2017年第3期),着重探究了郭氏对文字改革、文白之争、语文教育等方面的思想。郜元宝《音本位与字本位——在汉语中理解汉语》(《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2期)是最早关注到郭绍虞的文学语言观的。何旺生《郭绍虞的中国诗学语言批评》(《合肥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一文,则专门探讨了郭绍虞对语言之于中国文学的作用关系。,鲜有将其语言观与他的新诗建设路径勾连起来予以考察的。
本文提出郭绍虞诗学语言批评的出发点是为新诗的发展服务,旨在解决新诗面临的困境;探析新诗论者片面将语言文字的协同性割裂开来,建立纯粹的白话诗的构想能否实现;在语体化、散文化的发展趋势下,文字型、匀整化的旧体格律诗是否就丧失了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如果有价值,那么它赖以存在的土壤和条件是什么;散文诗和格律诗是否可以共存、相辅,一起完成建立合乎中国语言习惯而又富于音乐性的现代新诗。分析郭绍虞的诗学思想,能够为我们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一种思考角度。
一、 诗歌语言观:声音语、文字语并济
白话诗发轫初期,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和《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两文中,提出“八事”和“八不主义”,为白话诗的发展作了初步的构想。其中他从语言和体式两方面指出,“须讲求文法”“不讲对仗”“不重对偶”“不用套语滥调”等,就是意在打破旧体诗讲对仗、重对偶、用典等习以为常的传统规矩。而在此前与友人的书信中,胡适对诗歌革新的意图表现得更加突出:“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话怎么说,诗就怎么写”。[1]780即主张用口语去写诗,以文为诗,解放诗体。胡适之所以如此迫切地强调诗的“白话”化和散文化,目的在于剿灭旧体诗在语体方面的文言势力。然而问题并生,“白话诗”的重心在使用浅显晓畅的“白话”,对于诗的特质则缺少关注。因此,很早便激起了友人的反对,而胡适则坚定地表示“近来作诗颇同说话,自谓为进境,而诸先生不甚喜之,以为不像诗。话虽不谓然,而未能有以折服其心,奈何!”[1]838这段话一方面表达了友人对其“作诗颇同说话”的批评以及他的不服气;另一方面对于友人不能够理解自己对“白话诗”的良苦用心表示无奈。
那么,胡适为何这般执著地致力于新诗语言的改造呢?
胡适之所以重视语言和诗体的革新,是因为他深刻认识到了语言和文体之间的密切关系。旧体诗的语言基础是文言,为了推翻旧体诗,胡适有意勾勒出所谓“活文学”的发展脉络,并提出“这一千多年的中国文学史是古文学的末路,是白话文学的发达史”[2]5,从而向文言传统发起攻击。翻开他的《白话文学史》就能看出,他极力贬低杜甫晚年句法非常成熟的七律组诗《秋兴八首》,称其“都是一些难懂的诗谜。这种诗全无文学的价值,只是一些失败的诗玩意儿而已”。[2]355贬低杜甫的律诗毫无价值,目的就在于宣告文言是死去的文字、旧体诗是死去的文学。这样,胡适便顺势提出废除文言,建立起以白话为基础的“国语的文学”主张,为新文学(包括新诗)发展谋求出路。
但出乎胡适所料,“作诗如作文”的主张在降低白话诗写作门槛的同时,也造成了诗、话不分的尴尬局面,到了20世纪20年代后期,白话诗已经失去了市场。唯胡适马首是瞻的杨鸿烈在《中国诗学大纲》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新诗已经滥造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其中“混诗和语言为一”是最明显的一例,康白情《草儿·植树节杂诗》一类“都是白话,万不会是诗”[3]246。硕槐也指出,“新诗的毒隐微莫测,所以很多人不觉悟”,“习而不察,以为随便可以发牢骚”。[4]显然,白话诗运动在追求白话的同时,混淆了诗和文、诗和语言的界限,这种弊端在当时已经成为诗界包括新诗派在内的一个共识性问题。对此,作为新文学运动中文学研究会的重要一员,郭绍虞自觉为“研究旧文学,创造新文学”而求索。他敏锐地看出了胡适白话文学、语体文学这一主张的不足,不禁感慨道:“中国的文字假使此后不改为拼音文字,则无论如何提倡语体文乃至像现在一般人所主张的符合口语的语体文,我认为总不免受文字的牵制,不容易向这目标做去,达到完善的理想。”[5]这一论断显然是针对胡适建构国语文学的主张而提的,而立足点就在语言文字上。
郭绍虞不仅是文学批评史家,也是现代语言学家,这一点为他研究分析白话诗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从1927年起郭绍虞就已经注意到了语言与文学存在着密切关系,他在《论赋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位置》一文中指出,赋这一文体属于文学中的两栖类,非诗非文,亦诗亦文。因此,他将1924年左右盛行的散文诗,命名为“白话赋”。而20世纪20年代争议颇大的还有诗和小说的区界问题,当时有“小说的诗化”和“对诗的防御”的论战,郭绍虞所思考的正是新诗如何在文体上予以自立的问题。而郭绍虞之所以在1927年左右才将语言作为考察新诗问题的重要突破口,与格律派的主张也有一定的关系。在当时,闻一多已充分认识到了新诗“名为诗实是散文的居多”[6]3,遂将重心放在对中外诗歌形式的借鉴上来,着意从语言形式层面对新诗进行建构,而这恰恰给了郭绍虞以启发,促使郭绍虞将文学批评的视野放置到语言层面,将语言文字和文学批评很好地结合起来,从语言文字与文学的关系入手,从文体的角度对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规律作出总结。
按照语言文字之不同的关系结构,郭绍虞将中国文学分为五个时代,即“诗乐时代”“辞赋时代”“骈文时代”“古文时代”与“语体时代”。[7]第一阶段是“诗乐时代”,这个时代语言文字的关系表现为“语文合一”,即声音语、文字语还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差别。但郭绍虞强调,这个时代的语言文字只是比较接近,当时的“漆书”“简策”上使用的书面语,虽是人人共通的语言,可是已经过改造,并不是纯粹的口语。到了第二阶段“辞赋时代”,则言文开始分离,并沿着第一阶段“改造的口语”的路线继续前进,遂造成“离开语言型而向文字型演进的倾向”[7]。郭绍虞认为这个时代语文变化最为显著,由语言、文字的特点形成了语言型和文字型两种不同风貌的文学类型:一种是建立在单音节文字基础上,充分发挥文字的单音特长所形成的文字型的辞赋体制;另一种是“靠文字来统一语言”,即以古人的书面语为写作标准,郭绍虞将这种文学命名为“文字化的语言型文学”,如当时的史传文学就属于这一类。而这类文学不能等同于口语,是因为他们继承的是古人的书面语,所以如何追求口语化,也不能实现所谓的“言文一致”。第三阶段是“骈文时代”,这一时代文学家充分利用汉字一音一义的特点,形成了对偶工整、声律谨严的“文字型文学”,近体诗即为典型。物极必反,由于太过重于文字的特点而不顾语言方面的明畅豁达,于是到第四阶段韩、柳等人举起复古的旗帜,主张回到“古文时代”,使用古人的书面语,这样同第二阶段的问题一样,它也只是书面语,同唐代普通人所讲的声音语也不是一回事,也只是经过文字化的“语言型文学”。经过这一梳理,郭绍虞明确得出“古文、古诗是准语体文学”[7],准语体,只是向语体靠近,并非纯粹的、真正的语体文学。而真正的语体时代,要到宋代以后,随着语录体、戏曲、小说及方言文学的盛行,才算发挥了语言的特点。
显然,语言、文字的分合是造成文体殊异的重要原因。由五个阶段的文学类型,可以看出中国文学所凭借的语言文字,有时趋于文字语(“文字型文学”),有时偏重声音语(“语言型文学”),有时又追求言文合一的“文字化的语言型”;从整个过程来讲,也很容易看出文字语几乎都参与其中。“诗乐时代”虽以语言型为基础,但文字型这股暗流一直处于潜伏状态。到了“辞赋时代”,虽说模仿古代的“语言型的文学语言”,但古人的文学语言已经是改造过的。“古文”据郭绍虞所说“也是经过排列配合的特殊技巧所造成的文字语”,[5]特别是桐城古文家法中一直重视通过“音节”来体会文章的神理、气味,有别于说话语气。而“语体时代”的戏曲,实际上宾白中多夹杂着骈俪的文字语,所以只能说是主潮时期,决不能以整体命名之。
就语言文字与文学的关系来讲,有识力的新文学家大都以为文字与文学的关系要更为密切。周作人在《新文学的源流》第一讲中谓:“研究文学的人,当然先须懂得文字。”[8]10鲁迅在1926年前后完成的《汉文学史纲要》中,高度评价了汉字形音义三者兼备,可谓“一字之功乃全”。《汉文学史纲要》以“自文字至文章”作为首篇的标题,并谓“连属文字,亦谓之文”[9]3,这种解释与章太炎所讲“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国故论衡·文学总略》)是一个意思,可见周树人对文字之于文学的重要性有清醒的认识。周氏兄弟曾从章太炎治《说文》,他们有着较为深厚的文字学的功底和修养,因此能够在提倡白话文的大的潮流下,强调文字才是文学得以建立的基石,这对于规避白话诗文演变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是有意义的。
文言的基础是文字语,即书面语;而白话的基础是声音语,即口语。基于这种差异,语言和文字的二元对立成为近现代文学史上一直存在的重要现象,特别是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等新文学家将语言、文字之争视为活与死、新与旧的对抗。而胡适聪明的地方在于,他知道要想真正地建立起白话一统天下的格局,必须从文学革命入手,将语言的改造放置到文学的场域,毕其功于一役。胡适固执且想象地以为“作诗如作文”“作文如说话”在理论上可以成立,遂将文字和语言完全割裂开来。他只承认文学和语言的关系,没有甚至根本上就不想接受文字对文学的作用关系这一事实。然而,诚如郭绍虞所分析的,尽管文学演变的大势是趋于“语体时代”,但文言到底是不能从语体身上拨扯掉的,特别是文学语言。而胡适将声音语视为文字语的本质,竭力夸大“言文分离”的假象,但胡适之白话诗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众语运动”中也成为反驳的对象,以“新文言”的名义被贬斥。所以,胡适的白话诗理想就失去了理论和事实上的自恰性,从正反两方面凸显出这样一种结论:纯粹的声音语的白话诗是很难实现的,文字语在新诗诗性的建设问题上有着不可抹杀的意义。
二、形制上:骈、散兼宗
如果说,胡适“作诗如作文”的白话诗论,存在将语言和诗混为一谈的弊病,那么,郭沫若在主张从诗情上对其予以补救的同时,在形式上却进一步加速了胡适的诗体解放论。郭沫若提倡自由诗论,主张新诗的自由化、散文化,反对外在形式方面的一切格律对诗情表达上所构成的限制作用。郭绍虞是新诗创作的自觉实践者和支持者。1920年他的新诗《世界及流星》发表于北京《晨报副刊》,1922年文学研究会编辑的新诗集《雪朝》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其中第五辑为郭绍虞的十六首新诗。[10]他在《语文通论》一书中说道:“从文体演变上说,旧体诗以染指者众,难以为继,其势不得不另辟途径。从时代背景上说,社会机构既逐渐变动,则旧诗中所表现的雅人深致,不复能存在,自然只有渐趋于没落。于是运用新题材应用新形式的新诗,当然更有其生命。”[11]118所以,郭绍虞果断地认为新文艺远胜于旧体诗文的一点就在其能“创格”。这里的格正是从形制上来讲的。
郭绍虞认可散文诗,并根据“文学进化论”将中国文学的演变趋势归于自由化和语体化。他在发表于1926年的《试从文体的演变说明中国文学之演变趋势》一文中强调,“无论何种文体都有几种共同的倾向,即是(一)自由化,(二)语体化。而(三)散文化又是这二化的关键”。[12]30由此可见,肯定散文化是郭绍虞的基本立场。必须指出的一点是,郭绍虞所言的散文化已非胡适“话怎么说,就怎么写”的概念,这里的“话”是经过锤炼的文学的语言,同样的,散文诗是属于文字化的语言型的文学。这样一来,散文诗与旧体格律诗都离不开语词的锤炼,但二者又有明显的不同:散文诗是以复音节的汉语为单位,而传统的格律诗则是以单音节的汉字为基础。这样二者之间的分歧就表现为汉语和汉字的不协调性。
以汉语为单位的散文诗注重文法,而以汉字为基础的旧体诗则不必苛求词性的确定性。胡适等新诗人主张以“文之字”入诗,以自由化、散文化的诗句为诗,故而追求诗句的语序要固定。早在1920年以黎锦熙为首的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就制定了“词类连书”条例,为的是在原则上适应这种变化,但能否实现,还是一个问题。赵元任在《“连书”什么“词类”》(1933年)一文中给出了很好的解答,他说:“中国的白话的词类虽然有慢慢儿地变成两字词的神气,但是老实说,到底一半还是用单字词的。并且哪怕就是用多字词的时候儿,里头所用的单字的意思还是在说话人的脑子里头活着呢!并不像英法文的多字词里头的拉丁字的本来的意思都是半死半活的了。”[13]赵元任的意思是,即使在以复音节词为基础的现代汉语中,也改变不了单音节汉字在构词方面的作用,这种作用不会因词类连书现象的发生,其地位有所下降。比如说,“知识”二字,构成一个语词,但是“知”和“识”两字对于观者而言,并不随着两字连书就泯灭了各自的属性。
问题是,单音节的汉字是如何演变为复音节的汉语的?两者能否融通?对此,郭绍虞有着详细而周到的阐析。
郭绍虞将中国语词在声音方面的孳生繁衍的途径分为四种:其一,由单音重复而形成的重言,如茫茫;其二,由单音附加所形成的附加语词的相属连语,如旁边;其三,由单音的分合而形成的合音与双声叠韵;其四,由单音的变化而形成的平仄四声。[14]这就是单音节汉字衍变成为复音词的基本方式与形态,而他们的意义明显地体现在文学作品的修辞方面。
单音节的汉字与复音节的汉语,其区别与联系,据郭绍虞解释:“从书面语讲,目治的文辞不怕同音语词的混淆,为了要求文辞之简练,有时并不需要复音的词汇,依旧停留在单音阶段。”[15]所谓“目治的文辞”就是指用眼看,它是与“耳治的文辞”相对的。目治的文辞多是书面语,而耳治的文辞多是口头语,书面语不需要复音化,即读者可以通过眼观就能理解清楚文章所表达的意思,但口头语却因为同音字的问题,不得不采取复音化的办法。比如说,“衣”是目治的文辞,是书面语,我们无需复音化,也能理解它的意思;但是在口头语、耳治的文辞中就会发生歧义,因为与“衣”同音的字不止一个,如“一”“依”“医”等,这样的话如果没有具体语境的辅助,就很难分辨说者所表达的意思,所以只能靠复音节词“衣服”“衣裳”等去限定。这就是二者之间的矛盾之处。但这个矛盾绝非不可调和。从语词复音化的四种途径,不难看出每一种都是建立在单音节的汉字基础上的。郭绍虞指出,虽然汉字并不等同于汉语中的每个词,但汉语中每个语音的音节,因为结合得非常紧密而牢固,所以复音节的汉语也是用单音节的汉字来记录的,所以汉语被称之为“单音缀文字”。郭绍虞把双音节汉语和单音节汉字的这种不可协调性中的可协调关系,称为“语词的弹性作用”。
“语词的弹性作用”在文学作品特别是骈文、律诗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其作用在于形成匀整的句调和对偶的体式。郭绍虞按照“语词的弹性作用”在文学作品中的具体表现,将其分为四类,具体如下:
第一类,语词伸缩例,即语词成语之音缀长短,可以伸缩任意,变化自如。[15]
它又可分为“重言缩为单词”“单词衍为重言”“疾言徐言变化”“合体连语单用”“称名割裂”五种情况。
第二类,语词分合例,即单音语词可以任意与其他语词相结合或分离,复音语词也可分用,如单词。如单字不成词,特加一字成为复音词。[15]
它又可分为“助词之缀合”与“骈词之组合”两种情况。
第三类,语词变化例,即重言连语任意混合的结果,演变孳生为另一新语词。[15]
它又可分为“复衍连语”“缩合复重言”“连语合称”“重言连语合称”“组成相属连语”五种情况。
第四类,语词颠倒例,语词既可以分合变化,于是顺用倒用亦无限制。[15]
它又可分为“专名颠倒”“语词颠倒”“交体上应用”“古今语惯例”“修辞”五种情况。
以上伸缩、分合、变化、颠倒的四种语词形式,是郭绍虞从语言学、修辞学的角度作出的分类,很多术语都具有一定的专业性,今天我们很少提到,即使从当时来讲,郭绍虞的分类办法也是较为独特的。从他的每一种分类下又包含了更详细的节目,可见其研究功夫之深。
对于以上这些用例,这里不一一介绍,仅选取几例,窥其大义。比如,颜延之《秋胡诗》“燕居未及好,良人顾有违”,用的是《毛诗》中“或燕燕居息”之语。本来,只有“燕燕”重言,才能摹状鸟之比翼双飞之态,表达夫妻之情深,但颜延之之诗因为字数所限,不得不化复为单,以求句式整齐。而《诗经·邶风》“燕燕于飞,差池其羽”,单音节的“燕”衍为重言,既能将燕子比翼双飞之状描摹出来,同时在语气上有所延缓,是为了凑足四字句,与表意没有关系。再如《诗经·小雅》“渐渐之石,维其卒矣”,和《周南·卷耳》“陟彼崔嵬,我马虺阝贵”,据郑玄《毛诗传笺》云“卒者,崔嵬也”。郭绍虞分析说,第一处因为是四言诗,且有助词“其”,只能用疾言“卒”。第二处则因与“虺阝贵”对文,只能选用徐言“崔嵬”。再如《离骚》“忳郁邑余侘傺兮”,其中,单字“忳”与双声连语“郁邑”同义复用,依现代语法来看,本属累赘,但是古人因语缓重叠,并无辞费之嫌。
由此我们能够看出,这些语词的伸缩、衍化,是可以根据具体语句的对偶、双叠、长短、匀整以及语气的缓急等情况作出相应的调整、改变的,其弹性之大可见一斑。放在今天,我们会觉得有些词本身无意义,没有重复的必要,但是在古代的诗文中,却有着重要的断句或足句的功能,特别是经过颠倒、重复以后,能够求得语句的匀整、对偶和叶韵,而这些特点也决定了中国语和欧化的语言之间的一个最大的不同。中国的语词有“音句”和“义句”之分,比如“燕燕于飞,差池其羽”,前后两句如果单独出现,都只能称为音句,而只有将两句联合起来才能形成义句,表达完整的意思。音句的作用是为了协调语句,是为了诗歌音节的舒缓和审美的愉悦性,并不纯粹以表意为唯一目的;而且这些词性显然也不能够按照现代的语法观念进行一一明确的界定;所以胡适等新派诗人主张径直用表意为主的欧化句法,指斥旧体诗有凑句、繁复的毛病,要打破音节的束缚,但诚如郭绍虞所说“这是古人属文通例,不得以繁复病之”。[15]
那么,郭绍虞所总结的这些繁杂的用例,在讲求文法的现代又有什么意义呢?
反观白话诗文,因采用欧化的句调,读起来绕口,理解起来更与极端的文字语没什么两样。王力在《中国现代语法》中曾对现代汉语参照欧化的句法,使得语音趋于复杂化的情形作了大致的总结,概括出“复音词的制造”“主语和系词的增加”“句子的延长”“联结成分的欧化”四种方式。举例言之,如徐志摩《我所知道的康桥》:“它那脱尽尘埃气的一种清澈秀逸的意境可说是超出了图画而化生了音乐的神味。”这里用了复句,倘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则倾向于将其分成两个主谓分明的短句,表达为“它那一种清澈秀逸的意境脱尽了尘埃气,那种神味可说是超出了图画,化生了音乐”。[16]105两相比照,就可感觉到欧化的长句、复句,读起来既费力费气,从文义上来讲也较为费解。而中国化的语句,则划分为不同的短小的句子,既能舒缓语气,读来悠扬清远,更容易产生美感,增加接受的可能性。所以瞿秋白在《大众文艺的问题》(1932年)一文中批评胡适的白话文为“新文言”,批评“新文言的杜撰新的字眼,抄袭欧洲日本的文法,仅仅只根据于书本上的文言习惯,甚至违反中国文法的一种习惯”。[17]352
所以,郭绍虞提出的要充分重视、利用中国语言文字的特性来解决欧化的问题是有意义的。
中国语词的弹性作用很容易形成“匀整”“对偶”和“叶韵”的句调特点,这可以很好地优化欧化语言中的长句、复句。郭绍虞解释说:“求其匀整。则无论如何复杂的意义均可曲折达出,而不流晦涩,如佛经的翻译是。求其对偶。骈文在意义上虽觉难懂,而在诵读上却是方便。所以韩柳虽创古文,而唐宋四六依旧有其地位。求其叶韵,不匀整的固须用韵以为断句的标识,如长短句是;即匀整的也因用韵以后更觉郎朗上口。”[15]这三点虽然是就骈律化的诗文来讲的,但是在散文、语体文学中也有重要意义。如韩愈的《进学解》全篇虽以散行、杂言为主,但也多夹杂有四言、五言、六言的骈偶句,如“贪多务得,细大不捐”,“纪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等等。由此可见,中国文学史上,即使是古文运动,提倡散文、反对六朝的骈词丽句,但是终究没有黜骈。这进一步证明了讲究骈俪是中国语言文字的共性特征。诚如刘勰所讲“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文心雕龙·丽辞》)。现代新诗固然以学习欧化,主张散文化、自由化为目标,但是只要使用中国的语言文字,就必须承认它在构词、造句上所具有的特点,而且趋于骈偶也是不自觉的行为。诗是语言的艺术,自然不可避免地要从骈俪辞采中汲取养分。
三、音步划分:重视单音节汉字
新诗到底需不需要声律?如果需要,应该建立在什么基础上?
闻一多等格律派是较早从形式上对现代汉语诗歌的音节问题作出探究的。闻一多的研究思路是中西结合的,他在1922年所写的《律诗底研究》中就对旧体格律诗的音节、组织等方面的性质作了极为精细的考察,认识到了律诗乃是“中诗独有的体制”,新诗学不应将其完全否定,从而提出“不是揎弃中诗而代以西诗。所以当改者则改之,其当存之中国艺术之特质则不可没”[18]289的公允之见。这种不以新斥旧,不以西贬中的态度在当时无疑是可贵的。在《诗的格律》一文中,闻一多进一步提出新诗可以有“三字尺与二字尺,甚至另外的组合”[19],并且诗行也可以两个三字尺与两个二字尺为主,不断变化来设定。如“孩子们/惊望着/他的/脸色,他也/惊望着/炭火的/红光”,就是两个三字尺、两个二字尺,在节奏上形成四顿。
由此可以看出,闻一多的音尺划分标准是建立在现代汉语多音节词的基础上的。这种音节的划分方法在当时很有影响,形成“豆腐块”的诗,对于构建新诗的外形律颇有意义。
郭绍虞则对闻一多的音节论提出质疑。他批评闻一多的音尺和音顿存在不协调的地方:“有的顾到了每行的音步,却没有顾到每行的读,意义的停顿与音节的停顿不一定相符,便不免发生吟诵上的困难。”[11]128郭绍虞说的音步,就是上述闻一多所提的音尺。郭绍虞指摘闻一多以双音节、多音节来划分音尺、音句和义句的划分上存在龃龉不通的地方,有时候能够满足意义上的停顿,但是却不免在音顿上发生阻隔,顾得了一方,另一方却露出捉襟见肘之态。郭绍虞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矛盾冲突,是因为闻一多的音节论忽视了中国语言文字的属性。因此,他强调“音节的创造不能离语言文字的本质”[11]128。郭绍虞指出,以复音词为基础的汉语,以单音节词为主的汉字,很容易形成单音步和二音步的音节这一事实,提出新诗要充分利用“单复相合,短长相配”[15]的特点,来创造参差错落、铿锵顿挫的音乐美感;而且单音节的汉字兼具“同声相应”和“异音相从”的特性。基于以上两种规则,郭绍虞重点从以下几方面对新诗音节建设提出构想:
首先,在“同声相应”方面,郭绍虞指出要注意由子音和母音连缀而成的汉字,在双声叠韵方面的关系。他根据唐钺《国故新探》的考述,将双声叠韵皆作押韵考虑,接受了唐钺提出的“倒双声”“半双声”“旁纽双声”“应响”等元素,为新诗作殷鉴。所谓“倒双声”,即只要两字收声相同者,也算押韵,如“中堂”,“中”音为chung,“堂”音为thang,二者收声都是ng。“半双声”,如“端”和“透”属于“旁纽双声”,皆成因于口腔之同位。至于“应响”则是只要两字所含韵元相同并接连使用,就能创造一种音乐美。
其次,在“异音相从”方面,郭绍虞认为新诗应从音性与音势两方面着手探求更为丰富的抑扬律。
第一,音性上要充分利用平仄四声的变化。平仄是律诗所恪守的规则,四声在齐永明时期就主要用于求押韵之细密严格,至于沈约提出的“八病论”,即“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正纽”“旁纽”,据郭绍虞分析“此种问题不仅在后世不生影响,即在当时也无人遵守”。[20]所以“八病”不是声病,与四声平仄一样都可以用于构成异音相从的节奏。郭绍虞还指出要利用“入派三声”的演化趋势,为新诗音节服务。关于入声的问题,唐钺曾于1924年写有《入声的演化和词曲发达的关系》一文,说明了入声“急促、短收藏”,即收尾音不拖沓,现在这种音仍旧保存在方言中,如“不”“吃”等都是明显的入声字,它们与讲究“曼声而作腔”的词曲歌唱不相适宜,故其“收声”渐被淘汰,而归于平上去三声。郭绍虞接受了唐钺观点,提出“遇到其他三声字不妥而无可奈何之时,得一入声字便可通融过去”。[20]这一点也是被时人所遗忘的。
第二,利用音势上阴阳、高低、清浊、轻重的不同,也能形成抑扬律。鉴于音势根植于音素及音性,郭绍虞遂将三者结合起来予以分析。他指出,从音素的声韵之分讲,可以利用声在音势清浊方面的种种分别,如声位前后的变化、声类(气程由出之途)的不同、声气的清浊来联缀音节、调剂唇吻;还可利用韵方面的特点,如口、鼻韵分属阴、阳之声,齐撮是细音、开合是洪音,以及复韵的结合所产生的音强之不同,都能使音节富于顿挫之感。从音性方面考虑,平声有阴阳之分,阴声直而平、阳声高而扬,仄声亦可因声之抑扬分为上去,上声腔低、去声腔高,凡此种种,相互配合,都能生出许多的变化。
此外,郭绍虞在《从永明体到律体》一文中还对“双声叠韵”“永明声律论”及“律诗的平仄”三者间的关系有过非常深入而细致的分析,并指出声音语的双叠与文字语的声律论是可以交相并用的。文字音节上平仄的使用,可以补救滥用双叠所产生的诘诎之弊。如“纡余委蛇”属于连语性质的双叠语词,但四字皆为平声,读起来很有口吃的毛病,而一旦音调稍加以变化,如“著雨苦龃龉,苍茫荒羊肠”,读起来就不甚觉得节奏太过紧张。而唐律定型后,双叠也并未从平仄规则中剔除,最重要的是双叠可用以补救拗调,如韦应物“寒树依微远天外,夕阳明灭乱流中”一句,其音节关系为“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这里,上句中的“远”与“天”平仄失调,但因为“远”与下句中同样位置的“乱”是叠韵关系,上句中的“天”亦与同样位置的“流”是同为舌尖中音的双声关系。郭绍虞指出,这样“以合应救之,就不觉其拙”[14]。所谓“合应”是指双叠中偶式不限连语的整对关系。显然,律体定型后,单音文字的音节韵律并非铁板一块,不容越界脱轨,利用语言上的双叠也很能解决近体诗中声律拗扭的问题,方便诵读,使律体于拗峭苍秀中显出圆润流转之态。当然,这里只不过要说明的是,走向律体并不等于走向限制和毫无变通的格套中去。
由此可见,建立在中国语言文字基础上的音素、音性和音势方面的特点对旧体诗有用者,新诗同样可以取精用弘、广而用之。因此,郭绍虞不无欣喜地感叹道:“倘若新诗能注意到上述关系,人为地巧为运用,不失为一种新的尝试。人为的组合,有时比暗合于无心的更为和谐,更有意义”,“旧诗以每个字的音缀为单位,而新诗即以每个词的音缀为单位,可以增加很多的变化”。[15]这意味着新诗走向格律化并不见得就是束缚,也不是遁入旧体诗的窠臼中去了。
四、结语
新诗从诞生之日起,就着力在语言、形制、音节方面追新逐异,努力截断同旧体诗的联系。强调白话、语体文学以区别于文言文学;强调自由化、散文化以打破匀整、排偶的外形律;追求内在的情感韵律,以打破旧体诗积累几千年的韵律模式。新诗追求创格,这些自然不能一概否定,但是所谓的“创”,所谓的“新”,不是空中楼阁,无源之水,只要是中国诗,用中国的语言文字进行创作,就根本不可能彻底脱离中国化的语言文字习惯、蔑视经过先人试验成熟的韵律规则和片面地移植西方经验。从传统中汲取资源,在“新旧之争”激烈的时期,已经得到一定的认可。如胡适就已有所觉察,他在《谈新诗》(1919年)一文中对旧体诗中的双声叠韵问题重新予以审视,并极力提倡将其用到新诗的自然音节中;后来闻一多、刘大白、穆木天、梁宗岱等人都就双声叠韵的问题有专门的探讨和实践。这足以说明新诗人已经注意到音节的本土化问题。
郭绍虞关于语言、文字及其相关方面的分析,直接目的就是促进新诗形式的中国化,纠正过度欧化造成的不良影响。他敏锐地认识到语言文字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以由此入手展开分析,就语体文学、散文化、废音韵等问题作出一一回应,给予文学史和理论上的说明,清理了新诗建设过程中所存在的谬见。尤其是他提出的一些观点,能够发前人所未发,如入声、倒双声、声母、韵母、韵尾、韵腹等因素的各自特性及彼此间的关系,都是较为复杂而又重要的问题,这些观点在当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但是今后如果能有人在这方面作深入而专门的研究,总结成通则,相信对于依旧在形式方面继续探索的新诗而言是有启发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