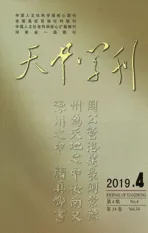《诗经》男性人物形象“美”的描写艺术
2019-01-19王亦玮
王 亦 玮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一、《诗经》中男性人物形象的分类
《诗经》的主题甚为丰富,从“国之大事,在祀与戎”[1]的祭祀和战争,到“宜其室家”“播厥百谷”的婚娶及农桑,涉及所属时代政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作为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对文学的贡献毋庸置疑,其中对女性形象的塑造尤为经典,为后世文学中的人物塑造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创作原型。事实上,《诗经》中不乏对男性人物描写的浓重笔墨。由于后来文学发展的历史局限性,无论是文学还是文化始终以男性审美为主导,《诗经》中极具特色的男性形象以及关于男性“美”的描写,往往不为人所留意。
通览“诗三百”,其中的男性人物森罗万象。《诗经》中的男性形象,以作者的态度划分,可以分做“誉”与“讽”两大类。继续细分,受到作者称赞的男性类型有政绩显赫的统治者(如《秦风· 驷驖》)、爱民善治的贤臣(如《召南· 甘棠》)、骁勇善战的将士(如《秦风· 无衣》)、温润如玉的君子(如《卫风· 淇奥》)、舍生守节的孝子(如《邶风· 二子乘舟》)等;被作者抨击的男性类型则有暴虐无能的昏君(如《陈风· 墓门》)、奸佞谋私的剥削者(如《魏风· 硕鼠》)、喜新厌旧的负心人(如《卫风· 氓》)、淫乱无礼的小人(如《陈风· 株林》)等。以人物的呈现方式划分,又可以分为直接描写的男性人物和间接描写的男性人物。直接描写的男性人物即通篇围绕该男性着墨,主题明确,褒贬分明,如《郑风· 大叔于田》以第三人称视角直接描述所见所知,用十分宏大的铺陈将主人公打猎时的威武英姿记录下来,且全篇描写集中于一人,目的是称颂共叔段(或说泛指猎人)的英雄气概。间接描写的男性人物在《诗经》中比例更大,多使用常见的比兴手法,不直言作者的创作意图,如《鄘风· 相鼠》《齐风· 卢令》用动物作比,以表达爱憎。
《诗经》以婚恋为主题的篇章,内容虽以女性为主,但其中也不乏与之相关的男性形象。这类形象多以被女子思慕的男子和追求女子的男子形象为主,如《秦风· 蒹葭》《郑风· 出其东门》以男子之口描述女子体盈貌美,其实是对专一痴情男性形象的成功塑造。此外,《诗经》中涉及社会生活的男性形象也不在少数:有厉声质问“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的劳动者,有无奈哀叹“自我不见,于今三年”的征夫,有激烈呼号“哿矣富人,哀此茕独”的贫苦人民,有高声诅咒“取彼谮人,投畀豺虎”的寺人小吏。这些男性形象实则代表了同样环境背景下的一类人,是群体式的男性形象。
由此可见,《诗经》中的男性人物类型繁多,描写方式多样,与女性形象塑造相比,两者既有相同之处,又各具特色。
二、《诗经》中的男性“美”
《诗经》中常以“美”字直接形容女子,如《静女》中“彤管有炜,说怿女美”,《野有蔓草》中“有美一人,清扬婉兮”,《有女同车》中“彼美孟姜,洵美且都”等,皆强调了女主人公美丽动人的仪态。《说文解字》释“美”:“甘也。从羊从大。羊在六畜主给膳也。美与善同意。”[2]可见“美”并不是形容女性的专属字。虽然一般很难将“美人”二字与男性相联系,但在《诗经》中,以“美”来形容男性的情况并不少见,如《简兮》中对于高大英俊的舞师,给予了“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的热情称赞。
《诗经》中男性的“美”大体可以分为三个层面。第一,体貌形态之美。对男性体貌形态之美的欣赏实则是人对“美”的本能关注和渴求,这种关注通常是无意识的、自然生发的。在《诗经》创作时期,已经基本完成了由女权社会向男权社会的过渡,男性成为当时最大的生产力。“当人类学会了审美以后,表现男性的这种美就被称为阳刚之美”[3]71,体现在《诗经》中就是女子对男子的倾慕与称赞。《汾沮洳》将男性的形态之“美”称扬到了极致:采用《诗经》惯有的模式,以“美无度”“美如英”“美如玉”将所慕男子之美层层推进。一个“美”字足以表达女子对男子俊朗形象的最高评价,加之每章结尾“殊异乎公路”“殊异乎公行”“殊异乎公族”的对比,更加凸显该男子卓尔不凡的气质。整篇虽无对男主人公外貌的具体描写,但从中也可以想见此人在女主人公心中近乎完美的形象。第二,修养气质之美。修养气质之美不再只关注男性“孔武有力”“颀而长兮”的健美形象,更加注重其内涵。以《淇奥》为代表,此篇以绿竹起兴,意在称赞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美德。《毛诗序》云:“《淇奥》,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听其规谏,以礼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诗也。”表明其所赞在德。这比起单纯地称赞外部形象更具审美价值,也意味着对男性“美”的关注由原始的本能上升为人文的内核。第三,先贤圣祖的大美。毫无疑问,这种颇具崇拜感、仪式感的美誉,多经人为渲染夸大,而逐渐脱离现实成为一种理想化的期待,集中体现在《雅》《颂》之中。如《崧高》“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万邦,闻于四国”对贤相尹吉甫德行、功绩的歌颂,远超过对“有匪君子”的褒扬。“男性美也从感性走向了理性”[4]9,对男性“美”最高层次的欣赏甚至尊崇是全民性的,才貌已然是“美”的附庸,真正的美在于这类人对国家、民族的杰出贡献。
三、男性形象“美”的描写
(一)衮衣绣裳——华丽服饰的描写
与女子形象塑造不同,《诗经》中对男子形象的勾勒很少出现“手如柔荑,齿如瓠犀,螓首蛾眉”这样对身体和五官的细节放大,取而代之的是对男性服饰细节的用心描摹。服饰是男性“美”的最直接体现,若将男性和女性服饰描写加以对比,不难看出《诗经》中男性的服饰、配饰通常都比女性更加绚丽繁复。在《诗经》中,女性的着装多偏向于素雅,我们也很难想象《蒹葭》《月出》这样苍茫洁白的背景中伫立的是衣着浓艳的女子。相较之下,《诗经》中男性服饰“锦衣狐裘”“黻衣绣裳”的情况比比皆是,《豳风· 七月》中“我朱孔阳,为公子裳”一句,说明贵族公子身着艳丽的红衣十分寻常。可以说在服饰之“美”上,男性绝对“艳冠群芳”,“在浅淡的背景中,在清淡的女性服饰映衬下,艳丽的男性服饰成为一道色彩亮丽的风景”[5]54。
服饰固然是“美”的,但穿着服饰的人是不是“美”,不可一概而论。羔裘是当时官员上朝时身着的礼服,《郑风》《唐风》《桧风》《召南》中都有对羔裘的描写,即使用意不同,羔裘这一服饰是华丽高贵的象征,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郑风· 羔裘》三章开头都以羔裘起兴,“羔裘如濡”“羔裘豹饰”“羔裘晏兮”,极尽细致地刻画羔裘的润泽华丽,意在赞美穿羔裘之人“洵直且侯”“孔武有力”。《桧风》《唐风》虽同样描写羔裘的华贵,却是为了讽刺那些尸位素餐的高官。
服饰描写是《诗经》中男性形象塑造至关重要的手段。在当时,服饰早已不仅作蔽体保暖之用,更多的是“礼”的要求。服饰的颜色、花纹、款式都有严格要求,体现着等级尊卑,不可轻易逾越。臧哀伯言:“衮、冕、黻、珽,带、裳、幅、舄,衡、紞、紘、綖,昭其度也。藻、率、鞞、鞛,鞶、厉、游、缨,昭其数也。火、龙、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6]诠释了服饰及其配件,甚至服饰的“文”“色”都是礼的象征。因此对于男性华丽服饰的刻画,不仅可衬托男子不俗的外观,又可体现其尚礼守德的内在素养。尤其是对于服饰细节的处理,最能以小见大,如《淇奥》提及“充耳琇莹,会弁如星”。“充耳”是挂在冕两旁的装饰品,多以玉质为主;“弁”指鹿皮制的帽子,“会”为皮子的缝合处。如此细节之处都极尽考究,其人通体衣饰之华丽精美可想而知。
出现的场合不同,身着的服饰自然不尽相同。男性服饰的类型有很多,朝服、宴服、猎服、婚服、战服等,皆各具特色。朝见时庄严典雅的礼服,尽可以凸显一派君仁臣忠的肃穆场面,如《小雅· 采菽》中“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大臣们统一穿着色泽鲜红的蔽膝,整齐地绑好裹腿,体现出大臣恭顺中显露出威仪的高贵之美。宴饮时与礼制相宜的服饰,可以表现主宾双方乐而不淫、规矩有序的场景,如《小雅· 頍弁》中三章的首句“有頍者弁,实维伊何”“有頍者弁,实维何期”“有頍者弁,实维在首”,强调了参会者佩戴的礼帽是多么端正,帽犹如此,想来宴席上嘉宾的通体着装必然十分规矩得体,才能让主人说出“既见君子,庶几说怿”这样赞扬嘉宾君子气度之美的话。阅兵时气宇轩昂的将领和士兵们身着战甲,展示的是一种威武英勇之美,如《小雅· 六月》中强调的“既成我服”“我服既成”,说明战服已经准备好,可以随时准备出战,是一种对己方强大军事力量的自信。迎亲时又是另外一种形象,因为“昏礼”在当时属大礼,婚服既是吉服又是礼服。《齐风· 著》描写前来迎亲的男子“充耳以素乎,尚之以琼华乎而”,这是女子对其未来夫君的观察。女子出于娇羞的心理,不敢仔细打量,只能盯着未婚夫高贵华丽的充耳,从悬挂充耳的丝带光彩耀眼,系着的美玉晶莹剔透,可以映衬出男子的华美形象。
对不同类型服饰“美”的欣赏,归根结底是对种种条件下“礼”的认同与尊崇。以狩猎为例,在农耕社会,狩猎的意义已经由提供生活必需品转向了“礼”的要求。“田猎活动不仅是‘礼’的象征,更是整个社会基本价值准则和行为规范的代表”[7],象征着等级制度的成熟与完善。《诗经》中大量赞美猎人的诗篇,表面看来是对男性矫健有力、威武英勇的夸奖,其实是礼制文化映射下的烙印。《小雅· 车攻》记述天子同诸侯田猎的盛大场面,朱熹《诗集传》谓:“周公相成王,营洛邑为东都,以朝诸侯。周室既衰,久废其礼。至于宣王,内修政事,外攘狄夷,复文武之境土,修车马,备器械,复会诸侯于东都,因田猎而选车徒焉。故诗人作此诗以美之。”[8]154朱熹认为该诗是借对田猎盛事的铺叙,来“美”诸侯“复会”天子这一尊礼行为。以此类推,可以说《诗经》通过服饰之美来刻画男子形象,是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当时“礼”“德”文化的潜在影响。
(二)公车千乘——宏大场面的烘托
场面描写属于“赋”的一种。朱熹在《诗集传》中说“赋者,敷也,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8]2,这一手法能“创造鲜明的形象和动人的意境,而远非一般的平铺直叙”[9]25,是《诗经》在男性形象塑造中极为常用的一种手法。《小雅· 采芑》共四章,属于《诗经》中的长篇作品,意在“美其成功,而原其老谋,著其宿望”[10]351。该诗男主人公“方叔”为周氏大功之臣,是《诗经》中常被赞誉的男性类型之一,但该诗没有具体呈现主人公方叔的体态样貌,而是通过对其领兵演习的细致描写塑造人物形象。首章方叔出场后,即将叙述的重点对准了方叔身后整齐严谨的战马、装饰威严的战车,即“乘其四骐,四骐翼翼。路车有奭,簟茀鱼服,钩膺鞗革”。第二章描写方叔的军队浩荡前行,军旗在风中飘扬,战马身上的鸾铃和方叔佩戴的青玉随着人马前进有节奏地响着,方叔“服其命服,朱芾斯皇”,穿着气派地坐在战车上,此时远方的“飞隼”时而高飞时而止息,战鼓震天地响,这是何等的气势。方叔坐镇在这千军万马的滚滚尘烟中,即使没有对他太多的特写,也能够使人感受到此人运筹帷幄、笑傲疆场的英姿。经过前三章的开阔铺陈,本诗末章坚定地喊出了“显允方叔,征伐玁狁,蛮荆来威”这样令外族侵略者闻风丧胆的口号。
这种对宏大场面极尽铺陈的描写多出现于《雅》《颂》中,主要对象一般是王公贵胄。《鲁颂· 閟宫》是《诗经》中篇幅最长的一篇,该诗以鲁僖公建造閟宫为主题,记叙了鲁僖公的种种功绩,包含着时人对鲁国在周王朝强盛时期尊贵地位的怀念。此诗前四章主要追溯周王朝的兴起及鲁僖公继承大统,在第五章篇头才以“公车千乘,朱英绿縢,二矛重弓。公徒三万,贝胄朱綅”为鲁僖公的丰伟形象壮大声势:他率领着数量庞大的战车,战车上立着长矛和大弓,成千上万的步兵随行,在这般行军气势下,僖公头盔上装饰的贝壳都显得英气逼人;侍从们拥护着僖公,信心百倍,警醒着敌军“烝徒增增,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则莫我敢承”[10]669。这一模式与《采芑》如出一辙,皆是从远处着墨,一步一步向男主人公延伸,却不在他们身上做过多停留,旋即又转回更广阔的视野中去。在被无限拓宽的场面中,主人公并不显得渺小,而是有着画面里最夺目的光彩,无论是衣着还是气势自是与众不同。如此一来,这些王侯将相就突显于无数尘埃之上,成为整个动态场面的主心骨,其尊贵威严、智勇伟岸的男性魅力就变得极为耀眼,颇有众星捧月的意味。
(三)我思古人——细腻的情感抒写
婚恋诗占据了《诗经》不小的比重,开篇第一首《关雎》对男女恋情的描写即奠定了爱情主题在《诗经》中的地位。然而,后人对婚恋诗的关注多集中于女性,忽略了男性在婚姻、恋爱作品中的重要地位。自古以来就有“女为悦己者容”的说法,处在恋爱中的女性总是艳丽姣好,殊不知男性在婚恋关系中一样有“美”的表现,这种“美”除了外表,更多地体现在情感上。在婚恋诗中,陷入思恋、求之不得的男性形象最让人动容。《陈风· 泽陂》中,一位痴情的男子日日望着远处铺满了蒲草与荷花的池塘,只因为岸边有他夙夜思念的女子。那“硕大且卷”“硕大且俨”的美人,让男主人公“寤寐无为,涕泗滂沱”,比起那些怀有相思之苦的女子有过之而无不及。该诗中男主人公最开始被女子高挑的身材、卷曲的秀发所吸引,又为其端庄的气质所倾倒,但不知出于何种原因,他的痴情并没有换来女子与其共度一生,故而他伤心欲绝,夜夜辗转难眠。从细节看,该诗三章首句换词,分别是“有蒲与荷”“有蒲与蕳”“有蒲菡萏”:荷主要以叶为主,蕳指莲蓬,菡萏则强调水上之花的形态。这说明男子的思慕不是一时兴起,而是绵长持久的,从碧叶到开花,从花落到结果,男子始终一往情深。《诗经》主要的创作时期,社会已进入了男权社会,在女性地位处于弱势的条件下,男子的专情可谓难能可贵。《郑风· 出其东门》中以男子之口直接说出“虽则如云,匪我思存”这般用情至专的誓言,何等令人动容。又有《邶风· 绿衣》一篇,是悼亡诗的经典之作。该诗中男子一看见亡妻生前缝制的绿衣,抑制不住对她沉痛的思念,反复摩挲着这件绿衣,仿佛往日有关妻子的种种画面都映上心头,不禁发出“我思古人,俾无訧兮”的哀叹,接着更进一步指明诗人穿着这件旧衣已经不能御寒,只得任由冷风凄凄。该诗既没有宏大的场面,又没有华丽的服饰,仅凭一件旧衣就引发了如此浓重的情感。这种情感真挚朴素,初看平淡,却随着时光沉淀愈加深沉。
除了这类哀婉的故事,男子细腻的情感也体现在热恋之中。《郑风· 女曰鸡鸣》末章中丈夫对妻子情感的回馈“知子之来之,杂佩以赠之。知子之顺之,杂佩以问之。知子之好之,杂佩以报之”[10]168,将夫妻间缱绻柔情一泻无余。正是这些生活中充满情义的零星片段,促成了二人“琴瑟在御,莫不静好”的恩爱岁月。
《诗经》中的男性形象并不都是深情专一的,也有像《邶风· 终风》这样狂傲暴虐、喜怒无常的男子。但女子面对“终风且暴”“谑浪笑敖”的丈夫,却仍然抱有“悠悠我思”“寤言不寐”的期待。此诗没有提及男主人公有什么值得女子怀恋的优点,只能猜测女子是被男子“谑浪笑敖”的浪荡子脾性所吸引。这种狡黠、乖戾的性格特点有时也颇受女性欢迎。《郑风· 山有扶苏》中女子钟情的对象就不是优秀的“子都”“子充”,而是“狂且”“狡童”。“狂且”在《溱洧》中是女子打情骂俏的对象,在郑国“狂且”是对爱人的昵称,“狡童”应与“狂且”意义相似,“有轻狡、狡黠之意”[11],是女子调笑的对象,“狂”与“狡”是他们的共同特点。虽然诗中没有记录他们的对话,仍然可以预想到他们面对女子的调笑不会无动于衷。这类男性的情感态度未必专一、痴情,但其幽默、狡黠的俏皮性格在《诗经》中同样散发着某种人格魅力,在后世文学作品中也是典型的男性形象之一。
除了服饰描写、场面描写、情感描写外,《诗经》对男性“美”的描写手法还有很多,如借女子之口诉说的侧面描写(《伯兮》),借动物特征加以形容的比喻手法(《卢令》),体现性格的语言描写(《庭燎》),等等。这些手法在文学作品的人物形象塑造中均有运用,可以说《诗经》对男性“美”的描写手法对后世文学手法的发展与成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