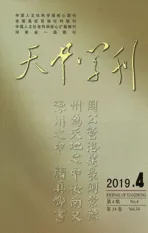《尚书》誓体研究述论
2019-01-19吴志刚
吴 志 刚
(南京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210023)
《尚书》研究的成果,可谓汗牛充栋。据王媛统计,仅20世纪80年代到2008年的20 多年间,国内就出版《尚书》研究专著70余部,发表研究论文近800 篇[1]。专著中,尚书学史方面约有30 余部,文本注解约33部,二者占全部论著的90%以上。这些论文中,关于尚书学史的研究成果约240 篇,占成果总数的30.0%;历史研究的论文约140篇,占17.5%;《尚书》思想研究和有关文本注解的论文均有105 篇左右,各占13.1%;语言学和文学研究论文各80 篇左右,各占10%;其他领域论文计30 余篇,约占4%[1]。在此期间,《尚书》的文体研究主要归属于《尚书》文学与语言学研究,成果并不突出。最近10年,《尚书》文体研究成为较为热门的议题,仅以《尚书》文体研究为题的博士学位论文就有多篇。潘莉在其博士论文《〈尚书〉文体类型与成因研究》的绪论部分,对包括誓体在内的《尚书》文体研究成果进行了述评,涉及文体分类研究、文体成因研究、文体功能内涵研究等[2]1―14,所述甚详。相较于其他五体,以《尚书》誓体为主要研究对象进行专题研究的现代学术成果,仅有几篇单篇论文以及数篇硕博论文中的相关章节,研究极为薄弱。与现代研究成果的单薄相呼应,古代学者关于《尚书》誓体的论述多零星分布于《尚书》文本注解类著作、总集类著作与诗文评类著作中,少有集中透彻的整体把握。因此,本文拟梳理历代与《尚书》誓体相关的论述与研究成果,围绕过往研究中的重点问题进行述论,以明确研究所取得的进展,为《尚书》誓体更进一步的研究奠定学术史及方法论基础。
一、《尚书》六体的成说梳判与誓体之为一体的理据
(一)《尚书》六体的成说梳判
《尚书》文体研究得以展开,得益于古代学者做出的文体划分,因为文体分类不仅是隶属于《尚书》文体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他诸如文体释名、文体功能、文体生成等诸方面研究在逻辑与实践上的起点与前提。
“六体”之说,最早出自孔安国《尚书序》,其文云:“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下,讫于周,芟夷烦乱,翦截浮辞,举其宏纲,撮其机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轨范也。”[3]11―12孔安国将典、谟、训、诰、誓、命并提,以之总括《尚书》各体之文,但并未给出“六体”的具体篇名和篇数。陆德明将“六体”分为正、摄两种,凡以典、谟、训、诰、誓、命之名命名者为“正”,不以上述之名命名但内容可以归入六体之内者称“摄”:“典,凡二十五篇,正典二,摄十三,十一篇亡;谟,凡三篇,正二,摄一;训,凡十六篇,正二,一篇亡,摄十四,三篇亡;诰,凡三十八篇,正八,摄三十,十八篇亡;誓,凡十篇,正八,摄二,一篇亡;命,凡十八篇,正十二,三篇亡,摄六,四篇亡。”[4]陆氏试图以“正”“摄”来解释“六体”之名与《尚书》篇名不对应的问题,虽给出了篇数,但未给出篇目。熊朋来《经说》则承陆氏之说:“典、谟、训、诰、誓、命,凡百篇,注者有正与摄之分,正者,有其义而正有其名;摄者,无其名而附其义。”[5]272并据百篇《书序》和伪古文《尚书》篇章给出了各体正、摄的篇名:“典,十五篇,正者二,《尧典》、《舜典》;摄者十三,《禹贡》、《洪范》、《汩作》、《九共》九篇、《槁饫》。谟,三篇,正者二,《大禹谟》、《皋陶谟》;摄者一,《益稷》。训,十六篇,正者二,《伊训》、《高宗之训》;摄者十四,《五子之歌》、《太甲》三篇、《咸有一德》、《高宗肜日》、《旅獒》、《无逸》、《周官》、《吕刑》、《典宝》、《明居》、《徂后》、《沃丁》。诰,三十八篇,正者八,《仲虺之诰》、《汤诰》、《大诰》、《康诰》、《九诰》、《召诰》、《洛诰》、《康王之诰》;摄者三十,《盘庚》三篇、《西伯戡黎》、《微子》、《武成》、《金縢》、《梓材》、《多士》、《多方》、《君奭》、《立政》、《帝告》、《釐沃》、《汝鸠》、《汝方》、《夏社》、《疑至》、《臣扈》、《咸乂》四篇、《伊陟》、《原命》、《仲丁》、《河亶甲》、《祖乙》、《分器》、《将蒲姑》。誓,十篇,正者八,《甘誓》、《汤誓》、《泰誓》三篇、《牧誓》、《费誓》、《秦誓》;摄者二,《胤征》、《汤征》。命,十八篇,正者十二,《说命》三篇、《微子之命》、《蔡仲之命》、《顾命》、《毕命》、《冏命》、《文侯之命》、《肆命》、《旅巢命》、《贿肃慎之命》;摄者六,《君陈》、《君牙》、《归禾》、《嘉禾》、《成王政》、《亳姑》。”[5]272至此,“六体”之名与《尚书》篇名不对应的问题告一段落。
自其表面观之,六体的分类方式似是以篇名末字为准,实质乃是以篇名末字确立正体与摄体(亦即变体),而摄体的区划,依据的不再是篇名末字的同异,而是篇章的内容。“六体”说之所以成为历来的主流,主要原因在于其分类标准并非仅仅依据篇名之末字,而是内外结合,只不过其内容上的区分标准未言明而已。
除了《尚书》“六体”的成说,孔颖达将伪古文《尚书》58 篇分为典、谟、贡、歌、誓、诰、训、命、征、范十体,并将各篇归入其类:“检其此体,为例有十:一曰典、二曰谟、三曰贡、四曰歌、五曰誓、六曰诰、七曰训、八曰命、九曰征、十曰范。《尧典》、《舜典》二篇,典也;《大禹谟》、《皋陶谟》二篇,谟也;《禹贡》一篇,贡也;《五子之歌》一篇,歌也;《甘誓》、《汤誓》、《牧誓》、《费誓》、《泰誓》八篇,誓也;《仲虺之诰》、《汤诰》、《大诰》、《康诰》、《酒诰》、《召诰》、《洛诰》、《康王之诰》八篇,诰也;《伊训》一篇,训也;《说命》三篇、《微子之命》、《蔡仲之命》、《顾命》、《毕命》、《冏命》、《文侯之命》九篇,命也;《胤征》一篇,征也;《洪范》一篇,范也。此各随事而言。《益稷》亦谟也,因其人称言以别之。其《太甲》、《咸有一德》,伊尹训道王,亦训之类。《盘庚》亦诰也,故王肃云:‘不言诰,何也?取其徒而立功,非但录其诰。’《高宗肜日》,与《训》序连文,亦训辞可知也。《西伯戡黎》云,‘祖伊恐,奔告于受’,亦诰也。《武成》云,‘识其政事’,亦诰也。《梓材》、《酒诰》分出,亦诰也。《多士》以王命诰,自然诰也。《无逸》戒王,亦训也。《君奭》周公诰召公,亦诰也。《多方》、《周官》上诰于下,亦诰也。《君陈》、《君牙》与《毕命》之类,亦命也。《吕刑》陈刑告王,亦诰也。《书》篇之名,因事而立,既无体例,随便为文。”[3]27―28历代论者均认为孔颖达是依据篇名之末字来分体定篇,属于“因名立体”,然而其关于《益稷》等篇章的归类,突出地体现为以各篇章的实际内容即孔氏所谓“事”作为归类依据。事实上,人们对孔颖达的分类方式一直存在着误解。孔颖达云“《书》篇之名,因事而立,既无体例,随便为文”,后世学者便以为《尚书》各体无体例而随便为文。其实,孔颖达所指乃是《书》篇之名。《书》篇之名,因事而立,因事有不同,故难有定例,故而“随事而立”。然而“事”总有属于同类之时,同类之事对言辞总有相近之要求,因此把篇名末字相同的篇章归为一类,绝非仅因篇名的相近,更多乃是因内容或功能上的相近,这即是中国古代文体分类的主要路数——“因文立体”。而“歌”“范”“贡”“征”四体则体现了孔颖达的另一种分类标准——“因文立体”。孔颖达对新立四体实际上是有整体考虑的:“……《禹贡》即全非君言,准之后代,不应入《书》。此其一体之异。以此,禹之身事,于禅后无入《夏书》之理。自《甘誓》已下,皆多言辞,则古史所书于是乎始。知《五子之歌》亦非上言,典书草创,以义而录。但致言有本,名随其事……”[3]27在论述“十体”之前的这段疏文表明,孔颖达是因为《禹贡》《五子之歌》《胤征》《洪范》四篇未涉及“君言”“上言”才将它们独立出来。这说明在孔颖达心目中,《尚书》是记载“王言”的书,而这四篇并非“王言”,只能另体归之。从这个角度看,孔颖达其实是将“十体”分为“王言”与“非王言”两部分,“王言”中有“六体”,“非王言”中有“四体”,惜其未能将归类层次明显表示出来,但据此判定其“最是无谓”,恐亦言之过重[6]16。
论者在综述《尚书》文体分类方式时,往往径直将“六体”或“十体”说的分类标准归之于篇名末字的同异,实则是只见其表而未见其里。“名”各随事而立,与其说是因篇名末字的相同而归类,毋宁说是因“事”的相同而归类。郭英德认为:“中国古代的文体归类主要采用了‘因文立体’的路数。也就是说,不是先有文类的设定,后有单篇文章的创作和归类,而是相反,先有单篇文章的创作,后有多篇文章因其文体功能或文体特征的相似性而合并归类,并为之命名。”[7]75现有研究成果表明,《尚书》篇章的命名发生在创作之后,即并非命题而作,这表明其命名方式本身便是一种分类方式,而其分类的依据或曰标准则是其内容。不过,各家对“六体”说或“十体”说虽有异议,然尚未深究篇章命名之时以内容的哪一方面或哪些方面作为分类的依据。
林之奇便不认可孔颖达的划分方式,其《尚书全解· 禹贡》云:“书有五十八篇,其体有六:曰典,曰谟,曰诰,曰命,曰训,曰誓。此六者,错综于五十八篇之中,可以意会而不可篇名求之。先儒乃求之于篇名之间,其《尧典》、《舜典》则谓之典,《大禹谟》、《皋陶谟》则谓之谟,至于训、诰、誓、命,其说皆然。苟以篇名求之,则五十八篇之义不可以六体而尽也,故又增而为十:曰贡,曰征,曰歌,曰范。虽增此四者,亦不足以尽《书》之名。学者不达古人作《书》之意,而欲于篇名求之,遂以一篇为一体。固知先儒所谓贡、歌、征、范,增而为十,盖有不知而作之者,不可从也。《禹贡》一篇,盖言禹之治水,其本末先后之序无不详备,名虽曰‘贡’,其实典之体也。学者知《禹贡》为典之体,则谟、训、誓、诰、命见于他篇,皆可触类而长。”[8]132《尚书全解· 洪范》云:“《书》之为体,虽尽于典、谟、训、诰、命之六者,然而以篇名求之,则不皆系以此六者之名也。虽不皆系于此六者之名,然其体则无以出于六者之外。”[8]445林氏此言针对孔颖达而发,认为“六体”之名与《尚书》各篇的篇名并不存在对应关系,但也承认“六体”是存在的。林氏反对机械地将“六体”落实到具体的篇章,而非否定“六体”之名与《尚书》各篇章之间的关联,如他认为《禹贡》实为典体,实质上是在篇名与内容之间更倾向于内容层面的分类标准而已。
其实,孔颖达的“十体”说并没有突破“六体”说的主框架,表明其认同六体篇名与内容之间的内在关联。无论秉持着内容层面上的何种标准,“六体”说均是被认可的。这成为后世进行单体或专题研究的前提与基础。就誓体而言,孔颖达云“《甘誓》、《汤誓》、《牧誓》、《费誓》、《泰誓》八篇,誓也”,熊朋来云“誓,十篇,正者八,《甘誓》、《汤誓》、《泰誓》三篇、《牧誓》、《费誓》、《秦誓》;摄者二,《胤征》、《汤征》”。姑不论正、摄之分,就誓体的篇章范围而言,是较为明确的。
(二)誓体之为一体的理据:《尚书》文体分类的诸方式及其标准平议
以上就古代关于《尚书》“六体”的成说进行扼要梳理,目的在于明确无论是基于内容层面的何种分类标准,“六体”说均可成立,而誓体作为“六体”之一,在古人眼中是一种独立的文体,这成为誓之为一体的理据之一。然而,古代学者也有认为《尚书》体例不纯或“书无定体”的。这其实是对“史体”与“文体”之别的误读,而其所关涉的乃是对于史官“记言”与“记事”之分的理解。
刘知几在《史通》中将隋唐以前的主要史书归纳为六种体例,即“六家”,《尚书》即为其中之一。刘知几认为《尚书》这一家“为例不纯”:“盖《书》之所主,本于号令,所以宣王道之正义,发话言于臣下,故其所载,皆典、谟、训、诰、誓、命之文。至如《尧》、《舜》二典直序人事,《禹贡》一篇唯言地理,《洪范》总述灾祥、《顾命》都陈丧礼,兹亦为例不纯者也。”[9]章学诚《文史通义· 书教上》则云:“《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今存虞、夏、商、周之策而已,五帝仅有二,而三皇无闻焉。左氏所谓《三坟》《五典》,今不可知,未知即是其书否也?以三王之誓、诰、贡、范诸篇,推测三皇诸帝之义例,则上古简质,结绳未远,文字肇兴,书取足以达微隐通形名而已矣。因事命篇,本无成法,不得如后史之方圆求备,拘于一定之名义者也。夫子叙而述之,取其疏通知远,足以垂教矣。世儒不达,以谓史家之初祖,实在《尚书》,因取后代一成之史法,纷纷拟《书》者,皆妄也。”[10]36认为《尚书》乃是因事命篇,本无成法。
无论是认为《尚书》体例不纯,还是认为《尚书》本无成法,实质上均是站在“史体”的角度而非“文体”的角度看待《尚书》的。所谓“史体”,乃是指撰述历史的体例,如章学诚在《书教》中曾作“记注”与“撰述”之分,而“文体”则是就其某一篇章而言的,只是“史体”的组成部分之一。作为整体层面的“史体”为例不纯,并不妨碍作为局部的“文体”有其成法。章氏谓“因事命篇,本无成法”,而文之成其为一体,乃是就体例相同或相近而类从,进而与它类相较以类分,《尚书》各篇章多是基于特定需求的应用型文本,势必需达成一定之目的,基于这一要求,对言辞必然有所规约,有规约则开后来同类之篇章的“成法”。
由此关涉到的史官“记言”与“记事”之分,实则和“史体”与“文体”之别密切相关。《礼记· 玉藻》云:“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11]班固《汉书· 艺文志》云:“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12]现代学者在对《尚书》文体进行分类时,往往把“记言”与“记事”作为语言形式或表达方式看待,却忽视了二者的历史语境。“记言”与“记事”作为史官的职责分工,所带来的是《春秋》与《尚书》两种“史体”的差别。不过,由于只是分工的不同,且记录下的“言”与“事”还要经由掌管档案的史官整理,故而原初形式的记录并不就是《春秋》和《尚书》,因此呈现在后人面前的两部史书整体上呈现两种不同的“史体”,但也有交叉、融通之处,并非纯然是“言”与“事”的区别。因而章学诚云:“《记》曰:‘左史记言,右史记动。’其职不见于《周官》,其书不传于后世,殆礼家之愆文欤?后儒不察,而以《尚书》分属记言,《春秋》分属记事,则失之甚也。夫《春秋》不能舍传而空存其事目,则左氏所记之言,不啻千万矣。《尚书》典谟之篇,记事而言亦具焉;训诰之篇,记言而事亦见焉。古人事见於言,言以为事,未尝分事言为二物也。刘知几以二典、贡、范诸篇之错出,转讥《尚书》义例之不纯,毋乃因后世之空言,而疑古人之实事乎!《记》曰:‘疏通知远,《书》教也。’岂曰记言之谓哉?”[10]38这提示我们在考察文体的文本时,需紧紧把握“历史性”这一原则,注意到文本定本状态的形成经过了一个历时的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史官分工、文献编纂和传播流传等诸种因素可能产生的影响。而“史体”与“文体”“记言”与“记事”的分别,则又提示我们需对研究对象进行准确的定位与剥离——从“史体”中剥离出“文体”,在“记言”与“记事”中定位“文体”,如此方能做到有的放矢。
现代学术关于《尚书》文体的分类,较之古人多以篇名末字的异同作为准的,对内容层面分类标准的探索则更深了一层,即其分类的背后实则是在追问文本内容的何种组成部分具有文体学上的分类标准意义。
其一,以记叙方式作为分类的标准,将《尚书》的文体分为“记言”与“记事”。蒋伯潜《十三经概论》就将今文《尚书》28 篇分为记事之文与记言之文,其中记言之文包括《尧典》《禹贡》《金縢》《顾命》4 篇,其余则均为记言之文[13]。有论者将这种分类方式溯源于《礼记· 玉藻》与《汉书· 艺文志》。前文已言明,这一区分方式可能存在误读。“记言”与“记事”原是“史体”的分类方式,以之作为标准,无形中取消了“文体”的身份。不过今文《尚书》誓体篇章全都属于记言之文,无疑是对其整体特性的一种认定。
其二,以功能与形式组合而成的多重标准作为分类依据。郑振铎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将今文《尚书》28 篇分为誓辞、文诰书札和记事的断片三类,他认为《甘誓》《汤誓》《牧誓》和《费誓》属于誓辞一类,而《秦誓》属于文诰书札之类[14]。誓辞与文诰书札的划分依据是文体功能,其与记叙方式结合在一起形成二级分类法,而在文体功能内部,将《秦誓》归入文诰书札,则主要是取其“告”义之功能,但对“誓”作为一种文体的“声讨”与“责罚”功能则有所不及。这表明郑振铎对文体功能的分类尚不够周密。陈梦家《尚书通论》亦将今文《尚书》体例分为诰命、誓祷和叙事三类,其中师旅之誓有《甘誓》《汤誓》(《泰誓》)《牧誓》《费誓》《秦誓》[15]。自表达方式的角度视之,诰命与誓祷是言行方式,叙事是记叙方式;自文体功能角度视之,前两类功能明确,而叙事的文体功能则隐晦不明。在郑振铎、陈梦家两位先生的分类标准下,《尚书》誓体的篇目范围进一步稳定,且二人已经对誓体的文体功能有所关注。
其三,以篇章名称与体例之关系为标准。对此做出重要贡献的学者是于雪棠。他通过对《尚书》文体分类及行为与文本关系的考辨,认为《尚书》文体源于篇章命名方式,而篇章命名是以行为动作为轴心形成的,《尚书》六体之名的确立经历了由行为之名转为文体之名的过程[16]。他还通过行为与文本关系的考察,确认了行为与文本体例之间的关联,而誓体之名与其体例之间确实相合,表明“誓”作为一种文体确实是成立的。
如果说以上均是以包括誓体在内的《尚书》文体为对象进行的专题研究,那么随着文章学观念的成熟以及作为现代文学类型观念的散文概念进入中国学术之后,《尚书》被视为中国文章与古代散文之源。散文作为一种现代的基本文学类型,与中国传统散文(文章)的内涵与范畴虽不尽相同,但传统文章学和现代散文学研究均试图对文章进行整体性的把握,并由此形成系统的分类体系。具体到誓体而言,则可在此体系中明确其地位及功能。
以传统文章学为视角,梳理涵容《尚书》文体的各类总集的分类体系,有助于理解古人对誓体篇章的定位与理解。黄佐《六艺流别》从“文本于经”的观念出发,首次以选本的形式将古代的基本文体形态分系于《诗》《书》《礼》《乐》《春秋》《易》六艺之下,形成六大文体类别,重新建构了中国古代文体的庞大谱系:“……《书》艺:典、谟。典之流其别有二:命、诰。谟之流其别有二:训、誓。命训之出于典者其流又别而为六:制、诏、问、答、令、律。命之流又别而为四:册、敕、诫、教。诰之流又别为六:谕、赐书(附:符)、书、告、判、遗命。训誓之出于谟者其流又别而为十一:议、疏、状、表(附:章)、笺、启、上书、封事、弹劾、启事、奏记(附:白事)。训之流又别而为十:对、策、谏、规、讽、喻、发、势、设论、连珠。誓之流又别而为八:盟、檄、移、露布、让、责、券、约。”[17]黄佐以源流为标准,将誓体视为谟体之流,给誓体进行了文体定位。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则以“门、类”为文体层级标准,建立了中国古代文章学的体系。他将文章分为著述门、告语门、记载门,其中著述门下分为三类:论著类——著作之无韵者,词赋类——著作之有韵者,序跋类——他人之著作;告语门下分为四类:诏令类——上告下者,经如《甘誓》《汤誓》《牧誓》等,奏议类——下告上者,书牍类——同辈相告者,哀祭类——人告于鬼神者;记载门下分为四类:传志类——所以记人者,叙记类——所以记事者,典志类——所以记政典者,杂记类——所以记杂事者[18]。著述门、告语门、记载门实则依据的是三种不同的标准,且“门”下之“类”的区别标准也未能做到统一周延,不过整体而言,是以内容和功用作为分类标准的,而在此标准下《甘誓》《汤誓》《牧誓》诸篇归为一类,表明了其为一体的同一性。
陈柱在《中国散文史· 序》中从文体角度将中国文学分为六个时代,将自虞夏至秦汉之际定为骈散未分之时代,又以文学与治化、学术之关系为准则将中国文学分为七个时代,其中夏商至周初是“为治化而文学”之时代,春秋之世“由治化时代而渐变为学术时代”[19]1―3。依照陈柱的划分,誓体的跨度,就文体角度而言,在骈散未分之时代;就治化和学术之关系言,则横跨前两个时代。前一划分标准以语言形式为主,后一划分标准以功能或目的为主。由此,陈柱对誓体进行了全面的定位:“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古代治化之文,不外记事记言二科。夏代之文,记事之最工者,莫如《禹贡》;记言之工者,莫如《甘誓》。”[19]6“(《甘誓》)此文为后世誓师文之祖。《史记· 夏本纪》云:‘启遂即天子之位,是为夏后帝启。有扈氏不服。启伐之,大战于甘。将战作《甘誓》。’则《甘誓》真当日誓师之词,而夏史录存之者也。其文奇偶互用,简而有法,后人为之千百言,逊其严肃矣。其后汤之伐夏作《汤誓》,武王伐纣作《牧誓》,均效其体。今附录于后,既以见文章之流变;亦以见文体既同。虽古之圣人,亦不能禁其相似也。”[19]14―15可知《甘誓》《汤誓》《牧誓》这一文体谱系是被陈柱认可的。不过以陈柱为代表的早期散文史家并未在其著作中明确建立起散文这一文类的体系,因此誓体篇章也只是归于散文一类,其作为散文这一文类下位文体的身份并未得到确认。
褚斌杰、谭家健在《先秦文学史》中明确提出了“尚书体”这一称谓:“《尚书》这种庄重典正的文体有其局限性,大抵只能作为政府的文告,却不便于人们思想感情的交流,因此,自春秋末年以后就很少在社会上流行了。不过,汉以后历代皇室文告往往还要模仿它,以表示威严与庄重。刘勰说:‘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文心雕龙· 宗经》)从汉武帝的《策封燕王旦》、《策封齐王闳》到明清某些诏告,常要用堂而皇之的‘尚书体’来撰写。它也是历代企望登上仕途的读书人学习和应试的课题之一。《尚书》对后世特别是对官方文告的影响,是十分邃远的。”[20]177―178不过两位先生这样的定义可能稍有不协。该著明确给《尚书》定性:“《尚书》意即上古之书,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散文总集。”[20]169既然《尚书》是一种总集,那么这里的《书》便不太可能是文体意义上的一“体”,因此《尚书》整体作为文学体裁是否能够成立实则存疑,故而在此处“体”的含义应该更接近于“风格”。两位先生所言“尚书体”实是以风格为着眼点,对《尚书》进行总体风格的观照。
褚斌杰在《中国古代文体概论》中,将包括誓辞在内的《尚书》文章大都归为公牍文类中的下行公文,归属于诏命之文[21]。至此,包括誓体在内的《尚书》各体作为散文下位文体的身份始得以阐明。陈必祥《中国散文文体概论》则力图以多重标准建立古代散文文体的整体体系:“……可以采用层面分类法,每一个层次采用基本统一的标准。如按语言形式分,所有文章可分为韵文、散文和骈文。关于散文的分类,可按表现手法和应用范围相结合的原则,先分为记叙性散文、说理性散文和应用性散文三大类。这三大类中,再根据内容和表现形式进行下一个层次的分类。”[22]5不过他认为《尚书》是散文的萌芽状态,包括誓体在内的《尚书》六体并未形成一定的体式:“《尚书》大多是一些誓词、政府文告和贵族的训诫之词。按其内容分,不外典、谟、训、诰、誓、命诸体。典,重在称颂尧舜德教;谟,意在赞许君明臣良;训,有教诲启迪之义;诰,为晓谕臣民之辞;誓,是约束士民之言;命,为号令臣工之诏。虽有六种分别,并未形成一定的体式。但后世的‘诏令’、‘奏议’、‘论辩’、‘叙事’、‘哀祭’、‘传记’等文体,皆滥觞于此。如《洪范》属于论辩;《无逸》属于奏议;《甘誓》属于诏令;《禹贡》、《顾命》属于叙事;《尧典》属于传状;《金縢》属于哀祭。”[22]34―35陈先生关于《尚书》六体并未形成一定体式的观点,对包括誓体在内的《尚书》文体成熟度的认识略显保守。
邵炳军在《先秦文系年注析丛书》总序中提出了其对先秦散文分类的看法以及建立科学散文文体分类体系的构想。他立足于客体的价值功能,建立了“文类—文系—文族—文种”的四层体类系统,誓体作为文种,属于事物文类下的军事事务文系①。邵炳军的这一散文分体分类体系,无疑强化了誓体作为一种文体的合法性。
综合传统文章学与现代散文学的分类体系及其标准,可以明确包括誓体在内的《尚书》六体是散文这一基本文类的下位文体,而这正是誓体作为一体的合法性所在。
二、誓体的释名与功能研究平议
(一)誓体的释名:行为与言辞双重理解视角
在关于誓体的诸多论述中,不少是以对其进行释名的方式呈现的。历代对包括誓体在内的《尚书》各体的释名,或是侧重于对行为的认定,或是侧重于对言辞的界说,或是凸显了从行为到言辞的完整过程。
侧重于从行为角度对“誓”加以认定者,较有代表性的有:《说文》云:“誓,约束也,从言折声。段注曰:周礼五戒。一曰誓,用之于军旅。按凡自表不食言之辞皆曰誓,亦约束之意也。”[23]《释名》云:“誓,制也。以拘制之也。”[24]《墨子· 非命》上云:“所以整设师旅、进退师徒者,誓也。”[25]《文心雕龙· 诏策》云:“誓以训戎。”[26]358宋林之奇《尚书全解》云:“古者将欲整齐其众而用之,则必有誓,而尤严于军旅。故《书》有六体,誓居其一焉。大抵为誓师而作也。《周官· 士师》之职:‘以五戒先后刑罚。一曰誓,用之于军旅。’军旅之有誓,盖所以宣言其讨罪之意,谨其坐作进退之节,而示之以常刑之必信。帝王之世所不能废也。故禹、启、汤、武皆有之。”[8]223吴讷《文章辨体序说》之《诸儒总论作文法》录宋张表臣《珊瑚钩诗话》云:“道其常而作彝宪者谓之‘典’;陈其谋而成嘉猷者谓之‘谟’;顺其理而迪之者谓之‘训’;属其人而告之者谓之‘诰’;即师众而誓之者谓之‘誓’;因官使而命之者谓之‘命’……”[27]从上述论述中,可以归纳出“誓”的重要特质:就行为的发生场合而言,用之于军旅;就行为的主导作用而言,用以拘束、拘制、训诫;就行为的作用对象而言,宣训我众、师众。
侧重于从言辞的角度加以界说者,较有代表性的有: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誓’:按誓者,誓众之词也。蔡沈云:‘戒也’。军旅曰誓,古有誓师之词,如书称禹征有苗誓于师,以及甘誓、汤誓、泰誓、牧誓、费誓是也。又有誓告群臣之词,如书秦誓是也。后世无秦誓之类,而誓师之词亦不多见,岂非放失之故与?今存一首,聊备其体云尔。又约信亦称誓,则另附于盟焉。”[28]薛凤昌《文体论》:“‘典’是典册高拱,谓尧舜的德教,可为后世常法;‘谟’是嘉谋嘉猷,谓禹与皋陶、益稷等赞襄献替,君明臣良,可为后世懿范;‘训’是诲导启迪之义;‘诰’为晓谕臣民之辞;‘誓’为约束士民之言;‘命’戒饬臣工之诏。”[29]从上述论述中,亦可归纳出“誓”的重要特质,即“誓”是一种从誓师这一特定行为中生成的用以约束士民的言辞。将行为与言辞两个角度沟通,无疑可以勾勒“誓”这一文体作用对象、作用场合的整体形貌。
文体拥有名称时往往已形成相对稳定的体例,即名实之间具有对应性。因而对于文体之名的认定,实则是对文体自身的一种认定。而通过对文体释名的梳理,会发现对文体的释名一般与文体的功能紧密相连,对誓体而言尤其如此。
(二)誓体的功能:“文体”与“书体”的多维向度
论述《尚书》的文体功能,需要明确其所具有的多元性与历史性。单个文体的文本最直接的现实功能是基于特定的需求而用以达到某种目的,就誓体而言即为了实现整齐师众、淬砺士气与宣扬战争的合法性,而达到获得战争胜利的目的,这是应用型文体的典型功能。文体文本的深层次功能,在于作为一个整体性的文本系统而实现的目的,这个整体系统可称为“书体”,而誓体所有篇章就是“书体”的组成部分之一。从“文体”到“书体”的转变需具备一定的历史语境,换言之,由原有“文体”的现实功能向“书体”功能嬗变的条件是历史语境的改变。
朱岩《〈尚书〉文体研究》认为,从初始有类无名的史官集结,到以“《虞》书”“《商》书”相称,再到以《书》定名,这个过程其实就是“六体”原有功能日渐消失和书教功能日益增强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起着推动作用的,便是“掌书以赞治”与“顺书以造士”的《尚书》学致用取向。在这两个致用取向的影响下,“六体”离原有的应用场合越来越远,离赞治造士的功能越来越近,普适性日益增强,形成了独具书教功能的“书体”[6]35―36。从作为“文体”的单个篇章,到作为“书体” 的一类篇章汇集,其中功能转折的节点,在于《尚书》的整体编纂与整理。而关于《尚书》的编纂与整理,前人多从历史或思想角度揭示其意义,如若从文体的视角观之,则可知其功能与其发挥作用的历史语境之间的深刻关联,这便是文体功能所具有的独特的历史性。
历代学者对于包括誓体在内的《尚书》文体功能已有论述。伏胜《尚书大传》卷三引孔子云:“六誓可以观义,五诰可以观仁,《甫刑》可以观诚,《洪范》可以观度,《禹贡》可以观事,《皋陶》可以观治,《尧典》可以观美。”[30]《孔丛子· 论书》亦引孔子说:“吾于《帝典》见尧舜之圣焉;于《大禹》、《皋陶谟》、《益稷》见禹、稷、皋陶之忠勤功勋焉;于《洛诰》见周公之德焉,故《帝典》可以观美,《大禹谟》、《禹贡》可以观事,《皋陶谟》、《益稷》可以观政,《洪范》可以观度,《泰誓》可以观义,‘五诰’可以观仁,《甫刑》可以观诫。通斯七者,则《书》之大义举矣。”[31]《颜氏家训· 文章》云:“夫文章者,原出五经:诏命策檄,生于书者也;序述论议,生于易者也;歌咏赋颂,生于诗者也;祭祀哀诔,生于礼者也;书奏箴铭,生于春秋者也。朝廷宪章,军旅誓诰,敷显仁义,发明功德,牧民建国,施用多途。”[32]“六誓可以观义”“《泰誓》可以观义”“军旅誓诰,敷显仁义”等论述,表明誓体篇章具有体现与宣扬道义的功能。而以上论述,是从整体角度对誓体做出的功能界说,而非单纯现实事件层面的界定,也即是誓体作为“书体”的功能,而非其最原初的“文体”功能。
现代学术成果对誓体功能内涵的揭示也侧重于其作为“书体”的功能。过常宝《先秦散文研究——早期文体及话语方式的生成》对《尚书》文体进行了分类,认为《尚书》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是以八诰为中心,包括誓、命、训等在内的周初政治文献;二是以典、谟为主的追溯性政治法规文献。周初八诰是周公通过宗教仪式,假天命祖灵之名而颁行的政治纲领。它们具有鲜明的现实意义,是周公制礼作乐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仪式性文献。典、谟等则借助上古尧舜禹等的名义,通过对流传的宗教乐舞或祭仪进行重新阐释,形成具有普遍意义的政治法典,对社会进行指导,这部分文献是周公神道设教理念的体现[33]112。在誓体篇章中,既有属于周初政治文献者,如《牧誓》;又有属于追溯性政治法规文献者,如《甘誓》《汤誓》等。过常宝在论述中主要以《牧誓》为例,探讨了誓体的成因、基本程式与功能,不过其所强调的重点依然在誓体篇章作为一类文体文本所具有的“书体”功能,即神道设教以维护统治[33]95―100。
誓体原初的文体功能是整齐师众、淬砺士气、宣扬战争合法性,而这种功能内涵的转移,实则彰显了包括誓体在内的文体从应用型文本转向教化型文本的历程。誓体作为原初的应用性极强的文体,这一转变的痕迹特别明显。前面说到的“六誓可以观义”“《泰誓》可以观义”“军旅誓诰,敷显仁义”等,表明作为“书体”的誓体具有道义载体也即所谓“义府”的功能。
对“文体”意义上的誓体功能的探究,现代学术研究也有所推进。潘莉在其博士论文《〈尚书〉文体类型与成因研究》中提出,誓体与古代帝王争夺军权的策略紧密相关:在争夺和巩固政权的过程中,战争是必不可少的,如何运用文韬武略取得战争的胜利是古代政治家考虑的重要问题;《尚书》的六篇誓词充分显示了中国古人的作战指挥和战术策略;人们往往在誓词中打出“替天行道”的旗帜,这让他们首先在政治斗争和战争中占据了道义的制高点[2]96。邹文贵《先秦誓言体战争散文论析》提出,誓辞是王权、军权与神权三权交汇的强制性话语,其功能在于克服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权力意志与社会认同的双重矛盾,解决战争的号召力与驱动力问题[34]。
与作为整体文本系统的誓体功能研究需要关注历史语境密切相关,在对誓体作为单个文体的功能研究中,历史维度下的受众视角作用尚未被完全抉发。于雪棠在《〈尚书〉的文体分类及行为与文本的关系》一文中,敏锐地关注到了发言人与受言人的上下级关系,可谓著其先鞭。然而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这种对受言人的关注主要还是抽象性而非具体性的,换言之,该文对历史性的关注还稍微欠缺。誓体篇章的纵向跨度有一千多年,在这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受言人的身份、特质已发生了变化,但论者还多从宗教礼制的嬗递、思想观念的变迁等角度着眼,实则是探讨外部环境对誓体的制约,如若对受言人身份多加关注,便可发现誓体是如何在文体内部对外在的宗教礼制与思想观念有所回应的,也只有在此双向互动的层面上,对誓体功能的把握才可能是全面的。
三、誓体的生成与文体形态研究平议
文体的生成指文体的形成过程,包括文体的成因与体例的历时演进过程。成因与彼时的历史背景紧密相连;体例在本文中指体裁与类例。体裁是应用于不同场合的文学样式,往往与文体功能密切相关;类例指文本的具体组成部分,是一类文体之文本所共有的惯例。文体形态在本文中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一为外在的载体形态,包括口传与成文等;二为内在的文本形态,指称的乃是“语言系统”与“结构体式”,这接近于文体生成部分的“类例”,但具有更大的普适性。如果说文体生成关注的侧重点在于起因溯源与纵向的誓体体例形成过程,那么文体形态则关注横向的文体体例细化研究。
于文哲从《论语· 尧曰》与《尚书· 汤誓》的比较出发,辨析“祈雨祷词”与“战争誓词”、“誓神”与“誓众”,考索了誓体的起源与功能演变,认为誓的起源意义乃是祭祀活动中的誓神之辞,随着祭祀活动向具体礼仪活动的转变,誓的意义由誓神之辞转向具体场合的誓众之辞[35]。于文哲将誓体成因归于早期祭祀活动的需要,并对誓体的演进提出了自己的解释,但对祭祀之誓与《尚书》军旅之誓之间的关系并未过多着墨,对誓体体例形成与演变的研究也稍显单薄。持类似观点的学者还有江灏、钱宗武以及李零等,但他们均是偶尔言及,未形成专论,故不赘述。
潘莉在《〈尚书〉文体类型与成因研究》的相关章节中,从先秦祭祀仪式、三代“纳言”礼制以及西周军礼等角度较为全面地爬梳了誓体的成因,认为誓体生成于先秦礼制活动之中,并比较了誓体与征体两种文体之间的区别[2]。但由于论题所限,潘莉没有对誓体体例的历时演进过程做出论述,是一个遗憾。叶修成在《西周礼制与〈尚书〉文体研究》一书[36]中指出,誓体生成于誓礼之中,是由相应的言说行为方式生成的,而言说行为又是在相应礼制之下发生的,是礼仪行为。接着,他又具体论述了先秦祭祀、会盟、约剂及军旅之誓的仪式性特征以及其宗教性和政令性合二为一的文体特征,涉及文体生成、文体功能及文化内涵。然而叶修成对《尚书》誓体文体形态的演进没有论述,亦是一大憾事。
潘莉和叶修成的研究均建立在誓体篇章的共性基础之上,而忽视了其共性形成过程中的差异性,对誓体历时考察重视不够,造成誓体文体形态及其演进研究的缺略。且他们均认为誓体的成因是现实政治的需要,而非祭祀活动的要求。现实政治需要与祭祀活动要求实则是同一问题的两个不同层次:现实政治的需要是作为主导原因存在的,而祭祀活动更多的是这一需要得以实现的一种形式,只不过这种祭祀活动较之现实政治的需要有更为长久的历史渊源和更为广泛的作用范围,二者的结合就是宗教性仪式与政教性需求的合一。
郭英德近年来对文体生成与演进过程提出了一些重要创见。他认为:“中国古代文体的生成大都基于与特定场合相关的‘言说’这种行为方式,这一点从早期文体名称的确定多为动词性词语便不难看出。人们在特定的交际场合中,为了达到某种社会功能而采取了特定的言说行为,这种特定的言说行为派生出相应的言辞样式,于是人们就用这种言说行为(动词)指称相应的言辞样式(名词),久而久之,便约定俗成地生成了特定的文体。”[7]29郭英德从理论上对中国早期文体生成过程进行的概括,无疑为包括誓体在内的文体的个案研究指明了方向。
其实,刘勰很早就敏锐地注意到了誓体生成、发展历程,《文心雕龙· 檄移》曰:“震雷始于曜电,出师先乎威声;故观电而惧雷壮,听声而惧兵威。兵先乎声,其来已久。昔有虞始戒于国,夏后初誓于军,殷誓军门之外,周将交刃而誓之。故知帝世戒兵,三王誓师,宣训我众,未及敌人也。”[26]377刘勰的观点应承袭自《司马法· 天子之义》:“有虞氏戒于国中,欲民体其命也。夏后氏誓于军中,欲民先成其虑也。殷誓于军门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周将交刃而誓之,以致民志也。”[37]《司马法》揭示了“誓”的宣读地点及“誓”的意图在历代的变迁,且注意到了受言人这一重要的言说对象,不过这种勾勒依然停留在描述层面,缺乏具体的论证环节。
誓体的文体形态研究,是近来兴起的重要学术生长点。张大烛《〈尚书〉五誓比较谈》[38]重在横向考察今文尚书五誓之间的不同,对誓体形态有所侧重,但尚未深入。王媛的博士论文《〈今文尚书〉文本结构研究》[1]以《尚书》文体结构为考察对象,以量化统计的方式揭示文本的内部构成,指出誓体作为一种文体,具有独白式与建设式二重结构,较为全面地勾勒了誓体形态的结构特征,但对结构特征成因的归纳稍显不足。朱岩的博士论文《〈尚书〉文体研究》[6]聚焦文体的语言系统,在对六体进行辨析之后,从对语言、语体、语篇等方面的量化统计中,得出文体的形态特征,具有较强的说服力。朱岩这种接近西方文体学的研究方式可成为中国传统文体学之借镜,不足在于研究对象为《尚书》整体,只是间或提及了誓体的文体形态,并未能进行誓体的专题研究。钱宗武及其弟子对《尚书》进行了一系列语言研究,成果丰硕。仅钱宗武一人,便有《今文尚书语言研究》[39]、《今文尚书语法研究》[40]、《今文〈尚书〉句法研究》[41]以及《今文〈尚书〉词汇研究》[42]等多部关于《尚书》语言的研究著作,对《尚书》“语言系统”进行了透彻的研究,为学界研究包括誓体在内的文体语言研究提供了便利。事实上,这些关于《尚书》的语言学研究成果,其目的是语言而非文体。进行《尚书》誓体研究则需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对具有文体特性的语言展开研究。欲达乎此,则有二重路径:首先,在专书形式的语言学研究基础上,将《尚书》的语言系统与同时期的语言发展情况作横向的对比,在汉语史的维度下明确《尚书》语言的整体特色所在;其次,在把握《尚书》整体语言系统的基础上,对其所凸显的文体特征进行提炼。
总体来看,在方法论层面上关于《尚书》文体的生成及文体形态的研究,主要是对一类文体的文本进行的静止性分析,未能联系纵向的文体形成过程作动态的研究,也普遍未将文体形成过程中的载体形态纳入研究视野。简而言之,在包括誓体在内的文体研究中,一直存在着“历时”视野的缺席,而这与文体功能研究中的“历史性”原则是紧密联系的。
由以上所述的誓体研究史,可知此前研究的收获与不足,而这凸显了“历史性”的重要意义。“历史性”既是研究对象复杂性的动因之一,也是研究方法体系化的组成部分,更是研究工作精密化的主要原则。在散文这一基本文类之下,在六体说这一次级文类分法的基础上,围绕着“历史性”,对纵向之誓体生成过程及横向之文体形态做全面考察,揭示先秦时期以功能辨体的主导取向之下,文体功能与文体形态之间的双向关系,无疑会深化对誓体特征乃至先秦早期文体之特征的认识。
注释:
①邵氏之总序见唐旭东《今文〈尚书〉文系年注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2―18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