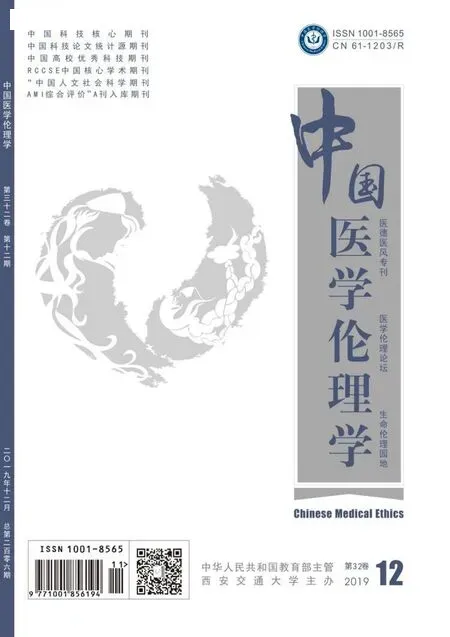中晚期癌症治疗中坏消息告知问题研究*
2019-01-17宋晓琳金琳雅
宋晓琳,尹 梅,金琳雅
(哈尔滨医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1,hmusongxiaolin@163.com)
从沟通层面来看,坏消息告知是医患沟通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在中国,由于家庭观念以及医疗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满足患者的知情需求仍是医务人员和家属共同面临的难题。
1 坏消息告知的概述
1.1 坏消息的概念和特征
早在20世纪60年代,坏消息告知就受到美国、加拿大及北欧等国家和地区的关注,随着法律和道德逐渐影响医疗实践,坏消息由完全隐瞒逐渐发生变化,学者开始探讨坏消息的告知及其是否符合患者的最佳利益。1984年,学者Buckman[1]将坏消息定义为“任何可能改变患者对其未来看法的信息”。
我国“坏消息”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但已有实质性进展。有学者认为,坏消息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当有关患者健康状况、诊断和预后的信息给患者及家属的行为和情绪带来持续性的消极影响,便被认为是“坏消息”[2]。也有学者认为,坏消息一般是指任何关于现在的或未来的,与人的愿望相违背的消息[3]。坏消息有主观性、相对性、广泛性以及消极性四个特征。
主观性和相对性。一次诊断结果对于患者来说是否为坏消息取决于患者及其家属对这一消息的接受程度。对坏消息的认知会因患者及其家属的年龄、性格、阅历及收入等原因产生差异。
广泛性和消极性。坏消息涉及范围较广,临床实践中各科室都有一些患者难以接受的坏消息。坏消息给被告知者带来身心健康上的消极影响,使其产生焦虑、抑郁等消极情绪,难以面对现实。
1.2 坏消息的告知对中晚期癌症患者的意义
坏消息的告知经历了较长的历史发展,家属的保护心理和坏消息的特征成为其难于告知的主要原因。一些国家在辩证和发展过程中,已经达成将坏消息告知患者的共识。我国在研究中也有学者提倡将坏消息告知患者本人,但实践中仍存在许多问题。在对中晚期癌症患者的告知中,这些问题尤为明显。
对中晚期癌症病情的告知是坏消息告知中最困难的一种。全面系统的检查、先进的医疗技术以及更有效的治疗方法,可以把癌症的诊断率和预后大大提高,但仍存在局限性。在告知坏消息时,将医学人文融入告知中,细化告知过程,采取科学告知方法,减少坏消息带来的恶性影响,在保障患者知情权的同时,还可以帮助患者减轻心理负担,提高患者的治疗依从性。
2 坏消息告知的实践困境
2.1 家属转告的偏差
面对中晚期癌症患者,为了向患者隐瞒病情等相关信息,医患之间的沟通常由家属来完成。医生将诊疗的方案告知家属,由家属向患者告知并解释。但家属往往认为自己知情且要求患者配合即可,这种情况极易导致患者对治疗方案的质疑和对医生的不信任,甚至出现一些过激行为。
笔者曾遇到一位患者,入院9天,医生一直在为其进行确诊工作,但检查结果无法快速取得。医生及时将这一情况告知家属,希望家属能安抚患者,耐心等待检查结果。但家属为了减少患者对费用等的顾虑,并没有告知患者,患者由于没有接收到任何诊断消息和治疗方案,产生了焦虑情绪。
实践中,由于过度保护心理产生的告知偏差时有发生。患者家属优先获得信息,经自己主观加工后转述给患者,很容易造成理解偏差或者与患者的关注点不符[4]。一些家属往往无条件地尊重医生的治疗方案,对诊疗目的缺少理解,也无法明确对患者进行解释。家属从自身角度出发替患者做决定,有时不仅违背了患者的知情意愿,也破坏了医患间的信任关系。
2.2 医学局限性带来的困境
医学存在局限性,很多恶性肿瘤不能通过医学技术治愈,晚期癌症医疗资源和昂贵费用的耗费与治疗结果和生存时间之间不成正比的现象时有发生。
一位患有肺癌的年轻患者,癌症已经发生骨转移,无法自主行动,生存概率大大降低。患者家属选择放弃治疗,将医疗和告知的难题摆在医生面前。另一位宫颈癌术后复发转移、预后较差的患者,在医院接受治疗时,患者因只了解部分病情,当身体其他部位不适,治疗无实质进展时,她的精神状态开始变差,情绪变得消沉、抑郁。
我国法律法规等都规定了医生的告知义务,以保障患者的知情同意权。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应当向患者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需要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医务人员应当及时向患者说明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并取得其书面同意;不宜向患者说明的,应当向患者的近亲属说明,并取得其书面同意[5]。面对临终癌症患者,家属因保护主义或无法表达,通常隐瞒实情,长期接受和奉行保护性医疗。而对临终癌症患者隐瞒病情,不利于医护人员开展死亡教育。
本研究所有的研究对象均为2016年到2018年我院血透中心的所有医护人员,共计选择15名护理人员进行分层管理,根据《护士岗位管理实施方案》的相关规定,并且根据我科的实际情况对于血液透析室的护理人员岗位管理制度进行制定,通过合理的方案进行落实,对于各个层级护理人员岗位职责和工作要求进行落实。
2.3 隐瞒病情的风险
在20世纪50年代及更早的时期内,故意隐瞒坏消息是国内外医生和家属普遍接受的一种常规做法。医生在描述病情时,一般会采用严重程度较轻的说法,如使用“肿块”或“增生”等非恶性病种来替代癌症。从伦理学的角度来看,隐瞒病情与不伤害原则和有利原则相一致,但却违背患者最基础的自主权——知情同意权。
在坏消息告知中,医生往往选择将病情告知家属,由家属决定是否告知患者,但患者家属对癌症诊断隐瞒现象普遍存在。在当今信息时代,完全隐瞒并不容易,患者可能通过多种方式得知自己病情,如偷看病历、偷听医生与家属谈话、其他患者及家属偶然告知等。通过非家属及医生告知的其他渠道得知病情可能使得患者情绪更为激动、愤怒。
一位患食管癌三年的患者一直对自己的病情不知情,家属从各个方面对患者进行隐瞒——延长放疗周期、用“烤电”偷换放疗概念、隐瞒实际治疗费用、与医护人员反复沟通防止信息泄露等。但这种看似没有疏漏的隐瞒往往具有不稳定性。如在某医院的某一次治疗前,值班护士在通知患者进行检查时,直接告知放疗和高额费用,使患者对自己的病情产生怀疑,拒绝继续进行治疗。
实际上,虽然对患者隐瞒病情在一定时间内可以稳定患者情绪,但若违背患者的知情意愿,编造“善意的谎言”搪塞患者等异常举动可能会使患者精神压力更大,思想负担过重,甚至会让患者产生被放弃的错觉,对治疗更加不利[6]。若家属及医生在此情形下选择继续隐瞒,则极易造成医患信任的缺失。
2.4 跨文化告知的差异
随着先进医疗技术的发展,外籍患者到中国就医的趋势不断提升。语言障碍和地域文化差异成为医生与外籍患者沟通过程中的主要矛盾。消除医生与外籍患者之间的语言隔阂和陌生感,帮助患者寻找归属感,恰当地告知病情,使患者明确治疗方案,积极配合治疗,是医生在医疗过程中需要重视的问题。
笔者曾与一位患晚期肿瘤的外籍患者交流,他曾在当地医疗水平最高的州医院看病,被告知预期寿命三个月。转入中国医院时,因对病情的不知情、癌症引起的疼痛以及周围的陌生环境,患者一直处于焦虑、烦躁状态,依从性较差。在此困境下,医生反复多次与患者和家属进行病情和治疗方案的沟通,患者的状态终于有了改观。
跨文化差异为坏消息告知带来困难。外籍病房常配有翻译人员辅助进行告知,但由于语言障碍,医生在某种程度上向翻译人员进行告知,通过翻译进行的语言告知是间断性的,且一些从事翻译的人员不具备医学背景,对于信息传达的准确度缺少良好的保障。
3 坏消息告知困境的应对
3.1 加强社会公众对健康和生死的认知教育
随着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模式转变,人们对身心健康和医疗服务提出了新的需求,这也对社会健康教育的普及提出新的要求。对社会公众进行知识讲解和健康宣教,能够帮助人们明确对恶性疾病的基本认识,减轻对疾病的消极看法,提高照护知识和技能,面对疾病时能够为患者提供更好的护理,从而提高癌症患者依从性及疼痛管理质量,帮助患者积极面对疾病。同时,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作出决策,明确治疗目的,积极面对疾病造成的消极影响,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促进医患之间的交流。
我国生死教育尚未健全,面对死亡时,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较差。对社会公众进行死亡教育,能够帮助人们了解疾病和死亡的相关知识,认清死亡的现象及本质,减少面对死亡时的恐惧、焦虑、抑郁等消极情绪,增进处理相关事件能力。面对重大疾病时,帮助患者及家属了解可能出现的病情变化,正确面对疾病的预后及发展并加快适应现状,使患者感受到尊重与关怀。
3.2 加强医生对患者评估与告知的能力
向患者告知关于诊断或治疗成功的好消息使医生获得成就感,相反,当向患者告知坏消息时,因欲告知的坏消息与患者的预期不符,医生由于没有做好应对患者不良情绪的准备,常常感到不适。部分国家在21世纪初已经开始对医生和医学生进行告知技能培训,如今已取得良好的成效。在我国,坏消息告知没有统一的模式,训练程度低,缺少独立的专业课程教育。医生在面对压力、焦虑和沮丧等外部因素时,往往采用错误的告知方式。
向患者告知坏消息是一项复杂的沟通任务,除了需具备口头的表达能力外,还应对其他能力进行培训,如回应患者及家属的情绪反应、让患者参与决策、处理由患者对治愈的期望而产生的压力、与患者家属进行沟通以及临终告知等。2000年,美国提出的SPIKES模式是目前最为常用、广泛被认可的用于告知坏消息的模式。其名称字母对应着该模式的六个方面:场景设立、评估患者认知、得到患者许可、医学专业知识告知、稳定/转移患者情绪及策略与总结[7]。其整个过程完成大约需要60分钟。2007年,日本心理肿瘤学会(JPOS)在研究癌症患者对真相偏好的基础上开发了SHARE模式。其实施需10~15分钟,包含着设定支持性的环境、如何告知坏消息、提供附加信息及提供情绪支持四个方面[8]。这两种模式在多个国家都已经得到验证,可以帮助提高医护人员的癌症告知技巧,对坏消息告知有良好的促进作用。针对我国的医疗环境,对这两种模式进行改良和本土化,适应我国医疗背景,通过实践的检验,熟练地应用于医学教育和医疗实践,帮助医生更好地对患者各因素进行综合评定,运用科学的方式进行坏消息告知,应对告知时的突发情况。在时机成熟时,可探索我国的坏消息告知指南。
3.3 完善医-患共同体的决策能力
“医-患共同体”是适应新的医疗环境所建立的一种医患共同参与、协商、确认拟定诊治方案并在诊疗全过程中医患积极合作,使双方获取最大受益的一种模式。它是建立在共同解决疾患、重视患者心理及社会功能康复的医患“指导互动型”或“共同参与型”医疗模式[9]。
坏消息告知中,患者对病情知情是医患共同决策的前提。知情患者依从性较高,在诊疗中和出院时会听从医嘱,在身体不适时及时就医。不知情的患者,往往会忽略他们眼中的“小问题”,如将肿瘤恶化引起的发烧当作普通感冒来治疗,如此便耽误了最佳的对症治疗时期。尊重患者的知情权,循序渐进地向患者进行坏消息告知,针对患者制定干预措施以提高患者的参与度,与患者共同分析利弊,共同面对癌症,提升医患之间的信任,做到完全的分工与合作,促成积极对抗癌症的治疗同盟。同时,推进医生与临终患者之间共同决策的能力,从医方角度给予患者情感支持和安宁养护,能够使患者感受到关怀所带来的温暖,帮助患者减少在面临死亡时的心理痛苦和生理不适,有尊严地走完人生的旅程。
如需隐瞒病情,医生可以稍微透露一些相关的非癌症病情,使患者在身体不适时及时就诊,防止患者放弃治疗;也可以告诉患者几个较易理解和接受的治疗方案,面对癌症带来的心理痛苦,应尊重患者的知情意愿,较早进行循序渐进的沟通交流,帮助患者树立治疗信心。
3.4 尊重跨文化差异
跨文化差异会导致患者对告知内容偏好、告知方法及告知程度有所不同,如受文化影响,以家庭为核心的东方比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西方更愿意讨论预期寿命[10]。西方患者更偏向直率式和预测式的告知方式,更直接地完成告知,东方患者对恶性病情的接受程度较低,更偏向停顿式和循序渐进式的告知方式[11]。同时,宗教信仰和地区文化能够帮助患者塑造与健康相关的价值观,从而影响患者告知需求。医生应对患者的具体情况进行考量,制定告知方案,在尊重患者文化背景及宗教信仰的前提下进行告知。
在临床实践中,除了良好的医疗技术水平和尊重各地文化背景外,掌握医患沟通技巧,注重医疗过程中的护理细节,通过人文关怀帮助患者接受环境和文化的差异,互相信任和积极帮助的态度是解决这一困境的重要途径,良好的氛围可以帮助患者缓解陌生环境带来的紧张感。此外,在沟通不畅时,可以使用微信翻译功能或非语言方式与患者进行交流,增进医患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