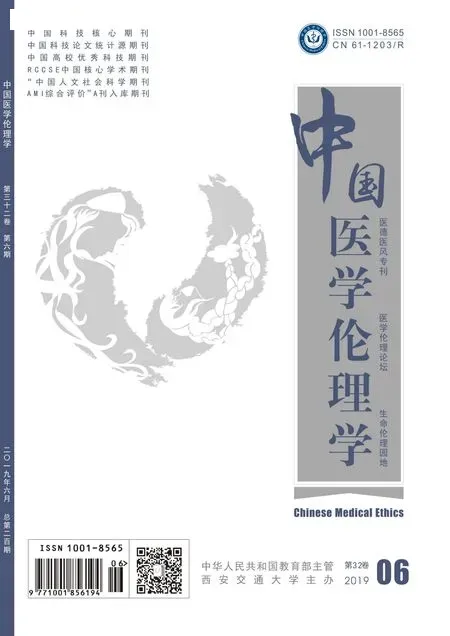子宫移植技术的伦理分析
2019-01-16雷瑞鹏邱仁宗
雷瑞鹏,邱仁宗
(1 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Lxp73615@163.com;2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2013年,22岁的杨某因从未来过月经,前去某医院妇产科就诊。B超检查结果表明其先天性无子宫和阴道。2015年,该院妇产科等11个学科、38位专家协作,成功将其43岁母亲的子宫移入女儿体内,新移植子宫成活。整个手术历时14个小时[1]。该手术是国内首例,世界上第12例人子宫移植手术。2018年杨某顺利产下一个男婴[2]。本文要讨论的问题有:子宫移植是一项新技术,实施这项新技术存在哪些伦理问题?如何鉴定、评估和降低风险,达到可接受的风险-受益比?如何从患者方面获得有效的知情同意?应该具备哪些条件才能在临床实践中应用?
1 子宫移植技术的发展
2014年瑞典某团队宣布子宫移植成功后第一个孩子顺利诞生[3],这时,对子宫移植的研究已经进行了50年。20世纪60年代人们开始用狗做试验,但进展甚微。2006-2010年在用小鼠和大鼠进行同种异体移植试验,2009年微型猪子宫移植后能长期存活,2011年羊子宫移植成功。这证明了子宫移植在哺乳动物身上进行的可行性。2013年有关灵长类子宫移植试验第一份报告发表,对18只雌性狒狒进行了子宫切除术、双侧输卵管卵巢切除术、双侧子宫髂内动脉和卵巢静脉移植。移植受体分三组:无免疫压制治疗、单药治疗、用三联疗法作诱导免疫治疗。手术后狒狒全部存活,40%恢复了激素周期性,然而都有不同程度的移植排斥。这次研究第一次表明在灵长类活体子宫移植的可行性,但尚没有满意的抗免疫办法。2000年第一次人类子宫移植是在沙特阿拉伯进行的。第二次尝试是在2011年,土耳其一位年轻妇女先天无子宫,接受供体子宫后定期来月经没有排斥。之后接受了两次胚胎转移(移植前体外受精)但均小产。这些试验说明人子宫移植是可行的,于是正式进行子宫移植的临床试验。2012-2013年进行了第一次前瞻性临床研究,9人参与,8人无子宫,1人因宫颈癌被切除子宫,其中4个供体是患者母亲,供体都是绝经后的,所有受体都接受标准化的抗免疫治疗。术后,2个受体由于并发症要求摘除,7人在6个月随访期子宫存活恢复行经,移植12~18个月行胚胎转移,其中一人于2014年成功产子。2018年12月有报道称,巴西第一次利用尸体子宫进行移植成功,诞生了一个正常的孩子[4-9]。
2 人类子宫移植从研究转化到临床需要解决的伦理问题
2.1 子宫移植的风险-受益分析
对一项新的干预措施,在伦理学上首先是对其进行风险-受益比的评估,包括对风险的鉴定,有哪些可能的风险,其发生的概率和严重程度如何,有哪些可能的受益,受益的对象是谁,受益的意义如何,然后评估风险-受益比是否可接受?但我们先要了解子宫移植与其他器官移植不同的特点。
子宫移植的特点之一是,子宫不是维持生命的器官(如心脏、肝脏或肾脏),它只是一种“工具性器官”,其唯一的功能是生育,子宫移植的目的是恢复不孕妇女的怀孕能力。这与其他的器官移植不同,这些器官移植是挽救生命,患者因器官衰竭而濒临死亡,如果不进行移植,患者就会丧失生命,而子宫移植并非救命,而是满足患者要生一个在遗传学上与其有联系的孩子需求,即为了生育。这一方面会使子宫移植在社会和伦理学上的可接受性较之其他器官移植要差一些;另一方面又使子宫移植在技术和伦理学上较之其他器官移植要更为复杂。技术上更复杂导致更大的风险,例如需要行许多手术,例如先在供体行子宫摘除术,后在受体行移植术,最后成功生出孩子后还要在受体身上行剖宫产术和子宫摘除术,因为不能让受体终身接受抗免疫疗法,且含连带的血管吻合术等其他手术。因此,这项手术有巨大的风险,这使它成功的可能性相对较低。而且还有与手部移植类似的一种特殊的心理风险,一些接受过这种手术的患者后来要求切除移植的手,不是因为其组织兼容性有问题,而是因为患者认为移植的手不属于自己的身体而产生的心理问题。伦理学上的复杂是因为在子宫摘除术,除了供体、受体需要关怀外,还有未出生的孩子需要关怀。
受益:在临床上推广一项新技术,首先因为它有潜在的、比较有重要意义的受益,为人造福:①对供体没有健康生命意义上的受益,但有精神上的受益。供体不管是亲属还是陌生人,捐赠子宫是他们做了超出义务以外的(supererogatory)好事或中文意义上的“行善”,他们因实现自己乐于助人的价值而得到精神上的满足,为亲人捐献供体,作了贡献而在感情上得到满足;②对于受体有非常重要的受益。子宫移植为患子宫因素不育症的妇女提供除领养和“代理母亲”以外的一个新的治疗选项,使这些妇女生出的孩子与其有遗传联系。所以,子宫移植确实能给一部分妇女及其家庭带来非常重要的、改善其生活质量、促进家庭和谐的受益。在许多文化中不育不孕往往被人轻视、贬损甚至歧视,而纠正这种偏见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做到的,子宫移植如果成功也是不孕妇女及其家庭有免遭歧视获得的社会受益;③帮助一个孩子平安出生也能使孩子受益。
2010年全世界有4800万夫妇不育。1/3不育的原因是男子的精子量不足或缺乏运动力;1/3由于妇女卵子质量低下、排卵困难、解剖异常影响卵子的正常轨迹,或影响受精卵从输卵管植入子宫;1/3由于双方的因素以及不明原因。患子宫因素不孕症(uterus factor infertility,UFI)妇女的特定解剖异常,大约影响所有不孕妇女的3%,在美国6200万育龄妇女中约有950万患子宫因素不孕症[4]。UFI可由于天生的、与疾病有关的或医源性原因引起。例如有的妇女天生没有子宫(Mayer-Rokitansky-Kuster-Hauser 综合征),因治疗癌症而被摘除,或分娩后产后出血或因创伤行紧急子宫摘除术。对此类不孕唯有领养或“代理母亲”才能解决有孩子问题,但领养无遗传联系,许多国家禁止“代理母亲”,二者均不能使母亲有妊娠体验。因此子宫移植成为一个患有子宫因素不孕症的妇女、不愿领养、代孕又被禁止的唯一可替代办法,随着安全性逐步提高,需求越来越大。在该手术尚未显示成功前,美国的一次临床试验在招募志愿受试者时,就有500名妇女申请参加。现在子宫移植技术越来越成熟,业已从临床前研究阶段进入临床试验阶段。虽然在人身上行子宫移植的可行性已经得到证明,但在手术中以及手术可能发生的风险还是很大的,因此将临床试验转化为临床实践必须小心谨慎为好。在我国,由于代孕非法,因子宫因素不孕而不能怀孕的妇女只能求助于子宫移植,以实现生育目的。从伦理学的视角来看,因子宫因素不孕与因其他因素不孕者都应该能够求助于辅助生殖技术,既然目前相关规定禁止代孕,子宫移植可以消除这一不平等、不公平的状况。
风险:子宫移植风险巨大,这使得有必要从动物试验开始一个漫长而周密的实验阶段。经过几十年的前临床研究,子宫移植现已进入临床研究阶段。子宫移植不同于其他器官移植的一个特点,涉及供体、受体和未来的孩子,对他们的健康和生命都需要细心照护。
供体:子宫摘除对活体供体是有风险的,可能会引起多种并发症,如血凝、感染、过量出血、对麻醉的不良反应,手术损伤泌尿道、膀胱、直肠或其他骨盆结构而要求手术修补,即使卵巢没有摘除可能引起过早停经等。使用尸体子宫可消除对供体的风险。
受体:子宫移植会给受体带来较大的健康和生命的风险。与其他器官移植一样,子宫移植术后可能出现出血、导致严重疾病甚至死亡的感染或移植的器官最终被摘除。术后在整个妊娠期直到分娩以前都必须服用抗免疫药物,而这些药物削弱免疫系统使感染的治疗和组织的恢复更为麻烦,而且还会出现各种并发症,例如高血压、糖尿病、白内障、骨质疏松症、肺栓塞、心肌梗死、纤维性颤动、胸膜积液等。子宫移植手术进入临床研究的时间较短,相关手术有待改进,例如连接血管的吻合术,而子宫的血管很难重新连接。为了避免长期服用免疫抑制药物,分娩后移植子宫必须摘除,这样受体需要经受至少两次大的腹部外科手术(移植和摘除),这就会增加风险。为了避免终生接受抗免疫治疗,必须采取两项后续的程序:剖宫产和子宫摘除。然而子宫不像肾脏和肝脏是静态的器官一样,移植入受体后大小和宽度不会改变,子宫的大小在怀孕时会发生相应变化。而摘除子宫又有大出血、对肠和膀胱的损伤以及血栓、不良麻醉反应甚至死亡等风险。当然,对于一些患子宫因素不孕症的妇女来说,这些风险再大,也没有生出一个与其有遗传联系的孩子更重要。
未来的孩子:与正常妊娠或借助辅助生殖技术妊娠不同,子宫移植后怀孕的孩子会受到额外因素的不利影响。为防止器官排斥必须对受体进行抗免疫治疗,虽然抗免疫不会致畸,但仍然可能影响胎儿的发育或引起并发症包括有早产、低体重的风险,甚至严重时必须将这个未来的孩子流产。
因此,子宫移植团队必须认真而仔细地鉴定对供体、受体和未来孩子的可能风险,对风险的严重性和概率做出尽可能精确的评估,并采取降低风险、使风险最小化的办法,使得有一个有利的可接受的风险-受益比。为此,有的医院的移植团队在临床试验中分成两组,一组关怀供体,努力保护供体的最佳利益,如果对特定的供体风险太大,甚至危及生命,则拒绝采用供体的器官;另一组关怀受体,对受体要测试其医学和生理学的适宜性,评估对受体的风险和受益努力维护受体的最佳利益,如果对于特定的受体风险过大,而成功生出一个孩子的希望不大,则应拒绝对受体进行子宫移植[4-8]。
有关尸体子宫与活体子宫的争论。对于利用尸体子宫还是活体子宫何者为优,一直存在争论。人们怀疑尸体子宫质量是否有保证。2018年12月22日英国《柳叶刀》(The Lancet)杂志发表了一篇世界首例利用尸体供体成功生出一个女孩的论文[9],该论文说明尸体子宫质量一如活体子宫。该例子宫移植手术在2016年9月实施,2018年出生一个正常的孩子。这个案例显示移植来自尸体供体的子宫与活体相比较有若干优点,包括消除了对活体供体的健康生命风险;其次,尸体供体作为移植子宫的来源要比活体供体好得多。此外在该案例中,早一点植入受精卵可减少服用抗免疫药物的时间,这有助于减少副作用和费用。研究表明,如果子宫来自与受者有血缘关系的供体,例如姐妹或母亲,那么移植成功的概率会更高一些。虽说子宫不是与生命有关的器官,但捐赠将对供体的身体健康、完整性,甚至生命产生不利影响。权衡起来,能够获得尸体供体的子宫应该是更好的选择。
2.2 有效的知情同意
按照有效的知情同意的条件,首先要向供体和受体提供有关子宫移植的全面的、充分的信息。“全面”是指要将子宫移植手术以及其他相关手术对供体的风险和受益,与移植手术相关的治疗对受体的风险和受益以及其他可供选择的办法的信息分别如实地告知给供体和受体,不可夸大受益,缩小风险;“充分”是指所提供的信息足以使供体和受体分别做出捐赠的决定和接受子宫移植的决定。要向她们说明子宫移植目前尚属实验性质,要向供体说明手术对她自己健康没有受益,而摘除子宫可能有多种风险,包括可能失败的概率;对受体尤其要说明,她需要经受三种侵入性手术,即子宫移植、剖宫产和子宫摘除,医生应清楚告知患者这三种医疗程序都可能会导致并发症和副作用,此外还要告知受体抗免疫治疗的使用情况及其对受体和胎儿的可能风险。子宫移植临床研究中的退出办法要比其他移植更复杂。如果妊娠时发生排斥,医生需要决定是否和何时终止妊娠,以挽救排斥移植子宫的患者。要求医生提供给受体的信息量和复杂性远远超过其他器官的移植。其次,要帮助供体和受体理解告知她们的信息,可以用提问和测验等办法了解她们对信息的理解程度;最后给她们充分时间就是否参与做出理性的、经过充分考虑的自愿和自由的决定,不要使他们处于胁迫或不正当利诱的情况下。目前子宫移植仍处于临床研究(即临床试验)阶段,必须从供体和受体那里分别获得本人签署的同意书。但知情同意是一个过程,不能将它归结仅仅为取得一份同意书,而是要认真地经历告知信息、帮助理解信息和自由同意这一全过程的三个阶段,否则即使取得同意书,这个同意也是无效的。
另外,由于移植子宫的需求大大超过供应,申请参加子宫移植的妇女往往要排很长的队,要告知这些妇女需要漫长的等待,很难预测需要多长时间才能进行真正的手术。由于要移植的器官必须与受体相匹配,往往不可能按照预定时间安排手术,这种不确定性会引起情绪和心理紧张,必须让受体了解这一点。
因此,有些国家为子宫移植设立专门的专家委员会负责处理与子宫移植有关的知情同意问题,检查供体和受体是否都被告知全面而充分的信息,她们是否已经理解了这些信息,她们的同意是否都是自愿的和自由的。医疗团队要把有关于临床病例所有可能的信息、涉及的风险因素、移植的结果、供体和受体的存活率、出生孩子的成功率等相关数据向该专家委员会汇报,这样有利于总结经验,改进子宫移植技术。
2.3 其他伦理问题
公平可及问题:从目前子宫移植技术发展趋势来看,其成功率正在不断提高。从临床试验转化到临床应用,也可能为期不远。然而由于子宫手术复杂,费用也比较高。而目前在我国所有辅助生殖费用都不为医疗保险覆盖。一旦允许在临床广泛应用,必定会出现不公平问题,使得生物医学技术的成果只能为一小部分高收入人群享用,而将大多数中低收入患者排除在外,这将扩大社会不公正问题。
资源分配问题:子宫移植不是救命的技术,而且目前其成功的概率很低,因此有人认为大规模投资于子宫移植技术研究妨碍了有限的资金流向成功率更高的技术或手术,这是不合伦理的。这需要对子宫移植技术进行成本-效果(cost-effectiveness)评估,即资金投入后能产生多大的健康受益,主要指标是能延长该患者群体多少经过质量调整的生命年(QALYs),以便就是否进行投入以及投入多少做出合适的决策。
商品化和商业化问题:一旦子宫移植被批准在临床应用,而求大于供的局面必然会形成,这样可能会产生将子宫商品化的压力,即将子宫作为一种商品来对待。在我国更令人担心的是将子宫移植的临床应用商业化,将其作为盈利的来源,这样很容易出现类似干细胞乱象那样的恶劣情况,这样不仅伤害患者,破坏子宫移植手术的可信性,也是对妇女尊严的亵渎,将妇女看作生育工具[6-9]。
2.4 对子宫移植技术研究和应用的治理
对子宫移植技术的研究和临床应用需要监控和治理。应该有专业的监控和治理,机构的监控和治理,以及国家的监控和治理[10]。目前唯有意大利对子宫移植有监控和治理的法律,其余的监控和治理规定都是属于专业性的。例如:
2012年一些国家的专家制定了《蒙特利尔子宫移植伦理可行性标准》[7],以指导临床医生和研究人员合乎伦理地进行子宫移植。随着子宫移植的临床试验向前推进,一组专家聚集在印第安纳波利斯,讨论与子宫移植的当前和未来状态相关的问题,他们提出了《印第安纳波利斯共识》,呼吁“持续而仔细地对移植进行伦理反思、评估和批准”[11]。此后更新了蒙特利尔标准[8]。大致内容为:①受体。为育龄女性,无移植医学禁忌证;存在备有证明文件的先天性或后发性子宫因素不孕症,且所有现行标准治疗和保守治疗均失败;在个人或法律上不能进行代孕和领养,具有想要一个孩子的愿望;申请子宫移植是体验妊娠、生出一个与自己有遗传联系的孩子的一种措施,并了解子宫移植在这方面的局限性;做出子宫移植的决定经专家心理评价不认为不合理,不存在干扰诊断检查或治疗的心理疾病;没有明显不适合做母亲的因素;可服用抗排斥药物,并以负责任的方式与治疗团队进行随访;且有足够的责任心去表达同意,已被告知和理解足够的信息做出一个负责任的决定。②供体。为育龄妇女,对捐赠无医学禁忌证;多次检查证明她同意捐赠;签署了一项关于死后器官捐赠的事先指令;无子宫损伤或疾病史;能负责任地表示同意,足够知情作出负责任的决定,而不是在胁迫之下。③医疗团队。所属机构稳定可靠;能够就风险、潜在后果和成功与失败的机会向供体和受体提供充分的信息并从她们那里获得有效的同意;与任何一方均无利益冲突;如果供体或受体没有明确放弃这一权利,则有义务保持匿名。
2018年美国生殖医学会发表《子宫移植声明:委员会意见》[6]如下:子宫移植是一种治疗绝对子宫因素不孕的实验性手术;子宫移植应该在机构审查委员会批准的研究方案内进行;子宫移植团队应该协调一致,多学科合作;在尝试在人类受试者体移植之前,动物模型和/或尸体实验室的外科训练是必要的;子宫移植过程中使用的器官可以来自在世或已故的捐赠者;透明的纳入和排除标准应该指导移植受者的选择;需要对子宫移植的结果进行标准化报告以评估与此手术相关的真实风险、受益和结局;需要收集每一例子宫移植有关数据以及新生儿和孩子长期存活及其健康的数据,纳入网络平台与他人共享。
根据以上论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唯有满足下列条件,将子宫移植从临床试验转化为临床应用才能在伦理学上得到辩护:①在临床前研究基础上,临床试验的风险大为降低,尸体子宫移植成功率大为增加,移植子宫存活率和生出一个正常孩子的成功率大为提高并稳定;②经过多年反复的临床试验已经可以据以制订子宫移植的技术规范;③已经形成一个对动物实验和临床试验经验丰富和技术熟练的医疗团队;④该团队是属于一家综合性的、具有相关学科的研究性医院;⑤该团队所属医院已经建立行之有效、能够进行独立审查、伦理审查质量较高的机构伦理审查委员会;⑥该团队已经拥有较丰富的获得有效知情同意的能力;⑦作为一种辅助生殖技术,子宫移植应纳入我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进行监管和治理,该办法应补充有关子宫移植的条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