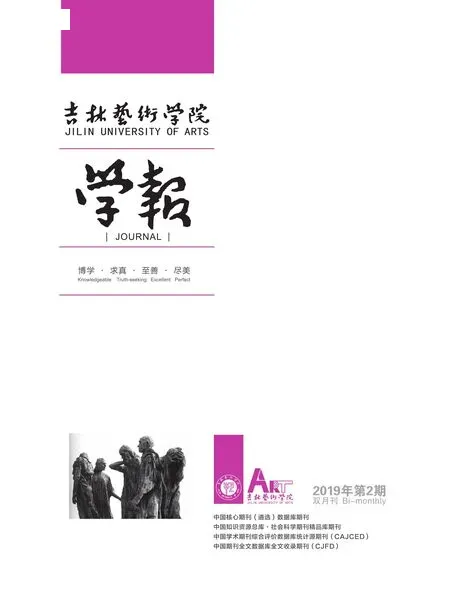从文字到影像
——试论《芳华》的改编
2019-01-16陈鸿秀徐娜
陈鸿秀 徐娜
(淮阴师范学院,江苏 淮安,223300)
由冯小刚导演的《芳华》为2017年的国产电影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电影改编自严歌苓的小说《你触摸了我》,后改名为《芳华》。这部电影由文字到光影的诉说,是冯小刚送给自己的一份时光纪念礼品,他对部队文工团的记忆,是“有一种光线在流动的,那些年轻女孩的身影如波光一样,在阳光里面流动。我的脑子里经常像有一道光甩过去了,然后就呈现出一张张脸来”[1]。选择严歌苓的小说改编,是因为原作中描述的部队生活给了导演再创作的意愿与灵感;与严歌苓合作,是因为这位作家的文字往往具有镜头感,多部作品被成功改编为影视作品。比较《芳华》的文学文本与电影版,诸多方面都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与再创作。
一、基调从冷峻到温情
《芳华》上映之后,读过原著的观众以及影评家都会发现小说与电影的基调差异明显。在严歌苓笔下,小说描述了文工团一群少男少女充满变数的人生,以及那个特殊时代下情感的克制与爆发,重点表现“触摸事件”对人物心理上所造成的创伤,以及对他们现实命运的影响,以此来反思当时的时代环境对于人性的压抑,具有批判现实主义意味,表达了作者对于人性、对于时代的冷峻思考。可以说,严歌苓是借萧穗子(即叙述者“我”)之口以一种反思反省的态度回忆那段荒谬的岁月,即便文工团里存放着作者多年的青春记忆,但她并未表现出明显的留恋;叙述者“我”时不时要跳出来以当今的眼光梳理审视一番,让读者与作品故事产生疏离感,同时也感受到作者冷峻清醒的笔调,以及对那个时代罪恶的批判。
严歌苓十分擅长描述人物的精神状态、刻画人物的心理,不同人物在人生不同阶段的遭遇以及外在形象、内心活动全都跃然纸上。如何小曼在失去生父的庇护后,跟着母亲在新的家庭中作为“零余者”如何卑微地活着,在母亲的示范下谨言慎行,既不让母亲为难,又努力想融进新家庭,渴望得到母爱亲情,并在努力失败后以她特有的方式反抗、逃离,表现了一个长期缺爱的女孩的心态。又如萧穗子因“纸上谈爱”被批后对刘峰的错觉、林丁丁嫁给首长公子后因无生存技能被挤兑后的无助无措等,既真实又冷峭,还带着些许心酸。然而大部分先前读过小说的人在看完改编的电影《芳华》之后,都会感受到改编后的电影相对于原著缺少了一种冷峻的声音,加重了温情与集体怀旧感。
影像叙事与文字叙事属于不同的媒介与载体,即使严歌苓的小说本身具备独特的影像化特征,但因为冯小刚和严歌苓是拥有不同生命体验的个体,加上文字与影像表现形态的差异,电影在主题基调表达方面相较于小说更需要符合大众的审美特质。冯小刚曾在高晓松的《晓说》节目中说过自己本身就是一个温情的人,最喜欢是枝裕和的电影,他不希望任何人有一个悲剧的、难以和解的结局。同时作为一个导演,他很善于把握节奏,在他拍摄的贺岁片中,总体现着娓娓道来的温暖与怀旧。如《不见不散》中,刘元和李清的他乡之恋给观影者带来的一丝温存,虽然他们在反反复复相互试探着分开,但最后还是因为一个契机互诉衷情牵手一起,这样的画面很温馨。又如《甲方乙方》讲述的一组让人捧腹却不失温暖的不同故事,影片最后的“圆梦”是姚远、周北雁把他们的婚房借给了由杨立新饰演的技术员,片尾那句“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它”,令人伤感且温馨。《芳华》从某种程度上延续着这种温情与怀旧。
缅怀过往、温情主义是冯小刚贺岁喜剧电影的基调,文艺片《芳华》无疑也带有这种特点。冯小刚把 “You touched me”单纯地变成了那个年代里“青春”的一种过错,更多地表现出对文工团大集体生活中女兵、男兵群体浪漫温馨的缅怀,仿佛在那个环境下少男少女荷尔蒙的散发才是正常和正确的。在电影《芳华》中,严歌苓小说中的冷峻基调与青春创伤以及对于阴暗人性的揭示也被冯小刚转换为对青春的光影怀念。影片以极其唯美的镜头,展现出了青春逼人的文工团男兵女兵最美好的一面:排练时的优美姿势,游泳、吃冰淇淋、谈笑时的蓬勃朝气。影片最后借萧穗子的旁白抒怀:“原谅我不愿让你们看到我们老去的样子,就让荧幕留住我们芬芳的年华吧。”冯小刚没有过多展示他们所受的苦难及芳华逝去后的状态,影片定格在刘峰与何小萍两位主人公依偎在车站一面暖色墙前椅子的画面上。冷峻的思考或是温情的回忆,是小说与电影呈现的两种不同的芳华。
二、人物塑造从群像丰满到主角突出
《芳华》原著大概11万字,以人物为线索,将刘峰和何小曼、郝淑雯、林丁丁以及萧穗子每个人物形象都描写得十分丰满,故事交叉碰撞,拼成一幅完整的青春“图画”。而电影由于主题表达的侧重以及放映时间的限制,在改编过程中需要对原作的人物的性格、命运等进行重塑。最明显的变化是将刘峰、何小萍作为核心人物,林丁丁、萧穗子与郝淑雯则作次要人物塑造。同时,有别于小说特有的文学性以及多视角叙述,电影调整了叙事视角与人物之间的关系,也没有向观众展现原作中人物的阴暗心理及人物具体的命运波折。
1. 两位受害者成为电影的核心人物
小说到电影的形象塑造中,改变最大的首推刘峰。小说中的刘峰个子不高,在文工团集体里也会受到男兵们的揶揄。例如在刘峰接替朱克与何小曼伴舞时,男兵们却在暗地里嘲笑刘峰是个低级且没有趣味的人,连那么馊的何小曼他都愿意摸。严歌苓笔下的刘峰命运悲惨,因为发生了“touched”事件,他成了一个遭受到集体反目的人,在被揭发后,下放去伐木;后来上了越战战场,受伤之后产生了不想活下去的念头,把救助自己最关键的时间用来替驾驶员导航去送弹药,从而失去了摸过林丁丁的右胳膊;退伍后去海南经商,卖盗版书,尝遍各种艰辛,婚恋生活也不如意;最后得了绝症,流落在北京,离开了人世,是何小曼陪伴他走过了最后的日子。另外,小说对于刘峰善良个性的描写十分细致到位,如萧穗子担心刘峰病情,最后去了他女朋友家找他,刘峰给她沏了茶,还把一个苹果扎在桌子上的固定铁钎上,用刀细细地削,说自己一只手削水果都强过两只手。而电影中并没有出现这个十分适合用镜头表现的细节。
在电影的开始,刘峰把何小萍接到文工团,画外音就告诉大家故事的主人公是何小萍和刘峰,整部电影就是以他们两个人的故事为主线。影片中,主人公刘峰由黄轩饰演后,整体形象变得阳光、帅气,且大家都很喜欢刘峰,对他的好表示赞赏,他与女兵、男兵相处都较融洽。在电影的后半部分没有表现出刘峰遭受的诸多苦难,也没让他患上癌症,更未描写其生命走到尽头时的状态。
何小萍在原著里叫何小曼,书中对她的描写较多,这源于严歌苓特别喜欢写边缘人物,认为自己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也都是一个边缘人物。“曼”这个字更符合原著中其父亲文人角色所起的名字,入伍前的何小曼在上海生活,生父在她六岁的时候就自杀了,随后母亲的改嫁让她变成了“拖油瓶”。对于何小曼的塑造,作者的叙事手法表现得十分成熟,把她安排在林丁丁和刘峰之后进行整体叙述,在小说开始一笔带过了何小曼的名字,说她和“我”一样只是被备受宠爱且家境优越的女兵邀请去见证她们受宠的边缘人物;后来在写林丁丁这个人物时,说喜欢林丁丁的人有很多,因为像何小曼这样的人都是有人追的,并简要叙述了她与排长的感情和她被文工团处理后的一些情节;之后又笔锋一转说自己扯远了,现在还不是何小曼应该出现的时候,转而继续叙述林丁丁的故事,插叙手法运用自如。
电影将何小萍参军前备受冷落甚至羞辱的家庭生活删去,一开始就成了从北京招来的新兵。片中她的父亲没有死,只是失去自由,因此她常给父亲写信表达自己的思念,同时排遣自己生活中的委屈。这也为电影中的军装事件做了铺垫:她迫不及待要给父亲寄去自己穿上军装的照片,所以偷偷“借”走了林丁丁的军装,去照相馆拍了照。她以为进了文工团,进了部队就不会有人欺负她,可是接二连三的“军装事件”“内衣事件”“舞伴事件”让她遭受到了持续的排斥与羞辱。
小说《芳华》的原英文名为《You touched me》,“touched”为过去式,是触摸也是触动。小说和电影中两次“touched”事件的主人公都是刘峰。其中一次是因为刘峰的善良本性,“触碰”了总是遭受他人嫌弃、跳舞时无人愿意托举的何小曼的腰肢:“刘峰来到小曼身边,伸出双臂说,来,我们走一遍。手触摸到她腰上,两只结实有力的手,虎口恰恰好地卡住她纤细的腰肢。”[2]121刘峰的这次触摸让何小曼为自己轻盈的身体骄傲,在她的生活里,除了小时候的爸爸,再没有过别人愿意这样抱她。刘峰的这次触摸,对于何小曼更多的是触动,也许何小曼就是在这个时候喜欢上了刘峰。电影叙事无法像小说描写得如此细致,尤其是刘峰和何小萍的那次“触碰”更是一笔带过,画外音也没有对何小萍的心理活动进行叙述,观影者甚至感受不到“触摸”的发生,只是单纯看到了善良的刘峰接替了总是被人嫌弃的何小萍的舞伴角色。
2. 其他女兵形象的“蜕变”
除了刘峰、何小曼外,小说中着墨较多的其他人物有叙述者萧穗子、林丁丁和高干出身的郝淑雯。她们在原作中都是“圆形”人物,带有年轻时的憧憬或莽撞、骄气或娇气、疑惑或自私,也带有她们出身的烙印,向读者展示了军营生活中的青春风貌。而电影中她们的戏份较少,形象相对单薄。
作为电影和小说的故事叙述者萧穗子,在小说中刚亮相就接受了批判:她与部队男兵少俊偷偷摸摸地谈着纸上恋爱。小说中关于萧穗子对于刘峰作为一个“活雷锋”存有的态度值得分析,她认为刘峰只是一个其貌不扬的人,对于刘峰的好自始至终保持怀疑,且这件事让她心里一直存在一个阴暗的角落。后来林丁丁与刘峰出了“触摸”事件,她一直以来的疑虑才有了一个答案。她认为文工团这个红楼里面所有的人都和自己心态相似,一直以来对刘峰的活雷锋形象没有完全信服,想看刘峰出糗,来维持心理的平衡。他们一边满足着刘峰的善良带给他们的好处,一边心里又存在怀疑,觉得他怎么可能比自己好那么多。而在电影中,萧穗子从被孤立的人变成一个从众的人,有过那个年纪的女生都可能会有的青春故事,一场被朋友抢走的暗恋。虽然她仍然心思细腻,但在她身上发生的激烈故事都没有了,她的形象变得相对单纯,似乎只是个话比较多的集体一员。
刘峰的另一位“触摸”对象林丁丁在小说中着墨不少,她本来游移在内科医生与摄影干事之间,还有其他的爱慕者,颇有待价而沽的意味,但她从未留意过刘峰。后者在爱和欲望的驱使下,利用一次独处的机会“触碰”了林丁丁的后脊梁,书中这样写道:“手从脸蛋来到她那柔软胎毛的后脖……衣服单薄,刘峰的手干脆从丁丁的衬衣下面开始进攻。”[2]49随之而来的是林丁丁惊恐而无情的一声“救命啊”, 把作为活雷锋的刘峰自此推进了黑暗的无底深渊,对于林丁丁来说,刘峰爱她的念头比实际的触摸更让她惊恐,难以接受。小说中严歌苓把她塑造为一个天然“萌”的人物,经过一系列事件的催化,比如“甜饼之夜”和“血案”等,让刘峰对她着迷,爱上了她。在第十三章对她的婚恋故事进行了详细叙述,从将军的儿媳到国外的老板娘到给人做保姆,通过外貌和语言描写,把林丁丁的形象刻画得十分深入。而在电影中,留给她的镜头不算多,仅通过刘峰不让摄影干事只拍林丁丁等侧面描写表现出刘峰对她的喜欢,以及在后来触摸事件的表白与林丁丁的反应。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无论在小说还是电影中都带有出身优越感的郝淑雯。在小说中,郝淑雯嫉妒心理很强,很多东西看不惯。例如她对萧穗子的嫉妒,怀疑萧穗子跟少俊关系特殊,就去勾引少俊,还怂恿少俊把情书交给领导,以此来获得快感。书中写道:“勾引他就为了搞清你;我年轻的时候,厉害吧?对厌了的男人,绝对无情,手段卑鄙着呢!我背叛你的时候,真觉着满腔正义!”[2]185从这其中不难看出她性格阴暗和扭曲的一面。小说中郝淑雯最后嫁了一个二流子,虽然最后老公成了商人赚了很多钱,她顺其自然成了富婆,但二人感情并不好。而在电影中,其形象没有那么负面,也没有与一个二流子结婚,而且是一个正义感多于令人厌恶感的人,有着在军大院长大的孩子特有的傲气和正直。比如,在文工团大集体一起吃饺子时,郝淑雯特别骄傲地说军队是她们北方人的天下,显现出她的优越感;又如文工团解散多年之后,她带儿子出来见忙生意的陈灿,看到刘峰被人欺负时,为他打抱不平,还帮他付了罚款,这体现了她的仗义和正直。即使是“抢”了好朋友萧穗子的暗恋对象,也不是用卑鄙的手段,她与陈灿两人都是高干子弟,且一开始冯小刚就把青春少男少女相互喜欢的细节写得特别到位,爱说反话、爱斗嘴,故意和她的朋友相处得好……所以她和陈灿是顺其自然地在一起,并非出于对萧穗子的妒忌。
从小说到电影,在对人物的重塑中明显加入了冯小刚个人的理解,淡化了人物的负面心理、也淡化了人物之间的恩怨关系。正如“芳华”一词所呈现的芳香与年华,冯小刚对于以上几位人物形象的塑造以及结局的呈现也多是美好而温馨的。
三、情节增减并行
英国电影理论家克莱帕克认为:“一部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绝不是原始材料的一种机械复本,而是从一套表现世界的成规转化和变换成另一套。”[3]158每一部小说改编为电影的过程,都是对原著的一次再创作,并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小说可以不受篇幅的限制,可以用数十万甚至几百万的文字去展开情节;而电影放映只有两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需要对原著(尤其是中长篇小说)做减法,并在局部作加法处理。虽然改编后的电影《芳华》其主要情节源自原著,严歌苓的小说文本有较好的影像化基础,不少故事情节在进行视觉转换(剧本)时,不用经过太大的改动。但即便如此,也不可能将《芳华》原著近11万字的所有内容一一以镜头展示,何况随着电影基调的改变、人物主次的分化,必须要对原著的情节进行取舍增删。
影片伊始,刘峰带何小萍走进文工团,扑面而来的是青春荷尔蒙的气息。乐队按部就班,分队长不断提点,文工团女兵的舞姿优美且英气逼人,一切紧张而有秩序。何小萍和刘峰如同引导者,把观众带入文工团的部队生活。随后,何小萍随着萧穗子入住宿舍、领被褥、洗澡等等,集体生活的细节与状态在银幕上跃动。小说中,何小曼(即影片中的何小萍)并非与萧穗子她们三人住在一个宿舍,电影为了让事件与节奏进行的更顺利,将她们安排在一个宿舍……冯小刚善于化繁为简,对于影片的信息释放掌控得很好,以何小萍报到为主线,不停地暴露着文工团的“内幕”:刘峰吃“破皮饺子”、打靶时吃摄影干事的醋,何小萍偷林丁丁的军装拍照、体味太重遭嫌弃,萧穗子暗恋陈灿等,让几位重要人物的性格在细节中展现。
影片的减法还集中体现在对小说后三分之一的删削。小说重墨描述了文工团解散后众人命运的曲折坎坷;而电影中文工团解散之后的故事则被浓缩在三个地点:海口、蒙自烈士陵园和火车站。这三个地点发生了五个故事:萧穗子和郝淑雯在海口相见;刘峰与联防队成员起了冲突;萧穗子、郝淑雯、刘峰三人重逢;刘峰和何小萍在烈士陵园扫墓;刘峰和何小萍在火车站送别以及最后两人相依为命。几组画面的转换体现了步入中年的他们谋生的不易以及淡然的心态,其后半生的波折在银幕上更像蜻蜓点水式的“关照”。
这一系列的删减除了和电影本身时长限制等因素有关,也和冯小刚主题表达的倾向有很大关联。由于改编过程中主题的置换,故事情节必须跟着进行删减,从而选取更精彩的镜头去贴近电影的主题基调。因为冯小刚对于集体记忆内容的看重,同时也就有一些自己想法上的“加法”:毛主席去世,全国上下集体哀悼,文工团也暂停了排练;萧穗子试穿郝淑雯一条从香港买回的紧身牛仔裤;陈灿与萧穗子、郝淑雯、林丁丁围在一起,偷偷听邓丽君的歌;离开文工团的散伙聚会等,这些内容是原著中没有的情节。原著中严歌苓把更多笔触放在人物个性的描写上,冯小刚则更重视追溯青春回忆,所以时代的烙印在影片中的呈现是顺其自然的。如陈灿与三位女兵偷听邓丽君歌曲的情节设置,在影片中具有重要作用。“这群深夜里不曾捅破爱慕薄纸的青春男女,在灯外蒙上一圈红纱布,让整间营房变得具有了浪漫情调。”[4]“侬情千万缕,丝丝为了你。盼君多珍惜,愿你长相忆,今生永不渝,今世永不移”,这样的歌词颇具煽情效果。还有文工团的告别聚会,镜头前呈现的是男兵女兵这个大集体的难舍难分以及个人对于未来的迷茫,集体合唱的《驼铃》很容易触动正步入中老年的观众,唤起他们的青春回忆。电影《芳华》中加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也是电影的经典一幕,即何小萍走出舞台的独舞。从前线下来之后,何小萍看了太多的战场残忍的一面以及生命的脆弱,精神失常住进了医院。后来作为精神负伤的军人出现在曾经待过的文工团告别演出的观众席上,此时精神失常的何小萍,眼神是呆滞的,她看着曾经的战友们在舞台上跳着舞,那段青春美好记忆竟被唤醒,她想起了刘峰,想起了文工团唯一一个愿意待她好的人,想起了与他一起跳过的舞,她穿着病号服走出了礼堂,在月下独舞。舞台上的表演者和何小萍这个“异类”的对比,反映了不同环境带来的境遇差别。
总之,电影删减了原著中相对冷峻的内容,删去了描写人物阴暗心理的文字,丢掉了无法在影片中呈现的内容,丢掉了他们波折的人生遭遇。而加法则糅合了冯小刚对于集体记忆的怀念以及对于文工团青春的缅怀。
四、色彩由普通到明丽
在阅读的过程中,我们总会在脑海里构建画面。于《芳华》来说,严歌苓的小说本身在色彩上有几处描写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如关于何小曼的故事中一件红色毛衣的叙述:“第二天她在妹妹的衣橱里找到那件红毛衣,对着太阳光看,尽管被虫蛀成了笊篱,可还红得那么好,红色微微晕在周围空气里。”“她和着咒语的节奏,看红色被咕嘟嘟黑水淹没,眼看着就黑透了。”[2]77这里写出了何小曼在这个家庭里的地位低下,对妹妹的嫉妒以及心理上的扭曲。还有在刘峰与林丁丁的触摸事件发生之前,作者对于刘峰外貌与穿着的描写:衬衫崭新雪白且微微透明,里面的蓝色跨栏背心以及肉色胸大肌都隐约可见,给人一种时刻要冲破禁欲的感受,为后来刘峰一时之下的冲动做了铺垫。其他还比如萧穗子得知刘峰病重之后去找他,见到刘峰时,萧穗子觉得他是灰白的,似乎皮肤和心境都褪去了颜色,这里会给人一种刘峰遭遇的惨淡和败旧感。
原小说的色彩表现如何,也许每个读者看法有所不同。整体来说,即使有色彩描写,也符合严歌苓的冷峻基调与反思人性的主旨,有一种压抑感。而冯小刚电影的呈现较之小说则十分明丽。由于画面的直观逼真要比靠想象的抽象文字描写更有优势,所以观众的眼球很容易被色彩冲击到。整部电影更像是一场视听盛宴,色彩饱满,镜头韵律十足。饱和度较高色彩的运用奠定了电影的整体基调,主要体现在绿、红、蓝、黄四种颜色的多处运用上。
首先是绿色,因为要表现的是文工团的故事,所以绿色在影片中的出现频率最高,成为全片的基础色。绿色代表着文工团,代表在文工团集体生活着的少男少女,象征着青春,同时也点亮了电影的主题“youth”。而红色在影片中意义则相对多变,它是军旗的象征、鲜血的颜色,也代表着浪漫主义。当陈灿作为小号手登上坦克吹响小号之后,军旗在风中飘扬,这里的红色有着对美好年华的寄托;当军人为国而战,英勇牺牲,沾满鲜血时,这里的鲜血是残酷也是军人不怕牺牲的伟大证明;当男兵女兵一起偷听邓丽君的《侬情万缕》时,吊灯上罩着的红纱,让当时的氛围变得极具浪漫情调,在这里,红色成为文工团下少男少女的爱情理想。还有黄色,它在电影中则象征着朝气和希望,文工团的墙壁是金黄的,这里映衬着文工团中他们的青春和朝气;在影片末尾,刘峰与何小萍依偎在一起,后面的背景墙面也是黄色的,可以看作是两位主人公历尽沧桑后相互守护的希望。另外,绿色、红色在《芳华》的海报宣传中也运用得十分极致,令人惊艳。
五、结语
1. 优雅浪漫的音乐为影片增色
对于电影《芳华》来说,除了给影片增色的丰富色彩之外,音乐的运用同样是不可或缺的名片。本片的音乐总监是赵麟——著名作曲家赵季平之子,赵季平是冯小刚的老搭档,创作有《一声叹息》《一九四二》《黄土地》《红高粱》《孔繁森》等著名电影音乐作品。音乐在人的身体里是有记忆的,不仅可以强化整部电影的温情基调,还可以使人物更为立体。
抛开作为主题曲的《绒花》不谈,片中插曲和配乐同样具有独特价值。对于配乐来说,它是没有歌词填充的,这也往往更能够给观众以想象的空间。如电影刚开始时,何小萍与刘峰进入文工团,大家在排练,乐队排练的间隙,陈灿用小号吹了一首《那不勒斯舞曲》,这是《天鹅湖》第三幕的舞曲,曲风欢快、活泼、优雅。又如开场《草原女民兵》刚结束,萧穗子带何小萍去女生宿舍的时候,宿舍楼中一个女兵拉的《巴赫(G大调第一大提琴组曲)前奏曲》,这首曲子让整个画面都显得平静、温柔和美好。这两处配乐,都十分符合电影刚开始何小萍刚进入文工团时对以后生活的一种向往、期待,似乎一切都显得岁月静好。
另有钢琴版的《送别》,是在刘峰要被下放到伐木连前夕,何小萍去话别,两人握手、互敬军礼时响起的背景音乐。前几个音听着很稀散,落在心上,给人以忧伤之感。一个是面临被喜欢的人伤透了心要离开这里的坦然,一个是面对文工团唯一一个善待自己的人要离开时的难过,两个没有被善待的人,最珍惜善良。另外,《沂蒙颂》在剧中出现两次,第一次是刘峰与何小萍的“触摸事件”;第二次是经典一幕——何小萍的月下独舞,安静而有力量,是这首曲子和舞蹈让何小萍回忆起过往。像何小萍这样不受善待的人,和舞台上的女兵不同,她的芳华是青春已逝时,在月下无人之地的独自翩跹。其他还有《洗衣歌》《草原女民兵》《驼铃》《英雄赞歌》《浓情万缕》等都在试图诠释冯氏的浪漫与理想。
2. 震撼真实的战争场面补写了壮烈青春
青春不只有靓丽、美好,也有挑战与牺牲,电影版《芳华》就通过战争场景的营造表现了青春岁月的另一种色彩与情怀。本片用了近20分钟的时间去展现1979年的对越自卫还击作战,其中血雨腥风、残酷惨烈的战场画面持续了数分钟。银幕上撕裂的肉体、迸溅的鲜血、凄厉的哀号、愤怒的喊叫,令人心理紧张、情绪激越。冯小刚之前在拍摄《集结号》时就提高过国产片战争场面的最高水平,在这一次的《芳华》里,他更进一步用一段长镜头让摄影师跟随战士们游移穿梭,配合几十人的走位,显得十分真实。冯小刚曾经说过自己对于一部好的战争片的看法,他认为它让观众看来一定是要呼唤和平的,同时让观众看到战争的残酷性,这样他们才会珍惜当下的和平。这段越战镜头是原著没有详细描述的,冯小刚最后呈现出来的“成品”,给观众带来极大的震撼与真实感,某种程度上也补充呈现了青春的另一种旋律:拼搏、热烈与牺牲。
3. 叙事视角单一便于影片解读传播
小说中,几个主人公的命运故事没有通过全知视角展开,也没有在哪个段落完整叙述一个人的命运,而是通过第一人称(即年轻萧穗子)、年长萧穗子和其他人的视角分散开来讲述,这种复调式叙事要求读者必须根据不够连贯的碎片化情节,适当“脑补”,还原出小说中人物的完整形象。而画外音式独白可能会使得读者在阅读小说过程中无法忘情投入,对此严歌苓在一次采访中提到她不需要读者跟着她的故事,陷进去出不来。“我这个作品就是要时时把你抓出来,让你停一停,跟着我思考,看看这个故事的发生。我要写的不是一个把你一直往前推的故事。”[5]这种叙事手法是受到其海外生活的影响,她坦言喜欢的欧美作家有索尔·贝洛、马尔克斯、博尔赫斯等,都对她的文学创作有较大影响。与文字这种冷媒介不同,作为热媒介的电影,较为单一的叙述方式与叙事视角便于观众解读接受,更易于传播。电影版《芳华》虽然采用萧穗子的画外音进行叙述,但剔除了小说中的其他视角,而且摒弃了原作中倒叙、插叙的手法,整部影片按照单一的顺叙进行,使情节衔接流畅自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