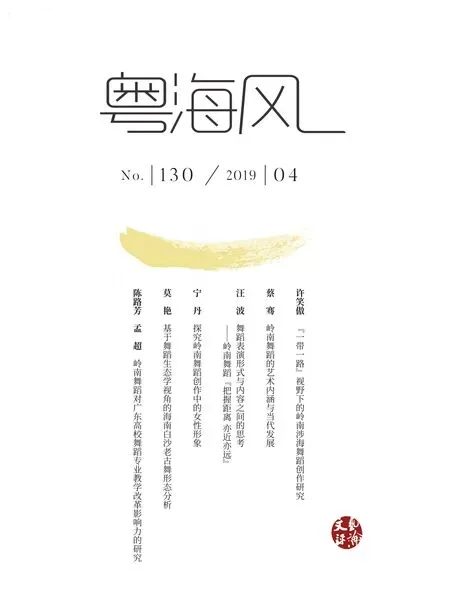试论道具在岭南舞蹈创作中的辅助性符号意义[1]
2019-01-15彭媛
文/彭媛
引 言
美学家苏珊·朗格在其著作《情感与形式》中指出:“艺术是人类情感的符号形式的创造。一切艺术都是创造出来的表现人类情感的知觉形式。”[2]从这里可以看到,艺术创造便是将情感通过艺术符号表达给世人的过程。何谓符号?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一书中指出,“我们建议保留用符号这个词表示整体,用所指和能指分别代替概念和音响形象……我们所说的符号是指能指和所指相联结所产生的整体”。这里所说的“能指”,是语言符号的“音响形象”,“所指”是它所表达的概念。“能指”是符号形式,亦即符号的形体。“所指”即符号内容,也就是符号所指能传达的思想情感或“意义”。例如,中国的“龙”是符号,那种奇特的动物形象是符号的能指,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是所指。因此,符号就是所指和能指,亦即形式和内容所构成的二元关系。
现代社会,人们生活在各种符号之中,用符号描述着事物的意义、传递着自己的经验。而舞蹈在“手舞足蹈”中用身体说话,以肢体作为动作“陈述”的主语言,其指向性直达欣赏者内心而使其得到共鸣。也就是说舞蹈运用肢体进行非有声语言的语言传播,将情感转化为艺术符号,传达给世人。肢体既是舞蹈动作的“直观材料”,又是舞蹈动作的“表现载体”,肢体语言构成舞蹈的主体性语言;而当主体性语言不能准确或完全地表达情感时,便需要凭借“辅助语言”的介入来完善表情达意。而直接与身体经脉相连的道具也就具有了物体语言的传播功能,成为舞蹈最常见的语言辅助性符号之一。从甲骨文中的舞“”字我们也可以看到,“舞”是“一人两手执物而舞”。
一、道具的表“象”性符号意义
与常用的语言性符号不同的是,“艺术是一种特殊的表象性符号”。苏珊·朗格在《艺术问题》一书中指出:“每一门艺术都有自己特定的基本幻象,这种基本幻象便是每一门艺术的本质特征。”这些幻象常常处于一种逻辑的“远处”,语言哲学的奠基人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认为它是“不可言说的”。而对于岭南舞蹈创作来说,这种“远处”,则恰恰是“不可言说的言说”。其肢体语言之所以能够创造“无限的可能”,从一定意义上看,得益于道具的“辅佐”、助力。
直观性是舞蹈“幻象”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编导在舞蹈创作中首先要注意的环节。在岭南舞蹈创作中,舞蹈编导在对生活素材进行集中再造的过程中,不是逐步撇开和脱离具体的动作形式,走向抽象的理念,而是时刻不脱离感性的形态,并逐步将其凝练为直观可感的动态形象。但在表现舞蹈直观性画面的时候,舞蹈肢体符号语言往往不能全面地进行表达,比如作品中的颜色、声音及氛围,此时,就需要道具的辅助,突出画面感,提升舞蹈作品中的直观性审美效果。
(一)以具象性道具直接“表象”,突出直观性
从符号学的“能指”意义上来看,道具的符号意义之一是它辅助舞蹈肢体,以象形道具直接表象。鲍列夫说:“舞蹈形象产生于具有音乐性和节奏性的表演动作,它们有时需辅以哑剧,有时还需配上特别的服装,以及日常生活、劳动和军用物品(武器、头巾、器皿)。”这里的武器、头巾、器皿等物品都属于道具的范围。在肢体表达并不足以表现出人物形象时,就借用道具描绘出“人”形,让观众直观性地看到人物的形象。
面具是人物形象的一种装饰,表达剧中人物的形象特征和喜怒哀乐的情绪,往往从面具的直观表象就能够看出人物的形象。如潮汕英歌舞的脸谱,有不同的颜色区分:红脸是秦明或关胜,乌脸是李逵,花脸是鲁智深,武生脸是武松。英歌舞的脸谱是极具潮汕地方特色的,它经过了数百年的发展与演变,逐渐形成了独特的舞蹈语言符号。面具在英歌舞中,用颜色从直观感受上将人物形象化。红色,直观感受是热情与正义,它是赤胆忠心的关胜;乌色,庄严肃穆,它是正直粗犷的李逵;花脸,多种暖色系搭配,它是嫉恶如仇、爱憎分明的鲁智深。在英歌舞中,如果光是舞蹈动作,是远远看不出人物形象的。而将面具戴上,人物形象顿时栩栩如生,使得观众能够直接通过面具看出来。因为这些脸谱都是观众所知道的水浒人物,所以一看到描绘这些人物的模具,观众自然能够直观地看出作品中的人物形象。
(二)以象征性道具间接“表象”,突出象征意义
“象征”是以可见的某种事物标记不可见的某种事物,被象征的本体是抽象的。在岭南舞蹈的创编中,象征是借助某一具体事物的外在特征,通过类比联想等思维手段,寄寓某种深邃的思想,或表达某种特定意蕴的艺术手法。“象征”能使抽象的概念具体化、形象化,创造一种艺术意境,增强作品的表现力和艺术效果。
1. 以象征意义的实体道具“表象”
笔者在学位专场晚会编创的岭南小舞剧《与妻书》的第五个舞段《战殇》中,运用红绸抽象性表象,来塑造人物形象。《与妻书》是以黄花岗起义为主线,以主角林觉民与其妻子陈意映为辅线的革命题材舞剧。其中《战殇》这一段说的就是黄花岗烈士战死后,他们妻子的悲痛与诀别之情。而怎么样才能突出妻子形象呢?从女演员们抚胸期盼、整理鬓角、碎步小跑等肢体符号语言只能看出她们的“等待”“思念”之情,妻子的直观形象表述得并不明确。于是,笔者便用了红绸这一道具,当大红色的绸缎盖在女演员的头上,一个“新婚妻子”的形象便凸显得淋漓尽致。在肢体的主体性符号语言尚不能表达清楚的情况下,红绸间接地完成了道具的“能指”性符号表达:塑造了一个让观众从直观画面上看到的“妻子”的形象。
以布景作为实体道具时,其表象性符号意义对于舞蹈的直观性审美效果的作用更大。如在大型民族舞剧《沙湾往事》中,为了营造出岭南风格的画面,突出岭南标志性建筑镬耳楼的形象,编创者们用到了一面画有镬耳楼飞檐的墙壁。在这里,岭南风景凝聚在一面墙壁中,墙这个道具在这里的表象性符号意义使得观众从墙壁的直观画面中可以看到岭南镬耳楼的缩影。由此,观众所看到的直观性画面审美感觉通过道具得到进一步深化,从而让观众更接近舞剧所营造的岭南氛围。
此外,全国家用电器工业信息中心还协同家电行业研究机构、数据调研机构及企业共同举办家电行业研讨会议;组织行业专家对行业创新技术、工艺、设计以及科技研发成果进行综合性审定、评价和推介;联合家电相关技术学会和大专院校举办学术交流活动,整理学术资料并出版学术论文集,促进行业信息互通和技术交流;同时,全国家用电器工业信息中心整合家电行业上下游信息资源,推进家电上下游行业融合、协同发展。
2. 以象征意义的色彩道具“表象”
小舞剧《红绫旭日》的群舞片段——“红棉颂”,运用了红色的绸子来表现“红棉”的形象。在舞蹈中,肢体语言的符号表现只能看到花的“枝叶”“蕊心”,对其颜色及品种却不能表现出一二。编导运用了大红的绸子来突出木棉的色彩形象,给人以直观的画面感:此花不是莹洁清丽、淡装素裹的玉兰;不是娇艳欲滴、富丽堂皇的牡丹;不是端庄秀丽、高风亮节的金菊;而是灿若朝霞、燃烧怒放的红棉。它是“英雄花”,它的色彩是革命烈士用献血浇灌而成的;观其色,犹如雾霭流岚,犹如英雄风骨。此外,编导在编创的过程中,或将绸子系在演员的腰际,让绸子随着演员肢体动作的摆动形成一定的“枝叶”弧度;或让演员将绸子拿在手中,让绸子翻飞、滚动,形成“花瓣”之象。这里“枝叶”“花瓣”通过道具的直观画面形象,完成了表象性的符号意义,从而辅助肢体表象符号语言来展示“木棉”坚挺巍峨的形象。
在有着“汉族舞蹈活化石”之称的禾楼舞中,稻禾的运用进一步突出了道具表象的直观性审美效果。禾楼舞中的稻禾是金黄色的,正是丰收的色彩。演员们用舞蹈动作表现出耕种、收割的农作画面,而这一抹金黄以直觉画面形象出现在观众眼前,让观众直接感受到这是稻穗成熟的画面。
3. 以象征意义的造型道具“表象”
梅州客家的“席狮舞”,运用道具席子形成造型,间接地完成了“狮子”的形象表达。“席狮舞的道具很特别,舞法也别具一格。由两人表演,一人就地卷起一张铺地的草席,捏成狮子模样,另一人手持蒲扇和一把青叶伴舞,随着鼓点音乐翩然起舞,或腾挪翻滚,或纵横跌扑、情趣横生”。在这里,通过席子的造型象征,给人以直观性的视觉冲击。此外,在原有“狮摆头”“狮脖伸缩”“参狮”“睡狮”“卧狮”等舞蹈动作的基础上,道具席子的运用,使得原有动作的幅度加大,狮子的形态更具有灵动性与趣味性,从而强化了狮子的表象特征,“在似狮非狮中显示出一种特有的质朴、亲和的美”。
二、道具的表“情”性符号意义
舞蹈的本质是一种表现情感的艺术。苏珊·朗格从符号美学出发,在《艺术问题》中重申了艺术的定义:“艺术是人类情感的符号形式的创造。”这种情感并非舞蹈演员本人情感的征兆,而是编导对各种人类情感认识的一种表现,也是符号的“所指”能传达的思想情感。苏珊·朗格在回答“舞蹈家为什么要进行这种创造”时,把我们对“舞蹈家创造了什么”的认识深化了一步——认识到舞蹈“虚幻的力的意象是舞蹈家‘内心生活’的外部显现及其‘情感概念’的符号表现”。“艺术家创造的意象是一种从实际的、因果的秩序中抽取的、仅为感知而存在的象征符号,是一种传达艺术信息的情感象征符号,而不是理性的语言象征符号”。舞蹈作品离不开“情”,情是一种感性的宣泄;是在舞蹈创作中第一步舞蹈构思的基础上发展开来;是从理性的桎梏中挣脱出来;是创作者的社会背景、生活背景,以及人生观、价值观的延续。而在岭南舞蹈创作的过程中,道具用象征的方法来营造舞蹈中的“意象”,实现其表“情”性符号意义。
(一)以道具作为情感反射的载体
舞蹈是抒情的艺术,情感的抒发需要一个载体,一种方式。在舞蹈作品中,舞蹈肢体语言尚不足以表达情之深刻时,道具此时运用象征的手法,以及通过改变身体语汇来达到更深刻的抒情效果。它既是一种内容上的强化,也是一种形式上的改变。而形式改变所创造出来的动作和姿势具有感情色彩和内涵意义,也就是通过“象”表白“情”。朗格认为艺术不是情感的“征兆性表现”,而是感觉形式的“符号性表现”,是对人类的“内在生命”的理解。因此,“表现性形式”作为一个整体包蕴着情感。道具在舞台创作时如何运用,所表现的形式,都体现了生命情感的特性,是一种情感的延伸。因此,这里的道具就超越了其本身的象形意义,带有了情感的符号意义。
笔者在舞蹈作品《睡、睡、睡……》中,以枕头为道具,反射现代人焦躁、不安的情感状态。在当下快节奏的“北上广”都市生活中,人们烦闷、不安、焦躁以致睡眠不安,渴望休息,心却被社会欲望填满,不能入睡。“白色”的枕头代表的是一种家的温暖,一种宁静与安详,一种不争与自如,而上述特征是当下都市人所缺少的。于是,演员疯狂地摔着枕头,不仅是暴躁不安的情绪的直接宣泄,更是“睡而不得”的愤怒反抗的心理表征。这一系列情感,无论是用跳跃语汇还是用旋转语汇,单纯的肢体语言都无法描绘出这种抽象的精神状态。而有了“枕头”的辅助,道具的所指意义便明晰可见:摔掉枕头,象征睡眠的破碎,让观众联想到暴躁的原因,从而揭示作品深刻的内涵。
(二)以道具作为情感寄托的媒介
“寄情于物”在舞蹈创作中比比皆是。通过“物”的象征手段,编创者们才能将作品中的人物情感思想表达出来。“艺术作品的情感,是艺术家在为了表现情感而创造符号形式时所想象的情感,而不是他在创作过程中真实感受的或者无意流露出来的情感。”作为情感象征意义的道具,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它自身的含义(也就是能指意义),而代表了作品中人物的情感思绪,是一种情感的寄托。
舞剧《沙湾往事》中,道具二胡的运用,是多种男女情感的寄托与象征。男女主角共同相拥拉奏二胡,二胡的连接与限制创造出了一系列表达爱意的倾仰、侧卧等舞蹈动作和姿势。二胡的形象,突出了其表情性符号意义:爱情。在后面的舞段中,当观众看到了男女主角拿着二胡出现之时就想到他们之间的情感纠葛。而后,女主角一个人拿着二胡进行追忆,到后来摔掉二胡表达情感的破灭,这一切情感的体现都是在观众们理解了二胡的所指符号性意义的基础上进行的。试想,女主角在表达追忆时,她的肢体语言是缓慢、停顿的,如果仅仅只是从肢体语言符号上来看,这个语言符号可以表达女主角独自的思绪,但可能是关于亲情、关于友情,而不能直接说明是表明爱情的。但当女主角将二胡拿在手上,经过前面观众对于二胡象征意义的理解,观众就能通过道具的表情性符号意义,以及肢体符号语言的共同作用,从而明白作品此处所要传达的思想感情了。
(三)以道具作为情感隐喻的触点
“喻”是比喻,是通过道具的“象征意义”来表达舞蹈作品潜在的情感思想。在岭南舞蹈创作的过程中,很多时候编导们并不会直接表明其情感内涵,而是会采用迂回间接的手法来说明主要情感。这里的道具所指符号意义主要是道具为作品营造出一种意象,这种意象效果一定是通过实物象征后作用于观众的视觉,其后观众通过自身的联想与想象而感受到作品表达的思想情感,从而产生共鸣。如此,则完成了作品的所指符号意义中的表“情”性符号意义。
比如在舞蹈作品《浮生若梦撑舟渡》中,编创者用咏春六点半棍的表象性符号特征意义,给观众直接展示出了“木舟”与“撑舟人”的形象,这是作品的形式表达。从作品的内容上来看,《浮生若梦撑舟渡》突出的是清朝年间红船弟子潇洒磊落、忠肝义胆的品质精神。中国自古就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士为知己者死”“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的侠义精神。编创者用木棍搭造了“红船”与“义士”,让人联想到了那个英雄辈出的年代,那段风云跌宕的岁月,表达了对红船弟子侠义精神的赞美之情。同时,“红船”与“侠士”是一种符号,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中的“仁”“义”“勇”。
三、道具的表“意”性符号意义
从结构语言学看,表意指能指系统和所指系统构成的表达含义的功能。任何一个舞蹈作品都离不开形式和内容这两方面的要素。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内容决定形式,形式又反作用于内容。岭南舞蹈作品如果避开内容而谈形式,是苍白无力的,因为作品凝聚了编创者独立思考的人生观,以及对待周围环境的经验与感受,它不可能是没有内涵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形式是为了表现内容,因此它是“有意味的形式”。这个“意味”是指舞蹈作品的意蕴与内涵,也就是符号学中所说的“所指”。当编创者在岭南舞蹈创作的过程中需要通过舞蹈画面向观众阐述舞蹈内涵,引起观众的共鸣时,就需要借助道具来表“意”。
(一)表达宗教文化之“意”
傩舞中的傩面具是一种特殊的符号。在“能指”意义上,它是“具象性表象”;而在“所指”上,“它是人类生命活动和内在精神活动的符号化呈现。在英歌舞的现代传承创作中,傩面具始终是傩舞的伴随符号。这一艺术符号本身又是‘有生命的’,它的‘生命力’在逻辑上与人类的生命力具有同构性”。“摘下面具是人,戴上面具是神”,一个“神”字形象地说明了傩面具所承载的宗教文化意义。
雷州海康县的《傩舞》中,“舞队包括戴有面具的土地公和土地婆,以及兵将。‘车’面具黑色,有胡须,手执斧头;‘麦’赤脸,有胡须,手执大刀;‘李’红脸,手执摇桨;‘刘’黑脸,手执铁链;‘洪’黄脸,手执三角红旗”。在这里,傩面具指代了与神进行“对话”的各种人物;而“傩”活动,则通过这些有特殊含义的面具与舞蹈肢体语言的共同作用,达到“赶鬼辟邪、祈祷平安”的宗教祭祀目的。
舞蹈是一种动态的、视觉性的文化现象,它与人类社会发展始终保持着同步性,从最初的娱神娱人到纯表演性质的舞蹈,逐渐从野蛮走向了文明。它通过其独特的语言来记载一个民族的生活特点、文化图腾。美国人类学家索尔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一个特定的人群在其长期生活的地域内,一定会创造出一种适应环境的文化景观和标志性的民俗符号。”傩面具因不同颜色、不同代表人物造型而有不同的意义:有表现勇猛、威武的各路神鬼;有表现滑稽、幽默的世俗人物;也有表现原始、神秘的动物图腾;傩面具与戏曲中的脸谱有异曲同工之妙。编导在传承性创作中,要特别注重根据地域宗教文化认真甄选面具,使傩面具与肢体语言共同达成“表意”性的符号意义。
(二)表达民俗风情之“意”
意象作为一个美学范畴,其“立象以尽意,观者辨象而会意”已成为舞蹈编导的创作航标之一。而其中的“意”,涵盖了风骨、品质、情志、风俗等内容。如何用舞蹈之“象”表现出岭南民俗之“意”,编导们在创作中除了运用具有民族特色的舞蹈肢体语言外,还大量用道具象征的生活环境缩影来进行表达。于是,道具富有了符号性的“所指”具体内涵——一个民族的生活习惯、节日风俗。如舞剧《沙湾往事》中高潮舞段《赛龙夺锦》,编导们为了突出岭南的龙舟赛事,用船桨做道具。这里的“船桨”就是岭南民俗“赛龙舟”的符号表征。
舞段中虽然没有河流和船只,但却通过船桨的象征意义,以及演员们用船桨所做出来的一系列前倾、后仰的大幅度动作,让观众感觉到这是一群在相互比赛划船的水手们,他们斗志昂扬,向着目标勇往直前。此时,道具的符号性辅助语言、肢体符号性语言再加上《赛龙夺锦》的岭南本土音乐,让观众们领悟到了这是岭南大地上流传已久的龙舟竞渡的民俗盛事。道具配合群舞整齐划一的龙舟划桨动作,创造出层次分明、立体震撼、排山倒海式的空间视觉效果,“透视”出中华民族不屈不挠、一往无前的精神力量与中华儿女的民族气节、热血本色,揭示岭南文化的大气魄。
(三)表达时代环境之“意”
时代环境的变迁,是推动舞蹈发展的主要动力因素之一。原始人类信奉神与巫,于是舞蹈以娱神;汉唐泱泱大国,接纳包容,于是舞蹈呈多元化发展;宋代程朱理学蓬勃发展,于是带有宋代严谨风格的程式化舞蹈应运而生。舞蹈创作如果抛开了“时代环境”,那么作品的发展空间是狭小的,不足以让观众反复进行推敲。那么如何对时代环境进行阐述?道具作为舞蹈形式手段的一种,辅助了舞蹈肢体语言的“表意”,让观众通过联想,感受直观舞蹈画面之下隐含的时代环境内涵。
在笔者创作的都市组舞中的第一个作品《离不开的手机》中,就是运用了道具反映时代环境这一表意性符号意义来进行舞蹈创作的。手机是信息快速发展,生活短、平、快的当今社会环境的缩写。看到手机,观众自然就会联想到生活中手机强烈的存在感:人们逐渐用手机代替了面对面的交流;家庭聚餐可以各人玩着彼此的手机而鲜少交流;朋友聚会是拿着手机进行各种拍照;走在大街上,到处都是低头一族……手机的符号性所指意义是信息的时代、匆忙的时代,以及人际交往渐渐冷淡的时代。于是,从手机的表意性符号意义出发,作品中的画面感就有了意义,其形式也就有了特殊的意味:拿着手机行色匆匆的上班族;自恋拍照的青年们;交流甚少的情侣;沉迷网络的游戏迷……通过手机的运用,作品中的动作与姿态形式具有了内涵意义,从而使得观众从形式画面之上懂得内容,深入了解作品的思想内涵。
结 论
随着未来符号学在艺术领域中的进一步运用和道具在舞蹈创作中的运用的不断探索,岭南舞蹈创作中道具的辅助性符号意义势必会得到更进一步的扩展。作为在岭南舞蹈创作中广泛使用的辅助性工具——道具,其“符号性”文化意义就具有了探索与研究的重要价值。从“象”到“情”与“意”是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象”是“情”与“意”的基础,而“情”与“意”又反作用于“象”。在研究“情”和“意”的时候不能脱离了“象”的表达研究,因为感悟“象”才能体会“意”,“象”是为了“情”和“意”做准备的。正如我国舞蹈理论家袁禾说:“‘象’不是生硬的概念,而是一个活脱脱的能变化的生命体,其鲜明生动的形象易于为人所感知,并在感知的过程中通过联想、体悟去领受更多、更深的‘意’,有利于人们从整体上把握对象。”对道具的符号性意义的解读,可以丰富道具在岭南舞蹈创作中运用的基础理论,为道具在岭南舞蹈创作中的运用实践提供理性思考。同时,道具作为舞蹈创作的一种辅助性手段,其符号性意义的探索可以推进舞蹈辅助性符号系统构建,为岭南舞蹈创编教材的编写提供理论依据。再者,从符号学视域研究道具在岭南舞蹈创作中的作用,可以开拓编创者的理性思维,并引用符号学的理论研究成果指导舞蹈创作实践。
注释
[1] 本文为笔者硕士学位论文《试论道具在舞蹈创作中的辅助性符号意义》节选,指导教师:成慧慧、李晓燕。
[2] [美]苏珊·朗格. 情感与形式[M]. 刘大基,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