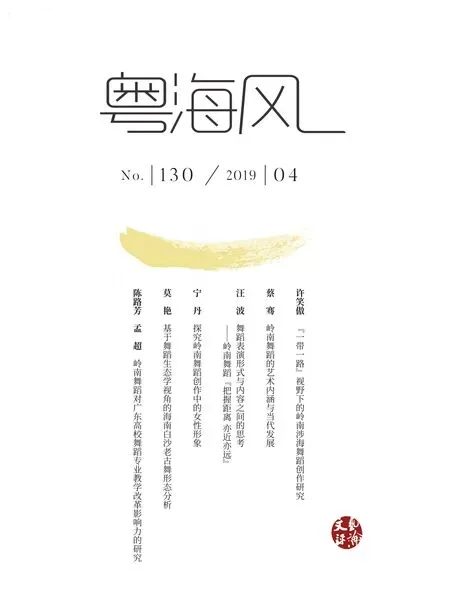舞蹈表演形式与内容之间的思考
——岭南舞蹈“把握距离,亦近亦远”
2019-01-15汪波
文/汪波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五岭之南——岭南,从地域上说涵盖广东文化、桂系文化和海南文化三大块,其中主体包括了广府文化、潮州文化和客家文化,岭南舞蹈是在岭南文化中滋生出的舞蹈艺术形态。其中舞龙、舞狮、龙舟、采茶、英歌、粤剧、雷剧、客家山歌、碉楼、飘色、渔人生活等,都是集地域特色文化于一体的象征。通过舞蹈艺术传播与呈现岭南特色,巧妙把握和运用尤为重要,创编者正如一名设计师,如何架接地域特色与舞蹈艺术之间的舞台呈现,是一部能较好突出岭南特色舞蹈作品其中的重要支点。通过人的身体构造赋予审美功能的视觉艺术,形成的动态行为和画面构图使感官认识获得一种精神对话、文化交流。舞蹈表演因地域赋予的特色具有独特的表演形式和鲜明的风格,同样相对应的内容交互地推动着舞蹈艺术的表达。
舞蹈表演的概念是指舞蹈演员通过身体语言,即有节奏地和有表情地对客观事物形象和主观心理世界的模仿与表现。舞蹈表演本身承载着舞者、编者、本源三者的情感内容理解与认识,是丰富亦是多维的。舞蹈表演为艺术创作活动提供了空间,交融三者之间产生的主观认识和情感赋予肢体的呈现状态与传达方式。舞蹈表演中形式或者内容,存在时已带有一定的意义和目的,两者之间产生的关系共同推动舞蹈表演呈现的结果,缺一不可。形式主外、内容主内,彼此过程中起到相互推动的作用。地域区间舞蹈艺术将要呈现的艺术审美指引了导向,准确地把握特色、特点,运用舞蹈形式的舞台化创作把内容(地域文化)立体化、视觉化。
一、内容存在的原因和组成因素
岭南文化是岭南舞蹈发展的核心,编创者在扎根地域民间文化活动的同时,吸收特色鲜明的原初形式,把握风格特点,结合时代特色展开舞台形式转换。
内容是支撑舞蹈表演的内核,是脉络走向的根本,有一定的稳定性。舞蹈表演内容具有时代感、典型性,经得起推敲,对同一内容不同人有着不同角度和方式的解读,折射出某个时期的个人观点和态度。内容被舞蹈艺术化后呈现在一定的时空中,打破限定,以另一种艺术形态审读某件事、某个人、某种现象。岭南中的地域特色涵盖生活习惯、区域环境,同时包括地理气候,以及人文精神等。
舞蹈表演中的内容是创作者对生活的概括、提炼和选择,是对客观现象和本质的反映。在提取的过程中编创者对所反映的生活或本质现象已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认识和理解,同时附着个人的社会理想和美学标准。舞蹈作品的内容存在于主客观因素,是能动的、发展变化的。由于客观生活现象的发展变化,促进了舞蹈内容的发生与变化,创作者存在不同的立场和评价,促使其塑造出丰富的艺术形象。“西关小姐”“东山少爷”这些具体的人物形象代名词,给予编创者一个丰富的想象空间,包括形式和内容。舞蹈内容带有阶段性和时代感,当中主观的情、意和客观的事、物等,是构成舞蹈内容的要素。舞蹈表演中的内容同时属于表演者的一种思想情感导向,存在一定范围,属于纵向的延展。舞蹈表演在所掌握的舞蹈动作、造型和技巧能力中,结合音乐、美术等艺术手段,将作品中的思想内容转化为可视可感的舞蹈形象。舞蹈表演中,演员(人的身体)是表演实践的主体,受到了作品的制约,同时也受到了编创者思想情感的影响,具有一定再创造的主观能动性。
二、形式存在的因素和组成部分
舞蹈表演中的形式包括了多种因素,存在于一定的时间、空间中,作用于视听,包括了舞者本身、音乐、画面构图、灯光服饰。其基本要素包括节奏性、连贯性、一致性和呼应性。[1]形式之间的关联主要通过外观要素和内部结构两方面。从美学角度探讨舞蹈内容包括:题材、主题、人物、情节和环境。形式包括了内在形式和外在形式,内在形式是结构、事件发展方式,外在形式主要指具体可感的物质形式。克罗齐在《美学原理》中说道:“画家缺乏了形式,就缺乏了一切”,“诗人或画家若没有掌握形式,就没有掌握一切。因为他没有掌握他自身。同一部诗的题材可以存在于一切人的心灵。但正是一种独特的表现,就是说,一种独特的形式,才使诗人成其为诗人”[2]。文学家歌德在《诗与真》中说过这么一句话“形式是一个奥秘”[3],对于舞蹈表演中的形式更要做到“四两拨千金”。
舞剧《沙湾往事》,根据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沙湾古镇有关“何氏三杰”的故事,从音乐形式、舞蹈形式等的设计充分突出地域特色。音乐“雨打芭蕉”“赛龙夺锦”的舞段与呈现内容相辅相成,同时从主线内容中加入时代背景,丰富情节,赋予家族人物音乐发展与传承更多的画面。
三、舞蹈表演中的形式分析
“没有无形的内容”[4],有意味的形式很重要。对舞蹈艺术而言,身体的运用组成根本的艺术传达,也就是运动的人体。舞蹈中构成的不同舞蹈动作经过提炼、组织,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或带有创作者的审美观点。舞蹈动作的形态、节奏和力量的强弱,构成了舞蹈表演形式中舞蹈形象的视态化,甚至达到形式即是内容,动作就是情节的审美意向。舞蹈动作具有形象性和抒情性,在舞蹈表演中产生了动作控制、表情控制等,做到形神兼备、虚实结合。罗斌老师曾在《舞蹈》中说道道,“动作,必涉及观念,而观念必触摸思想,过程中发生的舞蹈动作都是在传导编创者的想法与观念的一种形式。在似与不似之间寻找共通点,在心理理解有一个平衡的过渡,从而产生情感认同和思想共鸣。”
形式同时也是地域文化的标志,融地区人文风俗特色于一身,也是舞蹈艺术表达中重要的环节。但空洞的形式没有好的内容、饱满的内核,难以在鉴赏交流中产生精神享受和心灵震撼,最后只会形成视觉刺激。舞蹈艺术不仅追求视觉,同样还有听觉和心灵的交流。单纯的形式呈现在舞蹈艺术表达中是不可取的,舞蹈以人的身体为媒介,传达与交流是一种赋予现有空间和想象空间的探索,更多是在有限的空间中创造联想和想象情感。原创舞蹈《西关红棉》,以广州特色花裙木棉花为主题,寓意豆蔻年华中的女子丰富的内心。
除舞蹈动作本身,表演中还借助其他物质形式帮助舞蹈表现情感升华、环境渲染。音乐包含一定音乐表情和音乐形象、旋律色彩和音强节奏等,在舞蹈表演中赋予舞蹈动作更鲜明的情感色彩,并帮助舞蹈整体呈现营造出一个立体环境。音乐本身是一种形式,存在一定的情感表达,编创者在音乐体验过程中找到共通点,并把自己的思想观念附载在音乐旋律中,依照自己的设计以舞蹈动作为媒介物态化。音乐的风格类别和组织形式,同时体现了编创者思想内容的起伏变化。音乐的起承转合影响着编、演、观三者的内心感受,对心理状态起着导向性作用。音乐中的旋律和节奏帮助提升舞蹈艺术传达建立的审美感受,是形式中不可忽略的重要部分。舞蹈与音乐的交互推动舞蹈艺术表达,音乐能够在舞蹈艺术审美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岭南特色的民间音乐乐种丰富,同时特色鲜明。岭南文化中不可缺“水”,岭南音乐中也会突出“水”的重要位置,包括节奏感、音乐感等,与舞蹈相结合形成特点鲜明的岭南舞蹈审美。
舞蹈中使用的道具,有效提升舞蹈艺术传达。道具是集内容与形式于一身的物态存在,不仅凸显地域文化、时代特色、舞蹈形象,而且是连接想象的桥梁。舞蹈道具有象征、渲染氛围、点明主题、升华舞蹈内涵、传承舞蹈文化等作用。“风起岭之南”的《南狮梦》典型地体现道具舞蹈对传统文化的传承性。舞剧《沙湾往事》中的“群舟攘渡”,道具的运用营造了一个紧张宏大的环境氛围。在少儿舞蹈作品中对钱鼓的运用,突出了技艺的传承,还有内心外化的象征,比喻“明月”,表明月在岭南文化中占据重要的位置。岭南地区还有一个突出的“侨”文化,而“月”承载着对故乡的思念,以及一颗游子的心。道具在舞蹈艺术审美中的存在已不再是单一的物品存在,编创者结合舞蹈内容,在形式运用上借助道具拓宽了身体表达空间和审美情感想象。
舞蹈的构图,是一种视觉形式的组织与合成。舞蹈的媒介较为特殊,主要是人和人的身体,同时由人与外界物质共同构成的虚实画面。舞蹈构图是对整体空间的一种运用和切分,形成交互错落、主次之分的艺术空间。画面中有点、线、面的构成,以单模块画面构图中的方形代表安定,斜三角显示动势等带来不同的引申寓意和直观感受。俄罗斯小白桦歌舞团《小白桦树》当中的动作并不复杂,当编创者通过人群流动构成蜿蜒变化的队形,从而描绘出深邃的意境,令人记忆犹新,回味无穷。舞蹈表演中的形式离不开舞蹈构图、不同的队形、动作的层次、其他物质出现的时间、地点等,甚至由灯光切分后形成的空间构图。《再见吧,妈妈》运用了特殊的灯光效果,营造出朦胧、如梦似幻的母子相见画面,灯光呈现了另一种舞蹈语言。
舞蹈服饰,是舞蹈表演形式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服饰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带有一定的属性和意义。舞蹈表演中的服饰有助于点题,人们透过服饰获得基本的舞蹈信息,比如角色、地域、社会身份、年代等,并在此基础上“解读”舞蹈艺术作品。舞蹈演员在晚会开幕式中身着变色长裙,通过专门的设计使服装出现黄、红、绿、蓝四种颜色,呈现不同内涵,同时寓意四季变化。岭南因地域气候特征,整体服饰质地偏轻盈凉爽,区别于高原地区的服饰装束。颜色上的使用同样凸显了岭南特色,撞色的方式相对较少。舞蹈表演中的服装设计除了视觉引导外还有一个功能性,与舞者身体表达运用中产生视觉联动作用,增加层次感,创造出更丰富的视觉效果,提高舞蹈艺术魅力。
四、形式与内容的交互关系
岭南舞蹈中的创作与运用,是编创者在民间文化的原样中发挥想象,与其展开有机的结合,使得舞蹈表演具有一定的浪漫色彩并打动人心、感染观众。舞蹈表演中呈现的任何一种形式包括了“信息对审美主体(观众)的放射和传播,形式自身是形量,观众的接受是感量,信息的容量和对观众刺激程度的深浅更多依据信息(形式)自身”[5]。想象的空间是无限的,如同透过一种艺术形式遨游于另一个世界。
岭南舞蹈风格特色是我国民间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人物、故事、音乐、道具、服饰等突出文化特点和民俗特色。编创者把不可言传的时空物质化、视态化,把生命、情感视觉化,想象与科技相结合,产生亦远亦近的审美感受,丰富了舞蹈艺术表演中的肢体语言,以舞蹈为导引展开岭南文化传播与交流。借助形式各异的舞蹈语言组成从个体到整体从整体回到局部的艺术环境,过程中呈现的任何一种形式都是编创者的精心设计和选择,赋予一定的含义或引导性。“各个物品不再是孤立的摆设,而是有机地组合成一个整体,活跃于舞台上。”[6]编创者充分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充分调动不同的艺术审美,结合不同的技术手段使舞蹈表演中呈现出情感饱满丰富的艺术形象。舞蹈表演中的任何一种形式都是为了营造出特有的环境和独特的空间意境,透过肢体表演传达独特的思想情感,从而引起人们的思考与共鸣。
舞蹈中的题材和主题是舞蹈作品表演内容中的基本构成因素,主题是作品的灵魂和核心,影响着舞蹈作品思想性高度的主要因素。舞蹈选择的题材,以及表现的主题决定了舞蹈作品的基调,在实现传达结果之前的编创与设计都将以此为中心。题材和主题在不同的舞蹈作品中有着各自的存在方式,受到编创者本身的价值观和美学观的影响,由此产生一定的风格特点,舞蹈表演围绕着舞蹈作品需求展开组织、选择、创作等。舞蹈表演主要通过动作,动作是舞蹈艺术的语言,是主要的表现手段。当中的屈伸俯仰、高低起伏、轻重缓急、队形、节奏、动作本身的变化和转换,组成了动作形象,并塑造了舞蹈艺术形象。
舞蹈作品中存在的动作都是刻意而为之的,存在一定的目的性,包括思想和情感。编创者有组织地运筹舞蹈作品中的各种元素,形成了形式结构,也是结构视觉化的过程。舞蹈表演的形式产生于内容之后,并在舞蹈编创者对第三方理解认识后,寻找另一种传达方式,形成情感的寄托、精神的附载。舞蹈表演中的内容是思考中构成的想法,需要体现在具体可观可感的形式中,构造一定的境象,从而激发人们对此的呼应和联想。表演中的形式是刺激人们产生对舞蹈表演艺术中舞蹈语言的创造想象,包括时空中的情感与环境、事件与人物关系等。
(一)舞蹈表演形式与内容的情感关系
舞蹈在内容与形式上相互依存、交替作用下构成艺术传达的整体,舞蹈本身所具备的审美属性,是一种可视可感、富于情感节奏的动态艺术,舞蹈在传达美的过程中包括内容与形式两者构成的美的结构。在舞蹈表演过程中,营造一个特定的环境或氛围,为此时的舞蹈艺术呈现提供时空,同一个内容在不同的理解认识下可产生多种形式的艺术传达。舞蹈是视听艺术,当人们从一个现实空间中走进另一个特定的时空,以现代人的身份“亲临”审视过去或者未来,必须要有一个时空环境的转换,而此时舞蹈表演中的形式存在显为重要。通过特有形式的存在,把接受情感共鸣的观众带进一个特殊的时空中,跟随赋予舞蹈表演者本身的情感体味舞蹈艺术。舞蹈表演呈现的形式与内容两者间链接的主要因素是情感,没有情感就没有想象,情感是一种态度,是人对客观事物是否满足自己的需求从而产生的态度体验,影响着外在行为和主观意向。情感本身可以激发心理活动和行为的动机,舞蹈表演中的情感,存在于编创者的认识选择,同时展现了舞蹈者的理解和运用。只有融入情感的舞蹈语言在舞蹈表演中才能赋予舞蹈生命。
情感,作为舞蹈表演形式和内容之间的架构者,推动情节的发展变化。舞蹈表演通过形象的情景交融和艺术描绘将观众代入艺术想象的环境中,在有组织搭建的情境空间中体验情感。因境有情,因情出境,舞蹈表演需要凝练,避免冗长,在舞蹈表演内容链接中存在的形式和内容包括人与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牵引着舞蹈的开端、发展、高潮以及结局。经提炼并重新整合组织形成舞蹈方式的结构。高尔基曾说:“情节,即人物之间的联系、矛盾、同情、反感和一般的相互关系——各种不同性格、典型的成长和构成的历史。”舞蹈中的情节并不是叙事性舞蹈作品的专属内容,情感受到客观事物的刺激并存在于理性思考后,带有主观色彩,已被过滤后的情感具有个别性,当编创者将此情感转嫁在舞蹈作品中,影响着舞蹈的事态发展和审美取向。编创者的情感理解可以打破本身事件的发展规律,促使从舞蹈艺术审美出发,在结构中选择关键的“转折点”。通过舞蹈形象、舞蹈形态、舞蹈动作的不同节奏变化等诠释情感,在不同舞态形象相互交织的过程中产生带有主观色彩的情感认识,以此为基础推动情节发展。舞蹈表演中的情节不会无缘由地出现,情节归属于舞蹈内容,内容的存在附属于情感态度,舞蹈表演中提取的情节承载比现实生活中更为厚重的情感态度,并通过已被压缩的时空传达出来,以无限小而精的量感传递出丰富的思想和情感。
情感,作为舞蹈表演形式和内容之间的架构者,能赋予同一空间中其他物质形式寓意和想象,如寄物于思的方式,把形象的空间定格在物态形式中,例如原创舞蹈作品《号角声声》中一条铺满红色印记的布条勾起了那段烽火连天的日子的记忆。以一条红色布条为线索,拉开“时光倒流”的序幕,回到当年当时,在设定的情境中体验情感,获得共鸣,例如原创舞蹈作品《仿佛出现了你》中,一把空椅子放置在舞台的一角,伴随空灵的儿歌,灯光时明时暗,在视觉与心灵感受的刺激下获得时空转换和艺术形象情感凝聚点。除了实物的形式可以帮助想象外,舞蹈情感本身也是一种时间脉络,将其转化成可观的形式可以使调度或者路线,例如舞蹈作品《可预见的未来》中舞蹈演员从上台口开始沿着横向的一条直线表演到下场口结束,在不同阶段呈现的情感变化,由小至大,使得观者在短暂的时间里体味了人的一辈子,获得情感与思考。又如群舞《中国妈妈》,在舞蹈传达中抽取了“母亲”形象中的柔软慈爱,以中国母亲抚养日本遗孤的故事表现出母爱不因硝烟而陨落,不因仇恨而断裂的大美之情。舞蹈传达中塑造艺术形象,然而舞蹈形象本身有着典型性的特征,带有共通的情感态度,最大限度获得舞蹈艺术形象的共鸣点。艺术形象附属在一定的形式中,并包含一定的思想情感审美意向。舞剧《沙湾往事》中的故事人物情感,由“传承”推动着家族人物的价值取向和人生态向,彼此间的情感变化交流使人物在舞蹈表达中更具立体性。“以情推剧”,人物何柳年与许春伶的爱情故事推动发展,作为剧中的明线贯穿始终。
(二)舞蹈表演形式与内容的时代关系
时代,是以经济、政治、文化等状况为依据而划分的时期。生活百态,世态万千,生活中的个体不得不受所存在的时空影响,从而形成具有时间特性的三观,并对认识和观点态度的发展变化产生重要的影响。
舞蹈表演的形式与内容密切相关的是情感的附载,能够在一个寓意的物质形态中获得情感共鸣,无论对于编者、表演者或者观众本身,都是建立在认识与理解的基础上。舞蹈表演中内容不能只是表层的理解,需要深入事态本身的伦理、道德甚至人性中,从细微处传达大观之美。舞蹈表演的形式是创意之美,如何整合组织并富有新鲜感在舞蹈传达过程中显为重要。程式化的舞蹈表演不能带来过多的心灵震撼和思考,如同中国水墨画中的留白,以“空”为实,虚实相融,戏中有戏,寓意深远。舞蹈本身有自己的艺术局限性,在舞蹈呈现的过程中需要借助更多其他的艺术形式把非舞性的物态化,如时间、空气等。丰富的舞蹈语言,为舞蹈表演提供了完整立体的时空,使人们在其中感受到时间变化。
舞蹈表演中的形式与内容紧密相关,形成一个辩证关系。《论语·八佾》中孔子对《韶舞》和《武舞》的评论提及了传统的审美标准“尽善尽美”,强调双方完美地统一。舞蹈表演中运用的形式总是为适应特定内容需要而创造的,即内心有了趋向和要求,然后才有外部存在的物质形态(动作),外在因素的变化发展(生活、时代、人本身等)影响着舞蹈表演的形式变化。舞蹈表演中的形式相较内容来讲有相对的稳定性和独立性,稳定性主要体现在舞蹈表演中呈现的风格特点,舞蹈表演中的形式以民族舞蹈表演形式为例,受到地域文化、风俗人情的影响,在发展过程中形成具有一定代表性的表演形式,涵盖当地人文精神,体现在动作、体态、节奏、服饰颜色等,逐渐形成带有地域特色的表演形式。
同时舞蹈表演中的形式也有一定的独立性。内容决定形式,但形式作用于内容,可以使内容得到充分的表达,发挥了促进内容深化的能动作用。例如,同样的民族民间舞蹈的形式也能表现不同时代的生活内容,这些现象说明了舞蹈形式独立性的存在。必须在舞蹈内容形式的辩证关系中追求艺术作品的完美统一,从而“尽善尽美”。舞剧《沙湾往事》以家族变化与国家兴亡双线交互展开故事阐述,以舞叙事,从色彩秾丽转向基调深沉。时代背景赋予了故事更为丰富的艺术思考,反差对比将舞剧推动到情感表达的制高点。
五、结 论
舞蹈表演是艺术家的一种解读,在形式中渗透了内容,通过形式刺激感官产生联想,以此获得情感体验。直白地说就是借着艺术家建造的空间获得精神愉悦。内容是重要的,形式更是一种充满创造力的艺术想象,舞蹈表演中的内容与形式更是相扶相依的存在关系。彼此不能太近也不能太远,巧妙把握两者间的距离,才能创造出“惊喜”般的化学效应。岭南舞蹈的传承与发展,考验着我们每一个战斗在一线的编创者和岭南文化学者,时代赋予力量,弘扬区域特色文化,岭南舞蹈正向发展。“亦远亦近”,根植岭南,并从地区文化特色中得以提炼,通过艺术加工赋予其更为深刻的艺术感受和想象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