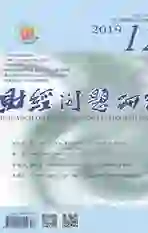财政政策的分配效应与中国经济增长
2019-01-13高远斌贾康
高远斌 贾康



摘 要:财政政策历来被认为是政府实施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造成严重影响,各国纷纷推出一系列刺激计划,中国也于2008年第4季度推出“四万亿”计划以促进经济增长。“四万亿”计划实施后,学术界对其评价存在显著差异。本文建立五变量VAR模型和三变量VAR模型,运用“四万亿”计划实施前30年和后10年的实际经济数据,具体研究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进一步分析财政政策对不同产业增长的分配效应,来深入剖析“四万亿”计划这一财政政策的具体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虽然财政政策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但“四万亿”计划的正向效应抵消了经济下行的负向效应,其有效实施确实缓解了中国经济下滑的趋势。本文是对“四万亿”计划实施10年的總结,对新时代中国财政政策的制定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财政政策;分配效应;经济增长;“四万亿”计划;VAR模型
中图分类号:F811.0;F0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9)12-0003-09
一、问题的提出
2008年开始的美国次贷危机迅速演变为全球金融危机,致使世界经济遭受重创,堪比1929—1933年的大萧条。受此轮危机影响,从2008年第3季度开始,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和俄罗斯等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均出现剧烈下滑,并持续至2009年上半年。在金融危机的严峻形势下,世界各国为了应对衰退,纷纷出台了超常规的财政政策,其力度之大、范围之广、数额之巨,在世界经济史上甚为罕见。在有效需求急剧下滑的外部环境影响下,以出口为导向的中国经济面临严峻考验。2008年11月9日,中国出台了旨在“保增长、扩内需”,促进经济平稳快速增长的十项措施,两年之内的投资总额达到4万亿元,全力保持国内经济平稳快速增长,减轻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中国全年国内生产总值为24.5万亿元;全年税收收入为5万亿元;全年公共财政支出为4.9万亿元。“四万亿”计划相当于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6%,财政收入的80%,中央政府救市的决心可见一斑。
对中央政府实施的“四万亿”计划学术界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评论。一部分学者认为,“四万亿”计划达到了预期目标,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如高培勇[1]认为,以“四万亿”计划为标志的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采取扩张取向并与时俱进地进行相机抉择, 在夺取应对全球性金融危机冲击的全面胜利、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并为中国未来五年规划的实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有利于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更直接、更有力、更有效”的作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等[2]研究指出,“四万亿”刺激经济政策的短期目标可以实现,但长期结构升级目标的实现有赖于抓住机遇大力推进体制改革。苏治等[3]指出,“四万亿”计划较好地熨平了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产生的意外冲击,对经济产生了积极的正向影响,使中国尽快摆脱了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然而,也有部分学者提出了不同见解,如卫梦星[4]认为,政府投资对2009年的“保八”目标从经济学意义上讲并非必须措施,其长期作用也不显著。高静严[5]认为,“四万亿”计划对提升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和国家综合竞争力的长期贡献很小,是一个救急的较为短视的政策。何治国等[6]指出,政府的经济刺激政策诱发的地方政府高杠杆率不仅影响了影子银行的发展,也影响了金融市场规制政策的落实。吴俊培和王玥入[7]认为,中国的积极财政政策虽然没有给政府部门带来直接债务风险,在短期内也能实现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但政策实施时间越长,积极财政政策的效应就会越弱。长期推行积极财政政策甚至可能会使得政策负向效应逐渐显现,政策风险也随之加大。金春雨和王伟强[8]认为,增加财政支出只能在短期内促进产出和引起通货膨胀波动,在长期内对产出增长和减少通货膨胀持续效果不强。
总体来看,关于“四万亿”计划的正向评价主要集中于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本身的短期效应方面,而关于“四万亿”计划的负向影响则更多集中于财政政策对经济社会其他方面的影响。从理论上来说,财政政策历来被认为是调节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但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长期还是短期是经济学家们普遍关注的问题,各大经济学派也围绕这个问题开展了深入的讨论,不同学者给出了不同的回答。如阎坤和王进杰[9]认为,中国在选择积极财政政策时要掌握好度,不仅要着眼于短期,也要着眼于经济的长期增长还要注意赤字政策的负向影响,以避免成为抑制经济增长的因素。满向昱等[10]认为,不同的财政政策具有不同的效应,要重视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非对称效应,充分发挥新生市场的基础性作用,根据经济运行状态相机抉择。许宪春等[11]认为,财政政策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比较直接,效果比较明显,但有时政策力度过大。储德银和崔莉莉[12]指出,政府在经济周期的不同态势下运用财政政策调节产出,不仅需要科学抉择其政策取向,还要准确把握政策的力度和节奏。刘金全和梁冰[13]指出,财政政策一直是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方式,财政政策操作的相机抉择要依赖于经济周期的阶段性。刘金全等[13]认为,中国应该在充分考虑财政政策成本的前提下,发挥积极财政支出政策对产业转型的引导作用,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有效组合,有助于防止经济出现持续下滑。除了上述关注财政政策总体效应的文献外,也有部分学者关注财政政策的分配效应,分配效应是相对于总体效应而言,即某一变量对另一变量产生效应时,在这两个变量可以分解为多个变量组合情况下,各个分解后的变量对另一变量或对另一变量分解后的变量所产生的分解效应,也称为分布效应。如Rong[14]最早研究了政府购买货物和政府雇佣冲击的分配效应,他通过实证分析得出政府两种购买支出类型对家庭收入的分配效应是完全不同的。Furceri等[15]以发展中国家数据为基础对政府支出项目的分配效应予以研究,Alan和Yuriy[16]以欧盟国家为例观察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都与Rong得出的结论基本相同。
本文在中央政府“四万亿”计划实施前30年和后10年实际数据积累的条件下,分析中国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分配效应。一方面,在分析财政政策的分配效应时运用的统计数据时间跨度大,且既考虑了财政收入情况,也考虑了财政支出情况;另一方面,在脉冲响应分析时不仅考虑了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总体效应,还考虑了对三大产业各自的影响。本文通过分析以期对新时代中国财政政策的制定提供启示。
二、研究设计
(一)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为了分析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分配效应,本文选取财政收入与支出增长率指标,同时为了进一步分析其对各产业的分配效应,选取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和三大产业增长率指标。经过整理加工,并剔除价格因素影响后得到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第一产业增长率、第二产业增长率、第三产业增长率、财政收入增长率(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率)和财政支出增长率(指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长率)共计6个变量的观测数据。本文数据均来自于国家统计局和财政部公布的官方数据,数据选取范围为1979—2018年。对上述6个变量的40年时间序列数据进行DF-GLS检验,数据均通过平稳性检验,说明变量平稳。1979—2018年具体观测数据值如图1所示:
本文分析的逻辑是先用第一阶段实际观测数据建立VAR模型,再由第一阶段的VAR模型预测第二阶段的经济变量,并将预测结果与第二阶段实际观测数据进行对比,从而说明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如果第一阶段模型可以看作是一个动态平衡系统,或者说金融危机和“四万亿”计划对经济增长没有影响,经济依然处于上升期,那么第一阶段对第二阶段的预测效果将非常好。反之,则表明第一阶段模型对第二阶段并不适用,各阶段需要分别建立模型。
三、五變量VAR模型构建与分析
(一)五变量VAR模型构建
由于国内生产总值可以表示为三大产业增加值之和,因此,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与三大产业增长率存在强相关性,不与三大产业增长率同时选入VAR模型。为了验证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分配效应,进而验证对不同产业增长的分配效应,选取反映经济增长率和财政收入支出增长率的指标。利用1979—2008年的第一产业增长率(Y1)、第二产业增长率(Y2)、第三产业增长率(Y3)、财政收入增长率(Y4)和财政支出增长率(Y5)5个变量按照内生性强弱顺序建立第一阶段的VAR模型,即五变量VAR模型[17]。根据LR、AIC、HQIC和SBIC准则选择五变量VAR模型的滞后阶数都为8阶,但这样会损失较多的样本容量,因此,通过FPE(Final Prediction Error)准则确定第一阶段的五变量VAR模型的滞后阶数为3阶,各阶滞后值表示形式如表1所示。
在应用模型分析前,首先,对第一阶段的五变量VAR模型中各个方程的联合显著性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由表2可知,无论是单一方程的某些阶数还是几个方程的整体,各阶系数均高度显著,模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二)五变量脉冲响应分析
本文利用不依赖于模型中变量次序的扰动向量正交矩阵的广义脉冲响应方法,生成的脉冲响应曲线都是正交化的结果。第一阶段的五变量VAR模型的正交化脉冲响应曲线如图2和图3所示,即财政收入增长率或者财政支出增长率变化1个单位对其他变量的冲击响应。
由图2和图3可以看出,长期内财政收入增长率或财政支出增长率两类变量的变化对三大产业增长率的影响都会被抹平,但短期内两类变量的冲击影响非常明显;短期内三大产业增长率对财政收入增长率的冲击表现为正向响应,而短期内三大产业增长率对财政支出增长率的冲击表现为负向响应,表明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政策对三大产业增长的冲击方向并不相同。财政收入增长率在短期内与三大产业增长率都呈现相同方向的变化,而财政支出增长率在短期内与三大产业增长呈现相反方向的变化。由此可知,财政政策在经济上升期对经济增长具有不同的分配效应,此时积极的财政政策应当是增加财政收入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
对第一阶段的五变量VAR模型进行方差分解,如图4—图6所示,从中可以看出,产业增长率受到的影响既有来自于第三产业自身增长部分,也有来自于第一产业增长和第二产业增长影响部分,且受到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自身增长的影响程度几乎相同;财政收入政策对三大产业增长率的分配效应明显大于财政支出政策对三大产业增长率的影响,尤其是对第一产业增长率的影响最明显。进一步说明,财政政策在经济上升期对经济增长具有不同的分配效应,此时积极的财政政策应当是增加财政收入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
用第一阶段的五变量VAR模型预测主要经济变量未来若干年的变化趋势,并与第二阶段经济变量的实际值进行比较,具体结果如图7所示。
由图7可知,第一阶段的五变量VAR模型明显高估了第二阶段的第二产业增长率、第三产业增长率和财政收入增长率3个变量,并且预测偏差进一步扩大趋势的可能性较大。这表明,第一阶段建立的五变量VAR模型从2009年开始不再适用。一方面原因是VAR 模型本身也预测不了金融危机;另一方面原因是金融危机前后,中国经济分别经历的是上升和下行两个不同时期,财政政策可能体现出不同的分配效应。因此,第二阶段需要重新建立VAR模型进行分析验证。
四、三变量VAR模型构建与分析
(一)三变量VAR模型构建
利用2009—2018年的第一产业增长率、第二产业增长率、第三产业增长率、财政收入增长率和财政支出增长率5个变量建立第二阶段的五变量VAR模型后,当根据阶数判别规则选择滞后阶数为1阶时,模型虽然通过了显著性和平稳性检验,但受观测值个数少、参数多的影响(仅有10年观测数据),无法生成脉冲响应函数。因此,为了消除样本容量损失太多而无法生成脉冲响应函数的影响,第二阶段通过减少模型中变量个数以提高自由度的方式,建立包含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Y1)、财政收入增长率(Y2)和财政支出增长率(Y3)3个变量的VAR模型,由此分析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分配效应。
在对三变量VAR模型进行平稳性检验时,特征值为0.8308、-0.0790+0.6110i和-0.0790-0.6110i,它们的模分别为0.8308、0.6160和0.6160,均通过了平稳性检验。
(二)三变量脉冲响应分析
由于第二阶段分析作为回应变量的总体经济增长率为单一变量,因而第二阶段的分析仅包含脉冲响应分析,而不包含方差分解分析。第二阶段的三变量VAR模型正交化的脉冲响应曲线如图8所示。从图8可以看出,财政收入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虽然会被抹平,但由于财政收入的汲取来源于国内生产总值,且主要通过税收实现,因此,在经济下行期过多汲取财政收入将会使经济增长率在短期内出现一定幅度下滑;增加财政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影响在长期内虽然会被抹平,但在短期内促进经济增长的效应非常明显。由此说明,一方面,“四万亿”计划在短期内对经济增长起到了促进效应;另一方面,财政政策在经济下行期对经济增长也具有不同的分配效应,此时积极的财政政策应当是增加财政支出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
2007年中国财政支出为5万亿元,2008年中国财政支出为6万亿元,财政支出增长率为20%(由于“四万亿”计划并没有完全实施,因而即使剔除“四万亿”计划部分,财政支出增长率也为20%)。如果“四万亿”计划按照原定计划在两年内全部落实,那么2008年财政支出增长率将达到60%,为20%的3倍。由图8可知,财政支出增长率提高1个单位时,大约两三年内可使经济增长率提高0.4个百分点。按照财政支出增长率提高为3倍计算,则最高可使经济增长率在两三年内提高1.2个百分点。这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然而“四万亿”计划最终并没有完全落实,实际经济增长率也没有达到第一阶段五变量VAR模型的预测水平,但已经起到了提振信心的心理作用,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经济下滑,对稳定经济增长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如果“四万亿”计划的实施是完全的,则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将更加明显。总之,虽然从长期来看,财政支出政策的促进效果会最终消失,但“四万亿”计划的正向效应和经济危机的负向效应相互抵消,短期内起到了阻止中国经济进入迅速下滑趋势的稳定器作用,有利于保持中国经济平稳运行。
五、结论与启示
(一)结论
本文通过建立五变量VAR模型和三变量VAR模型,运用“四万亿”计划实施前30年和后10年的实际经济数据,通过研究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一步分析财政政策对不同产业增长的分配效应,来深入剖析“四万亿”计划这一财政政策的具体效应。
第一,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政策对经济增长具有不同的影响,且表现出明显的逆周期效应,是政府实施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前的经济上升期,积极的财政政策汲取财政收入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金融危机后的经济下行期,积极的财政政策应当是增加财政支出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过多地通过税收汲取财政收入反而会抑制经济增长。“四万亿”计划的实施正是在经济下行期,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并且它实现了促进经济平稳过渡的目标。
第二,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短期效应非常明显。财政政策实施以后对经济增长的长期效应几乎会被抹平,不能对经济的促进或抑制发挥作用,但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短期效应非常明显,对防止经济短期内大幅波动具有良好的调节效果,是稳定经济增长的手段之一。
第三,第三产业增长受到的分配效应特点突出。从财政政策类别来看,在经济上升期第三产业受到财政收入政策的影响相对较大,即增加财政收入可以刺激服务业从业人员工作的主观能动性,从而促进第三产业增长。从产业类型来看,尽管各产业自身是其增长的内源性动力,但第三产业的增长不仅受其自身影响,还分别受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增长的影响,且来自于自身及另外两大产业的影响几乎相同。这表明第三产业受到的分配效应与另外两大产业有所不同,特点突出。
第四,“四万亿”计划有助于抵消金融危机的影响。尽管“四万亿”计划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时效有限,但“四万亿”计划主要投资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时,可以同时带动第三产业发展,可以对整体经济增长发挥良好的促进作用。中央政府的“四万亿”计划对于抵消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增长下滑的影响发挥了积极作用,维持了中国经济持续平稳发展。
(二)启示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后,中国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所体现出的分配效应,与Alan和Yuriy[16]于2012年对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的研究结果非常相似,这也进一步表明了本文结论具有一定的普遍适应性。以“四万亿”计划为代表的中国财政政策对现在和未来都具有重要的启示。
第一,积极的财政政策应进行相机抉择的逆周期调节。积极的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可以发挥良好的促进作用,但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应当选择不同的政策手段。在经济上升期,应当采取提高税收、减少支出或双管齐下的紧缩性财政政策;在经济下行期,则应当采取减税、增加支出或双管齐下的扩张性财政政策。
第二,财政政策实施过程中应当注重政策实施时效。由于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时效以短期为主,因而在政策使用过程中应当区分不同政策并注重政策的连续性。既要考虑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以及长远目标,也要注重短期效应与长期效应相结合,选择合适的财政政策。如增加政府投资,如果不是持续性的政策,则表明只能用作短期刺激。减税如果是持续性的政策则有利于在更长时期内发挥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
第三,积极的财政政策应当更加注重对第三产业的调节。国家通过财政政策调节宏观经济时应当充分考虑不同的产业特征才能收到更好的调控效果。投资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时可以同时带动第三产业发展。在经济上升期对第三产业增加财政收入政策的总体效果会更好,而在经济下行期则不宜对第三产业实施增加财政收入政策,减税是较好的选择。
第四,减税是当今形势下可取的积极财政政策。“四万亿”计划是国内經济面临类似金融危机事件时的突发性下降而选择的,其主要目标是发挥短期效应实现软着陆。而面对经济渐近式缓慢下行时,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应当注重政策的持续性,发挥对经济增长的长期促进效应。那么温和的减税政策可以持续实施,它有利于发挥财政政策促进经济持续增长的分配效应。因此,面对2018年中国经济再次出现困难的形势,对居民和企业实施长期减税是正确的积极财政政策选择。
参考文献:
[1]高培勇.新一轮积极财政:进程盘点与走势前瞻[J].财贸经济,2010,(1):5-12.
[2]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卢中强,隆国强,等.中国:在应对危机中寻求新突破[J].管理世界,2009,(6):4-18.
[3]苏治,李媛,徐淑丹.“结构性”减速下的中国投资结构优化:基于四万亿投资效果的分析[J]. 财政研究,2013,(1):43-47.
[4]卫梦星.“四万亿”投资的增长效应分析——“反事实”方法的一个应用[J].当代财经,2012,(11):16-25.
[5]高静严.从宏观角度分析“四万亿”计划对中国经济的影响[J].中国市场,2016,(50):12-14.
[6]何治国,陈卓,刘淳.“四万亿”政策背后的地方政府融资困局[J].清华金融评论,2017,(9):103-104.
[8]匡小平,龙军.现代西方学者财政政策效应理论文献综述[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10):76-81.
[9]王文甫,王雷. 1990 年后中国财政政策效应阶段性分析[J].经济问题探索,2012,(5):49-56.
[7]吴俊培,王玥入.积极财政政策风险的实证分析[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4,(1):3-12.
[8]金春雨,王伟强.我国不同时期财政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研究[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5):31-39.
[9]阎坤,王进杰.积极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的效应分析[J].世界经济,2003,(4):52-59.
[10]满向昱,宋彦蓉,郑志聪.中国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非对称性效应研究[J].财政研究,2015,(4):61-68.
[12]王文甫,张南,岳超云.中国财政政策冲击的识别与效应——符号约束方法下的SVAR分析[J].财经研究,2015,(6):70-81.
[11]许宪春,王宝滨,徐雄飞.中国的投资增长及其与财政政策的关系[J].管理世界,2013,(6):1-11.
[12]储德银,崔莉莉.中国财政政策产出效应的非对称性研究[J].财贸经济,2014,(12):27-39.
[13]刘金全,梁冰. 我国财政政策作用机制与经济周期波动的相依性检验[J].财贸经济,2005,(10):36-40.
[17]刘金全、印重、庞春阳. 中国积极财政政策有效性及政策期限结构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14,(6):31-43
[14]Rong,L. The Distributional Effects of Government Spending Shocks[J].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2013,21(10):1-29.
[15]Furceri,D.,Ge,J.,Loungari,P.,et al. The Distributional Effects of Government Spending Shocks in Developing Economics[J].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2018,15(57):1.
[16]Alan,J. A.,Yuriy,G. Output Spillovers From Fiscal Policy[J].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2013,103(3):141-146.
[17]陳强.高级计量经济学及Stata应用(第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361-445.
(责任编辑:巴红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