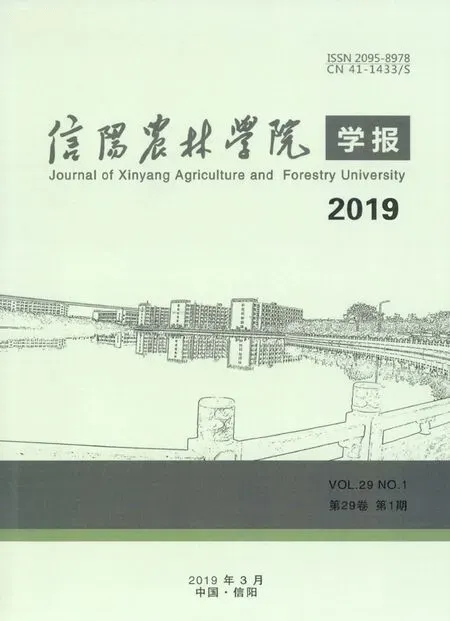乡村社会治理的法治路径
——基于乡村振兴战略的检视
2019-01-12周俊
周 俊
(信阳农林学院 发展规划处,河南 信阳 464000)
从乡村振兴战略到中央一号文件,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乡村社会发展问题。乡村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理论在乡村社会的生动体现。由于目前各区域乡村社会发展步调不一,经济政治文化生态差异万千、情况复杂,要实现乡村社会治理的良性循环发展,乡村经济振兴是基础,是保障乡村社会秩序和谐稳定的基石。从政策时间节点来看,从深化乡村改革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从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到乡村社区建设、乡村振兴发展,党的各级政府紧跟政策形势,保持着全国一盘棋的宏观规划思路。从治理空间布局来看,乡村治理改革的内容成为全面深化改革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治理成效影响着中国乡村社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进程。
1 乡村社会治理研究文献综述
通过中国知网搜索以“乡村社会治理”为主题的文献有875条结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层面:朱余斌从乡村治理主体要素——政党(中国共产党)、政府、农民、市场、社会组织等方面提出构建“政党领导、政府主导、农民主体、市场引导、全社会参与”的多元主体协商共治的乡村治理体制,从而助推乡村治理现代化目标的达成[1];吴莹以分析实证案例为切入点,以当前城镇化失地农民政治权利为例,从理论与实践双向维度提出中国农民政治利益变革与优化的实现路径[2];陈锡文以“乡村振兴战略”为视角,提出中国一直是传统的农业大国,区域发展不平衡、城乡发展不平衡,三农工作任重道远,意义重大,国情决定乡村必须振兴,和谐乡村社会的经济动能来源于乡村振兴发展,乡村能否振兴发展是乡村社会有效治理首先考量的基本点,是缩小城乡之间差距的战略路径选择,是新时代下“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农村的全面贯彻落实,也是整个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3];韩俊强调必须围绕“钱、地、人”等关键要素供给,建立向乡村倾斜的政策体系、盘活土地流转、强化人力资源优势[4];赵晓峰等以中央一号文件为观测点进行分析,将党中央历年发布的20个“中央一号文件”作为研究对象,论述村委会自治、新农村建设、农村社区管理、多元化乡村治理创新等内容[5];刘金海从乡村治理模式结构进行论证,总结村民自治30年经验,提出有一般模式、发展模式、创新模式等[6]。
马克思、恩格斯社会治理思想也在诸多方面对中国乡村治理的变迁轨迹和发展提供了思想来源和现实参考。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民性是国家最突出的性质之一,也是国家履行社会治理职能的最高原则。马克思认为,历史是人民书写的,自觉有序地参与治理国家和社会事务是人民群众主体地位的必需条件[7];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从形式、手段、线索等方面极大促进了国家进步[8];马克思、恩格斯建议,通过建立一种社会制度,使得社会成员不仅促进社会财富增长,参与创造社会财富,而且参加管理和分配社会财富[9]。
从国外的前沿学术研究来看,将以奥斯特罗姆教授夫妇为代表的印第安纳学派(制度分析学派)中的“多中心治理理论”引申到当前中国乡村治理中来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该学派坚持“多中心治理和自主治理”社会公共事务、社会协同参与、公民有序参与,优化治理结构秩序,以调动多元主体在公共管理事务的集体合力,从而保障社会治理的可持续发展。奥斯特罗姆在其经典著作《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一书中,主张通过实证的方法,从博弈论的角度把公共市民社会看作是一个多元的体制,探讨政府、市民、社会之间自主治理公共资源的可能性,就公共事务治理解决方案,设计有关社会治理的理论模型,强调自主核心社会治理的构成元素及其有关制度设计[10]。
从已有的研究乡村社会治理的文献看,主要从主体要素、历年中央一号文件、农民利益优化实现、国情现状、实践案例、关键要素等方面进行研究。乡村社会发展主要是振兴乡村经济,如适时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因地施策,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畅通农村发展道路,兴建水利灌溉工程,提升农民谋生本领,实施农业科普工程,惠及广大农村地区,实现农业发展、农村繁荣、农民富裕。探索从乡村社会结构秩序、实现路径和法治保障方面进行研究,希冀从全新的宏观视角,优化乡村社会治理体系,从而实现乡村社会振兴蓝图。
2 乡村社会治理的现实困境
乡村社会治理是发展中国家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不可回避的问题。欧美发达国家地区由于现代工业化进程历史周期漫长,其乡村社会治理主要是从欧美乡村社会长期自身发展及民间社会力量顺势而为的自然演进发展而来,乡村社会治理过程中各种利益主体间的冲突纠纷趋于温和,处于相对隐性发展状态。而广大发展中国家面临加速的工业化进程,为追赶欧美发达国家地区,往往采取自上而下、顶层设计的政府主动推进战略,其在乡村治理中产生的矛盾冲突问题处于阶段性对立的形势,呈现出显性发展状态。
能否妥善解决农业、农民、农村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乡村治理的预期成效。建国以来,国家优先发展城市工业,工业部门借助“工农产品剪刀差”的形式积累资金,农业、农村和农民为我国现代工业体系的建立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传统农业边缘化、村落日渐式微、农民因循守旧、农村文化休闲设施匮乏、闲时赌博成风等现象仍然存在,边远地方甚至仍有村民法制观念淡漠、村霸欺行霸市,严重败坏乡里民风的现象。据统计数据显示,55岁以上的农业生产经营人员占比33.6%,加之一部分双栖人(城乡之间流动的人口),实际农村老年人占比更高,“三八六零六一”现象突出。从收入和消费看,尽管近年来农村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增长速度快于城镇居民,但 2016 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和消费支出仍分别是农村居民的 2.72 倍和 2.28 倍,单位农村居民家庭的大件商品拥有率依然不容乐观。 从全员劳动生产率来看,2016 年非农产业达到人均 12.13 万元,而农业只有 2.96 万元,前者是后者的 4.09 倍[11]。2001年我国城镇化率38%,2015年已达到56%,年均增长1.2%[12]。以上数据表明,城乡之间的差距值非但没有缩小,反而一直在持续拉大,农村农业的发展前景令人担忧。要治理好快速转型的乡村社会、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乡村社会协调发展,需要从诸多方面探索乡村社会治理发展。改革开放40年来,城乡二元结构仍是我国最大的结构性问题,不仅是实施乡村社会治理亟待破解的突出问题,同时也是制约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社会问题。应该说,从改革开放的解放生产力到现阶段的乡村社会治理变迁,可以称得上是一场伟大的时代革命。
3 乡村社会治理的基础
当前要实现乡村社会治理和谐有序发展,必须通过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切实增加广大农民改革开放成果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一个重要理论基点就是关注国计民生、关注农村社会、关注基层发展。十九大报告中“优先发展”“农业农村现代化”等词的出现,体现了党中央对农业地位的高度重视、对农村未来的无限期许、对农民福祉的高度关心。因此,必须坚持优先发展和融合发展两大原则,统筹“三农”工作,补齐“四化”短板,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重要基础。
3.1 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原则
建国之后我国工业基础薄弱,百业待兴,并且受前苏联优先发展工业重工业思想的影响,集中一切力量建设城市、发展城市工业,长期利用工农业剪刀差支持工业发展。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继续沿袭计划经济发展思想,将发展重点长期放在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上,这主要是当时国家战略发展的客观需要,使得公共资源配置主要向城市集中的趋势越发明显。同时,生产要素在市场流通过程中,总是自发有序的向利润率高的行业集聚,农产品低廉的附加值造成农业发展后劲不足,乡村社会仅是表面相对繁荣,实际日渐衰退、凋零,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界限日益扩大。因此要牢固树立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理念,把对农业农村发展落实到具体惠农政策上[13]。
3.2 坚持城乡融合发展原则
受城乡二元经济体制的影响,过去一个时期内我国城乡间的发展是相互隔绝的,要素不能自由流动,产品不能等价交换,产业缺乏合理分工。特别是目前国家提出发展“中心城市”战略,本意是构建相对合理的区域空间城市群,带动新兴卫星城市,从而促进区域经济融合发展,但现在中心城市的首位度在本省经济中的占比越来越高,直接反映生产要素在中心城市的集中程度越来越高,产生城市虹吸效应,与城乡一体化进程背道而驰。因此理应坚持城乡融合发展原则,确立国家中心城市的目标发展定位,处理好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的错位有序发展,合理把握中心城市的首位度系数。从城乡居民的收入比来看,1978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57:1,而2017年城乡收入比是2.71:1,改革开放近40年,城乡两极分化日益严重[14]。这一现象引起党中央的高度重视,要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新时代我国的国情决定必须加强顶层制度设计,促进城乡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一体化,形成优势互补、互为支撑的城乡产业发展新格局。
4 乡村社会治理的法律体系
乡村社会治理需要探索一种将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结合在一起的社会公共秩序,既保障农民的个人权利,又维护公共利益[15]。通过历史上的乡村治理变迁可知:乡村社会必须落实村民的公民权利、确立乡村社会的主体地位、完善民众依法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渠道,确立为广大民众认可的公共治理规则,在法治轨道上推进乡村社会各领域的治理策略依法有序进行。因此,以法治推进乡村社会治理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实现新的跨越,不仅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应有之义,也是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之举。
4.1 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习总书记明确指出: 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为乡村社会发展和乡村社会稳定提供制度支撑体系。村民自治是基层组织自我管理的重要体现,是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在乡村社会的生动实践,也是我们党创新管理乡村社会的新思路,是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举措。法治是乡村社会治理的制度保障,健全的法制制度能够维护农村的安全,加强农村法制宣传,推动普法活动的开展,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树立文明新风尚,夯实乡村治理的道德基础,提高犯罪成本,有力地降低农村犯罪率。
4.2 完善乡村社会法治工作机制
注重发挥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的综合作用,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实力,构建良好乡村治理体系的组织基础和经济基础。坚持及时发现乡村邻里矛盾问题,未雨绸缪,做好有关纠纷解决的预案和防控措施,发挥民间乡贤和村两委、调解委员会的作用,把乡村社会矛盾消化在萌芽状态。坚持以法治建设为基石,建立健全社会矛盾协商沟通机制,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同时,积极推广“坚持重视和做好群众工作、坚持预防和化解矛盾、坚持尊重和维护人民权益、坚持注重和加强综合治理、坚持紧跟时代发展、坚持改善党的领导”的枫桥新经验[16],妥善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创新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模式,构建村民广泛参与的“大调解”体系。
4.3 发挥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关键作用
要加强基层党组织战斗力建设,提升自身组织治理水平。列宁曾指出,堡垒往往最先从内部攻破。因此,必须将党组织的“六大建设”贯穿基层党组织建设中,增强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协调能力,及时化解乡村社会治理中出现的各种利益冲突,保证乡村社会依法有序运转,保障村委会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实行村民自治管理。长期以来由于国家急于建设完善工业体系的经济需要,秉承对农业一味索取的政治政策,加之基层政权组织管理混乱,简单粗暴作风盛行,传统的鱼水之情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严重对立的干群关系,以九十年代中后期为甚。因此基层党组织要摒弃“家长制”“一言堂”等专横跋扈的专制作风,肃清基层党组织不良政治生态,将法治理念贯穿基层党组织民主政治制度中。在世情、国情、党情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党员干部要牢牢坚持依法治国的根本要求,切实提高办事法治自觉,坚持在乡村社会治理中践行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将法治精神贯穿于自身的底线思维[17]。 要加强基层组织党建工作,防止乡村基层一些人或群体在制度变迁中利用制度的漏洞谋一己私利或寻求部门利益,抓住基层党员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
4.4 加强乡村社会法治文化建设
列宁曾说过,在一个文盲的国家里是不能建成共产主义社会[18]。因此,法治文化理论在乡村治理中具有重要的指示作用。法律必须被尊崇,不能成为束之高阁的摆设,法律必须在社会实践中真正循环运行。乡村基层干部作为学法、守法、用法的典型示范者,应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同时,在法治环境上,通过乡村文化长廊基础设施建设,营造良好的法治文化氛围。促使民众在社会生活中积极参与法治文化建设,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开展“好媳妇”“好公婆”“五好家庭”等乡风文明教育活动,提升民众道德素养,养成道德习惯,倡导道德风尚,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增强法治的道德底蕴,在全社会形成崇德向善、遵法守法的良好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