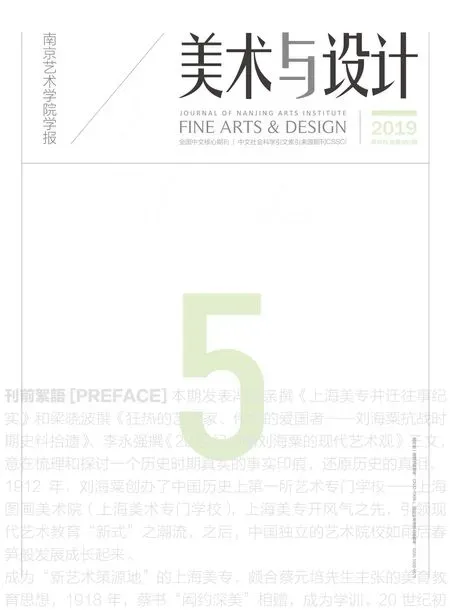隐叠复现:近代江南文化家族艺术文献整理的多重意蕴
——以平湖传朴堂葛氏为中心的考察
2019-01-09丁小明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上海200241
丁小明(华东师范大学 古籍研究所,上海200241)
江南文化家族作为特殊的文献整理集群,在近代中国艺术文献整理活动中起到重要作用。他们构建起闳伟的家族文献栋宇,向世人昭示文化家族艺术文献整理繁盛景象的同时,又往往会越出其家族文献整理的阃隩,在江南府州甚至更大的区域内推进艺术文献收藏、整理与出版事业的进行。有鉴于他们在艺术文献整理上实绩,我们理当将近代江南文化家族的艺术文献整理活动纳入我们研究的视野。本文以平湖葛氏所遗存的艺术文献为考察对象,在盘点葛氏家族艺术文献整理的基本内容后,进而探寻出葛氏家族文献整理中连续性与阶段性相结合的复合特质,并揭示近代江南文化家族艺术文献整理中所隐叠着的家族、地域与文献的多重意蕴。
一、葛金烺、葛嗣浵、葛昌楹:平湖葛氏艺术文献整理之精英
平湖葛氏在宋元明三朝一直播迁于江浙的金华、江宁诸地,到明末的葛如宇因避乱而迁浙江平湖乍浦后,始定居平湖,葛氏迁平八世祖葛肇基因在闽省贩运木材到外地而致富,为葛氏家族投身于文化家族准备了经济基础,葛肇基子葛金烺在光绪九年(1883)的登科折桂则为葛氏家族积蓄文化资本,而葛金烺、葛嗣浵、葛昌楹祖孙三代寄情翰墨、醉心于艺术鉴藏的家族文化活动,则不仅是葛氏家族“诵祖德之清芬,咏先人之骏烈”的家门盛事,更是一份极为可观的近代江南艺术文献遗产。
葛金烺是葛氏家族艺术文献整理的始祖,葛金烺(1837-1889)“异禀力学,十岁能诗”,同治四年(1865)成为廪生,惟科举不顺,乡试“八试不第”,迟至光绪九年(1883)才进士及第,后官刑部主事,改户部郎中。光绪十六年(1890)正月卒,享年五十四。葛金烺博通群籍,有《传朴堂诗文稿》行世。他早年为谋衣食,仆仆于江浙闽等地的商旅道中,风尘牛马之馀,唯嗜好品鉴与收藏名人书画,葛金烺在《爱日吟庐书画录·序》中曾云:“花于春,艳矣,足以悦吾魂;月于秋,皎矣,足以涤吾魄。然而花不常春,月不常秋也。惟骚人逸士,啸抒写之,则一展帙而恍遇于目,其为悦魂涤魄如故也。书与画之致佳者,无殊花之艳、月之皎也。余自束发,癖耽于此,见即罗而致之。[1]”显而易见,鉴赏书画带给葛氏的精神愉悦有如秋月春花的美景般“悦吾魂”“ 涤吾魄”,所以,他南北奔走,“遇有赏心,辄不惜倾囊以购”,其收藏也就随之日精且富。光绪七年(1881),葛金烺本着“花留其艳,月留其皎”之意,在参照乡贤高士奇《江村销夏录》体例的基础上,汇聚他二十年所得历代书画精品而成《爱日吟庐书画录》一书,此书成后,影响甚大,缪荃孙以为比之高士奇《江村销夏录》,而有“著录益慎、考订益精,后出愈工”的特色。当然,葛金烺的《爱日吟庐书画录》一书对葛氏书画收藏的意义还在于,不仅为葛氏艺术鉴藏及文献整理奠定坚实基础,也为其子葛嗣浵继续发扬家族艺术鉴藏及文献整理事业指明方向。
葛金烺卒后,其三子葛嗣浵继承葛氏家族艺术鉴藏及文献整理事业,葛嗣浵(1867—1935)曾官工部主事,庚子(1900)事变前,弃官南归,居家后,尽管风雨如晦,却以尚友先哲、摩挲前贤翰墨为乐事,在他的努力下,葛氏家族艺术文献整理成果更为丰硕。民国初年,他先后编成《爱日吟庐书画补录》《爱日吟庐书画续录》《爱日吟庐书画后录》三书,这其中后两书收录葛氏所藏三百馀件历代书画名迹皆为葛金烺的《爱日吟庐书画录》中所无有者,三书的编就既说明葛氏书画收藏与艺术文献整理事业的延续,更说明葛嗣浵继承父兄遗志而广大之的葛氏艺术文献整理谱系的确立。无怪乎金兆蕃赞其云:“词蔚聚二世数十年所藏,远对曩哲,挟旷代之思;近承家学,绎过庭之教。芬芳悱恻,感慨无涯”。而缪荃孙在肯定书中“乔木之思,堂构之喻,岂不欲继继绳绳,传之数百载而不敝哉”的宗族情怀之时,更指出葛嗣浵的家族艺术文献整理活动“不但为书画之光”,更有着“兼为两浙收藏家增色”的区域文献意义。
葛嗣浵侄子葛昌楹为平湖葛氏艺术文献的第三代精英,他在继承葛金烺、葛嗣浵书画鉴藏事业的同时,受清末金石学风潮的影响,对于篆刻有独嗜,在“搜印十五年,得印二千钮”的机缘下,进而将“传朴堂”打造成近成江南地区首屈一指的印学栋宇。葛昌楹(1893—1963)早年毕业于东吴大学,他在继承葛氏书画鉴藏家学的同时,将大量的财力和精力用在明清名家篆刻的搜藏上,并以为“辑梓印谱”是为保存印章艺术的上上方法,也因此不遗馀力刊成多部在近代印学文献甚至艺术文献史上有着重要影响的印谱。高野侯在《明清名人刻印汇存》曾云:“当湖葛子书徵,好古宿敦,于篆刻有笃嗜然,今之张夷令也。搜罗名人雅制,上自宋元,下逮明清。严派别之分,泯主奴之见。 趋向既正,审定益精。 曾选其优,撰成印谱若干种,传布印林”云云。据《西泠印社志稿》[2]上的不完全统计,葛昌楹与弟葛昌枌辑刊过《传朴堂藏印菁华》《晏庐印集》,与同道中人丁仁、胡洤等人先后合辑《丁丑劫馀印存》《明清名人刻印汇存》等,他因自己喜好邓石如的篆刻而辑有《邓印存真》,凡此种种,皆可说明以葛昌楹为代表的第三代平湖葛氏子弟在印章集藏与印谱辑梓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斐然,当然,平湖葛氏所取得这样守先而又开新的的艺术文献整理的实绩,就是在当时的江南地区也堪称犖犖大者。
二、从爱日吟庐到传朴堂:平湖葛氏艺术文献整理之内容
历经葛金烺、葛嗣浵父子两代人的努力,平湖葛氏基本上完成了家族艺术文献的累积期,从上世纪初始,平湖葛氏进入家族艺术文献整理的快车道,在此时段,平湖葛氏不但整理了“爱日吟庐”系列的家族书画文献,更开拓了“传朴堂”系列印学文献整理的新领域,并由此成就了平湖葛氏名动江南甚至全国的艺文家声。现就平湖葛氏书画与印学两方面文献整理的实绩略述如下:
(一)平湖葛氏“爱日吟庐“系列书画文献述略
平湖葛氏的书画文献整理实绩主要体现在存世的四种葛氏家族“爱日吟庐”系列书画文献著作中,这四种著作分别是:《爱日吟庐书画录》《爱日吟庐书画补录》《爱日吟庐书画续录》《爱日吟庐书画别录》,其中,刊于宣统二年(1910)的《爱日吟庐书画录》为葛金烺所著,刊于民国元年(1912)的《爱日吟庐书画补录》、民国二年(1913)《爱日吟庐书画续录》《爱日吟庐书画别录》均为葛嗣浵所著。
四卷本的《爱日吟庐书画录》原名为《欧舫书画录》,今之名盖为葛嗣浵刊书所改。朱福铣在《爱日吟庐书画录序》云:“同年友葛毓珊先生,……居江村之乡,天才卓绝,骈散诗词骊古作者,以其馀闲为《书画录》四卷,体仿江村而略变厥例,近世名作搜罗尤富,……今夏哲嗣词蔚部郎来都门,持是录见示,云将付剞劂,为序而归之。”[1]缪荃孙《爱日吟庐书画录序》亦云:“葛君毓珊同年,世居当湖,为詹事之后辈,濡染流风,景行响往,聚平生所得编成四卷,其体例一准《销夏录》,而著录益慎,考订益精,后出愈工。”[1]由朱福铣、缪荃孙两序可知,乡先贤高士奇《江村销夏录》对葛金烺编撰《爱日吟庐书画录》影响至深,而以“天才卓绝”的葛金烺为代表的葛氏家族收藏也是继高江村之后平湖书画鉴藏的“著录益慎,考订益精,后出愈工”者。
葛金烺所著的《爱日吟庐书画录》是以书画作品的创作朝代排列卷次的,卷一所收多为宋元书画,其中不乏范宽《晚景图》、王诜 刘松年《山水合册》、赵伯驹《太液龙舟图》、马远《柳堤渔艇图》、赵孟頫《行楷轴》、黄公望《秋山幽寂图》、吴镇《墨竹图》、倪赞《石壁精舍图》这样的大家作品,卷二所收的明代作品及卷三、卷四清代作品中则以吴门、松江及清初六大家的南宗作品为主。其编纂体例亦如朱福铣在《录序》所说的“体仿江村而略变厥例”,这其中所谓的“略变厥例”是指葛金烺于《爱日吟庐书画录》中每有品评这些藏品的跋语附后。当然,从这些跋语中不但可见葛氏精妙独到的品鉴意见,也往往可知他在择选个人藏品时的标准与态度。比如,我们从他跋王原祈《仿米襄阳雨山轴》所云的:“麓台司农山水,余斋收有五帧,而定为真迹无疑者。仅此一帧”的意见[1]可知,他在选择藏品时确实是遵循自序中所云的“俾确实一归于真而后已”的标准。再如他在跋恽寿平《寒林图轴》时所说:“恽迹赝本之多不亚于石谷,然鉴别较易。盖其神韵秀逸,本于天生,非他人摹仿所能到。且每帧题识,洋洋洒洒,从无仅落名款者。而书法之妙,直逼河南,更非作伪者所能率尔操觚也。是以一展卷而真赝立判。余斋收南田至十馀种,以此二帧最精,故著于《录》”。则体现出葛金烺在选择藏品时还有着“真中选精”的更高标准。
葛金烺身后,其子葛嗣浵继续进行家藏书画的整理事业,并先后编修了《爱日吟庐书画补录》《爱日吟庐书画续录》《爱日吟庐书画别录》三种葛氏家藏书画文献。就《爱日吟庐书画补录》而言,此书的落脚处正在一个“补”字。葛嗣浵在《爱日吟庐书画补录序》中对编著原委亦有交代:“辛亥夏日,刻先君所撰《书画录》成,沧桑之变起矣。浵旋病,病稍瘥,约二三同志至舍,借考镜书画为养病计。因尽出箧中物与先君所录之书逐件比对,见有说者固善,其无说者亦多名品在焉,信乎此录,盖先君所未竟也,因复相与考论,各抒已见,条而识之。”[3]如前所说,葛金烺在编著《爱日吟庐书画录》时往往会以跋语的形式来表达他对所选藏品的意见,但是检视其书,我们又会发现,《爱日吟庐书画录》中仍有一半左右的藏品葛金烺没有留下跋语,这也就是葛嗣浵所说的“其无说者亦多名品在焉”的情况。故葛嗣浵在“信乎此《录》,盖先君所未竟也”的认识下,就其父之“无说者”而“复相与考论,各抒已见,条而识之”所成《补录》一书,比较《爱日吟庐书画录》《爱日吟庐书画补录》两书,后书只是对前书藏品中葛金烺未加跋语者进行补加而已,故《爱日吟庐书画补录》只能算是《爱日吟庐书画录》附庸而已,并非独立意义上的书画文献著作。
与此同时,葛嗣浵所编著的《爱日吟庐书画续录》《爱日吟庐书画别录》两书则是对葛金烺的《爱日吟庐书画录》拓展与超越。先看看拓展,首先,葛嗣浵《爱日吟庐书画续录》收录大量原本属于葛金烺而《爱日吟庐书画录》中未收的藏品,关乎此点,葛嗣浵《录跋》中亦有言及:“先君于辛已夏消暑馀闲自为考订,只七月、闺七月两月之间已成如许,嗣以观郎署,不遑从事于此,故大半尚缺著录。”[3]可以说,这一“大半尚缺著录”的情况则是《爱日吟庐书画续录》最直接的编撰动因。再者,《爱日吟庐书画续录》所收录藏品除去葛金烺的藏品①葛嗣浵在《爱日吟庐书画续录·自序》云:“梓既竣,检箧中所藏书画名迹之未经著录者,若宋若元若明及清初最著各家大都为先君子壬午以后所得,视前录所收卷轴相埒,苟不甄综而荟萃之,不特诸名人聚精凝神之作,将日就湮没,而先君子网罗精意与夫平生摩挲爱玩不忍释之心,无由显白。”,亦有部分是葛嗣浵所收的藏品,缪荃孙在《续录》序中所说:“时时续收,所得已复不少”,以及沈曾植在《续录》序中云:“闻《录》成以后,续收弥富,比部继志,亦有纲罗,阙焉不述,岂曰为裘。”[3]都可以为证。值得一提是,《爱日吟庐书画续录》中除去葛金烺、葛嗣浵的收藏,还有不少是葛嗣浵侄子葛昌楣的收藏,如《爱日吟庐书画续录》卷二《明唐寅行楷诗翰轴》后中葛嗣浵跋语云:“是幅为犹子楣所收,余视之,果真也,喜而志之。”卷三《明八大山人草书册》跋亦云:“此册为犹子昌楣所得,余细审不谬,遂录之。”由此可知,葛嗣浵编著《爱日吟庐书画续录》不仅承接其父的收藏,继而收录他自己的藏品,同时本着提携家族晚辈的宗旨收入他的侄子葛昌楣的藏品,经此,葛氏三代的书画藏品济济于《爱日吟庐书画续录》一书中而传之后世的事实,既是平湖葛氏阖族相庆的家门盛事,更是近代江南文化家族绳绳相继的风雅景象。
此外,葛嗣浵在编著《爱日吟庐书画续录》《爱日吟庐书画别录》两书时,无论体例还是内容,都有着与葛金烺《爱日吟庐书画录》不同的别趣之处。具言之,在体例上《续录》增设附录以收入《刘其清楷书寿芝公七秩寿序》《徐用仪、许景澄行楷尺牍》等双款及多款作者的书画作品;《别录》更是以名人诗翰、尺牍、扇面与楹联这四种形式分别门类进行汇编,体例上的细化既体现出条目上清晰度,也增加收入藏品的数量,更体现出葛氏编撰文献后出转精的趋势。在内容上最显明的区别就是葛嗣浵对地方乡贤作品的重视,《续录》专辟一卷来收藏孙玺、冯汝弼、赵维寰、沈萃、李确、高士奇、沈季友、许箕、沈初、朱为弼、杨于高、叶恒、潘晨晖、许汝敬、张金镛、徐方增等乡贤先哲们的翰墨遗迹,《别录》在《明人诗翰汇册》《清人诗翰汇册》后列有《当湖先哲诗翰汇册》,《明名人尺牍汇册》《清名人尺牍汇册》后亦列有《当湖先哲尺牍汇册》,由此可见,葛嗣浵编撰家族书画著录时对乡贤作品的重视,可以说,对于乡贤作品重视既是考文献而爱旧邦的乡土郡邑情结的表露,亦是一种地域文化优越性的强调,更在家与国之间增加了一份文化上联系。
(二)葛氏“传朴堂”系列印学文献述略
葛氏家族艺术文献建设的另一贡献即是印学文献,其主要内容是对明清名家刻印的集藏和印谱的编印。传朴堂所藏的明清印章曾被当时篆刻界誉为“一时之最”,这一集藏的过程主要由葛嗣浵次子葛昌楹来完成。他在集藏印章的同时,还辑梓一批高质量的印谱传世,其中分别有:民国四年(1915)的《晏庐印集》八卷;民国十四年(1925)《传朴堂藏印菁华》十二卷;民国十四年(1925)《宋元明犀象玺印留真》;民国二十年(1931)《吴赵印存》;民国二十五年(1936)《宝穰室燹馀印存》;民国二十六年(1939)《丁丑劫馀印存》二十册;民国三十三年(1944)《明清名人刻印汇存》十卷等七种集古印谱。在这七种印谱中,以《传朴堂藏印菁华》《丁丑劫馀印存》尤为知名,兹分述如下:
《传朴堂藏印菁华》十二卷。民国十四年(1925),葛昌楹与弟葛昌枌于所藏明清名家刻印二千钮中,选其精者四百方辑拓而成。谱中收印人一百二十四人,明清重要印家,大都收入。印谱前有罗振玉序及葛昌楹自序,葛氏自序云:
昌楹少好篆刻,尤嗜名作,尝欲搜集古人所刻,辑为谱录,展转岁月,因循未就。辛壬以来,寒暑数易,家居多暇,辄与季弟昌枌广为收求。上自元明,下迄咸同之际,得若干家,其名之显者既远播于殊族,而晦者或不出于里巷,又或诗文道德,卓荦人寰,不以艺名而其印可传,即用采最。惟貌合神离,稍介疑似,辄屏不录。昔先王父之辑《爱日吟庐书画录》曰‘宁慎不滥’,家大人守此语以辑《续录》。今不佞幼承庭训,敢不亦恪守此语?于是检所藏弁,严加淘汰,又蒙当代名士吴苦铁、罗叔蕴、郑大鹤诸丈为之品定,凡存若干钮,列其次第,厘为卷秩。昔高西园得司马相如玉印,佩之恒不去身,非至亲昵者不获一见,是何异茧纸纳楹,卒为缸面之悔;况此累累者皆古人精神所寄,吾兄弟何忍秘之箧衍,为匿书生耶!谱而录之,不独用谂同好,亦以慰山臞泽叟刖璞自明之心。区区寸抱,幸大雅谅为。[4]
由葛昌楹自序可知,《传朴堂藏印菁华》一书刊成源于两方面的原因。一者是葛昌楹自幼爱好篆刻,并有收集古人印作的嗜好;再者,始自葛金烺的整理艺术文献的家族传统对葛昌楹的影响。相较而言,后者对葛昌楹整理印学文献的引导作用更大,特别是葛金烺“宁慎不滥”的艺术鉴藏品选辑标准更是葛昌楹在“审慎鉴别”所收诸印时所恪守的不二准则。正是有了这种源自家学的文献整理理念的支持,《传朴堂藏印菁华》才成为“撰择精严、无一赝作厕身其间”[4]的葛氏艺术文献珍品与“得者珍之”的近代印学名品。
葛氏印学文献中最重要的莫过于《丁丑劫馀印存》,此印谱是葛昌楹与藏印家丁辅之、高络园、俞序文合作辑拓而成。丁丑为民国二十六年(1937),是年日寇侵华,平湖沦陷,葛昌楹避难沪上。传朴堂之藏书楼“守先阁”被焚,所藏明清名家刻印,因先期埋入地下,得以幸存大半。时浙西藏印家丁辅之、高络园、俞序文亦避难在沪,所以各出劫馀所存,于民国二十八年(1939)拓成此谱。此谱每部四函,共二十册,计二百七十三家印作,集一千余方。成书二十一部,以“浙西丁高葛俞四家藏印集拓廿又一部已辰春成书”二;十一字为编号。杭人高野侯在惊心于“天不厌乱,劫运方兴”的“斯文之痛”的同时,又赞叹于四家合刊印谱之不易与伟卓,慨然撰《丁丑劫馀印存》序,其序文笔含情愫,句句肺腑,对后人理解兹事极具参考价值,故此处全录如下:
中元丁丑秋,吴淞兵起,冬,金山卫不守,平湖当其冲,吾杭遂相继沦陷,仓皇避地,御寒物外一切不暇顾及矣。兵燹之馀,文物荡然,即藏印一事,亦多散佚。吾浙藏印家,夙推泉唐丁氏八千卷楼(洪杨劫后,丁氏收集旧籍兼及八家刻石,太半为王安伯、谢卜堂旧藏,别辟“百石斋”以储之。至吾友鹤庐已三世矣,鹤庐继志搜集龙泓刻得七十二石,遂自署所居曰七十二丁厂,其七家亦增益至五百馀石。今年周甲又得丁黄二印拓入此集,虽非劫馀,以为劫后记验可也。)平湖葛氏传朴堂,亦号美备,均曾抑拓成谱(丁氏初成《丁蒋奚黄四家印谱》,既增秋堂曼生为六家,又增次闲、叔盖,是为西泠八家。……举凡清仪阁所用所藏诸印,附以文房器物,精拓成四卷,未及装订而难作,亦燬于劫。)馀杭俞氏香叶簃,收集日富(大兴傅氏华延年室节子先生酷嗜旧印,收集极富,有印谱,后人中落,悉以易米。序文为傅氏所自出,潜为收集,承护外氏手泽以偿夙好,于傅氏外,益以仁和王氏、山阴吴氏之藏,拟为印谱,而乱作矣。)吾弟络园二十三举斋亦藏有数百石(吾家与次闲交最深,刻印达二千数百石,红羊后所存不及四之一,人事迁变,各房所藏多佚出,络园见必拾收,辑为《次闲高氏印存》。又喜收集名人轩斋印,吾竹房印举第二十三,即举兹事,因颜其藏印之所曰二十三举斋,并辑《二十三举斋印攗》)惟丁氏于陷杭前,冒险携取,俞氏挈以避地艰难,转徙护如头目,遗失最少;吾弟与葛氏旧居均燬于劫火,藏印虽付密窖,逾岁发视所存仅十之六七矣。兹先后来沪渎,互以劫馀相慰藉,都计四家,所藏尚得千数百钮,丁兹乱世,幸得会合,惧其聚而复散也,因亟谋彙辑为谱,名曰《丁丑劫馀印存》。夫刻印则为文人馀艺耳,搜集旧印则又为鉴藏家之馀事耳,而乃为自来学者所珍视,非无故也。规模秦汉,上通古籀,其文字有可以订补许氏六书者,则为研讨小学之馀助;徵文考献,有可以证补记载之阙失者,则又为□辑史事之馀资;至秦朱汉白徽派浙宗,家数渊源,寻究刀法,则徒为艺事之馀技,而其人性情之醇驳,学问之浅深,犹可于此窥测焉。是故谱录旧印,以及一家之专谱,夙为藏书家所徵采,志艺文者所箸录,岂偶然也耶!是谱之辑综明清两代之印人所治之印,都二百七十又三家,得印一千九百馀石,虽曰劫馀,已成巨帙。鹤庐诸子,鉴别精审,余弟理董之劳,经始于戊寅五月,讫己卯六月告成,为时阅十又四月矣。噫!是累累者不知几经劫厄之馀,犹得从容审定,辑抑成谱,俾印人精神所寄之品,历劫不磨而永其传,印人之幸欤!而四家弥年累月精力所聚,纵遭兹浩劫,犹得萃所。劫馀摩挲赏析撰谱,以视方来,王丈福厂为篆同审定一印,俾钤简端以为记验,四家笃耆之志,亦可以告慰矣!噫!天不厌乱,劫运方兴,今之劫馀,将何以保守永久,未可以逆料也。而兹谱之成,尤不容缓也已!余遂为略述原委焉,古杭高野侯叙于海上梅花双卷楼。[5]
如高氏跋中所说,四家汇集刊行《丁丑劫馀印谱》有着多层意义:
首先,四家藏印皆有家学渊源。如丁氏藏印原得自王安伯、谢卜堂为多,传三世至丁辅之后,辅之继志搜集,又得丁敬刻石七十二方,其馀七家亦增益至五百馀石。馀杭俞氏香叶簃最初收藏是来自外家大兴傅氏华延年室,傅氏后中落,藏印悉出,俞序文为承护外氏手泽而暗自收集,后又益以仁和王氏、山阴吴氏之藏,遂成香叶簃印章收藏之规模。杭州高氏与赵次闲友善,存赵氏刻章达二千数百石,人事迁变,各房所藏多佚出,高野侯弟高络园见必拾收,辑为《次闲高氏印存》。
其次,此谱是集大成的印学巨帙。此谱汇辑了明代文徵明、文彭父子至民国初期叶玉森、高迥的二百七十三家印人的印作一千九百余万,收录印人、印作的范围甚广,明代吴门派、新安派、泗水派,以及朱简、汪关等家,清代徽派、浙派、皖派、闽派、如皋派;近代赵之谦、吴让之、胡、吴昌硕、黄士陵等大家,都有较系统的收录。而此谱以时代先后编次,上下四百年,“秦朱汉白,徽派浙宗,家数渊源”了然明晰。
最后,此谱在揄扬“敬宗”情怀的同时,也展示近代江南文化家族辉煌的艺术文献建设成就。当然,兵燹中保守祖业尤显“敬宗”之不易,如“丁氏于陷杭前,冒险携取,俞氏挈以避地艰难,转徙护如头目,遗失最少”;“吾弟与葛氏旧居均燬于劫火,藏印虽付密窖,逾岁发视所存仅十之六七矣。”等。而“而兹谱之成,尤不容缓也”的原由,实因“劫运方兴,今之劫馀,将何以保守永久,未可以逆料也”。由此可见,以平湖葛氏、杭州丁氏、高氏、俞氏为核心的江南文化家族在“几经劫厄之馀”而毅然成此巨帙,不仅他们的敬宗之心与其家族文献一样历劫不朽,昭然于天地间,而且弥年所聚的收藏亦历劫不磨而永其传也。
审视葛氏艺术文献建设历程,我们不难发现,平湖葛氏的艺术文献建设在晚清民国有一个方向上的转移,具言之,就是由历代书画的集藏与书画著录的整理转为了历代印章集藏与印谱辑梓,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变化,主要葛氏的品鉴趣味是受时代审美的影响,清中期以降,乾嘉考据学派的兴起,相应地激发了金石学研究的兴趣,作为金石学在艺术领域的延伸,研习篆刻及印学研究时风日盛,在这样的背景下,葛昌楹与时俱进,将家族艺术品鉴与相关文献集藏的精力转移到了印学上,并由此形成葛氏艺术文献建设上的方向性变化。这一变化在同期的其它文化家族的成员身亦有体现,如苏州贵潘的潘祖荫、顾氏的顾承,秀水钱氏的钱善扬等等,而最具代表性与戏剧性当数吴大澂,吴氏前半身的艺术趣味以书画为主,后半身的艺术趣味则几被金石所占据。
三、叠隐复现:平湖葛氏家族艺术文献建设的特质与意蕴
回望平湖葛氏以书画、印学为主鉴藏事业以及其复合多彩的家族文献建设轨迹,我们不仅能厘定葛氏作为一个艺文共同体整体呈现出来的艺术文献整理的成果,而且可看到它在不同时期文献建设的不同面貌。事实上,葛氏艺术文献建设的“宝藏之、增益之、传述之”的过程也正是其家族整体艺术鉴藏实绩不断丰富和建构过程。审之这一过程,不难获悉,以平湖葛氏家族为代表的江南文化家族艺术文献建设中所显示的连续性与阶段性并存的特质与其中所展现的家族、地域与文献的多重意蕴。
(一)延续与阶段:平湖葛氏艺术文献建设中的特质协奏
1.延续性
对于葛氏而言,这一特征有两方面的具体体现。首先,葛嗣浵在宝藏与传述葛金烺所遗存书画藏品的同时,又增益着葛氏的艺术收藏与艺术文献,葛昌楹亦是延续着先辈们从收藏到整理的艺术文献建设之路。可以说,葛氏家族丰硕的艺术文献成就正是从葛金烺、葛嗣浵、葛昌楹祖孙三代人前后相续、不倦于斯的努力下才完毕的。其次,这一连续性亦体现在葛氏对待文献整理的态度上,葛金烺在编撰《爱日吟庐书画录》时提出了 “宁慎毋滥” 藏品择选原则,他在具体编选时亦是以“一一甄录之,间有可疑必加裁汰”的举措来践行这一原则,葛金烺对藏品著录审慎求精的态度直接影响着葛氏后人,葛昌楹《传朴堂藏印精华》能得到罗振玉“无一赝作厕乎其间”的激赏,其实是他遵循葛金烺‘宁慎不滥’的宗旨而践行之。葛昌楹在编选《传朴堂藏印精华》时说:“昔先王父之辑《爱日吟庐书画录》曰:‘宁慎不滥’,家大人守此语以辑《续录》。今不佞幼承庭训,敢不亦恪守此语?于是检所藏弁,严加淘汰”,[5]显然,葛嗣浵、葛昌楹在整理文献时鉴别审慎、撰择精严的举措渊源于葛金烺的文献整理态度。
2.阶段性
就葛氏而言,葛金烺时期是葛氏书画收藏从无到有的积累阶段,这一阶段更关注藏品的收藏过程,对藏品的整理、研究与相关文献编撰亦处于起步阶级,从文献建设的角度看,这一阶级还只为后人全面整理家族文献做准备。相较而言,葛嗣浵时期则是葛氏艺术文献整理的高峰期,这一阶级不仅表现出书画著录类著作的高产,也表现在著录体例上更合理,内容上更全面,品鉴上更精当。以著录形式而言,专录名人诗翰、尺牍、扇面与楹联的《爱日吟庐书画别录》是对葛氏书画收藏体系的完善。以内容而言,葛嗣浵时期在关注历代名人书画的同时,他所编的《续录》卷八专收乡先哲遗墨,《别录》卷有平湖先哲诗翰与汇册的部分,国、郡、家三位一体的人文生态在葛嗣浵时期的书画文献著录中得到立体而全面的展示。而葛昌楹时期最大的不同的就是家族文献建设出现了方向性的变化,即由葛金烺、葛嗣浵时期以书画文献建设为主的转向葛昌楹时期以印学文献建设为主。之所以出现这一转变是由葛昌楹个人鉴赏趣味所定的,但归根结底是清末民初江南艺术风尚通过师友、姻娅等多重通道影响他的结果。可以这样说,葛昌楹的这一变化是江南文化家族共性的体现,颇具代表性。
连续性在葛氏艺术文献建设主要呈现为继承的一面,其具体反映为文献建设路线上从宝藏、增益到传述的相似性及鉴藏理念与文献整理态度的恒定基调。阶段性则表现出葛氏艺术文献建设发展的一面,往往表现是受个人际遇、师友交游与时代潮流影响而出现的文献建设从形式到内容的适应性地变化。从葛氏文献整理的实绩来看,连续性与阶段性是不可截然分开的,葛氏家族文献建设的连续性是基础,保持连续,文献建设始能固能厚;文献建设的阶段性是发展,由发展而文献建设始能合理、全面、精当。这两者在文献建设的过程往往会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共同表现为葛氏文献建设既有显明家族传统而又能与时俱进的复合文化特性。
(二)叠隐复现:平湖葛氏艺术文献建设中的意蕴投影
葛氏家族艺术文献编成后,所产生的展示家族文化、宣扬先世荣光的家族意蕴是显见的。事实上,艺术文献作为保存家族集群的历史文化记忆的重要载体,其客观存在的多重意蕴并不是编撰者所能够预期的,随着时间的流逝,葛氏艺术文献建设中所具所隐叠着的家族、地域与文献的多重意蕴也越来越得到显现。
首先,葛氏子孙们对艺术鉴藏深刻崇尚与痴迷之中既蕴含着保存群体文化记忆的追求,更有敬宗耀祖、不坠家声的道德目标。对于一个以艺术鉴藏为尚的艺文家族,要实现这样的目标,最好的方法莫过于以整理家族艺术藏品及梓行相关文献来为家族立言,葛嗣浵在《续录自序》中就说:“苟不甄综而荟萃之,先君子纲罗精意与夫平生摩挲爱玩不忍释之心无由显白”,[3]所以说,平湖葛氏绵延百年的艺术文献建设活动的指归就是以此在为家族及先人立言,换言之,这也是葛氏文献建设活动的家族意蕴之所在。
其次,葛氏艺术文献建设的意蕴已越出其家族阃隩,不仅为平湖及嘉兴地区的艺术文献建设有相当垂范作用,更为“两浙收藏家增色”。就区域文献建设而言,葛氏的艺术文献整理既是平湖地区文采风流的汇集,也是嘉兴艺术文献整理活动的动员,更是江南精英文化的一次生动展示。《续录》卷八中专收乡贤遗墨,别录中专列《当湖先哲诗翰汇册》《当湖先哲尺牍汇册》等项,这些都说明葛氏对乡邦文献的重视,而葛氏藏品的收集与文献的整理更是平湖与江南地区的收藏家与鉴赏家“共襄厥成”的,如《续录》所收的平湖乡贤孙玺《雪山履历图》与朱为弼《墨梅图》就分别是章钰与朱为弼侄孙朱象甫所赠,《续录》中藏品择选有陆恢的审鉴之功,梓行上版又有金兆蕃佐校之力,而葛昌楹所刊《丁丑劫馀印谱》为葛氏与杭州丁氏、高氏、俞氏四家精华所聚,《明清名人刻印汇存》也是合葛、胡两家合作而成。从某种意义上说,象《续录》《丁丑劫馀印谱》这样的艺术文献整理的意义已超越了家族本位而走向了更宽阔的江南文化大世界,其社会意义当为群集性的文化家族通过合作的方式向江南乃至全国展示他们辉煌的艺术文献建设成就。所以说,葛氏的艺术文献既属葛氏与平湖,又具备一定家族与区域超越性,甚至具有全国性意义。
最后,这些依据葛氏遴选的艺术精品著录而成的文本,实是“国粹之所赖以保存”的文献富藏,其资补足征的文献学意义有待阐明。如著录中所收的众多乡邦文献对地方志的编撰不无裨益,所收项元汴、张丑、高士奇等人的书画作品对于全面了解这些“述而不作”的收藏家提供了珍贵资料,所收的《曹三才集同人书画册》中有吴梅村子吴暻的《东山杂咏》绝句十首及和陶诗六首,由于吴暻《西庄集》已佚,其辑佚的文献意义更值得珍视,类似的文献还有归庄、袁枚等人的题跋均为现行的《归庄集》与《小仓山房诗文集》所未收。而葛氏整理的《传朴堂藏印精华》《丁丑劫馀印存》《明清名人刻印汇存》这一批影响甚远的印谱本身就是中国印学史上最重要的文献之一,凡此种种,无不说明葛氏艺术文献所附重的文献学意义。
综上言之,以葛氏为代表近代江南文化家族在其艺术文献建设活动中家族、地域与文献这三重意蕴是隐叠在一起的,家族文献整理的本质动力是来自于保持族群文化记忆与投射家族荣光的立言要求,家族后人在这动力的推动下,将立言的举措以复制的方式不断延续。对于葛氏这样以艺术鉴赏见长的文化家族来说,编撰艺术文献就是他们最好立言方式。一方面,葛氏艺术文献因累世收藏而变得内容渐深,质量渐精;另一方面,历时性的谱系编撰亦会使所涉的范围放大,即由家族而及郡邑,由郡邑而及国家,前者的层累说明了葛氏文献栋宇的数与质,后者的推延可证葛氏家族文献观照视域的广大及超越性,这两者相重叠则演绎出葛氏营之已久的艺术文献所具有的“永不朽兮”的文献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