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使初访中国记》虎图探微
2019-01-08任平山
任平山
一、《荷使初访中国记》
诞生于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与荷兰独立相辅相成的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成立与壮大。作为第一个股份有限公司,荷兰东印度公司被赋予多种国家权力,灵活地展开了金融、战争、外交和殖民。藉此,荷兰人突破了原来由葡萄牙和西班牙垄断的海洋贸易。远东市场获利极丰,明朝海禁却令欧洲市场欲壑难填。等到满清军队占领广州,公司看到了新的商机。
1655~1657年,荷兰东印度公司使团从巴达维亚出发来到广州,沿江西赣江北上,转入长江南京,复由扬州入运河,驶入北京。尽管得到清廷召见,使团开通广州贸易的愿望却没能实现。受公司委派,使团成员纽霍夫沿途记录并绘制中国风物。1665年阿姆斯特丹出版了他的见闻《荷使初访中国记》。这本图书在纽霍夫草图基础上印刷了大约150幅铜版画,描绘中国风情。
《荷使初访中国记》的史料价值,学界已有公论。笔者以为,该书也在文化交流的方式上意义非凡。此前一个世纪,西方大众了解中国,要么通过旅华传教士的文字描述,要么通过中国产品上的神秘图像,例如青花瓷。不同于这两种经验的互不干涉,纽霍夫系列中国版画从属于一个欧洲人能够理解的游记式文本。由此,欧洲人对中国的文字阅读和图像视觉知识得以系统地融合。
《荷使初访中国记》初版有荷兰语和法语两个版本,几年内又翻译成德语、拉丁语和英文。在这套铜版插图笼罩之下,《荷使初访中国记》影响了欧洲人对中国的想象,直至18世纪末叶。
二、新旧版本
《荷使初访中国记》由两大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为使团访问中国之旅程日志。第二部分是中国概说,涉及中国人的服饰、语言、动植物、历史等。本文主题“中国老虎”,是第二部分关于中国动植物的一张插图。不同版本的《荷使初访中国记》偶有版画删减或增加,但插图具体内容基本不变。“中国老虎”是一例外。1668年拉丁文版用一张新图替换掉了1665年初版时的旧图。这个改动,让我们有机会深入观察17世纪荷兰画家和出版商在建构中国图景时所处的环境与选择。
1665年荷兰文和法文版的《荷使初访中国记》中,老虎前方动物较多,背景是只麝香鹿,中景有人猿和鹦鹉,前景是一只野雉(图1)①。版画家在绘制野雉时,使用了可以称之为“破界法”的图像方式。雉爪轻轻抓破图像边界,这样一来,图像向画面外部,即与焦点透视相反的方向寻求空间。这只野雉的图像功能近似于15世纪中叶安托尼罗·达·墨西那(Antonello da Messina)《圣哲罗姆在书斋中》插图中的前景。老虎上方写有两种字体的西文——TIGER和Tygres,对不同语言的欧洲人做出解释。中国麝香鹿的上方只写有一行西文。

图2:1668年《荷使初访中国记》中的老虎插图
1668年拉丁文版《荷使初访中国记》中,老虎依旧占据图像左半侧,周边环境有所调整(图2)②。原图前景动物一概不要,原来安置在老虎对面的鹦鹉连同大树设置到了老虎身后。这棵树在1665年的版画中绘制在图像边缘,有平衡画面的功能。1668年保留下来也是出于同样原因,因为老虎的位置向画面中心偏移了一些,同时拔高了作为背景的麝香鹿及山林,这样在画面另外一侧,亦即老虎身后需要予以平衡。
两幅插图,效果迥异。在1665年的作品中,铜版画家尽可能多地在方寸之间展示东方的奇异物种。而在1668年的相关插画中,出版商更加看重老虎及其周边环境的合理性。如《荷使初访中国记》文本描述的,老虎前行的路径上,不应该近距离存在其他动物。
两幅图像最大的变化还在于老虎本身。1668年版老虎保持了旧版前行回首之姿,但观众由1665年版侧后方视角,转移到了老虎的侧前方。旧版老虎后肢别扭地并置,在新图中得到纠正。尽管新版老虎斑纹显得过短,和1665年版相比,早期版本更不合理——老虎身体上的浅色条纹看上去像是淤青或褶皱,而不是本应醒目的黑色斑毛。
三、《中国图说》
前述几个版本的《荷使初访中国记》都属于同一个阿姆斯特丹出版商。问题首先在于,如果对老虎形象做出改动的原因在于修改旧图中的错误,为何新改过的老虎形象依旧不够准确?
笔者认为,1668年版《荷使初访中国记》中的老虎形象受到1667年出版的《中国图说》影响。《中国图说》第七章“奇异的中国动物”、第八章“中国特有的飞禽”、第九章“中国的河鱼和海鱼”、第十章“中国的蛇”等章节配有“麝香鹿”“河马”“松鼠”“凤凰”“有毛的鸡”“绿毛龟”共六幅插图。虽然书中这个部分仅寥寥数语谈及老虎,但在第四章“中国山脉和自然奇观”所配插图中,出现了老虎形象。“江西省有一座有两个山峰的山,较大的那个山峰像一条龙,它在向较小的那个被称作虎的山峰猛扑过去,因此被称作龙虎山……见下图”。铜板画家似乎不知道如何处理这种匪夷所思的风景,干脆在山峰上画出龙虎搏斗的景象。龙是典型的西方中世纪图式,虎的形象和1668年版《荷使初访中国记》中的老虎形象相似,它们身体上的黑色皮毛纹路比豹子长,对于老虎则显得过短。
如果说“龙虎山图”中的老虎仅是一种对于自然的“不自然”的比喻,那么在《中国图说》第五章配有的老虎插图更能表明这时欧洲人对于老虎的误解和想象。在这个标题为“关于莫卧尔王国和那里的奇闻逸事,以及从那里去中国、印度与欧洲的不同旅程”的章节中,作者写到:“我要说的是在老虎胡须里发现的一种剧毒。老虎有驴那样大小的身材和猫那样的外貌,它动作迅速,有很多尖牙利爪,是所有动物中最残酷最野蛮的动物。从它的四肢来看很像猫,如下页图所示。在它嘴唇的周围长有长须,经验显示:这些胡须的毒性如此之大,如果人或其他动物接触它们,能被毒死,而且没有任何解毒药。孟加拉人在老虎聚居的地区观察到:当老虎到恒河或任何其他河流时,它们只喝从它们前面流过的水,而不是流过它们的水,可见虎也怕自己中毒而死。同一道理,它们从不站在沟内或池塘内饮水。由于这一原因,皇帝下令:人们必须把这些老虎送交莫卧尔法庭,私自持有胡须就判死罪。御用虎须制作出有毒的药丸,用于杀害国王要秘密处死的人”③。

图3:1667年《中国图说》中的老虎的真实形象

图4:1657年《自然史》中的“虎”
为上述文字配置的铜板画在中心位置是一只老虎正在漫步的完整侧面(图3)④。画面远景则绘有老虎上树,及被人捕杀等场面。这张插图名为“老虎的真实形状”,比“龙虎山图”中的老虎更清晰地展示了1668年《荷使初访中国记》中那种短短的老虎斑纹。
1667年《中国图说》和1668年《荷使初访中国记》,以及后者最初的两个版本都在阿姆斯特丹出版。《荷使初访中国记》出版商雅克布·范·梅尔斯(Jacob van Meurs)本人也是一位铜板画家。比较上述著作的动物图像,可以发现1665年《荷使初访中国记》中,作为老虎背景的麝香鹿,在1668年变成了低头吃草的姿态。这一变化亦来自1667年 《中国图说》中的“麝香鹿”插图。
除了老虎斑纹的共同特征,1668年“中国老虎”和1667年“老虎的真实形状”还阴差阳错地分享了同一尾部特征。《中国图说》版画中,老虎尾巴夹在后腿中间,末梢带有蓬松的长毛。这本来是狮子的特征。1668年《荷使初访中国记》中,老虎的尾巴高高扬起,末梢亦如此。不难推测,1668年“中国老虎”的绘制者参考了1667年 《中国图说》中的相关图像,但两张插画都没有参照真正的老虎。
四、知识谱系
不同于纽霍夫,《中国图说》的作者基歇尔(1602~1680)从未到过中国。身为耶稣会士和哲学教授,他对中国有着强烈的兴趣。基歇尔学识渊博、视野广阔,著作涉及数学、物理、天文、艺术、哲学、历史、地理等领域。博览群书是其主要的知识来源。与此同时,他和一些旅华传教士保持联系,收集他们的中国见闻。
比上述二书略早,老虎形象已见于欧洲动物志著作。1658年伦敦出版的爱德华·托普塞尔(Edward Topsel)所著的《四足动物和蛇史》,插图中的老虎和《中国图说》中的体态一致,同样的侧面视角,同样的步行姿态,同样的短斑,同样的夹在后腿中间的尾巴——末梢带有狮尾式的绒毛。书籍作者试图用猫、豹子和狮子的类似特征来向欧洲人解释老虎的相貌:“老虎身上布满斑点,这些斑点不像美洲豹的斑点那样圆,也没有多种颜色,而是只有一种颜色,四方形,有时是长的。也有观点认为它们的斑点有黄、黑二色,长条形”⑤。
《四足动物和蛇类史》(初版见于1607年爱德华·托普塞尔《四足动物史》)中的老虎形象,亦可见于约翰·琼士敦(Joannes Jonstonus)《自然史》卷1(四足动物卷)(图4),更早则可以上溯至1551~1587年期间苏黎世学者康拉德·格斯纳(Conrad Gesner)出版的拉丁文著作《动物史》(图5)⑥。相关动物志书籍中的老虎插图姿态大体一致,但格斯纳《动物史》和托普塞尔《四足动物史》中的老虎黑斑在腹部交错,形成方格。而琼士敦《自然史》中的老虎没有保留这一特征,版画家试图呈现毛斑复杂的纹路,结果黑色虎斑被不恰当地表现为波浪形。

图5:1551年康拉德·格斯纳所著《动物史》中的“虎”
《中国图说》中的老虎形象与上述图像大体一致,虎斑特征与约翰·琼士敦《自然史》中的插图最为接近⑦。基歇尔以拉丁文写作,他或他的阿姆斯特丹出版商,很可能参考了1657年同在阿姆斯特丹出版的拉丁文版《自然史》。
五、《世界四大洲》
17世纪初,安特卫普画家鲁本斯绘制过一些老虎图像。1665年纽霍夫《荷使初访中国记》初版插图中老虎翘臀伏身的姿态其实是对鲁本斯1612~1614所绘《世界四大洲》中老虎形象的拙劣模仿。
《世界四大洲》中老虎身下有几只幼崽。它后爪踮地,前肢匍匐,伏身欲扑,警戒着旁边的鳄鱼(图6)。1665年《荷使初访中国记》的制图工人可能没有参考鲁本斯原作,只是间接地目睹了类似画稿。两幅图像区别明显。《荷使初访中国记》中的老虎没有 《世界四大洲》中的语境,它后掌平落于地,前肢貌似悬空,姿态比较僵硬。一些细节表明两个图式密切相关。1665年版插图忠实地抄袭了《世界四大洲》中伏虎双耳和扭转头部的结构。老虎面部参考《世界四大洲》的痕迹也颇明显,但略有不同。鲁本斯笔下的虎头感觉真实,1665年版老虎的面孔则显得较长。狮子头颅较老虎略显狭长,加上雄狮颈部威武的鬃毛使其头部看上去比实际比例大很多。西方图像再现雄狮时,常常以其头部下垂之状,展现狮头硕大威武。为了突出这一点,画家和雕塑家会强调狮子正面眉头和额头皱起的肌肉,这一特征在1665年《荷使初访中国记》中被挪用到了老虎的脸上。这样,尽管间接参考了鲁本斯的图样,插图中的老虎看起来更像一只褪去了鬃毛的雄狮。

图6:鲁本斯所绘的《世界四大洲》
与纽霍夫或基歇尔著作中的老虎相比,鲁本斯笔下的老虎图看起来要逼真得多,除了头部特征,最重要的还在于对老虎皮毛的表现。1600年他到罗马参观学习,或许对阿尼巴·卡拉契(Annibale Carriacci)在法尔内塞宫券顶绘制的“大猫”留有印象。但《世界四大洲》中老虎腹部的黑毛斑纹交织成方形,还是反映了16世纪康拉德·格斯纳《动物史》中的特点。《世界四大洲》中的老虎尾梢为几缕长毛,不似狮尾蓬松,且被后肢遮挡。这进一步导致了1665年《荷使初访中国记》出版方的误会。插画中的老虎尾巴末端尖细,倒像是鼠尾了。
综上所述,《荷使初访中国记》中两版老虎图像源流如下:16世纪以康拉德·格斯纳所著《动物史》为代表,一种组合了狮子、豹和猫类特征的老虎形象在欧洲建立。这种对老虎的想象,以动物学知识的形态出现,一定程度上影响到17世纪初鲁本斯的油画创作。
1665年初版的《荷使初访中国记》间接挪用了鲁本斯油画《世界四大洲》中的老虎,但插图严重失真。
鲁本斯对老虎形象的创造多于继承。而17世纪动物志出版物更为保守地传抄了16世纪的动物学图谱。在略早出版的约翰·琼士敦所著《自然史》的影响下,1667年基歇尔所著《中国图说》顽固地保留着康拉德·格斯纳《动物史》的图式,但老虎斑纹变得更加短绌。
不同的图像传承路径,导致阿姆斯特丹出现了两类图像产品——1665年的《荷使初访中国记》和1667年的《中国图说》中老虎形象差异巨大。梅尔斯1668年再版《荷使初访中国记》时,将它们作了综合。1667年版老虎的“明显错误”淘汰掉1665年版老虎的“隐晦缺陷”,欧洲老虎的狮子尾巴被遗传了下来。
六、预成图式
纽霍夫《荷使初访中国记》的中国动物具有美术史学的话题性。“犀牛”“大象”“老虎”“鲸鱼”“鳄鱼”五幅插图中,“犀牛”(图7)、“鲸鱼”(图8)两图与贡布里希名著《艺术与错觉》中的研究案例高度吻合⑧。

图7:《荷使初访中国记》中的“犀牛”

图8:《荷使初访中国记》中的“鲸鱼”
1515年,丢勒绘制了一张犀牛的木刻版画。贡布里希认为,丢勒结合自己对披甲龙的想象,创造了并不真实的犀牛形象。他半发明的犀牛样式在欧洲固定了很长时间,甚至在自然博物志书籍中被一再复制。1601年一幅罗马版画描绘了该年被冲到安科纳海岸的一条鲸鱼。尽管声称根据实物描绘,但1598年一幅描绘荷兰海边鲸鱼的同样图像说明1601年的鲸鱼图像临摹自更早的图像而非实物。⑨
正如孙晶注意到的,《荷使初访中国记》中的“鲸鱼”亦与1598年的荷兰同题版画高度相似⑩。贡布里希认为即便1598年荷兰版画中的鲸鱼,也可能来自对其他图像的误读,而非描绘了一条真实的搁浅的鲸鱼。“因为这条鲸鱼显得有些可疑,仿佛长着耳朵;我有比较充分的根据肯定,有耳朵的鲸鱼是不存在的。那个绘图员很可能把鲸的一只鳍状肢误认为耳朵,因而把它画得太靠近眼镜了。他被熟悉的图式,即典型的人头图式,引入了歧途。画不熟悉的景象所遇到的困难比通常认识到的还要多。而我猜想这一点,也是那位意大利人宁可从另一幅版画上摹写那条鲸鱼的原因”[11]。
如果贡布里希关于画家将鲸鳍误解为耳朵的判断正确,那么《荷使初访中国记》中鲸鱼鳍肢的位置显然比1598年荷兰版画更加准确。与鲸鱼图相比,《荷使初访中国记》中的犀牛今天看来古怪而有趣。背部放射出起伏有致的条纹,脊柱前部长出尖锐的骨刺,这个“披盔戴甲”的动物完全是丢勒1515年图式的翻版。
贡布里希使用犀牛和鲸鱼被不断复制的案例论证他的“预成图式”理论。后人程式化地传抄这些图像,并不诚实地配上说明,这是事实。但在文艺复兴前后,多数图像通过室内拼构,而非户外写生完成。在这种情况下,丢勒赋予犀牛的奇特想象,以及不知名画家面对搁浅鲸鱼,第一次留下逼真的现场感,恰恰是两件作品最有价值的部分。画家绘制鲸鱼躯体和所处环境的构造方法,甚至勾勒线条的方式,都摆脱不了前期绘画训练或视觉准备的影响。从这个角度来说,贡布里希是对的。但他颇具创见地把图像传播和图像辨识相关联时,狡黠地回避了读者可能追问的问题——搁浅鲸鱼侧面翻转的视角是否也必然来自某种预先存在的知识,就像后来这个图式被不断传抄的历史那样。
“预成图式”的合理性毋庸置疑。在我看来,这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逻辑的一个方面。就这个方面而言,老虎在17世纪欧洲的图像谱系,比之同时代的犀牛和鲸鱼,更能够说明贡布里希想要论证的观点:“熟悉之物永远是描写不熟悉之物的合适的起点”[12]。
七、东方学
贡布里希也使用了“符号”一词。他的“符号”研究主要应用于形象辨识——图像的创作、识别,以及心理投射与视觉效果的关系。预成图式理论反过来也确认了作为其基石的心理学命题:观看图像时,知觉先于视觉的决定性影响。但是,知觉影响判断,不仅表现在视觉维度,更作用于广阔的文化认知。正如图像经验对于图像辨识和创造所起的作用,本土文化经验同样是理解异域文化的起点。
除了少量纽霍夫见闻,《荷使初访中国记》第二部分主要汇总了其他途径传入欧洲的中国情报。其中中国动物一节,如前所述,配置“犀牛”“大象”“老虎”“鲸鱼”“鳄鱼”共五幅插图。此外,在第一部分,还有“鸬鹚”和“飞鱼”两幅动物插图。相关动物版画中只鸬鹚一幅取材纽霍夫旅途手稿。

图9:磁州窑虎纹瓷枕(甘肃省博藏)

图10:鲁本斯所绘《虎之猎》,1615~1616年
中国读者看到西方人挑选出这些动物会感觉新鲜。它们要么属于传统视觉文化的盲区,例如鸬鹚和作为背景的麝香鹿;要么是远方朝贡的珍奇,例如犀牛和大象。它们在近古图像再现中多不具备本土动物的符号性,唯老虎属于双方选定范围的交集。老虎在古代中国广泛分布,且在历史文化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在代表方向的四种神兽中,老虎象征西方。它还是十二生肖之一。中国文辞和图像中的老虎,固然可以凶恶,也常常和神勇、威风、健康相关联。宋代磁州窑在枕头上绘出一只卧虎(图9),为睡眠营造出慵懒闲适的意趣。鲁本斯1620年与勃鲁盖尔合绘的《伊甸园中的亚当、夏娃》,伊甸园中卧虎和豹子打闹游戏,可堪与之比较。
卜弥格两次提到中国的“老虎图像”:“三品和四品武官的官服绣的是小老虎”,“画在器皿上的老虎和其他野兽的图像和绵羊不同,它们象征速度和勇敢”[13]。但欧洲的老虎叙事呈现了自己理解世界的方式。
《荷使初访中国记》谈到:“Linyao城附近的一些山上有野牛和老虎之类的动物,当地居民用它们的皮做衣服……浙江省有大量老虎,他们天性暴虐,但Kutien山上的老虎从不伤人……云南省Nula山满是野生的老虎和豹子。Xepao山亦如此。它们在广西省像狮子一样残暴,喜欢追捕男女和儿童。但大自然有一些方法可以躲避这种残忍的动物。总是有一个小动物伴随老虎左右,它持续地吠叫警示老虎的到来。听到这声音,所有活着的东西都想飞离或躲开道路。孟加拉人(Bengale)对这种野兽保持敬畏。据说老虎和犀牛是好朋友,彼此常常交流,其原因,据推测,并非不可能,老虎总是渴望食肉,必然有时胃部不适。而犀牛只吃草,老虎跟着犀牛,当感到不适时食用犀牛粪便可自愈,类似猫狗的异嗜行为。”
文本首先陈述中国老虎的地区分布,其次是其经济价值和社会危害。大量文字介绍老虎的奇特习性。老虎与小动物相伴的故事来源有待考证。为了增加文献的新闻效果,文本填充了来自印度的轶闻。17世纪欧洲人对于印度文化的熟悉多过于中国。如前所述,基歇尔的《中国图说》和同时代动物志书籍描述老虎时亦体现出这点。狮子、豹和猫的生理特征、古罗马记忆和印度传闻一起为欧洲人建构出关于老虎的知识储备,进而投射到对中国的想象和描述中。
老虎的所指,首先是一种四足猛兽的物种特征。而遥远国度的珍奇,作为一种全球地理知识,安排在纽霍夫游记,即《荷使初访中国记》的后面,结构性地指向欧洲文明发现新世界的巨大成就。鲁本斯所绘的《世界四大洲》用男女人物代表欧洲、非洲、亚洲、美洲及其主要河流的做法,后来在贝尼尼所著的《四河喷泉》中发扬光大。男子头发中隐藏着四大洲的不同物产,前景老虎代表亚洲。如是,人物、物种和地理互为表征,自然知识体系深深嵌入了殖民时代观看亚洲的角度和方式。《虎之猎》(图10)充分展示了鲁本斯绘画的雄浑之美。前景是一个海格力斯式的人物和狮子搏斗。画面中心,两个阿拉伯装束的东方人受到老虎攻击,险象环生。背景有两位欧洲骑士,他们奋力拼杀或可带来拯救。绘画贯彻着殖民时代的主旋律。东方是异教的、野蛮的、神秘的。但只要忠于上帝,勇往直前,就可以在那里开拓文明,带回财富与荣耀。
《虎之猎》让笔者想起近年美国热点图书《卧虎》。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用“卧虎”比喻中国军事发展可能造成的威胁。书中内容,本文不予评价。它糟糕的封面设计实在“题不对文”(图11)。骇人听闻的标题之上,是包括南中国海在内的中国版图。纳瓦罗强调中美冲突将在台湾、南海等亚太地区爆发,配印地图倒也合理。然而,为了迎合书名,在中国版图上伏一老虎,这种生硬的图像手段貌似直观,实际降低了图书的严肃性。美术编辑将老虎设置在中国版图边缘,以便露出地图主体的“CHINA”字体。这导致图书封面展现出和图书内容截然相反的寓意——恶虎疯狂地撕咬中国。《虎之猎》的图像经验,又或美国鹰派的对立立场,都可能强化这种解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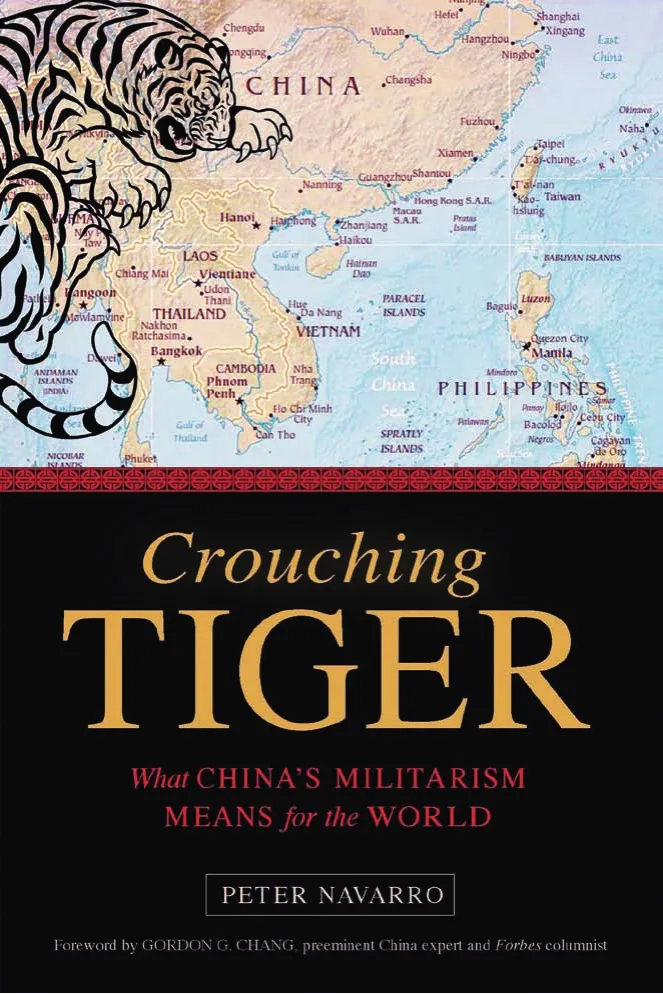
图11:纳瓦罗所著《卧虎》的封面
写生观念一旦确立,图像修正对于图式错误就会变得日益敏感。鲁本斯创造《虎之猎》系列时,参观过布鲁塞尔的动物园。欧洲曾经漏洞百出的老虎图像在18世纪被丰富逼真的形象取代。模仿论时代的绘画,预设为某个景物的再现。这意味着被再现的客体可以作为“客观”和“真实”的标准去评判图像的像与不像。文化符号则缺乏这种尺度,符号的合法性来自于其被定义的过程和被接受的程度。但它可以在歧义、分裂、竞争和包容、接纳、融合中有所调整,适应新的环境。
注释:
① Johan Nieuhof, Het Gezantschap der Neêrlandtsche Oost-Indische Compagnie,aan den grooten Tartarischen Cham, den tegenwoordigen Keizer van China: waar in de gedenkwaerdighste geschiedenissen, die onder het reizen door de Sineesche Landtschappen,Quantung, Kiangsi, Nanking, Xantung en Peking, en aan het Keizerlijke Hof te Peking,sedert 1655 tot 1657 zijn voorgevallen,op het bondigste verhandelt worden,Amstelodami:Jacob van Meurs, 1665,P154.
② Joan Nieuhof, Legatio Batavica Ad Magnum Tartariae Chamum Sungteium, modernum Sinae imperatorem.Historiarum narratione,quae Legatis in Provinciis Quantung,Kiangsi, Nanking,Xantung,Peking, &aula imperatioriâ ab Anno 1655 ad annum 1657 obtigerunt,ut & ardua Sinenfium in bello Tartarico Fortunâ,Provinciarum accurate Geographia,urbium delineation..,Amstelodami:Apud Jacobum Meursium, 1668,P112.
③(德)阿塔纳修斯·基歇尔,张西平、杨慧玲、孟宪谟译:《中国图说》,郑州:大象出版社,2010年,第165、166、316页。
④ Athanasii Kircheri,China monumentis:qua sacris quà profanes, nec non variis naturae & artis spectaculis, aliarumque rerum memorabilium argumentis illustrata,Amstelodami:Apud Joannem Janssonium à Waesberge & Elizeum Weyerstraet,1667.P83.
⑤ Edward Topsel, The History of Four-footed Beasts, and Serpents, London, 1658,P547-548.
⑥ Conradi Gesneri, medici Tigurini Historiae animalium lib.I .de Quadrupedibus uiuiparis,Apud Christ.Froschouerum,1551, P1060.
⑦ Joannes Jonstonus, Historiae naturalis de quadrupedibus libr , Amstelodami,1657, Tab.LIV.
⑧ Johan Nieuhof ,Het Gezantschap der Neêrlandtsche Oost-Indische Compagnie,aan den grooten Tartarischen Cham, den tegenwoordigen Keizer van China: waar in de gedenkwaerdighste geschiedenissen, die onder het reizen door de Sineesche Landtschappen,Quantung, Kiangsi, Nanking, Xantung en Peking, en aan het Keizerlijke Hof te Peking,sedert 1655 tot 1657 zijn voorgevallen,op het bondigste verhandelt worden,Amstelodami:Jacob van Meurs, 1665,P151-159.
⑨(英)E.H.贡布里希,林夕、李本正、范景中译:《艺术与错觉》,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1987,第95-97页。
⑩ Jing Sun, The Illusion of Verisimilitude--Johan Nieuhof’s Images of China, Leden University Press,2013,P249-251.
[11](英)E.H.贡布里希,林夕、李本正、范景中译:《艺术与错觉》,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1987,第95页。
[12](英)E.H.贡布里希,林夕、李本正、范景中译:《艺术与错觉》,林夕、李本正、范景中译,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1987,第98页。
[13](波兰)卜弥格,张振辉、张西平译:《卜弥格文集——中西文化交流与中医西传》,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72、18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