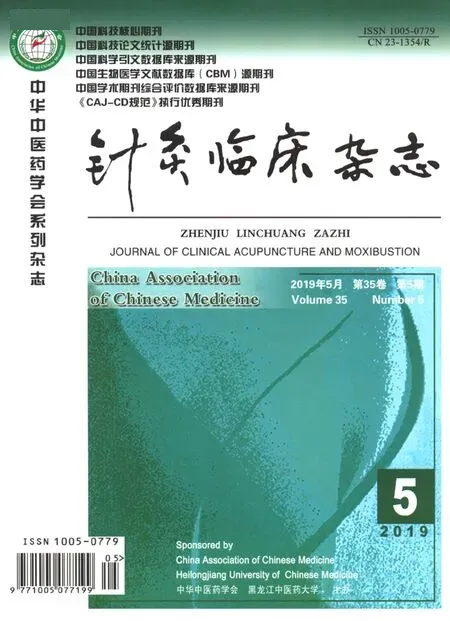针灸治疗放化疗后骨髓抑制研究进展*
2019-01-07李姗姗唐慧玲祝秋梅刘宝虎徐枝芳
李姗姗,唐慧玲,祝秋梅,刘宝虎,徐枝芳,2△,孟 红,2
(1.天津中医药大学实验针灸研究中心,天津 300193;2.天津中医药大学,天津 300193)
放化疗是多种肿瘤疗法中不可替代的一线治疗策略[1]。虽然放化疗可有效抑制肿瘤生长,但其副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骨髓抑制作为最严重的副作用,可引起患者粒细胞降低和血小板减少,甚至发生严重感染,致使化疗不能按时足量完成而影响疗效和肿瘤预后[2]。目前,临床最常用的升白药——集落刺激因子虽能迅速提高中性粒细胞,但因不能促进造血干祖细胞增殖而需反复用药,且存在加重肿瘤免疫抑制微环境的风险[3]。多项临床研究证实,在放化疗开始前或与化疗同步配合针灸疗法可在一定程度上预防和改善患者骨髓抑制及伴随的整体虚劳状态。基础研究揭示了针灸改善骨髓抑制的部分生物学机制但缺乏系统梳理。本研究将从临床疗效和作用机制等方面进行分析,总结针灸治疗放化疗后骨髓抑制的选穴规律、有效的治疗方式及作用机制。
1 概要
放化疗药物作用于癌细胞增殖周期的不同环节,可抑制DNA复制及癌细胞分裂,但这类药物缺乏选择性,会不同程度抑制处于增殖旺盛和分化程度低的骨髓造血干祖细胞和仍具有增殖功能的各系幼稚细胞,导致骨髓抑制而贫血[4]。
中医将之归于“血虚”“虚劳”等范畴。《诸病源候论·虚劳病诸侯》中:“虚劳之人,精髓萎竭,血气虚弱”“脾候身之肌肉,胃为水谷之海,虚劳则脏腑不和,脾胃气弱故不能食也”,初步阐释了虚劳的病因病机。现代医家虽说法不一,但公认其本属“虚”[5]。“虚则补之”是基本治疗思想。放化疗后的患者以气阴两虚和脾肾阳虚两种证型最为常见,治疗以补气养阴、温补脾肾为主。
2 临床疗效评价
骨髓抑制相关的临床报道较为丰富。笔者通过查阅三大中文数据库相关文献,分类整理38篇临床报道,发现单个临床研究常涉及多种癌型,并配合不同的化疗药物,这种设计可能源于中医诊疗强调辨证论治,异病同治,治病求本的诊疗思路。涉及的化疗药物包括烷化剂环磷酰胺(CTX)、抗代谢药氟尿嘧啶及一些抗肿瘤动植物成分药,部分文献并未说明化疗药物类型。
针灸治疗方式以艾灸为主(22篇灸法临床研究中,单纯艾灸14篇、温针灸3篇、天灸3篇、灸药结合2篇)。其他方式包括5篇电针、6篇穴位注射、4篇手针和1篇刺血拔罐法。选穴方面,主要选用足三里、气海和关元等补益要穴,常配合背俞穴。在38篇临床文献中,使用频次≥5次的腧穴包括足三里、膈俞、关元、三阴交、肾俞及气海等穴,其中足三里使用频次最高,是最常用穴。张圣宏报道放化疗后骨髓抑制用穴特点的文献中,总结了173条针灸处方,发现所用的33个腧穴中足三里、大椎和膈俞穴使用频次最高[6],与本文统计结果大致相同。但由于样本量大小不同,数据方法整理有异,统计结果也存在一定差异。张氏统计频次较高的大椎穴,笔者认为多集中在动物实验中。
2.1 艾灸
艾灸的功效以温通为主,故可治疗脾肾阳虚型骨髓抑制。徐红达等[7]对艾灸治疗放化疗后骨髓抑制相关文献进行总结,认为艾灸共涉及8条经,最常用的是足太阳膀胱经和足阳明胃经。单纯艾灸即取效不错的报道屡见不鲜,部分研究发现艾灸可一定程度抑制早期肿瘤生长和减轻癌症并发症[8]。
文献报道的艾灸方式多样,如雀啄灸、回旋灸和热敏灸等;艾条种类繁多,如清艾条和药艾条等。单次治疗时间为20~30 min,疗程常伴随整个化疗过程。隔物灸多取四花穴、大椎、关元和督脉诸穴。一项包含226例患者的大样本研究表明,艾灸背俞穴能防治化疗所致白细胞减少,并能减少人重组粒细胞刺激因子用量[9]。陈露等[10]使用背俞穴热敏灸与服用鲨肝醇、利血生进行对照,发现艾灸效果更优。
艾灸配合针刺或中药内服亦可对放化疗引起的骨髓抑制起到不错的防治作用。戴丽娟等[11]发现,在常规治疗基础上配合足三里温针灸可以更好地防治化疗引起的骨髓抑制。迟翔等[12]报道艾灸联合十全大补汤治疗非小细胞肺癌化疗后I度骨髓抑制(脾肾亏虚型),疗效较单纯服用汤剂更优。
艾灸治疗报道丰富但并没有普遍服务于病人,笔者认为广大民众包括中医从业者对艾灸疗法的认识尚为表浅。
2.2 电针
以电针作为治疗手段的临床研究中,单穴常取膈俞或足三里,双穴采用足三里配三阴交,刺激量常以患者耐受为度。电针治疗常用的两种波形是疏密波和连续波。王小寅[13]使用韩式穴位神经刺激仪疏密波,直流电针刺激化疗患者膈俞和足三里,发现在抑制血液白细胞和中性粒细胞方面,足三里较膈俞效果更优。
2.3 毫针刺法
毫针刺法治疗骨髓抑制一般采用平补平泻和重插轻提补法。黄海霞[14]用子午对冲针刺法治疗化疗后血小板减少症(戌时针大陵、足三里。亥时针天井、太白),不同时段检测血小板计数,计算血小板增长速度,结果证实针刺可显著提高血小板计数,且停止治疗后仍能维持增长趋势。
2.4 其他方式
多项研究报道穴位注射、刺血拔罐及穴位贴敷也可有效改善化疗后骨髓抑制。穴位注射常用穴包括足三里和血海,常用药物包括地塞米松、黄芪注射液、维生素B1、B12和重组人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等,如王均海等[15]报道足三里穴位注射黄芪注射液对改善化疗后白细胞减少疗效可靠。李波等[16]发现刺血拔罐肝俞、脾俞和/或皮下结节可改善肿瘤患者化疗后的血小板减少症。
3 作用机制研究
3.1 干预方式、选穴及疗效指标
针灸治疗放化疗后骨髓抑制的基础研究有文献记载可追溯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笔者整理的34篇相关基础研究中除2篇使用阿霉素外,其余均使用CTX造模。事实上现代肿瘤临床多以铂类药物为主。多数研究采用单纯腹腔注射CTX,部分以皮下植瘤后给予化疗药。动物实验涉及使用频次≥20次的腧穴包括足三里、大椎、肾俞和膈俞。使用频次分别为25次、22次、20次和20次。针刺和艾灸是最常见的干预手段,占实验研究的大多数,共计31篇。此外还有天灸2篇、电针刺激1篇。疗效指标涉及外周血白细胞、造血干细胞、骨髓有核细胞和骨髓粒系细胞。赵喜新等[17]发现,针刺可延长淋巴细胞及单核细胞寿命,艾灸侧重提升中性粒细胞数目。
3.2 作用通路探讨
3.2.1 改善骨髓细胞增殖 路玫等通过观察针灸对CTX化疗小鼠骨髓细胞DNA含量动态变化的影响,提出针灸可上调骨髓细胞DNA修复相关蛋白MGMT、POLβ和XPD的表达[18-19],同时,针刺与艾灸均可促进骨髓细胞周期调节蛋白cyclin Dl表达,增强细胞DNA的合成,加速细胞有丝分裂[20]。于冬冬等[20]发现,针灸可提高荷瘤小鼠骨髓细胞DNA的碱基切除修复能力(DNA切除修复蛋白DNA聚合酶β)。此外,针灸还可促进环磷酰胺造模小鼠巨噬细胞分泌更多的GM-CSF,促进白系细胞增殖分化。以上证据说明,针灸可直接促进骨髓细胞增殖功能,但是否作用于化疗药损害的造血干祖细胞尚未阐明。
3.2.2 修复造血微环境 骨髓造血微环境是维持造血干祖细胞增殖、分化及迁移功能的重要载体。既往研究证实,针灸可能通过修复造血微环境以改善骨髓抑制:金玉晶等[21]证实,针灸可提高环磷酰胺化疗小鼠骨髓组织中黏附分子ICAM-1、VCAM-1蛋白表达,改善组织细胞和造血细胞之间的粘附和信息交换;李昆珊[22]认为,针刺和艾灸可上调CTX化疗小鼠骨髓中趋化因子SDF-1表达,下调骨髓中粘附分子LFA-1的表达,保护化疗后骨髓间充质干细胞,以修复造血微环境,且艾灸效果明显优于针刺。
针灸还可以增强患者抗肿瘤抗感染的能力。崔尚敏[23]证实,针灸可以提高CTX化疗荷瘤小鼠脾脏指数、脾脏组织中白细胞介素-12和肿瘤坏死因子-α的含量,改善化疗后的免疫损伤,且疗效与治疗频次呈正相关。刘海伟等[24]通过干预CTX化疗小鼠,发现针灸可提高CTX化疗小鼠IL-7和IL-18血清含量,促进淋巴细胞生长,缓解CTX所致的免疫抑制,一定程度上提高抗肿瘤的免疫效应。
3.2.3 调节信号通路 在明确针灸通过修复造血微环境或直接作用于造血细胞促进增殖的研究基础上,部分学者对针刺靶向造血干祖细胞的上游信号通路做了相关研究。滕迎春、于冬冬[25-26]以Notch信号通路为切入点,利用基因表达谱芯片筛查出CTX可改变Notch通路上numb1、numb2、notch1、notch2、jag1、jag2及delta1等7个差异基因,针刺和艾灸可能通过调节numb1、numb2、notch2和jag1基因表达抑制过度过度激活的Notch信号通路,促进骨髓造血干/祖细胞增殖。
4 小结
综上所述,多种针灸方式均可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放化疗导致的骨髓抑制,其中艾灸是最常用的临床研究方式,足三里为最常用选穴。但已进行的临床试验存在设计不严密和样本量小等问题,今后可进一步完善临床设计,展开多中心大样本的随机对照试验。有关机制探讨的基础研究中,多以针刺和艾灸作为干预手段。针灸起效机制之一可能是通过Notch信号通路促进造血细胞增殖,这可作为一个切入点系统研究。然而机制研究虽已发现针灸可作用于骨髓细胞,但靶点是否为化疗药直接损害的造血干祖细胞仍不明确,故其生物学机制仍有待于深入探讨。从基础研究回归临床,针对恶性肿瘤患者,有必要建立一个完整的中西医综合防治体系,使中医药治疗优势充分挖掘运用。
值得一提的是,肿瘤免疫治疗由于其卓越的疗效和创新性,在2013年被《科学》杂志评为年度最重要的科学突破。近几年单克隆抗体类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性抗体、癌症疫苗、细胞治疗和小分子抑制剂等已在多种肿瘤(如黑色素瘤,非小细胞肺癌、肾癌和前列腺癌等实体瘤)的治疗中展示出了强大的抗肿瘤活性,多个肿瘤免疫治疗药物已经获得美国FDA批准临床应用。在本次调研中,大量证据提示针灸可调节肿瘤模型的免疫状态,如崔尚敏[23]证实针灸可改善CTX化疗小鼠化疗后的免疫损伤。刘海伟等[24]证实,针灸可提高CTX化疗小鼠IL-7和IL-18血清含量,促进淋巴细胞生长,缓解CTX所致的免疫抑制,一定程度上提高抗肿瘤的免疫效应。但目前尚缺乏针灸对肿瘤局部免疫微环境的实在证据。因此,针灸能否作为一种潜在的肿瘤免疫疗法仍有待于深入系统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