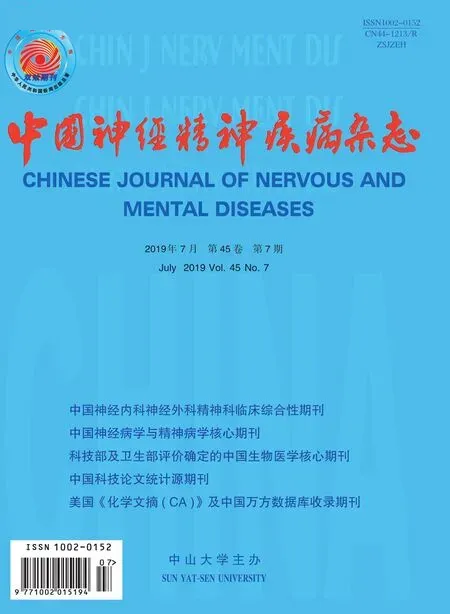大脑类器官模型在精神疾病研究中的现状及展望☆
2019-01-06黄兢刘方琨唐慧伍海姗李乐华陈晋东
黄兢 刘方琨 唐慧 伍海姗李乐华 陈晋东
精神疾病是常见的病因复杂、发病率高、多基因遗传疾病,造成了极大的经济负担和社会负担。目前各种体内外模型已广泛用于研究精神疾病的病因学机制和精神药物相关研究。然而,由于精神疾病的复杂性,如何选用合适的模型从结构、细胞和蛋白水平更好地研究精神障碍的发病机制和药物作用,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1]。大脑类器官(cerebral organoids)是由干细胞定向诱导分化形成的大脑皮质结构,可一定程度上在体外模拟人类胚胎早期大脑的发育过程和结构特点,在研究精神疾病的起源和病理学、药物筛选和基因改造方面显示了很大潜力[2]。本综述对大脑类器官在精神医学的研究进展与局限性进行探讨,并对大脑类器官未来的发展和应用进行评估与展望。
1 大脑类器官模型的建立与研究进展
自1981年研究人员从小鼠囊胚的内细胞团中分离出胚胎干细胞[3],干细胞技术在近几十年来快速发展,实现了人类大脑类器官的体外培养。1998年THOMSON等[4]成功分离出人胚胎干细胞,并将其进一步分化得到各种类型的组织细胞,包括神经上皮和胚胎神经节细胞等。2007年,TAKAHASHI等[5]在已分化成熟的体细胞中转入Oct3/4(Pou5f1)、Sox2、Klf4和c-myc等 4个关键转录因子进行重编程,使其回到多能性状态,得到人诱导多能干细胞(human induced pluripotent stem cells,hiPSCs)。 与胚胎干细胞相比,hiPSCs取材方便,来源广泛,可以取材于患者的体细胞,避免了伦理问题和免疫排斥反应,为个体精准治疗提供了新的途径。最早用于大脑研究的体外模型是拟胚体(embryoid bodie,EB)来源的神经玫瑰花结(neural rosettes,NR)。神经玫瑰花结是hiPSCs分化为大脑类器官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类似人体神经管结构,是各种神经细胞分化的基础。hiPSCs技术进一步发展促进了诱导多能干细胞神经球体和三维神经上皮组织的产生,它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人类大脑的基因学特点,但是它们没有形成完整、复杂的大脑结构,也缺少大脑不同亚区之间的协调作用[6]。
2013年,LANCASTER等[7]首次利用 hiPSCs定向诱导分化形成大脑类器官,并用于小头畸形研究。他们将hiPSCs定向诱导分化,产生具有内、中、外三个胚层的拟胚体结构,随后经过神经外胚层、神经上皮层,最后形成类似早期胚胎期大脑皮质的结构,能一定程度上反映人体早期胚胎期大脑的发育过程[8]。该团队还发现,小头畸形大脑类器官的大小、神经胶质细胞的数目和分布与正常大脑类器官相比,有显著区别[7]。DANG等[9]对类器官进行RNA测序发现,培养至第30天的大脑类器官与孕8~9周的人类胎儿大脑标本基因表达谱十分相似。与动物模型和细胞培养等研究手段相比,大脑类器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体外模拟人类胚胎早期大脑的发育过程和结构特点,并能较好地保持人体特异性基因型和蛋白表达水平,有很大的临床应用价值[2]。基因编辑工具进步,如规律间隔成簇短回文重复序列(clustered regularly interspaced short palindromic repeats,CRISPR)、转录激活样因子核酸酶技术(transcription activator-like effectors nucleases,TALENs)、 锌指核酸酶 (zincfinger nucleases,ZFN)等可以实现对任意基因序列的精准编辑。这些基因编辑技术在大脑类器官模型中应用,为疾病基因突变分析、目标基因修复以及遗传风险基因研究等提供了更有效的平台。
大脑类器官作为大脑疾病体外模型已广泛应用于多个研究中。研究人员可以直接将患者的体细胞重编程为hiPSCs,最终得到具有患者遗传背景的大脑类器官。通过这种人体细胞来源的神经组织模型,人们可以精确地分析不同神经精神疾病受到影响的大脑区域和细胞类型,并进行基因学分析和机制探讨。大脑类器官随后被应用于中枢神经系统疾病的研究,如大脑发育疾病、感染性疾病、癫痫、中枢神经系统肿瘤等[10-14]。大脑类器官模型的进一步优化以及与其它生物调控技术等结合也促进其进一步发展和在临床中应用。
2 大脑类器官模型在精神疾病研究中的应用
动物模型是研究精神疾病病因学和药理学的重要手段,它们在研究精神疾病的单基因突变以及发现药物新靶点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然而,由于精神疾病的复杂性,且动物缺乏人类遗传特性和某些人类特有的大脑区域,很难利用动物模型从结构、细胞和蛋白水平研究精神障碍的发病机制和药物作用[1]。非人类灵长类动物模型和人类脑组织模型的资源匮乏和伦理问题,限制了精神疾病研究的发展。
大脑类器官作为一种新兴的体外模型,在精神疾病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精神分裂症是高度遗传的精神障碍,基于精神分裂症患者的DNA全基因组测序的研究发现15q11.2基因拷贝数变异是其危险因素之一[15-16]。YOON等[17]比较具有15q11.2拷贝数微缺失与未缺失的iPSCs来源人类神经前体细胞发现,15q11.2拷贝数微缺失可以导致神经前体细胞粘着连接和顶端极性缺陷。进一步研究和基因分析发现,CYFIP1和WAVE信号通路的上位相互作用可能通过影响神经干细胞功能来增加神经精神疾病的易感性[17]。研究人员同时也用大脑类器官研究与精神疾病相关的其他常见遗传突变。精神分裂症断裂基因1(disrupted-in-schizophrenia 1,DISC1)是包括精神分裂症、抑郁症和双相障碍等很多精神疾病的潜在易感基因,尽管对DISC1的研究众多,DISC1蛋白如何与其他蛋白发生相互作用从而影响大脑功能却鲜有报道[18]。研究人员将携带DISC1突变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多能干细胞诱导分化为大脑类器官,发现了重要结果:DISC1和核分布蛋白类nudE因子 1 (nuclear distribution protein nudE-like 1,NDEL1)结合能够调节神经干细胞的分裂,DISC1突变导致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神经细胞分裂迟滞[19]。SRIKANTH等[20]在此基础上利用TALEN技术得到DISC1突变的大脑类器官,发现这些类器官与正常对照组相比,有着明显的形态结构和增殖异常。进一步研究发现,加用WNT信号通路抑制剂可以逆转DISC1突变导致的结构和增殖异常,揭示了DISC1突变、WNT信号通路和精神分裂症的潜在联系。
大脑类器官在孤独症研究中也取得了一定进展。比较孤独症患者及其家属iPSCs诱导分化而来的端脑类器官发现,孤独症患者的类器官并没有出现组织结构和神经元兴奋性异常。全基因组测序分析提示:孤独症患者的类器官细胞周期增快,且 γ-氨基丁酸 (γ-aminobutyric acid,GABA)能抑制性神经元增多。随后的基因干预研究证实,FOXG1过表达是导致GABA能抑制性神经元增多的原因,并与孤独症疾病进展及症状严重程度相关[21]。
同精神分裂症与孤独症一样,双相障碍也是病因复杂的遗传疾病,遗传率高达80%[6,22]。大脑类器官模型也运用到了双相障碍的研究中,以探讨大脑发育过程紊乱和疾病发生的关系。MADISON等[23]比较双相障碍患者与其家属大脑类器官分化早期的神经前体细胞发现,患者神经前体细胞的CXCR4表达明显增高。对患者的神经前体细胞使用抑制剂糖原合成酶激酶-3(glycogen synthase kinase 3,GSK-3)发现,神经前体细胞的发育异常可以被修复[23]。
大脑类器官模型在药物对胚胎早期大脑发育及机制研究方面也显示了很大潜力。WANG等[24]和ZHU等[25]利用大脑类器官模型发现酒精和尼古丁等可能导致神经分化和脑区形成异常。我们之前的研究也发现单胺氧化酶抑制剂反苯环丙胺(tranylcypromine)能抑制大脑类器官体外神经组织增殖,并降低神经元细胞和星形胶质细胞数目,以及组蛋白去甲基化相关基因的表达,如赖氨酸去甲基化酶1(lysine specific demethylase 1,LSD1)和二甲基化组蛋白(dimethylated H3K4,H3-di-K4)等[26]。
除此之外,研究人员尝试培养特定脑区的类器官以进行精神疾病相关研究,如海马类器官、中脑类器官、丘脑类器官等。XIANG等[27]成功培养与精神疾病密切关联的丘脑类器官,甚至将丘脑类器官和额皮质类器官融合培养以研究精神疾病的起因。
3 大脑类器官模型的不足与展望
HiPSCs细胞诱导形成神经元、神经胶质细胞以及大脑类器官的成功建立,为神经系统疾病模型带来了新的方向。然而,大脑类器官在精神科研究领域应用目前仍较少,而且存在一些问题和局限性,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改进。
首先,将人体细胞诱导为hiPSCs有较高的技术要求,在成纤维细胞重编程为干细胞的过程中,可能出现细胞基因结构变异,如拷贝数增加、染色体异常和点突变等,影响诱导后的干细胞基因稳定性[28-29]。因此,重编程后的hiPSCs难以完全准确反映患者的遗传特点。基因编辑技术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实现特定基因的点突变,得到稳定、可诱导特定疾病模型的干细胞[28]。另外,如何长期稳定地培养已分化成熟的大脑类器官仍是一大难题。目前,大脑类器官系统仅限于实验室研究,其他器官的干细胞培养已逐渐转向应用于移植治疗,如何将大脑类器官系统用于临床,需要更深入的研究。
大脑类器官已经应用于多种神经精神疾病的模型构建,并且取得了一些突破性的进展。来源于患者皮肤细胞、胶质细胞和单核细胞等细胞经重编程得到的多能干细胞,可以诱导分化为有特定基因变异的疾病模型,也可用于靶向药物筛选等。然而,精神疾病是多个致病基因和外界环境交互作用导致的,完善的机制研究和模型构建需要联合大脑类器官模型和动物模型共同实现[29]。
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很多精神疾病可能是多个发育进程紊乱导致的大脑发育异常和环路异常,如神经元和胶质细胞数量的改变,大脑细胞特定脑区的迁移以及准确合适的突触电生理活动等[30-32]。大脑类器官模型可以为研究精神疾病的起源和病理学提供一个新的体外模型,在分子和细胞水平研究精神疾病相关遗传变异对人类大脑发育和功能的影响。
除此之外,大脑类器官模型也可广泛用于药物毒理学研究和新药开发。很多研究表明,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脑体积减少,然而其具体分子学机制尚不明确,有研究表明抗精神病药物可以引起脑体积缩小,也有研究认为无法排除疾病自然进程的影响[33]。大脑类器官模型可以体外模拟患者大脑的早期发育和生长过程,因此可以对类器官使用不同抗精神病药物进行处理,以观察药物与脑体积的关系。总的来说,大脑类器官在精神疾病病因、病理、治疗等研究中显示了巨大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