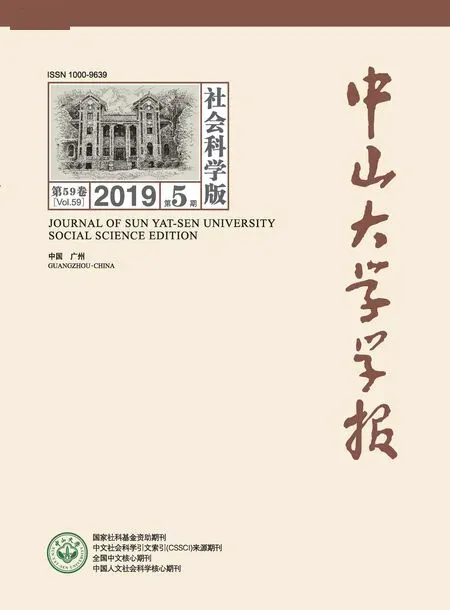新文学运动的边缘回响*──论澳门的早期新诗
2019-01-06邓骏捷
邓 骏 捷
自明代中后期开始,由于历史的原因,澳门文化的发展就走上了一条与中国内地不完全一样的道路,因此具有了自身的独特性。然而,同族同种,语言相通,交往密切,互相依赖,又使得澳门时时受到内地不同程度的影响。澳门文学是澳门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亦应作如是观。澳门文学的主体——华文文学,明清以来就是中华文学不可或缺的部分,因而其发展过程每每与内地息息相关,如澳门文学的三个繁荣时期,即明末清初、清末民初和抗战时期,皆是受内地政治局势的影响而产生的。另一方面,从文学本体发展而言,澳门文学所受的内地影响,最显著的例子莫过于澳门新文学的出现。过往一般认为“迄今尚未有发现任何资料,可以说明新文学运动在它最初蓬勃的十年对澳门产生何种影响”(1)刘登翰主编:《澳门文学概观》,福建:鹭江出版社,1998年,第100页。;也就是说,澳门新文学的出现不仅较内地迟缓,而且也看不到与内地“新文学运动”间的影响关系,不过事实却并非如此。
笔者近年整理研究民国时期的澳门文学史料,发现目前所知的澳门最早一首新诗(1920年)、最早的新诗集(1928年)以及第一个新诗作者群。这些发现有助于了解澳门新文学的起源和早期面貌,并可藉以探讨新文学运动对澳门文学发展的影响。通过澳门早期新诗的情况,不仅说明澳门新文学的发轫与新文学运动关系密切,甚至可以说澳门新文学是在新文学运动兴起的短时间内受其直接影响下的产物。不过,澳门新诗的发展过程却是曲折的,它反映出澳门新文学的发展受到一定自身因素的制约,并与外来影响形成了复杂的张力关系。
一、澳门新诗发轫寻踪
澳门虽一度在葡萄牙的管治之下,但地处岭南一隅,所以华文文学的创作和发展,一直与中国内地大体保持一致。明清时期,基本上是古典诗词的天下;进入民国,随着一批清遗民的涌入(其中汪兆镛是典型的例子(2)李杰:《“谁向虞渊挽夕晖”:汪兆镛的遗民身份及其自我建构》,《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诗词的势力更形重要。而在中国内地,1917月1月,胡适在《新青年》第2卷第5号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倡白话文学。1918年,《新青年》上发表了胡适、沈尹默、刘半农、陈独秀、唐俟(鲁迅)、陈衡哲、李大钊等人的第一批新诗(3)详参刘福春:《新诗纪事》,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年,第2—3页。。从此,新文学运动浪涛汹涌,席卷全国,使中国文学从形式到内容都发生了一次革命性转变。那么,当时以古典诗词为主要创作手段的澳门文学界对于新文学运动,尤其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新诗,反应究竟又是如何的呢?
首先需要界定的是,何为澳门新诗?郑炜明在《澳门中文新诗史略》中,曾经指出“澳门中文新诗作为一个文学研究的概念,应包括两大范围:(1)澳门人创作的中文新诗,(2)以澳门为题材的作品”;并据之认为“最早期的一首作品,也许可以追溯到著名的新月派诗人闻一多先生所创作的《七子之歌之澳门》。这首诗为组诗《七子之歌》的第一首,发表于1925年11月”;“至于30年代的澳门中文新诗,我们现在能搜集到的资料仍然屈指可数,大抵有德亢、蔚荫、魏奉盘和飘零客等几位在30年代末的几首作品”(4)郑炜明编:《澳门新诗选》,澳门:澳门基金会,1996年,第1页。。陈辽亦谓“至少从30年代起,澳门即有诗人从事新诗创作,(如)出生于澳门的华铃”(5)陈辽:《新诗·现代诗·新现代诗──论澳门新诗的发展轨迹》,廖子馨编:《千禧澳门文学研讨集》,澳门:澳门日报出版社,2002年,第98页。。不过,郑炜明所举的例子──闻一多《七子之歌》中的《澳门》,充其量只符合他所指的澳门新诗的第二个范畴,即“以澳门为题材的作品”。因为闻一多先生毕竟不是澳门人,而且从未踏足澳门。故此吕志鹏在遍考众说,却困于没有新史料的情况下,唯有同意郑炜明的结论;但他又据刘登翰的观点,指出《七子之歌》中的《澳门》“只是‘关于’澳门,而非本土创作”的新诗(6)详参吕志鹏:《澳门中文新诗发展史研究(1938—2008)》,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澳门:澳门基金会,2011年,第33—40页。。那么澳门本土诗人创作的第一首新诗,究竟产生在什么时候,又为谁所写,是否早于《七子之歌》中的《澳门》?就成为澳门新文学史上一个有待破解的悬案,并且可能触发对澳门新文学史的重新思考。
(一)《纸鸢》──澳门的第一首新诗
据今所见,澳门最早的白话新诗应是冯秋雪的《纸鸢》(拟题)。它写于1920年1月,较闻一多《七子之歌》中的《澳门》最少早近五年。冯秋雪是澳门近代商人冯成之孙,冯成长子冯嘉骥之子,长期在澳门生活和居住,是地地道道的澳门人;而且《纸鸢》发表在澳门的文学刊物《诗声》第4卷第8号的《诗声附庸》上,因此它可以当之无愧地称为澳门的第一首新诗。
冯秋雪(1892—1969),名平,又名宗樾,字秋雪,广东南海人。清光绪三十年(1905)前后,冯秋雪与其弟冯印雪(1893—1964,名祖祺,號乙盦)、赵连城(1892—1962,名壁如,别名冰雪,后来成为秋雪之妻)一同就读于澳门培基两等小学堂。1910年,同盟会在澳门下环四十一号设立秘密支部,又组织“濠镜阅书报社”。冯秋雪等人参加“濠镜阅书报社”,成为同盟会在澳门发展的最早成员,并积极投身辛亥革命的各项活动(7)详参冯秋雪:《辛亥前后同盟会在港穗新闻界活动杂忆》,陈夏红编选:《辛亥革命实绩史料汇编·舆论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1年,第269—278页;赵连城:《同盟会在港澳的活动和广东妇女界参加革命的回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硏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二集,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第302—322页。。民国成立之后,各地同盟会组织日趋解体,“濠镜阅书报社”不久亦告结束。1913年,冯秋雪与“留澳的当地同盟会几位会员,便在澳门组织了一个‘雪堂诗社’,寄情吟咏,不谈政治”(8)冯秋雪:《中华革命党澳门“讨龙”活动杂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硏究委员会编:《广州文史资料》第十一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38页。。雪堂诗社于1915年7月开始编辑出版社刊《诗声──雪堂月刊》,社址设在“澳门深巷十八号”的冯家。自创刊至“庚申年伍月”(1920年6月)第4卷第10号为止,《诗声》一共出版了4卷46期(9)过往学界对于《诗声》杂志了解不多,不过近年随着《诗声》的重新浮现以及澳门文化局将之全面刊布,其面貌已经清晰地呈现出来了。详参《雪社作品汇编》第1、2册,澳门:澳门文化局,2016年。。
雪堂诗社是民国时期澳门第一个以本土居民为主的文学团体,他们结集同道,以“月课”形式进行诗词创作,在澳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10)详参邓骏捷:《澳门雪堂诗社考述》,《学术研究》2016年11期。。由于“雪堂”以提倡风雅、畅论古典诗词为宗旨,所以过往不为治澳门新文学史者所注意,然而澳门最早的一首新诗却出现在《诗声》之上,不禁令人意外。
《诗声》从第4卷第1号(1919年2月)开始,增加了附刊《诗声附庸》,一共10期,分别刊载秋雪、连城合著的《并肩璅忆》、埜云的《云峰仙馆读画记》以及琴樵的《鼎湖游记》。《并肩璅忆》是冯秋雪、赵连城对少年生活的回忆,每每谈及二人相恋、相处等琐事,情意绵绵。《并肩璅忆》共有两章,分别是《画月》(载《诗声附庸》第4至7号)、《呜呼纸鸢》(载《诗声附庸》第8至10号)。《画月》为冯秋雪所撰,前有赵连城的《忆江南》题词。《呜呼纸鸢》为赵连城所撰,前有冯秋雪的新诗一首:
西风起,纸鸢飞满天,放哩!放哩!的声,闹成一片。/斜日照着林梢,好一个天气已凉,时节又暖。/放纸鸢!放纸鸢!冰姉呀!我要她又高又远。/不要和人割,恐怕他折我断。/执定这线儿,注定那眼儿,空中吗!任尔风云万变。/纸鸢!纸鸢!你好得意呀!又高又低,又展又转。/唉!风来了,雨到了,怎样好呀?冰姉呀!/刮喇!刮喇!疏疏!疏疏!──/哎唷!线断了,纸鸢呢?没由寻见。/为什么弄到这样呀?/都是他不知为人玩弄,翱翔天空,意满心足。
(九年一月秋雪题)(11)《诗声》第4卷第8号《诗声附庸》第8号,1919年10月8日,第23页。
落款中的(民国)“九年一月”,即是1920年。《呜呼纸鸢》写少年冯秋雪爬树观看两只纸鸢空中飞翔,继而相缠坠落;他在呼叫赵连城(诗中的“冰姉”)时,不慎失足堕地,触伤头面。此诗内容与之相应,当是《呜呼纸鸢》的题诗。然因没有诗题,暂可拟题为《纸鸢》。此诗结构完整,文字流畅,形象生动,配合《呜呼纸鸢》的内容,更觉主题鲜明,是一篇较为成熟的新诗作品。
附带说明的是,《诗声》第4卷第8号的出版日期标作“夏正己未年八月望日”,即1919年10月8日;然该号附刊《诗声附庸》上的冯秋雪新诗的题写时间为1920年1月,两者相差近三个月。考虑到民国刊物的实际出版时间,有时会较标示者略后,所以冯诗的写作时间仍以定在1920年1月为宜。由此可见,恐怕不宜再认为新文学运动“几乎没有在澳门引起回应”(12)刘登翰主编:《澳门文学概观》,第99页。,而是确实有所响应,且速度不慢,至少较香港《小说星月刊》(1924年)上发表的新诗为早(13)参见叶辉《新诗地图私绘本》,香港:天地图书公司,2005年,第242页。。
(二)《绿叶》──澳门的第一部新诗集
如果说只有一首新诗作品,其出现或属偶然,仍不能反映澳门新文学的早期面貌。那么,在1928年3月出版的冯秋雪、冯印雪、赵连城三人的古典诗词、新诗合集《绿叶》,则大体反映了澳门早期新诗创作的实绩和水平。
雪堂诗社在出版《诗声》第4卷第10号后,因“社友星散,尠获聚首”(14)黄沛功:《雪社第一集·叙》,澳门:雪社,1925年,第1页。,基本停止了文学活动。到1925年,冯秋雪重组诗社,并邀梁彦明等人入社,组成“雪社”,社员共冯秋雪、冯印雪、赵连城、黄沛功、梁彦明、刘君卉、周佩贤七人。“雪社”与“雪堂”的活动基本一致,主要包括雅集、畅游、聚饮、诗课等,但不再编辑出版社刊,而是改为出版社集,“雪社”前后出版了诗集五种(15)《雪社第一集》,澳门:雪社,1925年;《雪社第二集》,澳门:雪社,1926年;《雪社第三集》,澳门:雪社,1927年;《雪花──雪社第四集》,澳门:雪社,1928年;《六出集──雪社第五集》,澳门:雪社,1934年。《雪社诗集》五种,现已全部收入《雪社作品汇编》第3册,第8—284页。。
在出版《雪花──雪社第四集》的同一时间,“雪社”还出版了冯秋雪、冯印雪、赵连城的合集《绿叶》,作为“雪社丛书之一”(16)冯秋雪、冯印雪、赵连城:《绿叶》,澳门:雪社,1928年。《绿叶》收入《雪社作品汇编》第3册,第285—340页。。此书前有古畸、黄沛功的《序》、冯秋雪的《序:我们底〈绿叶〉》和刘草衣(君卉)的《绿叶集题词》。全书分为上中下三部分,“绿叶上”收冯秋雪诗10题21首、词3题3阕、新诗7题9首,合共20题33首(阕);“绿叶中”收冯印雪诗14题22首、词2题2阕、新诗3题3首,合共19题27首(阕);“绿叶下”收赵连城诗13题19首、词3题5阕、新诗3题3首,合共19题27首(阕)。其中部分诗词见于《雪社第二集》《雪社第三集》《雪花──雪社第四集》,当然也有一些新作,相信此书是三人的一部诗词选集。
最值得引起注意的是,《绿叶》收有三人的新诗作品共13题15首,即冯秋雪的《心海》《我愿》《笔》《看书》《小花》《北岭村口底新叶》《白莲洞杂诗》(组诗,共3首)(17)冯秋雪、冯印雪、赵连城:《绿叶》,第1—2、9—10、16—17、25—28,38—39、41、49,53、57—58、65,7—8,2—6页。,冯印雪的《梧桐》《天籁》《小诗》(18)冯秋雪、冯印雪、赵连城:《绿叶》,第1—2、9—10、16—17、25—28,38—39、41、49,53、57—58、65,7—8,2—6页。,赵连城的《良夜》《人们底慈母》《记得甚么?》(19)冯秋雪、冯印雪、赵连城:《绿叶》,第1—2、9—10、16—17、25—28,38—39、41、49,53、57—58、65,7—8,2—6页。。它们是澳门新诗史以及新文学史上的重要标志,即是早在20世纪20年代,澳门已经出现了一批新诗作品以及第一个关系密切的新诗作者群。同时也说明了“雪社”不仅是从事古典诗词创作的文学社团,也是一个新旧文学兼有,尝试创作多种形式诗歌的群体,这使得它在澳门文学史上的地位更显特殊和重要。
二、澳门早期新诗作品析论
“绿叶”中的新诗作品,数量不多,而且明显地带有尝试的性质,冯秋雪曾在《序:我们底〈绿叶〉》中写道:
绿叶,是我们品格的象征;是我们著作的象征;所以拿牠来叫我这本书。
……
我们的诗,仿佛像绿叶。不见得牠有甚么别的色采,不见得牠有甚么可爱。远看只见一片的蒙蒙地,近才知是一片一片底叶呢!这样的朴素冲淡,或许是牠们底本色呢!(20)冯秋雪、冯印雪、赵连城:《绿叶》,第1—2、9—10、16—17、25—28,38—39、41、49,53、57—58、65,7—8,2—6页。
由此可见,冯秋雪对于他们的诗词,以至新诗创作,抱着一种尝试和谦虚的态度,完全没有大张旗鼓的意思。至于冯秋雪等人写作新诗的缘起,古畸《绿叶的序》说道:
我的朋友秋雪先生,对于旧文学极有修养,同时对于近世的科学知识也很多通晓。所以他的为人,有和古人一样的真摰的深情和照人的肝胆;他的思想和行动,却又时时站在时代的前面,为一般时代落伍的人物所怀疑──他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也是一个理智充实的改革者。感情和理智,在他却尽量地得到平行的发展。
“抒情的文字大抵古人较今人好”,这句话秋雪也颇以为然,所以他每好作旧体的诗,但他也很相信社会蜕进的结果,今人也自有其古人所无的特殊情怀,不妨拿新的方法写出来,所以他又作了不少的新体的诗。
……
秋雪深于情,很有诗的情绪修养;就是工具的驱遣,也经过了不少的训练;宜其新体旧体无不工妙了!
绿叶是他和他的夫人连城女士,令弟印雪先生的合并诗集的一种。他们三人的见解和学问都大略相同;我所说的关于秋雪的话,移给连城或印雪,我觉得还都没有不适宜的地方。(21)冯秋雪、冯印雪、赵连城:《绿叶》,第1—2、9—10、16—17、25—28,38—39、41、49,53、57—58、65,7—8,2—6页。
冯秋雪等人熟读古典,对诗词时耽苦吟,同时又有写作新诗的情怀,拥有写作新诗的本领。而且,他们勇于接受新思想、新观念,在新文化运动浪潮中作出尝试,于是澳门诗坛出现了第一批白话新诗,成为澳门新文学的蒿矢,翻开了澳门文学史的新一页。
(一)冯秋雪的新诗
冯秋雪的古典诗词“以淡远胜”(22)黄沛功:《绿叶集·序》,冯秋雪、冯印雪、赵连城:《绿叶》,第3页。,而其新诗的情感却不一样,似乎来得浓烈许多。如《心海》:
我的心海啊!/我深深地拥护着你,/待你也算不薄了!/你为甚的时起潋滟底微波?/为甚的时起澎湃底洪涛?/使我不得一时的宁息呢?/我愿化作太阳,把心海曝干了,涸了!/要牠变做犹太底死海;/要牠变做蒙古底戈壁。/心海啊!/静默些罢!
今天已不晓得冯秋雪当时受到了什么刺激,心绪似乎很不安宁,令他急欲让自己平静下来。这首诗的情感表达如此强烈且直接,特别是提到要“牠”变作犹太的死海和蒙古的戈壁,形容十分新鲜。
冯秋雪的小诗颇有哲理。如《笔》:
笔对纸说:/“我和你都是给人们役使着呢!/人家对着我们哭和笑,/都不是真的啊!”
此诗借笔对纸的一番话,说明人性的虚伪,同时也点出一切的文字、话语也许都带着欺骗性。如果没有深刻的人生体会,恐怕是写不出这样的作品来的。
此外,《白莲洞杂诗》也值得注意。它由《松》《石》《泉》3首组成,是目前所知的第一首澳门新诗的组诗。全诗如下:
古松傲兀地立在路边,/斜睨着过往的行人。/“行人啊!/你们印出底足迹虽是很多,/然而匆匆就模拟了!” (《松》)
两块太古底大石,/在一个小澄潭上来接吻;/我们立在他俩底吻下,/惹起了无限底美感! (《石》)
滴滴底流泉!/既滴在石上,/又滴到我底心坎里。/经过石上底虽是无限的清,/但不及滴到我心底无限的凉。/流泉啊!/你自择吧! (《泉》)
1927年的冬天,雪社诸人相约同游位于香山吉大乡的白莲洞(今属珠海市)(23)周佩贤(宇雪)有《冬日游吉大乡白莲洞同观如卧雪》(二首),见《雪花——雪社第四集·雪花之外》,第55页。。此处“芳树阴森,饶泉石之胜”(《白莲洞杂诗》自注),冯秋雪意绪袭来,写下了这首既充满情致,而又饱含哲理的组诗。其中,第一首《松》,从松树的角度,质问行人——他们匆匆而重迭足迹,究竟有多少的不一样?第二首《石》写“我们”在小澄潭旁的“太古底大石”下,仿照它们的形态般“接吻”。第三首《泉》写泉水的“无限的清”,滴到我心底的“无限的凉”。这组新诗不仅采用了拟人化的手法,更写到“我/我们”与“物”的对话,反映出冯秋雪藉外物对人事进行思考,颇有一定的思想性。
此外,还有表现冯秋雪和赵连城“闺情”的两首新诗,写得十分生动、形象。如《我愿》:
我愿她做堤边的水,/她愿我做水边的堤;/朝朝暮暮底吻着——/天哪!她怎的不能变做水?/我怎的不能变做堤呢?
又如《看书》:
黄澄澄底灯光,/悄悄地偷进罗帏里。/手执书本的她,/一页一页的展读;/她底媚眼也随着一行一行的下去,/也随着一页一页的翻去。/呵!究竟是她底眼随着一行一页转动呢?/还是一行一页随着牠转动呢?
这类新诗通俗浅白,直接表现了秋雪、连城夫妇的鹣鲽情深;而且细味之下,还会感受到句中清晰的节奏感。毕竟冯秋雪深谙词章之学,精于古典诗词,所以在写作白话诗时,仍会自然而然地把握住句子的节奏。这是新旧文学交替时期的新诗特点之一,胡适的新诗如是,陈独秀的新诗亦如是。
(二)赵连城、冯印雪的新诗
秋雪之妻赵连城,虽然是一位革命女性,深受时代新思潮的影响,但从整体风格看,应属闺阁诗人一类。古典诗词如是,新诗亦如是。如《良夜》:
箫声远远地吹着;/月色低低地照着;/树影沉沉地睡着─/呵!难得底良夜!/可使它和梦各做各的吗?!
虽是新诗,不过仍是旧诗的作法:前三句写景铺垫,最后一句曲终奏雅,略具诗意。另一首《记得甚么?》则显然属于“闺情”诗:
黄昏近了!/悄悄地伏在窗阑上。/那年时底游踪——/一桩一桩的回上心来!/使我永久不会忘记。/记得甚么?/西湾么?北郊么?车厢里底笑声么?
此诗平白如话,诗意不浓,却反映了冯秋雪、赵连城夫妇的生活片断,与上引秋雪诗对读,可见两人感情之深。
至于冯印雪,生于澳门,多才多艺,诗书画兼擅,与高剑父交挚。剑父在佛山创立春睡画院时,聘印雪为秘书。冯印雪在澳门、香港、越南等地从事教育工作数十年,晚年参加澳门美术研究会,曾任副理事长。印雪逝世周年时,挚友黎心斋等辑其遗诗,刘草衣撰《冯印雪传》,刊于澳门《华侨报》以为纪念(24)参见《冯印雪先生逝世周年遗诗选辑》,澳门《华侨报》1965年11月29日。。
冯印雪与兄秋雪一样,性耽吟咏,既嗜古诗,亦尝试新诗的创作。他有一首《小诗》,可以说是作诗的宣言:
沈闷的黑夜过去了,/灿烂的朝阳再来;/我的朋友,准备着你底柔曼的歌声,/歌颂自然。
岭南著名诗人黄节曾评冯印雪的古典诗词“町畦自辟,造境冷峭”(刘草衣《冯印雪传》),而新诗则清新可诵。如《梧桐》:
撑着伞似的绿叶——/在热烈的太阳底下,/布置清润的绿荫,/表现牠的人格。
诗人用拟人手法,将树荫说成梧桐树主动“布置”的,以此显示其为众生造福的“人格”,诗短意深。又如《天籁》:
人们睡了,/幽悄底雨声依旧点滴着;/你休要嗔恨,/天籁不是给一般人们颂赞的啊!
这些新诗已经比较成熟,可见冯印雪的文学修养较深,无论旧诗新诗,同样得心应手。
总之,冯秋雪、赵连城和冯印雪的新诗,数量虽然不多,但已达到了一定的水平,而且各人的作品亦呈现不同的面貌。这恐怕与他们的旧体诗词修养有一定的关系,可见澳门的早期新诗并不完全与旧体文学绝缘,甚或可以说,它们与旧体诗词带有一定的内在联系。
三、冯秋雪等人与新文学运动的关系
民国初年冯秋雪等人创作了澳门历史上的第一批新诗,然而他们的这种尝试属于独立自发的呢?还是受到外来的影响,尤其是与当时中国内地的新文学运动关系究竟又是如何的呢?冯秋雪虽然居住在澳门,但时常往来穗澳两地,与内地关系甚为密切,不仅很容易接触到新文学运动的信息,而且的确也曾对新文学运动发表过的意见。冯秋雪曾藉评说胡适《沁园春·誓诗》,对新文学运动表达了一些个人的看法:
挽近文学革新之声浪,愈唱愈高,此世界潮流之趋势,无可抑制也。而提倡者,每矫枉过正,余窃病之。尝于某报,见胡适《沁园春》云:“更不伤春,更不悲秋,以此誓诗。任花开也好,花飞也好,月圆固好,月落何悲?我闻之曰,‘从天而颂,孰与制天而闭之?’更安用,为苍天歌哭,作彼奴为!文章革命何疑!且准备搴旗作健儿。要前空千古,下开百世,收他臭腐,还我神奇。为大中华,造新文学,此业吾曹欲让谁?诗材料,有簇新世界,供我驱驰。”此词上半阕,余颇不谓然。夫花何其好,月何其明,春何其丽,秋何其清。景物自景物人自人,惟吾人对之起哀伤愉快者,以所处境而定。人负景物,非景物负人,更非景物奴人……夫触物兴感,人之常情,否则,寡情者也。寡情之人,天性必凉薄,天性凉薄得谓之人乎?胡君见之,当韪余言。至换头以下,吾无间然。或曰:是达观语也,子何不察耶?曰:达观者,伤心之极致也。愈作达观语,越是伤心无可奈何者。虽然此语我不许,他人藉口代胡君辩护,胡君想亦不如是。盖胡君张主奋斗进取之人也。主进取者,乐观派也。既乐观,则怀旧、幽忧、哀怨种种无由成立;而达观者,则斯种种之结果也。胡君既无是种种,则达观何由而生;达观之念不生,则斯言又何为而发?质之胡君,应亦哑失笑曰:孺子可教也。(25)秋雪:《水佩风裳室笔记》(卅四),《诗声》第4卷第6号,1919年7月12日,第5—6页。
首先,在上文中,冯秋雪表示不同意胡适《沁园春·誓诗》上阕的作意,以为“触物兴感,人之常情”,故此“人负景物,非景物负人,更非景物奴人”,所以反对胡适所谓“更安用,为苍天歌哭,作彼奴为”的“矫枉过正”之病。其实词中的“景物”,是借指束缚中国文学的旧有思想(26)胡适在《尝试集自序》中说:“这首词上半所攻击的是中国文学‘无病而呻’的恶习惯。我是主张乐观,主张进取的人,故极力攻击这种卑弱的根性。”《胡适文集》第9册《尝试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75页。,而非单纯客观世界的“景物”,秋雪颇有郢书燕说之嫌。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胡适的《沁园春·誓诗》写于1916年4月13日,后载于1917年3月《留美学生季报》春季第1号(27)胡适:《尝试集》附录《去国集》,《胡适文集》第9册《尝试集》,第223页。。其时他与友朋讨论改良中国文学的方法,意兴正浓(28)详参胡适《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见《胡适文集》第1册《中国新文学运动小史》,第148—149页。。《尝试集自序》称它“其实是一篇文学革命宣言书”(29)胡适:《尝试集自序》,《胡适文集》第9册《尝试集》,第74页。,可见其于新文学运动上的地位。而从文中对胡适“乐观”“进取”精神的评说,可以推测冯秋雪所看到的“某报”,应是《新青年》第6卷第5号(1919年5月),上即载有胡适《尝试集自序》。由此足以证明,冯秋雪十分注意新文学运动的情况,并很可能读过胡适《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文学革命论》等新文学运动檄文;而在读到《尝试集自序》时,意有所感,遂写下了这篇“笔记”,发表于1919年7月12日出版的《诗声》第4卷第6号。
其次,冯秋雪肯定文学革新是“世界潮流之趋势”,无可阻挡,且对胡适“为大中华,造新文学,此业吾曹欲让谁”的呼唤表示认同(“吾无间然”)。这不仅与冯秋雪等人积极进步的政治主张和革命活动有着思想上的内在关联,也与他们当时在澳门热切追求各种新的文化思想相一致。如在民国三年(1914),世界语会会员钟宝琦(侠隐)来澳门宣传,发起世界语(Esperanto)夏令讲习所。秋雪即往学习,并称钟宝琦为“传播斯语于澳门之第一人,予亦为澳门世界语学者第一人。以沉沉长夜之镜湖而此一瞥之电光,虽转瞬即渺然亦足自豪矣”(30)秋雪:《水佩风裳室杂乘》(三),《诗声》第1卷第4号,1915年10月1日,第4—5页。。此外,冯秋雪又多次请钟宝琦为宋人姜白石的《齐天乐·蟋蟀》、黄雪舟的《湘春夜月》、苏轼的《念奴娇》《水调歌头》、李清照的《声声慢》等词制作西式乐谱(31)详见《诗声》第1卷第5号,1915年11月1日,第7—8页;《诗声》第1卷第6号,1915年12月1日,第7—8页;《诗声》第2卷第1号,1916年7月1日,第5—6页;《诗声》第2卷第5号,1916年11月1日,第6—7页;《诗声》第4卷第3号,1919年4月15日,第9—10页。,可见他们洋溢着以新的形式来改良中国传统文学的热情。冯秋雪的思想和行动“时时站在时代的前面”,“是一个理智充实的改革者”,“很相信社会蜕进的结果”(古畸《绿叶的序》);因此他在写下这篇“笔记”后不久,即创作了澳门的第一首新诗《纸鸢》,切实地响应了胡适所倡导的新文学运动。不仅如此,秋雪还结集弟弟、妻子,不断尝试,创作出澳门最早的一批新诗作品,从而成为了澳门新文学的“弄潮儿”。
四、关于澳门早期新诗的思考
冯秋雪等人的新诗创作从1920年至1928年,前后约维持了八年的时间,共得13题16首,成果不算丰厚,而且目前也未发现他们此后有其他的新诗作品。这就形成了澳门早期新文学史上一个颇值得引起思考的现象,即澳门作家受到胡适等人的影响,在新文学运动的最初十年内,开始尝试创作新诗,并取得一定的成果,但却浅尝辄止,没有坚持下去,更没有形成风气。
对于这个现象不妨从澳门当时的文学环境以及冯秋雪等人的文学观念进行分析。民国初年,澳门文坛主要由汪兆镛、吴道镕、张学华等一批清遗民诗人以及冯秋雪等本土文人所构成。前者成长于清季,思想上比较守旧,主要以古典诗词为创作手段。而在“雪堂”和“雪社”中,除秋雪三人外,其他各人均没有包括新诗在内的新文学作品;就算稍后的30年代,由高剑父、黎泽闿、张百英、张纯初、周贯明等革命志士组成的“清游会”开始在澳门活动,也同样是以创作古典诗词为主。这就意味着当时澳门无论新旧文人,皆以传统形式从事文学创作。另一方面,当时澳门没有出版稳定的文学刊物(《诗声》是一个异数,故此广受重视),而报纸副刊也只刊登杂文、小说,或者古典诗词之类较受一般读者欢迎的作品。因此说民国初年的澳门文坛基本上还是旧文学的天下,应该是符合事实的。在这样的文学环境下,冯秋雪等人勇于打破局面,追上文学潮流,尝试新的文学形式,无疑更加值得肯定。不过,孤军作战,缺乏同道的支援,互相讨论的促进,使得新诗创作仅仅是他们家庭成员之间的一种文学实验,因而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澳门新文学的进一步发展。
更为重要的问题是,冯秋雪等人受到自身的文学观念所制约。他们创立雪堂诗社,主要是针对当时“诗学寖微,风俗人心亦随之而日下,徒欣欧化,敝屣宗邦,而吾四千年之国粹,竟胥沦于冥冥中”;而出版《诗声》亦以“专究诗词,并征佳什以维国粹,庶免诗亡”(32)《雪堂求助小启》,《诗声》第2卷第2号,1916年8月1日,第11—12页。为宗旨。至于重组“雪社”,仍在于“提倡风雅”(黄沛功《雪社第一集·叙》),可见冯秋雪等毕竟是旧学出身之人,对于古典诗词有着深刻的缱绻,无法也无力完全割舍;而从事新文学活动,只是他们追求进步思想的一个方面,而且不是主要方面。与此同时,冯秋雪等人虽然向往新的文学形式,但受新文化思想的熏染不深,徘徊于新旧之际,思想上不免时有矛盾。赵连城的新诗《人们底慈母》颇能反映出这种心理状态:“科学!是自然底仇敌!/自然!是人们底慈母!/慈母啊!我愿永久的躺在你底摇篮里。”崇尚自然与科学精神本无冲突,赵连城却将它们对立起来,歌颂“慈母”以抗“仇敌”,可见其于新文化的认识还是比较肤浅的。
最后,不能忽略的是,冯秋雪等人基本上没有西方文学的素养,他们所创作的新诗虽然不是胡适的“白话词调诗”(33)许霆:《中国新诗发生论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87—289页。,但还是有比较浓烈的古诗气息。困于传统文学的惯用手段和指导思想,缺少西方文学的滋养和冲击,使得冯秋雪等人难以建立起新的文学观,因而导致新诗创作裹足不前,后继乏力。反观稍后出生于澳门的华铃(原名冯锦钊,1915—1992),1930年在广州知用中学读书时开始创作新诗,1935年入读上海之江大学,同年转至复旦大学外文系,师从李健吾,其后出版《向日葵》《玫瑰》《牵牛花》《满天星》等新诗集(34)华铃:《向日葵》,上海:五洲书报社,1938年;华铃:《玫瑰》,上海:五洲书报社,1938年;华铃:《牵牛花》,上海:五洲书报社,1939年;华铃:《满天星》,上海:五洲书报社,1939年。,孙玉石将其诗作归为象征派、现代派作品(35)孙玉石:《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04页。。华铃又写作了不少抗战诗,被郑振铎誉为上海“孤岛”文学时期中的“时代的号角”(36)参见傅玉兰《时代的号角——诗人华铃的生命乐章》,澳门: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2016年。。当然,时代造就了华铃,但是西方文学的修养,师友的鼓励,对华铃的新诗创作所起的作用不容忽视,而这一切却正是当时冯秋雪等人所最欠缺的。以上几点,或可解释为什么冯秋雪等人在出版了包括新诗作品在内的《绿叶》之后,就再没有其他的新文学创作了。
澳门的新诗作品,继冯秋雪等人之后,直到30年代末才开始再次零星地出现在澳门的一些刊物或文集之中(撇除上述华铃的作品不算)(37)参见吕志鹏《澳门中文新诗发展史研究(1938—2008)》,第41—45页。,这与冯秋雪他们的创作已经相距十多二十年了。因此,就形成了澳门新诗史上发轫早,起点高,中经停顿,再次起步的曲折过程。虽然如此,冯秋雪等人在澳门响应新文学运动的潮流,创作了澳门文学史上的第一批新诗作品,开启了澳门新文学的局面。虽然受制于外部的文学环境以及个人的文学观念,冯秋雪等人的新诗创作未能取得更高的成就,但是他们勇于开拓新的文学世界,故此在澳门文学史上的功绩不应湮没无闻,而是需要充分揭示和高度赞扬。
结 语
早在20世纪20年代,澳门已经出现了第一批水平不俗的新诗作品(包括第一首新诗《纸鸢》、第一首新诗组诗《白莲洞杂诗》、第一部新诗合集《绿叶》)以及第一个关系密切的新诗作者群。这不仅纠正了学术界过往对澳门新诗发轫的认识,使澳门早期新文学的面貌清晰地呈现出来;更加可以反映出在新文学运动的最初十年,澳门文坛对它的接受和响应,加深了解新文学运动在各地扩散和影响的一些具体情况。另一方面,由于澳门新诗的出现和发展,主要是基于外来的文学影响,而缺乏自身的文学土壤和文学环境,所以虽然出现较早,却是电光一闪,随即停顿。因此,从总体发展而言,冯秋雪等人的新诗创作在澳门新文学史上呈现出来的现象,正好说明文学发展的一个规律,即缺乏充足的内部主客观动因(这里包括诗人的个人素养和具体的文学环境),外来力量的作用往往只能是短暂而不可持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