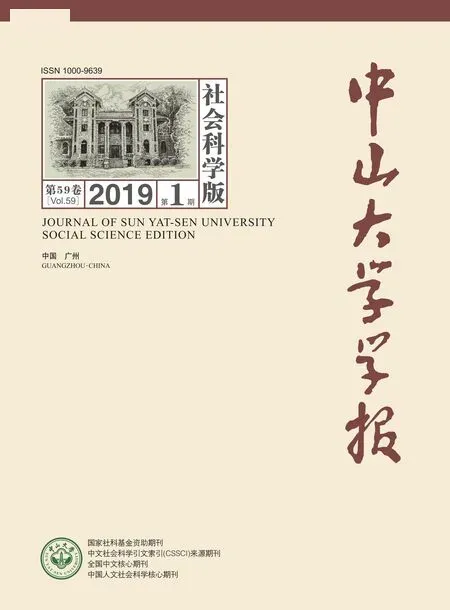科学思维的局限性与“诗话”批评的复兴*
2019-01-06龚刚
龚 刚
诗话是一种“片段性”的文学批评形态,它为唐以来历代学人所习用,但在近现代中国学术的发展进程中,已逐渐绝迹。和札记体著述一样,诗话也往往是若干没有直接关联或逻辑联系的知识片段的连缀,因此,诗话也可以说是一种札记体的文学批评形态。其具体特征为结构比较松散,内容比较驳杂,行文也比较散漫,作者的种种玄思妙想、审美感悟以至美学趣味、生活情趣也因而得以较本真地呈现。这也就是诗话何以更贴近人的生命体验、更贴近所考察作品、更具文学性和可读性的原因。笔者注意到,钱锺书在肯定“片段思想”的价值时,对诗话的特征作了点评,他说:“我们孜孜阅读的诗话、文论之类,未必都说得上有什么理论系统。”①钱锺书:《读〈拉奥孔〉》,《七缀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33—34页。由此可见,诗话的日趋绝迹,可以说是近现代中国学人渐重理论系统和周密思想的研究取向在文艺研究领域的直接体现。
那么,诗话这种文学批评形态是否还有复兴的可能和必要呢?笔者对此持肯定的态度。首先,纵观20世纪以来的文艺研究,有计划、有步骤、逻辑严密的科学主义研究模式日益占据主流地位。它固然使我们对文艺问题的思考更周到、更全面,但由于科学化研究模式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排斥感性与偶然性,因此,中国传统文学批评模式如诗话体以及评点体所显示出的即兴而发或有感而发的偶发性与性灵化特征便受到抑制。这一方面使当前的文艺研究由于过分追求科学主义规范而显露出程式化的倾向,另一方面又使崇尚兴会妙悟的文学批评方式得不到相应的重视。本文以钱锺书对神秘主义思维的辩护为切入点,探讨了艺术与科学以及审美批评与科学研究在思维方式上的区别,提出了复兴诗话体批评的构想。
一、“还乡隐喻”与神秘主义思维
钱锺书指出,思维科学的探讨者一向呼吁人们重视“图像思维法”的危险性和推理过程中对隐喻及类比的滥用。在他们看来,在诗歌中运用比喻是正当的,但对哲学而言,比较是非理性的思维模式,因此,“隐喻式推论(inference by metaphor)的有效性是相当可疑的”①钱锺书著,龚刚译:《还乡隐喻与哲性乡愁》,《跨文化对话》第15辑,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4年,第45,46,46,47,48,48,49,49,49,49,50,51页。。钱锺书举例说,古时的佛教智者虽然热衷于运用比喻与寓言,却劝谕世人慎用隐喻式推理,例如,《大般涅槃经》《翻译名义集》中质疑“面貌端正,如月盛满”“白象鲜洁,犹如雪山”这两个比喻说:“满月不可即同于面,雪山不可即是白象。雪山比象,安责尾牙,满月况面,岂有眉目?”②钱锺书著,龚刚译:《还乡隐喻与哲性乡愁》,《跨文化对话》第15辑,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4年,第45,46,46,47,48,48,49,49,49,49,50,51页。
钱锺书对佛教智者的劝谕不以为然,他指出,在最朴素的语言中也充斥着“亡隐喻”,且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创造隐喻的能力”是诗人创造力的最确凿标志③[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撰,陈中梅译注:《诗学》第22章,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58页。亚里士多德在这一章探讨了如何营造明晰而华丽的“言语的美”,钱锺书所引述观点的原话为:“最重要的是要善于使用隐喻词。唯独在这点上,诗家不能领教于人;不仅如此,善于使用隐喻还是有天赋的一个标志,因为若想编出好的隐喻,就必先看出事物间可资借喻的相似之处。”。他又认为,在所有哲学家中,惟有神秘主义者拥有以丰富的比喻进行言说的权利,因为其不可名状的经验无法以简明的语言加以表达。他宣称,在阅读中国神秘主义者的著述时,发现了一个堪称所有道家及禅宗说教之核心的隐喻,即漫游者回归故土的隐喻,也即“还乡隐喻”(the metaphor of returning home)④钱锺书著,龚刚译:《还乡隐喻与哲性乡愁》,《跨文化对话》第15辑,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4年,第45,46,46,47,48,48,49,49,49,49,50,51页。。这一隐喻是以“还乡”或“乡愁”暗示人类对本质真实的直觉、回归,或掌握本质真实的愿望。钱锺书指出,在中国神秘主义的框架内,对本质真实或绝对真理的直觉可以比之于沿着神秘主义者所共知的虚无之路返回家中。而掌握本质真实的愿望,正是一种身在他乡的故园之思⑤钱锺书著,龚刚译:《还乡隐喻与哲性乡愁》,《跨文化对话》第15辑,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4年,第45,46,46,47,48,48,49,49,49,49,50,51页。。例如,庄子所谓“旧国旧都,望之畅然”⑥钱锺书著,龚刚译:《还乡隐喻与哲性乡愁》,《跨文化对话》第15辑,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4年,第45,46,46,47,48,48,49,49,49,49,50,51页。,即是以“旧国旧都”比拟人性的原初或本真状态,而见性之乐,正如得旧之乐。在庄子笔下的“云将东游”与“鸿蒙”的对话中,后者劝说前者返归故土,“仙仙乎归矣,各复其根,各复其根而不知,浑浑沌沌”⑦钱锺书著,龚刚译:《还乡隐喻与哲性乡愁》,《跨文化对话》第15辑,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4年,第45,46,46,47,48,48,49,49,49,49,50,51页。,也是以“还乡”作为回归本真状态的隐喻。
钱锺书指出,时至唐代,“还乡隐喻”逐渐从哲学术语(philosophical terminology)演变为诗歌词藻(poetic diction)。唐代诗人中最精于禅宗思想的白居易对此极为偏好。在他的诗中,“身心安处为吾土,岂限长安与洛阳”(《吾土》)、“我生本无乡,心安是归处”(《出城留别》)之类诗句反复出现⑧钱锺书著,龚刚译:《还乡隐喻与哲性乡愁》,《跨文化对话》第15辑,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4年,第45,46,46,47,48,48,49,49,49,49,50,51页。。钱锺书认为,这些措辞会令人联想起古罗马诗人巴库维乌斯所谓“美土即吾乡”,但它们所体现的显然是佛教徒式的情感,例如北宋文学家、思想家晁迥在描述其神秘体验时比喻说:“栖心栖神栖真栖禅”,“如鸟之栖宿。”⑨钱锺书著,龚刚译:《还乡隐喻与哲性乡愁》,《跨文化对话》第15辑,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4年,第45,46,46,47,48,48,49,49,49,49,50,51页。
显然,在晁迥看来,灵魂的休憩即是回到本真,如倦鸟归巢。北宋理学家陈瓘则认为,真正的哲人当能发现其精神家园,生时即可栖居,他评价列子的以“鬼”为“归”之说云:“何待死为归乎?其生也心归,其死也形化。”⑩钱锺书著,龚 刚译:《还乡隐 喻与哲性乡愁》 ,《跨文化对 话》第15辑, 上海:上海文化 出版社,2004年,第45,46,46,47,48,48,49,49,49,49,50,51页。南宋初期理学家胡寅也认同“生也心归”之说,他批驳《楞严经》中的“行客”之喻说:“心欲遽止焉,又不安也。夫托乎逆旅者,不得家居之安也。未有既安于家而又乐舍于旅也。”⑪锺书著,龚刚译:《还乡隐喻与哲性乡愁》,《跨文化对话》第15辑,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4年,第45,46,46,47,48,48,49,49,49,49,50,51页。钱锺书指出,对一个确信道、菩提心或神意无所不在的虔诚的神秘主义者来说,他可以歇在此处,彼处,任何去处,四海为家。如果有人问:“家在何处?”(Where is your home?)他会回答说:“何处非吾家?”(Where is not my home?)⑫钱锺书著,龚刚译:《还乡隐喻与哲性乡愁》,《跨文化对话》第15辑,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4年,第45,46,46,47,48,48,49,49,49,49,50,51页。
在探讨了“还乡隐喻”的内涵(即人类对本质真实的直觉、回归,或掌握本质真实的愿望)之后,钱锺书随后以人类的普遍心理及神秘主义思维为考察对象,论证了“还乡隐喻”的恰切性。他指出,还乡既是休歇,也是复归。人类所有心理活动的目的都是终止心理活动,从而使受怀疑、悔恨、困境、疑难所破坏或困扰的精神恢复稳定或平衡。心灵厌恶令人烦扰和忧心的不确定性的程度不亚于本性之厌恶虚空;每一次从固定状态出发的漫游都包含着回归的意向。难题要么被解决,要么被舍弃,欲望要么得到满足,要么被压抑。提出问题的目的就是等待回答,也即是期望不再成为问题⑬钱锺书著,龚刚译:《还乡隐喻与哲性乡愁》,《跨文化对话》第15辑,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4年,第45,46,46,47,48,48,49,49,49,49,50,51页。。中国哲学每每将心的本体(mind-in-itself)比作“止水”(still water),庄子是开风气者。考虑到人体机能维护或恢复受不安或焦虑搅扰的固定状态的根本倾向,庄子所作的比附其实并不离奇。此外,这一倾向也表明,“止水”一词与心理学所谓“意识流”并不相悖。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在提出“河或水流是人类精神生活的最佳隐喻”这一观点的同时也指出,意识在流动的过程中也会有“休歇处”或“相对静止的阶段”,也就是在得出“确实结论”的时候①William James:The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Vol.Ⅰ,p.243,New Yor k:Henry Holt,1890.。由此可见,人类的精神总是在不安地追求安定,永不止歇地寻找休歇处。在永不停息的思想发展过程中,任何休歇处都是不易而易的,当视其为精神臻于完足之境的特定点时,它就是不易的。钱锺书总结说,“一切有目标的思考”都可以在情感层面被喻为一种“乡愁”,也就是寻求归宿的冲动②钱锺书著,龚刚译:《还乡隐喻与哲性乡愁》,《跨文化对话》第15辑,第52,53,53,53,53,54页。。这就从人类普遍心理的层面印证了“还乡隐喻”的恰切性。
钱锺书又从神秘主义思维取向的角度论证,中国神秘主义者不同于基督教神秘主义者,他们是在本心中发现本质真实或绝对真理③钱锺书著,龚刚译:《还乡隐喻与哲性乡愁》,《跨文化对话》第15辑,第52,5353334页。。老子告诫其门徒“不出户”,因为“其出愈远,其知愈少”④钱锺书著,龚刚译:《还乡隐喻与哲性乡愁》,《跨文化对话》第15辑,第52,53,53,535354页。。庄子以寓言的方式暗示远游求道反会迷真丧道:“黄帝游乎赤水之北,登乎昆仑之丘,而南望还归,遗其玄珠。”⑤钱锺书著,龚刚译:《还乡隐喻与哲性乡愁》列子的说法是:“务外游不知务内观。外游者求备于物;内观者取足于身。取足于身,游之至也;求备于物,游之不至也。”⑥钱锺书著,龚刚译:《换言之,对中国神秘主义者而言,智慧是回到你自己。用普罗提诺(Plotinus)的话来说:“灵魂的自然运动不是直线式的……相反,它是围绕某个内在的事物,某个中心而周行的。而灵魂周行所围绕的中心正是灵魂自身。”⑦Plotinos:Complete Wor ks,edit.by K.S.Guthrie,Vol.Ⅰ,p.163,Alpine(N.J.,USA):Co mparative Literature Press,1918.(笔者按:Plotinos即Plutinus,钱锺书所引段落,见美国学者Guthrie所编《普罗提诺全集》卷一“依附中心以成神性”一节)钱锺书指出,心智活动的这种“终始若环”的特性,使“还乡之喻”特别切合道家、禅宗及其印度和希腊同道的神秘主义感悟⑧钱锺书著,龚刚译:《还乡隐喻与哲性乡愁》,《跨文化对话》第15辑,第52,53,53,53,53,54页。。
综上所述,中国神秘主义著述中的“还乡隐喻”不仅彰显了中国神秘主义“务内观”、求诸本心的思维取向,也深刻揭示了人类的普遍心理(“人类所有心理活动的目的都是终止心理活动”)与思维的本质(“一切有目标的思考”都是哲性“乡愁”)。这就证明了隐喻思维作为神秘主义思维方式在本质直观中的有效性,也因而证明了至少在涉及人类的直觉、心性的人文学思考中(包括形而上学、文艺美学等),不应摒弃神秘主义而独尊科学主义。
二、“超科学”的求真途径与“美术之知”的价值
1923年2月14日,身为哲学家的张君劢在清华大学作了题为“人生观”的演讲,对科学主义“科学万能”的思想倾向提出批评。这篇演讲词随之发表于《清华周刊》。张君劢的朋友、地质学家丁文江随后发表长文《玄学与科学──评张君劢的〈人生观〉》,对张君劢的观点加以全面批驳,由此引发了长达两年的科玄论战。
张君劢指出:“科学无论如何发达,而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惟赖诸人类之自身而已”;“盖人生观,既无客观标准,故惟有返求之于己。”他又从方法论的角度指出:“科学为论理的方法(即逻辑的方法——笔者按)所支配,而人生观则起于直觉。”⑨张君劢:《人生观》,张君劢等:《科学与人生观》,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2、35页。丁文江批驳说:“张君劢的人生观,一部分是从玄学大家柏格森化出来的”,“西洋的玄学鬼到了中国,又联合了陆象山、王阳明、陈白沙高谈心性的一班朋友的魂灵,一齐钻进了张君劢的‘我’里面。”在他看来,“科学未尝不注重个性直觉,但是科学所承认的个性直觉,是‘根据于经验的暗示,从活经验里涌出来的’”⑩丁文江:《玄学与科学──评张君劢的〈人生观〉》,张君劢等:《科学与人生观》,第46—48页。。张君劢随即撰写了反批评的文章《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他在文中指出:“科学方法非达于真理之惟一途径”,“除学问上之知识外,尚有宗教美术亦为求真之途径。”所以,除科学之知外,还有艺术方面的“美术之知”,宗教方面的“道德之知”,尤其是哲学的“形上界之知”。因此,“科学决不能支配人生,乃不能不舍科学而别求一种解释于哲学或玄学中(或曰形上学)”①张君劢:《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张君劢等:《科学与人生观》,第89、94页。。由此可见,张君劢所谓“玄学”,即指哲学中的形而上学。
梁启超对科玄双方都提出了批评,他说:“在君(即丁文江,在君是他的字——笔者按)过信科学万能,正和君劢之轻蔑科学同一错误”,因为“人生关涉理智方面的事项,绝对要用科学方法来解决。关于情感方面的事项,绝对的超科学。”他指出:“生活的原动力,就是‘情感’。情感表出来的方向很多。内中最少有两件的的确确带有神秘性的,就是‘爱’和‘美’。‘科学帝国’的版图和威权无论扩大到什么程度,这位‘爱先生’和那位‘美先生’依然永远保持他们那种‘上不臣天子下不友诸侯’的身分……一部人类活历史,却十有九从这种神秘中创造出来。”②梁启超:《人生观与科学——对于张丁论战的批评》,张君劢等:《科学与人生观》,第128—130页。
由于张君劢以 “宗教美术”为科学之外的“求真途径 ”,并以“美术之知”区别于科学之知(尤其是重逻辑、重实证的自然科学之知),因此,科玄论争就不仅局限于科学与哲学(尤其是形而上学)的对立冲突,还触及审美活动(包括美学、文艺批评等)与科学思维的对立。在梁启超看来,作为情感表现的“美”,具有超越“科学帝国”的“神秘性”。这种“神秘性”当和被张君劢视为人生观来源的“直觉”相关,也和灵感、悟性、诗化想象等审美领域中确实存在却又无法用实证科学加以明确解释的因素有关。如前所述,隐喻思维是神秘主义者本质直观的重要方式,而“丰富的比喻”(包括“隐喻”)是神秘主义者表达其“不可名状的经验”的重要方式。这种带有“神秘性”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在审美研究尤其是在美学风格的品评和艺术境界的感悟方面,也具有重要价值。现代诗评家缪钺评论唐宋诗之别的如下文字,即是明证:
唐诗以韵胜,故浑雅,而贵蕴藉空灵;宋诗以意胜,故精能,而贵深折透辟。唐诗之美在情辞,故丰腴;宋诗之美在气骨,故瘦劲。唐诗如芍药海棠,秋华繁采;宋诗如寒梅秋菊,幽韵冷香。唐诗如啖荔枝,一颗入口,则甘芳盈颊;宋诗如食橄榄,初觉生涩,而回味隽永。③缪钺:《论宋诗》,《诗词散论》,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1页。
这一篇诗话式的评论中,有直觉,有悟性,有灵感,有想象,更有丰富而传神的比喻,是典型的“美术之知”。不过,若论“隐喻推理”之妙,当推原署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仅拈“典雅”为例:
玉壶买春,赏雨茅屋。坐中佳士,左右修竹。白云初晴,幽鸟相逐。眠琴绿阴,上有飞瀑。落花无言,人淡如菊。书之岁华,其曰可读。④乔力:《二十四诗品探微》,济南:齐鲁书社,1983年,第29页。
钱锺书在批评王国维未能深刻领会叔本华哲学,因而把《红楼梦》误判为“悲剧之悲剧”的评论文字中,也运用了隐喻思维和诗化想象:
苟尽其道而彻其理,则当知木石因缘,侥幸成就,喜将变忧,佳耦始者或以怨耦终;遥闻声而相思相慕,习进前而渐疏渐厌,花红初无几日,月满不得连宵,好事徒成虚话,含饴还同嚼蜡。⑤钱锺书:《谈艺录》(补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349页。
朱光潜以为:“中国向来只有诗话而无诗学……诗话大半是偶感随笔,信手拈来,片言中肯,简炼亲切,是其所长;但是它的短处在零乱琐碎,不成系统,有时偏重主观,有时过信传统,缺乏科学的精神和方法。”⑥朱光潜:《诗论抗战版序》,《朱光潜美学文集》第二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第3页。此说显然是从科学思维的角度揭示诗话的“短处”。问题是,“美术之知”与“科学之知”,确有区别,是否应将梁启超所谓“美先生”纳入以精密逻辑、客观实证为尚的“科学帝国”,尚可存疑。至于诗话的“不成体系”之弊,钱锺书已深刻指出:“诗、词、随笔里,小说、戏曲里,乃至谣谚和训诂里,往往无意中三言两语,说出了精辟的见解,益入神智;把它们演绎出来,对文艺理论很有贡献”,而“许多严密周全的思想和哲学系统经不起时间的推排销蚀,在整体上都垮塌了,但是它们的一些个别见解还为后世所采取而未失去时效。”①钱锺书:《读〈拉奥孔〉》,《七缀集》,第33—34页。质言之,审美批评不应迷信理论系统,而排斥片言居要的妙悟和灵光一闪的洞见。
不过,朱光潜对诗话之长所作的点评,却从批评动机(“偶感随笔”,也即乘兴而为)、批评状态(“信手拈来”,也即主观随性)与批评风格(“片言中肯,简炼亲切”)等三个方面揭示了兴会妙悟式的“美术之知”的特点,也当得起“片言中肯,简炼亲切”这八个字。
三、对“机械主义”的反抗与诗话体的复兴
徐志摩在《汤麦司哈代的诗》一文中指出:
艺术不是科学,精采不在他的结论,或是证明什么;艺术不是逻辑。在艺术里,题材也许有限,但运用的方法各各的不同;不论表现方法是什么,不问“主义”是什么,艺术作品成功的秘密就在能够满足他那特定形式本体所要求满足的条件,产生一个整个的完全的,独一的审美的印象。②徐志摩:《汤麦司哈代的诗》,梁实秋、蒋复璁编:《徐志摩全集》第六卷,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第90—91页。
显而易见,徐志摩与张君劢、梁启超等人一样,反对将艺术等同于科学和逻辑。在徐志摩看来,艺术作品成功的秘密在于产生“独一的审美印象”,这种“审美印象”需要读者亲自去感知,而不能由批评家代劳,也不能被先入为主的“主义”所框限。与此相呼应,在文学批评与鉴赏层面,他高度推崇个性化的整体领悟,而不是科学化的机械分析③徐志摩在评论济慈的《夜莺歌》时自谦说:“我只是在课堂里讲书的态度,按句按段的讲下去就是;至于整体的领悟还得靠你们自己,我是不能帮忙的。”(徐志摩:《济慈的〈夜莺歌〉》,梁实秋、蒋复璁编:《徐志摩全集》第三卷,第124页)。他认为:
能完全领略一首诗或是一篇戏曲,是一个精神的快乐,一个不期然的发现。④徐志摩:《济慈的〈夜莺歌〉》,梁实秋、蒋复璁编:《徐志摩全集》第三卷,第123页。
从思想渊源来看,徐志摩的反科学主义立场明显受到了罗素的影响。1923年初,徐志摩翻译、发表了罗素《教育里的自由——反抗机械主义》一文,在译者序中,他写道:“(罗素)所主张的简单一句话,是心灵的自由,他所最恨最厌恶的是思想之奴缚。他所以无条件的反对机械主义,反对科学主义之流弊。”⑤见徐志摩为罗素《教育里的自由——反抗机械主义》所作译序,赵遐秋、曾庆瑞、潘百生编:《徐志摩全集》第三卷,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1年,第321页。徐志摩在《唈死木死》一文中发挥罗素的观点指出:
人类共有的艺术,那是人类性灵活动的成绩,凡是受过教育的人们应得有至低限度的了解与会悟,因为只有在性灵生活普遍的活动的平面上,一民族的文化方才有向前进步的希望。⑥徐志摩:《唈死木死》,顾永棣编:《徐志摩全集散文卷》,杭州:浙江出版联合集团、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89—290页。
笔者以为,徐志摩的反机械主义的批评理论和性灵化的批评实践提示了一种注重“性灵”与“会悟”的富有生命力的批评方式⑦详见拙文《中国现代诗学中的性灵派——论徐志摩的诗学思想和诗论风格》,《现代中文学刊》2017年第1期。。所谓“会悟”,亦即中国古代文论所谓“兴会”“妙悟”,是心灵和心灵的对话,是性灵和性灵的感通。对照传统的诗话体、评点体批评与徐志摩所提倡的性灵化批评可以看到,两者在本质上是相通的,均与张君劢所谓“美术之知”相契合。
作为札记体的文学批评形态,诗话的结构比较松散,内容比较驳杂,行文也比较散漫,作者的种种玄思妙想、审美感悟以至美学趣味、生活情趣也因而得以较本真地呈现,这也就是诗话何以更贴近人的生命体验、更贴近所考察作品、更具“文学性”和“可读性”的原因。相对于文艺研究领域中所涌现的种种“理论系统”和“历史系统”而言,诗话或评点体著述显然更注重钱锺书所谓“具体的文艺鉴赏和评判”⑧钱锺书:《中国诗与中国画》,《七缀集》,第7,3页。。而注重“具体的文艺鉴赏和评判”,归根结底,就是注重文本分析和审美评价。这对于文艺研究领域而言,本是题中应有之义。但由于不少“文学概论”或“文学史”的作者,或沉湎于纯理论的思考而轻忽了文艺创作的实践,或热衷于“宏大叙事”而荒疏了文本细读的功夫,因此,强调“具体的鉴赏和评判”,就显得很有针对性和迫切性了。钱锺书曾描述过那些缺乏具体分析意识的文学批评家的特征:
旧传统里若干复杂问题,新的批评家也许并非不屑注意,而是根本没想到它们一度存在过。他的眼界空旷,没有枝节零乱的障碍物来扰乱视线;比起他这样高瞰远瞩,旧的批评家未免见树不见林了。不过,无独必有偶,另一个偏差是见林而不见树。局外人也就是门外汉,他的意见,仿佛“清官判断家务事”,有条有理,而对于委曲私情,终不能体贴入微。②钱锺书:《中国诗与中国画》,《七缀集》,第7,3页。
如果说,那些一味拘执于“零乱枝节”而缺乏“高瞰远瞩”的理论视野和历史眼光的批评家,未免有“见树不见林”之嫌,那么,那些缺乏具体分析意识的批评家,便难免“见林不见树”之讥。笔者以为,恢复传统的诗话体以及评点体,将有助于克服文艺研究领域存在的“见林不见树”之弊。因为,诗话体“摘句为评”的传统和评点体“随文而作”的特性,无不体现出对文本分析和细部分析的重视,因而能对作品的“委曲私情”也即为文奥妙有“体贴入微”的感悟,而不至于沦为“门外汉”式的解读。
其实,早在上世纪60年代,著名戏剧家丁西林就已开始提倡恢复评点体。他多次倡导“由前辈剧作家、剧评家每人选一篇话剧名著,不分古今中外,加上观点、立场正确的金圣叹式的批语和解释”③钱理群:《名作重读》,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33,133页。。他还亲自作了示范性的试验:译批了英国著名剧作家巴蕾(James Mathew Barrie)的独幕剧《十二镑钱的神情》。但由于后来无人响应,此项倡议也就被搁置下来。直到改革开放后的新时期,才有学者重拾丁西林的话题,对恢复评点体的现实意义(如有助于克服“空疏学风”等)给予了肯定。这位学者还承丁西林之余绪,完成了对丁西林作品《酒后》与《压迫》二剧的“批注”,并在“现代(文学)作品鉴赏”课上作了试讲,结果引起热烈反响。听课者纷纷反映,这种评点式的“细读”要比泛论丁西林戏剧的思想与艺术特色“切实得多”④钱理群:《名作重读》,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33,133页。。更重要的是,金圣叹式的文学评点是一种与机械主义作品分析相对立的性灵化批评,融入了作者的性灵与妙悟,并擅长以隐喻思维与诗化的语言对名著的美学特征予以评说,短短数语,即可传其神,摄其魂。
面对评点体在现代学术语境下的尝试与成功,笔者对诗话体的复兴有了更充足的信心。不过,由于传统“诗话”“词话”的研究对象是古诗词,表达形式一般是文言文,这就给诗话体在当代语境下的“复兴”提出了一个难题:如何以白话文的形式对文学作品的文学价值及相关背景(范围广于旧时所说的“掌故”)作出片言居要、富于灵心妙悟的评价,且又能在统一的风格下连缀成篇?这是一个需要在实践中去尝试、探索的问题。尤须强调的是,对“诗话”批评的复兴不应作胶柱鼓瑟的理解,它既不是文学研究形态上的复古,也不单纯是诗话体的现代转化。事实上,笔者强调“诗话”批评的复兴,并欣然于评点体的重现,最根本的着眼点并非诗话或评点这两类体式能否“续命”,而是更重兴会妙悟和具体鉴赏的文艺研究模式在现代中国学术演变之大趋势下的命运和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