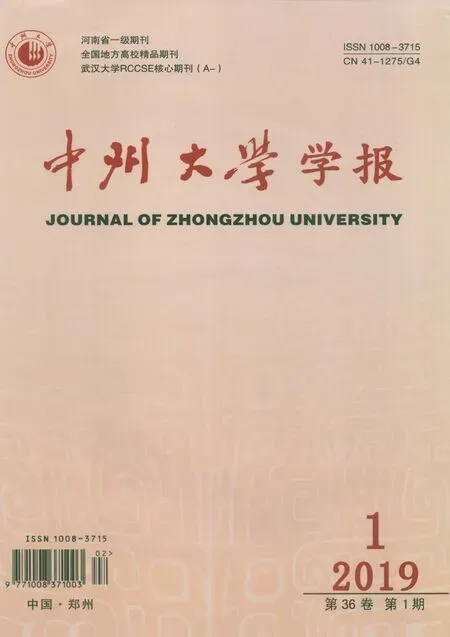雕刻一滴水
——读刘恪的《一滴水的传说》
2019-01-04张新赞
张新赞
(北京工商大学 艺术与传媒学院,北京 100048)
刘恪的散文,包括他的大部分小说,会让不少读者茫然失措,不知从何说起。但如果真正深入阅读下去,就会发现理解刘恪作品的过程,就是头脑中有关文学的教条不断被摧毁的过程。比如,关于散文,绝大多数人已经习惯于以下的“教诲”:
周作人:外国文学里的论文(essay),一批评的,是学术性的。二记述的,是艺术性的,又称作美文,这里边又可以分出叙事与抒情,但也多是两者夹杂的。治新文学的人应多作艺术性的美文。
王统照:要提倡纯散文(pure prose),有思想的根基,有文学的趣味。
胡梦华:散文应为家常絮语,是用清逸冷隽的笔法写出零碎感想的文章。
梁遇春:小品文是用轻松的文笔,随便地谈人生,信手拈来,信笔写去。
梁实秋:散文的美妙多端,最高理想也不过是“简单”二字而已。
郁达夫:小品文可爱的地方,就在于它细、清、真三点。
林语堂:小品文以性灵为主,不为格套所拘,不为章法所役。
鲁迅:小品文不是抚慰和麻痹的“小摆设”。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但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
朱自清:散文的趋向,可以是幽默,是游记、自传、读书记,也可以是长篇传记、报告文学。[1]
然而,我们悲哀地发现,以上这些文学大家对散文或小品文的理解,几乎不能为今天的散文写作提供多少有价值的参照。如果你已经习惯于阅读朱自清、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余秋雨等人的小品文、散文、随笔的话,阅读刘恪的散文会遇到巨大的障碍。这些散文理论面对刘恪的《一滴水的传说》,只能是无能无力。《一滴水的传说》完全打破了传统散文的写作方式。我认为,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观察这篇大型散文。
其一,“六经注我”或百科全书式写作。刘恪的写作,包括小说、散文都有一种知识上的野心。这与他大量的阅读有关,他的阅读涉及科学、文学、历史学、心理学、民俗、地方史志、神话学、哲学等。作为作家的刘恪与作为理论家的刘恪常常无法分辨,虽然他的写作只能展示他阅读的冰山之一角。《一滴水的传说》呈现出一种“六经注我”式的知识的丰富性,类似互联网时代知识的超级链接;灌注了作者对世界的整体性思考,这种百科全书式写作的探险,造成了从作者到读者、从文本写作到阅读的双重挑战。这篇巨量散文的诞生,是刘恪博学与才华的结晶,是高度理性和诗意抒情的完美熔铸。
其二,词语的复魅术,重新估价“一滴水”。写作就是恢复词的丰富性,就是唤醒沉睡的语言符号。水,在中西哲学中都是一个原初意义上的本喻,也在写作者笔下呈现为世界丰富性的象征。如:“大一生水”(郭店楚墓竹简《大一生水》)。徐子曰:“仲尼亟称于水,曰‘水哉,水哉!’何取于水也?”孟子曰:“源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尔。”(《孟子 离娄下》)“我在观看一条流水的源头,心中惊叹不已。”[2]361
现代性语境中,水这个词,早就丧失了它原本的形象丰富性和意义丰富性。水就是化学H2O的分子式,就是人们渴了需要饮用之物,失去了任何文学和哲学的意味。或许宗教里还残留着它的一些形而上的意味,但与大部分不信教的中国人无关。
与张锐锋、祝勇等“新散文”代表人物抱着“重述历史”的雄心、在历史的古旧宫殿里流连忘返不同,刘恪的写作,从小说到散文,几乎拒绝所有的历史题材。在刘恪的散文中,也包括他的小说如《蓝色雨季》,读者可以发现:“山水”成为他立体描述的基本物象和连绵不断的诗意化意象。《一滴水的传说》中,这样界定“水的语法”:
水是什么?
水是非要回答它的自身吗?可能不是水的本身,水本身只是氧原子与氢原子的结合,水作用时仅仅是它的水分子。
水不能仅仅是满足一个判断句。
水回答水是多个角度的能量。
……
水的形式和水的含义是同步的。水不着一形而赋予万形,它随万物而赋形,所以万物都体现了水的意志。水的意义也是万物实体的象征,那么有多少物义就有多少水意。而且几乎都是永恒不变的。
水的基本语法就是水的原型。
水,如果仅仅拥有一个科学的解释,无疑是水的悲哀,也是书写者的悲哀。在《一滴水的传说》中,水可以是声音性的存在,可以是身体和欲望,可以是时间的表征、梦想的形式、心灵的形式感,可以是发思古之幽情的对象,可以是人生命运的一个悲凉的隐喻,可以是返乡的秘密小径,可以是一首诗,可以是湖湘精神的象征,可以是性别、思维、原型、哲学……世界的秘密就是水的秘密。刘恪曾说,小说是精细的微雕术。《一滴水的传说》让我们看到,他在对一滴水的绽开进行雕刻,用词语进行雕刻。词,千姿百态,新的意蕴溢流。
其三,断片的与整体的。水可以是名词,也可以是动词——水的流动性成为这篇散文的结构方式。苏轼曾精妙地论述过行文的秘密的“流水之喻”:“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按照苏轼的理解,好的文章就是在“词达”与“有文”(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之间找到那个平衡点。
刘恪的散文,如《海然》和《一滴水的传说》,都在三四万字左右,传统散文、随笔、小品文根本没有这样的篇幅。几十个小标题,又连缀成一个整体,这个整体是开放性的整体、流动性的整体,是非因果性结构的整体,断片、句子、词语随时准备逃离整体,散逸出去。周行古今时空中的水滴,化作云气,弥散于天地。中国古典美学中的“韵”“气”常常被神秘化,若仅就文学作品来说,何尝不是一种令人玩味不已的情感感觉呢?这种感觉常常可以具体到文章中的词、句子、结构方式。如《诗经》中古老的四字一句,句子递进,循环往复,造成了抒情的一唱三叹或庄重肃穆的感觉。
《一滴水的传说》中,元叙述并没有(像博尔赫斯的很多小说)做纯观念的探讨或知识谱系的描绘,而是注入了深沉的人生、文化和哲学的内涵。多年前刘恪就在阅读博尔赫斯时,表达了自己对互文性写作的独到理解,“真正的互文应该是不露痕迹的形象互文”[3]292。《一滴水的传说》里,这些散逸又结合的词、句子、段落,如一滴滴色泽气味音响各异的水,交错汇合而成一匹流动的锦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