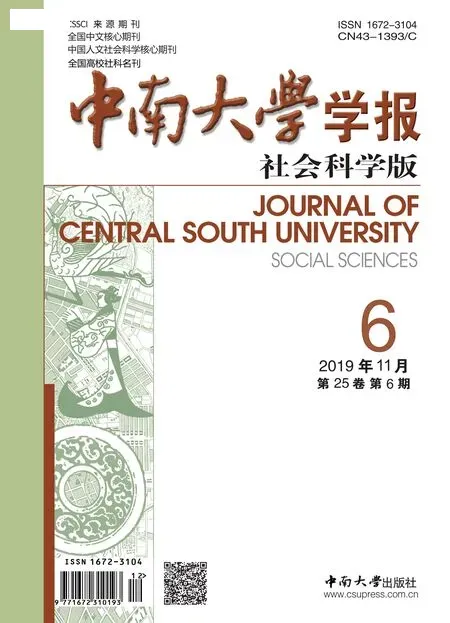《史记》入集的篇章考察与文体学意义
2019-01-04汪雯雯蒋旅佳
汪雯雯,蒋旅佳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陕西西安,710119)
《史记》作为一部史学著作,经由唐宋古文运动将其作为古文的典范之一,逐渐进入文章学领域。宋代以降,文章学领域有关《史记》的评论层出不穷,至清代达到高峰,最终成就了《史记》在文学史上的不朽地位①。从宋代以来《史记》进入文章总集的情况来考察其经典化过程,是《史记》文学接受研究的重要路径。伴随“子史衰而文集之体盛,著作衰而辞章之学兴……经学不专家,而文集有经义;史学不专家,而文集有传记”[1](61)的著述风气,文章总集在篇章内容的选取上,开始“收录先秦两汉子、史文章”[2]。自真德秀《文章正宗》以来,《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等史部著作入集,业已成为文章总集编撰的常见现象。以《史记》进入文学总集为观照点,在入集过程中,编撰者对《史记》篇章的采纳、截取或重构,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编撰者是基于何种维度接受《史记》的。
一、《史记》入集的篇章形态考察
《史记》篇章入集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作为唐前最重要的文学总集,《文选》对于“概见坟籍,旁出子史”的游说谏诤之辞,因其“事异篇章”而不予收录。史传中的叙事性文字,因缺乏文采,亦不加采纳。由于赞论具有“综辑辞采”、序述具有“错比文华”[3](2)的艺术性,《文选》从《汉书》《晋纪》《后汉书》《宋书》中选取十几篇赞、论、序、述入“史论”“史述赞”类,然而选择对象不包含《史记》。这一选取观念对其后许多文学总集的编撰产生了较大影响。例如补《文选》之遗的《古文苑》不收“史传”,在编次和分类体例上对《文选》多有继承的宋代大型文学总集《文苑英华》亦不收《史记》。《史记》作为体例完整、内容广博的史学著作,本身已经便于流传,这是总集不选《史记》的重要原因。北宋孔延之编撰地域总集《会稽掇英总集》,前十五卷收录诗歌,按“州宅”“西园”“贺监”“山水”等类目编排;自十六卷始选录文章,按“史辞”“颂”“碑铭”“记”“序”“杂文”等类目编排。在“史辞”一类中,收入《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中“太史公曰”的部分文字,并将其命名为《越世家史辞》。《会稽掇英总集》按内容与“会稽山水人物”有关这一标准进行择选,体现出地域总集编撰选文时强烈的地志化倾向[4]。其对《史记》的选录,与其他文章总集重《史记》的文章学价值而加以选录的出发点有别。
真德秀《文章正宗》创新文章分类体例,所录诗文分为“辞命”“议论”“叙事”“诗歌”四门,其中收录了大量的史部文献,《四库全书总目》称:“总集之选录《左传》《国语》自是编始,遂为后来坊刻古文之例。”[5](1699)《史记》中最具史传文学特点的叙事论赞类文字,自《文章正宗》以来,逐渐进入文章总集当中。据许海月统计,大部分收录《史记》的文章总集并非对《史记》各篇进行全文收纳,而是进行了相应程度的摘取[6](9-52)。至于这一行为的动机,《广文选·凡例》解释为:“子史等书,可入选者甚多,第以其俱有成书不能尽采。”[7](卷首)姚鼐《古文辞类纂》选《史记》“表序”“书说”“论辩”类文字而不收史传,其于“序跋类”序目中也予以说明:“余撰次古文辞,不载史传,以不可胜录也。”[8](3)当然,一些卷帙浩繁的大型总集如《文章辨体汇选》,以及出于编者的文学观念而对《史记》文章的整体性和完整性予以重视的个别总集,会对《史记》传记全篇引录,但仍为少数。清代于光华编撰《古文分编集评》,其在《凡例》中称:“前贤选本,每恐篇长难于熟读,节录数段,或截分数篇,非不便于初学。”[9](5)这也说明《史记》篇章的截取和重构是文章总集编撰过程中的常见现象。
《史记》篇章的截取和重构,从编撰意图和具体操作上来看,主要有如下几种不同的表现形式。
第一,在以类编次或以时编次的总集中,仅节录《史记》中契合编撰者选文观念的部分。宋代汤汉的《妙绝古今》选录上自《左传》下至北宋的“文之精绝者”,所录文字乃“一代不数人,一人不数篇”[10](784)的精妙文字。《妙绝古今》卷二收《史记》段落,涉及《伯夷列传》《屈原贾生列传》《乐毅列传》《楚世家》《鲁仲连邹阳列传》等11 篇篇目当中的内容,仅列出处而不给所选段落命名。《金圣叹批才子古文》中“《史记》选”类和“西汉文”类均摘录了大量《史记》段落,王符曾《古文小品咀华》、林云铭《古文析义》等也均是通过选录《史记》段落并加以评点来实现对《史记》文章学意义的阐发。以某一叙述事件为中心,摘取传记中叙事文字尤佳的部分,将《史记》作为叙事文学的典范加以收录、命名并评点,是其中较为常见的《史记》文章学价值阐述方式。《文章正宗》“叙事”类纲目称:“今于书之诸篇与史之纪传皆不复录,独取左氏史汉叙事之尤可喜者。”[11](6)故《文章正宗》选取《史记》中大量精彩的叙事段落,并以“叙+主体+事件名称”的形式为之命名。如《太史公叙秦孝公变法》《叙秦并天下后事》《叙秦焚书》《叙秦起阿房宫》《叙项羽救巨鹿》《叙刘项会鸿门》等三十多篇叙事文字,将原本以人物为中心的传记拆分成各类事件,并以其为作文之式。汪廷讷《文坛列俎》“史摘”类的小序交代了史部文献的入选范围:“叙事议论尤佳者数十篇,以见史之一班耳。”[12](241)叙事类事件包括《秦孝公变法》《秦并天下后事》《项羽救巨鹿》《项羽会鸿门》《平勃诛诸吕》《迎立代王》《赵武灵王立少子何》等,其后如清代林云铭的《古文析义》也对这一文本选录方式加以借鉴。
第二,在以体编次的总集中,节录《史记》部分内容进行文体重构并命名,不过分偏向纪传体史书写人叙事的完整性,而以保留文体属性为重要的选录依据。截取《史记》篇章使其成为独立的文体,并以文体命名的文本选录方式,在宋代以来的文章学选本中较为常见,其中节录“太史公曰”并以“论”或“赞”命名的选文命篇方式尤多。如陈仁子《文选补遗》“赞”体收录《燕世家赞》《韩世家赞》《孔子世家赞》《张良世家赞》等赞语20 条,刘节《广文选》、焦竑《中原文献》等文章选本亦收大量的赞语。除论赞之外,将人物对话中的应用性文字进行节录,则形成“说”“书”“对问”等应用文体。冯有翼《秦汉文钞》节录《史记》大量的“说”体,如《赵良说商鞅说》《苏秦说燕文侯说》《苏秦说赵肃侯说》等。《古文喈凤新编》收《李斯谏逐客书》《司马相如谏猎书》等公文,《广文选》将《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回答壶遂的文字进行节录,辑为《答壶遂问》。将“表”前用以交代制表始末的议论性文字进行节录,则又形成“序”或“论”体。以“序”名篇者,有姚鼐《古文辞类纂》“序跋类”收录的《司马子长十二诸侯年表序》《司马子长六国表序》《司马子长秦楚之际月表序》等6 篇序文;以“论”名篇者,有《集古文英》“史论”类所收的《十二诸侯年表论》《秦楚月表论》《汉兴诸侯年表论》等。
第三,节录《史记》传记中的合传为单传,并另拟标题。通过拎出单人传记,以保留传记记载一人始终的叙述完整性,并与唐宋以来的人物传记接轨。《文章正宗》卷二十将《屈原贾生列传》中有关屈原的文字截取,并且剥除屈原的《怀沙赋》,题为《屈原传》;明代刘祜的《文章正论》,将《汲郑列传》摘取为《汲黯传》;《文体明辨》将《管晏列传》摘为《管仲传》,将《平原君虞卿列传》摘为《平原君传》;等等。通过这一文本重构方式,既缩短了入选文章的篇幅,又使其体例更为接近唐宋以来的碑志记传。
对《史记》篇章进行摘录、重构,使之呈现新的篇目形态,是南宋以来《史记》进入文章总集的必要途径。在以体分类的文章总集中,对《史记》进行篇目形态改造有利于突出文体特征;在以类编次或以时编次的总集中,对《史记》进行摘录则有利于缩小篇幅,突出《史记》的某类质素以便集中学习。因此,节录及重构文本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编撰者的文体及文学观念。
二、《史记》入集与文章接受
关于《史记》的文章学意义,张新科、杨昊鸥等学者主要通过细致梳理历代对《史记》的评论来加以探讨。历代对《史记》的评论主要集中在《史记》的章法结构、叙事写人的高超技巧、总体风格的呈现等方面。若从各阶段总集编撰的角度观察《史记》进入文章总集的情况,对于《史记》的接受情况则有需要补充的地方。
《史记》入集与总集编撰所处时代的学术风尚密切相关。南宋收录《史记》的总集往往通过节录《史记》片段、分析其文章技法来阐明文道关系。北宋时期苏洵、欧阳修、苏轼、陈师道等人对《史记》的效法与探讨为《史记》进入文章学视野奠定了基础。南宋以来伴随着理学思潮的兴起,几部收录《史记》的总集都将文道、义理作为文章入选的首要条件。如《崇古文诀原序》称:“文者载道之器,古之君子非有意于为文,而不能不尽心于明道。”[13](2)按此标准,选入《自序》和《答任安书》。《文章正宗·纲目》称,“今所辑以明义理、切世用为主”,且“其体本乎古,其指近乎经”者才得以入选,“有志于史笔者,自当深求《春秋》大义而参之以迁、固诸书”[11](7)。因此,真德秀也是通过对《史记》篇章结构的分析上升到对文章写作和义理二者关系的讨论。《妙绝古今》称入选该集的篇章是“言之精者”,但又说学者“毋但求言语句读之工”[10](784)。《四库全书总目》称《妙绝古今》的编选“有感于士之不遇而复进之于道”[5](1700),意即既求言语句读之工,又需道合六艺。所选《史记》段落,如《伯夷列传》《屈原列传》《乐毅列传》等,主人公都有不平的遭遇和高尚的人格,正符合《四库全书总目》的评价。《史记》通变古今、成一家之言的著史理想,以及司马迁在叙写人物传记时开阖跌宕的笔法符合这一时期文章总集的选录要求。
明代对《史记》的评论进入兴盛期,“文必秦汉”的复古观念以及场屋之作的需求,使得这一阶段对《史记》的接受更加偏重于对篇章的细致分析和对创作技巧的师法上。受辨体风气和复古思潮的影响,这一阶段选录《史记》的文章总集以辨体和对古文写法进行赏析为主,前者如《文章辨体》《文体明辨》《文章辨体汇选》等,后者如《先秦两汉文脍》《秦汉文钞》《古文奇赏》《西汉文纪》《集古文英》《文编》等。钱忠义为《集古文英》作序,称“凡制策时务为天下有用文字,罔不该贯”[14](494)。《中原文献·自序》称:“一切典故无当于制科者,概置弗录。”朱之蕃为《中原文献》作序,认为“太史公苦心毕力,悉采金匮石室之编,惟取其词旨丰斐,文采陆离者入矩”[15](卷首)。因此,对章法布局、语言技巧的分析就成为《史记》接受的重点。《钜文》从文章风格的角度对《史记》悲壮宏放的境界进行标举,《文编》和《文章指南》则从法的角度提出古文写作的具体规范和技巧。《文编·自序》称“学者观之可以知所谓法矣”[16](103),《文章指南》则将对法度的揣摩和学习作为全选的编撰体例。《金圣叹批才子古文》卷七《西汉文》选《史记》传赞76 篇,卷八又选《太史公自序》《酷吏传序》《报任安书》3 篇,并从各个角度对所选片段详加点评,对司马迁讽刺笔法的运用阐释得十分透彻。当然,这一时期也有承接自宋以来对义理的重视而编撰的总集,如刘祜的《文章正论》自序称“诸家纂集,大率以辞之工拙为高下,而论世考德溺其识矣”,钟化民为之作序,称“是编者,求文于道,求道于心,求心于正”[17](423),所入篇目以六经冠其首而采史书大量篇章。但总体而言,明代对《史记》的编收和讨论主要侧重于《史记》本身的文学要素上。节录、摘取《史记》文本作详细分析、鉴赏,则使编选者对技法的讨论更为集中,更有操作性。
清人将“道”具化为义理和考据,更加重视文道合一,并首次提出《史记》篇章形态与接受的相互关系。许海月将选录《史记》篇章的总集在选取倾向上概括为“文章正统”“作文启蒙”“经世致用”等,较为全面[6](44-51)。清代对《史记》的接受大致建立在前代基础上而有所推进。除此之外,清人关于《史记》形态及入选次序的思考值得关注。如桐城派方苞将《史记》作为“义法”最精者的代表,并认为要接受《史记》则不能将其分割,否则会破坏义法。《古文约选·序例》称:“盖古文所从来远矣,六经、《语》、《孟》,其根源也。得其支流,而义法最精者,莫如《左传》、《史记》,然各自成书,具有首尾,不可以分剃。”故方苞专门评点《史记》而不将《史记》进行分割入集。《史记》中《太史公自序》一篇因具有独立篇章的性质而被收入,《古文约选·序例》称:“独录《史记·自序》,以其文虽载家传后,而别为一篇,非《史记》本文耳。”[18](4)另外需要关注的是于光华编撰的《古文分编集评》,其在《凡例》中总结前代选本节录《史记》入集造成的后果:“《左》《史》之神理血脉,未免割裂,妙处难得。”因此,此选本“每载必备原委”[9](5),这也是将完整的《史记》文本所凸显的神理作为入选前提。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传志”类收录的《史记》人物传记,除《屈原贾生列传》一篇中的《怀沙赋》《吊屈原赋》《鵩鸟赋》已入“辞赋类”和“哀祭类”,故不重复选录外,余皆全篇收入,不作分割。另外,于光华《古文分编集评》关于《史记》入集的篇次顺序探讨,尤值得注意。于光华(1727—?),字惺介,号晴川,自幼随父学古文,编纂有《文选集评》和《古文分编集评》。在《古文分编集评》中,他认为,“初学经书既毕,即宜授以古文。但前贤选本,俱从《左》《国》《史》《汉》六朝唐宋相承而下,编次之体宜尔,而塾师亦即从《左》《史》入门,初学遽难领略”[9](1),因此,“古文先由唐宋八大家起手,次两汉,次《左》《史》,层累而上,指点古文源流别派”[9](1)。该选本的编次顺序也与于光华本人的古文观念吻合,先由“唐宋八大家”入手,推至储欣“十家”,次两汉,最后为《左传》和《史记》,循流讨源之文章学观念贯穿其中。“且即唐宋两汉中,分为两种,择其起伏层折、路径可寻者,先为讲解,俾知古文大概,然后授以沉雄深厚之作,微寓由浅入深意”[9](1),集中所论不拘于章句品评,而能抉出气脉理路,重气韵神采。这部选集裒集“童年应读之文”[9](1)以作读本,同时秉承“时文本于古文,体裁格律原自相通”[9](3)的观念集中古文精华,以帮助读者学习时文的写作方法。此选本将《左传》《史记》作为古文的最高典范,同时打破了以往文集编次的惯例,将古文观念和编次体例巧妙结合。
在自宋代以来文章学兴盛的学术背景下,《史记》的接受在各阶段均有其特点,文道结合、行文方法和技巧、内涵和义理是《史记》进入总集在文学接受上的各个维度。各时期对《史记》的接受并不是单一状态,而是交互式地互相影响与推进。
三、《史记》入集的文体学意义
《史记》入集的重要原因在于其突出的文献和文体价值。《史记》作为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其于叙述中还原历史场景的史学特征,使得《史记》本身就保存了大量的历史文献。文章总集在收录这一类文体时,将《史记》作为保存文献的文献库加以采摘,这与将《史记》作为创作的典范加以择取不同。明代梅鼎祚《西汉文纪》、冯有翼《秦汉文钞》、陈仁锡《古文奇赏》等,均收录《史记》中大量的诏策文书;姚鼐《古文辞类纂》“碑志”类收《秦始皇二十八年泰山刻石文》《秦始皇琅琊台立石刻文》等6 篇刻石文,李兆洛《骈体文钞》“铭刻类”亦收此6 篇,也是将《史记》作为文献的采摘来源。《古文喈凤新编》点评《李斯谏逐客书》,称“峰回路转,波湧澜翻,备极文境之妙。……缘秦文无多,选此书具载传中,故钞入《史记》”[19](15),也是以《史记》为文献来源的证明。由于选编者文体分类的细致化,单篇文章会被分成若干不同的段落而纳入不同的文体类别中。如《广文选》将《太史公自序》一篇分为《自序》《答壶遂问》《六家要旨论》三篇;《中原文献》将《屈原贾生列传》分为《屈原传》《屈原赞》《贾谊吊屈原赋》三篇;《文坛列俎》将《淮阴侯列传》分为《汉王筑坛拜信》《韩信破赵》《韩信赞》三篇。诸如此类,入集内容既包括司马迁对前代文献的采摘,又包括《史记》的自我书写。《史记》的文献价值和文体意义并不会被截然区分,而是共同存在于《史记》入集这一行为之中。《史记》入集的文体学意义,不仅包括文章总集按照编选体例对《史记》的内容摘选及文体认定,也包括围绕这些文体而展开的文体学讨论。
首先,《史记》中的“传状”“赞”“世表”等因具文体开创意义或文体典范价值而进入文章总集。《文章正宗》“叙事”类前的小序称:“有纪一人之始终者,则先秦盖未之有而昉于汉司马氏,后之碑志事状之属似之。”[11](6)这说明《史记》传记之于唐宋碑志的意义。《文章辨体》卷四十五“传”体前小序称:“太史公创《史记》列传,盖以载一人之事,而为体亦多不同。”以《史记》列传为源头,开启了三种不同类型的人物传记:一是承接《史记》列传的风格,“前后两汉书、三国晋唐诸史”第相祖袭,以及后世之学者士大夫“或值忠孝才德之事,虑其淹没弗白,或事迹虽微而卓然可为法戒者”所作的人物传记;二是以范晔《黄宪传》为代表的“盖无事迹,直以语言模写其形容体段”[20](30)的人物传记;三是以韩愈《毛颖传》为代表的带有讽谕、游戏性质的传记,侧重于借传为说。故《文章辨体》只选择《史记》中的《孟子荀卿》一篇置于卷首,以示《史记》“传”之体的开山地位。《文体明辨》卷五十八“传”类小序称:“自汉司马迁作《史记》创为列传以记一人之始终,而后世史家卒莫能易。”[21](370)值得注意的是,《史记》虽在一篇传记中记载传主生平事迹,但也有不少合传合载两人事迹。刘知己在《史通·列传》中称:“传之为体,大抵相同,而述者多方,有时而异。如二人行事,首尾相随,则有一传并书,包括今尽。”[22](35)将二人合传叙写,是为了史书叙事的需要,这一写法虽历来为史家所重,但唐宋以来的人物碑传基本上是单传,选编者在表明《史记》传状的开创性时,就不免要将其截取为类似文集中的传记而尽量消除其史书的特征。因此,徐师曾将《管晏列传》摘录为《管仲传》,将《范雎蔡泽列传》一篇拆为《范雎传》和《蔡泽传》两篇单人传记,其形态就与后面的家传、托传和假传相近。另外,唐顺之《文编》、贺复征《文章辨体汇选》将《史记》中“世表”的文体开创意义也予以彰显。《文编》“年表”类收《史记》年表5篇;《文章辨体汇选》“世表”类前有小序。贺复征称:“表者,标也。标著其事,一览了然也。太史公年表月表实创厥始,录之为后来作谱系之祖。”[23](723)故收入《三代年表》和《秦楚之际月表》作为年表和月表的始祖典范。与一般总集只录表的序文不同,贺复征将年表和月表全文收入。在总集中选入《史记》的“论赞”“传状”“世表”,从文体学的角度说,有回溯文体源流,引出后世由其演变而来的相近文体的作用。另外,截取《史记》篇章,突出其文体特征,将其作为文体的典范以示写作门径,是编选文章总集的重要目的。《古文辞类纂》“序跋类”小序说:“载太史公、欧阳永叔表志叙论数首,序之最工者也。”[8](3)《古文辞类纂》将“序跋”类与“赠序”类分开,“序跋”类即是以《史记》年表序和《新五代史》年表序及其他书序为代表。《古文眉诠》《涵芬楼古今文钞》又将“表序”从“序跋”中独立出来,选取《史记秦楚之际月表序》《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等6 篇作为表序的典范,既突出了表序的文学价值,也使文体分类更为细致,便于取法。同时,文体的开创性和典范意义常常是同时具备的,因为古代文学批评领域,常以一种文体开创之初的风貌作为这类文体的本色,即最高典范。
其次,文章总集在具体的文体考察中,通过以“史”入“集”过程中的文体辨析,对《史记》“传”“序”“赞”等文体正变问题展开讨论,其中亦折射出相关的文学生态环境和文体观念。唐长庆二年“三史”科确立,使《史记》成为制举之常科,并被宋代科举所沿袭,大大提升了士人对《史记》的接受热情。加之古文运动促进了文章学的兴盛,叙事性文学也随之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因此,《史记》的记传写法便颇引人关注。史“传”与文“传”的接轨,是以“史”入“集”过程中需要辨析的内容。真德秀《文章正宗》首先将《史记》记传类文章分为“叙事”和“议论”两部分,《文章正宗纲目》称本选的目的是“以后世文辞之多变,欲学者识其源流之正也”[11](5),明确将《史记》以叙事议论为主的记传写法加以推举。前文已述,《文章辨体》和《文体明辨》同样也通过梳理“传”体的发展脉络,将《史记》开创的史书传体作为传之正体,而对于唐宋以来的传记,则认为是自然的文体发展,言辞之中并无轩轾。然而史学视野下对史家传记和私人传记的讨论却是另外一番景象,钱谦益《刑部郎中赵君墓表》中有“余尝以谓今人之立传非史法也,故谢去不为传”[24](1537-1538)的观点,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认为,“自宋以后,乃有为人立传者,侵史官之职矣”[25](3241),他们将史学范畴的传和文学范畴的传加以区分,影响较大。作为文章总集的《古文辞类纂》,其“传状”类小序称:“传状类者,虽原于史氏,而义不同。”[8](11)所选篇目如《圬者王承福传》《种树郭橐驼传》等,符合其在“传状类”小序中的观点,即“古之达官名人传者,史官职之。文士作传,凡为《圬者》、《种树》之流而已,其人既稍显,即不当为之传”[8](11)。选录这些社会较低层次人物的传记,可看出姚鼐对于传记写作是由官方掌握话语权这一史家观点的部分肯定[26];其所选不录《史记》篇章,直取自韩愈以来文人写作的行状和传记,虽有史书不可胜录的原因,但也表明其对唐宋以来文人传记的重视。《经史百家杂钞》也受桐城派观念的影响,故在选录时不以正变区分“传”之各类。“传志类”将“传”体分为“记载之公者”和“记人之私者”,并将二者并列,作为记载之公者的《史记》人物传记被大量选入。与《文章辨体》《文体明辨》等从文体正变角度考察史传与私传不同,《史记》“传”体进入文集又经过了新的考察与分类。又如,《史记》中的“赞”作为“论”体的开创之一被选入文集,一直作为正体出现。如吴讷《文章辨体》第三十五卷“论”体前有小序,用以梳理“论”体的演变。该小序称,“于传末作论议以断其人之善恶”的“史论”作为“论”之二体中的一体,由《史记》开创,并于正文选录项羽、商鞅、蔺相如三篇传记的赞语以示规范。《涵芬楼古今文钞》则从文体的演变角度说明《史记》的“赞”文并非正体。其《例言》中“颂赞类第十一”条称:“赞亦颂类,古者宾主相见则有赞,互相称誉以致亲厚之意,故文之称人善者,亦以赞为名。然至史家之体,每传必有赞,则其中贤否不一,亦时有贬词焉,非其正体。”[27](1)吴曾祺虽认为《史记》中的“赞语”并非正体,但仍大量采摘并示为典范,“赞”体收《史记五帝本纪赞》《史记项羽本纪赞》《史记孔子世家赞》等8 篇赞文。这里突破了传统的文体正变观,认为体之正变并不意味着文之高下。从《史记》入集的文体来看,论赞占有绝对优势,是入选最多的文体,这也能说明一些问题。论赞的受重视与赞体相对独立的篇制形态有关,又和宋代以来“以古文为法”的时文创作观念有密切关系。《史记榷参》评论赞为“不数言辄开阖顿挫,此所以为文字之祖也”[28](175)。牛运震《史记评注》称:“太史公论赞,或隐括全篇,或偏举一事,或考诸涉历所亲见,或证诸典记所参合,或于类传之中摘一人以例其余,……诚为千古绝笔。”[28](92)《史记》的论赞往往在较短篇幅内对人物进行评论,对整篇传记进行提要钩玄,寓有高超的艺术成就,因此,揣摩《史记》论赞的文法就成为学习古文、指导时文写作的重要途径之一。除“赞”“传”二体外,《古文辞类纂》“碑志”类小序讨论韩愈碑序和《史记》碑序“异体”,则为评价文体发展提供了依据。该小序称:“周之时有石鼓刻文,秦刻石于巡狩所经过,汉人作碑文,又加以序。序之体,盖秦刻琅邪具之矣。茅顺甫讥韩文公碑序异史迁,此非知言。金石之文,自与史家异体,如文公作文,岂必以效司马氏为工耶?”[8](12)姚鼐考察文体的变迁,重源流而又以动态和发展的眼光看待文体变迁,尤其突出文学性碑序突破《史记》传统而具有的创新性价值,这也体现了其重视唐宋且上接秦汉的古文观念。
以《史记》为代表的史部著作在进入文章总集时,不仅需调整其篇章形态,还需通过编选者对总集进行分类及说明编撰体例来进行文体的承接与融合。选编者对篇章进行重构,对文体进行重造,从而完成对经典的开掘与接受[2](199),其中蕴含了丰富的文体内蕴,寄托了各时期的选编者深层的文章学观念。
四、结语
自南宋以来,《史记》进入文章总集并不是偶然的,古文运动和程朱理学对文道关系的讨论是《史记》入集的重要契机。“古人之文,所以皆在六艺诸子之中,而不别为文集者,无他焉,彼以道术为体,而以文章为用,文章特其道术之所寄而已。”[29](188)摒弃浮华、重内质的文章观念使文章典范扩充到经史子部,以之补益文章学的不足。唐宋以来叙事文的蔚为大观,古文批评领域热衷于对叙事文的讨论,以及叙事文学地位的提高,都是《史记》入集的重要条件②。此外,“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1](219),《史记》写人叙事的巨大成就及其文学价值是《史记》得以入集的根本前提。“迁书体圆用神”,“迁书纪、表、书、传,本左氏而略示区分,不甚拘拘于题目也”[1](50),《史记》的体例既体现出通盘考虑的严密性,又能根据具体情况灵活变通,这为文章总集截取《史记》提供了更大的空间。通过观照《史记》入文章总集的过程,可以发现文章总集对《史记》的多维接受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通过截取《史记》中的历史文献,揭示《史记》保存的大量应用类文献的价值。二是通过节录文本突出单类文体,并对其进行分类或归类,标明《史记》中相关文体的开创性价值和示范性意义。在文体的探讨中,涉及有关文体正变以及文体流变等问题。三是在文章学领域,通过选录经典篇章或段落,赋予《史记》有关文道关系、行文技巧的文章学价值;通过对不截取《史记》篇章这一行为动机的阐释,或对《史记》整体性面貌的重视,体现出将《史记》作为古文最高典范的观念。从多个视角出发,同样的《史记》文本,也常因接受的维度不同而被归入不同的总集、不同的分类中。文章总集对《史记》的接受既受时代思潮的影响,也与编选者的思想观念以及文集的编撰体例有关。要言之,《史记》入集而被多维接受,是《史记》最终成为文学经典的重要助推力。
注释:
① 有关《史记》经典化的建构,可参看张新科的系列论文:《汉魏六朝:〈史记〉文学经典化的起步》,《甘肃社会科学》,2016年第6期,第33-38页;《宋代的〈史记〉文学评论》,《文艺理论研究》,2016年第5期,第117-128页;《〈史记〉文学经典化的重要途径——以明代评点为例》,《文史哲》,2014年第3期,第124-132页;《论清代的〈史记〉文学评论》,《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第57-65页;《〈史记〉文学经典的建构过程及其意义》,《文学遗产》,2012年第5期,第144-156页。
② 何诗海《“文章莫难于叙事”说及其文章学意义》,《文学遗产》,2018年第5期,对此论之甚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