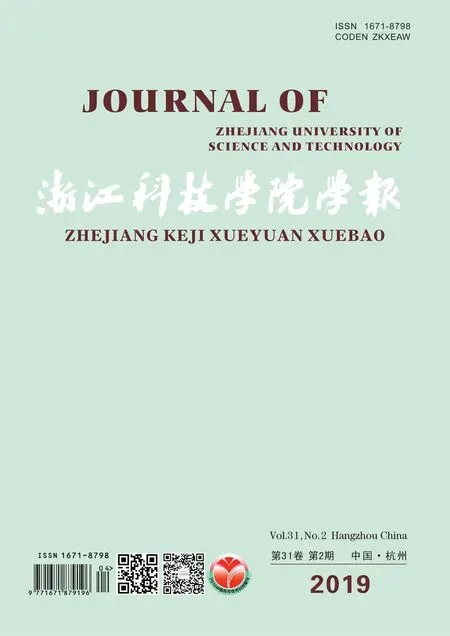浙江海外华人移民商业行为的文化模式解读
2019-01-04张崇
张 崇
(浙江科技学院 外国语学院,杭州 310023)
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许多20世纪七八十年代移民到海外的温州和青田籍的浙江籍海外华人,从默默无闻的打工者成为大老板,并在所居住国家的社会和经济领域崭露头角,在促进中国与其移居国家的交流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成为国际移民研究所关注的对象。哈佛大学学者孔飞力研究中国移民时提出:“中国文化使中国移民形成几个很有价值的特点,一个是家庭制度,一个是商业化。”[1]海外华人移民商业行为突出的文化特点之一,就是注重人情。人情作为中国社会人际交往的核心深层关系之一,在契约关系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是研究中国人商业行为的一个重要命题。国内早期研究侧重对这种人情的批评和反思,认为中国人重人情、轻契约的观念影响了商业企业的长远发展[2],人情似乎成为社会转型中的绊脚石[3-4]。以上观点把人情社会和现代市场法治经济视为矛盾,无法融合。其中原因是对人情的概念、人情社会缺乏了解与深入研究。近些年来,许多研究者开始用比较全面的视角来看待人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情关系与西方文化中的社会交换关系植根于不同的文化传统,应将二者有机结合[5];人情在契约的执行中有助于商业合作关系顺利进行[6],因此,中国人遵循的人情商业规范可以在行动上与契约策略相安无事[7]。国外研究者多把人情与关系结合起来研究,重视阐释人情、关系等概念的内涵,探讨中国传统商业行为文化规范与西方相关概念的共通之处,为具体国际商业实践中中西文化融合提供启示[8-9]。以上研究多从商业管理学、跨文化交际角度来研究人情作为中国商人行为的重要特征,探讨如何从西方商人自身角度去理解和适应这一文化,进而与中国人形成稳固且富有成果的商业合作关系[10-11];只有为数不多的研究者把焦点放在海外华人这一群体的具体商业行为上,如赵小建通过社会学调查研究,总结在美国和法国的温州移民的经商理念、创业模式、资金来源以及企业运作特点和原因[12]。以上研究较少有从文化视角对海外华人群体的商业行为进行阐释。如何从文化角度看待人情,理解中国传统的商业行为规范是值得探讨的。不能简单把海外华人移民商业行为中的伙计制和讲义气视为落后的象征。这种秉承中国传统人情的文化模式是海外华人在国内既有“熟人社会”关系圈子的海外扩展[13],使得海外华人能比较迅速地在海外站稳脚跟。本文运用露丝·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理论阐释浙江籍海外华人的商业行为。“文化模式”理论认为,群体所共同具有的文化观念和准则,是真正把人们维系在一起的因素;文化对人具有塑造作用,强调文化在群体中的代际传承,保证了文化的延续并能够表现出其不同于其他文化模式的特征[14]17-18。因此,要理解个体行为,不仅要把他的个人生活史和其天分联系起来,还要把个体从文化的种种风俗中选择出来的行为联系起来[14]233-234。本文从《论语》中的传统文化思想入手,分析其中提出的“洒扫应对进退”的伙计制和“仁”的思想中蕴含的“讲义气”文化,是如何构成浙江籍海外华人特有的文化模式,阐释其商业行为背后的文化内涵。
1 “洒扫应对进退”——华人移民的伙计制
余英时在考察明清时期商人与儒家伦理之间的关系时,对伙计制做了详细分析。他认为老板和伙计的关系不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而是伙计学成以后可以出去单干,自立门户。余英时提到,有的伙计和老板是亲族子弟,“这一事实恰好说明明清商人如何一面利用传统文化的资源,一面又把旧的宗族关系转化为新的商业组合”[15]329-330。现在浙江海外移民亦是如此,他们通过亲带亲、朋友帮朋友、老乡带老乡的方式出国寻求机会,在生意场上共同谋求生存发展,在异国他乡落地生根。从移民模式而论,这是一种“链式移民”[16]。海外华人移民基于亲情、乡情、友情的人伦关系,在创业之初大家同心同德,有利于增强企业凝聚力;一旦创业成功,可以根据自身的优势和条件,选择出去单干或者继续合作创业。余英时认为,伙计制作为一种新型人伦关系是中国经营管理阶层的前身[15]234。浙江海外移民在“伙计制度”中学习商业管理,用的正是《论语》[17]214中“洒扫应对进退”的学习方式:
子游曰:“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抑末也。本之则无,如之何?”
子夏问之,曰:“噫!言游过矣!君子之道,孰先传焉?孰后倦焉?譬诸草木,区以别矣。君子之道,焉可诬也?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
子夏让学生做做打扫、接待客人、应对进退的工作。子游觉得这些都是细枝末节,对个人修养来说都是细枝末节,不值得重视。然而,子夏却认为在处理日常细小琐事的过程中,人们可以获得生活教育。“洒扫应对进退”也是一种受教育的过程,只不过不是学校里知识的教育,而是一种生活和人格的教育。许多浙江籍移民在家乡大都以务农或者打工为生,没有接受太多的学校教育,在笔者的采访过程中,有很多移民都说自己“小学毕业,没有什么文化”。然而,他们虽然没有接受长期的学校正式教育,但是这并未成为他们事业取得成就的障碍。来自青田油竹的WSQ讲到自己1980年秋天初到西班牙时,有半年多都在流浪。后来他找到了在中餐馆打工的工作,在这里,他得到了直观又免费的学习机会,学会了中餐馆经营的门道和管理的基本流程。他三年在不同餐馆打工,既为自己创业积累了原始资本,也积攒下餐馆经营的经验,进而为后来的创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2012年笔者采访他的时候就已拥有五家中餐店和一家位于地中海黄金海岸边的饰品店,成为当地首屈一指的华人商人。与WSQ的经历相似,许多浙江籍移民初到国外,都会从每天的“洒扫应对进退”开始,学习积累经验,为未来创业打下坚实基础。温州乐清的DHL1990年出国到罗马,无亲无戚,只好睡在罗马市中心的地铁站,后来给在意大利普拉托的徒弟写信,半个月后才联系上。徒弟接他到普拉托并给他找了做衣服的工作。他不会做衣服,就改为熨烫工,因为人生地不熟,不管工资多少他只能去干。(此为笔者2012年5月21日在高岙村采访意大利华侨的文稿整理)后来,DHL根据自己积累的经验和人脉创办了服装公司,之后渐渐做大,开始经营服装大楼的生意。
“洒扫应对进退”是人格的教育,亦是生活的教育。在这个过程中,海外移民生活的技能、与人沟通的技能以及经营管理的技能都有机会得到锤炼。在每天简单机械的工作中不断察言观色,心领神会,敏慧于心,对后来自己单干自然也是绰绰有余。在海外的温州商人大多是做餐馆伙计、跑堂出身,他们善于在平时的工作中学习摸索,抓住各种机会,进而在各行业有所成就。像WSQ、DHL这样,通过以乡情、友情、亲情为纽带的人伦关系,在国外能够比较迅速地站稳脚跟,也为以后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努力拓展商业资本,熟悉所在国家商业经营领域的相关规则制度,把中国传统的商业经营管理文化与西方现代企业制度相融合,实现华人企业的成功,从而成为中国和他们所在移民国家之间的重要纽带。
2 “义”与契约
本研究的浙江海外移民,主要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到海外的新移民,这些移民身上存有鲜明的中国传统文化印迹,其中讲义气最为明显。“义”的繁体字为“義”,《说文解字》认为:“義,已之威仪也。”[18]通过讲义气,实践“义”的行为而使自己获得尊重,强调自己对他人的“义”,并不是一种自我牺牲,而是互惠互利。按照前文提到的西方学者的研究,即是一种人情。梁漱溟是新儒家早期代表之一,他认为“义”是中国传统伦理关系的重要体现:“伦理关系始于家庭,而不止于家庭。亲切相关之情,发乎天伦骨肉;乃至一切相与之人,随其相与之深浅久暂,莫不自然有其情。因情而有义。父义当慈,子义当孝。兄之义友;弟之义恭。夫妇,朋友,乃至一切相与指认,随其亲疏厚薄,莫不自然互有应尽之义。伦理关系,即是情谊关系,亦即其相互间底一种义务关系。‘伦理’之‘理’,尽正在此情与义上见之。”[19]这种“讲义气”与《论语》[17]147中关于“仁”的记载相一致:
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
这句话的意思是:“平日容貌态度端正庄严,工作严肃认真,为别人忠心诚意。这几种品德,纵使到外国去,也是不能废弃的。”“仁”是中国文化内在的核心价值,体现在商业行为上便是做商人的诚信。余英时认为,“仁”构成了中国人内在的价值核心,成为中国人中心而自主的价值立场[15]320。
在意大利做生意的DHL看来,是否讲义气是中国人与外国人最大的区别。他讲到自己的亲身经历:当时办服装加工厂需要20亿里拉资金,都是几十位温州籍工友凑起来的;为了还债,他们连续五个月加班加点,我们温州人就是义气。这种能够依靠借钱集资的方式,据学者王春光研究,其实是一种“会”。“会”是温州人借助朋友、亲戚关系建立起来的一种经济互助形式,这种筹资形式是民间的、非正式的形式,主要依赖彼此的信任。王春光研究法国巴黎的温州人时发现:温州人对入会是相当谨慎的,不是朋友不行,甚至不是要好、可靠的朋友也不行。但是即使这样,也会发生“倒会”。所谓倒会,就是会主不还钱。发生这种情况,主要有两大原因,一是由于会主不讲信用,卷款逃走;二是由于经营不善、亏损造成的。由第一种原因发生倒会的非常少见;对于第二种原因,入会的朋友都会给予谅解和支持,这就是他们所说的“朋友情谊”[20]。这种通过“朋友情谊”,即讲义气的经济互助形式,是许多海外华人移民能够比较容易获得投资资金进行创业的重要原因。对温州移民而言,讲义气就是一个人的名片,如果希望对方能够守信用,那么首先自己要做到;身处这样一个视信用为生命的群体中,自然要有一种内在自发的道德约束,否则将寸步难行。《高岙风采》中提到,高仁来是一个信守承诺的人,他在法国的生意刚开始时没有周转资金,向亲戚朋友借钱,每次都会信守还钱日期。每到给员工发工资的日子,他早早赶到工厂,员工一到就立即递上工资[21]。
与温州移民海外的华人讲义气不同,外国人更重视合同上的条文契约。DHL在意大利那不勒斯租用大楼建中国商城,与当地人讲好租用三年之后,再以一千万人民币价格买下来。然而三年过后,对方不想履行承诺,于是打起官司,由于缺乏凭证,DHL只好续租。商城70个商铺,只有一个商铺租给了意大利人,其他全部租给温州人,因为这个意大利人是DHL的朋友,不会像其他意大利当地人那样不赚钱就不付租金,还得打官司;温州人则不同,只要租了摊位,就会缴纳租费。
考察这些海外移民的商业行为模式,可以看出他们之间的信任是对人的信任,是一种“义”或者“兄弟情谊”,是靠自身的一种起码的道义去做事,而不是像西方人之间靠契约的约束而履行条规。这构成华人企业的重要特点,即“严重依赖人际关系和‘善意’”[22]8,这种“善意”更多是个人自发的对讲信用的坚守和认同,即使没有外在法律契约的束缚,依靠道德自律亦可产生自我约束的作用。事实上,市场契约与义气不应该矛盾,一个讲信用的人也能很好地履行契约;然而,一些国外的商人因为谙熟本地的商业运作套路,即使白纸黑字写明,也懂得利用商业契约中的漏洞趋利避害,从而使得一些华人企业家“有苦难言”。意大利的普拉托省是一个以纺织业为主的城市,最近十多年来,这个城市有许多来自温州的移民做“快速时尚”的服装加工作坊,使得普拉托成为时装界与时尚紧密相连的重要基地。由于温州移民众多,普拉托甚至被称为“温州城”。意大利Guercini研究发现,当地许多华人并不愿意接意大利人的订单,他采访的一位华人这样说:“真正严重的问题是,意大利人不支付报酬。他们或先叫华人干活,然后说会支付报酬的,但他们支付的前提条件是,在双方商定的价格基础上再扣除30%~40%。有些意大利人故意申请破产,这样就不用支付已经为他们干活的许多作坊的报酬。当他们对作坊的欠债达到50万欧元时,关闭工厂处境会更好。在普拉托,很难找到一个从未被意大利人欺骗过的老板。我经营的作坊由此损失了数百万里拉。我曾去向意大利人收款,但老板的女儿对我说:‘这不是我的名字。这笔账是已经倒闭的父亲的。’她就这样继续经营着父亲的事业,扣着我们的钱。”[22]54
华人移民行事中强调对他人的“义”,而西方人则不同,更强调的是个人的权利。西方人做事首先要签订合同,“口说无凭,立字为据”,契约的签订是对双方义务和权利的规定。有时白纸黑字的写明也难免有所疏漏,给不想履行义务而只顾享受权利的人以可乘之机,这时候难免要诉诸法律。然而,即使有各种法律契约的存在,当熟悉某一法律契约而心存恶意时,依然可以利用法律契约逃脱制裁,从中获利;即使受到道德的谴责,也于事无补。孔子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17]136可见,孔子不希望有诉讼的存在,而是希望人们都能够做好自己的本分,尽到自己的责任,从而能够与他人和谐共处。《周易注疏》记载:“天与水违行讼,君子以作事谋始。”[23]156王弼解释说:“契之不明,讼之所以生也。物有其分职,不相滥争,何由兴讼之所以起?契之过也。”[23]156-157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在契约中没有条条在目,给人以可乘之机,导致诉讼的发生,这是“契之过”。唐朝陆德明讲到:“物既有讼,言君子当防此讼,源凡欲兴作其事先须谋虑其始,若初始分职分明,不相干涉,即终无所讼也。”[24]157如果双方都能讲义气,按照“物有其分职,不相滥争”去做,把自己本分内的事情做好,即使没有契约存在,双方完全履行自己的义务,尊重对方的权利,那么有无契约都不重要,诉讼自然也不会发生。
温州人自古就有比较严格的自律,即能够尽力完成自己的义务和本分,大多数人都能够做到此点,即使没有法律,也可以形成一个稳定和谐的社会。明嘉靖《温州府志卷一·风俗》记载温州地区人们“务省事知耻自爱,鲜乐争讼”[24]。当下浙江籍海外华人移民讲义气正是体现了对中国固有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坚持。就像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所说:“个人尽自己义务为先,权利则待对方赋予,莫自己主张。这是中国伦理社会所准据之理念。而就在彼此各尽义务时,彼此权利自在其中;并没有漏掉,亦没有迟延……在中国弥天满地是义务观念者,在西洋世界上却活跃着权利观念了。在中国几乎看不见有自己,在西洋恰是自己本位,或自我中心。——这是很好的一种对应。”[25]由此可以看出,“重人情、轻契约”正是海外华人彼此间一种“义”的信任、“仁”的践行。“义”的存在保证了利益双方既能够得到相应的利益,也是对双方本分行为的约束。因此,这种“讲人情”和一些研究所批判的拉关系、走后门并不是一回事。一些华商也提到,当他们在国外做生意久了,回到国内做生意,也并不适应国内过于注重关系的人情社会;在国外,华人既注重人际关系,亦遵纪守法。
总之,浙江海外华人移民一方面遵守现代商业规范,遵循契约精神;另一方面,他们秉持中国传统的义利观和诚信精神。他们不仅着眼于经济利益,更愿意参与中国和移居国的社会公共事业和慈善活动。同时,勇于跳出传统“熟人社会”圈子的藩篱,将视野放在更广阔的群体和世界中;不仅遵守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德观念,也乐于接受并实践现代契约精神。相比较之下,与第一代华人“新移民”相比,华人二代在教育程度、思维方式、视野等方面已有很大不同,他们在创业动机、行业准则以及经商目标与策略方面不同于父辈,较易融入移居国,并拥有更多职业发展机会和平台[26]。不过,这并不代表华人二代不再传承父辈所秉持的文化价值观。现代的商业伦理并不能排除和否定传统的儒家商业伦理道德,而是需要不断继承和发展,并能够通过约束公权力和规范商业社会,实现在现代法治社会的转型[27]。华人二代乐于在移居国当地的政治、社会以及公共事业领域发出华人的声音,做出华人的贡献,不再只是囿于华人固有的社交圈子,而是有着更加开放的国际视野,获得了所在国家社会的肯定和赞赏[28]。《论语》中说:“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17]132从这个角度看,华人二代正是把父辈囿于“熟人社会”的文化价值观扩展到了与移居国当地居民互动以及跨国商业活动中,在契约式信任合作的基础之上,取得了商业上的成功,获得了所在移居国家的认可[25]。因此,中国传统的商业伦理道德规范成为海外华人二代所拥有的文化资本[29],是他们取得商业成功的重要文化基因。
3 结 语
本文运用“文化模式”理论,从《论语》中的传统文化思想入手,解读浙江海外华人移民商业行为背后的文化内涵,分析其如何通过遵循中国传统人情文化模式实现商业上的成功。可以看到,浙江籍海外华人移民把血缘关系、老乡关系扩展到企业经营中领导者与员工的关系,即伙计制,有效地解决了创业时期企业凝聚力和融资的重要问题;同时,其讲义气反映的文化模式是中国传统文化模式的延伸和当代实践,这是在理清契约文书的弊端之后,提出人本身讲信用、重道德,才是讲信用最根本和最重要的保障。从文化角度考虑,伙计制是不同于亲人、朋友关系的新型人伦关系。不过,如果固守这样的圈子容易使华人封闭自己,“爱抱团”,对当地政治、社会公共事业参与程度低,从而显得格格不入[30],这也是单纯传统人情文化的固有弊端。在现代以市场经济为主体的社会,中国传统“熟人社会”中的人际信任无法走向“陌生人社会”,无法适应全球化背景下新时代经济转型带来的各种挑战。因此,只有通过契约式的信任合作,才能使得海外华人在商业领域走得更远[31]。在他们身上体现了文化模式理论中“文化整合”的概念:“文化模式具有可塑性。因此,文化不是固定不变的,不是同质性的,是可变化的。”[14]233-234文化具有相对性,即文化不该故步自封,而是要对各种文化秉承开放和宽容的态度,从而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理解和沟通[14]249。这些都为如何把中国传统的文化模式融合于现代的商业行为实践,如何运用中国传统文化要素处理当下出现的社会经济文化问题提供启示。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主要运用文化模式理论,采用阐释学的研究方法,阐释浙江籍海外华人移民商业行为背后所蕴含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阐释学方法使用目的是为了从具体人的研究中获得“意义”,从而达到对所研究对象的共情和理解;所使用的案例主要来自于笔者在丽水青田和温州乐清北白象镇的实践调查,所搜集的相关地方材料倾向于具体个案细节的质性研究。由于笔者有限的实践调查材料和自身研究能力所限,对当下中国如何应对现代性的挑战,尚缺乏具体可操作性的启示。这需要深入调查华人二代的商业行为,以获得更加深刻的认识,同时也是本研究未来的努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