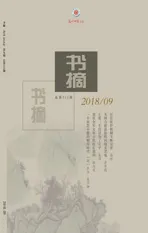《海霞》背后的故事
2019-01-04李晨声
☉李晨声
发生于1975年的《海霞》事件,距今已经四十多年了。其间,政治风云变幻,人事更迭繁复,几个当事人先后辞世更使人感慨万端。我作为幸存者,将这一事件尽可能完整地说清楚,既是应尽的责任,亦是不容推辞的义务。
难产的《海霞》
想把黎汝清的小说《海岛女民兵》改编成电影《海霞》,是谢铁骊导演1972年的打算。当年8月,谢铁骊、钱江、王好为到浙江、福建沿海体验生活并选外景地。回京后,王好为等立即开始为本片选演员。
此刻,江青却责令重拍样板戏《海港》,由谢铁骊任导演、钱江任摄影。紧接着又让他们赶拍样板戏《杜鹃山》,《海霞》的拍摄只得一推再推。这期间,曾让凌子风导演执导《海霞》,但样片不理想,拍摄半月便停产了。
由于谢铁骊连拍四部样板戏有了成绩,被擢升到国务院文化组创办领导电影创作,又兼任北影厂核心领导小组组长,使他《杜鹃山》杀青后亲自导演《海霞》的计划泡了汤,只好改由钱江、陈怀皑、王好为担任导演,钱江、王兆麟、李晨声担任摄影,于1974年7月28日开赴福建漳浦。《海霞》在搁浅多时后终于开拍。
由于《海霞》是民兵题材,需得福州军区支援。影片拍摄报告由周恩来、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圈批”,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叶剑英也签字“批准”。
福州军区司令员皮定钧指示驻漳浦的31军要把协助拍摄《海霞》“当一个政治任务来完成”。31军军长兼任协拍小组组长,并让边防5师参谋长坐镇摄制组具体负责。摄制组住进海边军营,营中官兵只好外出拉练。协拍组与摄制组人数比例为1∶1,他们对摄制组照顾得无微不至。
《海霞》的创作班子及演员阵容都由谢铁骊指定,样片每批都看。影片拍摄还算顺利,只是大海霞的表演不甚理想。谢铁骊在电话中对陈怀皑、王好为一再喊话:“不要示范,要多启发!”陈、王无奈地说:“还是您来吧。”谢铁骊果然立即飞到漳浦,苦心启发,但仍未奏效。回京后的内景拍摄中,谢铁骊每场亲自点拨,还是没能挽回颓势,最后只好尽量将主角拍成“侧背前景”或干脆置之镜外。这样,使本来就没能达到“三突出”原则要求的剧作基础,在拍摄时又打了折扣,“三突出”成了“三陪衬”;不过,从样片看画面质量不错,看过的人都很兴奋,对这部即将完成的影片充满期待。

李晨声(右)和钱江(左)在《海霞》外景地的海边
谢铁骊三告文化部
1975年1月25日影片正式送文化部审查。谢铁骊怎么也没料到,于会泳、浩亮、刘庆棠在刚登上部长宝座之后,立刻对他痛下杀手,而祭起的大杀器正是当时提升到文艺创作必须遵循的“三突出”原则。
审片时,三位部长嬉笑嘲讽,极尽挖苦之能事,让陪同审片的谢铁骊颜面尽失。最后,于会泳归纳了审查意见:主题思想不明确;一号人物没有树立起来,没有围绕着她组织安排贯穿性的中心矛盾线,既没有做到“三突出”,也没有做到“三陪衬”;影片结构松散,像一个“头大、脖子长、身子短的怪物”;有些细节不妥,片中解放军未经同意就抢着吃海霞家的苦菜,然后给她端来白米饭,是“拿穷人开心”,“不符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小海霞到前线送水,指导员为掩护她而受伤是给一号人物抹黑……总之,影片“除了个别外景镜头拍得较好”外,遭到全盘否定。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他们一再声称影片失败的根本原因是没有学习样板戏的创作经验,违反了“三突出”原则。须知,文革中谢铁骊拍摄了《智取威虎山》(京剧)、《红色娘子军》(芭蕾舞剧)、《龙江颂》(京剧)、《海港》(京剧)、《杜鹃山》(京剧)等多部样板戏,又是文化组推导“三突出”原则的创作办公室主任。这一顿迎头棒喝,把谢铁骊逼到了死角。盛怒之下,谢铁骊青光眼复发,住进同仁医院;钱江也因心脏病住进积水潭医院。
谢、钱住院,只好由陈怀皑、王好为、李晨声、王兆麟、谢飞(电影学院实习教师)对影片进行修改,方案经谢铁骊首肯,补拍、修剪了一百多处,看过的人都说比修改前的好。

李晨声(右)和蔡明(左,饰小海霞)、润红(中,饰阿洪嫂王苏娅的女儿)
6月15日再次送审,又被文化部驳回,理由是“吃苦菜”和“送水”两场改得不彻底。谢铁骊急了,把我找去要给江青写上告信。我担心地说:“这一写信,和于、浩、刘的关系不就更僵了吗?”他气呼呼地回答:“把关系弄僵的责任不在我。”
信连夜写成,我因为字写得不好,请岳母张楠代抄。她看了信稿,顺手做了些修改,精炼了,也刚健了许多,加上字体挺拔,确实有别于我们以前给江青上书的风格。信中表示“如完全按照部里的意见修改,不仅费力,而且势必改变人物关系,伤了影片的筋骨,造成支离破碎的结果”,“组织上服从,但思想上一时不能想通”,希望江青“能看看双片”给予“帮助和支持”。信经谢、钱签字,6月16日送江青。
江青很快做了批示:“北影的事不清楚”,“既然拍了,改了一百多个镜头,建议上映,组织评论队伍评论。”6月18日,她还致函张春桥:“我压了一些件,并告诉过文化部的负责同志我们今后不负责影片的审看,保留评论权。”张春桥在江青的信上批了‘同意’。这是个积极的办法。”然后将江青、谢铁骊、钱江的信全部转给文化部。
谢、钱越级告状,于会泳十分恼怒,立即向张春桥建议:《海霞》仍“按未经修改过的样子上映,就是他们送中南海审看的样子上映”。于会泳强调中南海看片的事,是吃准了江、张一伙反对周恩来总理的心理。
此时,《海霞》修改小组还在苦心孤诣地修改“吃苦菜”和“送水”,徒劳地企盼争执双方都能认可。6月22日将第三稿送审,部长们根本不予理睬。
6月24日,刘庆棠到北影召开全厂大会,宣读了“文化部核心组给北影厂核心领导小组及全厂革命同志的公开信”,认为江青、张春桥的批示“非常及时,非常必要”,“必须坚决贯彻执行”,并宣布文化部关于《海霞》的处理决定:“完全按原来的上映”,修改的镜头“一概不用”,因为“似是而非的修改,对于双方都是不得满意的”,“要通过上映,让广大群众进行评论”。
江青明显偏袒文化部,使于、浩、刘兴高采烈。谢铁骊却自做多情地认为江青同意上映《海霞》的修改稿,文化部有偷梁换柱之嫌。于是让我立即写信向张春桥申诉。此信仍由张楠修改誊清。
张春桥却批复:“我们也没有肯定按修改过一百多镜头的片子上映”,“既然文化部认为以上映未改本为好,可以照文化部的意见办”。江青在此件上批了“同意”,并将此件和谢、钱的申诉信一起转给文化部。这个“终审判决”,使谢铁骊的“防守反击”宣告失败。
7月4日,刘庆棠、浩亮在北影全厂大会上,宣读了张春桥的批示和文化部致北影第二封公开信,号召全厂批判以《海霞》为代表的文艺黑线回潮、坚决打掉北影厂行帮性的导演中心制和专家治厂路线。

海霞(由吴海燕饰演)
《海霞》修改组提出:“既然进行了修改,比原稿好,为什么还要上映原来的?不管双方是否满意,应当让八亿人民满意。”刘庆棠威胁道:“要提高警惕,防止被人利用”,“我已闻到一种五七年右派向党进攻的味道”。
他们另找人强行把影片退回原稿。然后,查封了剪辑室,封存了《海霞》全部底片、样片、磁带。这是建国以来对电影从未有过的严重杀伐。一时,厂里大字报铺天盖地,大会小会不断,讨伐《海霞》的声势越搞越大。
刘庆棠召开北影中层干部以上参加的“中型会”,特别通知王好为和我参加。进场途中,偶遇一直暗中支持我们的北影领导小组副组长丁峤,他紧张地望望四周,然后对我面无表情,口唇不动地小声说:“今天可能要动你,小心点。”
“动我?动我什么?怎么动?”一连串问题在我脑子里翻腾,以致开会后刘庆棠说了什么,我全没听清。突然,他猛拍桌子,声色俱厉地叫我站起来。会场一下子寂静无声。只听他大声质问:“谢铁骊、钱江的告状信是不是你写的?”原来为的这件事,我淡淡地回答:“不是。”
他看到自己精心构思的“闪击战”未能奏效,叱骂道:“这就怪了!谢铁骊、钱江一个住同仁医院,一个住积水潭医院,却能同步行动,一再写信,不是你干的才怪!”见我不吭声,他又猛地叫起了王好为,让她就谢、钱写信的行为表态。会场上的气氛几乎凝固了。王好为声音不大却清晰地说:“越级给领导写信,并不违反党章宪法,没有错。”
刘庆棠气得说不出话,浩亮跳了起来,挥着大蒲扇对空叫阵:“你们谁干的?有种就站出来较量较量!”
他们怀疑谢、钱背后有人操纵。会后更加起劲地“抓黑手”、查笔迹,查了十几天,让厂里的秘书科翻遍了我们的档案,比对字迹。
此刻,在医院中的谢、钱二位更是焦急万分。谢铁骊又一次令我给王洪文写信求助,信中提不出什么更新的论据,明显地苍白无力,方寸已乱。大家寄予最后希望的是钱江写给周总理的求助信。等了许久,总理办公室负责人罗青长才沉重地回答:“总理连续动手术,实在不能打扰了。”他还转达邓大姐的八个字:“顾全大局,保重身体。”
一时黑云压城,《海霞》组陷于彻底绝望之中。
胜利到来得多么艰难
1975年7月5日由邓小平提议,经毛主席、党中央批准,国务院设立政治研究室,由胡乔木、吴冷西、邓力群、胡绳等同志组成。
1975年7月9日、20日,邓小平向政研室负责人两次传达了毛主席对文艺工作的意见:“样板戏太少。而且稍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邓小平要政研室注意收集近些年来文化、科学、教育、出版系统不执行双百方针的材料,以供整顿文艺的需要。
7月20日,始终关心《海霞》命运的岳母兴冲冲地回来说:“老邓被落实政策,安排在小平同志的政研室工作。我把你们的困境告诉他,他很关心,邀你们去谈谈。”老邓是指邓力群,他是岳母的老朋友、老同事。对于他,一个刚刚被解放的老同志能解决多大问题,我们没敢抱什么希望。
当晚,邓力群在家中听了我和王好为详尽的汇报后指出:文化部这么干是完全违背党的文艺方针的。现在百花齐放没有了,好的小说、诗歌、散文、文艺评论都没有了。有的只是“三突出”。为什么一定要“三突出”,可不可以两突出?一突出?
一时,我俩全惊呆了。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这种话不要说讲,就是听,也足够当反革命了。最后他建议我们据实给毛主席写申诉信,他可以负责转交。
回到家已是深夜。待把情况复述了好几遍后,岳母兴奋地说老邓这个人从不随便讲话,敢这么说,肯定大有来头,看起来我们党和国家有希望了。谈到写信,我和王好为毕竟人微言轻,还是说服谢、钱二位,由他们署名,影响会大些。

小海霞(由蔡明饰演)
次日一早,我和王好为不顾重重监视,和谢铁骊见了面。他闻讯后很意外,也很冲动,同意出面写信。随后我赶到积水潭医院,钱江正和同病房的李少春聊天,我把他引到楼顶平台,小声而急促地介绍情况,他痛快地答应写信。
7月22日夜,邓力群在他家邀谈谢铁骊和驻北影军代表中唯一支持我们的惠宏安以及我和王好为。最终决定给毛主席的信由谢、钱署名,仍由我执笔,请邓力群把关。最后,大家一致表示要为捍卫党的文艺路线而奋斗,情绪庄严而激动。
北京七月底,溽暑难挨。为安全起见,我和王好为、惠宏安在八三四一部队宿舍惠宏安家中写信。老惠是副营级干部,住房狭窄,妻子和几个孩子要睡觉。我们只有挤在他家的小厨房里工作,还不敢开门,热得透不过气来。按邓力群“所写的一切都要实事求是,经得住调查。不得有半分虚构,也不要有一句赘言”的要求,我深感下笔维艰。三人字斟句酌,一封信竟写了整整一夜。
第二天上午,顾不得彻夜未眠,我和王好为骑车赶到邓力群同志家请他审定。惠宏安鉴于前不久发生的“对笔迹、查黑手”,要求这封信一定要谢铁骊亲自抄写。谢誊写后,发现一个错字,却拒绝我们让他重抄的建议,顺手在信上涂改了。谢、钱具名后,交邓力群转送。
这封信长达两千余字,据实反映了文化部于会泳、刘庆棠等背离党的文艺路线,以势压人,围剿《海霞》的行径,要求按修改稿上映。
此信经小平同志呈毛主席后,很快就有了回音。7月29日,毛主席在信上画了圈,批示:“印发政治局各同志。”
7月30日晚,小平同志与在京的八位政治局委员李先念、华国锋、余秋里、张春桥等在人民大会堂放映审看了《海霞》修改前后的两稿双片,长达四个钟头。看片时,钱江、谢铁骊坐在邓小平、李先念身后,对首长的提问,一一做答。另一侧的张春桥、于会泳、张维民则一直缄默不语。

著名导演谢铁骊
次日,邓小平主持政治局开会,作出了“《海霞》按作者修改过的影片上映”的决定。北影很快召开全厂大会,丁峤兴奋地传达了毛主席关于《海霞》的批示和中央政治局的决定。文化部无奈地给北影发出公开信,表示“一致完全同意”政治局意见,对《海霞》“要承担主要责任”,要“认真总结经验,吸取教训”。
群众写大字报指责:文化部前两封信对江青、张春桥的批示表示“热烈拥护”,这次政治局正式决定,你们仅仅表示“同意”,难道政治局做决定,还需要经你们同意吗?还有一些同志写材料揭露他们肆意践踏党的双百方针、大搞一言堂、压制不同意见,要我们设法转交给邓小平。
当材料交给邓力群时,我说斗争很复杂,这些材料中有的很尖锐,希望能保护这些同志。他默默地点点头。
《海霞》摄制组在第一回合的斗争中,在邓小平及政研室的支持下,暂时占了上风。可是不久,形势陡然生变。
暴风雨来临之前
9月15日,在大寨召开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江青说:“宋江架空晁盖,现在有人架空毛主席”,“我们党内的投降派、修正主义者干的事情,是公开的敌人做不到的……”
9月18日下午,江青单独召见北影、长影的人开会,点名批评邓小平。还说:“那天讨论《海霞》叫我去我没去。我要是去就大闹政治局,绝不会让他们通过。《海霞》不是部好影片,把主要英雄人物塑造成了城市大小姐。现在不批,将来要批,这笔账以后还要算!”
与会的北影老同志崔嵬、张平回京后,马上找到我,透露了消息,并忧心忡忡地嘱咐“要小心,千万谨慎从事!”
我和王好为把这风云突变的情况报告了邓力群,请他们早做应变准备。他沉吟良久,半天没有说话。第二天他把我俩找去,说已经向小平同志做了汇报。邓小平说:毛主席对江青在大寨的讲话很生气,说“江青放屁,文不对题。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又过了些天,他再次让我和王好为到他家,神情严肃地说:“将来要是实在挺不住,你们可以交待,但一定要按照事实的本来面目说。千万不要为了过关而添油加醋,把事情搞乱。”然后,他拿出前些日子我交给他那些群众写的揭发材料,当面一一点清撕毁,冲下抽水马桶,并郑重地让我通知这些同志可以放心。我明白这是在对事态做最坏的准备。
打倒“四人帮”以后,看到政研室一些简报,才知道邓力群在高压下,诚实无畏地担当了一切。
意想不到的演说
打倒“四人帮”之后没几天,《海霞》不仅彻底平反,而且出现在中共中央的红头文件中,被列为揭批“四人帮”的典型材料之一。于是,来采访的媒体蜂拥而至。开始两天的兴头一过,谢铁骊就不耐烦了,把这个任务推给我和陈怀皑导演。
1978年底,应北影要求,邓力群来厂做了个报告。讲话结束,不知是谁递了个条子要求介绍《海霞》事件的内幕。邓力群先是惊讶:“你们厂里发生的事还需要我来介绍吗?”经大家再三要求,他才据实做了介绍。出人意料的是,他除了介绍谢铁骊等主要人物的事迹外,着重地谈到我和王好为、惠宏安,并进行了褒扬。在场听讲的我完全懵了,丝毫高兴不起来,反而忧心忡忡。因为这和当时厂里及社会上流行的说法距离很大。当然,这次讲话也有积极作用,终于在群众中阐明《海霞》事件不再是哪个了不起的人物单打独斗、主动出击的传奇故事,而是一个群体在面临高压时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进行的一连串的斗争之一,是小平同志领导的全面整顿斗争中一个极小的部分。
2004年9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邓小平的二十四次谈话》,其中数次提到《海霞》。1975年7月26日,小平同志传达了毛主席对《创业》的批示。邓力群谈到《海霞》组给毛主席的信时说“有了《创业》的批示,关于《海霞》的争论就解决了。”还说“一些报刊的文艺评论文章把‘三突出’说成是适用于一切艺术形式的原则,有绝对化的倾向,我不同意”。小平同志说:“是啊!我们社会主义社会里还需要有讽刺文学。人民代表大会每次都有侯宝林当代表,而且主席每次开会都要问一问有没有侯宝林。”
1975年8月8日,在政治局决定“《海霞》按作者修改过的影片上映”后的第八天,小平同志在政研室会上再次提到《海霞》,说:“这部影片不算很好,但可以放映。文化部压制是不对的。文化部对一些问题的处理很成问题……”。至此,小平同志总结了围绕《海霞》这场斗争的原委,明确了党领导文艺的正确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