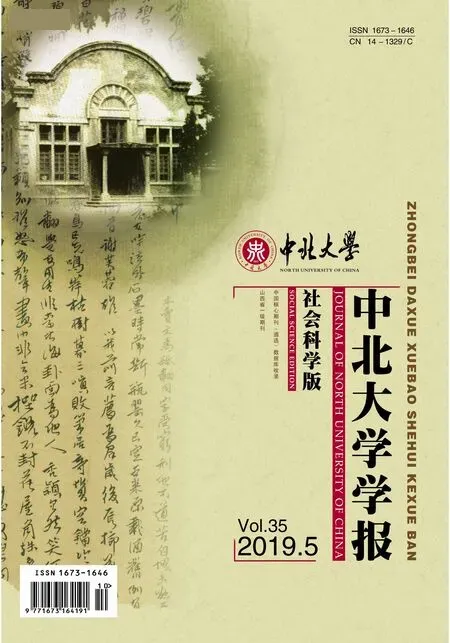从饕餮到“无脸人”
——东方神兽与基督教元素的对接
2019-01-03庞燕宁
庞燕宁
(山东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 山东 青岛 266590)
0 引 言
2001年7月由宫崎骏导演的动画电影长篇《千与千寻》(SpiritedAway)在全球动画界具有无可替代的地位, 它斩获包括第75届奥斯卡最佳动画长片、 柏林电影节“金熊奖”、 威尼斯等国际电影奖项在内的各种奖项。
宫崎骏在影片中成功塑造了一个家喻户晓的“无脸人”形象, 该魔怪形象博得了受众的喜爱。 “无脸人”的形象复杂、 多变, 他时好时坏, 在善恶之间相互转化: 变坏之前非常乖巧, 不会说话, 只能发出“啊哦啊哦……”的声音, 如同婴儿。 当它变坏时则暴露出贪婪的本性, 成为一个暴食暴饮的怪兽。 他还非常残暴,发脾气时变成椭圆状, 浑身上下只剩一个器官——大嘴, 并生吞得下三个活人。 变好后又乖如儿童。 该形象被认为是具有日本本土特色的卡通人物形象, 笔者认为, 该人物原型可以追溯到中国神话传统的饕餮怪兽形象,而其所犯罪行及受到的惩罚可追溯到西方中世纪的基督教文化, 其善恶可来回变化的属性则酷似日本本土教“神道”中的自然神。 可见, 该形象经过三种文化的受容, 最终成为典型的具有鲜明日本本土文化特色的怪兽。
1 日本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融摄
一部日本电影动画却具有西方中世纪基督教的文化因素是不足为奇的。 宫崎骏出生于1941年1月正值二战期间, 早年便开始接受全面的西方教育。 宫崎骏因为战争缘故在鹿沼市的乡间原野度过了田园牧歌般的童年。 二战结束后, 宫崎骏全家搬回东京, 宫崎骏开始全面接受战后以来的西方教育。 宫崎骏经历了日本前所未有的本土文化重创时期, 那时“日本人遭受了二战后的战败的悲伤, 并遇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时代大变局后的日本, 直到今天还置身于对传统文化进行极端批判和排斥的暴风骤雨之中”[1]2。 历史上日本醉心于西方文化, 主张脱亚入欧论, 直接输入西方文化。 在始于1868年的明治维新的前20年内, 达到狂热程度, 以福泽谕吉为代表的“明六社”不遗余力地开展启蒙活动, 号召对西方文化的全盘吸收。 作家森鸥外宣称:“彼(指西方)之所长并存于精神与技术两方面, 我国人唯予模仿与崇拜可也。”[2]但是进入明治二十年代以后, 国粹主义之风兴起, 猛烈批判“文明开化”运动是“以美为母, 以法为父, 妄自移风易俗, 傲奢淫荡”[2]。
日本的这种世界观尤其体现在宫崎骏的电影动画制作中。 西方文化对宫崎骏的思想成长影响很大, 他的许多作品取自欧洲文学作家的经典。 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 宫崎骏是第一位将动画上升到人文高度的思想者, 具有辩证的人文主义思想。 早在动画影片《风之谷》中就有宗教般的结尾, 而《千与千寻》所体现出来的文化更是一种东西方融合体, 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基督教价值观在东方神话元素上的大量植入。
通观日本文化的发展历程, 本国传统文化与外国文化的风潮之间的关系是主从或者受容。 外国的东西具有强烈的自我表现倾向, 而日本文化的特色在于简素精神, 具有强烈的自我抑制倾向。[1]322日本本民族的东西——简素精神和以此为根本的颇具特色的世界观(自我抑制性的主体性)——与西方文化中新事物的相容,从而获得自我创造、 自我启发的民族性。 日本的这种世界观自古以来就潜存着, 但至今未被自觉认识到。[1]324它是世界文化的一个独特组成部分。
日本神话中有诸多中国古代文化元素和观念与日本固有的文化元素交织在一起。[3]273日本文化可区分为模仿文化和独创文化, 日本人就其民族性来说, 是经常积极地受容外国优秀文化的。 日本自古就长期受容朝鲜半岛、 中国大陆的优秀文化, 从而构筑起本国的文化, 近世后期又把注意力移至欧美文化, 吸取受容, 直至今日。 日本的模仿文化指天平文化、 桃山和江户初期的文化。[1]98明治以后开始受容欧美发达国家的文化, 在模仿的同时对日本的固有文化也有所自觉和发展。 在受容过程中, 仍保存了日本本民族的东西, 而并不是无批判地原封照搬或无原则地盲目追随,[1]195-196使之逐渐自觉到本民族的文化特性, 作适合于自己的变更, 最终彻底还原为日本化的东西。
在《千与千寻》中, 宫崎骏以中国古代神话饕餮凶兽为原型塑造了“无脸人”这一财神怪兽的形象, 但是中国周商时代对饕餮纹的“尊神”意识和“敬天法祖”却消失了, 与日本本土神道教受容, 同时又植入西欧中世纪基督教中七宗罪理念, 于是宫崎骏通过这三重文化的受容, 创造出 “无脸人”形象, 使之成为典型的具有鲜明日本本土文化的怪兽。
2 “无脸人”的原型——饕餮
饕餮是中国神话传说中的神兽, 是“四凶”之一。 传说黄帝战蚩尤, 蚩尤被斩, 其首落地化为饕餮。 在《左传·文公十八年》中有这样一段记载:“缙云氏有不才子, 贪于饮食, 冒于货贿, 侵欲崇侈, 不可盈厌, 聚敛积实, 不知纪极。 不分孤寡, 不恤穷匮。 天下之民, 以比三凶, 谓之饕餮。”杜预注疏:“贪财为饕, 贪食为餮。”其又载:“舜臣尧, 宾于四门, 流放四凶族:浑敦、 窮奇、 梼杌、 饕餮, 投诸四裔以御先螭魅。”[4]416易言之, 在鲧治洪水过程中, 饕餮为尧舜相对抗的四大诸侯之一, 被舜流放。 据《尚书·舜典》载:舜“流共工于幽州, 放驩兜于崇山, 窜三苗于三危, 殛鲧于羽山”; 《左传·文公十八年》亦载:舜“流放四凶族:浑敦、 穷奇, 梼杌、 饕餮”[4]416。 这里所谓的“四凶族”分别指驩兜、 共工、 鲧和三苗。
饕餮作为凶兽样子的记载很多, 但不尽相同。 据《神异经》记载:“饕餮, 兽名, 身如牛, 人面, 目在腋下, 食人。”[5]6在《千与千寻》中, “无脸人”食人, 面如人脸, 贪吃时体型变得强壮、 巨大。 “无脸人”也极为贪食, 能把满满一整间屋子的食物吃掉, 身体变为椭圆状, 与其说是身子不如更像是一个大头, 因为浑身上下只有中间一个器官, 那就是大嘴, 因而也有头无身。 《吕氏春秋·先识览》记载:“周鼎着饕餮, 有首无身, 食人未咽害及其身, 以言报更也。”[6]其中的“食人未咽”跟“无脸人”酷似, 后者活吞下三个人, 并没有咀嚼, 就是上文所指“未咽”, 即未能把人咀嚼消化, 最后把他们完整吐了出来后三个人物又活了。 《山海经·北山经》有云:“其音如婴儿, 名曰狍鸮, 是食人。”[7]据晋代郭璞注解, 此处“狍鸮”即饕餮。 在这里记载的饕餮都食人, 音如婴儿。 在影片中, “无脸”在变坏之前不会说话, 只能发出的“啊哦啊哦……”的声音, 如同婴儿。 与千寻一起坐火车的时候, “无面人”在千寻面前突然变成了乖小孩。 陆荣(1436-1494年)在《菽园杂记》中最早的记载中, “饕餮性好水, 故立桥所。”[8]142而“无脸人”最初两次出现都是在桥上, 立在桥的一侧, 还出现在雨夜, 可见其性好水。 由此可见, 宫崎骏以中国神话的饕餮为原型塑造了“无脸人”这一形象。
3 多种文化的共体与改造
在中国古代神话中, 饕餮神兽的意义是什么呢?饕餮纹或是兽面纹作为铸造刻饰通常出现在商周青铜器上, 这种概括夸张的动物纹饰和造型反映了当时中国古人对自然神的崇拜, 因而有着神秘而肃穆的气氛。 青铜器是殷商先民“尊神”意识的体现, 周代则发展为“敬天法祖”, 形成宗教、 政权、 族权三位一体的表征。 大部分学者认为, 商周统治者用青铜器纹饰的“狰狞恐怖”来表达王权的“神秘威严”。 张光直先生认为这些动物纹样不是为了威吓, 而是为了与神沟通。 人们乞求神灵, 取悦神灵, 借助神力以支配事物。[9]但是, 在宫崎骏的《千与千寻》中, 中国神兽的这种神秘、 威严与肃穆感已经消失了, 其形象酷似日本本土教“神道”中不分善恶、 善恶可来回变化的自然神。 日本神道源起于日本神话。 日本原初的神包括日、 月、 星、 风、 雨、 雷等天体现象、 大地现象, 还包括动植物以及衣食住行水火职业等人类生活中的诸现象, 还有 “人灵”亦为神。 这些“神”没有善恶之别, 无尊卑之分。[3] 260-261日本人认为人性本善, 始终明确否认德行包含同恶进行斗争。[10]171-173日本神道中有“八百万神”之说, 实际上是无穷无尽的意思。[3]261日本本土的“神道从本质上说, 就是一种崇物的信仰体系与宗教精神”, 是日本的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 “日本神道宣扬多神, 历来有八十万神、 八百万神及一千五百万神之说”, 日本“所供奉的对象是自然界的万物”[1]12。 日本人崇拜万物, “崇物是日本民族精神的内在体现”[1]10。 因此, 日本本土文化在与中国神兽饕餮的受容中, “无脸人”变成了时好时坏、 善恶之间相互转化、 乖巧如儿童、 声音如婴儿的亲民形象的神怪, 成为日本特色的本土文化。
饕餮暴食的本性并不符合日本本土文化。 在饮食文化上日本人主张饮食节制, 虽然在余暇爱好烹调多种有讲究的菜肴, 但一道菜只有一羹匙。 对日本人来说吃饭应当是维持生命的必须, 不应把吃饭看做是享乐。[10]163-164现在的日本人仍保持着这种节俭的饮食文化, 一般各吃各的一份, 聚餐也都是按人头准备, 很少有剩菜, 不会像“无脸人”那样大吃大喝, 暴食暴饮, 影片中堆满屋子过剩的菜肴的景象在日本餐饮行业是罕见的。 因而这种罪行在文化根源上并非来自于日本本土, 而是来自欧洲中世纪基督教所定义的“宗教性”的罪。
基督教的“七项永劫之罪”: 色、 食、 财、 惰、 怒、 妒、 骄, 极为夸张地表现在“无脸人”和“油屋”里的员工身上, 以突出这些罪恶对他人的伤害, 这些思想行为罪恶其实被宫崎骏纳入了中世纪基督教道德规范范畴之内, 进行了与西方文化的对接。
按照基督教文化, 员工们表现的“贪婪”是对物质财富错误的爱, “贪色”是对他人错误的爱, “无脸人”不停地送千寻金子, 是对千寻错误的爱; “暴食”是对享乐错误的爱。 这三种罪恶是比较轻度的罪恶, 因为它们还至少保留着对上帝创造物的爱。 “懒惰”之罪比较严重。 “愤怒” “嫉妒” “傲慢”三罪极其严重, 因为这三种罪恶是以“恨”或“蔑视”取代了爱。[11]164-181按《中国大百科全书》记载: 《神曲》是中世纪人生观的最佳表述。[12]218在《神曲》中, 但丁将这三种罪恶认定为三种“怪戾”的爱, 把它们放在炼狱的最底下三层接受惩罚。 其中, “傲慢”是最为严重的罪恶, 因为傲慢是对上帝创造物的轻蔑, 是把自己摆在了一种居高临下的位置, 对上帝创造物的存在提出疑问和挑战。 “无脸人”集上述几种罪恶于一身, 他既暴食、 懒惰、 又愤怒, 对他人傲慢无礼, 还嫉妒千寻对自己的怠慢。 千寻也说“无脸人”来到“油屋”后学坏了。 在今天看来, 某些不严重的思想动机, 如傲慢、 愤怒、 嫉妒, 却被基督教视为最为严重的罪恶。 这种差异的原因主要在于中世纪西欧社会的伦理道德规范具有浓厚的“宗教性”, 而我们当今社会的伦理道德规范具有强烈的“世俗性”[13]44。
在《神曲》的“炼狱”中, 所受上述惩罚的都是由于人的欲望恶性膨胀、 不能节制而造成, 这是基督教思想家进行神学思辨的结果。 但丁为这七宗罪做出了相应程度评定以便惩罚这些灵魂。 在基督教看来, 一个人如果缺少乃至丧失了对上帝、 对上帝创造物的“爱”, 就意味着灵魂的罪恶。 宫崎骏对“无脸人”和“油屋”的员工们所犯的这种“宗教性”罪行进行了贬斥和惩罚。 在“油屋”里, 上上下下每个员工包括最高管理者汤婆婆在内都争着分得财神——“无脸人”的一份金子, 但最后他们不仅没有发财, 反而引来了杀身之祸, “无脸人”开始吃人, 众人纷纷落荒而逃。 在这里, 宫崎骏表明财宝的多少是不可控的, 他对当下社会一部分人贪婪的现象给予了讽刺。 在2016年吉卜力工作室(Studio Ghibli)回复受众的一封信中, 戈尔德(Gold)为宫崎骏代言, 表明了宫崎骏的态度, 他说在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泡沫经济中, 的确有些人变得非常贪婪, 而这些人并没有意识到。[14]
在“炼狱”的第三层, 维吉尔回答了但丁一个问题, 也表达了关于财富的观点。 他说, 因为人们的心太注意物质财产了, 分这种财产的人越多, 每个人享受的便越少。 可是, 如果人们把欲望放在至高的精神上, 那就不生这种烦恼了。 因为在那里只说“我们的”, 人数越多, 每个人的幸福越大。[11]182他继续解释这一悖论:“因为你还是只注意在地上的东西, 所以你从真光里取得了黑暗。 那无穷无尽的财产是在天上, 向着慈爱奔流, 如同光向着明亮的物体一样。 他越是找着了热心的, 越是给得多; 于是慈爱的范围越推广, 永久的善也由此增加; 天上聚集的灵魂越多, 慈爱的互施越广, 如同镜子互相反射他们所受的光一样。”在影片中, 宫崎骏对财富的态度显示了关于爱、 精神和节制的观点, 这与中世纪基督教文化对待财富的观念相吻合。
4 《千与千寻》与《神曲》的互文性
“无脸人”还隐喻了《神曲》中财富之神“百路督”(Plutus)。 前者能随意变出无穷的金子, 是财神的化身。 二者不仅都是财神, 而且身形相似。 “百路督”消失的样子“好像风吹桅断, 帆布落地一样”, 就“倒在地上了”[11]27。 在影片中, “无脸人”变坏时也是个可怕的魔鬼, 可以随意变换身体的形状, 既能变得硕大、 高耸, 也能变得瘦小, 还能瞬间薄得像纸片一样倒地, 这点颇似“百路督”。
《千与千寻》中对贪婪者和浪费者的惩罚也同《神曲》中所描述的场景极为相似。 财神“无脸人”的到来使整个“油屋”里的男男女女骚动起来, 使人不得安宁。 他/她们胸前捧着或者抱着“无脸人”想吃的东西, 频频奔波、 摩肩接踵, 难免不会相互碰撞, 每个人都生怕自己来晚了, 错失了发财的大好机会, 任凭整个屋子堆满了大量被浪费的食物。 他/她们对金子劳碌追逐的场景隐喻了《神曲·炼狱篇》中第四圈被命运捉弄的贪婪者和浪费者。 但丁认为, 爱得太过则表现为“贪”, 它们是贪财、 贪食、 贪色。 我们看到在但丁所描述的地狱第四圈, 生前所贪之人被惩罚的景象甚为惨烈。 浪费者和贪婪者的幽魂对舞着, 彼此都打碎了, 有的胸前推滚着重物, 彼此对撞着, 对骂着对方的罪过, 再转回头来走, “就是这样反复来往, 没有穷尽”[11]29。 这种拿着重物并且相互碰撞的惩罚的场景颇似“油屋”内众人讨好“无脸人”的混乱场景, 二者具有文本间性。
5 结 语
综上所述, 《千与千寻》一方面接受西方基督教和启蒙主义的影响, 其主题带有鲜明的西方基督教人文主义精神; 另一方面在神话结构方面承传了日本本土文化和中国古代文化。 但这两方面并非平分秋色, 而是在受容西方基督教文化后, 对东方神话进行了价值观方面的改造, 从而产生出具有世界性价值且独具日本本土文化特色的文化。 因此, 在宫崎骏的创作中, 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基督教价值观在东方神话元素上的大量植入, 虽然这部动画电影具有浓厚的日本本土文化特色, 但是其中演绎的主题精神不如说更具有基督教价值观, 在一定程度上保存和促使了日本本土文化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