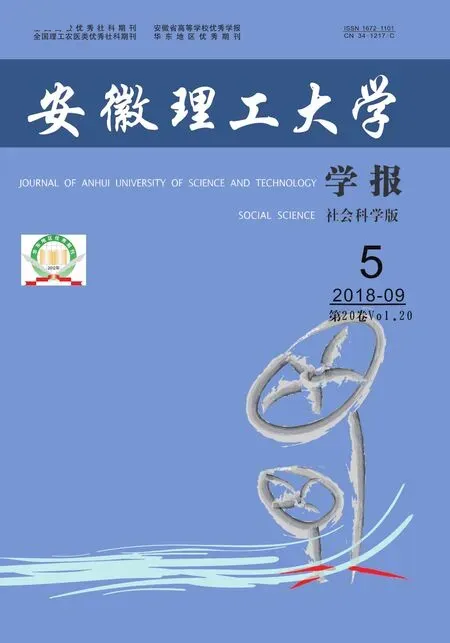暴力与消解
——《嘉莉妹妹》文本内外的话语博弈
2018-12-31赵梦鸽
赵梦鸽,戚 涛
(安徽大学 外语学院,合肥 230601)
西奥多·德莱塞是20世纪美国文学史上令人瞩目的作家。他的小说打破传统,力求以一种纪实的方式反映社会现实。其代表作《嘉莉妹妹》因此成为美国小说史上的经典之作。
文学界对该作品的研究已相当深入。早期评论多以自然主义和左派思想为视角,如门肯的《令人瞠目的德莱塞》[1]、派林顿的《德莱塞:美国自然主义作家的领袖》[2]。当代则向文化视角迁移:一些学者从消费文化角度,揭示了现代化对美国社会价值观和人际关系的冲击,如尼娜·马尔科夫的《<嘉莉妹妹>中的阶级、文化和资本》[3]。另有不少学者从性别角度,分析了嘉莉女性意识和身份的建构,如利马斯特在其《<嘉莉妹妹>中的女性物论》中剖析了嘉莉的新女性形象[4]。但对小说中不同价值观之间的话语博弈却鲜有触及。本文试从新历史主义“文本是话语博弈、角力的场所”这一理念入手,关注该小说文本内外的话语博弈,力图在把握当时美国社会话语生态的基础上,加深对该小说及美国文化的理解。
一、话语视角下的《嘉莉妹妹》
(一)新历史主义的文本观——文本是话语竞争的场所
福柯认为话语是“语言和言语结合而成的更丰富和复杂的具体社会形态,是指与社会权力关系相互缠绕的具体言语方式”[5]128。费尔克拉夫认为“话语是社会权力关系生成和再现的场所,它从事意识形态的工作,展现、加强、再生社会中的权力和支配关系,并使其合理化或对其进行质疑。话语是历史的,它构造社会结构,也被社会所构造”[6]。作为一种审美的意识形态,文学文本内外不可避免地交织着各种话语关系,因此,乔纳森·多利莫尔认为文学研究应从“一个更大的历史语境、社会文本、政治价值取向,去看待文学的现实‘效果’和文学对现实的反应”[7]。上世纪80年代出现的新历史主义就采用了这一视角。
新历史主义同意马克思主义和传统的历史主义批评将文学置于一定历史范畴的做法,但它却不同意把历史仅仅看成是文学的“背景”或“反映对象”。它认为“文学”与形成文学的“背景”之间是一种相互影响、相互塑造的关系;它不仅把历史和文学都看成是“文本性的”,而且认为历史和文学都是一种“作用力场”,是不同话语和兴趣的交锋场所,是“传统和反传统势力发生碰撞的地方”[8]。如格林布拉特所说的,要考察“深入文学作品世界的社会存在和文学作品中反映出的社会存在”[9]。
正如上文指出,这种交锋与碰撞实际上是一种利益上的博弈,体现着权力和支配关系。话语之所以具有暴力,是因为它们总是人为定义并维护着某种等级秩序;而不同话语之间,因为背后拥护群体话语权的大小,也存在一定的等级关系。本文意在从新历史主义角度出发,揭示《嘉莉妹妹》文本内外不同话语之间的等级关系和博弈态势,借以说明德莱塞所处的话语环境、价值主张,以及参与话语博弈的策略。
(二 )《嘉莉妹妹》相关话语概述
过往研究注意到《嘉莉妹妹》与社会达尔文主义、消费主义、女性主义等话语之间的关联,却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两种潜在的话语——精英主义和实用主义及其重要角色。本节将上述话语的主要内涵及蕴含的等级关系做一个梳理。
社会达尔文主义是当时流行的价值观。其代表人物斯宾塞主张,社会进化同生物进化过程一样,遵循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原则。他认为人类存在优等和劣等种族、优秀和低能个人之分。劣等、低能的种族与个体应当在竞争中被淘汰。如此的话语逻辑,树立了所谓“优秀、优等”人士与“劣等、低能”群体之间的二元对立,对后者构成话语暴力。这一价值观与当时同样流行的消费主义结合起来,构成了只有更多物质财富,才能成为成功者和“优等”人士的价值取向。
英国学者卢瑞认为商品的价值取决于消费者的价值观[10]1。“每个人既是价值的评判者也是被评判的对象,人们之所以选择这些商品,是因为它们有相应的等级”[10]13。在消费主义影响下,很多人认为成功仅仅意味着物质上的成功,个人价值唯有通过商品消费来体现。在《嘉莉妹妹》中,消费主义价值观无处不在。这一价值取向的泛滥,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均对弱势群体构成了话语暴力,让其难以找到生命的价值所在。
除了这两种显而易见的话语外,小说中还存在着两种隐形话语——精英主义和实用主义。如果说,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消费主义是美国社会各个阶层广为接受的话语,那么精英主义与实用主义则分属中上、中下两大阶层,构成一种对垒的态势。
精英主义者认为自身具备超越“庸人”的特殊品质,因而高人一等,应享受特殊的待遇。美国的精英主义传统源于清教主义。清教徒自诩上帝的选民、人间天使,天然地优越于那些注定下地狱的庸人。如果说,清教时期的精英主义主要表现为道德和行为上的自律,受现代化的影响,美国的精英主义此后越来越具有物质主义和文雅(genteel)色彩。无论内涵怎么变化,其重点都在于强调自身优越于他人的特殊品质。
建国初期,正是在精英主义者的主导下,美国宪法规定选举权与个人财富直接挂钩。因为在精英主义者看来,只有拥有一定财富的人,道德才足够高尚,才有权参与国家治理——以此对所谓“低能”的穷人,施以话语和政治上的暴力。随着社会财富的增长和民主制度的完善,尤其是新兴资产阶级的出现,财富和选举权丧失了博弈筹码的功效。出于需要,精英阶层一方面继续借助强调自身伪善的高端道德标准,与或多或少存在道德瑕疵的资产阶级实用主义者划清界限;另一方面则倚仗园艺、音乐、封闭的社交圈——舞会、沙龙、姻亲关系等,将自己与社会大众区隔开来,实现一种高贵的隐退。其目的均在于歧视圈外群体,维护自身的优越性。由于德莱塞主要关注中下阶层,所以这一话语在小说中只隐约地在埃姆斯身上有所体现。具体将在后文中论述。
相比之下,作为社会攀爬者的中下层人士所信奉的话语——实用主义则在小说中无所不在。实用主义注重“行动”与“效果”。其代表人物威廉·詹姆斯认为“有用就是真理”。他在《实用主义:旧的思维方法之新名称》一书中写到:“实用主义的方法,不是什么特别的结果,只不过是一种确定方向的态度。这个态度不是去看最先的事物、原则、‘范畴’和假定是必须的东西,而只是去看最后的事物、收获、效果和事实。”[11]他不仅将实用主义看作是一种方法论,并把它归结为一句格言:不讲原则,只讲效果。在那个急功近利的时代,实用主义大潮迅速席卷美国,成为当时一种“美国精神”和大众哲学。
这一话语的后果之一是“道德无用论”——如果说虚幻的道德,不能给人们带来实际的效果,那就是无用的。这一信条有助于抵御精英主义者伪善的道德标准所构成的话语暴力。但是这种只以成败论英雄的话语,也拉低了整个社会的道德底线,对诚实、守信的群体构成了一种话语暴力。小说中的杜洛埃、赫斯伍德夫人、甚至嘉莉等都是实用主义的代言人。
以下本文将对上述话语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展现它们在文本内的博弈生态。
二、文本内的话语暴力
(一)消费主义、精英主义及其话语暴力
20世纪初的美国,资本主义和城市化的发展,让消费主义大潮席卷美国各地。物质和享乐消费,成为生活的重中之重。人们开始习惯于借助炫耀型消费来彰显自己的身份。任何商品,无论是一辆汽车,还是一款大衣,都具有区隔社会等级和身份区分的功能,成为一个人财富多寡、地位高低的象征。处在社会上层的富人们因此获得心理上高人一等的满足感。
嘉莉妹妹离开小城镇,坐上开往大城市的火车,内心渴望的主要是物质上的享受。面对陌生男子的搭讪,嘉莉首先注意到的便是对方的穿着。在她看来:
男人衣服中有那么一种难以言传的微妙界线,她凭这条界线可以区别哪些男人值得看一眼,哪些男人不值得一顾。一个男人一旦属于这条界线之下,他别指望获得女人的青睐,男人衣服中还有一条界线,会令女人转而注意起自己的服装来,现在嘉莉从身旁这个男人身上就看出了这条界线,于是不禁感到相形见绌。她感到自己身上穿的那套镶黑边的朴素蓝衣裙太寒酸了,脚上的鞋子也太旧了[12]8。
斯坦利·科尔金在谈论嘉莉对物质商品的见解时如是说,“在嘉莉面前,一双鞋子所代表的已不仅是其最基本的使用价值,而是气质和品味的象征”[13]。对于一个不谙世事的小镇姑娘来说,物质主义及消费主义观念已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她的举止。和杜洛埃的衣饰相对比,嘉莉不免觉得自己寒酸甚至是低人一等。同样是搭讪,面对具有物质优势的杜洛埃,嘉莉是欣喜仰慕的,而面对和她同样拿着四块半周薪的鞋厂小伙子时,她则是厌恶躲避的。消费主义对中下层民众的话语暴力可见一斑。
此外小说还表明,有钱人的生活不仅是锦衣华服,还享受着经济实力薄弱的中下层民众难以企及的娱乐消遣活动——看戏、赛马等。还有经理赫斯伍德待人接物的不同做派——对穷人的冷淡、富人的巴结等,无不反映出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对中下层民众的话语暴力。
小说中精英主义的话语暴力则主要体现在上流社会生活方式、品味的引导作用,以及中下层人士对其的模仿方面。“埃姆斯是上流阶级,或是中产阶级上层的代表,与嘉莉社会底层或工人阶级庸俗的物质主义相矛盾”[3]4。尼娜·马尔科夫认为,埃姆斯是小说中的文化载体,通过表现自己独具一格的文学审美,如对欧洲文学的偏爱,他恰到好处的表现了自己在品味上的优越性。他不仅批评嘉莉的“低级”文学审美,还将自己定位为如巴尔扎克或哈代般的“高级”文学现实主义者[3]49。
相比之下,杜洛埃则是一个模仿者。他经常流连于豪华气派、名人们喜欢光顾的酒吧,试图模仿上流社会的高雅生活。
他斜靠在豪华的柜台上,喝了一杯威士忌,买了两根雪茄烟,其中的一支他当场点着了。这一些是他心目中的上流社会高雅生活的缩影。所谓管中窥豹,这就算领略了上流社会的生活了[12]60。
同时,杜埃尔还以和名人结识为豪,哪怕仅仅与他们共处一室也能给他带来极大的满足。但当时的上流社会对于杜洛埃来说,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因此,他极力模仿精英阶层的品味举止,希望能与上流社会产生一丝联系。
赫斯伍德虽然整日与上流社会打交道,但他并非其中一员,充其量是个高级打工者。他虽衣食无忧,但妻孩却并不满意她们的生活,而是渴望跻身上流社会。女儿“杰西卡还在上高中,对于人生的见解,完全是贵族那一套”[12]128,和赫斯伍德太太对她的期望一样:嫁给一位上流社会的男性,以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
身处更底层的嘉莉则是个天生的模仿者,尤其善于学习上流社会女性的穿衣打扮,举止神态。时过境迁,嘉莉身上的“那一点儿土气”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大城市时髦女性的风姿绰约。利玛斯特认为,“与其说嘉莉是一个受商品文化蒙骗的被动受害者,倒不如说她是个服装符号学的虚心求学者。当她在杜洛埃的‘指导’下学习鉴赏不同商品及女性魅力时,她不仅逐渐了解怎样才能成为男性眼中的‘万人迷’,并且不断通过实验掌握其中的艺术”[4]47。
通过这些人物,小说间接地展现了精英主义如何依靠其高雅的生活方式、审美情趣主导着社会价值观。中下层人士竞相攀附、模仿精英人群,与他们品味背道而驰的,则被视为另类,遭遇冷落。精英阶层因此获得了优越于其他群体的身份,也令难以攀附、模仿的人群自惭形秽,对其构成话语暴力。
(二)社会达尔文主义、实用主义及其暴力
在某种意义上,这两种话语具有一定的兼容性。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核心就是“物竟天择,适者生存”。这对中产阶级来说是一种励志的价值观。而在物质主义和实用主义盛行的年代,受急功近利心态的影响,主张将道德抛之脑后,用尽各种手段获取成功的实用主义价值观,则受到中下层民众的青睐。两者结合起来,令当时很多美国人相信:善于投机、敢于冒险就能成功,反之就只能失败。
从文中对嘉莉与赫斯伍德人生沉浮的描绘可以看出,德莱塞深受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相信优胜劣汰的丛林法则。小说中对赫斯伍德太太的描写着墨不多,但她无疑是实用主义及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代言人。她冷酷自私,为跻身上流社会不择手段。赫斯伍德与她同床异梦,貌合神离。当她捕捉到丈夫出轨的流言蜚语时,她并未恐慌崩溃,而是冷静地和丈夫的朋友周旋,以便套出更多的真相。同时采用手段将赫斯伍德的财产全部划归自己名下,逼他净身出户。
小说结尾,赫斯伍德在百老汇大街上乞讨时,他风光无限的妻女,连同那个上流社会的女婿正坐在舒适的卧铺客车上,准备去罗马度假。这一对比展现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对所谓“强者”的肯定,以及对“弱者”的话语暴力。冷酷自私如赫斯伍德太太和杰西卡等人,因深谙社会生存之道,不择手段为自己谋利,最终从中产跻身上流社会,成为人生赢家;而赫斯伍德最终自杀,似乎也是缺乏生存能力的弱者的必然归宿。
杜洛埃也是实用主义者的代表。他爱慕虚荣,处事圆滑。作为一名推销员,他同样擅长向漂亮的年轻女性推销自己。他瞅准时机,利用嘉莉初到大城市的天真,在她走投无路之际拿钱引诱她做了自己的情妇。不过,他在感情方面并不专一,只是一个贪图美色的浪荡子。但这样一个缺乏高尚灵魂的投机者,却过着自在逍遥的生活——当他与成名后的嘉莉重逢时,已从一个推销员摇身一变成为一个分公司的负责人了。而反观代表着传统道德观念的汉森一家,却仍然挤在又小又破的房子中,过着与享乐无缘的生活。同样地,像早期嘉莉那样的打工妹、打工仔,辛辛苦苦劳作,也看不到什么出头之日。
三、德莱塞对相关话语暴力的消解
从上文可以看出,小说体现了消费主义、精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实用主义对中下阶层弱势群体的话语暴力。德莱塞作为其中的一员,也深受其害。但他并未一概抗拒,相反,作为社会的一份子,他深受这些价值观的影响,一再在作品中肯定消费主义、实用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价值观。
正如马尔科姆·考利指出的那样,德莱塞“害怕贫穷……热烈地向往着煤气灯与光灿灿的东西(当时的奢侈品);他憎恨世俗的(道德)标准,这些标准使他的许多兄弟姐妹受到审判,被宣告有罪”[14]。德莱塞曾经表示,“我的眼睛总是盯着那些地位远远比我高的人,最使我感兴趣的是银行家、百万富翁、艺术家、总经理,他们是统治这个世界的人”[15]。他从事小说创作,也是希望自己像当时成功的作家霍雷霄·阿尔杰那样,从穷光蛋一下子变成富豪。他强调一个人如果做了什么违反社会规范的事情,也是在欲望驱使下,不得已而为之。嘉莉留地址,跟杜洛埃、赫斯伍德同居都是为了追求更好的物质生活。
但让他困惑的是,为什么少数人过上了逍遥的日子,而许多人,包括自己,虽百般努力却也无法改变境遇。精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对成功途径的阐释,令他的困惑雪上加霜。因此,他对强势话语的消解,更多体现在对这两种话语的重构上面。
上文提到,社会达尔文主义基本内涵是“物竟天择,适者生存”。精英主义认为少数精英天生优越于其他社会群体,因而应当享有更高的权利。在此语境下,对上层人士来说,他们的成功是因为自己天生独具一些高贵品质,因而在竞争中处于优势,以此让自己的价值得到肯定。按照这种逻辑,中下层人士在竞争中处于劣势,皆因能力和道德上低人一等,以此否定了他们的价值。身处社会下层的德莱塞迫切需要消解这些话语的暴力。
有学者注意到,即便对社会达尔文主义德莱塞也未全盘接受。杰克尔认为“尽管他对斯宾塞的理论表示尊敬,但他作为《嘉莉妹妹》一书的作者,他的关键作用是将自己定位为‘知识之父’,而非斯宾塞”[16]。德莱塞消解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主要话语策略是否定“个人意志”的因素,强调“天”的因素,把“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变成“物竞天择,幸运者生存”。他把成功描写成一种由环境中一只看不见的手所决定的纯粹偶然的东西,与个人的道德、能力或者上流社会引以为豪的品味等,全无关联。
在他笔下,嘉莉的成功极具偶然性。她通过杜洛埃偶然得到了一次上台演出的机会,并且大获好评,这为她在纽约走投无路而不得不出门找工作时提供了方向。嘉莉之所以会来到纽约,也完全具有偶然性:赫斯伍德鬼迷心窍的偷走了保险柜中的钱,从而带嘉莉逃到纽约。而嘉莉得到的第一句台词也是出于偶然:“只是碰巧这时是嘉莉在他面前行礼,就他而言,原本随便对谁都是一样的,他并不指望听到回答”[12]342。
从这个偶然事件开始,嘉莉深受命运的青睐,事业顺风顺水,成了百老汇的名角。这一切似乎都出于偶然——嘉莉并未主动争取什么,也未刻意做出任何选择,完全随波逐流,凭着运气和机会获得了成功。而取得成功后的嘉莉似乎也并不幸福,“独自渴望着,坐在你的摇椅里,靠在你的窗户边,梦想着永远不会感受到的幸福”[12]450。对嘉莉成功后心理状态的描写,表达了德莱塞对成功的质疑,进一步消解了来自上层的话语暴力。
反观赫斯伍德,他的失败也充满偶然性。他曾经的成功似乎突然被夺走,最终沦为乞丐,在饥寒交迫中自杀身亡。他的命运在那晚从酒吧保险箱里并不完全有意识地拿了一万美元后开始急转直下,之后任凭他再怎么努力,都难以遏止走下坡路的命运。由此可见,成功与不成功之间并不存在那么深的鸿沟。机会来了,像嘉莉那样,一路扶摇直上。而没有机会或是运气很差,像赫斯伍德这样,即使精明能干,世故圆滑,最终也免不了从高处跌下,凄惨地死去。
文本是话语博弈、角力的场所。在文本内,通过对嘉莉和赫斯伍德不同命运的安排,德莱塞重构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将成功与否归结于环境和运气,拒绝用内在因素解释一个人的成败。如此一来,便削弱了成功和精英阶层自我标榜的“自身优越品质”与“高端道德标准”之间的联系。以此来化解来自上层的话语暴力,维护自身的身份利益。
但是,德莱塞借助《嘉莉妹妹》的话语博弈并未因此结束。正如新历史主义主张的那样,作者建构话语为的是让话语流通以争取更大的话语权。一旦话语进入流通领域,又会发生新的博弈,使得话语博弈的战场从文本内延伸到文本外。《嘉莉妹妹》被禁就是文本外博弈的结果。
四、文本外的话语博弈[注]本文关注的文本仅为《嘉莉妹妹》,从这个意义上而言,《珍妮姑娘》存在于《嘉莉妹妹》文本之外。
(一)精英阶层道德观的话语暴力
在当时的美国,精英主义者强调“高尚”的道德标准,为的是在他们与实用主义者之间划出一条清晰的界线,用以强调自身的优越。
但身处社会底层的德莱塞显然并不为这些道德标准所左右。《嘉莉妹妹》至少在无意识上认同实用精神,将实用效果置于道德考量之上。文中,为了过上有安全感的生活,嘉莉先后与两个男人同居,其中一个还是有妇之夫。在传统的文学作品中,作家通常会对这种作风不良的女性进行批判和谴责,或让其得到应有的惩罚。但在德莱塞的笔下,他不仅没有这么做,反而对其行为进行辩护,认为嘉莉只是为了生存不得已而为之:
倘若城市的工作无利可图而且难以忍受;倘若这是只会使人脚疲心灰,却永远达不到美的漫长路程;倘若追求美的努力使人疲倦得放弃了受人称赞的道路,而采取能够迅速实现梦想的但遭人鄙视的途径时,谁还会责怪她呢?[1]285
正因如此,此书一度变相被禁,面世后也屡遭抨击。例如斯图尔特·舍曼在《西奥多·德莱塞先生的自然主义》一文中,指责德莱塞“没有真实地描写美国社会和人,而是将人视为动物,有意忽略小说家的崇高职责——理解和表现人物的发展”[17]。他认为嘉莉妹妹是个淫荡的女人,作者忘记了自己的崇高责任。由此可见,小说进入话语流通之后,遭到了其他话语集团的强烈打压。
(二)父权主义的话语暴力
事实上,对德莱塞和嘉莉的攻击不仅来自于精英主义者的道德完美主义,同时也来自父权主义。嘉莉的形象颠覆了父权主义对女性的认知,对其构成了极大的挑战。父权主义认为女性就应该是“房子里的天使”,勤俭持家,任劳任怨,体贴温柔,专一不二。而文中的嘉莉先后和两个男人发生非婚同居关系,其目的都是为了过上她向往的安逸生活。后来由于赫斯伍德光景每况愈下,同样出于生活考虑,嘉莉不得已走出家庭,不经意间在百老汇舞台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名利双收。成功后的嘉莉并未像传统道德期待的那样,扮演天使角色,照顾赫斯伍德,而是将其抛之脑后,最终导致他自杀身亡。这样的结局在父权主义者的心里无疑是投下了一颗炸弹。文中赫斯伍德赋闲在家、伸手向嘉莉要钱支付家中日常开支的情节,也狠狠戳痛了父权主义者的自尊。
长久以来,父权主义一直试图将女性他者化,限制她们自我成长和发挥创造力的空间。但是,这种企图在嘉莉身上失败了。从嘉莉身上,读者看到的是传统父权的瓦解。嘉莉依靠自身的美貌和运气,成为成功的职业女性,也并没有像男性期待的那样成为拯救男性的天使。这个结局令父权主义者难以接受,于是引发他们强烈的弹压。
曾任道布尔迪出版社(最初签约出版《嘉莉妹妹》的出版社)律师的麦基在来信中写到:“对于道布尔迪太太这样拥有崇高品质的女性来说,不管(《嘉莉妹妹》)由谁发行,她都会抵制。她抚养着三个孩子,并努力教他们辨别是非。像嘉莉这种丧失道德准则的女性,正是她想让她的孩子们远离的。”[18]
(三) 德莱塞对精英和父权话语暴力的妥协与消解
精英主义和父权主义者的话语暴力让德莱塞始料未及,令其深受打击,并一度因为精神崩溃不得不去疗养。为了抵抗这种话语暴力,他在其第二部小说《珍妮姑娘》中对其进行了消解。
有了前车之鉴,在这部小说中,德莱塞所做的妥协显而易见。初看上去,嘉莉与珍妮如同双胞姐妹——无论出身、经历还是价值观,都如出一辙。但是两者又是不同的,嘉莉生活在没有道德规范的世界,很容易被人理解为一个“贪图享受的堕落女子”。而珍妮的行为决断则处处体现出道德上的考虑。
德莱塞之所以做出妥协,是因为话语博弈必须遵循自身独特的规则。居于主流、上位的话语拥有更多的话语权。边缘化的话语如果不能与上位主流话语达成某种妥协,即便不被禁止发声,也会遭人唾弃。所以德莱塞只能在与主流话语妥协暧昧的前提下,对其进行颠覆。
其颠覆表现在,尽管珍妮尊重道德准则,但她与嘉莉一样还是越过了道德的边界——同样存在两次与人非婚同居的行为,还有一个私生子。但德莱塞给了她的越界,以合乎其他主流话语的理由——为爱情和家人舍己付出。“在德莱塞的精心安排下,珍妮每次越界都是为了他人的利益而‘不得不’舍身付出。这样,她的每一次越界不仅不是迈向堕落,反而向人间圣女又靠近了一步”[19]。
《珍妮姑娘》[20]小说结尾,当莱斯特意识到和珍妮的结合将把自己永远逐出上流社会时,他动摇了;看到杰拉德夫人“身上有一种可以称之为飞黄腾达的大好机会”时,莱斯特心中的天平再一次偏离了珍妮,选择了和杰拉尔德夫人结婚,从而最大程度实现自己的经济利益。不难看出,珍妮之所以无法成为莱斯特的合法妻子,并非因为珍妮缺乏美德,而是因为,在金钱至上、道德伪善的上流社会,道德的作用实在有限。如此一来,就模糊了绝对的道德边界,让实用精神得以合理存在。
不仅如此,德莱塞还借来自上流社会的男主人公之口,暗示世界上没有天经地义的道德准则,因为人类的生活是由难以预测的目的所控制的。通过这些组合拳:越界、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珍妮的形象、道德无用论,德莱塞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来自精英阶层的话语暴力,维护了底层人士的身份利益。
五、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从文本内外两个角度探讨了当时美国话语博弈生态。首先从新历史主义角度提出“文本是话语竞争的场所”这一论点,再借助现有研究成果,引入并介绍了文中涉及的主要话语。接着从文本内部的角度分析了不同话语所代表的不同身份利益及其话语暴力。消费主义作为当时盛行的一种价值观已经深入骨髓,成了一种社会无意识。崇尚炫耀型消费的消费主义对经济实力薄弱的中下层阶级具有话语暴力。精英阶层以高雅的生活方式、审美情趣及“高尚”的道德标准主导着社会价值观,与中下层民众划清界限,以强调自身身份的优越性。本文通过分析文本内赫斯伍德太太和杜洛埃等人“不讲原则,只讲效果”的实用主义精神,反映了实用主义的话语暴力。而嘉莉和赫斯伍德的不同命运揭示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对无法适应环境的“弱者”的话语暴力。德莱塞通过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重构将成功归结于运气而非个人道德、能力等,消解了来自精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话语暴力。文本外,小说进入话语流通之后,因德莱塞将实用效果置于道德考量之上,对嘉莉的行为进行辩护,遭到了其他话语集团的强烈攻击,最终导致此书变相被禁。于是在《珍妮姑娘》中,德莱塞在与主流话语妥协的前提下,对其进行颠覆,维护了底层人士的身份利益。本文通过分析文本内外的话语博弈,借以说明德莱塞所处的话语环境、价值主张,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展现当时美国社会话语博弈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