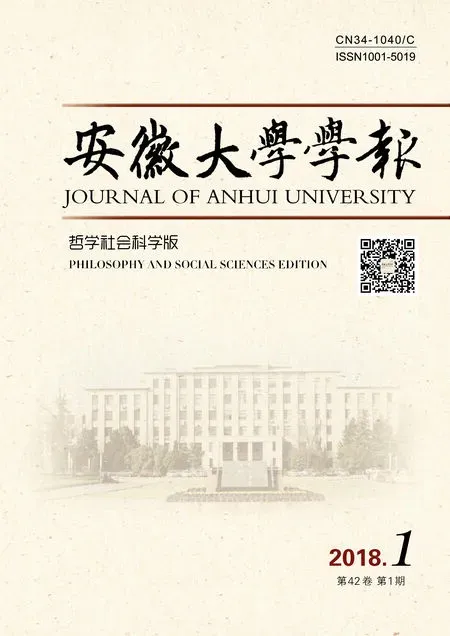侨易美学阐释
——以《射雕英雄传》中的“烟雨江南”为例①
2018-12-31叶隽
叶 隽
一、武侠小说的“生活世界”
按照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可区分两层意义:一是作为经验实在的客观生活世界,一是作为纯粹先验现象的主观生活世界,二者之间的界限则是“先验还原”*朱刚:《胡塞尔生活世界的两种含义——兼谈欧洲科学与人的危机及其克服》,载尹树广、黄惠珍编《生活世界理论:现象学、日常生活批判、实践哲学》,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06页。另参见[德]埃德蒙德·胡塞尔(Husserl, E.Edmund):《生活世界现象学》,倪梁康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这段表述则更中国化:“人们生活在一定的时间、空间和种种人(物)际关系之中,就必然以经验自我为中心形成一个由意识的意向活动范围及其所建构的周围环境。这样一种与人联系在一起的具有意义的‘界域’就是人所经验的生活世界。生活世界也就是人们对现实的直接在场,是人们与其感知到的生活环境之间互动的场所,是实现人的现实意义及价值的最原始和最根本的世界,同时也是日常生活得以正常运转的整体世界。”*伍麟:《“生活世界”的心理学意义》,载《光明日报》2007年3月27日。即便是虚构的文学文本中也存在日常生活的生活世界,即便是相对虚幻的武侠小说,作为一种文学文本的历史镜鉴功能也是强大的,譬如金庸作品就是相当成功的典范。
在金庸作品里,不但有精彩绝伦的故事、奥妙神奇的武功、迂回曲折的情节,也还有平淡无奇的日子、俯拾皆是的景物、水到渠成的爱情,这就接近于我们所谈论的“生活世界”。移易现象在武侠小说里很常见的,譬如郭靖从江南到大漠,再从蒙古返回江南,如果说前一段还是孩子的懵懂无知的话,那么后一段则变化极大。首先是装束、习惯、风物等的变化,但在蒙古大漠培养出来的北人耿直生性,却并没有根本性的变化,这是“常”的一面。移交或许是更值得关注的一个现象,正是由于江南的嘉兴醉仙楼的比武之约,使得郭靖得有可能脱离北方的大漠而进入到江南的灵韵世界,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人物和可能,这其中既有像梁子翁、沙通天、欧阳克等对手,也有王处一、洪七公、周伯通这类他的“福音”。这是一个有点传奇的故事,但正是借助这些奇人的帮助,他实现了一个少年成长为“大侠”的过程。最重要的,当然还是与黄蓉的相遇、相交、相知,最终使得一对江湖侠侣终于“完成塑形”的过程!
按照说书人张十五的说法:“诸君住在江南,当真是在天堂里了,怕只怕金兵何日到来。正是:宁作太平犬,莫为乱世人。”又说:“江南花花世界,遍地皆是金银,放眼但见美女,金兵又有哪一日不想过来?”这里的江南概念显然有一种想象成分在内。其实即便在历史上,江南概念也有一个演变过程,汉代以前多指今湖北省长江以南部分和湖南省、江西省一带,所谓“湛湛江水兮,上有枫。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屈原《楚辞 招魂》);到了南北朝时代则将隔江而望的南朝之治下地区称为江南,所谓“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谢朓《鼓吹曲》)。文学叙述中的江南,则更近乎一种文化符号,譬如庾信《哀江南赋》中说:“日暮途远,人间何世?将军一去,大树飘零;壮士不还,寒风萧瑟。”负面的声音当然不是没有,譬如鲁迅就说: “我不爱江南,秀气是秀气,但小气。”(鲁迅《致萧军》)这姑且可以看作是另类的眼光,对江南有特别的理解。而吴梅村则感慨:“关河萧索暮云酣,流落乡心太不堪。书剑尚堪驱使在,世间何物是江南?”(《遣怀》),这自然是对江南的一种怀之系之恋之的深情流露。
这其中特别值得开掘的,则是诗文语句之外的美学感觉,这其中不仅有情感的蕴藏,也有意境的拓展,甚至是地理的跃动,譬如简单的一句“江南可采莲”(汉代《江南》),就被认为“既是一种地理知觉,也是一种审美发现”*周晓琳、刘玉平:《空间与审美——文化地理视域中的中国古代文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17页。,寥寥数字,仿佛尽得风流,既有地理概念的呈现,也有植物的具感,人物的动作和意境,勾勒出很是灵动跃如的画面来。所以,侨易美学的展现,乃是一个流动之美视角的获得过程,为什么这么说呢?叶廷芳先生曾有书题名为“美的流动”,他之遍寻缪斯,追寻的正是流动之美的踪迹,静态的美固然赏心悦目,动态的美则更添加了丰富多彩的交感的可能,因为在不断侨动之中,所以有移交之生发,乃“生生不息”。或者,美的侨易正是一种可以进行另类把握的角度,所谓“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辛弃疾《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表现的也正是那种异地他乡的江南人物的思乡之情。而在武侠小说里,“江南”几乎就是个“常项”,在金庸作品里固然不用说了,梁羽生《云海玉弓缘》的开局就是由西藏回江南的“江南”引发,而古龙干脆将书名定为《剑花·烟雨·江南》,明显的也是有江南情结的。但江南又未必是简单的江南而已,因为“江南的流人,是北方的骨血与后代,江南认同的骨子里,其实深深包含着北方中原意识的底色。”*胡晓明:《“江南”再发现——略论中国历史与文学中的“江南认同”》,《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11 年第 2 期。这又呈现出二元相交的“南北遇合”的因素来,在审美之外,则种族、文化的重要性也都不能忽略。
二、烟雨江南的侨易之美
所谓“行走,是人类一项经常性的户外活动,以不断移动空间位置(即‘游’)为本质特征,人类通过这种活动以求达到某一预定之位置,从而实现自身的预定目的。从古至今,人类的行走历史经历了一个范围由小到大、时间由短到长、态度由被动到主动、目的由功利到审美的发展演变过程,当人们排除了直接的、现实的功利面对,将其升华为一种审美实践活动时,行走便被称为旅游。”*周晓琳、刘玉平:《空间与审美——文化地理视域中的中国古代文学》,第145页。这和侨易学的基本思路颇为接近,即可将“行”(或“游”)理解为“侨”的过程,而不断推演的审美目标的设置,则使得侨易空间的立体呈现成为可能。行也好,游也罢,其实都是一种侨动的过程,是展现物质位移和精神质变关系的一种纽带关系。旅游的方式有多种,乘坐交通工具是一种,自助游也是一种,而跟着武侠世界里的人物去行走江湖,也是一种有趣的方式,如谓不然,则不妨来看看其行迹如何,有论者如此说道:
在《射雕英雄传》的第一回,地点也是江南,临安(杭州)附近的牛家村。从自北方金国来的、爱慕江南风土人情的赵王完颜洪烈眼中看去,即使江南普通春日也心醉不已,秀美温雅的江南少妇包惜弱更令他一见钟情,生出一段巷缘,以至种下以后的无尽情节故事。此后故事转到嘉兴,这是江南文化悠久鼎盛之地。而南湖之旁的醉仙楼上,江南风光如画、江南人物云集,《射雕英雄传》正式篇章从这里揭开。正文开始在北方草原大漠长大的郭靖和从江南桃花岛来的黄蓉在张家口相遇后,结伴南下,开始他们的少年漫游。这是《射雕英雄传》最吸引人的篇章。这一对少年侠侣过了长江,到了江南的太湖、苏州、临安,江南风华物胜之地,令他们生出许多奇遇。《神雕侠侣》故事开始发生的地方也在嘉兴,“江南多水,小船在碧琉璃般的湖面上滑过”,湖边还有垂柳,典型的江南风情。《倚天屠龙记》正文一开始也“正是暮春三月,江南海隅。一路上桃红柳绿,春色正浓”。之后写到武当的俞岱岩乘船时,又写到钱塘江夜潮。*吴晶:《金庸小说的江南情韵》,《浙江学刊》2000年第1期。
这段描述很能见出作者观察视角的独特,郭靖、黄蓉的恋情固然是金庸武侠史上相当典范的一种类型,但一幅桃花江南图,所叙述的情事又岂仅是比翼双飞的理想爱情,像杨铁心和包惜弱的悲欢离合就同样是值得同情的,而杨康与穆念慈“始恋终散”悲剧更是让人扼腕不已。还有种种插曲,譬如这段描述江南景观以衬托完颜洪烈与包惜弱的感情萌生就相当精彩:“这时正是江南春意浓极的时光,道旁垂柳拂肩,花气醉人,田中禾苗一片新绿。颜烈为了要她宽怀减愁,不时跟她东谈西扯。包惜弱的父亲是个小镇上的不第学究,丈夫和义兄郭啸天都是粗豪汉子,她一生之中,实是从未遇到过如此吐属俊雅、才识博洽的男子,但觉他一言一语无不含意隽妙,心中暗暗称奇。”金庸写情是圣手,状景摹物也是高人,他笔下的风景胜地,不仅起到简单的语境衬托作用,而且能够赋予更多的文化意涵和神韵。对于江南男子和女子,各有各的风流倜傥与美丽可爱:“江南的男子即使是侠客,也多是书生打扮,轻袍缓带,折扇方巾,名士风度,风流儒雅,一样善解音律,惯吹笛笙,就像诗词里常常写到的‘金鞍白马,雕裘宝剑’的‘春衫薄’的‘太狂生’‘陌上少年郎’一样。这是南朝谢家子弟裙履风流的遗风。有的人物干脆就不是纯粹的江湖豪士侠客,骨子里更是书生。如陈家洛、袁承志、张翠山、段誉。黄蓉、温青青、殷素素、程灵素等女主角,也是才女气质多过江湖侠女。”诚然如此,这幅名流画卷确实让人联想翩翩,但此处我们抛却诸多的英俊潇洒的侠客不谈,且聚焦这个傻小子郭靖,这个差点成为黑风双煞手下小鬼的昔日幼童,初出茅庐却能机缘巧合,不断获得武功的提升机会,并且最终成为为江湖传颂不已的武林领袖和侠之大者。
或许这里我们可以借助侨易学的若干概念来略作分析。移易这组概念由移变、移常、移简、移交组成。郭靖从漠北到江南的过程,正可为此概念做很好的注脚,移变自然是第一个层次的,正是因为从大漠到江南,所以由“万里黄沙尘满天”到“小桥流水夕阳斜”,郭靖的变化也是很明显的,一方面是“初履中土,所有景物均是生平从所未见”,另一方面则是所遇到的各种江湖风险和人与人之间的互不信任、相互为敌、尔虞我诈,都让他不再那样的天真烂漫,而是开始真正地“行走江湖”。无论是与钱青健、侯通海、沙通天等的较量,还是后来碰到梁子翁、完颜康、欧阳克等人,都是让他不断成长、不断成熟的“加热剂”,他开始逐渐成长为一个开始能够独立行侠之人。移常则是另一个很重要的面相,我总以为郭靖虽是南人,但却更契合蒙古文化的精神脊髓,他的性格更是一种内在耿直、正直侠义的类型,或许也可解释为郭家后裔(其祖先为梁山好汉赛仁贵郭盛,其父郭啸天本就有着一般江湖英雄的粗犷与豪情)所独有的血脉系统,再经成吉思汗的金刀长弓所熏陶,更长出一份豪侠的气质,但正是这种基本的侠义精神和正道本色,是无论如何颠沛流离、南奔北走都不会改变的,这点在他最后的近乎疯狂地想“自绝武功”的表现中似可视为一种征象。移交更是明显,他与全真七子之一王处一的交往,是他到江南后收获的“第一桶金”,再次则是碰到了洪七公,与当时武侠大师级人物的偶逢,使得他能够迅速转换门廷,成为一流帮派甚至武林领袖级人物的入室弟子,“降龙十八掌”的学习,成为其扬名武林的标志性符号,使他能够迈入大侠行列。最典型的则是与黄蓉的爱情的收获,这不仅是一份两情相悦的青春期恋情,而且也是一份志业相知的天长地久的爱情,相比较少年时代与华筝公主的青梅竹马,这份爱情饱经考验、终究圆满,但却不是没有遗憾,譬如这段写郭靖在与黄蓉重逢后回想少年往事的笔墨:“郭靖怀里藏着华筝刻着字的那块皮革,想到儿时与华筝、拖雷同在大漠游戏,种种情状宛在目前,心头甚有黯然之意。黄蓉任他呆呆出神,自行在灯下缝补衣衫。”虽然文字很简练,但却非常传神和多义,不尽的风义情谊都在其中了。移简则为简洁的原则性规律的产生,正是在不断逡巡迁变、江湖和历史交织纠葛的过程中,郭靖学会了快刀斩乱麻地处理问题,他和华筝的关系一直是“剪不断理还乱”,那种兄妹间的亲情和情人间的恋情其实很难分得那么清楚,如果一直待在大漠,他可能早就顺理成章、顺水推舟地做了实质上的金刀驸马,但江南行旅使得他终于重新认知了自己(当然反反复复,在然诺和爱情之间徘徊),对问题有了本质性的认识,所以终究能狠下心肠,排除困难,最终以对黄蓉的爱情为最终选择。
郭靖确实是一个拙朴却不平凡的人,他不但能够展现移易的多层次含义,而且他能够高交,在侨易十六义中,高交是一个非常关键性的概念,因为到了一定程度,就必须通过自己境界的提升来实现更高层次境界的获得甚至创生,那么郭靖与周伯通的交往则可以做此看。最典型的就是七十二路空明拳和左右互搏,以黄蓉这样聪明的人物,居然也不能掌握,而且第一步“左手画方,右手画圆”就学不会;但“郭靖初练时双手画出来的不是同方,就是同圆,又或是方不成方、圆不成圆。苦学良久,不知如何,竟然终于领会了诀窍,双手能任意各成方圆。”恰恰是笨人能一心二用,没有想着克敌制胜的周伯通练就了最高武功,天下第一就是这样自然而成的,可他却偏又不居之。按照黄药师的说法:“老顽童啊老顽童,你当真了不起,我黄老邪对‘名’淡泊,一灯大师视‘名’为虚幻,只有你,却心中空空荡荡,本来便不存‘名’之一念,可又比我们高出一筹了。东邪,西狂,南僧,北侠,中顽童,以你居首!”(《神雕侠侣》)虽然是小说家言,但却也能反映出某种高简之理,就是无为而有为,游戏而至高。将这思路用在那些纯粹的艺术家、科学家身上也是完全有效的。
我们借助侨易之眼看江南,看郭靖游历行走其间的江南,其实正如卞之琳那首著名的《断桥》:“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江南的景象多姿多彩,来看景者也是多元丰富,但却是一个相互叠加和彼此交错的过程,郭靖增加了江南烟雨的风采,也属于江南风景的部分。但如果认为侨易经验对郭靖仅是武艺的增强功用就显然错了,他的思想也在随着这个过程而不断变化,譬如他的追问:“我一生苦练武艺,练到现在,又怎样呢?连母亲和蓉儿都不能保,练了武艺又有何用?我一心要做好人,但到底能让谁快乐了?母亲、蓉儿因我而死,华筝妹子因我而终生苦恼,给我害苦了的人可着实不少。完颜洪烈、魔诃末他们自然是坏人。但成吉思汗呢?他杀了完颜洪烈,该说是好人了,却又命令我去攻打大宋;他养我母子二十年,到头来却又逼死我的母亲。我和杨康义结兄弟,然而两人始终怀有异心。穆念慈姊姊是好人,为甚么对杨康却又死心塌地的相爱?拖雷安答和我情投意合,但若他领军南攻,我是否要在战场上与他兵戎相见,杀个你死我活?不,不,每个人都有母亲,都是母亲十月怀胎、辛辛苦苦的抚育长大,我怎能杀了别人的儿子,叫他母亲伤心痛哭?他不忍心杀我,我也不忍心杀他。然而,难道就任由他来杀我大宋百姓?”在这里,作者将非常沉痛的家仇国恨毫不留情地摆在这个青年人的心灵地图上,因为“心灵地图是每一个个体基本认知的一部分。个体与集体对世界的空间认知之间,是一种交互影响的复杂关系。我们绝不能将人类的空间观念,单纯地理解为静止的图像和固定的符号。所谓中国式空间观或伊斯兰式空间观,是不存在的。人类的空间观念是开放的,它必须不断接受新事物,并将各种‘前所未闻’之事变成自我认知的一部分。”*[德]于尔根·奥斯特哈默(Osterhammel, Juergen):《世界的演变——19世纪史》第I册,强朝晖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185页。显然,这段论述是相当深刻的,且所涉及的根本性概念很重要,因为“时间和空间的关系问题,是一个重大的哲学问题”*[德]于尔根·奥斯特哈默(Osterhammel, Juergen):《世界的演变——19世纪史》第I册,第160页。,这当然不仅是表现在抽象的哲学讨论过程中,也是在具体的生活世界和历史世界中的,虽然作者背后的思路在于,“在19世纪,没有任何一种非欧洲空间观能够与欧洲人的全球宇宙观相匹敌。除了欧洲之外,没有哪个地方曾经出现过一种能够对世界各大洲和各大区域做出系统化划分的元地理学理论”*[德]于尔根奥斯特哈默(Osterhammel, Juergen):《世界的演变——19世纪史》第I册,第186页。,但我们更宜理解其作为普遍性思维的价值。这其中也有一个侨易时间问题,即在我们能明显看到的侨易空间之外,还有一个时间性的纵轴关系。要知道,“一个历史时期从本质上讲是以时间来定义的,但与此同时,它的空间形态也是可以被描述的。这些形态的重要基本模式是中心与边缘之间的关系。所谓中心,是人与权力、创造力与象征性资本在一个较大的关联体之中彼此汇聚的地方。这些中心既向外辐射,也向内吸引。而边缘则与之相反,它是与中心处于非对称关系的力量较弱的各极。它们更多是脉冲信号的接收者,而非发送者。另外,在不同的边缘位置,总是有新的事物不断涌现。庞大帝国的兴起,总是从边缘地带开始的。宗教在这里得到资助,重大的历史在这里书写。在天时地利的条件下,这些活力充沛的边缘地带也有可能转化为中心。中心与边缘之间的力量重心总是在一寸寸地发生转移,在某些时候,这种变化也有可能是翻天覆地的。人们往往必须同时与几个中心打交道,这些中心之间有可能是合作关系,也有可能是竞争关系。因此,世界地图总是呈现不同的面貌,一切取决于人们从哪一个系统化角度去观察它。政治地理与经济地理是难以协调的,全球文化中心的分布与军事力量中心的分布也往往截然不同。”*[德]于尔根·奥斯特哈默(Osterhammel, Juergen):《世界的演变——19世纪史》第I册,第161~162页。不仅对集体来说如此,对个体来说亦然。像郭靖这样的人物,如果没有其成长过程的“四面八方”和“大开大合”,如果没有其生命经验的“博大丰富”和“多重训练”,如果没有类似西方“教养小说”的艰难成长,他是很难成长为近乎“大侠符号”的形象的。他始终是在两个层面上不断拓展自己的,一方面当然是武功,这是侠客立足江湖之本,但达到高端武功层次的不止一人或数人而已,像欧阳锋、裘千仞等都是,对于郭靖来说,虽然说“笨鸟先飞”,但显然不是这点能概括的。他以一个凡人的朴拙之资质而终成大器,甚至作者赋予其黄药师、周伯通等人都难有的武林领袖的江湖地位,显然有着他特殊的气质。在我看来,这就是他精神世界的追求,是从一个普通少年成长为江湖英雄的质变过程,这些仿佛絮叨但却精辟的自语值得品味:
学武是为了打人杀人,看来我过去二十年全都错了,我勤勤恳恳的苦学苦练,到头来只有害人。早知如此,我一点武艺不会反而更好。如不学武,那么做甚么呢?我这个人活在世上,到底是为甚么?以后数十年中,该当怎样?活着好呢,还是早些死了?若是活着,此刻已是烦恼不尽,此后自必烦恼更多。要是早早死了,当初妈妈又何必生我?又何必这么费心尽力的把我养大?”翻来覆去地想着,越想越是糊涂。接连数日,他白天吃不下饭,晚上睡不着觉,在旷野中踯躅来去,尽是思索这些事情。又想:“母亲与众位恩师一向教我为人该当重义守信,因此我虽爱极蓉儿,但始终不背大汗婚约,结果不但连累母亲与蓉儿枉死,大汗、拖雷、华筝他们,心中又哪里快乐了?江南七侠七位恩师与洪恩师都是侠义之士,竟没一人能获善果。欧阳锋与裘千仞多行不义,却又逍遥自在。世间到底有没有天道天理?老天爷到底生不生眼睛?
郭靖的反思不但彻底,而且更立即用于实践。所以他干脆放弃使用武功,于是一代大侠竟然因为穿了蒙古服装而被南人殴打,“郭靖这几日来常觉武功祸人,打定主意不再跟人动手,兼之这些人既非相识,又不会武,只是一味蛮打,当下东闪西避,全不还招。但外面人众越来越多,挤在小酒店里,他身上终于还是吃了不少拳脚”,幸得丘处机出手,才免去被重伤的危险。这类深层的思想问题在书中其实虽未太多展开,但却如思想光芒,稍纵即逝,值得深入开掘,譬如最后这段华山论剑上的哲学思考:
欧阳锋心中愈是糊涂,只觉“欧阳锋”这名字好熟,定是自己最亲近之人,可是自己是谁呢?脱口问道:“我是谁?”黄蓉冷笑道:“你就是你。你自己都不知道,怎来问我?”欧阳锋心中一寒,侧头苦苦思索,但脑中混乱一团,愈要追寻自己是谁,愈是想不明白。须知智力超异之人,有时独自冥思,常会想到:“我是谁?我在生前是甚么?死后又是甚么?”等等疑问。古来哲人,常致以此自苦。欧阳锋才智卓绝,这些疑问有时亦曾在脑海之中一闪而过,此时连斗三大高手而获胜,而全身经脉忽顺忽逆,心中忽喜忽怒,蓦地里听黄蓉这般说,不禁四顾茫然,喃喃道:“我,我是谁?我在哪里?我怎么了?”
若非黄蓉及时转圜,郭靖几乎也为同样一个“我是谁?”的问题而走火入魔,但恰恰是这种不经意间,让我们打开了郭靖思想世界的钥匙,这个行走江南而成长起来的郭大侠究竟是谁?他真的就是那个在《神雕侠侣》中扬名立万、正统一面的郭大侠吗?这显然是一个过于深刻的问题,值得深入探究,此处不赘。
三、侨易美学的深层阐释
流动不居的世界和滚滚轮动的红尘,借助各种可能的媒介,会以多姿多彩的方式呈现在我们的面前。譬如小说,当然也是一种媒介方式,因为没有这种文字书写就不可能实现人们的一般接受过程(像口头史诗或民间故事那样毕竟是困难的),当然对它的阅读也是通过介质而实现的,无论是早起的印刷品,还是日后的电子版(计算机、电子书、手机等都可作为载体),都是属于人的感知的延伸。当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引入电子媒介的功用无疑是非常重要的,譬如影视作品的出现就可以进一步将本来停留在文学空间的意象具体化了,我们可以看到音像图景中的郭靖、黄蓉,乃至江南烟雨、亭台楼阁、园林风景等等。
就《射雕英雄传》而言,我们熟悉的就是三个版本:黄日华翁美玲版、李亚鹏周迅版、胡歌林依晨版等。这些电视连续剧各有特色,各有演绎,相对已成经典的83版射雕,我还是觉得张纪中导演的李亚鹏与周迅版更能契合侨易美学的理念,或许是因为格局和境界的不同,譬如镜头的调用、演绎的生动、大气的画面,那种气势确实是很难比拟的。当然作品本身的媒介侨易过程也是值得考察的一个角度,从影音共鸣,再到借助插图、连环画等形式,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立体艺术的“射雕世界”,其美学意义值得大加发覆。
这里,仅就侨易美学的核心理念略做阐释,至少包括以下三层:其一,以一种流动的眼光和变化的思维去审美,去审视我们周遭大千世界的诸种风景,横看成岭侧成峰,将“静”与“动”形成一种整体性的有效互补维度。譬如我们可以看到的《射雕英雄传》呈现的江南风光,小说描写固然如此,在张纪中版的电视连续剧中或许可以呈现得更为清晰与直观,这是现代科技的好处。
其二,侨易还是一种系统思维,是有一种整体性观照的大框架在的。所以它既能让我们注意到始终存在的二元三维的基本结构,而且也还可以展现出追索寻道的自觉意识。观侨取象更进一步,不仅有求真层面的察变寻异,或者更有价值层面的向善审美。将美学意趣补充进来,有利于我们构建一个另类第三维,即在“学”之外的“美”的侧翼。所以我们不仅看到郭靖的江南之行的武功长进,还看到他对于美的体验和收获,譬如和黄蓉的结识和恋爱过程;譬如他侠义精神的逐渐形成,侠之大者人格的塑形等。
其三,美学当然不仅仅意味着“审美”而已,它还可以有更高的境界和更深的追求,席勒(Schiller, Friedrich, 1759-1805)将古代希腊人作为典范,认为他们具有性格的完整性,而近代人则不是:“给近代人造成这种创伤的正是文明本身。只要一方面由于经验的扩大和思维更确定因而必须更加精确地区分各种科学,另一方面由于国家这架钟表更为错综复杂因而必须更加严格地划分各种等级和职业,人的天性的内在联系就要被撕裂开来,一种破坏性的纷争就要分裂本来处于和谐状态的人的各种力量。”*[德]席勒:《审美教育书简》,载冯至:《冯至全集》第11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36~37页。这里的近代,亦可理解为现代。在与希腊国家进行比较之后,席勒对近代社会做了如下的描述:“……如今已被一架精巧的钟表所代替,在那里无限众多但都没有生命的部分拼凑在一起从而构成了一个机械生活的整体。现在,国家与教会,法律与道德习俗都分裂开来了;享受与劳动,手段与目的,努力与报酬都彼此脱节。人永远被束缚在整体的一个孤零零的小碎片上,人自己也只好把自己造就成一个碎片。他耳朵里听到的永远只是他推动的那个齿轮发出的单调乏味的嘈杂声,他永远不能发展他本质的和谐。他不是把人性印在他的天性上,而是仅仅变成他的职业和他的专门知识的标志。……死的字母代替了活的知解力,训练有素的记忆力所起的指导作用比天才和感受所起的作用更为可靠。”*[德]席勒:《审美教育书简》,载冯至:《冯至全集》第11卷第,37-38页。这种美学思考显然超越了简单的审美范畴,而更深刻、更犀利地融入到时代大语境中去,这种所谓“精巧钟表的时代”,正是资本时代的代名词,席勒以他作为诗人和史家的敏锐洞察力,非常准确地捕捉到了大时代变化的症候,可谓是“一叶落而知天下秋”。按照李泽厚的说法:“哲学美学感兴趣的仍在于:由个体身心直接参与,具有生物学基础的动物游戏本能,如何能与上述这种社会性文化意识、观念相交融渗透,亦即是个人身心的感性形式与社会文化的理性内容,亦即‘自然性’与‘社会性’如何相交融渗透。”*李泽厚:《华夏美学插图珍藏本》第9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也就是有着游戏的内涵在的,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郭靖的江南行旅或经验,就给我们理解了那个大时代提供了一个入手的枢纽。侨易美学是否可以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一般的流动性视域与系统性视域之外,继续拓展批判性视域,但又不是简单的评人说事而已,而是应更接近于德国人所谓的“文化批判”(Kulturkritik)传统,深入底里地进入到文化与文明的深处,以批判性的思维来反省人类文明的进程,或可别出手眼。譬如《射雕英雄传》的世界就不妨视作一个多媒体交融构成的立体世界,在张纪中所导演的电视剧版(李亚鹏饰演郭靖)里,主题曲唱着:“千秋霸业,百战成功,边声四起唱大风。一马奔腾,射雕引弓,天地都在我心中”,其画面则千军万马、滚滚黄沙,奔马长啸,英雄弯弓,大雕盘旋、激荡长空,不但很好地体现出历史侨易的沧桑感,而且也展示出一种壮阔的审美精神,让人体会到历史之重、历史之变、历史之美!真是要情不自禁地去追问:“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在何方?”而郭靖与成吉思汗的那段对话则更能见出这种悖论,按照郭靖的看法:“自来英雄而为当世钦仰、后人追慕,必是为民造福、爱护百姓之人。以我之见,杀的人多却未必算是英雄。”成吉思汗的反馈是:“我一生纵横天下,灭国无数,依你说竟算不得英雄?嘿,真是孩子话!”但当郭靖向他揭明了人死后不过黄土一抔的悲哀事实之后,成吉思汗确实不得不反复回味“英雄”的概念究竟是什么。如果借用侨易美学的概念,我们可以欣赏到此处的一种凄凉之美或悲凉之美,成吉思汗纵横疆场,一生英雄,但到临终之际,却不得不面对良知拷问和另类标准的“质疑”,虽然可以自我安慰,但恐怕多少也意识到历史本身的吊诡之处,正如毛泽东晚年所言,他一生努力是否能真正影响到北京周边的地方都还是个问题。不是别人,而正是江南归来的郭靖提出了如此尖锐深刻的问题,或许也正可见出侨易美学的价值,因为正是郭靖,经历了种种变化而耿直不变有常;其他的人物也不是完全没有这种侨易经验,譬如拖雷、哲别也曾去过江南,丘处机也曾为万民请命,因其“一路西行,见到战祸之烈,心中恻然有感,乘着成吉思汗向他求教长生延年之术,当下反复开导,为民请命。成吉思汗以年事日高,精力渐衰,所关怀的只是长生不老之术,眼见丘处机到来,心下大喜,只道纵不能修成不死之身,亦必可获知增寿延年之道,岂知他翻来覆去总是劝告自己少用兵、少杀人,言谈极不投机”。但前者或许是更多了利害关系而不愿去“逆龙鳞”,后者则最多不过借《道德经》提出“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等劝言,与郭靖的直言无忌还是不同。
侨易美学这个概念的提出,当然是应对了日益迁变和变动不居的时代,尤其是全球化的整体趋势,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的则是,这其中更有侨易学发展的内在逻辑存焉。在强调了作为方法论的侨易学之后,我总是觉得似乎远不能穷尽侨易思维的内在奥义,但却又困然不知其路将安出,因为从本质上来说我还是更在意作为本体论的侨易学,设如是则“侨易美学”概念的提出,似乎使我能够在另外一条蹊径上行走,虽未免潇洒倜傥,但却动感盎然,展现出一种别样的致思景观。所以,侨易学不仅应该是一种问道之学,这当然是根本性的精神骨架所在,但它同时也应该是寻美之学,在万千景象的混沌风采中去追寻至美大美,哪怕是艰难荆棘,哪怕是风雨如霜,哪怕是晦暗幽明,我们总可以执着地坚持,去寻找那可以更好地安顿我们诗意的生命和精神的方向,正如同“诗与远方”,都应该是我们生命中时时逡巡的灵性的魂魄,是不可缺少的!或许《射雕英雄传》的尾声正给我们展现了这样一幅侨易美学的复杂系统的画卷:
当晚成吉思汗崩于金帐之中,临死之际,口里喃喃念着:“英雄,英雄……”想是心中一直琢磨着郭靖的那番言语。郭靖与黄蓉向大汗遗体行过礼后,辞别拖雷,即日南归。两人一路上但见骷髅白骨散处长草之间,不禁感慨不已,心想两人鸳盟虽谐,可称无憾,但世人苦难方深,不知何日方得太平。正是:
兵火有余烬,贫村才数家。无人争晓渡,残月下寒沙!
这里至少有几重维度值得揭示:其一则就个体而言,郭、黄鸳梦得温、佳侣终成,南归宋土,再度侨易,将演示怎样的侠义图谱?其二则兵火方起,万民艰辛,贫村数家,残月无言,真是难免不让人想起杜甫那首著名的《兵车行》:“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道傍过者问行人,行人但云点行频。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作者所谓“世人苦难方深,不知何日方得太平”,正是一极为简约的注脚而已,历史苍凉之美,凄婉哀歌之意,由此一语而尽见之焉;其三则对于大历史而言,一代天骄成吉思汗驾崩金帐,意味着历史的中场转换,宏大历史叙述中体现出的浩瀚和悲壮,无以言表,英雄概念的追问则似乎能够穿透历史的帷幕,一层层逼近当代。烟雨江南的扑朔迷离或许终将淡去,人性光辉的侨易之美才是让我们能够流连忘返的精神之光!陈寅恪先生说:“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在那些远逝侠客的背影身上,我们仿佛能看到这个民族最光辉的那些东西。想起金庸引用的那首李白的《侠客行》:
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
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
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
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
闲过信陵饮,脱剑膝前横。
将炙啖朱亥,持觞劝侯嬴。
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
眼花耳热后,意气素霓生。
救赵挥金槌,邯郸先震惊。
千秋二壮士,烜赫大梁城。
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
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
这不是最美的一幅侨易美学之画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