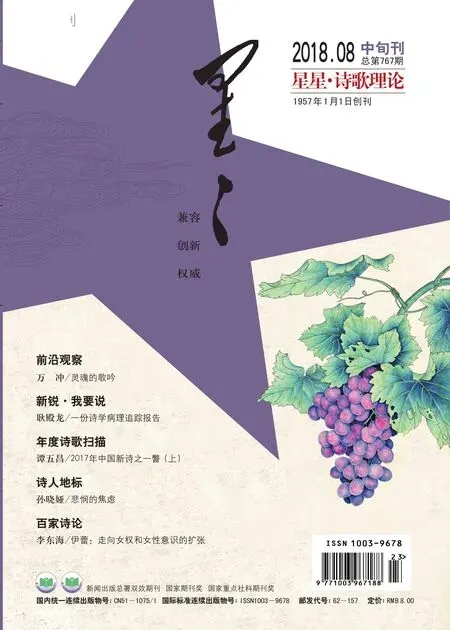诗化空间的出色叙事及创作技巧
——张二棍诗歌赏析
2018-12-30
张二棍是勤奋的诗人。他的诗表现手法多样化,挖掘的诗歌素材丰富,善于深挖蕴藏在底层生活中的习俗、现象及事件。也许他朴实且耐读的诗唤醒了人们尘封的点滴回忆,因而受到读者的好评。他曾于2015年参加《诗刊》社第31届“青春诗会”,获得“《诗刊》2015年度陈子昂诗歌奖”,并被评选为《诗歌周刊》2013年“年度诗人”,还被遴选为2017—2018年度首都师范大学驻校诗人。他1982年生于山西代县,常年跋山涉水,游走在荒凉与清贫的社会底层,目前是山西某地质队职工。
在社会经济发展,人们生活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当今,他经由对底层人群生活的怜悯而抒发生活体验及体会的篇章,蕴含着人文情怀和社会良知。他通过驾驭文字,以出色的叙事及白描抒写、现场再造等,在诗化空间里遨游。应该说,由于文学观念与时代语境的互渗影响,他不仅写出许多备受称颂的诗篇,而且还对底层图景进行记录和追述。这个过程,他练就集观察、审美、创作于一身的诗歌创作技能,时刻分享他对社会底层的观察与思考的诗行。
张二棍的诗与地质队队员身份咬合在一起,便有了亲切、朴实的元素。他的诗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地质勘探队员之歌”一类的“山野诗”,也迥异于文人骚客以亲近自然之名、行亵渎自然之实的“山水诗”[1]。从人文情怀角度看,他的诗细腻地洞察生活,令人能够在匆匆前行的岁月中驻足思考,修正人生观念;从阅读感受去看,他的诗基于底层生活,有一种跳跃灵魂的、穿越于朴素的生活场景;而从创作态度去看,他以诗为媒,在字里行间吟唱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和愿景。他是一名歌者,一名充满警醒及充满诗歌灵性的诗人。
一、出色的叙事和发现能力
本文谈论的“叙事”和小说、散文、剧本等文学作品的“叙事”性质不完全相同,这里指语言风格基于日常语言表述,诗意诉求传达极具个性化的生命经历及体验,诗歌文本呈现“事态”或“情境”的诗歌作品。
先谈张二棍出色的诗歌叙事能力。“我无数次地看见过麻雀/有时在枝丫间/跳跃。有时掠过我的眼睛”。(张二棍《雀》)自古麻雀是生命气象的典型反映,古代的诗人也喜欢诗颂麻雀。譬如,清代著名文学家、诗人家李调元《麻雀诗》“一窝两窝三四窝,五窝六窝七八窝。食尽皇王千盅粟,凤凰何少尔何多!”诸如此类朗朗上口的诗句,有很大部分是描写麻雀的。可以说,历代诗人乐此不疲地追逐描摹麻雀生命的轻灵。张二棍的《雀》一诗,明显以诗歌叙事的方式,像“慢火熬好汤”般讲述他看到的事件。那种叙述,慢悠悠的,似乎怕语速过快而吓跑了诗中“麻雀”似的。诗中继续写道:“它躺在我的手心里/不挣扎,甚至不颤抖/小小的翅膀,淌着/血。它不懂/架网捕鸟的人/多喜欢它们/它怎么会懂/人间的杀戮,占有/和出卖,是喜欢的/另一种表现方式”。读后,顿感诗中讲到麻雀这些可爱的生灵的生命受到猎人的侵害。诗人以反讽的语调,叙述“它不懂/架网捕鸟的人/多喜欢它们”,一针见血地影射人的冷漠和贪婪。将人类阴暗的一面批判得体无完肤。
他在《黑夜了,我们还坐在铁路桥下》一诗中也出色地“叙事”。诗作这样描述:“幸好桥上的那些星星/我真的摘不下来/幸好你也不舍得,我爬那么高/去冒险。我们坐在地上/你一边抛着小石头/一边抛着奇怪的问题”。诗人以叙事的姿态,延伸了心灵无限的想象。诗人以“桥上的那些星星”作为自己人生的奋斗目标或生活愿景。而“我真的摘不下来”才最终导致“幸好你也不舍得,我爬那么高/去冒险……”这是诗人写给自己六岁孩子的诗,最后说:“我已为你,铺好铁轨/我将用一生,等你通过”。这才是诗人叙事的核心,可以说,诗歌核心内容已经通过最后两句表达出来,以此来增强诗歌的张力。可以这么说,这首诗在叙事过程中,虚与实完美地结合,以小见大,以一个父亲和孩子的故事来映射更多类似的家庭境遇。于是时代的印记,便通过诗句得以保留,令更多人引起对留守儿童、留守老人及外来劳务工生活境况的关注。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诗人是“发现者”,在出色的诗歌叙事语境下,同时也具备诗境中的发现能力。张二棍总能俯下身子将目光集敛于生活的日常,在细碎之生活情景中发现题材。可以说,他致力于对“彼岸世界”的虚构性再造,他善于对生活题材进行深层次解剖、挖掘及展示,让诗人的意志得以呈现。作为发现者,他选取的是日常生活的切面,将自己的触觉碰触到的“点”放在自己诗句中,并在特别设定的语境下扩大,于是那些眼熟的,因熟悉而被人们忽略的事与物得以凸显。例如:《原谅》《有间小屋》《空山不见人》《蚁》《听,羊群咀嚼的声音》《独坐书》等诗作,皆努力从平淡的生活镜头中提取文学的元素,做到贴近,努力保持和事、物之间的原态贴近甚至渗透,在平淡中寻求真味。
张二棍具有那种让“司空见惯”的事物重新转换到陌生的叙事能力。他采用熟稔的手法,让读者从日常中熟视无睹的部分事物,自然地伸展到现实生活之外,成为一种令人意想不到又似曾眼熟的程度。其实,诗境的布置,是一种难度较大的全新的诗歌创作思维。如此,再来回味他的诗句:
“他蜷在广场的长椅上,缓缓地伸了下懒腰/像一张被揉皱的报纸,妄图铺展自己/哈士奇狗一遍遍,耐心地舔着主人的身体/又舔舔旁边的雕塑。像是要确认什么/或许,只有狗才会嗅出/一个被时光咀嚼过的老人/散发着的/——微苦,冷清,恹恹的气息”。(《安享》)
其实,《让我长成一棵草吧》一诗,也体现诗人的发现能力。诗这样写道:“让我长成一棵草吧,随便的/草。南山,北坡都行/哪怕平庸,费再大的力/都挤不出米粒大的花/哪怕单薄,风一吹/就颤抖着,弯下伶仃的腰/哪怕卑怯,蝴蝶只是嗅了一下我的发梢/缄默的根,就握紧了深处的土/哪怕孤独,哦,哪怕孤独/也要保持我的青。”这里的“孤独”是诗人独特视角的发现。诗人发出内心的渴望:“让我长成一棵草吧,随便的/草。南山,北坡都行。”这可作为“托物言志”的一种叙事,即是通对“草”的描写和叙述,从而表达诗人的志向和意愿。事实上,这是诗人在其作品中惯用的写法。诗人常用某一物品来比拟或象征某种精神、品格、思想、感情等。这里无疑是借“草”来表达“物品”与“志向”,“物品”与“感情”的内在联系。诗人将自己比喻成一棵草,尽管“平庸”“单薄”“卑怯”“孤独”,但却始终要保持自己的“青”,从而象征着诗人一种坚强的生活态度。
此外,扎实的诗歌语感也是张二棍的创作能力。一般来说,语感并不止于语感,还直接关系到诗人的创作风格和艺术个性。一位成功的诗人,必须具备特定的创作风格或语言个性。这些风格,能让诗人拥有标签或符号,不论他在诗歌作品中如何“隐姓埋名”,有心的读者总会认出作者来。譬如,诗人李白的奔放飘逸,杜甫的沉郁顿挫,舒婷的细腻和敏感,于坚的冷抒情风格等等,都是诗人独具个性的语感所使然。诗歌创作语感的养成,是诗人从起步到成熟的创作过程中,熟悉地进行语言运用并逐步取得的。对此,郭沫若说:“大凡一个作家或诗人,总要有对于语言的敏感。”叶圣陶说:“文字语言的训练,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训练语感,就是对于语言文字的敏锐感觉。”又说:“多读作品,多训练语感,必将渐能驾驭文字”[2]。这些观点说明语感不仅是写作的必备素质,而且也是写作能力形成和发展的前提条件。
二、对底层现实生活的再造
诗歌是真实与想象的巧妙对接,在写作技术处理与文学艺术的表现手法方面,都非常重要。可以说,诗人是底层生活的见证者,更是参与者。诗歌文本虽然处于静态,但其生命活力无限,它见证社会生活的种种。正如诗评家何光顺所言:“生活被遮蔽,而只有文本与符号出场,诗歌成为语词、概念和符号的衍生物与超链接”[3]。同样,张二棍的诗歌文本深入生活,让生活场景频频出场,从文字里抠出血泪来,真实反映外来工底层生活的真实境遇。对此,魏天无认为,在对张二棍诗歌最初的推荐和褒奖中,“疼痛”与“介入”是两个频繁出现的词。与之相应,他被迅速划归到“底层写作”的行列,与打工诗人或余秀华的诗歌相提并论。[4]
张二棍具有强大的“悲剧”气场。可以这么说,诗人身上具有那种特有的、生鲜的“悲悯”气度,为他再造底层生活现场提供了条件。譬如他的诗《在乡下,神是朴素的》,全诗如下:
“在我的乡下,神仙们坐在穷人的/堂屋里,接受了粗茶淡饭。有年冬天/他们围在清冷的香案上,分食着几瓣烤红薯/而我小脚的祖母,不管他们是否乐意/就端来一盆清水,擦洗每一张瓷质的脸/然后,又为我揩净乌黑的唇角/——呃,他们像是一群比我更小/更木讷的孩子,不懂得喊甜/也不懂喊冷。在乡下/神,如此朴素”。
一首简短的诗,经诗人寥寥几笔,一个全新的生活场景便跃然纸上。这些生活场景,其实对于来自乡村或生活在城中村的人来说会感觉比较熟悉。经诗人的艺术加工,生活场景等素材便成为精品。诗中,有“神仙们”“小脚的祖母”“木讷的孩子”的诸多人物形象,这些人物是有关联的,神仙们“接受了粗茶淡饭”,接受了小脚祖母的“擦洗”,它们即使在冬天“不懂得喊甜/也不懂喊冷”。可以想象,在人们看来,高高在上的“神,如此朴素”,仿佛它从来就生活在人们的身边,未曾“高高在上”。“神仙们”虽然得到人们的膜拜,在人们的心目中具有无穷的力量和能量,但从未轻视过人类。可以说,这是做人的一种姿态,难怪小脚祖母除了“擦洗每一张瓷质的脸/然后,又为我揩净乌黑的唇角”,这是一个多么巧妙的神居与坊间的“平衡点”啊。张二棍诗歌的魅力,便是隐性地设置人物的冲突,而又淡定地平衡他们之间的关系,从中找到一个和谐点,令生活境况趋于“公道”,而其中也不忘抒发人性的悲悯情结。
再造生活现场之后,塑造底层人物形象便不可忽略。倘若说《在乡下,神是朴素的》一诗凸显的是原生态的生活现场,其中人物(包括“神”)如此鲜活而极具个性,而对底层人物的塑造,也成为他诗写的一种特长。他塑造了憨厚的农民形象,不论是神,还是农民,其实都是同一类型的人物,即是生活在特定环境中的人,需要面对着生活的各种问题。可以想象,观察与记录成为张二棍写作的最初动机。这一动机与他在写作塑造的人物、构筑的现场均有着隐秘的联系,不过,不论如何隐性设计人物、事件和思想,诗歌还是自然回归生活的本身。再看看他对人物的塑造:“而现在,只有几个枯槁的妇人/伏在垃圾山上,翻捡着/为什么那个最瘦的女人,要带着一个/更瘦的孩子。为什么她那么小/却有着那么多的力气”(《十里坡》)。诗人通过诗行触摸到社会痛处,诗中人物“枯槁的妇人”, 挣扎、坚韧而富有“力气”,暗含着对贫苦生活的反抗精神和警醒意识。
场景布置、人物塑造,讲述人生种种,便能呈现生活精神和理想信念。诗歌呈现生活精神,是诗人人生观的一种体现,也是诗人传递给大众的一种生活境界。唐朝诗人王维在《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一诗中写道:“倚杖柴门外,临风听暮蝉。”诗歌叙写诗人与裴迪的闲居之乐。“倚杖柴门,临风听蝉”,把诗人安逸的神态,超然物外的情致,写得栩栩如生。这是一种境界,不追求物质享受,只重视内心世界,成为精神生活的一种体现。追求禅韵,品味大千世界,更是追求一种旷达的人生。诗人叶芝曾在《当你老了》一诗中写道:“当你老了,头发花白,睡意沉沉/倦坐炉边,取下这本书来/慢慢读着,追梦当年的眼神/那柔美的神采与深幽的晕影。”这种精神上的追求,也是呈现生活的一种态度,一种存在。“诗向来都是心灵的艺术, 它是生活逼入诗人心灵产生震动之后而形成的情绪凝聚”[5]。学者赵金钟这样阐述诗与心灵、诗与精神境界的关系。
诗是心灵的产物,也是精神的产品。在特定的社会语境和主流文学话语评判体系下,对底层生活现实的再造,要求诗人不仅要深入社会底层,还要具备必要的转换、过滤、变形和提升的能力。无疑,张二棍坐拥利于诗歌创作所需的生活环境条件,通过诗写再造底层生活便在情理之中了。
三、白描手法中的张力隐现
张二棍亲历社会底层的生活,因此特定的生活环境为他注入了泥土的味道,造就了其独特的创作手法。他以白描手法获得读者的称赞。而在诗作的叙说过程中,诗人有时适时保持着一种节制。他借“蚂蚁”写童真。打动人的算是诗写中由情感之“真”带来的细致刻写。无父子之真情,则无如此细致之观察,无如此细致之观察,则无此诗。“命名”一语,于最寻常中见“奇崛”。此诗如下:
“一定是蚂蚁最早发现了春天/我的儿子,一定是最早发现蚂蚁的那个人/一岁的他,还不能喊出,/一只行走在尘埃里的/卑微的名字/却敢于用单纯的惊喜/大声的命名//——咦”(《蚁》)
再以《雪上,加霜》为例,这些白描的文字里,几乎没有枝蔓点缀,潜伏着磅礴的力量。试读“在雪上/加霜/就像给水果加糖”这几句,在流畅中顿觉多种意象物在脑海闪现。这些诗句虽不长,都是生活中常态化的事物及现象,但并列出现后,就有深刻的内涵。短短几句话,一语双关,起到了多层次的意象转折,烙上现实生活的色彩。又如,“风里雨里,她一次次/来到这里,又离开/她带着哭腔/和自责。她带着/路上吃的干粮/和给儿子/买的糕点”,如此形象的人物形象,其神情构成生动的画面,由现实生活到文本,这些画面是动态存在的,其再次在人们视野中放映,倾诉生活的酸楚,却也以一种朴实的精神感染别人。诗歌创作正是用白描的手法,使语言更加诗化,把诗外的情感置于留白处,最终将诗作的思想和意境张力无限放大和延伸。正如德国诗人赫尔曼·黑塞(Hermann Hesse)所言,“一朵花或路上的一只虫,比图画室所有的书,蕴含着更多的内涵”[6]。可见,像雪、雨、糕点这样的意象物,在诗歌中发挥巨大的作用,而最直接的作用是成为张力延伸的坚实基础。
陈仲义认为,毋庸置疑,一首诗是一个张力场,一首诗的结构是一种张力结构。处在这样一个魔力场上,任何平凡的东西都有可能在里面被转化为光华璀璨的珠宝。[7]陈仲义“张力场”的提法比较切合诗歌艺术的实际。一般来说,张力的美学功能体现在词、词组之间的关系上,这是词、句、段系统组合的具有外延扩张的功能,具备放射性,使现代诗语言较旧体诗更具完美风格。
张二棍的诗写更自然地将张力隐藏于白描手法中,令人意想不到瞬间战栗。试看以下诗句,感受隐现于诗行中的张力:“他祖传的手艺/无非是,把一尊佛/从石头中/救出来/给他磕头/也无非是,把一个人/囚进石头里/也给他磕头(《黄石匠》)”“风是干净的,风吹过岩石的时候/岩石也净了。露珠滑过草木/悄无声息。(《无题》)”“我也觉得它们,英雄无用武之地/可还是买了。可能是为了/找个闲逛的理由/……/我拎着它们/叮叮当当的,在集市上/东瞅瞅,西望望/像是恋恋不舍/又像是别有用心/回来的路上,它们闪烁着寒光/想了想,我才三十出头/其实也可以,等几年再买”(《一辈子总得在地摊上买一套内六角扳手)》。
除了采用白描手法来激发张力的延伸之外,张二棍还喜欢用一种新的叙述方式,给人带来视觉和思维的冲击波,看看以下诗句:
“字和字挤在一起。逼仄让它们重新/分配着各自的地盘。嘘——/它们有了争吵,有了帮派,有了杀戮/嘘——。它们有了交易,有了宗教,有了朝廷/嘘——,让它们更乱一点。让它们,更像一首诗”(《元神》)
当然,诗歌的张力延伸的幅度随着读者的综合素质而变化。李永才认为,由于诗歌审美活动是人的个体心理体验,故必然受到个体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文化心理结构和时代价值观念的影响和制约,所以不同的诗人、批评家和读者有不同的审美视角和层次,标准和尺度。[8]为此,在诗歌阅读方面,由于张力延伸的作用,诗歌的审美尺度和视角应是多样化的。
四、生活素材与社会视角相结合
诗人每天一边用脚步丈量生活,一边凭借眼睛捕捉世界的万物。他像参加体力劳动一般,用一支笔,便能把一个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物和屡见不鲜的事物,如变戏法似的展开叙述,使其具有深度和亮色。他将生活素材与社会视角相结合,让每一首诗巧妙地切中人性的痛点,令诗歌的主题得以升华,从而传递一种独特的诗意。
张二棍每天除了完成工作任务,便奋笔疾书。他将写作当作一种特定的行为,像参加体力活一样投入,于是播种和收获属于自己的生活的乐趣。他像很多诗人一样,将笔触及到“乡愁”,对于思乡的情感,他别出心裁地进行处理,此种构思上的巧妙,那样朴素、自然,抒发情感又是那样的合情合理。《旷野》流露出对过去的怀念和对现今生活的种种顾虑,他这样写道:
“五月的旷野。草木绿到/无所顾忌。飞鸟们在虚无处/放纵着翅膀。而我/一个怀揣口琴的异乡人/背着身。立在野花迷乱的山坳/暗暗的捂住,那一排焦急的琴孔/哦,一群告密者的嘴巴/……/是啊。假如它脱口喊出我的小名/我愿意是它在荒凉中出没的/相拥而泣的亲人”。
又如,他的“拆字重组”的表达,令他的故乡“代县”如此亲近,如下:
“我说,我们一直温习的这个词,/是反季节的荆棘。你信了,你说,/离得最远,就带来最尖锐的疼/我说,试着把这个词一笔一画拆开/再重组一下,就是山西,就是代县,/就是西段景村,就是滹沱河”(《故乡》)
除了从社会视角诠释人生之外,张二棍还挖掘生活素材,讲述社会问题,其诗歌具有警醒世人的功能。因此,诗作《五月的河流》,亮点全在前半部分,诗人这样流畅地叙述:“只有我知道,一条河流的伤痛/它在五月干旱的人间,一寸寸收紧两岸/现在,它被掠取了澎湃,汹涌,荡漾/哦,这些波光粼粼的字眼。/它消失在自我的放逐里/它干涸,它生锈,/它在下游,用一尾泥泞中挣扎的鱼/殉葬。而我,/一个越来越冷漠的人类/把浑浊的两滴眼泪/收紧。仿佛那是悬着的命”。此诗无疑从社会视角,结合当下自然环境污染的问题,借季节性“五月”的大自然题材“河流”,讲述更深层的忧患。诗人借“干涸”写忧患,刻画更见锋芒,更有深度,更具震撼力。
张二棍的诗歌大多数从社会视角切入,反映社会生活现状。如《有间小屋》:“要秋阳铺开,丝绸般温存/要廊前几竿竹,栉风沐雨/要窗下一丛花,招蜂引蝶/要一个羞涩的女人/煮饭,缝补,唤我二棍/要一个胖胖的丫头/把自己弄得脏兮兮/要她爬到桑树上/看我披着暮色归来/要有间小屋/站在冬天的辽阔里/顶着厚厚的茅草/天青,地白,/要扫尽门前雪,撒下半碗米/要把烟囱修得高一点/要一群好客的麻雀/领回一个腊月赶路的穷人/要他暖一暖,再上路”。这首诗非常明快,勾勒出一幅温暖的画面:羞涩的妻子、胖胖的孩子、好客的麻雀。正是普通农家小院这样平常无奇的素材,在社会视角下,我们容易读出诗人平实而博大的情怀,也读出社会生活和谐及温暖的一面。还有诗人的《入林记》,同样从社会视角切入,讲述一群人或一种人的人生。诗作最具备调侃、深思的内容。在最后,诗歌这样叙述——
“我折身返回的时候/那丛荆棘,拽了一下我的衣服/像是无助的挽留。我记得刚刚/入林时,也有一株荆棘,企图拦住我/它们都有一张相似的/谜一样的脸/它们都长在这里/过完渴望被认知的一生”。
张二棍的诗歌总能给读者带来阅读上的痛快感。他虽生活在社会底层,直面荒凉与清贫,但他作为一个诗人,自然会凭借敏锐眼光和敏捷的思维,去观察社会和剖析人生。他的游走、观察、深思,积累了丰富的社会生活体验,也让他自然地拥有悲悯的情怀。路还在继续,生活中磨砺出来的诗意,总能鞭策诗人的诗歌创作继续向前,携带沉甸甸的梦,用灵魂倾听万物,进入生活的心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