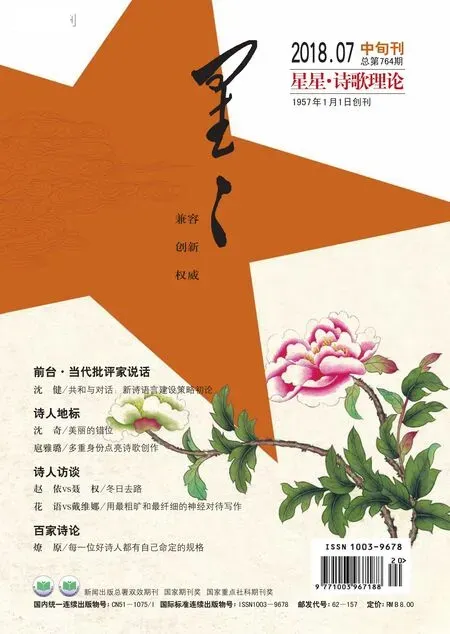共和与对话:新诗语言建设策略初论
2018-12-29沈健
沈 健
1978年以来的40年是百年新诗中兴的40年,其标志就是诗歌语言本体日趋独立与成熟,为现代汉语注入表现力的丰富性与深广度,“完成了中国经验的诗歌‘转译’,建设了自己的象征体系和文类秩序”[1]。一大批杰出诗人艰苦卓绝的语言探索和文本创构,支撑了新诗群峰巍峨、绵延起伏的兴盛格局,形成诗人风起云涌、文本精彩纷呈、语言绰约多姿的繁荣态势。
细究起来,近40年新诗语言的渐趋成熟,可分为两个层面,一为语言理念自觉,一为文本创构丰硕。先看语言自觉一面,于坚、韩东“诗到语言为止”等观念提出,是百年新诗语言本体自觉的肇始,其功不可埋没。接着,第三代诗人登场,“口语写作”“叙述诗学”“智性写作”“草根写作”等纷繁斑杂的“个人化写作”,将百年新诗带进了语言自觉、本体独立阶段,“语言工具论”被消磁,“语言就是诗本体”,“语言既是形式又是内容”“语感就是生命言说”等观念深入人心,并内在驱动着诗人们在文本实践方面殚精竭虑地开疆拓土。如果再稍稍上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纪弦、洛夫、郑愁予等人孤悬海外的摸索与积累,到80年代左右传入大陆,无疑加快了新诗艺术自觉的步伐,丰富了现代汉语写作本体自觉的层次与内涵。
不妨以“语感”为例略作展开。语感在语言学中是指对语言的感觉,作为诗学概念出自杨黎和周伦佑1986年的一次头脑风暴。此前在一篇文章中,杨黎曾朦胧意识到,“语感,就是射向人类的子弹或子弹发出时所发出的超越其自身意义之上的响声”,“语感就是一口气,写诗也就是一口气的纯化、虚化和幻化”[2];周伦佑接着进一步充填了语感的诗学内涵,“语感先于语义,语感高于语义,故而语感是指诗歌语言中超语义成份”[3];在此基础上,在于坚与韩东一次对话中,“语感就是生命有意味的形式”这一生命诗学的核心终于水落石出。可以说,伴随着国人生命意识的觉醒和西方语言哲学的转向,正是“语感”一词催发了新诗向生命本体深度掘进的诗学之潮,使诗歌回归到透明、自然、本真、个人生命存在状态。应该说,对“语感”概念的发现与体认,为新诗语言自觉敞开了一个新的疆域,对引领提升胡适以来口语新诗抵达新境界的作用显而易见。
接着来说诗歌文本创构一面。从多多、杨炼、顾城、舒婷等“今天派”诗人开始,加之彭燕郊、曾卓、昌耀、孔孚等“归来派”诗人,新诗“像悬崖边上的树”绝处逢生,接通了郭沫若、冯至、穆旦等人创建的新诗前30年“小传统”(何其芳语),并与西方现代诗歌汉译全面对接融通。一种“汉译中所移植的西方语法和西方感性”“白话文与汉译的混合体”被建构出来[4],“新的美学原则”崛起于当代诗坛。随后贯穿整个90年代以至新世纪最初十年,经于坚、韩东、欧阳江河、西川、杨克等大陆“第三代”诗人的精耕细作,包括港台乃至全球华语界在内,对新诗语体技艺多样化、细密度、柔韧性、繁复程度进行了持久而耐心的探索,奠定了现代汉诗日渐成熟的性状基础。在这一阶段,汉译更大规模地涌入,一些小语种如西班牙、阿拉伯、东欧、拉美甚至日本诗人,被多元化、多层次地译入汉语诗界,成为新诗诗写资源。与此同时,起步于台港的“新古典主义”诗潮追求,遥与大陆文化守成主义思潮呼应,新一轮“化古”诗学取向悄然复苏,为新诗创造性转化提升辟开了一个源头。柏桦的《在清朝》《水绘仙侣》、肖开愚的《向杜甫致敬》、杨键的《哭庙》、潘维《太湖龙镜》等文本的涌现,标志着“中国新诗的作者们开始掌握了古诗中那种实实在在、细节充盈的写法,亦即大量的用典、细部刻画和说理”的语言方式[5],多元化的现代汉诗形态日益丰富多彩。
及至当下,姜涛、江非、朵渔、巫昂等70后诗人,郑小琼、肖水、黎衡、胡桑等80后诗群,从各自的优长与方位出发,为新诗语言的特立独行的表现力作出了多方创造与纵深细化。而以北岛、严力、张枣、雪迪、李笠等流落海外的诗人身处异乡反观母语的写作,从非母语的反差与参照中,为新诗重新注入了多样态的“异质性”和汉语古老的“德性”。
由此粗略勾勒,可以见出40年来新诗在呈现汉语经验的繁复性、深刻性和生动性等维度上,已取得远超于前60年诗学探索的成就,形成了繁复与幽深同在、俏丽与高峻并存、冷冽与优雅共融的现代汉诗语体。
但是,深度质疑新诗成就的声音一直不绝如缕。而且这种质疑来自诗人自身,可见其真诚与善意。如上世纪40年代走上诗坛的“九叶”诗人郑敏,将“中国新诗创作已将近一世纪”,却“没有出现得到国际文学界公认的大作品、大诗人”之因,归咎于“自绝于古典文学”[6];再如,上世纪50年代走上诗坛的老诗人流沙河,到了晚近时候在多个场合承认新诗是一场失败的实验。如此等等,这无疑为诗界以外否定新诗成就提供了“口实”和“把柄”。至于诗界内部,争名夺利的内耗更是层出不穷。远的不说,仅上世纪末“盘峰诗会”后,“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论争造成诗坛的深刻撕裂,至今仍阴影难散;稍后的“下半身写作”“梨花体”“羊羔体”“口水诗”“垃圾诗”等,则严重消蚀了新诗的信用成本,在诗歌文化方面造成的负面影响十分深远;而“底层写作”的道德化诉求,对余秀华“摇摇晃晃在人间”的身份与写作的尖锐对立的臧否,又为新诗“滑向”意识形态写作推开一隙小门缝。
不妨以“知识分子”和“民间立场”为例,回望一下当年双方水火难容的诗学路向选择之利弊与得失。“知识分子”一路,追求形而上的神性超越,倾心于语言技艺精湛磨练,醉心于客观节制隐忍的“中年写作”,但也出现了冷漠炫技、空泛失效的症候;而“民间立场”形而下观照中,为诗歌“及物”和“口语化”叙事提供了原生态生命经验,却因过于粗鄙琐屑陷入浅白与俗陋。前者过于高蹈抽空了人学的大地真气,后者偏向世俗失却了精神超拔,一方地气不足,一方自甘沦落。两大阵营的攻讦、谩骂等非理性行为,恰恰为诗界以外制造了“诗歌死了”的现象学“绞索”。美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当代诗歌的巴尔干化”现象几乎在汉语界被重演一遍,“导致相互批评的尖酸刻薄”,“自相残杀的激烈争吵”[7],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从诗人主体性重建来说,这是一场生命和文化的困境;从社会自主性浴火重生来说,这是一场涉及整个中华民族的体制困境。后一困境,乃是由于全球性的开放与冲突中,时代将现代性、野蛮性并存的“时间”叠加在当下中国“空间”内而形成,语境极其复杂。总体上说,它们表现为一种存在论诗学本体的语言困境。
这种困境的解开有待于诗人自身的文化创新能力的提升与不竭投入,有待于诗人个体深入到生命与语言内部,通过个体历史细节性多元、形态多样的挖掘,进而为诗歌输献来自生命源头的哲学活力。当我们说,新诗兴盛繁荣,是就纵向比较而言的,如若将新诗置于全球现代诗学文化参照系来看,也许尚需生生不息的创造努力。个人非常赞同李少君关于新诗发展的预测,“一个融会贯通的时期”已经到来,“众多具有个人风格和审美追求的优秀诗人相继涌现”,“将有集大成的大诗人出现”[8]。新诗希望内蕴于新诗危机之中,在百年新诗再出发之际,倡导良性竞争意识,促进新诗沿着理性、有序、健康的论争前行,诗人和诗界应该如何应对与自处?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重大课题。
以政治学的共和理念引领诗歌语言的创新,也许不失为有效策略之一。作为一个政治学术语,共和意指非君主制混合政体,在本文中是喻指诗歌语言、题材、风格、形式理想化的大综合、大混融的共生状态。即,以人性、自然性、神性和诗性为美学天宪,以提供人心慰藉、人生庇护、生命安妥为终极旨归,忠诚于汉语的主体尊严、个我纯粹与开放性活力的迸发,“把美团结起来”(李浔诗句)。无论诗人个体,还是传播平台,包括意识形态管理者,都必须以共和理念贯穿诗歌生产与传播全程,充分尊重个体创造,处理好地方与京畿、方言与书面语、个人私语与公共话语、历史与现实、瞬间与永恒、自我与他者、全球化与地域性等多元主体间的复杂关系,共和于语言建设,共和于文本创新,共和于美学实验。
具体说来,以下几个方面须要特别强调。
一是现代汉语、口语、古诗词、文言、翻译语体间的对话共和。如前所述,百年新诗写作资源主要在“化欧”一脉,无论是前30年的陆志韦、李金发、戴望舒、艾青,还是后40年来昌耀、海子、王家新、西川,甚至江南诗人潘维、陈先发、陈东东、庞培等,都无不受益于翻译语体,因接通西方现代诗歌脐带而奇峰异起。但毋庸讳言的是,从发生学上看,新诗对文言传统的断崖摈弃,是百年新诗先天不足的一个遗传学症结。最近李敬泽《重回中国文学“文”的传统》、李少君《我的心、情、意》等文章对回归传统精神立场的强调和文化保守主义的申明,体现了将以文言为代表的悠远传统重新纳入当代文学精神食谱的良苦用心,值得诗人群体的高度重视。
事实上,文言与白话在写作中并非二元对立,作为一种传统它们一直辩证地活在现代汉语衍变之中,百年新诗文本上游也一直鲜活地跃动着古典的美学影姿,这一事实曾被许多诗人反复提及。多多虽说“书架上没有一本中国古典文献”,但他坦陈写过古诗词这一事实,“我个人非常喜欢辛弃疾的诗词……这种古典文化的影响是致命的,因为汉语的精髓就在这里,汉语最精妙、最具尊严的部分都在这里[9]”;张枣认为现代汉语诗歌的中国特征,就在于,“既能从过去的文言经典和白话文本摄取养分,又可转化当下的日常口语,更可通过翻译来扩张命名的生成潜力[10]”;诗人梁晓明更是奇绝无比,他的代表作《开篇》《敬献》等巨制,《玻璃》《各人》等短章,都无不混凝着惠特曼、聂鲁达和艾吕雅等西方超现实主义大师的质地。但这个“一直在写着现代诗”的怪侠,居然30多年来一直在译写唐诗。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忆长安——诗译唐诗》译诗集子,译有李白王勃白居易等人诗歌50首。请看《夕次盱眙县》的转译:
“篷帆从手中落了下来/我面对着淮水的南岸/驿站孤单地看着停船/浩大的风/吹起了浩大的波浪/无言的黄昏降下了沉默的太阳//
人一走开/城墙就一片黑暗/大雁收起翅膀的芦花/水泽一片雪白/独自的/夜晚/想起秦关一带/钟声盘绕在耳朵上/有一个客人/整夜难眠”
韦应物的原诗是这样的:“落帆逗淮镇/停舫临孤驿/浩浩风起波/冥冥日沉夕/人归山郭暗/雁下芦洲白/独夜忆秦关/听钟未眠客”。对读一下,我们发现,梁晓明的翻译已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译写,而是现代诗性话语的创造性转换。无论是话语节奏、表达技艺、内在韵律,还是诗思方式、动宾主格、沧桑情怀,都散发着现代汉语特有的冷峻而客观、自由而细密的生命感怀。梁晓明是越过“七律、七绝和沁园春、虞美人之类的东方篱笆”走上诗坛的,唐诗的美学气韵、意象构成、细节摘取作为背景与传统,作为悠远博大的文化基因,在他的创作中起着怎样作用?其影响属正面,还是负面?
无独有偶,于坚近年也一再表明对古典的回望,“我是想让新诗更接近于古代的感觉”,“把现代和古代时空的断裂融合在一起”,在《苍山之光一秒钟前在群峰之上退去》等诗中,于坚反复嵌套古人诗句进而形成互文结构,为汉语灌注“混凝土式创作”的词语张力[11];诗人汗漫试图“跨界融合”苏东坡与布罗茨基,“用一枝笔作为还乡的栈桥”,他甚至写下了大量拆解、重组汉语成语的诗歌,为现代汉语锻打了一种罕见的柔韧性与鲜活度;诗人李亚伟则从“莽汉”转身为“只能活在自己命里的长工”,沿着河西走廊的史籍残片,深入中古汉语的“欧亚大陆交界处”,他的长诗《河西走廊抒情》似乎要为汉语找回一个中亚的精神源头。这一切都无不意味着对地道汉语传统回归的“尝试”,正在成为诗人们自觉行动,佐证着艾略特所说诗人“所生活于其中的不但是现在,而且是过去的时刻”,传统从未完全断裂或阻隔,一直活在诗人的创造之中。
如是而观,除了坚持“别求新声于异邦”,我们还要回头“别求新声于”“文言”,“别求新声于”“化古”,从而多元混杂地创造出一种集大成的汉语经典文本。比如,古汉语中孔孟的平和仁慈、庄老的渊默超妙、史记的浑朴遒劲、《世说》的简洁高远、《梦溪》的博闻精微,明清小品的家常亲和,近代小说的怪异阴谲,都是值得现代汉诗埋头勘掘汲取光大的富矿。青年诗人胡弦近年的创作可以说是得益于传统回归的典型个案。他的《空楼梯》、《沙漏》等代表作,文白杂陈,长短句穿插自如,三字句、四字句、五字句较多,甚至一字句、破折号感叹号也频频出场,随着诗意传达需要自由错置,顿挫抑扬有如宋词,俚语偈句的植入又酷似元曲与明清说书。胡弦对现代汉语、欧化译语、文言经典的共和态度与开放汲纳对诗界不无示范意义。
二是地方、京畿、全球文化间的对话共和。京畿之音与地方之声自《诗经》以降就已经存在,西方现代诗歌也存在着地方差异性、多样性与互文性相互激荡相互成全的现象。法国就存在着“外省”与“巴黎”之别,美国诗歌除新批评派诗歌中心外,在旧金山有“垮掉”一代,马萨诸塞有“黑山派”,明尼苏达则有勃莱与默温的“新超现实主义派”;英国也是如此,以艾略特、奥登为代表的工业文明对人的异化批判,属于学院派主流诗写,以叶芝、希尼为代表的神秘主义自然主义诗歌,属于爱尔兰地域性的书写,麦克迪尔米德等人的诗歌,则代表了苏格兰的方言抒情,他们都是英语诗歌共和繁荣不可或缺部分。回首近40年来的当代新诗创作,事实上也存在着地方化与京畿圈的紧张,存在着全球化与汉语的对立。“京城”由于文化资本与政治权威以及来自全球化的“跨国影响”,客观上附加着一种高屋建瓴的话语权优势,以王家新、臧棣、唐晓渡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写作群体,穿梭在学院、刊物、国内外诗坛,天然拥有一种布尔迪厄所谓文化资本的场域能量。与此同时,在全国各地甚至京城底层密布着不可胜数的地方性诗人。两者的身份标识与美学分野比较清晰。相对来说,京畿知识分子多处学院与科研机构体制之内,更注重专业与形式实验,有着鲜明的技术主义取向;外省诗人则多游离于体制之外,偏重于道义担当和自由抒情。另外,台湾港澳地区的华语诗人,游走于国外“漂泊者”群体如前述北岛、杨炼等,也在各自领域内为百年新诗再出发集聚着力量。尤其是“漂泊者”群体,为新诗“汉语性”与“世界性”的整合优化贡献着才智与创造,作用不可替代。
西川在中央美院工作,是当代“诗歌炼金术”发明者之一,他中正、纯粹、平和的诗学技艺,为新诗创构了集西方与东方、古典与现代、宗教与世俗于一体的综合性话语谱系。在《致敬》《午夜钢琴曲》《戒律》等作品中,西川将反讽戏仿与经书箴言嫁接起来,将杜甫的精湛细节和博尔赫斯的神秘幽邃榫合一体,形成了中国古典汉语中的骈偶回复与《圣经》散文语体共生互构的形态,极大地丰富了汉语的表现力。西川的成功实践表明,有效地将诸种异质文化共和于诗人内在的创造之中,必然会催生汉语的良性衍化。偏居大漠的沈苇超越地域之限,将新疆大地作为一部线装经书来书写,他的《新疆诗章》《高处的深渊》《我的尘土我的坦途》等诗,在形式的杂烩、文体的混血、诗思的多元方面,创构了一种当代诗坛罕见的“混血写作”模式,为现代汉诗注入了罕见的开放自信与大气。“突厥语,波斯语,阿拉伯语/交换内在的信物和光芒/正如小径交叉的喀喇汗花园/慷慨的百花交换着各自的芬芳”(《喀什噶尔》),各种语言、多样文明、不同人种、迥异时间在他的诗中媾织、对话、叠加、交流,呈现了“百感交集”的生命面相。近年来沈苇的写作变化明显,《对话》《向日葵》《秋日,旅途》等诗,彰显着对生命的绝对尊重、对人性的无条件肯认、对爱的宗教布施等普世情感。他早年诗歌“高处的深渊”的空疏与旷远被细节渐渐填满,奇峭富丽的语言也转身为朴素柔韧,语调日渐深沉和缓,表现力、喻指性日趋综合多元。对西川、沈苇的综合写作的解读,本文旨在申明,区域对话、民族对话、文化对话、体制共和、全球对话等,对营造综合性大诗人成长环境有百利而无一弊。
在当代诗歌群星灿烂的版图上,任指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都能发现钻石一般优秀的诗人群落。比如在浙江东海之滨,李郁葱、韩高琦、蒋立波等人所组成“原则诗群”,数十年来追求“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境界,悄无声息地浇灌着个性峥嵘的诗歌园圃。蒋立波《帝国茶楼》《辅音钥匙》等文本,执着于词语挖掘、拆分、重组,胶合了修辞、韵律、政治、社会的肌体,给诗歌带来了传统中医针灸一般荡人心魄的功效。据我所知,“原则诗群”心平气和自甘边缘,不为外在所动,甚至连发表、获奖也不甚热心,其写作动机只有一个——内在的自我完善与语言创造。而像这样的群体在全国各地比比皆是。
如是而观,必须以共和理念倡导激发新诗创造的能量,特别是要鼓励偏远地方、小众群体、片面美学、极端嗜好的诗学探索。如雷平阳在人性的批判与地域文化内在沟通方面的宏观照亮与微观传达的有机结合;再如黄礼孩对人性的纯正如银、清朗如歌书写;西部叶舟对江南太湖风情异域华滋的瑰丽呈现;重庆张远伦蛰伏乌江老宅专注的诗意“请水”;还有孙文波、哑石、陈先发等人回归古典的探索,都是百年新诗再出发值得重视的力量。
三是自然、人性、历史、哲学、想象力、自我间的对话共和。应该说,新诗在呈现复杂主题、多元人性、跌宕命运、卓异体验方面,已积累了自成一体的技艺修辞与话语经验,“由生活现实向精神现实和写作现实转换的难度不在于语言、修辞、技艺的难度(实际上这在很多熟练性的诗人那里已经不再成为问题)”[12]。接下来需要强调的是,强调对话,而非对抗,强调互文,而非排异,强调竞争批评,而非专制毁弃,如青年诗评家杨庆祥所言,要“通过对话摆脱现代主义一极化的危机”,努力涵养有益于综合性大诗人成长的诗歌文化。
在共和理念下,要推崇新诗与自然、历史、哲学等精神资源之间的对话。李少君近年来力倡心学与自然哲学,他的诗集《自然集》以及《神降临的小站》《东湖边》《碧玉》等短制,通过永恒与消逝之间的紧张来“抓拍”急剧流变中人性的自然恒存,这是一种借力梭罗生态美学与王阳明学说杂糅整合,从而凸现生命关怀的诗学探索,其语言散发着一种王国维所谓的“古雅”气息。李少君对宋代诗歌“自然之趣”“日常之理”“宗教之悟”等道统的追求,对杨万里“努力要跟事物——主要是自然界——重新建立嫡亲母子的骨肉关系,要恢复耳目观感的天真状态”[13]“活法”的化用等等,给新诗带来的也许将不仅仅是一种启示。
多多诗歌通过音乐节奏的想象力来“经营一首诗的苛刻”,也是诗人强化人性、自我共和对话的经典创造。评论家李章斌通过耐心细致的文本细读,找出了多多诗歌中“同声、同韵以及同一字词发反复使用”,如同一场“诗歌内部的战争”,为多多诗歌带来历久弥新张力的秘诀,是对新诗内在音乐性的重要发现。在多多《北方的夜》《没有》《什么时候我知道铃声是绿色的》等诗中,他所“追求声义并茂的努力实质上是一种回到语言之本源与原点的努力”,“更新语言与世界的最初联系,激活语言根的生命力量”[14],是人性复苏与激活的卓越语言创造。相信随着研读的深入,多多新诗所蕴含的营养还将被不断发掘出来。
王寅和陆忆敏对现代人的荒诞、孤独与冥想以及被现代秩序规制中人的隐忍克制与自我修行的书写;余怒从早期暴烈的陌生化语言策略到晚近及物场景平静叙述的人性雕刻;伊甸对现代人性遭遇暴力戕害的抗议所呈现的语言古典德性与现代批判间的歧义张力;池凌云对制度压抑下女性内心分裂与自洽努力的深度描述;苏野通过“中古”情境来再现“当代”情怀与气度的精神实践;张执浩在喧嚣时代对日常人性“轻言细语”的“复活”与“唤醒”;莫非试图通过词语原初意义的复归来抵达生命本色的冶炼;蓝蓝对人性和语言张力纤细而峭拔的穿刺;张二棍对现实与生命北魏石雕匠人式的剥蚀能力,等等,都从各自领域体现了当下诗人与人性、哲学、现实、历史和自我对话的开拓掘进。让这样“八仙过海”的写作对话共和于新诗创造的天空之下,承继多多、昌耀、张新泉、黑陶等人的硬语盘空,杂融王小妮、陈东东、庞培、李元胜等人的软语商量,互文马新朝、江一郎、古马、人邻等人的朴素劲健,形成综合共生的话语态势,我们有理由相信,百年新诗“黄金时代”的到来,一定不会是一种一厢情愿的海市蜃楼。
总之,我们要反对那种唯我独大、老子独尊、不灭他人不朝食的绿林意识、帝王姿态、诸侯立场。在共和共建共生、互竞互促互构的文化氛围中,形成“多元共生体系”或者说“多元一体的诗学结构”,百年新诗再出发,集大成的诗人必将诞生。
【注释】
[1]王光明《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39页
[2]杨黎《声音的发现》,民刊《非非》(1988年鉴·理论卷)
[3]周伦估《非非主义小辞典》,民刊《非非》(1988年鉴.理论卷)
[4]黄灿然《在两大传统的阴影下》、杨克《1999年中国新诗年鉴》,广州出版社2000年版,第419页
[5]王凌云《回到沉郁:中国当代新诗的古典取向》,《东吴学术》2016年1期
[6]郑敏《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文学评论》1993年6月
[7]丹尼尔.霍夫曼《美国当代文学》(下),裘小龙等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第718页
[8]李少君《当代诗歌40年》,《文艺报》2016年5月25日
[9]《多多访谈:我主张“借诗还魂”》,《南方都市报》2005年4月9日
[10]张枣《朝向语言风景的危险旅行——中国当代诗歌元结构与写者姿态》,《张枣随笔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72页
[11]于坚 傅元峰《在古典的方向上长出一毫米——于坚、傅元峰对话录》,《艺术广角》,2013年9月
[12]霍俊明《没有“远方”的诗学——关于诗歌写作与当下现实》《艺术评论》2014年9月
[13]钱钟书《宋诗选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5月,第255页
[14]李章斌《多多诗歌的音乐结构》,《当代作家评论》,2011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