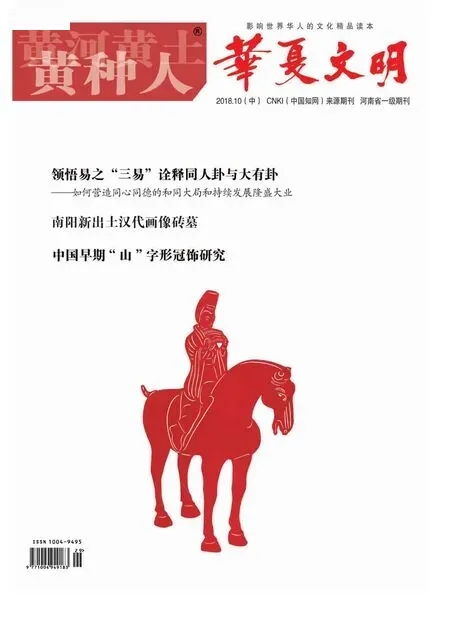重庆城墙的营造特征与文化遗产价值探析
2018-12-25蔡亚林
□蔡亚林
城墙是古代城市的组成要素和象征符号,其发展演变与国家产生、文明形成、环境变迁及社会结构等重要历史研究密切相关。柴尔德将社会从史前进入文明的巨大变革称为“城市革命”,并提出“有10个以上的考古学材料演绎出来的抽象标准,可以把甚至是最早的城市与任何过去的或当代的村庄区别开来”,其中即包括城墙在内的“巨大的公共建筑”[1]。 《吴越春秋》曰:“鲧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这一“卫”一“守”,说明城墙产生即伴有浓厚的防御色彩,同时也兼具区分君民的政治功能。
城墙作为城市边界的象征意义和军事防御功能,已伴随着近现代以来的城市发展建设而逐渐没落消亡,但作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和生生不息的实物见证,古城墙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是宝贵且不可再生的文化遗产资源。准确把握不同城市城墙的营造特征,深入挖掘并科学评估城墙的文化遗产价值,是城市考古和历史研究的必然要求,也是我们做好城市规划、遗产保护的基础和前提。
1986年,经国务院批准,重庆成为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2013年,重庆市规划局组织《重庆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编制,并于2015年1月获得重庆市政府的批复。笔者有幸参与了该项工作,在实地调研、课题研究与规划编制过程中,结合既往在渝中区的文物调查与考古发掘工作,对重庆城墙的营造特征与文化遗产价值进行了初步思考。现将相关理解与认识梳理如下,以期抛砖引玉,助力古城墙的研究、保护和合理利用。
一、重庆城墙的历史沿革
重庆古城位于渝中区,地处长江、嘉陵江两江交汇的半岛之上,明曹汴在《重庆府城垣记》中称其为“蜀东巨郡”。重庆古属巴地,据段渝先生考证,殷墟卜辞中即有“巴奠(甸)”之称,至西周初年,巴国王受周室分封,不可能不形成早期城市,但其形态至多可定义为正在形成中的城市[2]。目前,学界普遍认为重庆城始建于战国,经蜀汉、南宋、明代的重修,于明初形成“九开八闭”十七门的城垣布局,清代经过多次修葺,民国以后逐渐废弃。其中,比较重要的阶段,有巴国分封、明玉珍大夏政权、抗战时期临时首都与秦张仪、汉李严、宋彭大雅、明戴鼎四次较大规模的筑城活动,故重庆城市发展沿革有“三次建都、四筑渝城”之说。
公元前314年,秦将张仪在巴子城基础上筑江州城,《华阳国志》云“仪城江州”。东汉时期,江州城一度迁至北府城(今江北嘴),后迁回南城(今渝中半岛)。《华阳国志》载:“汉世,郡治江州,巴水北有甘橘宫,今北府城是也。后乃还南城。”蜀汉建兴四年(226年),江州都护李严自永安还驻江州,修筑江州城墙,设苍龙、白虎门。宋嘉熙三年至嘉熙四年(1239—1240年),为抵抗蒙古入侵,四川制置副使兼重庆知府彭大雅抢筑重庆城,至少已设有洪崖门、千厮门、太平门、薰风门、镇西门等五门,并在城西南设一字城以加强长江沿线防御。明玉珍大夏政权时(1363—1371年),对重庆城墙的垛石进行了加砌。明洪武六年(1373年)设重庆卫,重庆卫指挥使戴鼎在旧城基础上砌石为城,设“九开八闭”十七门。
明代中晚期到民国时期,重庆城墙又经历了数次毁建。隆庆初年(1567—1568年),王乾章对重庆城墙进行了一次修补。清康熙二年(1663年),四川总督李国英对重庆城墙进行了补筑。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重庆知府陈邦器对城墙进行了修补。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四川总督曾开泰下令修补城墙。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巴县衙门对东水门至元通寺段低矮城墙进行了增高补筑。清咸丰二年(1852年),重庆知府鄂惠重修城墙。清咸丰九年(1859年),川东道王廷植复又重修。清同治九年(1870年),川东道、重庆府、巴县衙门三级官府共同对城墙进行补修。
近代以来,重庆城因城市建设活动而受到一定程度破坏。1922年,重庆商埠督办扩建郭外马路,拆除临江门瓮城、通远门瓮城及城墙。1926年,潘文华任重庆市市长时,为建筑马路,宏阔码头,朝天门、南纪门、西水门、定远门、太平门(瓮城门及城墙)等悉被拆毁或掩埋。1935年因修建缆车,太安门被拆除。
二、重庆城墙的考古发现
重庆城的文物考古工作开展较早,比较重要的有:20世纪60年代,在一号桥铸造厂汉墓中出土的“江州庙官”汉砖;1953年,在朝天门片区发现的汉代水井、绳纹陶片;1958年,在千厮门一带发现有汉代水井及井圈;1976年,道门口四川省轮船公司修人防工程时,发现直径1米的水井栏,出土战国时期绳纹陶罐,西汉如意云纹瓦当[3];1980年及1982年,分别在左营街、临江支路发现西汉木椁墓等[4]。这些发现,虽年代较为单一,亦与城墙营造无直接关系,但与水井、墓葬的分布相关,为探讨重庆早期城市空间布局提供了重要线索。
与城墙本体直接相关的调查、考古发掘工作,在近十年里有较大进展。2010年,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在发掘老鼓楼衙署遗址时,开展了太平门至储奇门段顺城街城墙、城门专项调查,发现并载录了因施工出露的人和门。2012年,渝中区文物保护管理所对重庆古城墙遗址开展了首次调查,编制了《重庆母城“九开八闭”城门城墙现状调查报告》。2014年,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与渝中区文物保护管理所,对太平门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面积800平方米,清理了太平门城门、瓮城、城墙、道路、排水沟等各类遗迹33处。2015年,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对朝天门至西水门段城墙开展考古发掘,发掘面积3335平方米,发现有城墙、房址、道路、水井、排水沟、水池、灰坑及柱洞等遗迹285处。其中,在北段发现了宋、明两期城墙叠压现象,印证了文献记载明初“因旧址筑城”的具体方式。如明正德《四川志》卷13《重庆府》中“本府石城,因山为城,低者垒高,曲者补直”的记载。2015年,受重庆市规划局委托,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对重庆城墙城门遗址开展专项调查,基本掌握了重庆城墙的分布情况[5]。
三、重庆城墙的保存现状
据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调查材料,重庆现存城墙分布于渝中半岛东部,城圈西至七星岗,南北顺长江、嘉陵江走向依山就势延伸,至两江交汇的朝天门处围合,平面略呈东西尖、南北缓的椭圆形。除个别炮台、排水孔外,未见马面、敌楼等城墙附属设施。城墙时代面貌以明清时期为主,部分段落叠压有南宋城墙。201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通远门及城墙、东水门及城墙遗址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重庆清代城墙原周长“二千六百六十六丈七尺”[6],约 8720米,现存城墙 4364米,除部分掩埋段落外,目前可确认的明清城墙总长约3744米,南宋城墙长约150米。重庆城墙原设“九开八闭”17座城门,开门包括朝天门、东水门、太平门、储奇门、金紫门、南纪门、通远门、临江门、千厮门,闭门包括翠微门、太安门、人和门、凤凰门、金汤门、定远门、洪崖门、西水门。开门中,有朝天门、太平门、储奇门、南纪门、通远门、临江门、千厮门七个门设有瓮城。现存城门7座,其中开门6座,分别为东水门、太平门、通远门、千厮门、南纪门、储奇门,南纪门、储奇门、千厮门仅存部分瓮城;闭门1座,为人和门,保存较好。
重庆城墙依山傍水而建,现存各段均为夯土甃石结构,由包边石墙、女墙、顶部石板道路及内部夯土等几部分组成,整体保存较好。以2015年清理发掘的朝天门至西水门段明清城墙为例:城墙基厚14.70米、顶部残宽8.50米、残高10.88米。外墙墙基以8层大条石丁砌,层层收分,高3.20米。下部外侧发现碎石夯筑的墙基护坡。墙体在基础上内收约0.25米,高7.68米,错缝丁砌,条石间以泛黄白灰填缝。壁面斜直,倾斜度约71°。女墙残宽1.40米,高度不明,未见垛口。城墙顶部道路原宽度应在7米以上,残宽1.6~3.4米,规整石板铺就,中部略下陷,踩踏修补痕迹明显。城墙内部夯土可分39层,层厚0.04~0.45米不等,内高外低倾斜堆积。夯土以黄、灰色黏沙土夹石块及鹅卵石夯筑,质密,夯窝不明显。夯土内包含物以宋元时期青、白及影青、黑釉瓷片为主,另见较多外素内布瓦片、缸胎硬陶片,少量汉至六朝时期墓砖,宋代礌石1枚,瓷器可辨器形有碗、盘、碟、罐、壶、灯及高足杯等,窑口主要有湖田窑、龙泉窑及涂山窑等。
四、重庆城墙的营造特征
重庆位于重山重水之地,城墙依山而构,临江而筑,“山、水、城”的有机融合与“九开八闭”的城门设置,在古代城市营造理念方面别开生面、独树一帜,具有鲜明的区域特征。
重庆城墙是中国古代“道法自然”思想的重要体现。重庆古城突破《周礼·考工记》的传统束缚,区别于既往北方平原城市受“方九里,旁三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拘囿的情况,城郭不中规矩、道路不中准绳,忽略中轴线与对称性,重视城市营建与自然山水的和谐共生,依山就势,随意赋形。城门至明代发展至“九开八闭”,或象征“九宫八卦”,营建思想具有浓厚的道教色彩,是中国古代“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思想的传承与实践。
规划布局方面,重庆城墙为中国南方山水城市的营造范例。重庆古城承袭《管子》城市营建思想,依山为城,以江为壕,随山形走势构筑城墙、城门布局,平面形状呈不规则形,设“九开八闭”十七门。城墙充分利用渝中半岛西高东低的地势特点和两江环抱的地理优势构筑,东西最大高差达155米,雄伟、峻拔,“石城削天,字水盘郭”。城内布局利用北高南低的地势特点形成上半城、下半城的城市空间格局,极具山城特色。道路有机生长,建筑重叠错落,街市随意赋形,城区跳跃拓展,各个历史阶段风格鲜明,城市形态独具特色。
结构设计方面,重庆城墙是城市与自然山水和谐共生的杰出代表。城墙选址走向利用山水形胜之便,利用山岩与江岸的自然高差,设计为外高内低,多不设内墙,城墙顶部即为顺城街道。城墙结构为夯土甃石结构,底部基础多直接坐落于基岩之上,在建筑材料、营造技术方面,就地取材、因地制宜,与其他地区明代以来城墙夯土甃砖传统有着明显区别,故有“天生重庆”之美誉。
灾害防御方面,重庆城墙具有较为先进的“城堤一体”科学理念。重庆古城将城墙与堤坝有机结合,是中国南方山水城市规划和防御工程技术水平的重要体现,经受了诸多历史洪水灾害的严峻考验,至今在水利、内航及城防建设方面仍有参考借鉴意义。
五、重庆城墙的文化遗产价值
城墙是重庆城市发展演变沿革的直接见证。古城在古巴子国的基础上,历经战国、蜀汉、南宋、明初四次大规模修筑,逐步形成了“九开八闭”十七门的城市格局。城墙遗址包含南宋、明、清各个时期的城墙、城门(含瓮城)和炮台遗址,遗存类型丰富、时代特征鲜明,堪称记录重庆历史演变的“活化石”,是研究重庆城市空间布局变化、中国古代城池发展演变史的重要实物标本,是重庆城市从蹒跚学步、筚路蓝缕到跨越发展历经沧桑的生命印记。
城墙与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密切相关。古城墙是“四筑渝城”“三次建都”等城市发展进程的实物载体,城墙的历史环境包括了秦灭巴蜀、三国争霸、宋蒙战争、元末起义、张献忠屠蜀及抗日战争、重庆城市近代化进程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与古城墙直接相关的重要历史人物更是不胜枚举,张仪、李严、彭大雅、余玠、明玉珍、戴鼎、王乾章、张献忠、陈邦器、李国英及杨森、潘文华等,均在重庆古城墙留下了浓厚的一笔。古城墙是相关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推动历史进程、改变世界格局的珍贵见证,是相关历史研究与人物考证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
城墙可证实、订正、补充大量文献记载的史实。基于古城墙遗址的科学调查、发掘及研究,可透物见人,亦可“证(正)经补史”。《华阳国志》《晋志》《三国志》《宋史》《明史》《四川通志》《重庆府志》《巴县志》及《水经注》《文献通考》《舆地广记》《舆地纪胜》《读史方舆纪要》《元和郡县志》中,对重庆古城的地望、筑城活动及沿革变迁等,均有不同程度的记载与描述。其中不乏模糊、矛盾甚至错误之处,通过古城墙科学的考古及研究工作,可正文献之误、补历史之缺。
重庆城墙是城市建筑景观艺术的有机结合。诚如梁思成先生所言,城墙是人工劳动的创造,它朴实无华的结构,单纯壮硕的体形,是劳动人民血汗和集体智慧的结晶,它不是一堆平凡叠砌的砖土,而是磊拓嵯峨、意味深厚的艺术作品。重庆古城墙除了人文景观外,其与山水交相辉映的选址走向,临崖傍水、古树枯藤,夕阳晚照下的沧桑古城,樵子渔夫漫步其上,本身亦是蔚为可观的园林景观。
重庆城墙是历史文化名城的核心构成要素。古城墙凝聚着巴渝先民的聪明智慧和忠勇精神,是巴渝文化的重要见证和城市文脉的重要载体;作为重庆人心中的乡愁,古城墙承载着历史的情感、记忆和辉煌,也见证着城市的过去与未来,具有不可替代的情感价值;面向未来的古城墙,也是重庆城市形象的文化符号、塑造城市个性的重要依托。
此外,《实施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操作指南》II.D77条,对文化遗产具有的突出的普遍价值,提出了六项标准。对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相关要求,重庆城墙至少符合其中(Ⅳ)、(Ⅵ)两项标准:
一是符合标准(Ⅳ):“是一种建筑、建筑整体、技术整体及景观的杰出范例,展现历史上一个(或几个)重要阶段。”重庆城墙集中展现了景色壮丽的山水城市和功能完备的军事要塞的独特景观。它的筑城思想和技术反映了中国古代南方沿江城市发展的一种重要阶段,“战、雄、险、奇、秀、幽、古”的特殊风貌,是城塞景观的一个杰出例证。特别是重庆城作为宋蒙战争山城防御体系的发源地和指挥中心,是川渝地区方山城堡防御建筑群的核心和典型代表,其背后“道法自然”的营建思想,强调山、水、城和谐共生的规划设计,无愧于山地城池防御建筑的杰出范例。
二是符合标准 (Ⅵ):“与具有突出的普遍意义的事件、活传统、观点、信仰、艺术作品或文学作品有直接或实质的联系。”重庆城在宋蒙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宋季三朝政要》载:“淳祐三年……刘晋之言:蜀当置阃重庆。彭大雅守重庆时,蜀已残破,大雅披荆棘,冒矢石,竟筑重庆城以御利、阆,蔽夔峡,为蜀之根柢。”当时的蒙古汗国军队三次西征,铁骑横扫中亚、西亚以及欧洲40多个国家,罗马教皇曾惊呼其为“上帝罚罪之鞭”。1259年,元宪宗蒙哥亲自督战于山城防御体系的重要节点钓鱼城下,久攻不克,撤退途中去世,由此引发了蒙古贵族内部集团的汗位争夺战,蒙古帝国由统一走向分裂,南宋得以喘息。此后,倾慕汉文化的忽必烈在灭亡南宋的过程中,一改蒙古传统的血洗屠城政策,保留了南宋先进的文化。同时,第三次西征大军止步于叙利亚、埃及,阿拉伯世界得以挽救,蒙古帝国的大规模扩张行动从此走向低潮。重庆城作为当时四川地区的军政中心,也是宋蒙战争西线战场的核心组成部分,是这一重要历史事件的重要参与者,直接见证了世界中古史的重大转折。
六、结语
重庆城墙作为巴渝文化的重要载体和城市形象的文化符号,具有鲜明的营造特征和重要的文化遗产价值。其“踞山围城,依江为壕”的规划布局、“城堤一体、随意赋形”的筑城理念、“夯土甃石,外高内低”的营造技术及“九宫八卦,开闭相间”的堪舆文化,是中国古代南方山水城市的杰出范例,是研究重庆城市空间沿革、中国古代城池演变及宋蒙(元)战争史的重要实物标本。
由于地处两江交汇的渝中半岛,重庆城墙的地标位置突出,作为重庆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支撑,具有重要的展示利用及旅游开发价值。城墙的展示利用设计,可围绕“英雄之城”与“战争之城”两大主题,结合周边重点遗址公园、历史风貌街区及山城步道系统进行统一打造,渐进式地复原城墙布局,择机成立重庆城墙遗址博物馆,促进城墙保护与现代城市和谐共生,以提高城市品位,增强城市凝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