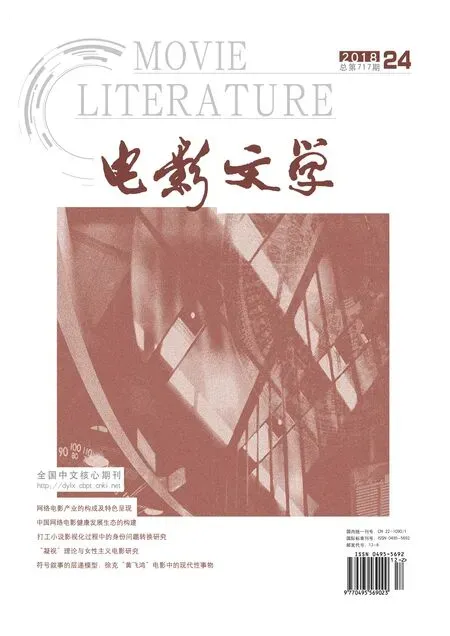符号叙事的层递模型:徐克“黄飞鸿”电影中的现代性事物
2018-12-10袁道武
袁道武
(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上海 200072)
20世纪90年代初,香港电影人以徐克为首将搁置了十年之久的“黄飞鸿”题材重新搬上了银幕,收到了良好的市场回报和评价,以致滥觞终成奔流形成了“黄飞鸿”电影可称蔚为壮观的观影风潮,其中徐克作为主创制作的“黄飞鸿”系列电影因其突出的电影形式风格和深刻的家国情怀而尤其出彩,从具体的层面来分析徐克系列电影的与众不同之处,大概其中“西方的带有洋派色彩的事物”便是最明显的表征。
“洋派”所指涉的当然为现代性这个范畴,作为学术意义上的现代性这个哲学概念来自18世纪的西方,它涵盖的意义非常纷繁,对现代性的研究成果也非常博大,但正因为其覆盖范围是如此之广甚至模糊了具体的边界,至今还没有一个统一具体的学术界定。然而,将“事物”这个微观具体的坐标放置在现代性这个宏大的场域系考察时,这个范围就一下收紧而具有清晰的参照维度——现代性事物。
有关现代性事物,目前国内还缺乏相关研究,徐敏的论文集《现代性事物》是唯一直接研究现代性事物的著述,作者选取“现代影像”“移动机器”“城市经验”“消费文化”四个角度将现代性事物归述为中国的现代性进程中出现的有标志性的现代性符号。本文认为徐克版“黄飞鸿”电影中现代性事物应为近代中国在逐渐被世界列强强行推入现代化进程中那些具有文明交流和冲撞意味的标志性符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将徐克版“黄飞鸿”电影中具有明显的现代性色彩的事物作为研究对象是可以成立的。需要说明的是,由于“黄飞鸿”电影作为一种“社会镜像的反映”本身就是现代化进程(20世纪90年代同时也是香港历史文化语境特殊的阶段)的结果,而不是在近代中国向现代化转换的见证,所以需要指明的是,对“黄飞鸿”系列电影中“现代性事物”的分析是实证的而不是规范的,是针对电影文本的而不是历史在场的,探究的是电影作品中的现代性事物呈现意义的方式和路径而不是现代性事物存在本身的书写。再者,“符号可以分为话语的和非话语的,其中话语符号是指通过字词或者书面语言传达意义的符号”,因此笔者以为,现代性事物虽然属于物质文化的范畴,但本文研究的“黄飞鸿”电影的现代性事物属于文本中的文本,电影叙事的历史所指,透过文本的意识形态在场,我们需要对其中的现代性事物统计的口径进行符合电影文本分析的界定,某些虽然不具备物质属性但符合上述现代性事物指向的人事,比如电影中反复出现的“报纸”“传教士”等,也一并作为符号纳入现代性事物范畴中。
一、“黄飞鸿”电影现代性事物的分类
所谓符号学,一般的学者观点认为,“符号学是关于记号、记号过程或记号系统的理论研究”,影视作品被指称为文本即是符号学的典型影响,符号学视文本为一系列符号的集成,但需要指出的是,符号学重视文本中符号的建构过程大于意义的评判以及作为系统的符号如何生成意义,因此对蔚为可观的符号进行体系分类是进行符号意义建构的前提。
目前比较受认可的符号学分类主要来自罗兰·巴特1970年发表在《电影手册》上的《第三层意义》。文中巴特将电影符号的类型推向后结构主义,分为:信息层、象征层、意指过程层。
(一)信息层符号
信息层符号是一种认知层次,它包括电影中的布景、服装、人物,并不是这些符号不再可能成为象征层或者意指过程层,而是它们作为信息展现的符号时,属于第一层次。“黄飞鸿”电影中的信息层现代性事物大体上有箱包(6)、洋酒(5)、雪茄(4)、肥皂(1)、蛋糕(1)、电话(1)、广告(1)、戒指(1)、玫瑰(1)和熨斗(1)。这些信息层符号的现代性事物,因为其主要的表征功能在于展现而不是表意,所以成了影片叙事的一种辅助性信息,但是由于同一种现代性事物可以出现在不同场戏中,具体的戏剧情境的不同使得现代性事物承担的符号功能也会不同,这些信息层符号也会兼具有象征功能,但这种表意是否将现代性事物的符号层次递进至象征层,主要取决于影片的具体情境。
(二)象征层符号
象征层符号在第一层信息展现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符号的象征指涉,精神分析、女权主义、意识形态等都可以视为象征层符号的表征,象征层符号是通过文化的权力的意识形态的规则联系在一起的。与信息层不同的是,这些现代性事物开始融入具体的故事情境,巴特将这种类型的符号所指呈现方式为“显义”,象征层符号将会以一种形式技巧,一种明显的侧重功能认知的指涉方式成为意义建构的方式,这将会在下一章论述。从第一部《黄飞鸿》(1991)到这个系列的最后一部《黄飞鸿之西域雄狮》(1997),徐克版“黄飞鸿”电影中象征层现代性事物在三种符号层面出现最多,大体上有照相机和摄影机(3)、轮船(2)、蒸汽机(2)、火车(5)、汽车(2)、报纸(4)、电报(1)、管弦乐器(4)、留声机(2)、枪炮(7)、望远镜(2)、西餐具(4)、西服(4)等。
(三)意指过程层符号
意指过程层符号则是在以象征层的表征为前提的基础上,对充满着晦义的符号的所指进行的一种“症候式解读”,是对那些无法具体阐明含义甚至不知其指向性的符号进行的增添的意指过程,巴特称之为“晦义”,意指过程层如同数学意义上的“零向量”,它没有具体的可分辨的方向却指向一切方向。因为意义的晦涩和扩散带来的不确定性,笔者所列意指过程层符号的现代性事物也是一家之言,它们是:钟表(4)、电灯(5)、地球仪(1)、宗教和传教士(4)。
二、图像志:“黄飞鸿”电影中现代性事物的符号叙事化
当我们将“黄飞鸿”电影中的现代性事物进行符号分类后,一个紧接着的问题是,如何就这样的符号分类进行合理的解释?我们将用何种方法对这个系列电影中反复呈现的现代性事物的某种意象和意义进行解释?对此,托马斯·沙茨关于图像志的理论提供了一个参考:“图像志包含了由一个流行故事的不断重复而产生的叙事和视觉编码的过程,这个编码的过程发生在所有电影中,因为电影故事讲述的本质就是故事发展时把它指派给‘空的图像(bare images)’。”对此的一个通俗的解释是,“图像志(iconography)是把艺术作品中的形象、主题和题材加以鉴定、描述、分类和解释的学科,它不同于对艺术品进行整体考察的图像学(iconology),但两者之间有很深的联系”。本文即采取这种图像志的研究方法,同时因为行文所限,仅选取三种符号层次中具有代表性的现代性事物进行图像志叙事解读。叙事化这个概念则“主要关注的是把展示转化为讲述的过程,把电影集结的大量漫无目的的现实主义转化成朝向一定的叙事目的……叙事化在电影的符号表达里规范着影像现实和叙事功能之间的平衡”。
(一)信息层符号现代性事物叙事化
在属于信息层符号的现代性事物中,出现最多的依次是箱包、洋酒和雪茄,信息层符号的特征是能指和所指基本上是同一重合的,大部分信息层现代性事物并不具备表意功能,而是成为能指和所指同一的,雪茄的出现基本上属于人物设定的需要,无关指涉,即在电影中光影所构成的形状(能指)和摄影机记录下来的那个真实空间中的物体(所指)是一致的,实际上这也是大部分画面中事物的符号层次。需要说明的是,在本系列电影中,箱包和洋酒大量出现不是没有特殊的况味的,它们在电影中首先作为信息层现代性事物出现(事实上也更多地承担如此的功能),但最终,在某些场景中,这些现代性事物的所指开始脱离能指的范畴,具备象征层符号的所指功能。以洋酒为例,在《黄飞鸿之龙城歼霸》中,黄飞鸿与众徒进入海盗船只,看到海盗畅饮啤酒不禁好奇品尝,结果除了在美国生活过的华工后裔牙擦苏以外,无不吐出,而在《黄飞鸿之男儿当自强》中,清廷高级官僚在参加英殖民者的舞会时,则非常自如地品饮红酒,舞会中甚至出现了清廷官员和英国使馆人员共舞的场景,遑论他们不合场所的清朝官服,应该说这样的现代性事物其实已经指涉了早期西学东渐中对西方文化的无所适从到开始“师夷长技”的转变。
(二)象征层符号现代性事物符号叙事化
在徐克“黄飞鸿”电影中,象征层的现代性事物出现的频率是最多的,具有代表性的有照相机和摄影机、蒸汽机、火车、轮船,这些西方工业文明孕育的最具有代表性的产物。照相机是伴随着十三姨第一次出场而出现的,在这个系列第一部电影中十三姨的第一次出现所携带的文化符码,作为一个从西方留洋回来的外来文明的积极提倡者,十三姨成为整个故事序列一个极其重要的人物,她是承担着将西方文明反哺给渴望中国富强的黄飞鸿们(同时也是一个已经被世界甩在身后的文明顽固的提倡者)的媒介。不可避免的,照相机被本土的蒙昧代表群众当作“摄魂器”而避之不及,落后保守完全排斥西方文明的代表“白莲教”指斥为“西洋妖术”。
关于蒸汽机作为工业革命发端以及它对进入工业时代国家的重要意义无须赘述。李泽厚认为,“现代化的基本观念、思想,特别是物质方面的因素、基础,如近代的生产工具、科学技术以及生产关系、经营管理都来自西方,是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学习得来的”。我们认为,现代交通工具正是以符号的方式,成为表现这一大时代社会巨变的重要影像三棱镜。可以说,“现代交通工具是我们理解现代中国电影及现代社会历史进程的关键之所在”。
在《黄飞鸿之狮王争霸》中,故事背景被置于洋务运动时期的北京,而黄飞鸿的父亲黄麒英则非常突兀地成了兴办实业的民族企业家,十三姨为黄飞鸿一众乡绅代表讲解现代西方工业文明的核心驱动源——“西洋瓦特机”的功能,俨然是黄飞鸿开始接纳西方工业文明的启蒙导师。值得一提的是,在由刘家良执导,成龙主演,几乎同时出品的《醉拳II》(1994)中,工厂里的蒸汽机成了资本剥削工人的血证,暴动的人们砸毁了这奴役着他们的机器,这种带有马克思工人阶级暴动学说影子的情节其象征符号叙事化的所指是不同的。而其实,在徐克系列的第一部《黄飞鸿》(1991)电影中,蒸汽机就已经成为一个主要的叙事象征符号了,开场的镜头从中国酒楼茶馆嘈杂的人群拉出,扫过街头的商贩、流民,被衙役押解的囚犯,居住中国的外籍人士、殖民者的巡警和高声布道的外国传教士……酒楼的中国茶客和传教士互相试图“遮盖”对方“话语权”的争执中,码头停岸的蒸汽渡轮一声汽笛轰鸣,双方都被这巨大的声响所怔住,中西文明碰撞中多元的异质的甚至是体用之争的嘈杂,都将毫无疑问地被这工业文明的强势淹没。
火车在《男儿当自强》《狮王争霸》《龙城歼霸》都出现过,甚至在《男儿当自强》中以片头序幕多角度多景别的形式出现。“领土、交通与速度,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空间的三大支柱性构成要素”,火车作为依托于蒸汽动力所诞生的现代交通工具,“是电影所反映的时代与社会背景的一种象征”,“是现代性空间及其社会形态的核心代表”,火车内部就是一个社会标本,它有自己明确的轨迹和目的地,它不可阻挡,俨然是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的具象,它的出现是“黄飞鸿”电影的故事背景——处于急速剧变的中国往何处走这种迷茫和疑问的一个答案——工业化铺就的轨道。
(三)意指过程层符号现代性事物符号叙事化
意指过程层现代性事物出现的次数是三者中最少的,这和意指过程层符号的属性有关,这里以钟表这一时间的物象为分析对象。钟表在《黄飞鸿之男儿当自强》中以重要的故事元素多次出现,在这部“黄飞鸿”电影中,编导从一开始就试图将影片的语境设置在更广阔宏大的历史背景中去,家国历史中的孙中山和民间传说中的黄飞鸿在虚构的情境中相遇,一个救国图存的革命者先行者将影片的历史诉说带到了新的高度,而“黄飞鸿”系列电影中,钟表(包括怀表)出现次数最多的就是《男儿当自强》。影片中孙中山时时刻刻都将怀表带在身上,孙中山告诉黄飞鸿“中国现在最要紧的是抓紧时间”,值得玩味的是,一向排斥西方枪炮推崇中国功夫的黄飞鸿在听闻孙中山这句话后因不能通过怀表认识“时间”而羞愧不已。这不能不联想到胡风那首著名的长诗《时间开始了》,他们的指涉是如此的相同,真正的时间开始了,之前的都是无效的时间,这是“第三种时间”,黄飞鸿收到孙中山赠予的怀表和胡风宣布的时间,这是一个现代意义的时间,这样的时间里包罗了一种革命性,这种革命性所隐含的逻辑,是与资本主义同时产生的一种主义,这就是现代主义。影片中的怀表作为意指过程层符号指向一点:中国的现代化是一个迫切需要被提上日程的议题,而现代性的内容又是如此纷繁复杂,它是民族觉醒的一个重要注解,时间遭遇现代化这个节点,它所引发的合理想象和意义拓扑,便是扩散到另一个数量级的层面了。
综上,在意指过程层符号这里,符号的所指经过“零向量”式的扩散,在语义上意指过程层符号打开了意义的场域,它已经超越了已有的功能认知从而走向了意义的无限扩散和无限扩散的意义。
三、层递模型:作为符号的现代性事物意义的生成路径
“黄飞鸿”电影中的现代性事物作为符号,应该说本身并不具有某种内在的必然逻辑,即对它的研究是“时间在后”的而非一种先验性的总结。对这些现代性事物的分类,严格意义上说,是根据这个系列电影中这些现代性事物出现的方式和特征,找到可以用理论归纳其分布及构成的意义。根据上文的分析,这些现代性事物出现的符号层次及其隐藏的表征(所指和能指)关系是有一种递进的逻辑关联的,简言之就是前一符号层的现代性事物总是可以在某种情形下进入后一符号层次,以此递进。我们试图理清这些现代性事物作为符号系统的内在关联机制和它们生成意义的某种路径,即:

表1 现代性事物符号层递模型
在上述的后结构主义——符号学分类视域下,“黄飞鸿”电影中的现代性事物的符号表意过程可以归纳为一种层递模型。在信息层符号中,诸如雪茄、箱包、肥皂等,在影片中的所指和能指是统一的,此时A2类似于A1。
至于象征层符号中的现代性事物,诸如轮船、汽车、蒸汽机等,这些现代性事物的能指则是信息层现代性事物能指和所指的结合,亦即影像中的能指(A1)和现实中的所指(A2)共同构成了这类事物的能指(B1),再和编导设计的语境产生化学反应。这个现代性事物本身并没有象征功能,作为自然物它的象征意义来自“自然物被用在抽象的思想中加以运用的概念范畴,然后被当成对自然与文化经验加以理解和综合的、知觉的和分析的框架”,比如在《黄飞鸿之王者之风》中,东交民巷遭遇红灯照组织的火攻,黄飞鸿看到火灾后立即赶赴现场救人,在其准备带上一贯的防身武器——伞——的时候,导演安排了一个值得把玩的细节,即黄飞鸿先将一把油布伞拿起,随即又立即放开,拿走旁边的一把洋伞,此时它的表意重心从象征层的能指(B1)转向所指(B2)。
除了有关怀表的现代性时间外,现代性事物表意方式如何从象征层符号进入意指过程层可以从蒸汽轮船进行分析,相对于火车的线性历史想象,轮船则更加带有不同文明和话语的交互融合的意味在其中。轮船在《黄飞鸿》《男儿当自强》和《龙城歼霸》都有出现,而在《黄飞鸿》中则是开场就出现在清朝水军和外国列强船队的对峙中,具有特别的象征意义,是外域他者文明的强行停泊和震慑,而在《男儿当自强》中,轮船是最后出现在孙中山码头等黄飞鸿、陆皓东送来名册时,当孙得知陆的死讯,展开“青天白日旗”时,蒸汽轮船便脱离了作为交通工具的存在的所指(A2),成为一种隐喻叙事的符码(B2),作为一种现代文明的载体,它是国家出路的一种想象,承担着革命志士救亡图存的理想和诉求,从而将其在象征层符号的所指意义转向无限的意志层面(C2)。
四、结 语
综合全文的分析,可以认为,20世纪90年代徐克系列的“黄飞鸿”电影,之所以能赢得口碑和票房的胜利,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是只要我们考虑到其在“黄飞鸿”电影序列中不一样的美学追求,就可以发现,现代性事物的确是其中非常明显的不同之处,有了这些现代性事物符号,电影的叙事情节和意义表达都显示出了不一样的意味。“现代性事物”的引入并且着重将之纳入叙事系统,在一个结构主义符号的体系中,那些从影像故事的皮肤肌理深处散透出的创作思想和人物形象,已经很好地达成了与电影的统一,也完成了故事的叙事和观众的认同,“它们本身有强烈的再现功能,但又同时在超越着它们自身的再现功能,不仅仅表达为观念、符号与规则体系,不只是与社会形成镜像化的反映、表现或意义刺激的关系,还能以互动的和再生产的方式构建着各种全新的社会形态”,所有这些都说明了影视图像可以记录一些具有象征性的东西来呈现给观众,用卡林·塞的娜的话“现代性事物都被写入了文本性”来描述再合适不过了。
列维·斯特劳斯认为,“符号永远不是单纯的,它是物质与形式的结合,结构与结构的部分的结合,具体实物与抽象概念的结合,符号和形象组成的、凝缩着和聚合着的事物……把符号加以区分并将其纳入一种形式代码中去,这种代码可以吸收任何一种内容,而且它同时可涉及事件与结构,自然与文化,美学对象与逻辑对象”。
当我们回过身来观照“黄飞鸿”系列电影时,就能明白以上理论家所言的意义,此系列电影中的现代性事物就其本身来看,很难说其负载了文化研究和意识形态的表达,但当这些现代性事物作为符号出现在电影人物黄飞鸿所处的现代化初期的视域中时,一个具体的语境下的意义便生成了。考察这种符号的序列的归码和意义的表征也许很难从大的层面和艺术创作上体现前瞻性的意义,但我们现在的影视创作和学理分析不正是愈发流于空洞和宽泛,而缺少一种在影像的肌理下那些血液深处的毛细血管式的探究吗?将“宏大理论”结合“中观层面”的研究路径,正是笔者试图在本文中所要尝试的,至于这两种思路,何者为“体”何者为“用”,则是另一个有待深入的命题了。
注释:
① 括号中数字表示出现该现代性事物的电影数量,比如“箱包”在6部电影中出现,下同。
② [C1,+∞)为数学区间符号,表达意思为从C1到无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