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阴影与历史幽灵
2018-12-08法人王立刚
文 《法人》特约撰稿 王立刚
巴尔干地区的历史基本上是各国之间打成死结的各种梁子。久负盛名的地缘学家、美国著名的新闻记者罗伯特·卡普兰新作《巴尔干两千年》一书被认为是巴尔干问题的经典之作,揭开了巴尔干的“欧洲火药桶”的秘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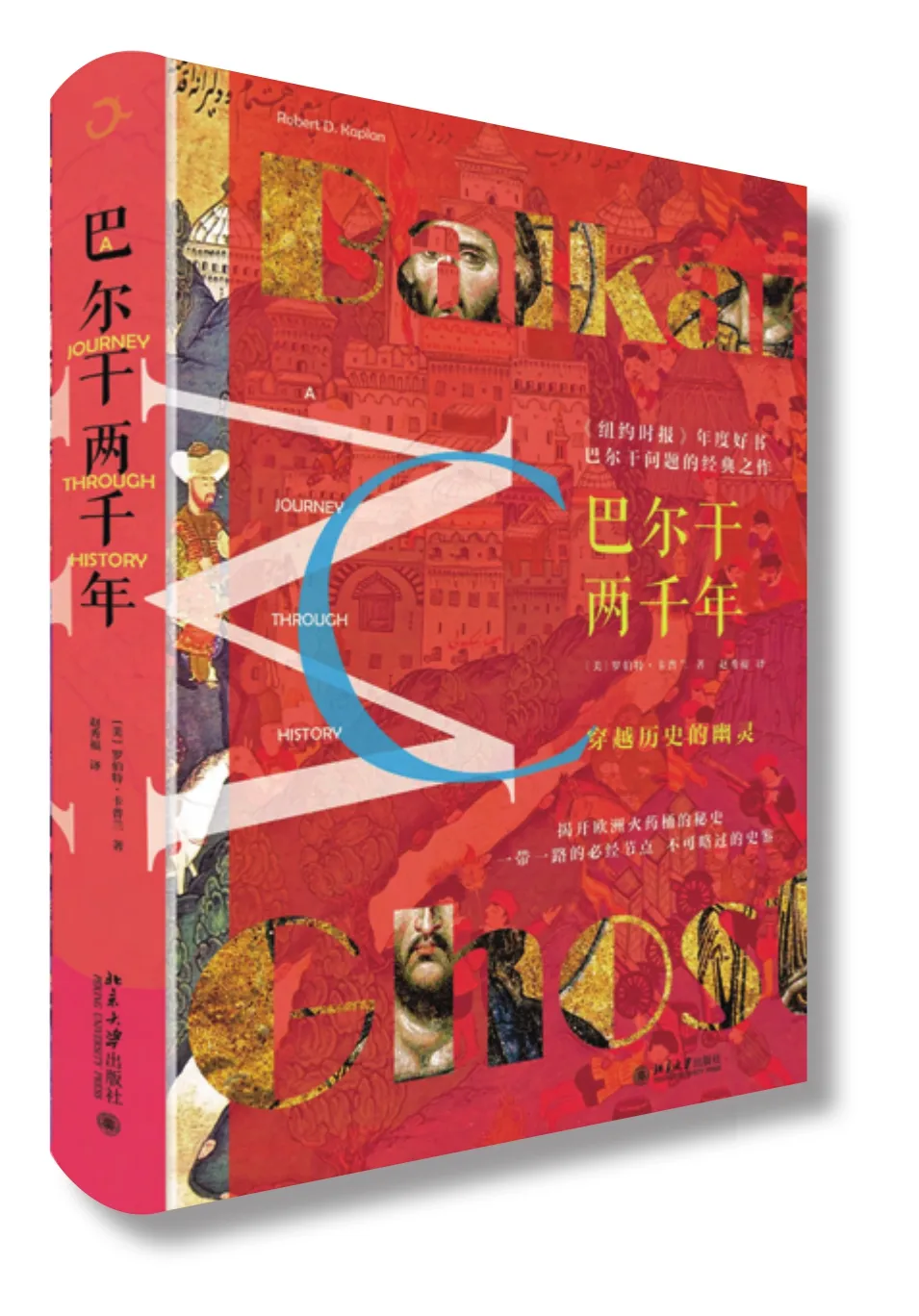
戴蒙德的《枪炮,病菌和钢铁》里提到了“安娜·卡列尼娜原则”,幸福的国家都是一样的,不幸的国家各有各的不幸。因为幸福的国家大多会把给定条件中好的方面发挥到极致,而不幸的国家则相反。《巴尔干两千年》里的巴尔干各国可以说是这一原则的生动注脚。千年来外来征服、君主制、战争、仇杀、民族矛盾、宗教派别等等,都在这里展现出阴暗的一面,这些因素有着不同的排列组合,造成这些国家“各有各的不幸”。
无法挽救的种族教派裂痕
美国著名的新闻记者罗伯特·卡普兰,可称得上是一位眼光犀利的地缘学家,在东欧、中东、中亚、南亚、非洲等诸多地方有过极为丰富的报道经历,《巴尔干两千年》一书因为准确预言了高压统治结束后必将爆发残酷的民族内战,而在波黑战争期间得到重视,据说克林顿曾经多次阅读该书,为其制定巴尔干对策提供参考。之后卡普兰在《地理的复仇》一书中凭借其地缘知识对全世界主要国家的未来进行了预测。军方聘请他进入国防政策委员会(Defense Policy Board),可算得上是最高阶的学以致用。
卡普兰在《巴》一书中呈现的是令人震撼的口述史,作为记者他有着一般学者难以企及的文笔和观察能力,在和形形色色的巴尔干各国人的交谈中,勾画出历史是如何在这里塑造人的心灵的,他所交流的每个人都是各国独特历史的产物,如此鲜活。虽然当时东欧的铁幕瓦解的进程才刚刚开始,书中描绘的基调是灰暗压抑的,但每个人内心中对美好生活的渴望是如此强烈明晰,正如默默蓄积的热油,只需要一点火星,就成了熊熊之火。
当然就像卡普兰事先观察到的,这里国与国、民族与民族、教派与教派之间的裂痕是如此之深,即便铁幕崩塌,立刻到来的不会是全新的完美世界,恰相反,在各族群领袖、世界大国、人民还没做好充分心理准备迎接高压统治崩溃之后的局面时,历史上的伤口稍微被撕开一点,立刻就会喷涌出鲜血和深仇大恨。在这里,历史的幽灵从来没有走远,只是在等待附体的 。
各个国家虽然都有着不幸的历史,但国情不同,其悲剧有着各自的“丰富性”,卡普兰善于抓住这些差异,并且用最生动的人展示出来。
前南地区两大族群的世仇
前南地区是20世纪的热点。南斯拉夫国内的两大族群,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一直矛盾不断。虽然两者其实都是斯拉夫人,语言也一样,但前者信天主教,认同的是西方,以曾经是哈布斯堡帝国和奥匈帝国的一部分而自豪,他们看不起“东方的”塞尔维亚人,因为塞人信仰东正教,先是被东罗马统治,后来又被土耳其征服,从骨子里已经被东方的君主专制腐蚀了。
由于文化认同上的差异,克族和塞族历史上就不和睦。一战期间,克罗地亚因为是奥匈帝国的一部分,所以加入了同盟国,而塞尔维亚则加入了协约国。同盟国战败,克罗地亚被合并进了塞尔维亚;二战期间,克罗地亚为了摆脱塞尔维亚独立,加入了法西斯轴心国阵营,再次跟塞尔维亚成为敌人。然而这次又站错了队,之后克罗地亚成了塞尔维亚占主体的南斯拉夫的一部分。在铁托的高压统治之下,看上去这个国家各族相安无事,但内心深处的怨恨并不需要深挖就能看见。近半个世纪后来到萨格勒布的卡普兰能够感受到这种扑面而来的情绪。詹森诺瓦惨案是克族和塞族心头的死结。二战期间,克族的法西斯组织乌斯塔沙在詹森诺瓦杀死了大量塞族人,拉开了现代“种族灭绝”的血幕。几十年来,两个族群一直在为屠杀的人数而争执不休。塞族,包括南斯拉夫官方都认为,大屠杀中死亡的塞族人有70万。卡普兰在拜访克族教会的大人物考克萨时,考克萨说,“我们不能对所有的事情都予以否认。在詹森诺瓦发生的事情是悲惨的;也许是6万人被杀,或许略多一点,但肯定不是70万人。”而当地的犹太社区领袖葛德斯坦金则和他争论过,在詹森诺瓦,犹太人被杀了2万,吉普赛人3万,而被杀的塞族人远比犹太人、吉普赛人多。
在这里,数字不仅仅用来衡量血腥和仇恨的深度,同时也和对很多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价相关。比方说对于克族的精神领袖斯蒂匹纳茨。对于这位活跃在20世纪上半叶的克族红衣主教,克族人和塞族人(包括南斯拉夫政府),评价截然相反。1984年卡普兰首次拜谒斯蒂匹纳茨的墓地时,一位年长的女人靠近并恳求说:“说他的好话吧。他是我们的英雄,不是战争罪犯。”但是,政府里的一位官员在贝尔格莱德告诉我说:“我们的判断是确定的:斯蒂匹纳茨是一个内奸屠夫——名义上是神父,一只手为人们洗礼,另一只手却用来杀戮。”这位官员接着告诉我,天主教的神父们如何在斯蒂匹纳茨的指挥下,在克罗地亚的恐怖分子要处决东正教的塞尔维亚人之前的几分钟,主持宗教仪式对他们进行强迫性的集体皈依,“于是他们就可以上天堂”。
罗马尼亚地区的民族和文化分裂
同样,宗教引发的民族问题还出现在塞尔维亚的科索沃。在那里信仰伊斯兰教的阿尔巴尼亚人一直想独立,或者和阿尔巴尼亚合并。当地的塞族和阿族关系非常紧张,只是由于铁托的高压作用引而不发,但国家一解体,这里果然就被引爆了。
与前南地区被宗教纷争引爆的成片的政治地雷不同,东边的罗马尼亚则陷入到民族和地区间的文化分裂之中。卡普兰还专门写过一本关于罗马尼亚的著作,《欧洲的阴影:两次冷战和三十年罗马尼亚之行》,可见他对这一地区的熟悉程度。当地一个谚语说,“罗马尼亚农民就像是玉米粥,你尽管加热,他们不会爆炸”。
罗马尼亚的另一个不幸是民族矛盾。
首先是犹太人。这里成为犹太人二战期间除了德国以外最大的地狱。1941年和1942年,在安东内斯库的监督下,185000名犹太人被罗马尼亚军队送到洲唯一的非德国人控制的种族灭绝营。
比犹太人稍幸运,但对政治却影响更大的是另外两个族裔。特兰西瓦尼亚地区的200多万匈牙利人有着巨大心理和文化优越感。
除了匈牙利人,还有哈默林地区的德意志人,他们自认为是萨克森地区的德国后裔。这个德裔社群被认为是法西斯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的、非罗马尼亚人的社群,数量高达数百万的萨克森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成为罗马尼亚政权的首要牺牲品。
保加利亚人心中的幽灵是他们对苏联的纠结情感和领土问题。俄国和苏联在历史上侵略过保加利亚,但也帮助保加利亚抗击过土耳其,在华约里,苏联对保加利亚也是最“善意的”,在这里没有苏联驻军。但保加利亚人也明显感受到,这种善意是“他人身体的温暖”,是一种严格受控的政治福利。
保加利亚人更在意的事情是领土。卡普兰说,巴尔干各国似乎都怀念其历史上最大的疆域,并以此来要求领土。保加利亚曾经在土耳其到来之前建立过一个“庞大的帝国”,巴尔干各族摆脱土耳其独立之后,保加利亚试图拿回自己的领土,为此先后进行了两次巴尔干战争,但越打越小,保加利亚不但失去了马其顿,还失去了色雷斯,失去了爱琴海的入海口。
巴尔干最南端的希腊也曾经为了领土和土耳其大打出手。但对于希腊人来说最大的不幸,在卡普兰看来是其内在心智的转化,这里已经不是苏格拉底、欧几里得、梭罗的希腊,那个奠定欧洲科学和民主基础的圣地。
巴尔干地处三大洲之间,其地缘位置非常重要。但以往的历史开发的都是这一要素的负面功能,这里成了几大宗教、几大帝国爪牙重叠撕扯的地方。造成的不幸如同不散的幽灵,至今仍盘踞在这里。
卡普兰对巴尔干难题给出的对策是“解铃还须系铃人”:既然以前大国为了私利造成了不幸,那么今后也只有大国本着公心加强介入才能解决问题。这当然基于他本人的西方价值中心主义。今天,事情似乎有了别的选择,那就是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已经开始给这块欧洲的“第三世界”带来转机。经济的繁荣和交流的加强最终很可能会有助于解开各国之间的死结,巴尔干的幽灵最终将失去蛊惑的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