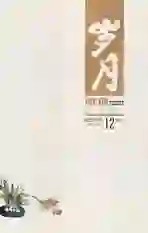等风吹来
2018-12-07红孩
红孩

从北京的东三环到东五环,直线距离最近也就四五里地,可是从我居住的西坝河要到双桥的于家围就得二三十里,虽然一个在三环里,一个在五环外。过去,这西坝河一带,也属于农村,归太阳宫乡管辖。我印象中,这里不种小麦、水稻和玉米,专门给城里种各种蔬菜。中国人很会发明词汇,比如农民就又可划分为菜农、果农、烟农、茶农、粮农。我从小居住的于家围,现在属于豆各庄乡管辖。豆各庄,听起来很土的一个地名,即使这样,还分南豆各庄北豆各庄,想必豆字开头要比张王李赵好听一点。其实,稍微熟悉这一带历史的人都知道,北京的东南郊,在明清时期,基本上都是城里人家的坟地。于家围过去叫于老公坟,周围的村庄还有什么何家坟、孟家坟、英家坟等等。几年前,作家叶广芩根据儿时的记忆,写了中篇小说《太阳宫》,引起了太阳宫乡政府领导的关注,四下里托人寻找叶广芩,最后找到我。我和叶广芩很熟悉,便打电话给他们牵线,终于在一个炎炎夏日于太阳宫乡政府见面。乡长说,太阳宫过去叫太阳庙,可惜“文革”时给拆了。现在,老百姓要求重建的呼声很高,希望叶老师能够参与其中。我和叶老师听罢,频频点头,表示只要政府找到钱了,我们愿意出些主意。
双休日,我回于家围。这已经是我多年的习惯,只要不出差,我就回父母家。此时,父亲已于几年前去世了,母亲一个人独自撑着大院子。院子里种植着石榴、柿子树,当然还有蟹爪莲、夹竹桃、月季和茉莉花。父亲过去在村里当支书,大约当了有三十年,属于老干部,我和妹妹、母亲,当然属于干部家属了。在农村,家里有当干部的,在诸多方面都很方便。譬如,家里来个亲戚朋友找我父亲,我只要到房后的村办公室对着传达室喊一声“广播一下,说书记家来人啦”,一会儿那广播喇叭就会连续喊上三五遍。再譬如,我每天中午都可以看到《北京日报》《法制日报》,包括我的各种信件,不管刮风下雨,传达室的本家瘸二哥都会准时送到家里。最让我享受的,引以为自豪的,就是每天晚饭后,父亲都要在大喇叭上就一天的工作进行总结。他说话没有什么逻辑性,说起来啰嗦没完,一说就一个多小时,也不知道村民认真没认真听。用当下的时髦词形容,他那是在刷存在感。后来父亲去世了,我们家就像破落王孙,再也没有往日的优越感。有一次,我家的电灯不亮了,母亲让村里的街坊跟电工打个招呼,结果等了一天电工都没来。晚上,我亲自到电工家找他,他懒洋洋地把一碗热粥喝干净才不情愿地跟我回家。要是在过去,我只需在他家门口喊他一嗓子,他就会放下任何事情马不停蹄地到我家。过去,我体会不到什么叫世态炎凉,什么叫人走茶凉,现在终于明白了。
我对母亲说,太阳宫乡政府要重建太阳庙了。母亲说,修坟建庙,这可是积德行善的好事。你还记得小时候咱们村西的大庙吗?我说记得,当然记得。我上小学一二年级就在那庙里。那庙是土地庙,前后两个宅院。前院有一棵千年古槐,由于年代太久了,树中间形成一个巨大的空洞,里边能坐下三四个学生。唐山地震那年,这棵树倒了,从树洞里爬出几十条草蛇,很是吓人的。从那以后,学生们就再也不敢再到大庙里上课了。母亲回忆道:我刚嫁到于家围的时候,你父亲在大庙旁开一家小卖部,那时叫合作社,虽然卖的东西不多,也就是简单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可乡亲们买着方便。我说,爸是个老实人,他不会作假,比如往酱油、醋缸里兑水;他人脸又热,谁要是没带钱,常在柜台上赊账,时间长了,小店连进货的钱都没有了。母亲说,谁说不是呢,那个年月,家家都穷得叮当响哩。
我喜欢一个人在上房最西侧的那间房里写作。八十年代,家里翻盖了新房,由村中搬到东南,门口有一个大大的鱼塘,写累了,我就到鱼塘的坝上遛弯儿。在这间房里,我的作品源源不断发表,最终让我走上专业写作的道路。我离开农场前,正赶上下海经商热。我们双桥农场,下辖5个乡政府,包括我曾经担任过4年团委书记的豆各庄乡。记得我要注册的公司叫北京八达广告公司,跑手续用了二十几天,还花了三千块钱验资费,眼看执照就要批下来了,这时北京市总工会的《北京工人报》创刊了。报社的领导是我的老朋友,希望我能代表农垦系统进入报社,做专职记者。听到这个消息,我的惊喜是无法想象的。要知道,进报社,对于一个长期在基层从事业余创作的普通人来说,那简直是梦幻。我找到农场场长,告诉他我不想开公司了,我要到报社当记者。我甚至说,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补交三千块验资费。场长一听笑了,说你到报社,是好事,是咱农场的光荣。不要说出三千块钱,就是三万也值得啊!不过你要记住,农场永远是你的家,你随时可以回来。场长的话让我很感动,在以后,我先后又调动了五六家单位,再也没有遇到农场场长那样境界的领导了。我是含着眼泪离开农场的。那里有着我的青春岁月,也埋葬着我的亲人。
印象中,我在房间里正在写小说《青春的答卷》。这个小说,我从18岁就开始写,写了好几次都半途而废。我不是缺少生活,而是缺少对生活的提炼。尤其是坐在电脑前,有时头是懵的,怎么也找不到进入的节奏。于是,就坐在桌子前面发呆。这时,母亲往往就会说,出来待会吧,老在屋里写,能把人写傻的。对于我的写作,写什么,母亲是理解不了的。她和村里的许多人一样,对写作这行业是拒绝的。在当地人眼里,写作的还不如做小买卖的,更不要说当个场长、乡长什么的。这让我想起,在1990年夏天吧,那时我还在农场搞工会工作,在《农民日报》举办的一次文学作品征文中,我得了个小奖。颁奖那天,我心中仰慕已久的作家浩然老师来了。还有一位,是著名作家刘震云。那时的刘震云因写出了《塔铺》和《新兵连》正红得发紫。刘震云的身份是《农民日报》记者,我很羡慕他。午间一起吃饭,刘震云不善言辞,倒是浩然老师谈笑自如。当有人问到刘震云出名以后有什么感觉时,他的一席话让大家哭笑不得。刘震云说,他从北大毕业分到《农民日报》,村里的人很不屑,认为这北大白上了。村里人问刘震云,在报社都干什么,刘震云说就是编辑稿件,写写文章。村里人说,写那玩意儿有什么用,不如到农业部帮助批几车化肥,弄几吨盘條。刘震云实话告诉乡亲们,他没那个本事。
我和刘震云有同样的处境。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我双休日照常回家。进门,看父亲闷闷不乐。我问他怎么回事,父亲说,乡里的党委书记找他谈话,说他年龄大了,观念陈旧,跟不上形势,决定让他退居二线。我知道父亲距退休还有几年,他是不舍得那个官位。一个当了几十年村支书的人,冷不丁地让他退下来,他还真忍受不了,关键是有几个比他年龄大的村干部也还没有退下来,这让父亲很不平衡。我问父亲,你哪里得罪领导了?父亲说,党委书记和村长到洗浴中心一晚上消费六千多,他们拿发票让我签字,我说一个农民撅屁股干一年活都挣不了六千块钱,这票我不能签。父亲天生胆小,让他干伤天害理的事,他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出的。我和这个党委书记在农场曾经共过事,他的北京市劳动模范的参评材料还是我帮助起草的。我不想找他为父亲说情,只给他写了一封短信,告诉他做事要小心,不要以为有点权力就可以任性,那样最终只会害了自己。
也许,在父亲的眼里,他的儿子还不能保护他。同样,我的同学也觉得我没什么用。我有个初中同学,上学时跟我关系很好,毕业后多年没联系。某日,在地铁站相遇。他问我做什么呢?我说在报社当记者。他又问我,平常都跟什么人打交道?我说,主要跟作家、记者打交道。或许由于我说话语速快了一些,他听成了跟做家具的打交道。他便跟了句,你问问谁有刨花板?我听后先是一愣,然后告诉他,我认识的人不卖刨花板、三合板,他们像我一样,只会写写文章。同学看着我,感到很失望。我们只好就初中的几个能记起的同学聊了几句。临分手,同学突然想起了什么,问我跟他们那个乡的乡长是否认识。我说,过去在农场工作时,见过几面,没有什么深交。同学说,他们家马上面临拆迁,如果我要能和他们乡长说得上话就好了,起码能给多算点赔偿款。我说,这很难,我自己家的亲戚拆迁也不曾找过任何领导。同学说,你书读多了,要知道,这是个人情社会,你平常不和人家走动,人家怎么会主动联系你呢?同学的话,让我很吃惊。想想也是,我在农场工作六年,几乎所有大小官员都认识,可这几十年来,我找过他们办过一件事吗?或许,在世俗的眼里,我这叫资源浪费,可是,我也没有损失什么呀?
“别写了,出来一下,你二舅来啦!”母亲的呼唤,打断了我的思绪。
我写作的时候,是不愿中间停下来的。村里找父母串门聊天的人很多,我如果每个人都打招呼,这一天就什么也别干了。我多次对母亲说,家里一般的街坊来了,您张罗一下就行了,最好别叫我。母亲说,出来说句话又能怎么样?千万别让人家说你架子大。“我能有什么架子呢,我只是不想耽误时间。”我不止一次赌气地对母亲说。母亲听后,很是不高兴,说照你这样,街坊都会让你给得罪光的。
母亲说的二舅,是一个收废品的中年男人,五十多岁。他骑一辆自行车,车后座一边一个大筐,筐里放一杆秤。他从门口路过时,正好母亲出门倒垃圾。“你不是老陈家的大姐吗?”中年男人看着母亲,惊喜地叫道。母亲停下脚步,手里拿着土簸箕,定睛看了看中年男人,问:“你是……”“我是村西塔凤和家的塔老二啊!”“怎么,你是塔老二?”母亲也感到十分惊喜。虽说母亲的娘家归通州,距我们于家围也就十几里,骑上车顶多半小时的路。但自从十几年前我姥姥去世后,母亲几乎很少再回娘家了。对于娘家村里的人,母亲由于十八岁就出了门子,她能记住的十分有限。以前,父亲当书记的时候,母亲娘家村里时常来人找父亲寻活干,或者要买稻苗、草绳等。
母亲的娘家叫口子村。塔姓人家有三十几户。我要说明的是,这塔姓人原籍在双桥的塔营村。塔营位于通惠河南岸三四里,在清朝时住着一个掌管漕运的粮官。其级别为千户营,大约相当于现在的处级干部吧。相传,在康熙年间,这塔千户在管理漕运粮食时动了歪脑子,偷偷克扣公粮往家里藏,结果东窗事发,被康熙派人把家抄了。巧的是,当时塔千户有个小儿子,没有住在村里,而是随母亲回了娘家,也就是口子村,由于姥姥疼外孙子,留孩子多住了几天,因此抄家时免于一难,留下了这根独苗。经过几百年的繁衍,如今的塔姓人家在口子村共有几十户上百口人。我小舅舅八十年代中期结婚,娶的媳妇就是塔姓姑娘。
按街坊辈分,中年男人管我母亲叫大姐。于我,自然而然地就要称呼他二舅。二舅一点不见外,往院子中央的茶桌旁一座,母亲给他沏好茶水,又切了半个西瓜,还把我珍藏的中华烟打开一盒给他抽。二舅和母亲唠着家常。我出来叫了他一声二舅,就坐在旁边和他攀谈起来。他说,我小舅妈是他的堂妹,没有出五服。我说,你们塔姓本来就是一家,几百年来,从一个人繁衍到几十户上百人,这本身就是个奇迹。二舅说,谁说不是呢。我问二舅,这收废品一天能挣多少钱?二舅说,说不准,凑合挣口饭吃吧。
聊天中,得知二舅有两个孩子。姑娘嫁到太阳宫乡,儿子则在当地的一个乡镇企业。我一听说二舅的女儿嫁到太阳宫,就问,您听说太阳宫那边要重修太阳庙了吗?二舅说,好像听过那么一耳朵,只是那庙跟咱们关系不大。“那您说什么跟您关系大?”我问二舅。二舅说,以前日子过得饥荒,什么也不敢想,现在日子好过了,我们塔姓的几个管事的人商量,想建个塔姓祠堂。我说,建祠堂是好事啊,可以团结族人,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二舅问,你说这祠堂是建在口子村好呢?还是建在塔营村好?我想了想,说,还是建在塔营村好,只是这建房要经过政府部门批准的。听说塔营村即将面临整体拆迁,估计比较难。听我这么一说,二舅说,你是文化人,用你的笔杆子在报上写篇文章,给我们呼吁呼吁。如果需要花钱,我可以出一点,不会让你白忙活。二舅的话让我无地自容。我真不知道该怎样回答他。
中午时分,母亲在厨房好一通忙乎,为二舅做了五六个菜。我不善喝酒,还是陪二舅喝了几杯。二舅走的时候,我在床上已经睡了一个多小时。等我醒来,母亲对我说,你别忘了,你答应你二舅的事。我问母亲我答应什么了,母亲说,在报上写文章啊。我听后,脑子不由嗡地一下,心说,好端端的休息日,從哪冒出来一个二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