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和这个社会
2018-12-07张新颖
☉张新颖
不能不把事想得远一点,深一点
1946年8月27日,沈从文一个人从上海乘飞机回到北平,就任北大教职。
第四天,《大公报》记者徐盈和子冈来访,子冈随后发表《沈从文在北平》,做了生动平实的记录和描述,带着亲切的幽默:
……“我没有像振铎、一多那样做,我想”,他手指着前额画了很多圈圈说,“便是因为我能承受生活上的一切压力,反抗性不大,这或许是弱点。”
他完全不以报纸上说丁玲批评他与人民脱节为伤害他,“她一向那样说的。抗战初期,曹禺、巴金都曾有可能约往延安去,可是不知为什么,都没去成。我自己是一个没受过教育的人,所以书也教不好;不习惯受管束,也不会管束别人。还是让我和青年在一起,看了他们如何转变。”……
……似乎他还是看重作家的作品,或者更在为写作生命的有限担心,因为他说:“我也许还能写十年,别人写百万字的时间,我只能写十万字。我曾经和巴金同住过,他写《火》,我写《边城》,他一天写七千字,我一周才写三千字。”
他说他的原稿是别人看不清的,东一点,西一点,句子不完全,修整好了才对凑起来。果然桌上正在修整的旧稿好似女人正在电烫的头发,添的句子像夹子卷儿向四周散射。
……
……沈夫人……现在在苏州娘家。沈先生说:“来不了啊,……教授们的较好房子要等抽签。”他的12岁的儿子已上了苏州中学了。
版税呢?读者们会惊讶的。可是他不会愤怒,却显然是会伤心的,“今年开明结算稿费,我拿到三百六十元,因为是按照伪币折合的。算起来要自己一本书十八年的版税才能买一本书,这是书店的制度。”他又讲起部定的那本国定教本逻辑学。作者的数年版税值九元七角五分,为此他慨叹:“文化文化,原来我们就活到这么一种现实文化空气中,奇异的是活在这种文化空气中,居然还有人写作……工作的庄严感终未失去……原因是这种人明白现实尽管如何要不得,他的对面还有读者。”
……
由《忆北平》也可以看出他对时局的焦愁,他屡次地追问时局的症结,坦白地说:“你们告诉我,批评我,免得我发了傻气说了糊涂话。”……
如果你在北平的庙会或小胡同碰见一位提了网线袋,穿着一件灰色或淡褐色毛质长衫,身材矮小瘦弱,一脸书卷气,眯着眼睛在书摊子上找旧书或是在找门牌号数,说一口湖南北平云南杂糅的普通话,那便是沈从文。你可以告诉他,他该去理发店理发啦。
一个多月后,沈从文又接受《益世报》记者采访:“记者提出了郑振铎与郭沫若,他表示摇首,拿了巴金与茅盾来做比。他说:‘文化生活出版社是有极大贡献的,但巴金却在那里默默地支持着它,而且是很吃力的工作。茅盾也很沉稳,不像郭沫若一般的飞莫斯科。像女作家凤子穿的花红柳绿跑到苏联大使馆去朗诵诗,丁玲则到铁矿上去体验工人生活写了文章还要请工人纠正。’”提到何其芳等,并且还说:“假若国家把作家都放在宣传部里,那成什么样子”,“文学是可以帮助政治的,但是用政治来干涉文学,那便糟了。”
记者姚卿详做“学者在北大”系列采访,最先发表的是朱光潜的访谈,所以关于沈从文这篇在《益世报》10月23日刊出时,题为《学者在北大(二):沈从文》。沈从文没有料到,上海《侨声报》于11月3日又登载此文,且改题为《沈从文论作家》,他指名道姓的点评益发传播开来。
很难确定记者的记录准确到什么程度,描述中渲染的成分有多大。这篇访问记倒是有一点生活信息:沈从文搬进了较大的宿舍,“他的住房已不是鸽子笼式的了”,“他现在‘和朱先生他们在一块吃饭’。”
回北平后还不到一个月,沈从文就在9月22日的《经世日报·文艺》发表《新烛虚》,10月刊于《上海文化》时改名为《北平的印象和感想》,难抑痛苦地表达对所见的厌恶和失望。
运煤的脏骆驼进城,忽然看到美国出品的坦克;六轮大汽车出城,满载着新征发的壮丁。“就在这个时节,我回到了相去九年的北平。”在人群中散步看人,“俨然已多少代都生活在一种无信心,无目的,无理想情形中,脸上各部官能因不曾好好运用,都显出一种疲倦或退化神情。另外一种即是油滑,市侩、乡愿、官僚、××特有的装作憨厚混合谦虚的油滑。……我们是不是还有方法,可以使这些人恢复正常人的反应,多一点生存兴趣,能够正常地哭起来,笑起来?……我们是不是对于那些更年青的一辈,从孩子时代起始,在教育中应加强一点什么成分,如营养中的维他命,使他们在生长中的生命,待发展的情绪,得到保护,方可望能抵抗某种抽象恶性疾病的传染?方可望于成年时能对于腐烂人类灵魂的事事物物,具有一点抵抗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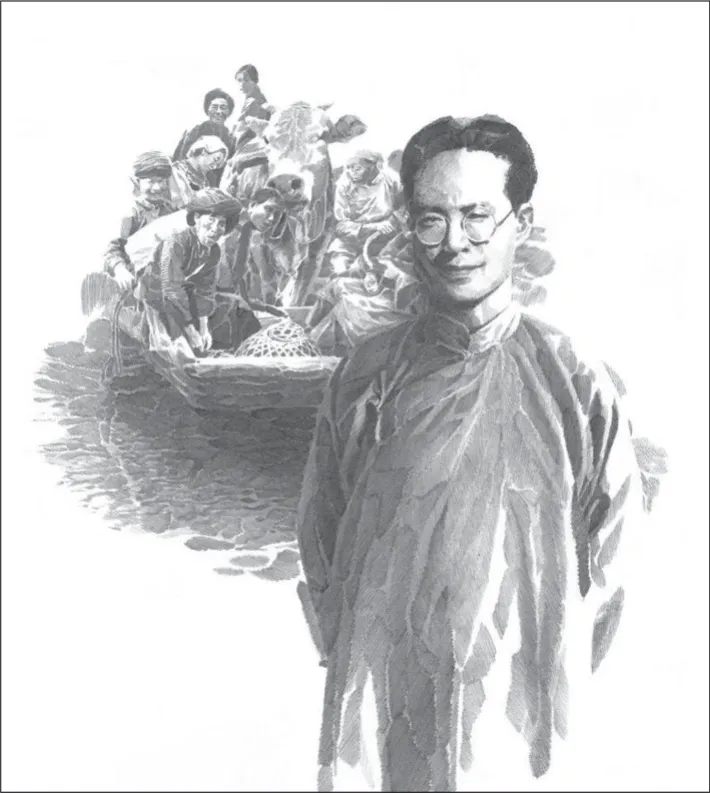
沈从文
他想到的是,“北平的明日真正对人民的教育,恐还需寄托在一种新的文学运动上。文学运动将从一更新的观点起始,来着手,来展开。”
北平之外,零下30度的一些地方,集结50万人在打仗。“读书人纵无能力制止这一代战争的继续,至少还可以鼓励更年青一辈,对国家有一种新的看法,到他们处置这个国家一切时,决不会还需要用战争来调整冲突和矛盾!如果大家苦熬八年回到了北平,连这点兴趣也打不起,依然只认为这是将军、伟人、壮丁、排长们的事情,和我们全不相干,沉默也即是一种否认,很可能我们的儿女,就免不了有一天以此为荣,反而去参加热闹。张家口那方面,目前即有不少我们的子侄我们的学生。我们是鼓励他们作无望流血,还是希望他们从新作起?显然两者都不济事,时间太迟了。他们的弟妹又在长成,又在那里‘受训’。为人父或教人子弟的,实不能不把这些事想得远一点,深一点,因为目前的事和明日的事决不可分。”
为寄托希望的新的文学,沈从文又忙碌起来:他和杨振声、冯至主持天津《大公报·星期文艺》副刊,10月13日出第一期,不久此副刊全交由冯至发稿;接任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主编,10月13日在第十期发表《文学周刊开张》;12月,与朱光潜、杨振声、冯至、徐盈署名编辑的《现代文录》杂志出版,但只出了一期;经萧离介绍,主编北平《平明日报·星期艺文》副刊,12月29日创刊,他题写了刊头,此副刊实际主要由北大同事周定一负责。
沈从文把编副刊的工作看得很重,如在《益世报·文学周刊》第11期的《编者言》中所表示的那样的:“第一句应交代的话,是‘没有热闹’”;“对作者将为一个自由竞争表现新作的据点,对读者将为一个具有情感教育的机构”;“若有人问我,在你这个理想发展中”,产生有成就的作家和有分量的作品,“用来和这个乱糟糟的现实社会对面,有什么作用?我不必思索即可回答,希望它能有作用,即在多数人情感观念中能消毒,能免疫。不至于还接受现代政治简化人头脑的催眠,迷信空空洞洞‘政治’二字可以治国平天下,而解决国家一切困难与矛盾。却明白一个国家真正的进步,实奠基于吃政治饭的越来越少,而知识和理性的完全抬头。”
围攻
1946年,沈从文发表作品近四十篇,有少数是重刊。在这些文章中,最受瞩目的是《从现实学习》,11月3日、10日《大公报·星期文艺》天津版和上海版同时刊出,紧接着即遭到异常激烈的批判。
文章正文前有一小段引言:“近年来常有人说我不懂‘现实’,追求‘抽象’,勇气虽若热烈实无边际。在杨墨并进时代,不免近于无所归依,因之落伍。这个结论不错,平常而自然。极不幸即我所明白的现实,和从温室中培养长大的知识分子所明白的全不一样,和另一种出身小城市自以为是属于工农分子明白的也不一样,所以不仅目下和一般人所谓现实脱节,即追求抽象方式,恐亦不免和其他方面脱节了。试疏理个人游离于杨墨以外种种,写一个小文章,用作对于一切陌生访问和通信所寄托的责备与希望的回答。”
《从现实学习》是这个特殊阶段产生的自传,偏重对所经历的不同时期社会现实的个人性认识和反应,对别人是“回答”“责备与希望”,对自己是寻求和获得内生的、根源性的支撑。
既然谈“从现实学习”,就无可避免要涉及社会、政治、时局问题,正是在这些敏感问题上,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和一触即发的尖锐冲突。
文章结尾,沈从文写道:“……在企图化干戈为玉帛调停声中,凡为此而奔走的各党各派,也都说是代表群众,仔细分析,却除了知道他们目前在奔走,将来可能作部长、国府委员,有几个人在近三十年,真正为群众做了些什么事?”这段话不仅批评正在武力交战的双方,而且并及以民盟为代表的第三方力量。他不信任任何的政治派别。
12月21日至25日,上海《文汇报》分五次连载两万字长文《沈从文批判》,作者史靖,本名王康,西南联大社会学系1944年毕业,抗战胜利后参与民盟刊物《时代评论》编辑工作,这个刊物主要由吴晗和闻一多负责筹集经费。文章说,沈从文“一天一天和自己出身的阶级远离,在八年抗战和一年内战的期间他且显然站在对立的地方,以致为时代所讥讽所唾击,为同时代的同道者所遗弃”,“事实迫使着像我这样曾经对沈先生有过爱好和希望的一些人不能不有所遗憾和谴责”。《从现实学习》更加让人“失望和憎恶”,“充满了一个被时代所遗弃了的作家的控诉和愤懑,因此在全文里到处都弥漫着自辩和抑不住寂寞的声音,在祈求着读者给他以同情和支助”,“不仅固执着错误,而且要将错误送给别人。”
《从现实学习》谈到云南阶段的生活时,说:“在这段时间中,对于能变更自己,重造自己,去适应时代,追求理想,终又因而为愚人一击毁去的朋友,我充满敬意。……”
史靖揪住“愚人一击”,厉声反问:“好一个‘愚人的一击’!谋杀闻先生的仅仅是‘愚人’一击可以遮掩的吗?沈先生,你为了讨好,真是煞费苦心了,你可知一个杰出的人才就在你轻描淡写之下给‘毁去’了吗?”他如此断言:“沈先生不仅在积极地帮凶,而且消极地一字一句的都在宽恕和抵消反动者的罪过。”
12月29日,中华全国文艺协会上海分会举行辞年晚会,检讨文艺界四种不良倾向,第一种是,“产生了一种自命清高,但不甘寂寞的人。脱离现实在清高的地位上说风凉话,这种人的代表是沈从文。”第二天《文汇报》以《作家团年》为题刊登了此消息。
郭沫若看到新闻后,立即写《新缪司九神礼赞》,声援文协同人,批评“搞小说的少数温室作家”——直指沈从文——“他们把文艺的圈子画得很紧,除掉自己的小说之外差不多就无所谓‘创作’。”在列举了一大批作家、学者的名字和文艺的各部门之后,郭沫若说:“朋友们哟,我想称颂你们为‘新时代的缪司九神’,你们真以过人的努力,克服着当前的超级地狱,而在替我们播着火种。说你们没有货色拿出来见人者,那是帮凶者的诬蔑!但你们受着这种诬蔑,也正是你们的光荣。”此文发表在1947年1月10日《文汇报》。
郭沫若这篇文章还顺带回击了沈从文访谈中的“摇头”:“有一位‘自由主义’的教授,听说一提到我便摇头,因为我去年曾经‘飞莫斯科’,更成了他的摇头材料。……假使有机会飞,我还是要飞的,尤其是‘飞莫斯科’。我并不怕教授们向我摇头……我假如努力到使教授们把头摇断,那是最愉快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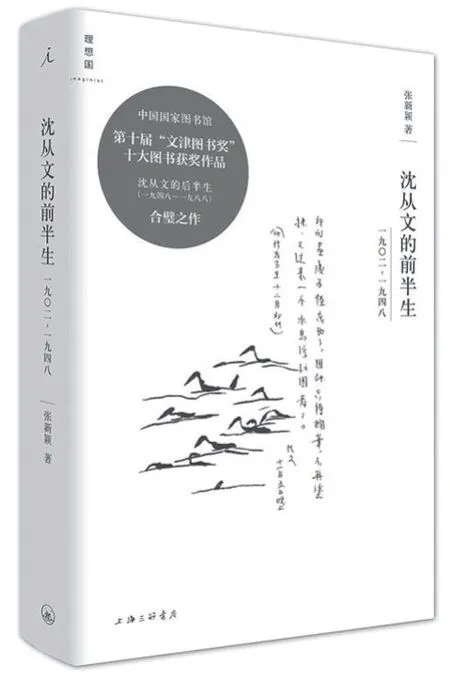
1月18日,沈从文在天津《大公报》发表《新书业和作家》,21日上海《大公报》也刊出此文,简述新文学以来作家和出版之间的关系,呼吁作家和经营书业者,双方都要有一点理想,“希望有人能记住这不是纯粹商业。”文中谈及创造社,“一面感于受当时有势力文学社团压迫,一面感于受出版方面压迫”,“因此来自办出版,直接和读者对面。努力的结果,虽若干短时期即作成两面的突破,过不久终因为经济方面转手不及,不易维持。”不料这也引起郭沫若动干戈,他在27日的《文汇报》发表《拙劣的犯罪》,说“书业的不振或不正和作家的受罪,分明是政治问题”。沈从文“信口开河”,“冒充一个文坛长老而捏造事实,蒙蔽真相,那明明是一种犯罪,而且是拙劣的犯罪。”文章说,沈从文“极尽了帮闲的能事,一面做掩饰工作,一面做离间工作”。又说,沈从文“一手轻松便把政治的责任推开,而把严重的罪状加在出版家们的头上”,“这简直是超过了帮闲的范围,而死心踏地的帮凶了。”
“帮凶”,“帮闲”,“诬蔑”,“犯罪”,猛然间已成口诛笔伐之来势。沈从文本能地想要反驳,2月前后,起笔四篇文章,但四篇都未完稿,可以猜想他一次又一次欲辩,而终于废言的情形。这四篇残稿集于《政治与文学》题下编入《沈从文全集》,现在能够看到他当时的一些内心活动:
老朋友说:“你是不是有点痛苦?”我说:“唉嗨,有一点儿。那就是没有属于任何一党,也没有什么后台,自己也没有钱,不然倒很想把自己的文章和那些批判汇拢来,印个小本本,留下来有目共赏。”

1981年夏,沈从文、张兆和夫妇在寓所
我怕争斗吗?是的,我怕我和我们一辈爱这个国家而又沉默工作了四十年的一些专家,毁于混乱中,我更怕这个国家会为国力消耗太大而毁去。……但是战争还是来了。这是我们的痛苦,凡有做人良心的总会感到痛苦,是国家民族的羞耻,因为直到如今,我们还缺少一种稍进步的观念,能由战争以外找寻调整这个国家的矛盾方式。
2月初,沈从文给在上海的李霖灿、李晨岚复信,主要是想托他们为汪曾祺找一个工作,当时汪曾祺在上海一所中学教书,不遂意;顺便提及自己的情况,如此说道:“在这里一切还好,只远远的从文坛消息上知道有上海作家在扫荡沈从文而已。想必扫荡得极热闹。惟事实上已扫荡了二十年,换了三四代人了。好些人是从极左到右,又有些人从右到左的,有些人又从官到商,从商转政,从政又官,旋转了许多次的。我还是我。在这里整天忙。”
2月3日,给上海一位熟人信中说,“这里一切照常。事能进行,惟在此死城中所进行的虽若也还庄严,但想起千里内一片杀声,一片血影,便不免令人茫然了。照上海扫荡沈从文的消息说来,我倒俨然像是要清算的一位”,“四个月来,一大堆访问记,都从莫名其妙情形中转成上海报纸资料,如说巴金不问国事,如说西谛,如说凤子,断章傅会,都成瞎说。到之琳来,方知道还多为《侨声报》故意大大登载。又这里一某某,又说我提拔的萧乾如何如何,我想生平从不曾如此说,怎么会有这类语气?”——姚卿详的那篇访问记,有这样的叙述:“另外他称赞的有卞之琳与萧乾。他说卞之琳在静默中写着他五十万言的英文小说,而他在大公报时代提拔出来的萧乾,认为他的学习与创作的态度及努力也都是极认真的。他连口说:‘萧乾很好!’”
汪曾祺也关注到这场“围攻”:“沈先生写了两篇杂文,引来一场围攻。那时我在上海,到巴金先生家,李健吾先生在座。李健吾先生说,劝从文不要写这样的杂论,还是写他的小说。巴金先生很以为然。我给沈先生写的两封信,说的便是这样的意思。”
“不毁灭的背影”
1948年8月12日,朱自清因严重的胃溃疡导致胃穿孔不幸去世,终年50岁。19日,沈从文作《不毁灭的背影》,28日刊《新路》周刊第一卷第十六期。
悼念朱自清的文章短时期内出现很多,哀痛之情弥漫字里行间自不待言,不同的认识和表达却也见出悼念者各有所重,各有突显的方面,隐现其中的朱自清形象自然也多少有些不一样。在众多的文章中,《不毁灭的背影》不被注意几乎是必然的,它没有高调,只是低沉地说了一些平实的话。
沈从文和朱自清有相当长时间的共事同处,从沈从文看朱自清,自是有不可替代的角度,而且,沈从文看朱自清,见出他的固执,他的信守,还有他的悲哀:
“其为人也,温美如玉,外润而内贞。”
旧人称赞“君子”的话,用来形容一个现代人,或不免稍稍迂腐。因为现代是个粗犷,夸侈、褊私、疯狂的时代。艺术和人生,都必象征时代失去平衡的颠簸,方能吸引人视听。“君子”在这个时代虽稀有难得,也就像是不切现实。惟把这几句作为佩弦先生身后的题词,或许比起别的称赞更恰当具体。佩弦先生人如其文,可爱可敬处即在凡事平易而近人情,拙诚中有妩媚,外随和而内耿介,这种人格或性格的混和,在做人方面比文章还重要。
沈从文在这里特别说道:
正如作家的为人,伟大本与素朴不可分。一个作家的伟大处,“常人品性”比“英雄气质”实更重要。但是在一般人习惯前,却常常只注意到那个英雄气质而忽略了近乎人情的厚重质实品性。
显然,他不会顺势发声,把亡友往“英雄”方向上推靠,就此而说到文学教育,也是强调“厚重质实品性”之意义:
文运的开辟荒芜,少不了一二冲锋陷阵的斗士,扶育生长即必需一大群有耐心和韧性的人来从事。文学教育则更需要能持久以恒兼容并包的人主持,才可望工作发扬光大。佩弦先生伟大得平凡,从教育看远景,是惟有这种平凡作成一道新旧的桥梁,才能影响深远的。
沈从文追悼“近乎人情”的“常人品性”,追悼“伟大得平凡”、“伟大本与素朴不可分”的为人为事,虽然无意于自我投射,但这种追悼本身,连同这一时期他自己所努力所挣扎的一切,正是面对这个时代的个人方式。然而,他个人的这种面对,又像是背对,给时代留下一个背影——一个有“悲哀的分量”的背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