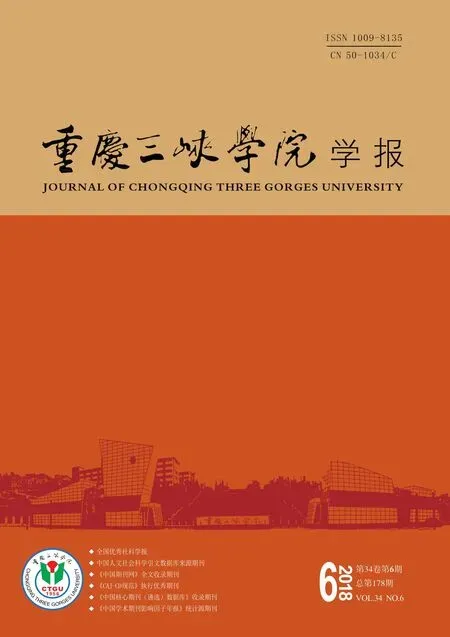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语境下的环三峡地区巫文化
2018-12-05邓晓何瑛
邓 晓 何 瑛
三峡研究 栏目主持人:滕新才
主持人语:三峡地区是远古巫文化的摇篮。《山海经·大荒西经》载:“有灵山,巫咸、巫即、巫朌、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又《海内西经》:“开明东有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巫相,夹窫窳之尸,皆操不死之药以距之。”说明三峡地区是巫文化的核心,巫咸国、巫臷国都是承载“不绩不经,服也;不稼不穑,食也”“爰有歌舞之鸟,鸾鸟自歌,凤鸟自舞;爰有百兽,相群爰处,百谷所聚”的远古社会理想的渊薮。本刊历来关注三峡巫文化研究,2011年以来陆续发表了《三峡巫文化中的医学易学灵学》《论巫山大溪文化遗址中绿松石的巫医和巫饰功效》《论巫文化视野下的三峡丧礼习俗》《三峡古代巫文化研究的若干思考》《三峡巫文化的审美阐释》等论文,成为三峡巫文化研究的一方重镇。本期刊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环三峡地区远古巫文化探究”阶段性成果《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语境下的环三峡地区巫文化》,将研究视野拓展到三峡周边地区,鉴于巫文化已深深融入民风民俗和乡规民约的现实,提出优先保护、重点保护、鼓励性保护、选择性保护四类原则。诚如屈全绳中将撰文指出:巫文化植根于原始社会的土壤之中,涉及人的生存诉求、思维习惯、情感记忆、价值认同和审美意识,蕴涵着“以人为本”的文化内核;扬弃巫文化、创新巫文化,让巫文化在返璞归真中踏入现代文明之路,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巫文化的基因要到文化遗址中去寻找,到古史典籍中去寻找,到民俗文化中去寻找,到群众生活中去寻找,到释道仪规中去寻找。本期另一篇《万州唐墓出土人物俑服饰研究》以冉仁才“驸马坟”随葬的文吏俑、武吏俑、武士俑、骑士俑、侍从俑所著服饰探索初唐服饰承上启下、糅合胡汉的文化特征,凸显唐人独特的审美观,致思路径亦有相通之处。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语境下的环三峡地区巫文化
邓 晓 何 瑛
(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重庆 401331)
巫文化是人类童年时代的认知产物,是遍及全球的原始宗教现象,且有着深刻的内涵和丰富的表现形式。如今,源自远古的巫文化在民间依旧有着相当强的生命力,除了人们认知的局限所致外,更重要的是它在相当程度上已经融入了民间的风俗与乡规民约。对远古巫文化遗产应该理性地认识、辩证地看待、有效地保护,保护的方法可以根据需要分为“优先保护”“鼓励性保护”“重点保护”和“选择性保护”四类。
巫文化;环三峡地区;认知;保护
在“非遗”保护语境中探讨巫文化遗产,其尴尬之处有四:一则因其在意识形态领域被长期视作封建迷信而禁止公开;二则它遍及各地且表现形式千差万别;三是它与民风民俗长期杂糅、且已融入文化传统;四是因其濒临消失而被列为需要保护的遗产。问题棘手并且讨论者甚少,对该问题笔者虽有过初步讨论,但仍有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必要。
一、巫文化的缘起与影响
巫文化大约产生于旧石器时代的末期。它的出现首先与“万物有灵”进而对“鬼神”的认识相关。“人所归为鬼”[1]188,在那个人类尚不知道自己来自何处,也不明白生死道理的年代,如同尼安德特人或山顶洞人那样,以随葬富于生命力的山羊角①或赤铁矿粉呼唤亡灵是合乎情理的。“万物有灵”观念源于原始先民认知能力的低下,它既是促使宗教产生的最早观念,也是原始巫术得以产生的重要原因。尼安德特人和山顶洞人实施的巫术行为,亦即为其面对的生死现象和他们需要解决的死亡难题所找到的答案,随葬什么样的物品,即体现出他们解决该问题的不同思路和方法,这方法体现了那个遥远时代的理性。

法国人类学家列维·布留尔认为,对原始人而言“彼世的人也像现世的人一样直接出现;彼世的人更有力量更可怕”[2]435。在其所著的《原始思维》一书中,根据对当代原始部落的调查结果,将占据原始人思维的力量概括为三类:一是死人的鬼魂,二是广义的神灵,它使自然物、非生物及人所制造的东西具有了灵性;三是由巫师所实施的妖术或巫术。他指出,这三类常常是彼此重复的。显然,万物皆有“灵魂”的认知,是原始社会巫术进而专职巫师产生的前提。巫师的职责是与不同灵魂乃至鬼魂沟通并产生联系,或亲近、求佑,或躲避、镇慑鬼灵,然后达到为我所用或彼此和谐相处的目的。《说文解字》称:巫师能以舞蹈通神,且初为女性,即“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1]100。女性最早从事巫术活动符合其当时的社会核心地位,继而才有了男性巫师称“觋”。巫师用来沟通“灵界”的方法称为巫术,巫师、巫术以及实施巫术产生的影响共同构成了巫文化。
站在今天的角度,巫师所实施的巫术无疑属于非理性的范畴,在方法上也有违科学;但从历史唯物史观出发,原始时代巫师的观念和行为却自有其合理性。巫文化的出现,是先民在其普遍认知力、生产力均极为低下的时代为征服自然做出的最大努力,它曲折地表达了人类认识、沟通自然,追求和谐生活的愿望。英国宗教学家弗雷泽在他的《金枝》中强调:“如果巫术能够变为真实并卓有成效,那么它就不再是巫术而是科学了。”[3]88为此,他指出原始先民很早就开始探索那些能扭转自然事件进程使之有利于自身的普遍规律,久而久之他们积累了大量经验,其中“属于真理的或珍贵的规则成了我们称之为技术的应用科学主体,那些谬误就是巫术”。需要指出的是该观点实际上是作者站在后代立场上的认知,而事实上其所谓的“属于真理的或珍贵的规则”与被称为“谬误”的巫术,在先民那里都体现为巫术本身,并且它们出自同一群巫师之手,此时的真理与谬误本身就是合而为一的。马克思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认为,古代世界的民族都是在幻想与神话中度过自己童年的,他们的“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4]。在此,我们所关注的正是远古巫师们努力探索世界之行为本身的积极意义,就如同神话本身,它虽然包含着不少错误的认识,但人类的探索精神,神话中折射的现实与历史和神话故事的奇幻与美丽,不也是很有价值么。在这混沌的世界观里,包含着后来人类认知世界的主要方法,宗教、哲学、科学和艺术的萌芽。
如今,我们对原始时期巫师及其活动的详貌,由于资料的缺少而难以管窥,但可以推定,倘其巫术毫无效果对巫师自己肯定没有好处,这表明他已经失去了通神的能力,其结果可想而知。而事实上从夏商至秦,我国一直盛行巫师与占卜的记载,且从殷墟大量出土用于祭祀的甲骨文这一现象看,他们受此威胁的程度似乎并不太大。究其原因,巫师无论是为了窥测天意还是影响他人,除去预测中非此即彼可能成功的对半概率外,在主观上为确保其巫术效果,他们可能还需付出种种的努力。在当时,统治者往往兼有巫师的职能,张光直先生就此指出:“如我们所知,商汤可祭祀祈雨,后稷具有使庄稼生长得更快速的特殊才能。这些传统信仰得到了商代甲骨文的印证,这也说明帝王确为巫觋之首。”[5]36弗雷泽在分析个体的巫师是如何成为政治首领的原因时指出,当巫术仪式与部落的利益息息相关时,巫师的声望和地位就会进一步上升,并可能因此很容易地取得首领或国王的身份和权势。显贵的地位对部落中那些最能干、最有野心的人最具有吸引力,当然“在职业巫师的前进道路上有许多陷阱,照例只有头脑最冷静和智力最敏锐的人才有可能平安地绕过它们”[3]81。其所列权力、危险与智慧之间的游戏法则,恰好证明了胜任巫师职能的不易。
巫文化在古代社会的影响是明显的,它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协调人与环境的关系,人与社会生产的关系,人际间关系。且在这三个方面均可谓利弊兼具:从有利的方面看,一是崇拜强大自然力的心理(感恩或畏惧),在客观上能够约束人类破坏自然环境的行为;二是通过对丰产的祈祷和对生产禁忌的规定,有利于人类的社会生产发展;三是通过宣扬“头上三尺有神明”的警示,有利于规范道德,稳定社会,和谐家庭。而其负面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一则,用巫术的非理性指导社会生产与生活,会有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二则,巫术常被权力掌握者利用,以之作为控制民众思想、维护其统治的工具。
探究巫文化得以在远古产生重要影响的原因,在宗教学上,源于民众对自然的敬畏、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对精神领袖(能够沟通灵界)的期盼;在心理学上,“咒语”和“神力”附体的幻象起着重要作用,这与个体差异和实施心理暗示、催眠术相关;在艺术学上,巫师常以舞蹈、戏剧、绘画等艺术形式宣扬其理念,极易煽动和左右民众的情绪。宗教亦即前哲学,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与方法论,都可以在原始宗教里找到根源,与西方自然哲学追究万物本源(from)与最小构成(minimum)不同,基于神权政治的东方哲学思想,则更注重于社会控制的效果,在该过程中祖先崇拜与巫术便成了重要的方式。从商代卜辞中我们发现“帝王在筑城、征战、狩猎、巡游或举行特别祭仪之前,都倾向于通过占卜来取得其祖先的赞成或认可”[5]45。在其后的诸多文献史籍中,我们也不时看到巫师的身影,读到帝王迷信巫术的记载。
概言之,巫文化是一种全球性的人类文化现象,是原始时代人类智慧的体现,旨在认识自然规律和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因此在当时具有先进意义,并在客观上起过积极的作用。巫师是原始社会的智者且往往为领袖,其地位随着人们心目中巫术的地位而发生变化。巫术与应用科学曾经同出一源,继后分道扬镳,为现代科学与理性所扬弃。
二、巫文化遗产在环三峡地区
巫文化遗产在环三峡地区不仅源远流长且内容也十分丰富,这里的巫师既是巫术的实施者,也是它的主要传承者。正如宋兆麟所谓,作为史前时代的智者,巫师是最早的杰出歌手和舞者,最早的口述史学者、星象观察者、治病救人的医者和绘图人[6]。而相对封闭的自然环境及民众对巫师的认同,则是当地巫文化遗产得以较好传承的重要保障。于是,通过该地区各历史时期巫师与信众的共同努力,巫文化代代相传;而促成民众传承巫文化的动力,则是他们对美好生活的真诚向往。概括环三峡地区巫文化遗产,其内容主要体现在“巫教”“巫俗”和“巫艺”三大方面,笔者对此曾有过归纳[7]。
作为巫文化内核的“巫教”,包括各种巫术以及祭祀、避邪及崇拜。它属于宗教的低级阶段,在环三峡地区的民间遗存有鬼教、娘娘教、苗教等形式,其中以“鬼教”最为典型。“鬼教”盛行于商代的“鬼国”,中心在平都(今重庆市丰都县),后被当地的巴人信奉,并有“人祀血祭”和“彼崖獭祭”的传统。东汉时张陵采用“黄老之说”改造“鬼教”,创立了“天师道”(五斗米道,亦称“鬼道”)。在隋唐的古籍中亦有“夷事道,蛮事鬼”[8]卷十引《夔城图经》的记载。北宋时,晏殊的《晏公类要》还明确记载“白虎事道,蛮蜑人与巴人事鬼”。到了清代,该地“每岁孟夏,或设坛玉皇阁斋醒数日,文武官亦诣坛上香,为民祈福”。而每当“乡里有争角,辄凭神以输服,有疾病则酬神愿,大击钲鼓,请巫神以咒舞”[9]。环三峡地区相对闭塞的环境,使尚巫占卜的传统在不少地方延续至今,如“跳端公”“告阴状”“请七仙姑”“请桌子神”“化九龙水”等均为巫教的余脉。
基于原始巫术的“巫教”,与宗教之间有着质的区别。前者强调人(巫师)在目的、动机和行为上的关键作用,后者则注重“神灵”对于解决问题的绝对权威。宗教强调世界是由神来引导的,人类对它只能无条件地服从;而巫教则认为“一切具有人格的对象,无论是人还是神,最终总是从属于那些控制着一切的非人力量,任何人只要懂得用适当的仪式和咒语巧妙地操纵这种力量,他就能够继续利用它”[3]91。于是巫师对于神灵的态度不是像僧侣那样去服从或取悦它们,而是利用手中掌握的“技术”去驱使它,因此不能将巫术与宗教、巫师与僧侣一概而论。由巫教向盲目崇拜的宗教发展,有着质的变化。
作为巫文化重要载体的“巫俗”,主要包括民俗、丧俗、禁忌、巫医等形式。环三峡地区自古巫风盛行,久而久之便积以成俗,例如南朝时当地便有“正月一日……鸡鸣而起,先于庭前爆竹,以避山臊恶鬼”[10]的记载。就葬俗而言,远古巴人以船为棺、高悬于崖上的安魂方式亦颇具巫术意义[11]。在当地如今的土家生活民俗中,依然保存着浓厚的巫味,人们在建房动土、伐木、奠基时,都十分强调要选择“吉日”烧香敬神;他们的民间丧葬,仍有人沿袭请巫师“看风水”择墓地,为亡人招魂,敲“断气锣”,作道场、念经超度,唱“丧鼓歌”,拂晓前出丧“克鬼”等传统。而“禁忌”巫俗,在如今的环三峡地区仍俯拾皆是。例如正月初一不扫地,以免财气外泄;吃年饭不能泡汤,怕来年涨水冲垮田坎;正月祖坟前不动土,怕挖断灵气;还因为“丧”和“扭”会带来家运不顺,于是他们在门前不栽桑、屋后不栽柳。繁体的“”字便是古时巫医不分的证据,巫俗中的“巫医”在环三峡地区历史悠久,“古之巫书”《山海经》述及巫师时,常常将其与使用药物联系在一块,如“开明东有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巫相,夹窫窥之尸,皆操不死之药以拒之”[12]。对该六巫,郭璞注称:“皆神医也。”此外,《吕氏春秋·勿躬》《世本》等书中,都将巫彭称为“初作医”者。至今,环三峡地区的巫师多自称有驱邪治病的本事,如“化九龙水”(消骨刺)“治犬咬伤”“杀羊子”(消包块)等[13]。
仪式与规则在“巫俗”中举足轻重,而仪式与规则本身的形成又往往源于巫术。人们在现实社会面临的问题是全方位的,从季节变化、岁时延续规律与作物生长的相关性,到生老病死、悲欢离合与人的生存状态、生存环境的联系等;无论问题大小,在“巫”的世界都被认为是可以探知和控制的。于是,通过制定规则合理地避开危险,依据特定仪式实施巫术去摆脱困境或谋取利益,便成为民间巫师常用的方法。久而久之,这些巫味浓厚的仪式、规则和方法便约定为民俗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里,巫俗与宗教祈求神灵施恩的方法虽然异曲同工,但前者确实更具有人的主观能动性。
作为巫文化重要形式的“巫艺”,包括巫歌、巫舞、巫戏(傩)、巫画、神话等形式。楚歌是巫歌的代表,它对“楚辞”的产生意义重大,楚辞语言形式的某些特征“更直接地脱胎于巫歌”[14],楚辞中《九歌》《离骚》《招魂》《九章》及《大招》等的形式与内容无不与巫、觋相关。岳麓书社1989年出版的《梯玛歌》,是土家巫师作法时唱的巫歌,其内容包罗万象,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环三峡地区的“巫舞”,尤以古代的“巴舞”最为杰出,史载武王伐纣时随从的巴人军队“歌舞以凌殷人”[15]卷一《巴志》,“巴舞”即巴人的战阵舞,旨在以巫术的力量鼓舞士气、镇慑敌人,有学者考证“巴舞”演变成了后来土家的“大摆手”;而巴人“男女相携,蹁跃进退”旨在取悦神灵、祈祷丰年的生产巫舞,则演变成了今天土家的“小摆手”舞。此外,诸如“打绕棺”“仙娘”“马脚”“七姊妹”等,亦是环三峡地区的民间巫舞形式,旨在消除病害、祈祷平安、祭祀亡灵、驱逐鬼邪,并且在事实上它们“都依附着民间传说和民俗活动而广泛传播和不断发展”[16]769。环三峡地区的“巫戏”则有“茅古斯”“还傩愿”“还坛神”等,其中作为巫戏活化石的“茅古斯”还“具有戏剧舞蹈双重性质”[17],它由男人们披戴着稻草进行,表演祈丰年、求生育的巫术,其内容体现出原始生产的双重性(生产资料的生产与人类自身的繁衍),通常在舍巴日(摆手)祭祀中演出。环三峡地区还是中国神话与传说的重要产地,与其相关的有《山海经》中叙述的远古神话和“十巫”故事;有诸史书所记载的历史传奇;有《中国民间故事集成》②收录的女娲补天、巫山神女、大禹治水、开天辟地和烛龙等著名神话,呼归石、廪君化白虎、盐水女神、巴族悬棺等传说。它们以特殊的艺术形式,向后人传递着由巫文化曲折反映的历史。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环三峡地区出土的巫文化雕像。在这些原始“巫艺”中,有展示巫师形象的,如湖北省秭归县柳林溪遗址第一期遗存中出土的“秭归柳林溪人物坐像”[18],重庆巫山大溪64号墓出土的“巫山大溪双面人面雕像”[19];有表示原始崇拜的,如湖北省秭归县东门头遗址东北部江滩断壁发现的“秭归东门头人物”[20],巫山县大水田遗址出土的“人形饰”[21];此外还有在大水田遗址出土,作为陪葬品的猪、穿山甲和鸟头等动物雕饰。包括这些雕像在内的上述各种艺术形式,都有着祀神、祈福的目的。在没有文字的社会,由巫术制定的规则起着重要的传承作用,长此以往便形成了表演形式的仪式化、表演内容的规范化、表演程序的秩序化及表演特征的符号化,且对其表演的时间、地点都有了特定的要求,诸如摆手舞、褥草锣鼓、哭嫁歌[22]等“非遗”也深受其影响。
环三峡地区的巫文化遗产种类繁多、内涵丰富,它们不仅源远流长,还因为该地区特殊的地理与人文环境得以较好地保留到今天,在民间信仰、民风民俗、民间艺术等方面表现尤为突出。经过漫长岁月的积淀,远古巫文化已经通过不同方式渗透于人们社会生产与生活的方方面面,外化为特定的仪式与规范。
三、环三峡地区巫文化遗产的保护
古老巫文化至今犹存的原因大致有三:一是缘于人类未有穷期的认知历程,事实上当代人和历代前辈一样仍会不断面临难以克服的未知,并由此不断产生新的敬畏及探求的欲望; 二是巫文化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已有不少与民风民俗水乳交融,并以喜闻乐见的形式成为人们生活中难以分割的一部分;三是在宗教信仰业已得到各国政府普遍尊重与认可的今天,作为其先声的巫文化,其满足普通民众精神需求的实践价值,使其在民间依然拥有较广泛的生存空间。
民族学常常被用做研究原始文化的例证。列维·布留尔的《原始思维》,便是欧洲社会学家依据对上世纪初澳大利亚土著居民、斐济人、安达曼群岛土著居民以及非洲土著的调查研究完成的。书中将当代土著的认知方式称为“原逻辑思维”,以其与地中海的“逻辑思维”区别,作者欲以前者的“反逻辑”证明后者的先进。这是当时欧洲中心论在学术界的明显体现,但在后来作者给俄文版的序中,又不得不承认当今社会“在人类中间,不存在为铜墙铁壁所隔开的两种思维形式”[2]2的事实,处在原始状态下的人类,其思维水平是大致相同的。
在近代社会,真正形成列维·布留尔所谓“原逻辑思维”与“逻辑思维”差异的前提,往往是地域分割导致的,与人种无关,越是封闭落后的地区,原始风貌的保存越是完好。自古以来,环三峡地区就巫风浓厚。峡谷深山、相对闭塞的地理环境,使当地巫文化遗产的标本丰富且保存较好。时至今日,漫长岁月的积累已使之根深蒂固,它们涉及面广、内容庞杂,但在其传承了大量积极内涵的同时,封建迷信的渗透使之良莠不齐。因此,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实施过程中,对属于“原逻辑思维”下产生的巫文化,如何进行历史地、理性地、辩证地鉴别和评判,如何实施及时的、切实的、卓有成效的保护便显得十分重要,为此笔者作如下思考。
从本质上说,三峡地区的远古巫文化和世界其他地区一样,为先民认识、改造自然、推动社会发展的智慧结晶。巫文化遗产中的正能量在于,它体现了人类对未知世界的探索精神,蕴含着先民朴素的宇宙观,而在其解决问题的方法中,又积累和总结出许多后来人类的知识。因此,最早的巫师应当是那个时代的智者与民众的领袖,他们表达了人类掌控自然与自身的愿望,体现了当时社会先进分子特有的“理性”。也正是基于此,有学者将三峡远古文化(包括巫文化)称为“中华民族南方文化源头”[16]44。而巫文化的消极内涵亦是显而易见的,它强烈的个人主观意志与思维方式,在特定条件下难免带来负面影响。正是环三峡地区巫文化产生的特定前提和意义,其发展过程中与民风民俗的深入融合,为该文化作为区域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准备了条件。基于此,我们在讨论其性质与作用时,就不便随意、简单地下结论,而应当客观、审慎地进行判断。
从方法上讲,由于环三峡地区巫文化产生于自然力十分强大而人类相对弱小的时期,其探索自然规律、征服自然的手段便只能采取迂回、祈使的巫术形式,也就不可避免地打上了神话、迷信甚至想当然的烙印,但这就是当时所能采用的最正常方法。进入阶级社会,当巫术的实施与大多数人的现实利益相关联时,巫师的智慧越来越多地与权力相结合,在特定时空下,其统治者的主观意志甚至会以巫术的形式体现,使理性丧失。历史地看,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巫术的神秘性与非理性必然越来越淡化,其大多数的表达手段将为人们所扬弃。但这不会就是全部,那些已经融入民风民俗的巫文化内涵,仍然会伴着诸如神话、传说与音乐、舞蹈、戏剧、美术等民间艺术形式,得到保留和传承;一些因远古巫术而兴的仪式、规则与禁忌,亦会随着人们对乡规民约的遵守而代代相传。对那些在形式和内容上已经与地方民俗互为表里的巫文化遗产,我们不能生硬地将之剥离。
从内容上看,通过环三峡地区数千年的文明进程,传自远古的巫文化已经深深地植根于民风民俗之中,在当地人的社会生活与生产中,它们多以大家约定俗成的规则或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展示,在相当程度上规范着人们的社会生产与秩序,引导、娱乐和丰富着人们的精神生活。就性质而言,巫术与艺术是矛盾的,前者是人的自我异化,后者则力图确认人的自由本质[23]。但两者之间的关系却又颇为密切,一则人是情感的动物,巫术需要激情地表达才能对人“动之以情”进而产生信仰;二则人类的艺术活动是激情创造的来源,为此巫术需要相应的艺术表达形式。就这样,巫术与艺术在相互的博弈与利用中消长,并极大地影响着人们的社会生活。于是,我们看到带有巫术色彩的各种舞蹈、戏剧、游戏便在民俗中融为一体,互为表里,成了特色鲜明、价值突出、基础广泛的民间非物质文化。基于此,对具有巫文化内容的艺术遗产,我们需要辩证地认识。
从特征上看,艺术性与奇幻性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巫文化最显著的特色。与巫术结合的艺术形态,一方面它具有人们喜闻乐见的表现形式,使人们能够从中(通过观赏或参与)得到美的体验;另一方面又因其浓重的巫术意味而直逼人心,给人十分复杂的心理体验与强烈的情感冲击。例如,在土家族的丧舞“撒尔荷”的表演中,亲友们对悲痛情绪的宣泄、对亡灵的怀念与守护、对死者未来的祝福等复杂的情感和心理期盼,都能够通过舞者(由巫师领导)艺术(美的)的祭祀仪式(舞蹈)得到淋漓尽致的表达。由于这种特殊的表演全方位地渗透了观者的视觉与心理,其带来审美体验往往超越了单纯的艺术表演或者是祭祀。而正是这一切使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巫文化具有了奇幻的魅力。所以,对巫文化遗产的艺术特征我们有必要认真把握。
时至今日,传统的巫文化由于分散零星地存在,得不到社会如同对宗教般的认可;由于其自身未形成理论体系,面临宗教势力的排挤;由于其非理性的行为方式,受到科学进步的不断质疑。这使得巫文化随着文明的不断进步,由曾经的“显学”逐步地沦为“遗产”。笔者认为,对环三峡地区巫文化遗产我们今天保护它的理由至少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看重它所蕴藏的时代信息有利于探讨人类文明的起源,且环境越封闭其信息价值越高;二是看重它在民风民俗及艺术形式上的精彩体现,这是人类历史时期精神与物质文明不断积淀的硕果;三是看好它在当今区域社会发展中可能起到的辅助作用,例如在推动地方旅游经济发展中,进行适度的巫文化展示有利于人们娱乐身心,感受并记住乡愁。
对巫文化遗产的保护应该是分类进行的。分类的依据则是它们的重要程度,而重要程度又是根据其价值确定的。对那些已经成了“化石”的巫文化遗产,因其具有历史证据价值,需要我们刻不容缓地进行抢救;对业已融入民俗及民间艺术形式、为人们喜闻乐见的巫文化遗产,要注意不同门类的协调保护并合理利用;对特色鲜明但不再具有普遍意义的巫文化遗产,要重点保护其原真性;对与封建迷信密切相关且缺乏积极内涵的巫文化遗产,也可以有选择地“立此存照”用作学术探讨,而不是简单地扬弃。
在保护原则上,可大致采取以下四种分类的方式:首先,“优先保护”类——主要针对濒临消失的巫文化遗产活化石如“茅古斯”等,实行优先保护,其巫术内涵和表演方式最为原始,保护其原生状态尤为重要。其次,“鼓励性保护”类——针对艺术形式特别突出、并且已经被民众广泛接受的巫文化遗产如土家族的“摆手舞”、苗族舞蹈“踩花山”等,予以传承保护,该类遗产将民族性、艺术性、生产性、社会性与巫术祈福融为一体,成为颇具代表性的区域文化。第三,“重点保护”类——主要针对具有特殊表现形式的巫文化遗产如“撒尔荷”等,它们的巫艺特征浓重,表现形式具有典型性,且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第四,“选择性保护”——对内容和形式一般的民间巫术,亦可从中筛选具有代表性的样本存留,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
在保护方法上,时至今日,我们对巫文化遗产的保护方法亦可以是多角度、多形式的。对那些受众少、即将消失的巫文化遗产,我们除支助其非遗“传承人”口耳相传外,更需要通过录音、录像建档的形式立此存照,实施抢救性保护,使古老文化不至消失;而对那些受众广泛、生命力较强,民族性凸显、艺术形式独特的巫文化遗产,则应采取主动性保护,相关部门可有计划、有组织地协调、支持其展示和传承。对有争议的巫文化遗产,亦可经专家协同鉴别,有选择地抽取样本进行保护研究。值得一提的是,在操作方面,全息3D投影、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技术建模等高科技的利用,极有利于远古巫文化场景的重构,通过拉近时空距离,达到使观众身临其境的效果,将传承介绍与欣赏娱乐融为一体,在有条件的地方不妨尝试。
综上所述,我们得出以下三点认识:第一,巫文化产生于原始先民对美好生活的期盼,是人类童年时代对世界与自身的认知,其文化特质受时代性的羁绊于今天已经很难与时俱进,其总体趋势的衰微使之迅速沦为需要我们保护的“遗产”;其次,巫文化仍是一种具有生命力的可持续文化,因其在漫长的岁月中已经渗透到了人类社会的乡规民约与喜闻乐见的各种艺术形式中,并以民风民俗的形式保留至今;第三,基于巫文化遗产深刻的内涵和丰富的表现形式,基于其在历史与文化传承方面的重要意义,我们有必要对其进行保护,而保护是需要分类的。总而言之,理性地认识、辩证地看待、有效地保护,此即我们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语境下,对环三峡地区巫文化保护应持的态度。
[1]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81.
[2] 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M].丁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3]J.G.弗雷泽.金枝——巫术与宗教之研究[M].汪培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4]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9.
[5] 张光直.艺术、神话与祭祀[M].刘静,乌鲁木加甫,译.北京:北京出版社,2016.
[6]宋兆麟.巫与巫术[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9:5-6.
[7] 何瑛.对巫巴山地巫文化遗产保护的理性探讨[J].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6):1-5.
[8] 向达.蛮书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62:260.
[9] 重庆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重庆宗教[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0:434.
[10] 宗懔.荆楚岁时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155.
[11] 邓晓.论巴人与“土船”[J].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5):87-92.
[12]山海经•海内西经[M].王斐,译注.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4:321.
[13]唐明哲.楚湘巫术类说//方培元.楚俗研究:第三集[C].武汉:湖北美术出版社,1999:65-66.
[14]蔡靖泉.荆楚巫风与楚辞文//方培元.楚俗研究:第一集[C].武汉:湖北美术出版社,1993:64-65.
[15]刘琳.华阳国志校注(修订版)[M].成都:成都时代出版社,2007:4.
[16]重庆市文化局.重庆民间舞蹈集成[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769.
[17]宜昌市文化局,三峡大学三峡文化研究中心.三峡民间艺术集粹[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624.
[18]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秭归县柳林溪遗址1998年发掘简报[J].考古,2000(8):13-22.
[19]本书编委会.中国美术全集第23集:原始社会至战国雕塑[M].图44.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14:26.
[20]司开国.曙光初照:三峡秭归的太阳神石刻[N].中国教育报,2010-7-24(4).
[21]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巫山县文物管理所.重庆市巫山县大水田遗址大溪文化遗存发掘简报[J].考古,2017(1):42-60.
[22]宦书亮.论巫文化视野下的三峡丧礼习俗[J].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11(1):9-13.
[23]孙美兰.艺术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72.
① 在“苏联乌兹别克的切舍-塔什洞发现的尼人小孩遗骸,头骨周围安放六对山羊角,排列成一圈,有的学者认为这表示产生了太阳崇拜的萌芽”(林耀华主编:《原始社会史》,北京:中华书局,1984:394)。
②1980年代中期,由文化部、国家民委和中国文联三家协作、组织编撰了中国民族民间文艺十部集成志书,其中包含民间文学方面的故事、歌谣和谚语三套集成,各涵地方卷。经20余年努力,于2009年全部出齐,被誉为民族文化的长城。
The Witch Culture Around the Three Gorges Area in the Context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DENG Xiao HE Ying
Witch culture is the cognitive product of human childhood and a worldwide primitive religious phenomenon. It has profound connotations and rich manifestations. Nowadays, witch culture from ancient times still has considerable vitality among the people. Apart from the limitations of people’s cognition, more importantly, it has been incorporated into folk customs and folk conventions to a considerable extent. The ancient witch cultural heritage should be understood rationally, treated dialectically and protected effectively. The methods of protection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categories: priority protection, encouraged protection, key protection and selective protection.
witch culture; around the Three Gorges Area; cognition; protection
K29
A
1009-8135(2018)06-0001-09
邓 晓(1956—),男,重庆人,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中外文化比较、区域历史文化等。
何 瑛(1963—),女,四川成都人,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文化遗产。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环三峡地区远古巫文化探究”(16XZJ002)。
(责任编辑:滕新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