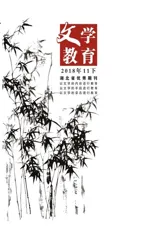《北鸢》形式与内容上的美学统一
2018-11-29郭磊
郭 磊
《北鸢》是葛亮历经七年完成的一部长篇小说,这篇小说极具文学想象力。小说以主人公卢文笙、冯仁桢的成长历程起笔,讲述民国时代的波诡云谲。以襄城商贾世家卢氏与没落士绅家族冯家的联姻为纬,采用工笔细描和泼墨写意相结合的叙述方式,鲜活地呈现出动荡年月中家族的兴衰、命运的沉浮、爱情的甘苦。在形式上,《北鸢》提供了一种新的语言范式,用经济的笔墨勾描人物和事件的神韵,而避免铺排渲染,从民间市井入手,用新的语言模式来表达传统元素,这给《北鸢》带来了形式美。在内容上,作者在传统符号的复兴化合以及重新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视角两个方面对中国的生存哲学和传统文化进行了审视和理解,带给读者不一样的内容美学感受。
一.《北鸢》的形式美
(一)北鸢的语言范式
葛亮的《北鸢》开创了新古韵小说的先河,小说通篇追求用经济的笔墨勾描人物和事件的神韵,而避免铺排渲染,这种写法是一种大胆的创新。
1.淡笔写深情
葛亮在写《北鸢》的时候,在语言的内在节奏以及语意上注重克制和留白,尽量将一腔深情用淡淡的笔触表现出来,留给读者去理解和体会,用王德威先生的评价就是“淡笔写深情”。葛亮的这种写法,让平凡的人物和生活也变得有滋有味起来。例如描写秀芬做饭的一段是用以下语句描述的:
“秀芬做饭的声音很轻,切菜都是均匀而细密的,不疾不徐,如蚕食桑。这些天他已熟悉这种声音,包括气味。秀芬喜甜,烧肉菜先熬糖,便有一股焦香,也是淡淡的。然而今天,都没有。”
这是《北鸢》中的一段日常描述,在这种描述中,参杂了作者的诗性,让人读起来有一种很舒服的诗的美感。者在描述的时候并没有刻意的去解释永安对于秀芬的看法的不同,但是通过这一段话,可以让读者读懂永安对秀芬的感情变化,从原来两个各有所图的人慢慢的熟悉起来,甚至知道了对方的做饭细节、做饭声音、做饭气味等等。在《北鸢》中,作者大量的采用了这种写法,虽然作者只是用了寥寥数笔,但是却将这种从各有所图慢慢变成爱情的感情一下子呈现出来1。
2.语言富有隐喻性
《北鸢》小说语言的另一大特色就是语言富有隐喻性。例如在“楔子”中,主人公卢文笙、冯仁桢以简单的对话将故事的引线拉开,并没有直白的进行平铺直叙,而是具有一定的隐喻性。“单传”的手艺,“净是外国人”的买家,“按老例儿”等等都可以说明《北鸢》语言具有一定的隐喻性。2
(二)《北鸢》的写作特点
1.围绕民国主题
葛亮受到了家庭背景的影响,所以其创作的的小说有很大一部分是围绕着民国主题来描写的,对写作环境的创设更容易让作者表达传统元素。围绕民国主题来写一方面可以更加方便的表达作者对于传统的追溯,也方便作者展示属于东方的独特的生存哲学。3《北鸢》是围绕着生活开写的,无非就是家长里短,但是作者在叙述这些家长里短的时候,用到了书画、民间曲艺、查到、饮食、服饰等等元素,通过对这些元素的描写,让小说中的人物更加有生活气息。而且葛亮在《北鸢》中描写了近百位人物,包括政客、商人、文人、军阀等等,这些人物因为对民国生活元素的描写栩栩如生,反映了在无常时代下的世道人心,俨然是民国版《红楼梦》的派头。
2.重拾古典传统
《北鸢》里面关于中国抒情美学和传统文化的描写非常的惹人注目,在很多方面都可以媲美一些成功的古代小说。葛亮强调的核心问题就是重拾古典文化。虽然在近几年的飞速发展中,让我们忽略了传统元素,但是我们却不能否认传统文化的魅力。葛亮的《北鸢》给我们敲响了警钟,让我们知道在飞速发展的过程中,还要注意传统元素的传承和发展。小说并没有局限于传统历史小说所设定的套路,没有抗战,没有杀戮,而是将家族的兴衰作为导线来阐述民间人们的生存,以及在生存过程中的日常传统。葛亮通过对这些日常传统的描写,激发了人们去探索精神文明的心里,让读者重新审视精神文明,重新去追索精神文明。4
二.《北鸢》的内在美
(一)传统符号的复兴化合
1.传统文化均的考究
新古韵小说善于化用中国传统符号,链接情节,传情达意,含蓄蕴藉。罗兰·巴特《符号帝国》认为,东方文化普遍重视符号、形式、过程,表达个人情致和灵魂,以达到理想的无言之境。5《北鸢》以民国时期襄城的民族资本家卢氏与士绅家族冯家的联姻为主线,刻写卢文笙的成长史,借家族史,书写近现代史的家国兴衰。风筝符号不仅是书名,而且是全书串珠,一路旖旎而来,不可或缺;且用大量典故,涉及“扎、糊、绘、放”四艺。不像明清人情小说只是以“珍珠衫、百宝箱”等为重要道具,《北鸢》的风筝符号隐喻丰富,带出主旨寓意,不可小觑,有结构串针、情感隐喻、哲理寓意等重叙事功能。
2.风筝结构抒情串针
《北鸢》每次写风筝,都选取独特的抒情时刻,见出独特的抒情自我。如写卢文笙与毛克俞谈画,引用葛亮在《北鸢》新书分享会上徐渭的《墨荷图》款识:“拂拂红香满镜湖,采莲人静月明孤。”论画谈文格调颇高,足可见葛亮艺术造诣,状物写景具画意美感;李欧梵认为,中国抒情从诗画传统演化而来,其特点在于抓取一个瞬间,将之变成比较永恒的境界和视野。全书的抒情笔墨像写意画作,诗画中国与血肉中国并叙,诗情与苦情同抒,叙述宛转,文辞优美,实与虚,意与境,相谐。6
(二)重新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视角
1.作家对历史的理解力和领悟力
《北鸢》有一种能使读者心甘情愿进入作品的魅力。这多半源于作品对一种物质真实的追求。许多资料都提到葛亮为创作这部小说所做的100万字资料储备。而小说对民国风物的信手捻来也的确印证了葛亮对民国日常生活的熟悉程度。试图从地理风物上提供切近历史的真实,这是历史写作中最为基础的一步。但更重要的是作家对历史的理解力和领悟力。《北鸢》没有满足读者对民国历史的某种阅读期待,事实上,它着意躲避了那种通过家族兴衰讲述民国历史的路径。它关注的是大时代环境中个人生存的心迹,个人命运在乱离时代面前的荒诞,人在变故面前的软弱和强大。
2.试图使历史漩涡中的个人成为个人
《北鸢》不追求历史叙述的整体性,不追求把人物放在群体中去理解,小说试图使历史漩涡中的个人成为个人。对“个人”的细笔勾描最终使小说呈现的是民国众生相:昭德、小湘琴、凌佐、毛克俞、吴思阅,每个人物的眉眼音容都是清晰生动的,人物遭遇也并没有八卦小报中的那么有戏剧感。名伶言秋凰是为了女儿而刺杀日本军官的;从军的文笙是被老管家灌醉背回来的,而不是自愿回到家族生活中;毛克俞的婚恋有阴差阳错也有半推就……那都是具体环境中人的选择,并不那么果断,也没有那么传奇。《北鸢》强调个人处境,强调的是时代背景下每个人选择的“不得不”。
两位民国青年站在江边看渔火点点,船已破旧,那似乎是停留在古诗词里的场景,但“民国、民权、民生”的大字却分明提醒人们,时代已远,民国已至;课堂上,年轻的文笙作画,为自己的风筝图起名“命悬一线”,那是华北受到入侵之际,也是万千青年的痛苦所在;但风筝图被老师毛克俞命名为“一线生机”后,同一图景因不同表述便多了柳暗花明之意,那也正是战争年代人们的心境写照。——历史事件就这样影响着个人的命运。
3.对民国人精神生活的勾勒
许多读者提到作品对乱离时代人与人之间情感的眷顾,那是时间长河中的“人之常情”,是推动人物命运的重要动力。父亲每年为儿子送风筝的嘱托,母亲为了女儿不惜尊严和生命的爱,毛克俞对吴思阅的深情一吻,仁桢顺着文笙手心慢慢划过的手指,以及两位青年人对永安儿子的郑重收养……但是,更让人难以忘记的恐怕是作品中对民国人精神生活的勾勒。
《北鸢》写出了我们先辈生活的尊严感,这是藏匿在历史深层的我们文化中的另一种精神气质,这是属于《北鸢》内部独特而强大的精神领地。一如陈思和先生在此书长篇序言中所评述的,《北鸢》是一部“回到文化中国立场”进行写作的小说,它重新审视的是维系我们民族文化生生不息的“民心”。
三.结论
经过由点及面的梳理分析,笔者发现,《北鸢》开辟新古韵小说,不讲男性英雄霸业,不讲神魔小说的求真求知历险;不是人情小说的对家族鼎盛时代衰亡的悼词和哀歌;而是古风人格与风格统一,承续孔孟儒家的向善传统,承续五四时代人的文学与平民文学传统,注重追溯民间精神、弘扬民众大义;崇尚自然和谐的性别关系,寻求男女相互尊重、对等的生存意义;既有史诗色彩,也继承了抒情传统,且抒情比重更大,文气更足;既传承古典因素,也开拓时代新变的因素。香港先锋小说多讲究形式的西化新奇,而《北鸢》却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朝中国古典看齐,因此在香港文坛更独树一帜。在当前弘扬传统国学的时代语境下,葛亮开拓新古韵小说可谓恰逢其时。由此牵引,未来,新古韵小说类型必将蔚然成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