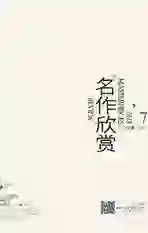历史本真性探询下的城与人书写
2018-10-20史倩文
史倩文
摘 要:葛亮的《朱雀》以其身处异乡的南京人的身份讲述南京故事,他笔下的南京记忆和南京人具有区别于其他作家的情感质地和民俗风韵。同时,作为新锐“70后”作家,葛亮书写历史的方式也是值得研究的课题。本文从南京叙事、宿命观等角度切入,探讨其小说的历史、人性场域以及对当代中国命运的思考。
关键词:葛亮 南京叙事 宿命
南京这座城市千百年来不断被言说,如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杜牧的《夜泊秦淮》、姜夔的《杏花天影》、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再到叶兆言的“夜泊秦淮系列”等,它不仅是一座地理意义上的城,而且是一座文化意义上的城。葛亮以其身处异乡的南京人身份讲述南京,使他笔下的南京记忆和南京人呈现出区别于其他作家的情感质地和民俗风韵;同时,作为新锐“70后”作家,从较早的《七声》到《北鸢》《朱雀》,葛亮试图在具备话语表征的“归属”指认上深入人性叙事的复杂场域,从而探讨当代中国的命运。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笔者认为,研究《朱雀》当中的南京叙事以及宿命观是对葛亮文学创作探索性的有效揭示。
一、南京记忆的复活
南京作为一座古都纵然长时间身处历史旋涡之中,但其古色古香、风情万种的底子还在,一如古船画舫、雕梁画栋的夫子庙,烟雨迷蒙中洗尽铅华、清新诗意的秦淮河。岁月终究只是斑驳了表面,城市的精神气韵是深入一草一木、一言一行中的。
《朱雀》中他如是形容程囡:“是江南老院儿里西厢房的竹帘子,轻轻掀开了一角,没待你向里头看个仔细,她倒先静悄悄地合上了。”①这里没有直接的描绘,却在读者的脑海中形成了一个江南女子娴静羞涩的形象。《北鸢》中写仁桢与文笙的相见:“半晌,她张一张口,终于开了声,说,我认得你。少年没应她,开始缓缓地收线。风筝在夕阳里浮动,好似一只墨色大鸟。周边的云,颜色红得重重叠叠,像是打翻的胭脂,氤氲开来。仁桢有些恍惚,觉得它在光的笼罩中,渐渐消失于血红的太阳里了。”②情境的描摹与简单的文字勾勒出两个讷于言却内心笃定的人物形象,如同传统的水墨画,用最简单的色调与笔法展现出一幅疏淡却意味无穷的画面。而在另一部以南京为背景的小说《儒林外史》中,有一节写两个挑粪的平民,卖完了粪,收拾了活计,就到永宁泉茶社吃一壶水,然后回到雨花台来看落日。里面的主人公就感叹:“真乃菜佣酒保,都有六朝烟水气。”
南京是一座雅与俗共存的城市,在江南烟雨的迷蒙中独具“萝卜气”,“大萝卜”也就是荤素咸宜的意思。“南京大萝卜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六朝人物精神在民间的残留,也就是‘菜佣酒保,都有六朝烟水气。自由散漫,做事不紧不慢,这点悠闲,是老祖宗留下来的。”③南京有一句民谚“吃辣萝卜喝热茶,气得大夫满街爬”,躺在澡堂的竹椅上,在雾气朦胧中喝上一杯热茶,吃上一根“心里美”大萝卜,一个悠长的嗝让整个人都释放了。作者笔下的南京女子不仅具有或疏雅或冷艳或柔媚的气质,还有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的精细与能干。例如程云和除却风尘之后,过起日子来也是一把好手,即使是最饥饿的日子也有油煎蜜枣与糯米粽叶的清香与风味;保温桶里的马兰头炒鸡蛋和腌西瓜皮清爽干净,吊足人的胃口。程忆楚与江一纬短暂的小日子也过得有滋有味,红枣山药糯米粥在钢精锅上咕嘟作响,慢火熬制,香气四溢。这座城市的女子让人留恋的除了烟雨江南的气质,还有生活深处的精细与情调。
二、人与城的宿命观
小说题名“朱雀”,在此具有双重含义。首先,朱雀是传统文化中的四象之一,屬火,代表南方。“早在东晋时期,朱雀已经浮出南京地表。当时秦淮河上建有二十四航(浮桥),其中规模最大、装饰最为华丽的就是朱雀航。朱雀航作为交通枢纽见证了世事繁华,往东便是乌衣巷,东晋最大的士族王、谢的府邸坐落于此。”④多年以后王、谢家族败落,繁华不再,唐朝诗人刘禹锡因此写下“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南京的命运似乎也同这诗句暗合,十个朝代相继在此建都,终究没能善终,“金陵王气黯然收”,随风一同沉入秦淮河的桨声灯影中去了,所以朱雀之于南京兼具地理与文化意义。其次,“朱雀”在文中具体指一个小物件,这一小物件既作为信物贯穿全书,同时也具有隐喻意义。许廷迈是一个具有南京血统的异乡者,贸然闯入这座城便为柜台里这只“金色的小雀”所吸引,关于这只朱雀的故事也由此展开。它历经三代人的手,记录了每一代人的爱恨纠葛,从南京城到北大荒再到遥远的北美,经历了时间与空间的双重迁徙,最终它的一双血红的玛瑙眼睛在洛将军的手中重见天日,而这正是洛将军年轻时在珠宝店当学徒满师之日亲手镶上去的。故事在这里达到了高潮,一切兜兜转转似乎又回到了原点,然而一切已经物是人非。几代人的命运通过这只小朱雀交缠在一起,关于这座城的宿命也在人的身上得到了体现。
“生活时时被残酷的现实所洞穿,露出脆弱的本质。这样的故事,剔除了传奇色彩,其实经常在你我的周围上演。它的表皮是司空见惯的元素与景致,温暖人心。然而,却有个隐忍的内核,这是谜底的所在。我不期做一个谜的破解者,只是尽力将谜面记录下来。”⑤例如葛亮早期小说《谜鸦》中那只黑色的、羽翼蒙着色泽的乌鸦“谜”,它就像黑暗中不可预知的旋涡,悄无声息地将人们拽向深不可测的黑洞之中。小说中弥漫着一股魅气,作者企图用一只乌鸦引发的悲剧来表现一股悄然酝酿的力量,这股力量改变我们的生活,并将我们推向岌岌可危的边缘,它是难以名状的却又真实存在的。到了《朱雀》中,葛亮延续了前面的宿命主题,在这里他赋予了宿命更清晰的轮廓。
叶毓芝为名门闺秀,气度袅袅,却在山河破碎之际爱上了日本人芥川,在民族大义、家族荣誉和个人情感间苦苦挣扎,最终选择忠于爱情,独自生下芥川的孩子。其女程忆楚容貌姣好、就读名校,本可以有一番大好前程,却因爱上有妇之夫江一纬放弃前途,并为其生下了女儿程囡。程囡同样也因袭了母亲与外祖母对爱情的执着,与外国间谍泰勒恋爱而被退学,后又与雅可情感暧昧,怀上了雅可的遗腹子。纵然时代背景不断变换,这三代女子为爱情而执着的态度却始终没有发生变化。《朱雀》以女子的传奇为主线,三代女子不断重复的命运构成了一种宿命的回环,作者也正是希望用这三代人重复的人生来阐明这座城市的个性与命运,如作者在书中所言:“这城市女人骨子里的烈是造成叶楚生对女儿多年教育毁于一旦的根源,这份烈,不见得个个都铆足了劲,要血溅桃花扇。只是平日里宠辱不惊的风流态度,就是极危险的汹涌暗流。”⑥表面上看起来疏疏淡淡,其实内里却有压不住的火热与倔强。南京这座城市上演了太多的兴衰荣辱,那些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积淀下来的繁华与颓败、绮靡与萧条、美好与挣扎、巧合与错失融进了普通民众的生活中、血液里,成了他们的集体经验。
三、伤城:南京大屠杀书写
葛亮笔下的南京记忆和历史之间的勾连常常发生一种对话关系,但是,葛亮并不陷入历史的局限之中为书写历史而结构故事,一种作为“局外人”的叙事视角,让他的文字中迸发出人性和历史碰撞的巨大张力。
南京大屠杀作为南京城的一段重要历史,作者没有直接描写它,而是选择了天主教堂这样一个特殊的空间来侧面描写。“《拉贝日记》《魏特琳日记》等一系列海外文献的发掘使得日本军队对中国人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以及西方一些留宁人士对中国民众的人道主义援助展露在世人的面前,也为新世纪以来创作南京大屠杀题材的作家们提供了新的素材与角度。在这里民族间的冲突与矛盾不再是主要的书写对象,战争、历史与人性成为重要的关怀对象。”⑦人性书写是葛亮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叙事场域中具有穿透力和反思深度的重要一环。
《朱雀》中秦淮名妓程云和在战火纷飞的混乱时刻隐藏身份避难于天主教堂,但是,为了搭救垂死的国民党军人,她不惜牺牲了自己的肉体。严歌苓《金陵十三钗》中的妓女赵玉墨同她的姐妹们同样也是牺牲自己、保全他人的例子,但两人的书写方式却有所不同。这群妓女刚出场时风尘味浓厚,与圣洁的教堂似乎格格不入,与女学生也常产生争端,但是,就是这样一群貌似低贱、自私的姑娘们却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人性的光辉在前后的强烈反差中展现,成就一曲悲壮的人性之歌。而《朱雀》中的程云和则始终以一种圣母的形象存在,除却她的身份,她的其他言行举止都被一股母性的光辉笼罩,所以当她看到那个身负重伤的小战士时,选择救护他而非抛弃他就变得顺理成章。作者以一种想象的姿态写作,书写他记忆中的南京城、记忆中的南京女子,他抓住南京女子美好的秉性选择性地进行塑造,使人物特点可以一以贯之。但是,这样写也并非毫无缺点,那就是容易使人物类型化和单一化。
四、多重视角下南京叙事的可能性
葛亮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南京“70后”作家,成年后外出求学并定居他乡,南京的血液流淌在他的体内,他有着言说南京故事的强烈欲望。王德威认为,葛亮的古老南京和青春南京的书写,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以看作一种“局外人”视角的叙事。同时,作为一位年轻作家,他并没有亲身经历过他所书写的那些历史,他想要抓住的是在这些具体史实下亘古不变的流动着的古老南京的精魂。因而,笔者认为,葛亮在《朱雀》中尝试了对某种历史本真性的探询和想象化的叙述,并保持了二者间适度的张力和平衡。
“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试图为城市寻找记忆的书写行为,必然是一种怀旧的想象行为,它是在传统即将消逝的时刻对记忆的追认,是一种现代人的怀乡病,同时也是一种重构传统记忆的方式。”⑧正如他不止一次在访谈中提到的关于历史叙事的问题,即青年人作为历史的不在场者,对于历史的叙述具有想象的权利。在他过去的南京书写中,南京或优雅,或沧桑,但逃脱不了的是悠久历史所带来的厚重感。陈晓明提出在多重文本中重建历史本真性,认为“总有那些作为‘历史生活的本真性的质素留存下来,历史却又并不是按其已经烂熟于心的格式来进行,而是被作家的主观意愿重新编排,历史的存在被作为一种对话的单元重新复活”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葛亮的《朱雀》是以个体经验为基础的、通过想象的方式对古老南京的一次追忆。历史在这部小说中,其实是作为背景而存在的。所以,与其说这部小说描写的是南京城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到20世纪末的历史,不如说是一部南京三代女性的历史,是一段被个性化和性别化的历史。
同样书写南京的作家还有叶兆言,他的“夜泊秦淮”系列小说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不仅详细地描写了南京城的风土人情,还有那些在动荡不安的岁月里展现出来的形形色色的人性故事以及精神症候。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都表现了“金陵王气黯然收”的颓败,但在这颓败之中还有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节屹立不倒。例如葛亮《朱雀》中的叶楚生宁愿生意受损也不愿接受日本人的帮助;叶兆言《追月楼》中的丁先生冷落日本学者,拒绝供职于日本人扶持的书院,并且登上了追月楼,发誓日本人一日不除便一日不下追月楼。叶楚生与丁先生都展现了民族存亡之际知识分子的民族气节,他们不屈服于金钱、权力,不屈服于日本人的淫威,这种精神不随南京城外表的颓败而改变,是浩荡千年中生生不息的东西。不过,二者的南京书写还存在许多不同。首先,葛亮是在异乡完成对故乡南京的追忆,他笔下的南京故事以及南京历史多是以一种想象的姿态存在,从而赋予了南京唯美浪漫的气息。而叶兆言是一位一直在南京本地笔耕不辍、记录南京故事的作家,他笔下的南京城揭去了朦胧的面纱,是较为真实的南京,有学者曾说:“叶兆言对十里秦淮,乃至对整个南京城市的兴趣,或许也不过是借助这个城市地理空间,探测复杂多变的人的内在世界。”j其次,相比于叶兆言具有挽歌情调的南京书写,葛亮笔下的南京城不仅是一座古老的城,有着老南京的风花雪月、历史沧桑、名士风度,同时也是一座年轻的城,融入了青春的底色以及后现代的浮华与躁动。《朱雀》中许廷迈与雅可是两个富有意味的形象:许廷迈是一个有着南京血液的华人,对这座城从陌生到熟悉再到深陷其中,这座城仿佛有一种“瘾”在吸引着异乡人;雅可是长于南京的桀骜少年,他不为金钱折腰,能大段背诵《规训与惩罚》,读《二十四史》《洛尔伽诗抄》,但同时他又吸毒、颓废。他们两个人阐释了当下的南京城,新的文明、新的生活方式、新的血液在不断地注入,精华与糟粕、坚守与颓废杂糅、共生。
此外,作者还有意设置了一些具有象征意味的画面,例如许廷迈和程囡在明朝皇帝的墓碑上做爱,泰勒充满仪式感地用南京的云锦包裹住身体和欲望,叶毓芝在黑暗中对着药柜上的辟邪神兽犀利的眼神而沉沦等,他们都是葛亮记忆里南京城的代表,西方与东方、古老与现代融合在一起。每一座城都会有自己的言说者,每一代人眼里的同一座城也都有着变与不变。葛亮的《朱雀》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属于“70后”作家、属于异乡人的南京记忆:它历史悠久、古朴厚重,它雅俗共赏、人与城共荣共生,它贯通古今中西、唯美浪漫、依旧年轻。
af 葛亮:《朱雀》,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9页,第79页。
b 葛亮:《北鸢》,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45页。
c 葉兆言:《南京人》,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55页。
d 王德威:《归去未见朱雀航——葛亮的〈朱雀〉》,《当代作家评论》2010年第6期。
e 葛亮:《谜鸦》,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页。
g 孙正飞:《新世纪南京大屠杀小说书写视角的转变》,《百家评论》2017年第2期。
h 陈平原、王德威:《北京: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40页。
i 陈晓明:《“历史化”与“去历史化”——新世纪长篇小说的多文本叙事策略》,《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
j 曾一果:《叶兆言的南京想象》,《上海文化》200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