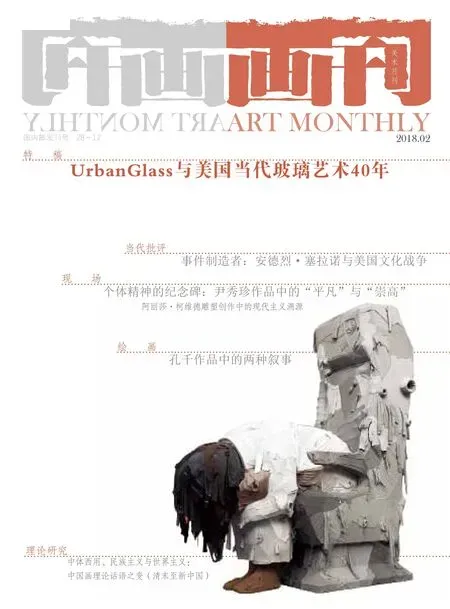中体西用、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中国画理论话语之变(清末至新中国)
2018-11-29盛葳ShengWei
盛葳(Sheng Wei)
什么是“中国画”?“中国画”的美学标准是什么?“中国画”的边界在哪里?如何进行“中国画”的传承和创新?诸如此类话题被清末以来至今的艺术家和艺术批评家反复讨论。其根本和核心议题是中国遭遇全球化、国门洞开以后,在国家和社会文化现代转型过程中遭遇的“中西”问题和“古今”问题。尽管后者是中国画史画论中的固有命题,但在19世纪下半叶以来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它又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古今”问题,而是转变为与“中西”问题直接关联的现代问题。因此,这个层面上的“古今”问题,实际上是“中西”问题的附属和延伸。历史地看,这两个核心问题所涉及的具体内容虽然在不同时代具有差异,而且表现方式也不尽相同,但在近现代,总体说来具有统一性和连续性。然而,尽管如此,讨论这些问题的理论话语却并不总是统一的。相反,它们发生过数次大的范式转型,而且,每一次转型都与现实语境和思想潮流的转变有着极其密切的关联。因此,本文试图从艺术史、社会史、思想史三者的交错视角中来看待近代中国画理论话语之变及其基础与成因。
在通常的讨论,甚至学术研讨中,“中西”问题、“古今”问题,常常容易被“本质化”:中国是中国,西方是西方,似乎这是两个相互隔离、完全不同的东西。但借助于福柯(Michel Foucault)和赛义德(Edward Said)的观念来理解,它们并非“本质主义”的,而是在历史中被各种不同的权力话语所建构起来的。这为讨论中国画的理论话语提供了基本的支持。“体用”是近代以来中国人试图认识和解决“中西”问题和“古今”问题的最初理论框架,同样也常常被人们“本质化”。然而,“体用”真的是一种基于“事实”的描述吗?一定必须是某物为“体”、某物为“用”?其实不然,“体用”远不是公理,而是一种哲学意义上的认识论;换言之,是我们(主体)使用了“体用”的概念和范畴去认识和理解需要讨论的“对象”。因此,“体用”本身并不是“事实”,而是认识现象的“方法”。它既不是真理,亦不唯一。譬如,19世纪的中国人不需要用同样的思维模式和认知框架去理解欧洲世界,而同时代的欧洲人也不可能用“体用”这对范畴或类似范畴来理解我们所指的同样现象。概因立场不同、文化不同、语境不同,导致所选择的理论话语也不同。
甚至在当时中国国内,也未必是全体中国人都使用“体用”理论框架来对“中西”问题进行认知,这对范畴的使用主体主要是官方和民间“自强运动”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对于他们而言,这是一种认识和解决“中西”问题相对贴切的“观念”和“方法”。对于“自强运动”之前及其早期的保守力量来说,“体用”问题根本就不存在,它既不是一个“事实”,也不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因为对于他们而言,唯一的正途可能是“中体中用”。但如果“体”和“用”都围绕“中”进行,那么,区别“体”、“用”就缺乏实际意义。在绘画领域,传统意义上的“古今”问题自宋代以来就有一套完整的系统来应对和处理,而泰西画法尽管明代就传入了中国,但并不与中国画形成冲突,故尚不存在“体用”层面上的“中西”问题。年希尧所著《视学》成书于清雍正朝,在郎世宁的指导下,他完成了中国第一部西法透视专著。年希尧的看法具有代表性,如同该时代许多评价一样,他认为中西绘画各有所长,并不需要厚此薄彼。究其原因:一则年希尧并非科考出身,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文人士大夫,故无需固守中国儒学之本;二则绘画并未被提升到文化核心中讨论,尤其是西洋画,尚属“奇技淫巧”,中西绘画远未到文明冲突、抵牾或需要合二为一之时之境。
邹一桂是年希尧同时代人,雍正朝进士,翰林院编修,官至内阁大学士,是标准的上层儒学文官,其《小山画谱》约成书于乾隆二十一年(1756),则能看出与年希尧之异同。年希尧醉心西法30年,肯定中西画法各有擅长。而邹一桂尽管也看到西法部分技术特点,但就美学层面而言,他对西法持否定态度,而且,这与前人对西洋画“阴阳之法”、“奇幻之术”在器物层面上的批评有着本质的不同。《国朝画征录》的作者张庚,职业画家,雍正朝应鸿博诏,亦是前二者同代人,他评价康雍朝画家焦秉贞所习西洋画法“得其意而变通之,然非雅赏也,好古者所不取”[1],其美学层面的价值观立场与邹一桂接近。但值得注意的是,邹一桂的评判标准在“中”,而张庚的评判标准在“古”——换言之,在艺术史内部。然而,他们的结论仍具有强烈的一致性,预示了在不久以后“中”、“古”的价值统一,并与“西”、“今”这另一价值统一的尖锐对立。
从上述三篇同时代文献的对比来看,尽管有所不同,且其理论话语主要是传统意义上的“华夷之辨”、“夷夏之辨”,但同时也具有向“体用”转移的趋势与可能。但是,处理“中西”问题和“古今”问题的基本理论框架均尚未直接和正面涉及“体用”之争:西洋画在艺术的系统之外,并不是系统之中,更重要的是,尚没有将其纳入本系统的必要性。“体用”仅仅是当我们需要着手解决将西方知识纳入中国古代知识系统内部时才需要面对的问题。直到同光时期,中西矛盾空前激化,无法调和,才变得具有共识性。因此,“体用”之辩在晚清呈现复兴之势,所涉领域则由此前的哲学义理向社会历史扩展[2]。甲午战争后,无论是洋务派、革命派,还是儒学清流,习洋务已是朝野共识。“体用”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和这一背景下开始成为处理“中西”问题的主要理论框架,其特点不倾向于义理层面,而是注重经世致用,这使得“体用”之争能够被社会政治和几乎所有学术门类所借鉴。
在朝堂之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同光之际曾任军机大臣的冯桂芬的“中体西用”论。在精英阶层、社会和学术层面,张之洞则是“中体西用”论的集大成者,影响广泛且深远。作为时代思潮,康有为、梁启超在学术思想上与张之洞颇为相似。这些“中体西用”论在学术和文艺的革新之路上直接指向两点:其一是“返本开新”,以固中学之根本;其二是“中西合璧”,明确“西”与“新”的直接价值关系。而他们关于艺术的看法,也大抵如此。康、梁认为当世绘画“衰敝极矣”[3]、“价值极微”[4],故亟须变革,发展方向也与学术与社会层面类似。在“返本开新”方面,康有为在“托古改制”、“维新变法”的学术和社会改革原则指导下,提倡对绘画及其理论“正其本,探其始,明其训”。他认为“今欧美之画与六朝唐宋之法同。惟中国近世以禅入画,自王维作《雪里芭蕉》始,后人误尊之”,故需“以复古为更新”[5]。在他看来,与儒学经典“作伪”相似,作为“标准”的二王书法帖学代代临习,今已“面目全非”,故需正本清源,“不得不尊南北朝碑”[6]。梁启超则将清代200年学术史概括为“以复古为解放”[7]。在“中西合璧”方面,张之洞明确在“中”与“旧”、“西”与“新”之间建立起价值统一关系,康有为则希望“合中西而为画学新纪元”[8]。梁启超也认为需要对西方美术“采纳之而傅益以己之遗产,创成新派”[9]。
从康、梁的思想以及处理艺术问题的理论框架来看,显然与前人有了本质的不同,他们自觉地使用了“体用”的范畴来认识绘画和解决绘画所遭遇的当代难题。但很快,在“体”的层面,发生了从“中”到“西”的更迭。“中体西用”在甲午以后不久,已经面临破产;因为,所谓“中学”,已然有名无实。譬如,钱穆就认为当时“已届学绝道丧之际,根本就拿不出所谓‘中学’来”[10]。同样,在绘画领域,按照传统价值和美学标准审视,出众者亦是寥寥无几,甚至“体用”理论框架本身也开始逐渐被摒弃。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1902-1904)发表之时,该理论框架仍对梁启超有效;但在《清代学术概论》(1921)出版前后,梁启超则对“中体西用”论点进行了否定。随时代之变化,在很多领域,“中”和“西”已经交融,无法割裂为二元,因此,用“体”与“用”的传统哲学范畴来进行二元的对应处理已然不再有效,对新出现的社会和政治现象,更无法应对。但是,绘画实践不同于社会和政治只能有唯一发展的选项,而是具有大致统一方向之下的多种可能。中国画“衰敝极矣”业已形成共识,其“边界”问题和“标准”问题亦被鲜明地标示出来。“中体西用”框架下的“返本开新”和“中西合璧”依然具有一定作用,且对至今的中国画发展具有影响。
在宏观的社会层面,尽管严格意义上的“体用”已不再有效,但其意义却并未完全丧失。随着时代的发展,在理论话语断裂的同时,其内涵也具有一定程度上的连续性。但“体用”之争及其所面对的问题,逐渐被转化到“民族主义”(Nationalism)和“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辩证统一的理论话语体系之中。从社会历史的角度看,这有赖于中国国家性质的现代转型及其观念在全社会的普及。列文森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将这一转型描述为“从天下到国家”的进程[11],这种看法代表了史学界的主流。在年希尧、邹一桂、张庚所处的清中期,“天下”观念仍是主流,“中西”意义上的“体用”问题尚未浮现。在张之洞、康有为、梁启超所处的清晚期,“天下”观所昭示的古代东亚“政治秩序”——宗蕃朝贡体系——被逐渐打破,与西人短兵相接,国家性质的现代转型也呼之欲出,“体用”之争故而凸显,中国画之变革亦因此被提上日程。而当民国初建,“天下”荡然无存,中国作为现代国家的转型已是大势所趋,即将成为事实。那么,处理中国画之变的理论话语也由“体用”迅速转变为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辩证统一。
中国画在观念和实践两方面的民族意识诞生于清中期至清末的固“中学”之本,明确和昌盛于清末至民国的现代国家转型。其关键一环在于现代国家的主体,即“民族”的确立,以及民族认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产生与普及。梁启超思想路径的变化不仅显示了这一变化,更是这一意识形态转型的重要的理论创建者和推动者。他创造了“中国民族”(1901)[12]和“中华民族”(1902)的概念[13],并通过“国族”开启了在“国家”意义上使用“民族”概念之先河(1902)[14]。在20世纪的前20年,民族主义在全中国的各个层面影响渐大,并逐渐成为一种“事实”,从而对社会政治与文化艺术产生了强烈的凝聚作用,尤其是在民国建立以后,以“中华民族”为基础的现代中国民族主义更是成为建立新型国家的重要依据和基础。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提出:“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15]
中国画家和理论家同样置身于这样的社会思潮中,而且,正是在此基础上,“中国画”在20世纪的前20年开始广泛地在“民族”意义上被使用[16]。尽管这一概念是因明代传教士为区分西洋画而创造的,但在此时,“中国画”概念的自觉使用已经不再仅仅是技术风格上的差异区别,而是具有了特定社会政治及其框架下的美学内涵,并深烙于中国画的“边界”和“标准”问题上。不仅如此,对现实的认知同样也构成了重建其历史的当代视角和话语基础;反过来,历史的重塑又不断加强着“中国画”的当代民族内涵,为这一事实获取其历史合法性。这有赖于史学和史学理论的转型以及对现实的影响。梁启超正是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开创者,而新史学最重要的当代视角,正是新兴的民族主义。在梁启超的史学理论中,艺术的位置被极大提升,成为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具体的历史认识中,艺术史也超越了传统纪传体的评品框架,采用了与新史学相似的西方进化论的史学视角,加之其民族主义史学价值观,现代意义上的中国艺术史的观念和叙事由此改变。从民国初创到20世纪20年代,中国艺术史学完成了现代转型,第一本中国人所著的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美术史作者姜丹书在《美术史》(1917)开篇中,阐明了其著作的“国民”基础,其性质则是“研究美术之源流与变迁、盛衰与性质之专门史”[17]。
在西方美术史的介绍方面,这样的历史逻辑就更加顺理成章,譬如吕澂所著的《西洋美术史》(1911),它们甚至定义着中国美术史的理论框架和书写方式,尤其是日本的近代国家和学术研究理念,从甲午至20世纪30年代,都深刻地影响到中国的文化和艺术。甚至康、梁本人,其思想也在逃亡日本期间发生了巨大转变。吕澂早年就东渡日本学习,而稍晚傅抱石、丰子恺写作的美术史也与之相似。滕固亦曾留学日本,并受梁启超影响,于1926年出版《中国美术小史》,具有强烈重塑民族文化的目的,他对中国古代美术的分期亦与新史学实践类似。《中国画学全书》的作者郑昶亦直言不讳:“我国画感人之深,其于民族问题上的意义,或较任何正知作用为重且大也。”[18]新史学或者新艺术史学,几乎都鲜明地以民族意识作为基础,这并非是一种完全主动的行为,而是在与西方,尤其是与日本的互动中形成的。一方面,在以西方为师的过程中,西方以正面的方式促进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形成;另一方面,国家和民族的对抗特别是战争,逼迫中国民族主义的更快发展,以及向社会和所有学科的蔓延。
因此,可以说,现代民族主义从根本上来自于西方。从这个意义上看,现代民族主义自身就是世界主义的一部分,二者具有统一辩证的理论关系和现实趋势。近代中国的世界主义绝非传统意义上的“天下”,康有为的《大同书》尽管借鉴了《春秋》公羊“三世”说、《礼记·礼运》“小康”、“大同”之说,但究其实质,也与其学术上的“托古改制”相似,是用中国传统学说包装西方思想。这一思想与西方从古至今的“乌托邦”思想一脉相承,远追柏拉图的“理想国”,近及康德的“永久和平论”。世界主义尽管来源于社会现实,而且也致力于社会现实的改变,但它仍然是一种理想主义,而非社会政治与文化艺术实践的现实指导。梁启超的早期世界主义观来自于老师康有为,其后又随世界与国内时政的变化而调整。在1899年的《答客难》中,他试图调和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但他此时的世界主义是理想主义的,而当时中国的主要问题则是国家主义:“世界主义,属于理想,国家主义,属于事实;世界主义,属于将来,国家主义,属于现在。今中国岌岌不可终日,非我辈谈将来、道理想之时矣。”[19]
1919年一战后,梁启超遍游欧陆,从而将观看立场从中国转变为全球,这对他的世界主义观念带来了极大的改变。一战及其结果深刻地震撼着他,国家间的世界大战破坏了整个欧洲,民族主义带来了更多国家的独立自主,同时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密,是为世界主义,但西方却一蹶不振、前途堪忧,故需“新文明之再造”。在记录其观感的《欧游心影录》中,他谈到世界局势时说:“19世纪后半期欧洲民族运动史,总算告一段落……总算人类社会组织一进步……虽然理想的国际联盟,未见完成,国家互助的精神,已是日见发达,质而言之,世界主义,要从此发轫了。”[20]对于孙中山而言,中国的前途依然必须基于民族主义,因此而反对世界主义。因为,在他看来,世界主义就是帝国主义:“世界上的国家,拿帝国主义把人征服了,要想保全他的特殊地位,做全世界的主人翁,便是提倡世界主义,要全世界都服从。”[21]但孙中山并不是在普遍意义上反对世界主义,而是基于中国在当时全球政治秩序中的地位,尤其是一战结果和巴黎和会上中国的遭遇,以及在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下来谈论世界主义的,在更普遍的意义上,他与梁启超的观点并没有本质冲突,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是统一辩证的:“把从前失去了的民族主义从新恢复起来,更要从而发扬光大之,然后再去谈世界主义;乃有实际。”[22]与此同时,蔡元培、胡适、陈独秀、戴季陶等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则更注重世界主义的积极方面。
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的出现几乎是同时的,世界主义的流行略晚于民族主义,但大抵是在20世纪的前20年。这一时期,中国更广泛地被卷入到全球化进程之中,清帝逊位、民国建立、参与一战,中外人口流动、文化往来,都是直接结果。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统一辩证的社会政治话语也鲜明地投射到艺术领域,对中国画的理论话语产生了极大的直接塑造作用,成为处理中国画的主要框架,而在这一框架中,世界主义又占据着一定的优势。1914年,蔡元培与李石曾等筹办《学风》杂志,在发刊词中,他认为今天是一个“全世界大交通之时代……全世界之交通非徒以国为单位,为国际间之交涉而已……而其最完全不受他种社会之囿域,而合于世界主义者,其唯科学与美术乎(科学兼哲学言之)!”[23]。而且,还从历史上将中西的艺术互动,尤其是古代中国文化对西方的影响,追溯到古代,从而建立艺术之世界主义的历史合法性,“故曰:科学美术完全世界主义”[24]。
继而,“美术革命”的争论又印证了蔡元培的判断。吕澂在1918年《新青年》上发表了《美术革命》,他所言革命的对象并不是单一的某家某派某类艺术,而是传统美术之衰敝、西画东输之艳俗的中国现实。故需阐明若干事实,从而让“社会知美术正途所在”,最终达到“美育之效不难期”的目的[25]。不难看出他对前一年蔡元培倡导美育的呼应,但他的论述尚缺乏蔡元培基于全球的宏观视角,而是更注重艺术的现实社会功效。而同期刊登的陈独秀同名评论《美术革命》则直接将论点引向了“革王画的命”,“采取洋画的写实精神”来“改良中国画”[26]。一方面,他对中国画的看法与康有为相当接近;但另一方面,他主张用写实来改造中国画则是世界主义的实践,而非“中体西用”的结果。在该文发表的前一年,他曾在答陶孟和关于世界语问题时,对其“将来之世界,必趋于大同”的论点“极以为然”[27],世界主义是全球的未来趋势,他对中国画发展前景的判断正是基于此。
无论是梁启超、蔡元培、陈独秀,还是徐悲鸿,均怀着“科学化的美术”[28]、“用科学方法以入美术”[29]之希望。当然,倡导世界主义者并不是铁板一块,并不一定都赞成科学写实的西方古典艺术。汪亚尘对“传习的艺术”的批判,不仅包括“我国近几百年的画家”,也包括“全世界学院风(Academy)的作家”[30]。他的看法具有一定代表性:“艺术是具有世界性的东西,既没有界限,也不可固守……我以为往后不妨采用西洋艺术上的学理,以救时弊”“习洋画的人,就负有革新中国画的责任”[31]。只不过与徐悲鸿不同的是:他所倡导的“革新中国画”的参照对象主要是西方正流行的现代派艺术。但无论是徐悲鸿,还是汪亚尘、刘海粟、林风眠、庞薰琹、倪贻德,在融汇东西方艺术的观点上,依然是接近的。
中西艺术之辩被置于了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的辩证统一框架中讨论,尽管不同论者偏重不同,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调和主义占主流,绝对主义的论点非常罕见,且难以产生社会影响和舆论效应,譬如陈衡恪、胡佩衡、金城、黄宾虹、姚茫父的论点无法引起广泛的社会和学术共鸣。在今天艺术界认为的复兴更古老传统以入画的吴昌硕,在当时却也少见被艺术史和美学方面所认可。吴昌硕未被作为理论上的重点予以放大,问题并不在于他未遵从古代的经典和美学标准,而恰恰在于他太遵守这样的规范——尽管对于他而言,与对于必须被革命的“四王”而言,“传统”可能完全意味着不同的东西。但这说明,评判艺术自身的根本标准发生了变化。无论是民族主义,还是世界主义,美学标准已经显而易见地转变为一种全球共通的标准,而“美术”自身被提升到文化领域如此高的地位,也说明美术的实质已经现代化,成为现代社会结构中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譬如,周鼎培在《世界主义和国画》中将“美”看作艺术的本质,“环境和民族性的殊异”造成了“美的认识”和“艺术表征”的不同[32]。不难看出,在他看来,艺术的本质具有世界普遍性,但艺术的现象却在不同环境和民族中有所差异,因此,从根本上而言,艺术是世界主义的。
美学转向世界主义,实际上改变了艺术的根本理论和评价标准,无论是科学写实也好,现代派也好,乃至宋画、“四僧”、“扬州八怪”,实际上已经在新的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辩证框架中生效。这些标准不仅针对当时艺术创作的现实有效,而且也有效于艺术历史的重塑和改造,从而为“西”和“今”统一的价值寻找到了在中国艺术历史中的合法性,也为它们的当代现实和未来发展寻找到了依据:对于倡导写实的艺术家和评论家而言,可以从宋代院画着手;对于提倡现代派的艺术家和评论家而言,则可以从清初“四僧”、“扬州八怪”着眼。历史正是通过这样被改写、被重新评估,从而建立起中国古代艺术与西方现代艺术之间的关系,亦重新发现和定义了中国画“固有”的美学和形式特点,为未来之发展扫清了理论障碍。从话语的角度而言,二者亦可理解为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之辩证,并最终指向一种融合中西之后的具有全球共时性的新艺术。但是,正如之前所述,艺术领域的世界主义同样是一种理想主义,远非现实的实践策略。从艺术评论的主流来看,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之关系的性质在这一时期相对稳定,但此消彼长的强弱差异却随历史和社会事件有所变化。
在民国初创期,因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之需要,民族主义的趋势体现得更加鲜明;在一战以后至20世纪30年代,欧洲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充分暴露,为寻求解决之道,尤其是重建新的全球秩序,世界主义显示出更光明的前途,并在中国社会和思想界产生了广泛影响,艺术界亦无能例外。但在30年代以后,随着中日关系的恶化,并最终诉诸战争,激发了国内民族主义的新高潮。在社会政治方面,体现为国共第二次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这种趋势也同样鲜明地投射到中国画的创作和研究中,成为支配性的理论话语。如郑昶在1934年就写道:“国画已受世界文化侵略之压迫,宜速自觉而奋起”;“‘艺术无国界’一语,实为帝国主义者所以行施文化侵略之口号,凡我陷于文化侵略的重围中的中国人,决不可信以为真言,是犹政治上的世界主义,绝非弱小民族所能轻言侈谈也”[33]。
这造成了潜伏在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之间分离趋势的突出。在清末民初,世界主义是一种抽象的理想主义,这使得它能够被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嫁接到民族主义中;而在20世纪30年代,世界主义不但在社会革命的政治实践中被具体化,而且还随着革命进程的高涨而在全社会被普遍化。这一在30年代开始逐渐明晰化的倾向肇始于20年代的新文化运动,而在40年代以后的社会主义革命中被不断强化,并在新中国成立后达到高潮。汪晖在《文化与政治的变奏:一战和中国的“思想战”》中描述了《东方杂志》与《新青年》之间关于世界局势、文明差异与中国前途的论战。这一论战发生在对欧洲一战及其后果进行反思的基础上,中国从前所效仿的西方形象轰然坍塌,这意味着中国的发展丧失了原有的参照系,因此,中国之前途成为了讨论的中心。相较于杜亚泉等从中国古代传统、中国现代状况进行“接续”[34],陈独秀、李大钊更倾向于着力欧洲的最新思想、“超西方”的解决方案,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吸引了他们,而俄国革命的胜利又为其吸引力增加了分量。因此,从流行思潮看,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世界秩序,被跨国家、跨文明的阶级联合所取代。这是一种具体的、全新的世界主义——国际主义(Internationalism),它具有强烈的政治实践色彩和前途,有别于此前抽象的、理想主义的世界主义精神。循此路径,中国经由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而国际主义亦在中国生根发展。50年代,新国画运动和彩墨画的实践,都是国际主义的直接产物;而民族主义则相对被压制。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对立与辩证的新理论话语开始取代既有的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理论框架,成为新时代中国画的主题,一直延伸到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甚至对今天艺术批评家的判断也造成了影响。
注释:
[1]张庚:《国朝画征录》,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1年版,第59页。
[2]杨国荣:《体用之辩与古今中西之争》,《哲学研究》,2014年第2期,第36页。
[3]康有为:《万木草堂藏画目》,郎绍君、水天中编:《二十世纪中国美术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99年版,第24页。
[4]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23页。
[5]同[3],第21-22页。
[6]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艺林名著丛刊》,北京:中国书店,1983年版,第4-5页。
[7]同[4],第9页。
[8]同[3],第25页。
[9]同[4],第129页。
[10]钱穆:《国史大纲》(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900页。
[11]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7页。
[12]梁启超:《中国史叙论》,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1页。
[13]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9页。
[14]梁启超:《新史学》,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1页。
[15]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二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页。
[16]水天中:《“中国画”名称的产生和变化》,贾方舟主编:《批评的时代:20世纪末中国美术批评文萃》(卷一),南宁:广西美术出版社,第101-107页。原载《美术史论》1985年11月刊。
[17]姜丹书:《美术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第1页。
[18]郑昶:《中国的绘画》,郎绍君、水天中编:《二十世纪中国美术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9年版,第351页。
[19]梁启超:《自由书·答客难》,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9页。
[20]梁启超:《欧游心影录》,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9页。
[21]孙中山:《三民主义》,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九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16页。
[22]同[21],第231页。
[23]蔡元培:《日英联盟》,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一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61页。
[24]蔡元培:《〈学风〉杂志发刊词》,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一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35-336页。
[25]吕澂:《艺术革命》,郎绍君、水天中编:《二十世纪中国美术文选》(上卷),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9年版,第26-27页。
[26]陈独秀:《艺术革命》,郎绍君、水天中编:《二十世纪中国美术文选》(上卷),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9年版,第29页。
[27]陈独秀:《(与陶孟和)通信》,《新青年》(第三卷第六号),1917 年8月1日,第4页。
[28]梁启超:《美术与科学》,郎绍君、水天中编:《二十世纪中国美术文选》(上卷),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9年版,第97页。
[29]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上的演说》,郎绍君、水天中编:《二十世纪中国美术文选》(上卷),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9年版,第37页。
[30]汪亚尘:《为治现代艺术者进一言》,郎绍君、水天中编:《二十世纪中国美术文选》(上卷),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9年版,第101页。
[31]同[30],第104页。
[32]周鼎培:《世界主义和国画》,郎绍君、水天中编:《二十世纪中国美术文选》(上卷),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9年版,第146页。
[33]同[18],第351-352页。
[34]杜亚泉:《接续主义》,汪晖:《文化与政治的变奏:一战和中国的“思想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43-1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