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香玉版《花木兰》折射之豫剧审美镜像
2018-11-28白宁
白 宁
豫剧是流播地域广、拥有广泛欣赏群体的戏曲剧种。在从河南梆子向豫剧的发展过程中,其艺术呈现始终带有浓郁的方音、语调、土腔等初始性音乐印记,这使得豫剧在众多北方声腔中,能够彰显鲜明的艺术个性。20世纪50年代创作并由表演艺术家常香玉主演的《花木兰》,是在传统剧目基础上整理、加工的豫剧作品,以丰富的音乐内涵和声腔演唱提升了豫剧的艺术表现力,可以说,这是豫剧在成熟形态下的巅峰之作。虽然常香玉先生辞世多年,她主演《花木兰》的影像资料,仍然是豫剧演唱学习与审美研究的范本。如果将常香玉版《花木兰》比作一件艺术瑰宝,从演唱审美的角度进行分析,那么,可以找寻出这部作品所折射的北方梆子腔的音乐特色、地域方音态的演唱吐字、圆融贯通的用声技法、“本色化”的戏曲审美等多棱的艺术镜像。
一、 多种地域性声腔的滋养与“本我”的坚守
《花木兰》搬上豫剧舞台时,音乐主体是河南梆子,也有意识地从其他北方声腔中汲取营养,1957年出版的由河南豫剧院整理的《花木兰豫剧(剧本与曲谱)》序言说:“常香玉同志首先用豫剧的形式搬上了舞台。在她的唱腔中也吸收与融合了‘河南曲子’‘坠子’‘河北梆子’‘大鼓’等曲调,更加丰富了它的表现能力。”(1)河南豫剧院编《花木兰豫剧(剧本与曲谱)》序言,河南人民出版社,1957年。为什么豫剧音乐在已经相当成熟的情况下,仍然从其他地域性音乐中吸取营养?这缘于豫剧本身就是由多种地域性民间音乐融合而生养成的声腔,兼容并包是豫剧音乐的基本属性,而在吸纳与融合过程中,又始终保持自身的“底色”。正因为如此,河南梆子形成的历史虽然不算很长,却能在二百多年的发展中创造出瞩目的艺术特色。
(一) 土腔、土曲、土戏是豫剧音乐的源头之水
豫剧的前身是河南梆子,20世纪20年代,已开始以“豫剧”来称呼河南梆子,20世纪50年代初又正式赋名。河南梆子形成初期,从多种外来声腔及本地土腔中汲取营养。这里引用几则清代史料:
徐大椿《乐府传声》论及北曲时说:“若北曲之西腔、高腔、梆子、乱弹等腔,此乃其别派。”(2)(清) 徐大椿《乐府传声》,载《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七),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第157页。
李调元《剧话》提到:“女儿腔亦名弦索腔,俗名河南调。音似弋腔,而尾声不用人和,以弦索和之,其声悠然以长。”(3)(清) 李调元《剧话》,载《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八),中国戏剧出版社,1960年,第47页。
钱泳《履园丛话》记载:“梨园演戏,高宗南巡时为最盛,而两淮盐务中尤为绝出。例蓄花雅两部,以备演唱,雅部即昆腔,花部为京腔、秦腔、弋阳腔、梆子腔、罗罗腔、二簧调,统谓之乱弹班。”(4)(清) 钱泳《履园丛话》,述德堂本,“清代史料笔记丛刊”,中华书局,1979年,第332页。
清代初中叶,京腔、秦腔等多种声腔兴起并多有流播,当时统称“乱弹”,其中弦索、梆子、罗罗腔后来成为河南梆子的早期音乐来源。地处中州,连接南北、东西交通的开封,多种声腔集聚,一些乾隆年间史料记载了当时开封及附近地区的戏曲声腔演唱。
乾隆五十三年(1788)修《杞县志》之《风土志》记载:“愚夫愚妇多好鬼尚巫,烧香佞佛,又好约会演戏,如逻逻、梆、弦等类,殊鄙恶败俗。近奉上宪禁,风稍衰止,然其余俗犹未尽革。”(5)(清) 周玑篡修《杞县志》卷八,“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485号,影乾隆五十三年刊本,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第496页。(案,笔者句读)这与此前乾隆十年(1745)修《杞县志·风土风俗》记载基本相同。杞县,清代为开封府属县。虽然《杞县志》对地域性声腔持贬斥态度,但可从中见知这些声腔的历史存在。
约成书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的李绿园章回小说《歧路灯》,敷演发生在开封的故事,虽然人物、事件、情节是虚构的,但反映的社会生活是现实的,其中记载:
那快头是得时衙役,也招架两班戏,一班山东弦子戏,一班陇西梆子腔。他给了四十两银买的去。(第七十七回)
这门上堂官,便与传宣官文职、巡绰官武弁,商度叫戏一事。先数了驻省城几个苏昆班子,福庆班、玉绣班、庆和班、萃锦班……又数陇西梆子腔,山东过来弦子戏,黄河北的卷戏,山西泽州锣戏,本地土腔大笛嗡、小唢呐、朗头腔、梆锣卷,觉俱伺候不的上人。(第九十五回)(6)(清) 李绿园《歧路灯》,李颖点校,中华书局,2004年,第570、674页。
《杞县志》提到的“逻逻、梆、弦”,应指罗罗腔、梆子、弦索。《歧路灯》提到的外来声腔有山东弦子戏、陇西梆子腔、黄河北的卷戏、山西泽州锣戏,本地土腔有大笛嗡、小唢呐、朗头腔、梆锣卷。这里,锣戏又称罗罗腔,弦子戏是弦索系统的声腔。在开封及河南其他地区聚集的多种声腔,逐渐融为一体,后来被统称为河南梆子。
这些史料,是考证河南梆子音乐构成的有力佐证。可以说,构成河南梆子音乐要素的多种声腔在乾隆年间就已存在。河南梆子的最终形成,应在此之后。
研究河南梆子的音乐形成,需注意河南不同地区梆子腔既有音乐的同宗性,由于吸纳其他声腔、土曲的音乐营养不完全一样,又各有特色。河南梆子通常分作祥符调、豫东调、沙河调、西府调四种流派,也可概括地分为豫东调、豫西调两大腔系。以开封为中心的祥符调、以商丘为中心的豫东调、豫东南的沙河调,由于语音、唱腔、板式相近,常统称为“豫东调”。以洛阳为中心的则称“豫西调”,又称西府调。这种同源共生又各具特色的音乐,是河南梆子的一大特色。
常香玉出生于豫西的巩义,学艺于豫西调。后来多次到郑州、开封、陕西等地演出,又融合了祥符调以及其他戏曲的演唱风格。《花木兰》的音乐是典型的豫西调,对于欣赏者来说,常香玉的演唱是正宗的豫西调唱法,也深得祥符调的精髓,是醇正、具有浓郁中原韵味的豫剧。
(二) 梆子腔板式为豫剧提供了音乐发展空间
清代李调元《剧话》云:“《诗》有正风、变风,史有正史、霸史,吾以为曲之有弋阳、梆子,即曲中之变曲、霸曲也。”(7)(清) 李调元《剧话》,载《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八),第47页。清中叶后,北方的梆子腔盛行,有山陕梆子、山西梆子、河南梆子、直隶梆子、山东梆子等。其中,河南梆子是梆子腔系中音乐特色较为鲜明的声腔,板眼铿锵、行腔酣畅。由于梆子腔的板式结构有较大的音乐兼容度,使得河南梆子能够融汇众多外来声腔与本地土曲。
与曲牌体不同,梆子腔属于板腔体。曲牌体音乐是以旋律为中心展开的;梆子腔音乐则以板式为中心展开,旋律发展的自由度较大,可以为音乐创作提供较大的表现空间。
河南梆子的板式主要有[慢板]、[二八板]、[流水]、[飞板],被称为“四大正板”。其中,[二八板]是一板一眼,板式变化较为丰富,有[慢二八板]、[中二八板]、[快二八板]、[紧二八板]、[紧打慢唱]、[二八连板]等变化板式,[二八板]还衍生出[呱哒嘴]、[狗撕咬]、[搬板凳]、[乱弹]等板式。[慢板]是一板三眼,有[金钩挂]、[反金钩挂]、[迎风板]等变化板式。[流水]是眼起板落的一板一眼,有[慢流水板]、[快流水板]、[流水连板]等变化板式,还衍生出[垛板]、[两锣钻子]等板式。[飞板]无板无眼,属于节奏自由的散板。此外,还有[滚白]、[栽板]、[叫板]等板式以及[哭韵]、[行韵]、[绝韵]等格式。
与其他北方梆子腔相比,河南梆子的基本板式并不复杂,但每一板式都有多种变化,这种既简洁又富于变化的板式结构,适于将多种地域性音乐融入唱腔,而音乐载体却能保持统一。

豫西梆子也称“靠山簧”(靠山吼),融汇了河洛地区的“十字调”梆子与伏牛山区的“靠山簧”,由于豫西与陕、晋相邻,因此与秦腔、蒲剧音乐互有借鉴。其唱腔采用大声口,演唱风格雄劲激越,浑厚深沉。缘于历史原因,河南梆子与其他戏曲一样,原来没有女演员,20世纪20年代后,旦角进入河南梆子。随着旦角唱腔的革新,一些优秀的旦角成为舞台中心,在遒劲阳刚的演唱中揉入了委婉柔情的一面,丰富了音乐表现的维度。这些特点,可以从常香玉版《花木兰》中得到映现。
(三) 由土腔、土曲绵延而来的中原地区音乐审美
河南梆子融汇了多种外来声腔与本地土曲,但它的音乐审美并不是这些音乐的简单相加,它所反映的,是中原地区的审美取向。戏曲声腔的地域性特点,决定了它须“合水土”、“接地气”,契合于本地域民众的音乐审美,才能植根或融入这片土壤。
音乐审美具有延续性的特点。就河南梆子而言,原来本地土腔大笛嗡、小唢呐、朗头腔、梆锣卷等,虽然在与外来声腔的碰撞中没留下过多的印迹,在汇入梆子腔板式时失去了原有拍板,但是,它们承载的音乐审美却延续下来。这也是地域性音乐审美的一种历史性选择。
豫剧的发展,存在着“变”与“不变”两方面的作用影响。《花木兰》一剧,音乐语汇吸纳了诸多戏曲声腔的营养,旋律走向借鉴了其他剧种的发展手法,舞台呈现借用了写意化的方式,使得这部作品的音乐更加规范,更加鲜活。另一方面,它又是“不变”的,常香玉版《花木兰》,从唱腔、韵味到风格,仍然是中原音乐审美的呈现,那些吸纳来的音乐要素,完美地融入作品之中。对于欣赏者来说,常香玉演绎的《花木兰》就是地地道道的豫剧,豫剧就应该是这个样子。这里,有扑面而来的中原风,有割舍不下的故土情,有百听不厌的家乡韵。这种散发着中原气息的“乡土味”,反映了豫剧演唱审美始终有一种执着的“本我”坚守。
二、 音乐化的语音、语调、语感
传统戏曲声腔演唱的一个本质特征,是采用什么样的方音以及如何将这种语音运用于音乐之中,这是一种声腔区别于它种声腔的显著标志。豫剧用中原地区方音演唱,在语音运用中采用了富于音乐化的表达方式,因而富有特色,常香玉演唱的《花木兰》是这方面的典范,演唱语音运用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彰显出极强的审美特征。
论及戏曲声腔的演唱语音,不能不提到《中原音韵》。元代中叶,周德清所撰《中原音韵》及其衍生出的卓从之“中州韵”是元代北曲的语音遵循,这源于元人的一种认识,周德清说:“欲正言语,必宗中原之音。”(11)(元) 周德清《中原音韵》,载《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一),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第175页。范梈说:“四方偏气之语,不相通晓,互相憎恶。惟中原汉音,四方可以通行。”(12)(元) 范梈《木天禁语》,载《诗品二十四则 风骚旨格 木天禁语》,“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八年,第12页。孔齐说:“北方声音端正,谓之‘中原雅音’,今汴、洛、中山等处是也。”(13)(元) 孔齐《至正直记》,粤雅堂丛书本,“宋元笔记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5页。明太祖朱元璋推崇中原雅音,加之北曲在明代广泛传播,明代许多传奇、声腔都以“中原音韵”或“中州韵”为演唱语音遵循。这种情况延续至清,许多戏曲声腔都讲究“中州韵”,使它们得以在更广阔的地域流布。
河南地处中州,现实中的河南话与元代流传下来的“中州韵”并不完全相同,河南梆子演唱也不讲究“中州韵”,许多艺人说,他们“是用河南话唱豫剧”。河南话属于音韵学范畴的中原官话,音韵学把汉字语音分为声、韵、调三部分,中原官话的“声”即声母,与《中原音韵》基本相同;中原官话的“韵”即韵母,与《中原音韵》大致相同,也有个别不同,如中原官话区一些读歌戈韵的字,在《中原音韵》中属萧豪韵;中原官话的“调”即声调,与《中原音韵》一样,都是“入派三声”。河南话的“声”、“韵”与普通话也较为接近,但二者的“调”即调值却不同。此外,河南话保留了尖团音。常香玉版《花木兰》十分注意方音的运用,把语音、语调、语感旋律化、语气化,唱腔中透发出浓郁的中原语音韵味。
(一) 切字过程的夸张化
吐字,是中国传统演唱的一项重要技法。戏曲声腔极重视吐字,需唱出字头,带出字腹,收束字尾。常香玉演唱的《花木兰》,吐字时有意将切字过程夸张化,也就是把声母和韵母的拼读过程夸张化,形成了一种极具个性的演唱特色。
传统演唱的吐字技法源于切字,并在这个基点上丰富发展。北宋沈括《梦溪笔谈》云:“切韵之学,本出于西域。”(14)(宋) 沈括《梦溪笔谈》,载《元刊梦溪笔谈》,影古迂陈氏本,文物出版社,1975年,卷十五,第1页。明代王骥德论曲时提出了“反切”之法,其《曲律·论平仄》云:“今之平仄,韵书所谓四声也,而实本始反切。”王氏虽提出用“反切”厘整字音,对于演唱时如何反切未作进一步阐析,“今无暇论切”(15)(明) 王骥德《曲律》,载《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四),中国戏曲研究院编校,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第105页。。明末沈宠绥《度曲须知》将演唱字音的头、腹、尾与切字之法相联系,提出了“切法即唱法”,其《度曲须知·字母堪删》云:“予尝考字于头腹尾音,乃恍然知与切字之理相通也。盖切法,即唱法也。曷言之?切者,以两字贴切一字之音,而此两字中,上边一字,即可以字头为之,下边一字,即可以字腹、字尾为之。”沈氏还举出例子:“如东字之头为多音,腹为翁音,而多翁两字,非即东字之切乎?”(16)(明) 沈宠绥《度曲须知》,载《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五),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第223—224页。清代李渔、徐大椿、王德晖、徐沅澂等诸多曲家均就此做以探索,如王德晖、徐沅澂著《顾误录·出字》提出:“每字到口,须用力从其字母发音,然后收到本韵,字面自无不准。如‘天’字则从‘梯’字出,收到‘焉’字;‘巡’字则从‘徐’字出,收到‘云’字;‘小’字则从‘西’字出,收到‘咬’字;‘东’字则从‘都’字出,收到‘翁’字之类。可以逐字旁通,寻绎而得,久之纯熟,自能启口即合,不待思索,但观反切之法,即知之矣。若出口即是此字,一泄而尽,如何接得以下工尺?此乃天籁自然,非能扭捏而成者也。”(17)(清) 王德晖、徐沅澂《顾误录》,载《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九),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第59—60页。
观察《花木兰》演唱中的字音表达,既合于传统的切字之法,又不囿于传统演唱强调的快速咬字,有时反而将切字过程放慢。“花木兰羞答答施礼拜上”唱段(18)电影: 豫剧《花木兰》,河南豫剧院改编,刘国权、张新实导演,常香玉主演,长春电影制片厂,1956年摄制。以下正文所引唱段出处均同,不另标注。首句,“花”、“兰”、“羞”等字的演唱都是一个夸张的放大的切字过程,呈现出独特的字音韵味,将花木兰欲倾诉满腹话又不知从何说起的羞怯神态表现得惟妙惟肖。
中国传统演唱讲究“先须道字后还腔”,这源自南宋张炎《词源》所云“腔平字侧莫参商,先须道字后还腔”(19)(宋) 张炎《词源》,“万有文库”,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六年,第19页。。观察昆曲、皮黄、秦腔、川剧、黄梅戏、花鼓戏等剧种,几乎莫不如此。豫剧处理“字”、“腔”关系时有自己的独特做法,长腔演唱是先道字后还腔,而短腔演唱特别是一字一音、一字二音时,切字的过程常常就是行腔的过程,切字与行腔几乎是一致的。《花木兰》“谁说女子不如男”唱段,“这女子们哪一点不如儿男”乐句中的“男”字是先道字后还腔,其余字音,都将切字与行腔融为一体。这种唱法极其“上口”,演唱的叙述感强,有一种“叙家常”的感觉。从音乐学角度看,豫剧的演唱音乐如果按记谱法无法一一标注出来。就习唱者来说,如果只按谱面去唱,唱不出豫剧的味道,需得师父的“真传”。这些,都源于豫剧独特的切字技法。常香玉演唱《花木兰》时,无论长腔还是短腔,“腔”都是围绕“字”进行的,使“字”的韵味更为凸显。
把切字过程夸张化,把方言韵味与行腔过程统一起来,是演唱语音的音乐化运用,这是豫剧演唱始终保持乡土韵味的一种审美体现。这种唱法,在河南其他土曲、土腔韵味较重的声腔以及北方一些说唱艺术中也时有所见。
把切字过程夸张化,实际上是加强地域性方音的表达,这并不影响其他地域观众对豫剧的欣赏。由于中原官话与普通话在声、韵方面基本相合,也由于切字过程放慢、夸张甚至强化,可以让欣赏者听得清表演者所唱台词,这也是一些外地人听不懂河南话却能听懂豫剧演唱的原因。
(二) 中原语调的旋律化
除豫北一带属晋语片、豫南部分地区属江淮官话片,河南省大部地区均使用中原官话。中原官话与普通话都有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四个声调,最大区别是声调的调值不同。这里分析“中原官话-洛阳话”与普通话的调值区别。普通话的四声调值是: 阴平55,阳平35,上声214,去声51。据贺巍先生1984年对洛阳老城区中心魏家街的调查,洛阳话的四声调值为: 阴平33,阳平31,上声53,去声412。(20)贺巍《洛阳方言记略》,载《方言》1984年第四期,第278页。可依此列出二者的四声调值(均不含轻声调值):

常香玉版《花木兰》的字音调值与此表所列洛阳话调值基本相合。中原官话与普通话相比,还有个别不同,这里不作详解。
豫剧的音乐发展通常围绕语音、语调进行,旋律线走向常常与字音的调值一致。“花木兰羞答答施礼拜上”唱句的落音“上”字是一个长腔,旋律虽经蕴拭,总体走向与去声字的调值一致,听觉上是调值的一种夸张性呈现。
“上”字的去声字调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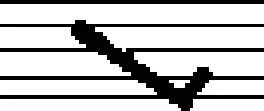
《花木兰》中“上”字的旋律(21)河南豫剧院《花木兰豫剧(剧本与曲谱)》,河南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77—78页。:

分析常香玉版《花木兰》,演唱字音的语调韵味比较足的通常是阳平、上声、去声这三声。“刘大哥讲话理太偏,谁说女子享清闲”唱句中的“理”字是上声,普通话的上声调值是先抑后扬,《花木兰》则由高向下滑落。“谁”字是阳平,普通话的调值是稍向上挑,《花木兰》则是一个小的下落音,出音的调值低于洛阳话的上声,常香玉有意加重字头。虽然这些演唱字音的调值与普通话有别,但河南之外的观众多能听懂。
豫剧属于演唱语音语调与旋律关系较为密切的一种声腔,欣赏常香玉版《花木兰》演唱语调的旋律化呈现,可以从中体悟出这样一些认识:
——豫剧极重视“正字”,旋律围绕语调展开,实际上是为了字音的清晰表达。在“字”、“腔”关系中,豫剧更重“字”的表现,这样,既不“倒字飘音”,又能保持河南话的原有韵味。
——把演唱语调旋律化,是以语音、语调的表现为核心,将吸纳而来的多种音乐元素有机地融入旋律。这样,既丰富了音乐的内涵,又使音乐的进行合于声、韵、调。
——演唱语调的旋律化呈现,重在“火候”的拿捏。“火候”不足,难以表达中原语音语调的韵味;“火候”过了,又会让人有矫揉造作之感。对“火候”的准确把握,源于演员的深厚功底、对艺术的领悟能力以及对作品的深刻理解。
——很多戏曲的吐字都有所长。昆曲的字头、字腹、字尾处理,“功深镕琢,气无烟火”(22)(明) 沈宠绥《度曲须知》,载《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五),第198页。,是为“水磨”。京剧长于吐字、过度、归韵,名家的收韵功夫极好,被称作唱得“上韵”。豫剧的功夫在于切字的夸张与语调的旋律化,这种吐字既有力量感,又富于音乐性。
(三) 戏曲语感的口语化
语感,是对语言的感觉,也是对语言情绪自觉不自觉的流露。豫剧演唱非常重视语感表达,常常将演唱语感口语化,以增添情绪的传递与演唱的感染力。常香玉版《花木兰》是这方面的典范,这里列举一些较为典型的演唱语感口语化处理方法:
——层次分明的语气描摹。常香玉常常以夸张化、旋律化的语气表达,强化唱句的语感。“谁说女子不如男”唱段,是花木兰对士兵刘忠所说“这天下苦事都叫我们男子做了,这女子们成天在家清吃坐穿”表示不满,并用事实予以驳斥的片断。开头一句“刘大哥讲话理太偏”,“理太偏”三字用了大甩腔,有一种较强的情绪化表达。“你要不相信(哪),请往这身上看……千针万线可都是她们连(呐)”,前两句是据理力争,最后一句是充满辨驳的语气表达。唱腔尾句“这女子们哪一点不如儿男”,结合语气表达,再次将演唱情绪推强。
——倾诉式的行腔表达。豫剧长于借助行腔来加强音乐的倾诉性,特别是长腔演唱往往跌宕起伏,适合于声情多的演唱表现。“花木兰羞答答施礼拜上”唱段,起板处的演唱,有种羞于启齿的扭捏;转板处唱腔“我的父在军籍就该保边疆,见军贴不由我愁在心上,父年迈弟年幼怎抵虎狼”,又是一种回顾性的娓娓道来。
豫剧的短腔也常有叙述性行腔,虽然词情多、声情少,但通过流水般的行腔、口语化的演唱,仍然可以较好地传递出内蕴的声情。“居家人听说心花放”唱段,是贺元帅准花木兰探亲后,花木兰对回乡时情景的憧憬。这个唱段采用上下句式的短腔,节拍短促,音乐空间小,常香玉通过强化演唱语感和演唱情绪,增添了声情内涵,特别是“开我东阁门(哪),坐我西阁床(啊)!脱我战时袍,着我旧时裳”这几句,每句都是干净利落的语气表达,将喜出望外、望眼欲穿的心绪表现得淋漓尽致。
——妥帖嵌入的语气助词。在唱词中加入语气助词,是中国传统演唱的一大特色。豫剧是使用语气助词较多的戏曲剧种,分析常香玉版《花木兰》,可以看出豫剧演唱中语气助词使用的一些特色。
一是用于表现剧中人物情态。“脱去了连环甲换上罗裙”唱段,是花木兰回家后恢复了女儿身,即将见到元帅时的内心独白。常香玉演唱的每一句都加上大量语气助词,借此表现羞涩、忐忑,甚至有些惶恐的情态:“脱去了连环甲(呀)换上罗裙(哪呀呀哈哈)。羞渐渐我只把(哪哈呀哈嗯啊哈)这客厅来进(哪哈呀),量元帅认不得儿是那阵前的将军(哪)。”演唱时如果去掉这些语气助词,就难以表达出花木兰此时此刻的情态。
二是可以推助唱词的语感和语气表达。“将姐姐和弟弟的手儿拉紧”唱段,是花木兰即将从军、与家人话别时对姐姐、弟弟的嘱托。常香玉通过在唱词中融入“唉”、“呀”、“哪”等语气助词,较好地传递出千般叮嘱的语气,借而表现依依不舍的心绪,如“我的姐姐(呀)!我的弟弟(呀)!咱姊妹都需要这各尽各心(哪)!”
三是在唱段句尾加上大段语气衬字,延续整个唱段的表现内涵。“花木兰羞答答施礼拜上”是全剧的重要唱段,在尾句“花木兰改木力我的元帅呀!你莫怪我荒唐”之后,常香玉缀入大量语气助词:“啊,啊啊呀、嗯嗯啊、嗯嗯呀啊呀唉那个呀唉啊呀唉嗯啊依呀哪……”时值延续了8个半小节。借助于这些语气助语,将花木兰内心百味杂陈、感慨万千,又怕元帅生气,惴惴不安的复杂心绪恰当地展现出来。这些语气助词承担了“声情”的表现功能,具“此处无词似有词”之妙,犹如《礼记·乐记》所言:“长言之不足故嗟叹之。”(23)(汉) 郑玄注、(唐) 孔颖达疏《礼记注疏》卷三十九,影武英殿本。
三、 极具张力又不着纰颣的声音技法
豫剧的声音技法富有特色,上乘的演唱可以入味、传神,这在《花木兰》中有完美的体现。常香玉的演唱,用声敦厚而富于张力,行腔流畅又不着纰颣,能够通过演唱塑造出活生生的角色形象。
(一) “用声”: 铿锵激越的声音色彩
“用声”,是采用什么样的声音去演唱。对于欣赏者来说,是一种直观的听觉,感知的对象是声音的本体。“用声”是以“美听”为基础的,是将声音作为审美欣赏的客体。由于不同戏曲声腔有不同的审美取向,它们“用声”的特点并不完全相同。豫剧的演唱,追求的是铿锵激越的声音色彩,这是中原地区音乐审美的体现。
元代燕南芝庵《唱论》提出:“南人不曲,北人不歌。”(24)(元) 燕南芝庵《唱论》,载《历代散曲汇纂》,影元刊本,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页。这里既包含南北演唱形式的区别,也包含南北音乐审美的不同。明代徐渭《南词叙录》说:“今之北曲,盖辽、金北鄙杀伐之音,壮伟很戾,武夫马上之歌,流入中原,遂为民间之日用。”(25)(明) 徐渭《南词叙录》,载《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三),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第240页。当时江南地区的人们,多认为高昂、壮伟的北曲是“杀伐之音”。魏良辅《曲律》说:“北曲以遒劲为主,南曲以婉转为主。”(26)(明) 魏良辅《曲律》,载《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五),第6页。是对南北演唱“用声”差异作出的一种较为准确的归纳。
辽、金、元等朝代,华北、中原地区的民众主体是汉人,北曲并非契丹、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的音乐,徐渭所云“辽、金北鄙杀伐之音”,是站在南人的角度,对北地音乐的概括性感知。到了清代,北地民众仍然喜欢高昂、激越的声音,诸如皮簧、秦腔、梆子等时行声腔,莫不如此。后来的豫剧,追求铿锵激越的声音色彩,也是对北地演唱审美的一种抒写。
“用声”具有双重属性。就共性而言,反映了地域音乐审美对演唱的要求;就个性而言,则体现演员的艺术个性。“用声”,通常包括音质、音色、音域、音量、共鸣腔体、发声位置等因素。1956年河南第一届戏曲大会形成的陈素真、常香玉、马金凤、阎立品“四大名旦”,她们的“用声”各有特点。欣赏常香玉演唱的《花木兰》,其“用声”具有音色纯,音域广,声口宽,膛音重,音响强,沙喉响润,声音敦实,高亢激越等特点。从演唱发声的角度分析,包含有自然条件好,发音位置靠前,嗓音亮,胸腔重,富有共鸣感,真声偏多,真假声过渡自然、声音控制力强等因素,这使得她的演唱既慷慨高昂,又敦实厚重,有一种豪迈飒爽之感。《花木兰》用调1=bE,最高音至小字二组的g音,演唱音域并不算高,但常香玉的演唱却能传递出一种高昂、铿锵之感,使声音富于张力又极有气势,这是她的演唱深受河南以及北方其他地区民众欢迎的重要原因。
从一定意义上说,“用声”是演唱声音的“底色”,这种“底色”是音乐表现的基础。在《花木兰》中,常香玉富有色彩的“用声”,适合于表现从军、征途、巡营、阵仗等行伍情景,反映花木兰勇敢、刚毅、坚韧的性格。即使在表现花木兰烦愁、忧虑、羞涩、喜悦等情绪时,如第二场“送别”、第七场“提亲”、第八场“荣归”,常香玉的“用声”揉入了温润委婉,但声音的“底色”仍然是刚健的,塑造的人物形象不是一个柔弱女子,而是英气豪迈的巾帼英雄。
(二) “行腔”: 行云流水般并富有华彩的音乐表达
行腔是演唱声音的表现性运用,可以对声音进行各种润饰来增添旋律美感。在传统戏曲中,许多行腔技法如滑腔、甩腔、抖腔、哭腔等为多种声腔所采用,不同的是,不同戏曲声腔基于不同的审美取向,对这些技法有不同的应用。豫剧行腔常有一种行云流水般的行进感,不仅流水板,其他板式的流动感也较强,并且能够将声音、气息、运腔等多种技法有机地融入行腔,富有华彩。分析常香玉版《花木兰》,可以从流畅、圆润、醇美的唱腔中,找寻出许多富有特色的行腔技法,这里分析其中几种技法:
“夯音”,是以丹田为根基,结合急促收腹,震响胸腔,使气息通过强烈冲击而发出坚实、浑厚、短促的强顿音。豫剧中的生、净行使用夯音较多,常香玉等唱家将夯音用于旦角,以致后来成为豫剧演唱的一种特色。《花木兰》中的夯音使用,常用在乐段结尾,或与“唉嗯啊依呀哪”等语气助词结合使用,使行走般的唱腔在收束处敦实厚重,增加了音乐的力量感。“谁说女子不如男”唱段结尾处“男”字,在长腔收束处使用了夯音,增加了情绪表达的力量感,把女扮男装的花木兰有意表现男儿阳刚气质的一面展现出来。
“甩腔”,豫剧是采用甩腔较多的剧种,行腔中有小甩腔,也有大甩腔。采用甩腔时,有时突出字音的表达,有时强调甩出的腔音。常香玉版《花木兰》对甩腔的运用得心应手,有的是夸张化地表现字音,强调“字”的表现;有的是加重语句的韵味,强调“句”的表现;有的是增添行腔的色彩,强调“腔”的表现。“花木兰羞答答施礼拜上”唱段有多处甩腔,“羞答答”中的“羞”字,常香玉采用一个大甩腔,强调“字”的表达。“施礼拜上(啊)”的“上”字,采用了大甩腔并与语气助词连用,强调“句”的表达。这两处甩腔极有韵味,将花木兰害羞忸怩的情态活脱脱地表现出来。
“笑声”,是常香玉首创的豫剧行腔技法,她借鉴了俄罗斯民歌中的笑声并将这种方式创造性地运用在豫剧演唱。《花木兰》中笑声的运用与行腔紧密结合,生动自然,恰到好处。“用巧计哄元帅出帐去了”唱段中“我自己好笑”的“笑”字,是随着笑声唱出来的。“花木兰羞答答施礼拜上”唱段中“我原名叫花木兰(哪)是个女郎”,“女郎”二字中有笑声,是唱腔中夹带出的笑声。“自那日巧改扮乔装男子”唱段中“蒙元帅来探病又把亲来提”,“亲”字是直接笑出来的。这些笑声的灵活应用,很自然地表现出花木兰对自己女扮男装引出的一系列事情感到好笑的情境,也显露出花木兰活泼开朗的性格,既增强了戏剧性效果,也使人物形象的塑造更为丰满。
行腔是作品表现的重要手段,也能从中反映演唱者的艺术个性和艺术功底。名角、名家对行腔技法的运用,不仅驾轻就熟,难能可贵的,是运用这些技法时的浑然天成。明代王骥德《曲律》在“论套数”时提出:“务如常山之蛇,首尾相应,又如鲛人之锦,不着一丝纰颣。”(27)(明) 王骥德《曲律》,载《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四),第132页。这既是对文本间架的要求,也是演唱审美的体现。从常香玉版《花木兰》的演唱中,可以体味到这种演唱审美的神韵,她的行腔自然流淌,有一气呵成之感;她的技法应用,诸如滑音、颤音、喷口、哭腔、咳咳腔,仿若信手拈来,不着痕迹,有如王骥德所言:“不知所以然而然,方是神品,方是绝技。”(28)(明) 王骥德《曲律》,载《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四),第132页。
(三) “曲情”: 着意于音乐形象塑造的声情传递
声音具有可塑性和情绪性的特点,可以模仿、可以形声、可以传情,也可以用于刻画和描绘。这些特点,丰富了声音的表现力。分析《花木兰》演唱声音的表现,是通过音色、音调、音态、音响以及声音的疾徐、开阖、宽窄来实现的,并因此赋予人物形象以相应的声情表达。
古人很早就注意到演唱声音的表现和摹拟作用,如明代臧懋循《元曲选·序》云:“行家者,随所妆演,无不摹拟曲尽,宛若身当其处,而几忘其事之乌有。”(29)(明) 臧晋叔编,隋树森校订《元曲选》,中华书局,1958年,第4页。清代曲家更是提出了“曲情”的命题,李渔《闲情偶寄》指出:“唱曲宜有曲情,曲情者,曲中之情节也。解明情节,知其意之所在,则唱出口时,俨然此种神情……有终日唱此曲,终年唱此曲,甚至一生唱此曲而不知此曲所言何事,所指何人,口唱而心不唱,口中有曲而面上、身上无曲。”(30)(清) 李渔《闲情偶寄》,载《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七),第98页。徐大椿《乐府传声》指出:“唱曲之法,不但声之宜讲,而得曲之情为尤重。盖声者众曲之所尽同,而情者一曲之所独异。……必唱者先设身处地,摹仿其人之性情气象,宛若其人之自述其语,然后其形容逼真,使听者心会神怡,若亲对其人,而忘其为度曲矣。”(31)(清) 徐大椿《乐府传声》,载《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七),第173—174页。
欣赏常香玉版《花木兰》,可以领略到常香玉娴熟自如、既形似又神似的声音表现力,声音的格调合于剧中人物身份,声音的摹写合于人物性格,声音传递出的神情合于人物神态,声音的刻画合于人物心理。
“用巧计哄元帅出帐去了”是全剧一个中心唱段,是得胜后元帅提亲时花木兰的内心倾诉。常香玉演唱声音的总体设定,合于花木兰戎马生涯十二载、由豆蔻少女成长为花将军的身份。常香玉以质朴、纯挚、爽朗、直抒胸臆的声音,配以干净利落的唱腔,准确地摹写出花木兰直率、爽快、利落又有几分俏皮的性格。在人物情态、心理刻画方面,常香玉结合多种技法的灵活运用,展现出极强的声音表现力。“羞得俺花木兰脸上发烧”一句中,“俺”字是一个大甩腔,“脸上发烧”四字收束得干净利落,通过音调变化、音速的疾徐对比,表现花木兰羞怯的情态。“我(这)低下头”的尾字“头”,常香玉有意将音色变暗,采用22小节的长腔,配合顿挫、甩音,将花木兰先是不好意思进而陷入沉思的心理线条铺陈出来。“我自己好笑,我是个女儿家怎把亲招”一句,羞涩中有顽皮,演唱中有较强的语气感,特别是“己”字的演唱极有特色,先以明快的音色拉出长腔,长腔尾处突然将声音收窄,融入沙声,与顿挫腔、挑腔、咳咳腔配合使用,妥帖地表现出花木兰俏皮中夹有得意的情态。“在军营十二载”是一种回忆,常香玉将音速放慢,表现追忆、感慨的心境。“花木兰就要快马转还乡”一句,速度先快后慢,配合紧打慢唱的音乐,表现急切的心情。“转还乡”三字,速度突然放缓,“乡”字的拖腔,声音收窄,音色变暗,音响转弱,让观众与花木兰一起,引入对还乡的憧憬。
四、 把二度创作推向高峰:“本色化”的审美表达
豫剧是“本色化”特征较强的剧种。常香玉版《花木兰》,在文本创作“本色化”的基础上,通过演唱、宾白、科介等表现手法,塑造出“本色化”的人物形象,这是“本色化”审美追求的完美呈现。
(一) 透发着乡土气息的审美表达
浓郁的生活气息和乡土韵味,是《花木兰》作品表现的审美基调,从文本到演唱呈现,都传递着这样的审美表达。
就文本创作而言,豫剧的表现维度多是平视的,常常以平民的视角去观察、去表现,即使是历史题材中的帝王将相、金戈铁马故事,也往往拉到庶民的角度去解读。《花木兰》是一个生活气息比较浓、情感线条比较重的故事,创作者没有过多地着墨于鏖战边关、气壮山河,而是围绕替父从军的主题,细腻地展示纺织、话别、思乡等生活性场景,塑造出一个有血有肉的女英雄形象。这种审美表达更容易为老百姓所欢迎,是在用他们熟悉的语言去讲身边的故事。
从音乐本体的角度分析,戏曲是由地域性声腔发展而来,在长期发展中,一些戏曲声腔为了提升自己,对音乐反复打磨,逐渐走上“雅化”的路。也有一些戏曲声腔,不尚雕琢,较多地保留着初始土曲、土腔的音乐形态、音乐要素与音乐色彩。豫剧音乐显然属于后者。常香玉版《花木兰》,演唱语音是地地道道的河南话,作品传递的是浓浓的乡土气息,通过流淌着乡音、乡情的演唱,将千百年来传颂的花木兰故事,演绎得活灵活现,塑造出呼之欲出的人物形象。
从音乐审美的角度分析,一些戏曲声腔的“雅”与另一些戏曲声腔体现出来的“土”,最终都由欣赏戏曲的民众的音乐审美所决定。《花木兰》音乐体现的浓郁的乡土韵味,与中原地区的音乐审美密不可分。正是这种醇厚质朴的乡土气息,牵出与普通人一样的喜怒哀乐,深深地感染并打动着观众。
戏曲声腔具有流播性特点,一些“雅化”的戏曲声腔可能为流播地欣赏者所喜爱,一些带有厚重乡土气息、没被“雅化”的戏曲声腔也可能深受欢迎。细腻委婉的声音与粗犷、大线条的声音,同样会受到欢迎,这反映了音乐审美既有地域性因素,也有多元取向的特点。
决定戏曲声腔流播一个重要因素,是演唱者的二度创作。常香玉凭借深厚的演唱功底与艺术积累,将《花木兰》的演绎推向高峰,使豫剧的艺术魅力得以充分展示,观众从中感受到的,是充满生活气息的温馨、难舍难离的眷恋,并由此而生发出的“替父从军”、“为国杀敌”的家国情怀。这样精湛的演唱呈现与审美表达,会让许多原来不熟悉豫剧的欣赏者喜欢上这个作品。
(二) 慷慨激越、元气淋漓的演唱风格
豫剧的演唱大多是一种高揭激昂、铿锵有力的抒发、通过浓墨重彩式的渲染,展现着中原地区的音乐审美,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常香玉演唱的《花木兰》,将这种演唱发挥得淋漓尽致,彰显着豪放、粗犷、遒隽的艺术个性。它是一种演唱风格,也是一种审美表达。
分析常香玉版《花木兰》,可以观察到豫剧演唱的许多典型特征:
豫剧的音乐语汇具有流畅性特点,演唱音域多在中、高音区。与秦腔、河北梆子等高腔类声腔相比,豫剧演唱的最高音并没有那么高,而在欣赏者听来,却是高亢激越,豪放遒劲的。常香玉的演唱,结合情节的铺排、情感的宣泄,常常唱得慷慨激越,一泻千里。
豫剧的旋律进行,级进少、跳进多,不重于过度音的表现,而重在旋律的行进或转折中展现音乐的韵致。常香玉的演唱,随应情节的起伏、情绪的涨落,唱腔大开大合、跌宕有致,常常让人有荡气回肠的感觉。
豫剧音乐的节奏感强,在鲜明的行进节奏中又内蕴一个个“筋节”。常香玉采用简洁、明快的口法,唱腔铿锵,落音收束干脆利落,特别善长于在“筋节”处表现音乐的韵致,因而唱得富有韵味。这与明代王世贞论曲时所云“北字多而调促,促处见筋”(32)(明) 王世贞《曲藻》,载《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四),第27页。,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合的。
豫剧的演唱格致,舒展大方、刚健畅达,属于大线条的艺术呈现。常香玉的演唱,重腔口,不重揾拭,大气豪迈,挥洒自如。她的吐字行腔清朗利落,技法运用隽秀灵动,风格表现奔放洒脱,唱腔中透着一股英气,使音乐表达显得大气爽朗。
《花木兰》第三场“拜别爹娘离家园”唱段,是分析常香玉演唱风格的一个范例。这个唱段几乎句句都有旋律跳进,常香玉结合紧二八、迎风、散板、紧压板、飞板等板式转换,强调行走、宣泄式的音乐表达,在行进感极强的音乐中又注意强化“筋节”处的音乐刻画,将花木兰日夜兼程赶赴边关的急切情态生动地表现出来。“提缰催马往前赶”一句中的“往前赶”,旋律线条起落较大,是音乐中的“务头”处,常香玉结合旋律走向,通过华彩性的上滑音、下滑音,有力地表现出花木兰性格中的勇猛果敢。
常香玉演绎花木兰的唱腔,韵味足,张力大,风格性强,这与她善于运用各种板式及板式转换是分不开的,特别是拽板、等板、紧打慢唱等板式的演唱,不拘一格,富有变化。在音乐处理上,她娴熟地掌握和活用甩腔、滑腔、断挫、挑腔、抻音等行腔技法,能不着痕迹地将这些技法融入唱腔,常常是寥寥几笔,就能将花木兰的情态表现得活灵活现。
常香玉的演唱风格中,还有一种难以形容的恣肆和率意,使演唱洒脱自如,往往成为一个唱段、一个唱句的点睛之笔。许多豫剧演员习学常香玉的演唱风格并多有心得,惟有这种恣肆率意是极难得其精髓的。
(三) 角色的“本色化”是文本“本色化”的最终呈现
“本色化”是戏曲声腔创作的重要原则。这一命题的提出,始于明代何良俊《四友斋丛说》所云:“盖填词须用本色语,方是作家。”(33)(明)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万历刻足本,“元明史料笔记丛刊”,中华书局,1959年,第337页。其后,徐渭、王世贞、徐复祚、沈德符、王骥德、吕天成、凌濛初等人结合作品品评各抒己见,以致倡导“本色”、“当行”成为当时众多曲家的共识。明代曲学中的“本色”理念,后来成为戏曲创作的重要原则,也成为传统戏曲审美的重要内涵。
戏曲的最终呈现形式是舞台。再好的文本,如果不搬上舞台,只是“案上之物”。常香玉版《花木兰》,通过艺术家精湛的二度创作,将文本的“本色化”成功地演绎为角色的“本色化”,使“本色化”的创作得以终极呈现。
评价常香玉版《花木兰》,可以说,艺术家对人物形象的塑造极为成功。在观众的眼睛中,看到的是女扮男装的壮志青年,是英气勃发的巾帼英雄;在观众的听觉中,听到的是替父从军的动人故事,是报国杀敌的情感抒发。在动情之处,欣赏者甚至会有“宛若身当其处”之感。《花木兰》中“爹娘的言语我记心间”唱段,是一种大情怀的抒发,特别是常香玉演唱“挥长鞭催战马追风擎电,为杀敌改男装赶赴阵前,要学那大丈夫英雄好汉,但愿得此一去不露红颜”乐段时,通过敦声、甩腔、紧拉慢唱等演唱技法,将花木兰的胸中壮志以及豪爽、豁朗的性格,表现得栩栩如生,塑造出一个英气豪发的舞台形象,生动地诠释出《木兰辞》中“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的情感内涵。
结 语
自1956年常香玉先生主演的豫剧《花木兰》搬上舞台,迄今已过去半个多世纪。经过长时间沉淀,淡化种种主观因素之后,分析、鉴赏这部戏曲作品时可以更为理性、客观,由此引发的有关豫剧演唱审美的讨论与思考,也应该具有更为广泛的学术意义。
戏曲声腔的艺术呈现,最终应该完成于舞台,其中,艺术家独具特色的演唱是体现剧本创作精华的动能。地域性方音、地域性音乐的内在韵味,是戏曲声腔演唱的内核。有如台湾学者曾永义先生在近作《“戏曲歌乐基础”之建构》中所说:“歌乐关系的终极,实在于语言情趣与所承载的旋律之融合。从而使词情与声情互为生发,而终于施以音乐旋律的衬托、渲染、描述、强化而更趋于完美。”(34)曾永义《〈戏曲歌乐基础〉之建构》,三民书局,2017年,第103页。
演唱审美的表达,是艺术家二度创作的结晶。吐字、行腔、用声、气息是戏曲声腔的表现手段,而在戏曲声腔艺术呈现中发挥主导作用的,则是艺术家的演唱审美表达。由于常香玉版《花木兰》在浓郁的中原地区音乐审美底色上,努力将二度创作推向极致,塑造出艺术上独有的“这一个”,实现了最佳的艺术效果。
“名角”、“名家”演绎的“名作”,在特定的历史截面,常常代表一个戏曲剧种的艺术高峰。笔者曾在台湾《艺术论衡》期刊发表《豫剧的音乐审美表达之观察》(35)白宁《豫剧的音乐审美表达之观察》,载台湾成功大学艺术研究所《艺术论衡》复刊第9期,2017年11月,第63—78页。,这次更将研究视角聚焦于豫剧“名家”之“名作”,以期窥得艺术家如何通过精湛的二度创作,努力将戏曲声腔演唱审美推向极致。可以说,常香玉先生主演的《花木兰》,以其独具特色的艺术呈现,成为豫剧中的精品,也成为20世纪戏曲艺术的经典之作,这对于豫剧乃至戏曲声腔演唱审美研究,亦具有典范性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