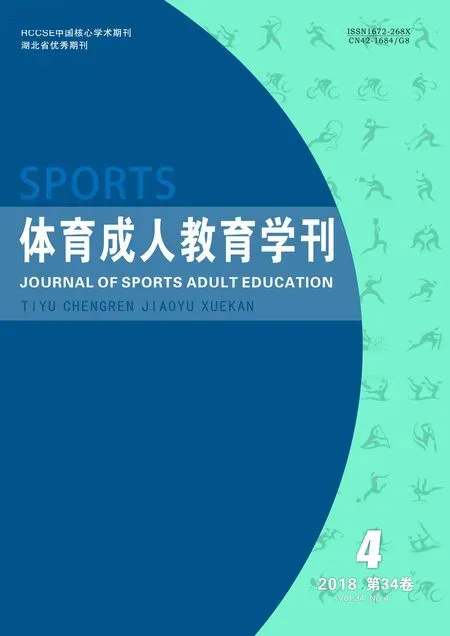吉拉尔“模仿欲望”的体育人类学实践:三公下水操的个案调查
2018-11-25郭学松
郭学松,陈 萍
(宁德师范学院 体育学院,福建 宁德 352100)
在现实社会中,“模仿”可谓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在身体运动的社会层面,模仿的痕迹更是清晰可见。诸如白鹤拳、鹤拳、猴拳、地术犬法、罗汉拳、螳螂拳、牛拳等乡土武术拳种都是一种对模仿对象的高度复现,再如基于历史战争而演绎的三公下水操,基于狩猎文化而建构的畲族狩猎舞以及为了争夺生存空间而导引的畲族打黒狮运动等皆蕴含了高度的模仿因子。然而,不同群体或个体之间的这种模仿总有其特殊的缘由,那么,是什么致使他们产生这种“模仿欲望”?法国哲学家、人类学家勒内·基拉尔的《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中所提出的“模仿欲望”(也称三角欲望)理论能够较为深刻地解读模仿的心性。通过微众社会的“小历史”洞悉大社会的现实哲理理应是体育人类学研究需要特别关注的议题,并且这种研究应当扎根于本民族的乡土体育文化之中,“如果分析不以被研究民族的文化中对象征的解释作为基础,那么这一分析就值得怀疑”[1]。本文通过走进乡土仪式体育的现实场域,尝试从身体运动的模仿场景中探索模仿者的“欲望”及建构这项乡土仪式体育的历史心性。
1 “模仿”在乡土仪式体育中的身体表象
模仿(imitate)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主要是指个体或群体自觉或不自觉地重复他人或群体行为的过程。在柏拉图的哲学理论中,模仿是一个重要的、应用十分宽广的学术词语和社会现象,诸如行为方面的效仿,哲学家们的追求,政府部门的一些工作,乃至于整个自然界的形成,都毫无例外地呈现着模仿的原则与效应。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模仿是人与生俱来的一种特殊能力,人与动物最主要的区别之一便在于人最善于模仿,并通过不断模仿而获得最初的知识。于是,模仿也被视为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能,这不仅是一种能力,而且也是一种倾向,型塑了“模仿欲”[2]。模仿动机又相当于吉拉尔(René Girard)所称的模仿欲望(mimetic desire);在亲近且敌对之个人或群体之间,由于追求较优越的存在地位(being)而产生一方对另一方的模仿[3]。这种生活中最普遍的模仿行为在吉拉尔(Girard)的《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一书中更好地呈现了出来,逐渐形成了模仿理论。吉拉尔在模仿理论中提出了模仿欲望(三角欲望)(mimetic desire),称“欲望的本质是模仿”。这一理论性概念的提出被誉为“智慧、正义和美德的大厦”,同时在学界也引起了强烈反响。基于此,他推出了《暴力和神圣》、《论世界创立以来的隐蔽事物》、《替罪羊》等系列著作,通过历史、神话、人类学资料、宗教典籍等,更加深入地论证了“模仿欲望”的表现和结果,逐渐形成了一个理论整体。
“模仿欲望”理论不仅在吉拉尔一系列的著作中可以得到印证,而且在现实的社会生产、社会生活中皆有其影像缩影,特别是在体育人类学领域中。在中国传统武术文化的发轫过程中,人们依据徒手与野兽进行搏斗的形式或模拟动物的行为孕育了诸多武术拳派,诸如龙拳、虎拳、豹拳、狮拳、象拳、马拳、猴拳、鹰爪拳、蛇拳、螳螂拳、醉拳、鸭拳、鸡拳、白鹤拳、地术犬法等,这些武术拳种通过对动物肢体攻防行为的高度模仿而形成与成型,逐渐形成了中国乡土武术门派林立及独具一格的社会现象。在这种形神兼具的模仿过程中,人们的模仿欲望始终是模仿行为的逻辑起点,就像皮特·里弗斯(Pitt-Rivers)将军指出,古代战争中诸多战斗装备都是从动物那里模仿而来,一些战争方法,也全是从鸟兽那里学来的[4]。在人类模仿动物的过程中,我们似乎也可以洞悉到,行为或是活动仅仅是手段,都是为了有所为而为的[5]。在乡土仪式中所展演的身体运动中,这种模仿的行为同样源自于“欲望”,这种模仿欲望是一种“原生性”与“建构性”的矛盾对立统一的二元关系。
课题组在村落民间体育田野工作中发现,在乡土社会仪式过程中蕴含了诸多身体运动成份,这些身体运动元素往往是以神人共娱为建构根基的,同时又以被祭祀对象的生活故事为背景依托进行行为模仿[6]。在这些乡土社会仪式展演过程中,年复一年的循环往复出场,并非仅仅向我们展示一个公认的脚本,更多地呈现了一个群体的一种行为模式,这种模式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模仿实现的[7]。福建珪塘村的族群祭祀仪式,在“三公下水操”的水中“梨神”与火把奔跑巡游肢体展演的现实场域中,通过身体运动的高度模仿,历史事件被反复地模拟与重现,历史记忆被表达与传递,族群成员的历史心性被勾勒。
2 仪式过程中身体运动“模仿欲望”的社会生产
在马克思(Karl Marx)的思想中,“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8]乡土社会仪式为何得以被生产出来,且传递至今,正是因为创造者的需要或者社会的需要。由于族群生存的需要,不同的族群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往往会假借一些记忆来识别“我族”与“他族”。用仪式中“模仿”的身体展演使抽象的历史记忆具体化,有利于记忆的保存与传递[9]。于是,一些被具体化的特殊乡土仪式便在社会中被生产出来,但是,这些仪式不是凭空想象而构建出来的,它们在不同的社会中可以找到其相似或相同的社会本相。被生产出来的乡土仪式往往会假借一些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或故事情节,通过一些肢体或行为的模仿,去建构一个属于自我族群的历史记忆与展演仪式。在这种社会生产的过程中,被模仿的对象往往以一种楷模的形象出现,我们把这个楷模称作欲望的介体[10]。在三公下水操的仪式活动中,“三公爷”陆秀夫就是导演这个族群仪式的楷模,是被模仿的介体,这个介体的正能量是通过历史事件(崖山海战)而得以发挥出来。
在福建珪塘村叶氏族群祭祀仪式中的三公下水操的身体运动中,身体展演所呈现的是一种历史情节的记忆。情节是行动的模仿,同时还是模仿一个完整的行动[11]。在三公下水操的整个活动过程中,水中的“梨神”运动环节就是对陆秀夫在水中与敌人搏斗场面行为的完整模仿。在田野工作中,叶氏族人通过一代代的口述诉说着这个颇具传奇性而又有社会事件情节依托的“历史”。在宋元崖山海战中,宋军战败,陆秀夫背着九岁的赵昺跳海,在海中与元军继续搏斗,终因体力不支及寡不敌众而壮烈牺牲。这种在水中不屈不挠的搏斗精神,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身体运动,被叶氏族人高度模仿,逐渐演化成今日“三公下水操”仪式活动的“水中犁神”环节。在陆秀夫牺牲之后,当地(新会)民众感念其民族气节,便自发组织队伍,在夜间举着火把寻找陆秀夫的尸身。这种历史场景同样被叶氏族人高度模仿,演绎了三公下水操的“火把巡游”环节。这些所谓的“历史”,在现实的场域中被演绎得绘声绘色,精彩绝伦。但是,课题组经过不断深入的田野调查,以及查阅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后,发现这种具有一定社会背景的“历史”,更多的是基于一种传说或者村民们的建构,可以说是村民们后天的一种“社会生产”。
在三公下水操的“水中犁神”和“火把巡游”场域中,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当年崖山海战的历史情境及保存在我们思想中的历史记忆,其中夹杂着相关的“传说”。对于乡土体育研究者来说,这些乡土民间的传说从历史记忆的意义上来看,与正史文献传达的历史在价值上是平等的[12]。钟敬文将《搜神记》中关于“宫人草”的传说指出来,其目的无非是想说明这个故事并非历史事实,但其所展现的帝王宫中存在怨女这个现象却并非捏造[13]。在乡土民间社会中,因民间传说的历史流传性而建构的记忆“文本”并非仅存续于大脑之中,更加外显于表演仪式之中,而这些循环往复的仪式身体展演使得族群体中的人获得了连续的传说记忆[14]。虽然,在三公下水操的仪式展演中,诸多场域是以传说为主体,但这些传说都可以在当时的社会中找到“本相”,正是这些“介体”形神兼具的特性,使得叶氏族人的模仿欲望被激发并持续保持至今。这种模仿欲望不仅通过一种历史记忆来激发,更重要的是村民们在“水中犁神”环节中与自己尊崇的历史英雄形成了近距离的互动,当介体越是靠近欲望主体,欲望就越是强烈[10]。正是因为这种族群内心的模仿欲望,在仪式的过程中,现实展演场域中的人群才能更好地与英雄人物、历史事件形成相互交融,从而导演了特纳所谓的“阈限”前、中、后三个社会空间展演场域中人物心性的结构与反结构。
3 仪式过程中身体运动“模仿欲望”的结构与反结构
在泰勒、罗伯逊·史密斯、弗雷泽、赫伯特·斯宾塞、涂尔干、莫斯、列维·布留尔、休伯特、赫兹、范·杰内普、马克斯·韦伯、博厄斯、罗维、马林诺夫斯基、拉德克里夫·布朗迪特尔伦等思想家中,宗教信仰以及由此而型塑的行为,对人的身心方面都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15]。然而,这种影响力的形成与传递往往又是通过宗教仪式展演的场域得以实践达成。莫妮卡·威尔逊的研究指出,人们在这些仪式中所表达出来的,源自他们最为之感动的事物。这种仪式中所呈现出的表达是囿于传统与形式的,所以仪式所揭示的实际上是一个群体的价值[16]。马林诺夫斯基[17]和道格拉斯[18]也都积极肯定这种仪式行为对参与者身心的影响,而其中所呈现的身体运动模仿行为往往最具象征寓意。这类社会中的主要团体或社会力量正在从一种文化状态过渡到另一种文化状态。这些现象实质上是具有转换性质的现象。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众多的运动之中,相当数量的神话故事和象征手段都是从传统的过渡仪式里借用出来的,无论这些仪式是本族的文化中所包含的,还是他们亲身接触的文化中所包含的[15]。
正因为仪式在社会中的重要影响,所以诸多人类学家持续不断地对仪式进行研究。英国人类学家特纳最经典的理论之一便是通过对仪式过程的研究而得来,他的“阈限”理论是对范热内普的“分离、阈限、重合”理论的升华与推进[15],但其中的“结构与反结构”的“翻转”效应仍具有十分独到的见解,且出现在现实社会中的各个角落。升华中所出现的阈限现象并不全是以语言的形式,也可能是以象征的形式,是身体展演的象征[15]。在郭学松等人对“送王船信仰仪式”[19]、“陈靖姑信仰仪式”[6]的身体运动解构中,就曾分析了这种“结构与反结构”的“翻转”。但伴随对该方面理论的深入探讨及反复实践,课题组发现,特纳所谓的仪式“阈限”是一个很庞杂的有机体,“分离、阈限与交融”的过程其实更像一个大的“阈限”范畴,而仪式过程是“阈限”的核心部分,其实可以用“大阈限”和“小阈限”的思维来思考,从而衍生出“前阈限”、“阈限”及其“后阈限”的学术思想问题。但在不同的“阈限”仪式中,身体运动的模仿欲望诠释了主客体的行为意识,客观与主观之中的成见殊途同归,因为它们往往都植根于我们为自己的欲望所设想的形象之中[10]。为了深度了解族群人员身体运动模仿欲望的情况,在“大阈限”及“小阈限”的仪式过程中,笔者将参与身体运动模仿人员的心声融入进去,为了尊重被访者的意愿,受访者的姓名将用假托之法,又因参与人员都是叶氏族人,不可皆用“Y”替代,故借用G、F、M等代替受访者的姓名。
3.1 前阈限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所处的每一个社会职位都或多或少有一些神圣之处,而这种所谓的“神圣”成分,往往是任职者假借通过仪式的特殊性而获得。阈限有这样一种暗示,即如果没有身处低位的人,就不可能有身处高位的人[15]。这也是诸多乡土社会仪式在宗教祭祀、宗族祭祀或节庆中保持持久生命力的重要因素之一。虽然,并不是所有仪式中的参与者都会如特纳所说的发生社会地位的“翻转”,但心理效应或者“阈限”过程中的自我认同效应仍是客观呈现的,这种欲望在“前阈限”阶段就有所显露。参与者G说:“我们村里人口很多,每年参与‘水中犁神’的队伍只有6~8支,每队就固定为6个人,除了新婚、新公、升学的人必须参与之外,其他人都是要提前报名的,而且还要经过一些规定的训练,这些是在正式活动前要完成的。在准备的过程中,我们都很认真,严格按照祖辈们的做法,不能出错,怕惹‘三公爷’不高兴,也丢不起人。”
从参与者G的访谈中,我们可以发现在“前阈限”过程中,参与者就已经拥有了足够多的身心准备或者强烈的参与欲望。在平淡的生活中,他们也许是默默无闻的普通村民,如果能够参与这个具有象征性的族群仪式,成为族群仪式形象的代表,那么至少他们可以“暂时”体感到特纳所谓的社会地位的“翻转”。正因为这种参与性的意义,他们在“前阈限”的过程中就已经进入了一种状态,这也很好地诠释了他们为什么积极报名、认真学习礼仪、刻苦训练身体动作等,因为他们“丢不起这个人”。这也是这项族群仪式得以顺利开展及保持持续生命力的主要动力之一,这种认知感、责任感以及荣誉感在整个仪式的身体展演现场得以很好地呈现。
3.2 阈限中
在社会演进过程中,每个人在不同的历史情境中都会产生一种自我需要,而急迫地想使某种“需要”在日常活动之中得到满足的人,又会在仪式的阈限场域中去寻求[15]。作为族群中最为普通的一员,每个人都希望得到他人的认可,参与族群仪式也往往成为他们获得认同的一种重要方式。在三公下水操族群仪式中,受访者G和F感触颇多。G:“我是被选中的,而且经过了‘培训’。在整个‘水中犁神’过程中,我表现得也很不错。在水中,我拼尽全力,不停地晃动着‘三公爷’的神像,好像是在打架一样。看到亲人们为我加油呐喊,这么多人看着我表演,好像我成了她们的‘偶像’呢。”F:“我参与这个‘三公爷’活动已经好几年了,只是今年我结婚了,才得以参加这个‘水中犁神’表演。在水中,我与家族中的神灵距离很近,我似乎与‘三公爷’一起打仗。大家不停为我加油,本来只有三圈活动路程,我们共绕着水塘走了六圈,结果被主持喊上来了。当时累得不行,但是还有劲。”
阈限能被部分地表述为反思的阶段[20]。这种反思有思想的反思、行为的反思,还有思想通过行为而形成的反思。在这种仪式阈限场域中,社会的等级关系及矛盾逐渐得以化解,更有甚者是日常生活中的等级关系会被颠倒过来,型塑了一种反结构的状态[20]。在身体展演的“阈限”阶段,参与人员G和F从平时村落的普通一员成为被关注的对象,甚至成为众多人员的“偶像”,使他们体感到现实生活中从未获得过的一种“荣誉”。他们在族群仪式的现实场域中,身体动作的模仿使他们更加接近“介体”,参与者F即使用尽全力仍乐此不疲地将这种模仿动作重复展演,也诠释了吉拉尔所说的“距离‘介体’越近,人的模仿欲望愈强烈”。从现实的展演场域中及参与人员的体感中,似乎都可以感受到这种模仿欲望所不断呈现的“历史记忆”以及现实社会的乡土情怀。
3.3 后阈限
特纳所谓的交融是关系的一种形式,是具体性、历史性、特异性的个体之间的关系。其包括存在性交融(existential communitas)或自生的交融、规范的交融(normative communitas)和空想的交融(ideological communitas)三种形式[15]。交融以阈限的形式,进入到了结构的缝隙之处;以边缘的形式,进入到了结构的边缘之处;以地位低下的形式,进入到了结构的底层之处,并随着在社会中生活经历的发展而不断发展[15]。在三公下水操的仪式过程中,叶氏族人假借历史记忆,运用模仿的形式,创造了属于自己族群独特的身体运动文化,在循环往复的身体展演中,他们成为历史的传承者,在现实的展演场域中,他们成为历史事件中英雄人物的现实“化身”,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与身体展演的叶氏族人形成了一种交融关系。行为与决定的细微差别有着阐明性的作用,将理论与实践、存在性的交融与规范的交融之间的关系所具有的发展结构显明了出来。兰伯特指出,当自生的交融进入到社会历史之中的时候,它的运行轨迹具有了进程范式。随之而来的运动,无论是宗教运动还是世俗运动,在与这个世界进行交往的时候,都倾向于以不同的程度,来遵循圣·方济各式的生活方式[15]。
在三公下水操仪式结束后的访谈中,参与者G说到:“这个仪式我都参与了,整个过程都很热闹,仪式结束之后,晚上都不好睡觉,折腾一整晚上。在平时遇到不好的事情时,我老是想,我曾和‘三公爷’一起战斗过,他会保佑我的,于是就安心多了。”参与者F说:“我家是在外面做生意的,每年都回来参加这个家里的活动,希望‘三公爷’可以保佑我的生意兴隆,我今年刚结婚,也想早点有个孩子”。参与者M表示:“我今年考上大学了。我也是经常参加我们家乡这个活动,早期想过‘三公爷’保佑考上大学,看我今年考得还真不错,接下来我还希望他能保佑我顺利毕业并找个好工作”。虽然这些参与者的祈愿有迷信之嫌,但是可以看出,在三公下水操的仪式过程中,参与者从族群社会中的不同结构中被释放到仪式的“阈限”中,通过仪式过程的身体展演,他们体感到了与仪式的交融。后来虽然他们又重新回归到原来的社会结构中,但是这种与仪式的交融,为他们的生活注入了新的活力。通过参与者G、F、M的心境呈现,我们能够想象这种仪式所产生的社会效应,同时也在思考这种仪式中,身体模仿欲望所生产的族群心态。
4 仪式过程中身体运动“模仿欲望”中的族群心理建构
可以说,任何欲望追根溯源,都有另一个真实的抑或虚构的欲望[10]。这种模仿的欲望是一种形而上的形式体现,形而上欲望具有极强的传播性[10]。其不仅会代代相传,而且也会产生共时性社会效应。这些形而上的模仿欲望不是为了模仿而模仿,其总是会以某一历史事件为记忆原点,以英雄人物或英雄祖先为尊崇对象,并由此产生身体动作模仿,其背后往往都隐藏着不同的历史心性,这些形神相似的身体运动的模拟,勾勒出人们的历史记忆与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及群体认同[6]。在三公下水操仪式中,身体运动模仿的欲望更多的层面是通过个人及族群两个不同单元所呈现,具体为个人的自我认同与族群认同的心理建构。
珪塘叶氏族人对陆秀夫的身体运动的模仿,总是以族群的模仿欲望为逻辑起点,以个人的模仿欲望为构成部分,在仪式的深层结构中以展示自我和彰显族群为宗旨。叶氏族人对陆秀夫与敌人斗争场景的模仿,更多的是彰显其族人与达官贵人同袍作战的历史记忆,以显示族群之优越。在仪式过程中,他们的社会空间发生了变化,从一个普通的民众上升到被族人敬仰的“英雄”,促使参演者获得了极大的自我认同感。在历史场景的现实展演中,他们成为村里集体的公众形象代表,激发着模仿欲望不断迸发,从这种交融的展演中产生的模仿欲望,使他们的身体运动的模拟更具“工具性”,不仅成为一种难忘的记忆,更深刻地影响着未来的生活,这一切都是源自于对自我身体运动模仿的个体认同。这种个体的自我认同是一种小范围的,甚至是主要对内的,总是以族群体为依托,特别是在区别“我族”和“他族”的过程中。
文化与族群身份的攀附欲望,产生于攀附者与被攀附者间被创造、想象或建构的社会与文化差距之中,借此造成“我群”与“异己”间的“区分”[21]。这类似于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所称的,在社会阶级人群间以定义、夸耀与操弄“品味”,以造成社会区分(distinction)的策略[22]。在三公下水操族群仪式活动中,参与群体与介体愈接近,与形而上欲望相关联的现象就愈具群体性。在欲望的最高阶段,群体性质尤其显著[10]。其实这种欲望的最强烈的表达就是在“小阈限”阶段的身体模仿展演部分。叶氏族群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将这种身体运动延续500余年,其目的不仅是一种文化的保存与传递,更多的是族群优越性的彰显,以建构一种族群心理,从而区别“我族”与“他族”。通过实现族人的族群认同意识,加强族群向心力,形成团体,争夺社会生存空间及社会生产资源。叶氏族人为了实现最终的社会目的,他们必须寻找一个可以凝聚族群仪式的“介体”,具有重要历史影响的人物、事件便自然而然地与族群先祖建立了关系,因祖先尊崇或历史人物崇拜而建构的“三公下水操”仪式活动在叶氏族群中被展示出来。他们不断扩大仪式展演的影响力,夸张身体运动模仿的程度,形成一种巨大的张力,在展示“我族”之优越性的过程中,也在不断地重新建构或强化一种族群心理,从而趋向于适应社会的发展,为了生存或者更好地生存,因为“竞争、夸耀”与“摹仿、附和”仍是此社会过程的主要动力[21]。
5 结语
伴随乡土仪式而生的身体运动总是与模仿、象征、认同等文化因素交融在一起。三公下水操仪式活动中的身体运动是以历史事件为依托,以历史人物为介体,通过对某一时刻介体的身体动作的高度模仿来诠释不同历史时期的族群心理动态。从吉拉尔“模仿欲望”理论出发,走进乡土仪式的现实展演场域,我们发现身体运动更多是以一种模仿的表象而存在,这种身体运动之所以被族群体生产出来,是因为其能够满足族群体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需求。通过对仪式过程中“大阈限”及“小阈限”中参与者的口述分析,展示了不同参与对象在不同“阈限”范畴中的身体“模仿欲望”,从而阐释了族群心理如何在“自我认同”与“族群认同”的相互作用中被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