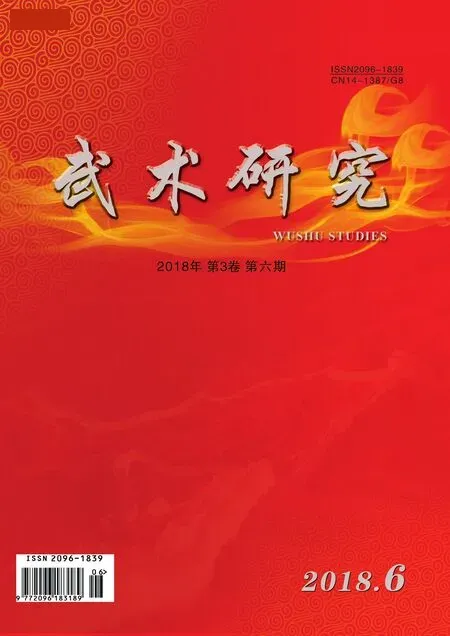吴越剑器起源探析
2018-11-25郑将栋
郑将栋
浙江旅游与健康职业学院,浙江 舟山 316100
剑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从简单到复杂,从萌生到壮大,成为社会文化现象,都与我国社会的发展紧密相联。剑器在武术器械中占有重要地位,一直以来被称为“短兵之祖”,是起源最早的兵器之一。江南铸剑术一直代表着我国最高的铸剑水平,其水网交错的地貌,使得剑在这一地区有着独特的历史地位、文化内涵和发展轨迹。
1 新石器时期剑的产生
剑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源远流长,最早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在出土实物中,有用细长的石薄片嵌入兽骨两侧的“石刃骨剑。”[1]在山东出土有龙山文化时期的青石剑,形制与匕首相似,有剑柄、剑脊、锋刃,长约200毫米,宽约30毫米。”[2]这是剑最初的雏形,显然石质剑和骨质剑的发明,仅是为了当时的生产和生活,以方便古人狩猎、切割食物,与恶劣的自然环境相斗争,剑最初扮演着生活工具的角色。
新石器时期,还没有国家的出现,人类社会不断地向前进化,部族的概念日益明显,古人开始研制兵器以便于在战争中取得优势。随着部落之间不断吞并,逐渐形成了黄帝和蚩尤两个大部落,据《史记·黄帝本纪》记载:“帝采首山之铜铸剑,以天文古字铭之”,[3]又据《管子·地数篇》记载“:昔葛天卢之山发而出金,蚩尤受而制之,以为剑、铠……”,[4]由此可以推知,黄帝与蚩尤作战时代,均已开始制剑为兵,最终黄帝在战争中取得了胜利,此时剑已经逐渐由生活工具转向技击的武器。
2 夏商时期青铜剑的应用
经历了尧、舜的统治,禹执政后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封建王朝夏朝,“家天下取代了公天下”。夏朝至春秋战国是我国历史上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时期。我国的铜器时代始于夏,1959年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出土了大量四千多年前夏朝的青铜器。我国最早出土的青铜器始于夏朝,夏朝已经具备了铸造青铜剑的条件,但现今没有实物出土。现藏于南京博物馆,江苏邳县大墩子遗址出土的一柄玉石质地的商代短剑,剑长 210毫米,剑刃锋利,制作精美,可用于自卫防身。用剑作为陪葬品的情况在我国先秦时代南方墓葬中屡见不鲜,正是因为古代江南地区人们对剑器的喜爱,使得一部分青铜剑在黄土中保存下来;2014年江苏高邮市发现商周时代的青铜古剑,剑的构造分为剑身和剑茎两个部分,长26厘米,造型精致,顶端有小孔,可以用做装饰和自卫防身。商周距今3000多年,也是青铜剑的发源,受当时铸造工艺的限制,此时期的剑长度相对较短,相当于现代的匕首。
陶弘景的《古今刀剑录》记载:“夏禹子帝启,在位十年,以庚戌八年铸一铜剑……。”青铜剑实物的出土,年代都在西周以后,青铜器的应用无法准确地追溯其时间,但目前可以断定在西周时期,古人已经熟练掌握了青铜铸剑技术。青铜器的发明和冶炼技术的提高,使剑的击刺功能得到了很大的发挥,成为战争中的常规武器。《史记·周本纪》记载:“乃克射之,三发而后下车,而击之以轻剑……散宜生、太颠、夭皆执剑以卫武王。”由此可见,在西周时期剑已经装备于军队之中。
3 吴越剑器蓬勃发展
3.1 江南剑器发展的社会条件
由于殷周实行奴隶制严重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直到春秋战国时期,封建制替代奴隶制的社会大变革,治铁技术得以快速发展,为剑的繁荣普及奠定了技术基础,春秋晚期周王朝实力衰落,诸侯争霸,各诸侯之间为了扩大势力展开军备竞赛。当时在中原地区,主要以车战为主,士兵多使用戈、戟、矛、受等长兵器,强的诸侯国有千乘之国的美誉,此时剑通常作为长兵器之下的辅助武器。《左传·姜子春秋》中有过记述,在车战中,都是用戈作为直接对攻的武器,用戈将敌方勾下战车以后,再用剑进行击杀,称“戈拘其颈,剑承其胸”。而吴、越两国因为境内山川河流交错纵横,多以水战为主,剑成为主要的直接对攻武器。据《考工记》记载:“吴粤之剑,迁乎其地而弗能为良,地气然也。”[5]也说明了吴越地域内有丰富的资源,是铸剑的绝佳之所。加之优异的制剑传统工艺,使吴越宝剑流传千古。在《淮南子》称赞:“夫宋画吴冶……尧、舜之圣不能及”。[6]所以吴越的铸剑技术和击剑理论都要领先于中原各国。
历史上吴越名剑辈出,在《越绝书·外传记宝剑》中就记载了,吴越铸剑师欧冶子、干将的铸剑事迹,及龙渊、泰阿、工布等吴越名剑。在《史记》《拾遗记》《吴越春秋》中均对吴越名剑有相关介绍,早期吴越的好剑之风,对后来剑在华夏大的发展、普及起到了推动作用。
3.2 出土吴越古剑拾雲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战争的需要,剑成为近身格斗的主要兵器,随着铸剑技术的发展,此时剑的长度也得以增加。改革开放后,我国陆续出土先秦古剑,其中最耀眼瞩目的是1965年出土的越王勾践剑。越王勾践剑是在楚国墓葬中发现,剑长557毫米,宽46毫米,柄长84毫米,重875克。有中脊,两从刃锋利,前锋曲弧内凹,剑身经过硫化处理,增加血槽,提高了兵器的杀伤力。虽然在地下掩埋两千多年,依然锋利无比。在出土时曾一剑划破百张宣纸,惊艳一时。后曾在海内外展出,代表了中国古代高超的铸造工艺。与越王勾践剑一起出土的还有一柄宝剑,形制和铸造工艺与勾践剑相似,剑上镶嵌有蓝色琉璃及绿宝石,至今保存完好,经鉴定属于战国时期的吴越宝剑;
与越王勾践剑同时期的还有吴王剑,吴王剑剑身宽阔,剑首向外翻卷作圆饼形,内为空心。剑身铸有10个字的铭文:“攻敔王者彶虐自乍用。”越王勾践剑和吴王剑距今2500多年,仍然保持锋利,光洁如新;我国至今一共发现了九柄越王州句剑,其中有一柄用复合金属技术铸造。剑体上都铸有“越王州句自作用剑”的文字。州句是勾践之孙,在越国消灭吴国后,越国实力大增,向北与中原各国争霸。根据州句剑出土的数量和铸造技术判断,很有可能越王州句曾命人成批量的铸造刻有自己名字的剑器。
越国最后被楚国所灭,楚国吸收了吴越的铸剑技术和重剑的风气,在许多的楚国墓葬中,都用剑器作为陪葬品。现收藏于洛阳龙门博物馆的楚国青铜剑,斜从厚格式,附剑鞘,剑身宽长厚重,剑身布满菱形纹饰,造型优美,整个剑身采用曲线设计,由剑柄处向前逐渐变窄。更加值得一提的是剑鞘至今保存完整,由两块薄木片粘合而成,并在鞘外等距离缠缚丝线,外面涂有黑漆,这是研究春秋时期剑鞘珍贵的标本。
1976年,长沙长杨六十五号墓出土一柄春秋晚期的铁质钢剑,也是我国考古发现的第一柄铁质剑。因在长杨出土命名为长杨剑,长杨剑属于短剑,剑长384毫米,茎长78毫米、身长306毫米。[7]虽然在形质上与青铜剑相似,但铸造工艺方面是一个巨大的跨越,说明我国在春秋晚期就已经掌握了冶铁技术。
在历史的长河中,很多史书上记载的吴越宝剑已经消逝踪迹,但随着考古工作的推进和研究技术的不断发展,相信能够逐渐了解古人的智慧。先秦时期铸剑工艺高超,剑注重战场击杀,锋利无比,而且在剑身纹饰造型上各有风格,是上层人士的重要配饰。这一时期出现了名剑众多,如“越王八剑”“定光剑”“干将”“莫邪”等,也由此出现了很多铸剑、相剑、剑术的故事。如“庄子说剑”“越女论剑”等。《庄子》外篇中关于古人对宝剑的喜爱有这样的描述:“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宝之志也。”[8]此时也出现了一批铸剑名师,干将、莫邪、欧冶子等吴越工匠,都被奉为铸剑师祖。
现出土的先秦古剑,大多在历史的变迁中锈迹斑斑,但仍旧闪烁着古人的智慧,闪烁着江南剑文化的历史和辉煌。不仅是研究标本,更是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加强对出土先秦古剑的研究,能够更好地去挖掘古人的冶炼技术,对研究武术文化具有积极作用。
4 剑的社会转型
战国时代,战车衰落,步兵兴起,剑在战争中的作用更加得以发挥,成为当时战斗士兵的标准装备。在剑的材质方面,春秋战国时代虽然有铁质钢剑的出现,但由于冶炼技术的限制,在军队配备中仍然以青铜剑为主。《武备志》中记载:“古之言兵者必言剑”[9],充分说明了剑在中国军事历史上的重要地位。随着冶炼技术的发展,至汉代在铸造工艺上铁质剑取代了青铜剑,剑的长度得以增加,提高了攻击能力。
自汉王朝自建立以来,长期遭受北匈奴的困扰,在经历文景之治后,汉武帝时期大力发展骑兵,以增强对匈奴的作战能力,虽然在战场上剑逐渐被利于砍劈的刀取代,但在民间却以蓬勃之势的进一步发展。
剑在江南地区的发展有着长期的基础,早在春秋时间吴越人民重剑轻死,有着高超的铸剑技术和完备的击剑理论。剑退出战争舞台后,剑却因为其悠久的历史和精美的形制,在宫廷和民间广为流传。在传承过程中,剑文化的范畴不断扩大,为社会各阶层所追捧。剑被君王赋予权力的象征,被文人墨客赋予文化的色彩,被一些艺术家当成抒情明志的工具。剑在宫廷、诗词等多个领域中都有体现,《史记·太史公自序》载:“非信廉仁勇不能传兵论剑,与道同符,内可以治身,外可以应变,君子比德焉。”[10]可以说明,当时的剑文化已经发展到一种精神层面,被当时的人们所追捧。
江南自古以来就是人杰地灵,名剑辈出之地。顺沿着历史的脉络,江南剑器在我国兵器史中的地位无出其右。与之承载的剑文化,有独具特色的文化气息和十分丰富的内涵,在几千年的发展中,剑文化传承有序、不断演变,早已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阶层之中,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念。
5 结语
通过剑发展的历史背景,可以认为剑最初是作为生活工具之雏形,为什么的生活服务;慢慢演变为部落、国家之间斗争的武器,为兼并战争成为击杀的工具;退出战场以后,剑自身悠久的文化、精致的造型、便于携带等特点,使剑在社会的各个领域深受追捧。并与书画、舞蹈、文化相结合,不断扩大文化内涵,满足了人们的精神需求。
春秋战国时期战争频发,吴越因其水陆相间的地理特征,剑成为船上直接对攻的武器,凸显了吴越地区剑的军事地位。丰富的矿产资源、精湛的铸剑技术,为大量铸造剑器奠定了基础。加之剑器造型优美,便于携带等因素,促进了剑在民间的传播。由此形成吴越好剑之风盛行,其民多“重剑轻死”。系统而又成熟的剑术技击理论应运而生,拉开了江南剑文化蓬勃发展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