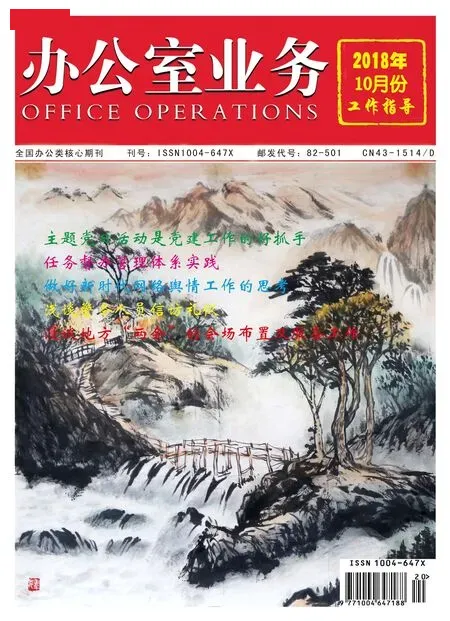从“丕植争储”结局的必然性审视秘书的导向作用
2018-11-24黑龙江工业学院韩涛赵欣健刘金铎
文/黑龙江工业学院 韩涛 赵欣健 刘金铎
曹操作为东汉末年一位出色的政治家、军事家、诗人,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曹操在汉末群雄并起、风云际会的大时代中,“挟天子以令诸侯”,充分施展政治手腕而统一北方,为后来西晋重新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诚然诸葛亮所说“曹操占天时”(《隆中对》)的因素,但天时是上天赋予的,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机缘,而曹操的高明之处在于“用天时”,把“天时”用到了极致。正所谓“大奸必有大智”,不得不承认曹操是一代谋略大师,对手下各色人或打压、或重用、或猜忌,都体现出一代枭雄的政治智慧,也正应了诸葛亮所说“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隆中对》)自然,曹操对自己继承人的选择,也充分体现出了曹操的智慧所在。正所谓“知子莫若父”,曹操对自己继承人的选择经历了一个艰难的抉择过程,在选择继承人的过程中,曹操不仅仅只局限于观察两位候选人的曹丕与曹植,也同时在观察两个儿子身边之人,而后来的事实证明曹操的确目光如炬。我们从曹丕与曹植争储的结局中,可以明显看出两位公子身边“秘书”的眼界、智慧、行为等各个方面的高低优劣。可以说,正是因为曹丕与曹植这些身边“秘书”导向作用的差异,为后来两位公子争储结局的必然性产生了决定作用,同时,身边“秘书”也对曹丕与曹植在性格、心智、为人处世等各方面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我们分别通过陈寿《三国志》中的相关记载,就可以看出,曹丕与曹植身边“秘书”对二人政治智慧、行为方式所产生的影响:
《三国志·魏志·陈思王植传》记载:“陈思王植字子建。年十岁余,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善属文。太祖尝视其文,谓植曰:“汝倩人邪?”植跪曰:“言出为论,下笔成章,顾当面试,奈何倩人?”时邺铜爵台新城,太祖悉将诸子登台,使各为赋。植援笔立成,可观,太祖甚异之。性简易,不治威仪。舆马服饰,不尚华丽。每进见难问,应声而对,特见宠爱。建安十六年,封平原侯。十九年,徙封临淄侯。”
从以上选文可以看出,曹植是一个聪颖早慧、天纵奇才的少年文豪,后世以“才高八斗”形容其诗才是当之无愧的。也正是因为其出色的文学造诣,深受同样是文学家的父亲曹操的喜爱。同时,在与杨修、丁仪、丁廙等人交游之前,曹植“性简易,不治威仪。舆马服饰,不尚华丽”的低调作风,也深得当时因“挟天子令诸侯”而被世人称作“汉贼”的曹操赞许,从“特见宠爱”四字可见一斑,而“建安十六年,封平原侯。十九年,徙封临淄侯”,则将曹操的宠爱推向了顶峰。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曹植时年20岁,“封平原侯”;而当时年长曹植5岁的兄长曹丕为五官中郎将、副丞相;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曹植时年23岁,“徙封临淄侯”。其时,曹操尚未晋位魏王(曹操于建安二十一年,即公元216年晋位魏王),而据《三国志·魏志·文帝纪》载曹丕“二十二年,立为魏太子。太祖崩,嗣位为丞相、魏王”。因此,我们可以据此判断,从建安十六年至建安二十二年,这六年间,曹丕与曹植在继承人问题上,应该是并驾齐驱、你追我赶的,起码在曹操心中还没有最终拍板谁为王世子,在《三国志》相关记载中,我们可以找到两条证据可以证明:
《三国志·魏志·文帝纪》:魏略曰:“太祖不时立太子,太子自疑。”
《三国志·魏志·贾诩传》:是时,文帝为五官将,而临淄侯植才名方盛,各有党羽,有夺宗之议。文帝使人问诩自固之术,诩曰:“原将军恢崇德度,躬素士之业,朝夕孜孜,不违子道。如此而已。”文帝从之,深自砥砺。太祖又尝屏除左右问诩,诩嘿然不对。太祖曰:“与卿言而不答,何也?”诩曰:“属适有所思,故不即对耳。”太祖曰:“何思?”诩曰:“思袁本初、刘景升父子也。”太祖大笑,于是太子遂定。
从曹操“不时立太子”的行为和贾诩“思袁本初、刘景升父子也”的表述,可以看出,曹操对曹丕与曹植的继承人问题长期以来是十分挣扎的,而最终确定继承人为曹丕,当然不会如史书记载中所说“太祖大笑,于是太子遂定”那么简单,仅凭“外人”贾诩的一句话,就把关系到家族命运大事的“立储”武断地做出决定,显然不是政坛老手曹操的处事风格。
可出人意料的事情最终还是发生了。就在曹操晋位魏王的第二年(公元217年),曹丕被立为王世子,并于三年后(公元220年)废汉自立为皇帝。根据上述相关史料记载,从建安十九年至建安二十二年,短短三年中,曹丕与曹植的命运发生了急剧变化,曹丕成功实现“逆袭”,最终战胜了曹植,成为曹操王位的继承人。显而易见,这并非曹操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经过三年甚至更长时间对两人(甚至包括他们身边之人)的仔细观察和比较,经过深思熟虑后做出的决定。那么在这三年中,曹丕与曹植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曹操下定决心确立曹丕为王世子?曹操临终前对曹植的评价“为人虚华少诚实,嗜酒放纵”(《三国演义》第七十八回)是否符合史实?曾经被曹操“平生所爱第三子植”究竟哪些行为让曹操放弃了他?我们还是需要从历史事实中找到答案。
首先确定最初曹操看重曹植,而非曹丕,这是“丕植争储”的前提。按照古代嫡长继承制度,曹丕继承曹操的丞相位和魏王位是顺理成章的。如果曹操从来没有器重过曹植,那“丕植争储”的命题便没有讨论的价值。我们从《三国志》中能否找到蛛丝马迹呢?答案是肯定的。
《三国志·魏志·丁廙传》中记载:“……植,吾爱之,安能若卿言!吾欲立之为嗣,何如?……太祖深纳之。”
《三国志·魏志·陈思王植传》中“……植援笔立成,可观,太祖甚异之。”“每进见难问,应声而对,特见宠爱。”
《三国志·魏志·任城王彰传》:魏略曰,彰至,谓临淄侯植曰:“先王召我者,欲立汝也。”
《三国志·魏志·丁仪传》中“太祖既有意欲立植……”
《三国演义》第七十八回:“孤平生所爱第三子植,为人虚华少诚实,嗜酒放纵,因此不立。”
兴趣是数学创造的重要动力之一,兴趣是力求探索,获得数学创造的带有情绪色彩的意向活动。学生对数学的迷恋往往是从兴趣开始的,由兴趣产生动机,由动机到探索,由探索到成功,在成功的快感中产生新的兴趣和动机,推动学习的不断成功。
《三国演义》第七十九回:丁仪骂曰:“昔者先王本欲立吾主为世子……”
从陈寿《三国志》与罗贯中《三国演义》相互对照分析,从曹操、曹彰、丁仪等人的表述中可以看出,最初曹操对曹植的器重是显而易见的,而从曹操所言“吾欲立之为嗣”可以证明曹操最初欲立曹植为继承人是有充分依据的,即便在曹操临终时依然说曹植为自己平生所爱,而“因此不立”一语,则从侧面证实了曹操曾经是想立曹植为继承人的。
如果说丁仪、丁廙兄弟身为曹植门客,为自己今后的事业发展计,绞尽脑汁地在曹操面前说自己主子好话在情理之中,而不能作为曹操器重曹植依据的话,那么,作为竞争对手的兄长曹丕的一些行为则足以证明,曹操对曹植的偏爱已为曹丕所惧与所忌。
《三国志·魏志·陈思王植传》“世语曰:修年二十五,以名公子有才能,为太祖所器,与丁仪兄弟,皆欲以植为嗣。太子患之,以车载废簏,内潮歌长吴质与谋。……太子惧,告质……”
从太子(指曹丕)的“患”与“惧”明显可以看出曹丕已经感受到了曹植的威胁,曾在袁绍与刘表那里发生过的“废长立幼”之事将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因此,他不惜甘冒其险“以车载废簏,内潮歌长吴质与谋”。此外,曹丕身边的重要谋士,后成为曹魏司徒的华歆在对曹丕讲“子建怀才抱智,终非池中物。若不早除,必为后患”(《三国演义》第七十九回),于是有了后来“七步成诗”,也有了曹植一生贬谪数地的后话。
“丕植争储”结局的必然性分析。“丕植争储”最终以曹丕胜利、曹植失败而告终。究竟哪些因素导致了曹植的失败?曹丕通过哪些方式实现了“逆袭”?通过《三国志》等相关史料的整理与分析,我们认为除了曹丕与曹植的性格以外,两人身边“秘书”人员对其政治智慧、行为方式等方面的形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曹丕的成功、曹植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是由两人身边“秘书”人员所导致的。
一个人的性格决定了他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也决定了他所能承担的责任。若单论继承人这一点来说,曹植无疑是失败者,而且败得一塌糊涂,但从后人评价其“才高八斗”来说,曹植无疑又是文学方面的成功者;而曹丕最终成为魏文帝,自然是政治的成功者。对于两位“成功者”与“失败者”来说,两人的性格决定了自己的命运。我们从针对同一事例的比较中,就可以看出曹丕与曹植性格的不同。
《三国志·魏志·陈思王植传》:“……植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文帝御之以术,矫情自饰,宫人左右,并为之说,故遂定为嗣。”
《三国志·魏志·陈思王植传》“……太子患之,以车载废簏,内潮歌长吴质与谋。修以白太祖,未及推验。……世子从之,修果白,而无人,太祖由是疑焉。”
在未经查验、不明就里的情况下,杨修就武断地“以白太祖”,想通过私会大臣的罪名置曹丕于死地,但弄巧成拙,不但其构陷之术被吴质轻松识破并化解,而且反咬杨修一口,最终祸及曹植。从杨修与吴质的这一次斗法,可以明显看到杨修的意气用事与吴质的胸有城府,于是“太祖由是疑焉”便顺理成章了,曹操对曹植的不信任也就正常不过了。
杨修等人政治智慧的不成熟,直接影响到曹植行为方式的不成熟。可以说,曹植身边的“秘书”多为狂士,书生气十足,缺乏足够的政治谋略与智慧。同时,杨修等人犯了下属的大忌:“忖度太祖意”,而最终杨修“至二十四年秋,公以脩前后漏泄言教,交关诸侯,乃收杀之。”杨修等人的这种书生气的大忌自然影响了曹植的政治选择,在与曹丕争储中多表现出的意气用事给曹操留下了不良印象。杨修之死其实不过是替曹植受过,同时也是曹操最终放弃曹植的直接表现。
杨修等“秘书”的导向作用对曹植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而他们在犯错之后,并没有及时地去弥补,没有及时对曹植的行为做出规劝与调整,致使曹植在错误的道路上越陷越深。例如:
《三国志·魏志·陈思王植传》:“……二十二年,增置邑五千,并前万户。植尝乘车行驰道中,开司马门出。太祖大怒,公车令坐死。由是重诸侯科禁,而植宠日衰。太祖既虑终始之变,以杨修颇有才策,而又袁氏之甥也,于是以罪诛修。植益内不自安。二十四年,曹仁为关羽所围。太祖以植为南中郎将,行征虏将军。欲遣救仁,呼有所敕戒。植醉不能受命,于是悔而罢之。”
《三国志·魏志·陈思王植传》:典略曰:……植后以骄纵见疏,而植故连缀修不止,修亦不敢自绝。至二十四年秋,公以修前后漏泄言教,交关诸侯,乃收杀之。
《三国志·魏志·陈思王植传》:世语曰:……修与贾逵、王凌并为主簿,而为植所友。每当就植,虑事有阙,忖度太祖意,预作答教十余条,敕门下,教出以次答。教裁出,答已入,太祖怪其捷,推问始泄。太祖遣太子及圆各出邺城一门,密敕门不得出,以观其所为。太子至门,不得出而还。修先戒植:“若门不出侯,侯受王命,可斩守者。”植从之。故修遂以交构赐死。
从以上四则史实可以看出,杨修等人作为曹植身边的智囊,没有充分发挥自己的参谋功能,没有为曹植提供正确的思维导向和行为导向,而在屡次吃亏之后,也没有充分吸取经验教训,未能采取适当措施对曹植的不成熟行为加以引导和劝诫,导致曹植政治不成熟的程度日益加深。“司马门事件”充分体现了这一点,此事一出,曹操大怒,导致“植宠日衰”。此时正是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即曹丕被立为王世子之年,也许正是“司马门事件”为“丕植争储”的结局画上了句号。
通过《三国志》与《三国演义》有关“丕植争储”的记叙和描写,我们可以看到,这场争储结局是必然的,除曹植“虚华少诚实,嗜酒放纵”的性格以外,以杨修、丁氏兄弟、贾逵、王凌等人为代表的“秘书智囊团”对曹植性格的发展、思维方式、行动方式等方面的形成有十分严重的导向错误。他们没有审时度势地发挥自身应该具备的观察、分析、参谋、辅助决策的秘书职能,没有为曹植在这场争储大戏中提供正确的路线和策略,因此,曹植在与曹丕的争储斗争中的结局是注定失败的。我们通过对比杨修等人与贾诩、吴质等人的导向作用与参谋智慧,更加深刻地证明了这一点。历史就是一面镜子,今天我们分析“丕植争储”结局的必然性,其实是以古证今,为今天的秘书人员提供借鉴的范本,使秘书人员能够更好地发挥参谋咨询、辅助决策的正确导向作用。